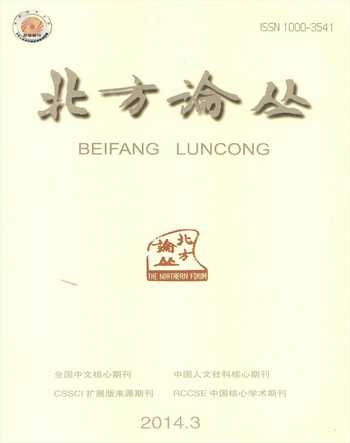资本积累的空间表达
刘爱文
[摘要]进入人类视域的空间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它总是反映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空间表象是特殊社会组织形式的映射。作为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资本积累体制,其背面也体现为相应的空间形态,从而为该资本积累体制有效运作提供空间支撑。一般意义,空间与社会之间是同构的,体现为社会建构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积累体制包含了不同的关系范畴;借助关系范畴,资本积累体制与空间之间所共享的映射元素得以凸显。
[关键词]资本积累;空间表达;关系向度;空间意指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3-0131-06
Abstract: As Emile Durkheim says,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is mapping of special social organization form. As aspecific social organization form, there are the space order as its support behind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system accordingly, and this is the so-called the spatial metaphor of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system. 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intrinsic haunts between the space and social relation, and reveals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space is social construction, then analyzes how many relation dimension are included in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system, finally the paper take apart allusive element between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system and spatial metaphor, namely spatial signification of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system.
Key words:capital accumulation; spatial metaphor; relation dimension; spatial signification
一、空间的社会建构
空间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空间无处不在,“从物理学到美学、从神话巫术到普通的日常生活,空间连同时间一起共同地把一个基本的构序系统揳入到人类思想的方方面面。”[1](p.5)然而,在架构人类思想的历史进程中,相对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向来是被冷落的,“空间维度是不重要的”这种观念已普遍渗入到思想界的潜意识中,如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马歇尔就认为,“空间的利益服从于时间的利益。”[2](p.496)与此相印证,在经济学逻辑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假定:要么所有的经济事实发生在某一个无体积无形状的理想化质点上,要么那些经济活动在两个不同地方转移不存在任何交通成本。在这些假定里,我们何曾看到半点空间叙事的影子,空间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荡然无存。
直觉上,“物体”术语更具空间内涵,但更体现时间性的“事件”术语应用更广更普遍,事件叙事更能得到思想界的认同;事实上,事件与物(体)这两个范畴是相互纠葛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物被定义为一个事件、事实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它的出现就意味着其发生、成长及消失的过程,其存在就涉及从空间广延性上对其进行测度,因此,物的存在以及变化必然牵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事实上,空间与实体是二位一体,两者须臾不可分离,但是,当人们把空间作为一个对象来分析、讨论时,又必须从概念上把二者分隔开来,这也就是说,空间作为一个思想模式的子范畴或者楔子,作为概念体系,同样遵循“物象二重性”的原则,二者从概念上必须有所区隔。所以,我们谈论空间系统时,实际上就是指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体系,它涉及空间与实体二者分离的概念距离,使得从实体到空间会形成不同的抽象层次。事实上,“人们是从理论物理学、哲学以及地表等这些不同的层次上来谈论空间的,况且地理空间本身并不是空无一物的,它被各种各样的物质、能量或者实物所充盈。”[1](p.5)
因此,空间并非不重要。空间与物相互缠结,每一个思想领域都嵌入了特定的空间概念,这导致空间成为一个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单独将其分离出来分析的概念。思想模式不同导致空间概念生成的路径也存在差异;由于物象二重性的存在,空间与实体由此相互揖别。然而,思想模式的阐释功能又需要将相互分离的空间概念相互拼接起来,这就凸显了特定空间概念本身的所指或意义所在的重要性,相互分离的空间概念就需要按照实体到空间的映射法则重新关联起来,其实质就是通过从实体中抽象出的空间概念的关系予以确定,正是关系这个范畴,将空间与物质从概念上内在地串接起来,“包含空间术语的重要物质参照系的正是社会科学中的空间关系概念”[1](p.69),对于所有空间关系,都可以通过“一致性和邻接性”[1](p.74)这两个最一般的空间关系的表达形式来阐释。
然而,资本主义空间广化和空间深化过程极大地冲击着人们先前的空间观念。首先,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开启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帷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凭借其喷薄而出的旺盛生命力开始其征服全球的历史过程,世界历史也由先前的地理上分散的各自独立发展,强行纳入相互依赖的统一发展,资本主义空间开始不断地向外围拓展。其次,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现代科技文明的狂飙突进,进一步夯实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如此高度,正如人类玩魔方一般,在资本的支配下,资本主义世界中地理景观有如万花筒一般变幻万千,它们不断被摧毁和重构,资本主义空间成了资本的工具、玩物,形式越来越精致,其可塑性和实用性也随之增强。
上述资本主义空间广化和空间深化的过程所诱致的碎片化、差异化的空间重塑过程,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撕裂了之前人们基于自身体验的朴素的空间观念;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的兴起,空间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倾向更加流行,人们试图从现象经验上直接推导出空间的客观规律,大量数学公式、统计资料充斥于空间研究前沿学术领域中,通过对空间经济数据进行拟合的数学建模的空间研究范式,被大量应用于对于空间格局合理性研究中,空间理论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脱离地方性和稳固性,并造成一种困惑或假象,只见空间不见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3](p.426)空间虚幻表示为一些空间要素符号,如形状、模块等,在各种最优原则的支配下,经由各种函数和规划型构而成的一个体系,空间的这种致用性引起了资本主义空间研究者的膜拜,他们开始关注诸如形状或距离等外在的空间表现形式,空间研究的目的就是探求纯粹的空间机制和空间规律,诸如中心场所理论、土地利用理论、重力模型理论等就是用来研究经济景观的空间分布。这种对于精美的空间几何法则的苛求,导致在空间学术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空间拜物教倾向。
经济景观的空间演变与空间分布只能是社会过程的结果。纯粹的空间机制或空间规律是根本不存在的,也不存在纯粹的空间过程,经济景观的空间演变和空间分布不可能是纯粹空间过程的结果所造成的。事实上,事物的空间性和社会关系性是相互建构的,也即“空间—社会关系”的同构性。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同构性的意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二者的同构性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绝对空间的概念,也就是说,空间并不是先验存在的;其次,这种同构性也意味着各类社会现象之间的拓扑关系型构着空间,形成不同类型的空间,意味着社会关系是空间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基于此,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同构性也体现在二者的辩证关系上,社会中的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形成的各类关系创造各种差异空间,反过来,这些差异空间又会影响这些关系的结构化的状况,这表明,空间既是由社会关系建构的,反过来,社会过程又是在空间中建构的。经济景观能够被建构为社会关系,根源在于这些差异景观对象背后所依存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则形成拓扑网络,将这些差异景观对象纳入这些拓扑网络之内或排斥在这些网络之外。所以,空间只能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过程的结果,而社会过程又必须在特定的空间中发生或进行。
我们可以把空间的本质看作是一种社会经济生活中“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体系建构,其特征在于社会关系的展开、相互交切和接合,这样一个概念一开始就将社会与空间整合在一起;而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必定会涉及行动者,也即各类主体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所以,空间很自然地就把社会权力囊括进来了。我们从空间组织背后所折射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充盈了权力支配为特征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解释经济景观的分布,较之于那种仅把空间视为绝对的、原子化的、纯粹的空间的分布,具有更为合理的意义。
当社会关系面临全面重新调整的时候,那么这也意味着它所建构的经济空间(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形式)重新布局。新的空间布局不仅仅是把同样一副扑克牌在地理上的一种重新组合,实际上,它们反映了不同场所的经济活动之间的一系列全新的关系、社会组织的新的空间形式、不平等的新维度和新的支配与依附关系。每一次新的空间布局都代表着一种真实而又全面的空间结构化过程,当然,它也带来了新形式的地区问题,但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新空间的创造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社会关系的空间中的一种新的重组。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空间是极其复杂的,涉及空间的多重性和空间的差异性等方面,所以,如何从社会关系方面尤其是资本积累方面来对空间进行正确解读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资本积累的关系向度
社会关系是事物之间所有关系中最为特殊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关系的主体特殊性,社会关系的主体主是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组织,这就使社会关系区别于其他关系。社会关系的涵义就是,两个主体之间所发生的一种社会交往的过程,这里将关系界定为一种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的存在意义非常重要。在社会实践中,人不仅要和自然界,而且要和其他主体发生各种关系,前者是生产力研究的范畴,后者则是生产关系研究的范畴。这些关系由于人的参与,都具有自觉意识以及社会历史的规定性。按照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只是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就是资本的真正积累。积累就是资本在一定点上把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聚集在一起。”[4](p.511)资本积累过程涉及到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诸多活动环节,它借助资本再生产过程来实现,后者要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诸关系不断再生产出来。作为资本积累依托的社会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特定的资本积累体制反映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为更具体地剖析资本主义积累范畴,我们借用一个拓扑学术语——关系向度——对资本主义积累体制进行剖析。关系向度亦称为关系基础,它是指两个经济主体所共享的某些属性,它具有指向性或同向度。关系向度是一种被动的客观存在,这区别于作为一种主动的、动态过程的关系,关系由关系向度来结构。我们把它借用到资本积累体制语境中,主要是就其构成社会空间的基本要素而言,即研究型构资本积累体制的基本组成部分有哪些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指向性。资本积累体制的关系向度主要是指,在资本积累过程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分析其参与主体相互关系的社会规定性,以此来解释和界定资本积累的模式,并且认为这些社会关系的规定性构成了资本积累体制的主要内容和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5](p.542)
生产关系:资本积累第一个指涉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一直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将资本概念泛化,超脱于历史,将资本等同于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物资资料,甚至将原始人的石头也称之为资本。实质上,资本是个历史形成的经济范畴,与这些庸俗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认为:“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6](p622),因此,应该将资本看做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个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就是针对资产主义社会而言的,针对资产阶级而言的。因为作为资本载体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等,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积累的;这些资本载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不断进行的。事实上,正是这种特定的社会性质完成了社会产品由人类社会的一般的产品到资本的转变。由此可知,“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5](p.168)作为资本积累最核心的关系,生产关系必然会孕育出其他一些统治和从属关系,主要体现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相应地也使劳动过程也具有统治和从属关系的性质,而这些统治和从属关系都会外化为资本日常生产实践中的政治特权表现。因此,尽管社会生活中关系错综复杂,但并不是无序的,它们彼此联系并且受制于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关系的整体构成了一个社会运行的基础,并且社会的性质也由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来确定。
分配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7](p.999)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总是将分配与生产割裂开来,认为生产是一般,分配是特殊,生产是受自然规律支配,而对于分配呢,则认为它是受社会规律所支配,在分配领域,人们可以大有所为,所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总是将分配置于首要的位置。然而,资本主义生产,首先是以生产条件的分配为前提,即“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中”[7](p.995)。同庸俗经济学家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整体地看待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并且将分配分为两类,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分配,其次才是作为前者结果的产品的分配。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前者说明生产即分配,这类分配关系完全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生产与分配不仅存在语义上的差异,其实质就是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生产构成母体结构,分配体现这种结构的功能,通过“生产关系组织说明社会制度,并认为这种生产关系组织本身已经含有一定的分配制度”[8](p.403)。庸俗经济学回避生产条件的分配,只关注供个人消费部分的产品的分配,脱离生产关系孤立地研究分配关系,将分配关系人为地拔高,认为分配是受法律和习惯等“社会规律”的支配,决定分配的统治者的好心歹意,完全受主观意志决定。事实上,分配关系的母体是生产关系,从发生学角度审视二者具有同一性,“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7](p.999)
交换关系:一般来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出现分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原始自足的生产方式遭到破坏,社会需求也逐渐多样化,因而人们必须采取某种方式交换他们各种的劳务活动和劳动产品,这么一种活动就是交换活动,而在这种交换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是交换关系。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来看,“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5](p.22)因此,交换是内嵌于再生产过程中的,其本身要素都由生产来决定,例如,交换的性质取决于生产的性质,交换的方式也由生产的结构所决定。所以,“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5](p.23)交换关系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对于现存社会形态的解体以及新的社会形态的建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具有不同的交换形式,原始部落之间个别的、偶然的、短期的物物交换形式,导致原始社会的解体,农耕社会中以货币为媒介,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对象化劳动与对象化劳动之间的商品交换形式,加速了农耕社会的坍塌,也使得交换关系发展到了最高级的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值基于普遍的、经常的、长期的商品交换,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形式,其实质是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交换,但这种交换关系是以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为基础,它掩盖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
消费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按照庸俗“三段论”来看待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认为“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而消费则是个别”[5](p.13),这种观点除了规定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外,特别强调消费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它与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其本身就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等量齐观,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从整体辩证的视角看待消费,认为四个环节是一个整体,生产与消费之间呈现为对立统一的关系,其同一性具体表现在:其一,生产就是消费,消费就是生产,“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5](p.14)其二,生产和消费互相依存、互为前提,“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5](p.15)其三,生产和消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5](p.17)然而,生产与消费之间更为重要的它们的矛盾对立面,在社会再生产的统一体当中,生产是处于基础性地位,生产决定消费,“如果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主体的或者许多单个个人的活动,它们无论如何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9](p.33)只有在承认生产的主导性前提下,消费对于社会生产的能动性作用才能得到体现。
三、资本积累体制的空间意指
资本积累体制如何能够和空间关联起来呢?或者说资本积累体制的空间逻辑是怎样的呢?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资本积累体制的空间意指问题。我们知道,空间由社会生产出来,空间与社会关系是同构的,其背后缠绕着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在其中。资本基于控制劳动和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不断重新规划生产空间的布局,进而也影响到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空间形态表现。作为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总和的“资本积累体制”是指资本主义现存的在生产、收入分配和需求之间的动态协调机制,是在两种结构性危机之间长期存在的正常的积累模式。参Boyer, Robert, 1990,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35.,必定存在相应的生产空间规制及其所承载的分配空间规制、交换空间规制和消费空间规制等。而作为资本积累基础的生产关系所涵涉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10](p222)等关键问题,都指向诸如:“土地、森林、水流、矿藏、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10](p.222)生产资料的空间要素问题,因此,任何资本积累体制都相应地存在一个外显的空间形象,因为“空间的形象只不过是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的投射”[11](p.13)。这就很好地诠释了意指内涵,更严格来说,意指(signifying)就是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影射关系,因此,资本积累体制的空间意指就是指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与其所映射的喻体空间之间的关系集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特征的矛盾,资本主义必须采取不同的机制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总产品以及推进资本积累的进程。由于不同时期的资本积累体制迥然不同,相应地,它们所对应的空间逻辑差异极大,每一特定的资本积累体制背后都有一个特定的空间秩序作为支撑,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特定的资本积累体制都意味着一个很特殊的空间机制。接下来,我们从一般意义上刻画资本积累体制的空间所指——空间逻辑如何与资本积累逻辑协同。
“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5](p.169)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彻底地撕毁了田园诗般的空间景观,颠覆了地区、国家甚至全球的地理风貌,领土不断重组成为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资本主义空间规划本身构成为资本积累的须臾不可分的促进因素。因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7](p.922)这不仅表明资本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存在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其次,它也是一个社会范畴,表征了存在于该物中的所有关系或占有关系中的一个交错点。“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实质上是一种强制性的客观力量,体现着其自身的逻辑,即支配社会资源流动,分配社会财富,组织社会的扩大再生产,使整个社会组织成为追求资本增值的机器”[12](p.13)。作为强制性客观力量的资本体现为一种压制劳动的权力,“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13](p.757)。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这种权力不断地进行空间规划从而为资本生命注入新的活力,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14](p.34)所以,资本对劳动的权力内在地具有生产和再生产空间的趋势。资本具有超越时间,直接穿透到各个实体层面,并随着生产力的展开发挥影响的能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的重组主要与支配性的体制的再生产相关,而支配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成为资本主义自身存续的基础。由此,空间的生产必然带来支配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支配性生产关系则通过支配性的空间结构,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得以再生产。
至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一下资本逻辑与空间逻辑的两个范畴,资本的生命力在于追求绝对财富,而绝对财富本身是无止境的,这就决定了资本永不停息的扩张,相应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呈现为一个开放系统,不断自我膨胀,内在地决定了资本逻辑脉络,即“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其活动历程具有必然如此的内在联系、运动轨迹和发展规律”[15]。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作为资本积累喻像的空间只是由资本积累线性地、单向地决定呢?事实上,空间既与资本逻辑的展开相结合,同时,空间也不是完全被动地踩着资本逻辑的节拍,资本积累与空间两者之间是辩证关系,空间具有工具性,能够与资本积累协同运动,构成资本积累的要素,此即空间逻辑,它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方面空间随资本扩张而扩张,另一方面借助空间重组主动介入资本积累运动。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生产手段集中在资本家的手里,工作地点集中在车间和工厂,工人在资方的监督下为了工资在这里工作。工作与家庭分离了,领土控制变得专门化,涉及工作场所(在工业的控制下,并得到政府通过产权法等而给予的支持和政治领地)。新的经济秩序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以及使用可靠而又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的“自由”贸易。所有这些因素改变了社会与场所的古老的域融合。把社会与场所的基本融合转变到更大地理范围的独立国家,再到现代民族国家,从而实现了经济功能的协调。无论从资本主义企业的空间规划,还是城市的空间规划来看,资本逻辑与空间逻辑的对抗性矛盾高度一致表现出来。从企业空间规划来讲,比如,协作,“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3](p.374)合理的企业空间规划提高了劳动过程的时间连续性,以及增加了劳动强度,意味着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地增加了,另外,由于工人在空间上的集聚使得不变资本利用率相应提高,其价值也相应地降低了,这些都增加了资本对劳动的压制力量。
从城市空间规划来看,“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13](p.757)生产要素在空间上越是集中,资本越能够利用空间消灭时间,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加强资本积累,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景观的异化,体现且服务于资本的高楼大厦、交通设施空间上日益膨胀,而属于劳动力再生产范畴的贫民窟的空间越来越局狭。空间既是资本运动的载体,又是资本积累的要素,资本积累与空间喻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资本主义空间规划全程参与到资本积累过程中。
由此我们都可以发现,尽管空间尺度不同,但空间因素在资本积累中的基础性影响却是趋同的:即通过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实现资本的循环,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和对抗,资本积累总是不断遭遇瓶颈,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空间景观特别是吸纳过剩资本的城市建筑不断重塑。
[参考文献]
[1]罗伯特·戴维.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36,8th ed, Book V. chapter 15, part 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列宁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一些经济问题的论述[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10]斯大林文集(1934—1952)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2]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郗戈,从资本逻辑看“全球现代性”的内在矛盾[J]教学与研究,2011,(7)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教师,博士,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冒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