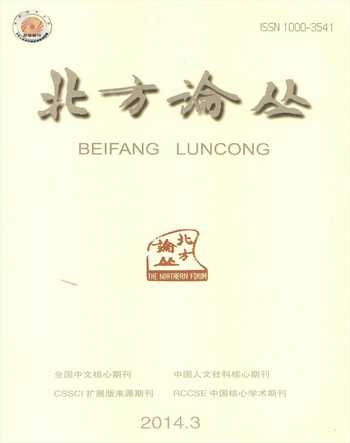民俗文化圈与元杂剧中民俗趋同现象
彭栓红
[摘要]元杂剧中民俗元素出现频率较高的往往是各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反之,出现率低。元杂剧所反映的民俗文化有很大相似性,具备多民族共同的审美接受心理,这是与元代多民族杂处、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环境相适应的,为了争取更广的观众群体的民俗文化认同而采取的策略。这种增强民俗认同的策略就是在体现个性民俗的同时,不忘彰显共性民俗文化,充分考虑民族的、地域的民俗文化圈因素。
[关键词]元杂剧;民俗;民俗文化圈;民族;地域
[中图分类号]I23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3-0025-04
Abstract: The more accepted by every nationalities, the more frequently a folk culture would appear in Yuan-Dynasty Zaju plays.The folk cultures reflected in Yuan-Dynasty Zaju plays share great similarities, and are commonly accepted by multinational aesthetic perception. For more extensive acceptance from folk culture, such similariti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multi-ethnical inhabitation and the coexistence of diverse cultures of Yuan-Dynasty. Such folk culture enhancing strategy highlights common folk cultures while reflecting individual character of folk culture and fully considering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folk culture circles.
Key words:Yuan-Dynasty Zaju plays; Folk culture; Folk culture circles; Nationality; Region
[收稿日期]2014-03-02
[基金项目]2012年大同大学博士科研项目“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研究”(2012-B-26)资助;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751017)资助。
民俗文化传承有纵向和横向传承两种方式。民俗文化的纵向传承具有历时性特点,而横向传承较多地体现在空间地域上扩张。民俗文化变迁主要体现纵向传承,对元杂剧民俗的选择会产生影响。当然,在元代民俗文化的横向传承也是空前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民俗文化加速传播、融合。有元一代,女真、蒙古、回回等族汉化加深,汉族也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因素,从而各民族民俗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现趋同性,反映在元杂剧中大量民俗事象呈现相似性特征。这对于作为接受者的观众面临一个民俗认同的问题,也就是各民族、各区域民众对本民族、本区域的民俗在元杂剧演唱表演中的认可度。
一般地说,要增加民俗认同的可信度,办法有两个:一是杂剧选取能体现民族地域特色的个性民俗文化,如杂剧中体现蒙古族的蒙语表达、暖帽貂裘、羊酒毡车,女真的玉兔鹘、缠须,回回衣帽、回回曲等;二是杂剧选取超越民族地域界线的共性民俗文化。各民族相似民俗文化的大量体现,使得民族民俗认同容易超越狭隘的民族观,而滋生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这种民族文化的认同,反过来又会促成民族和解,加速民族融合。笔者检索元杂剧中的民俗事象,发现除了那些因剧情表演需要突出民族民俗文化的作品,会较多注意选取符合该民族的个性民俗文化,大多数剧作都选取那些能代表多民族的共性民俗文化来描写。即使表现少数民族文化题材的杂剧,其民俗事象的选择也未必完全是本民族独有的民俗,而更多地表现该民族所处民俗文化圈体现出的共性民俗。
一、民族与民俗文化圈
20世纪末21世纪初,学术界热议民俗文化圈,何谓民俗文化圈?马成俊说:“民俗文化圈是一个背景性的问题,它是由一定的生物性成分、地区环境成分、历史沿革成分和民族文化成分构成的共同的民族文化空间。”[1](p.90)陈华文则认为:“民俗文化圈是一种以族群为活动依托,具有地域性和传承性特征的民俗文化生存形态。”在民俗文化圈里,“民俗文化在相对的环境、族群和空间,存在相对的民俗文化事项;换句话说,民俗文化是在相对的族群中以相对的内容和方式独立地存在”[2](p.40)。还有学者提出我国有七大风俗文化圈,即东北风俗文化圈、游牧风俗文化圈、黄河流域风俗文化圈、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青藏风俗文化圈、云贵风俗文化圈、闽台风俗文化圈。关于民俗文化圈的类型划分,学者们众说纷纭。笔者为论述方便,结合宋元文化、民族、地域和生活方式特征,暂划分为游牧狩猎民俗文化圈和农耕民俗文化圈。
民俗文化圈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也意味着圈内的民俗文化相对稳定。元杂剧涉及的匈奴、契丹、突厥、回回、蒙古、女真等族,长期居于我国北方或西北方,相对稳定地以北方地域(主要是草原区域)为活动空间,基本上都属于阿尔泰语系;文化上以游牧特征为主,狩猎为辅,其生活习性和风俗有着雷同性。这些民族基本归于我国古代游牧狩猎民俗文化圈,因而元杂剧在描写蒙古、女真等族时,就充分表现游牧文化圈的共同特征:胡语奇服、飞鹰走犬、能歌善舞、嗜酒肉割食、骑马飞箭、狼鹿鸦等动物图腾信仰、飞鹰走犬的围猎文化、割食习惯,以及萨满教信仰在蒙古族、女真族都存在;烧饭习俗是契丹、女真、蒙古等族重要的礼俗,这些民俗文化在元杂剧民族题材中多见。宋德金考证:“烧饭是女真丧葬中另一重要习俗……在辽金元的史料中均有关于烧饭的记载。”[3](p.149)正是游牧狩猎民俗文化圈中民俗文化的共性特征,使得我们在体验元杂剧蒙古、女真、回回等少数民族风情时,总有似曾相识之感,很难判断某一民俗为某一民族独享。而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民俗文化圈,其活动地域主要在长江、黄河流域,汉语汉字是其文化传播的有效媒介,定居的农耕生活是其主要生存方式,社火文化、村井文化、岁时节日民俗、家宅六神、传宗接代、明媒正娶、土葬哭丧、贞洁伦理、抛绣球、接丝鞭等,民俗文化在元杂剧中均有细致的反映。元杂剧大量农耕民俗文化圈和游牧狩猎民俗文化圈的民俗事象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存在的胡汉、华夷之分,表达的是在蒙元统一全中国后,汉族不得不直面新的多民族现实的文化反差感和民族冲突与融合下的各民族本位体验。
民俗文化圈有稳定性特征,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文化圈还具有“活”的特征:“民俗文化圈这种‘活的特征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它的承袭性。承袭性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民俗文化圈内部的承袭,另一种是在民俗文化圈传承过程中空间的扩张,后者,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传播。”[2](P.43)元代的疆域扩张之迅速,人口迁徙之频繁,双语、多语并存现象地域之广阔,都非前代可比,这就为不同民俗文化圈的传播、扩张提供了便利。因此,民俗文化的共性特征,不仅体现在同一民俗文化圈内的文化类同,而且体现在不同民俗文化圈的传播扩张,导致民俗文化趋同现象。同样的民俗事象一般会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处于同一文化圈基于共同文化心理产生的相对稳定的民俗,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一种是民俗文化跨地域、跨文化圈传播,并导致的民俗“同化”现象。元杂剧中的民俗事象到底属于哪类,需要理性看待,具体分析。我们着重探讨跨文化圈的传播导致的民俗文化趋同现象。
汉族民俗文化主要分布在农耕民俗文化圈,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狩猎民俗文化有着比较大差异,但历史上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往几乎从未间断过,宋辽金元尤甚。扎拉嘎先生认为:“历史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多数属于狩猎—游牧民族。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农耕文化与狩猎—游牧文化之间的互相竞争、互相补充和互相融合,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历史中是一个基本的线索。其中,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事件,应该是黄帝进入中原……促成了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狩猎—游牧文化的一次大融合。”“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农耕文化与狩猎—游牧文化的大融合,发生在元代。”[4](pp.93-94)因此,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时代特征,使得元代不同民俗文化圈间碰撞、交融乃至吸收同化,在所难免。
譬如,元杂剧中岁时节日民俗异常丰富,主要表现的是汉族的节日文化内涵,而女真人初不知纪年,也没有岁时节日,后来在汉化中接受中原岁时节日,如元宵、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蒙古族入主中原也逐渐接受了大部分汉族节日文化。《元曲选》《元曲选外编》中涉及清明三月三的作品有25剧,中秋作品10剧,元宵节4剧,端午节、七夕各5剧,重阳6剧等。这些岁时节日在反映不同民族题材的作品中都有折射,正是民族融合、同化的体现。再如,汉族的出生礼有生日、满月、百天等,蒙古、女真等族对生日也很重视。根据《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记载,元朝“每年,那位皇帝要保留四大节日,就是说,他的生日,他行割礼的日子,等等。他召他的诸王、他的俳优及他的亲属都去参加这些节日盛会……特别在他的生日和割礼日,他希望大家都出席”[5](p.79)。可见,蒙古人十分看重过生日。女真人也重视生日,因初无纪年,而自择佳辰为生日,据《松漠纪闻》所载,以汉族岁时节日为生辰:“酋长生朝,皆自择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乌拽马以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7](p.2798)基于这种共同的过生日习俗,《元曲选》有《还牢末》《任风子》《竹坞听琴》《灰阑记》《杀狗劝夫》《东堂老》《儿女团圆》《金安寿》等剧都出现庆贺生日的描写。可知,生日文化在蒙、汉、女真民俗文化中都有体现。少数民族在生日文化传播中,多吸收了汉族民俗文化因素。汉族有指腹为婚的习俗,女真族也有。宋德金认为:“女真有指腹为婚的风俗。《大金国志》《松漠纪闻》均记载。”[3](p.148)民俗文化圈的传播中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也是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在女真、回回、蒙古民族中都存在,元杂剧多有体现,如《磨合罗》第三折:“老夫完颜女直人氏。完颜姓王,普察姓李”,这是女真贵族遵照汉族的百家姓取大姓优先,再结合女真部族的贵贱程度取姓的一种方式。儒释道文化在汉族根深蒂固,对其他民族也产生过某些影响,例如,佛教对蒙、汉、回、女真等族都有影响,《松漠纪闻》载,回回“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6](p.2791),女真族“胡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焚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座”[7](p.2798)。即使像关羽这种汉族神祇也逐渐在元代为各族所接受。因此,元杂剧中表现弥勒、观音、哪吒、关羽信仰等的作品为数不少。
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是双向的,汉族也接受了许多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女真、蒙古族都存在火葬习俗,汉族在民族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对火葬有一定的接受。宋德金结合考古认为,女真等北方民族有火葬习俗:“由于受到佛教和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影响:在与辽金同时的两宋某些地区也行火葬”[3](p.149)。烧埋习俗入元后也为汉族所接受。女真服饰对宋元之际的汉人也有影响,“金朝统治者强制推行服饰女真化,使得女真的衣着、发式在金统治的北方地区汉族中流行开来,其窄袖、挽髻、带裘皮帽成为时尚,同时也影响到南宋”[7](p.104)。从元杂剧审美接受的角度看,正是元代民族融合是双向的,才使得观众对元杂剧中民族习俗的模拟表演和唱词叙事不会“陌生化”,也使得元杂剧的传播和受众群多元化。
有些共性民俗事象是基于人类的共性思维,这部分民俗事象在民俗文化圈的传播过程中,更容易为各族民众所接受。祭天在我国古代东北民族中就有,辽金、蒙古都崇拜天,汉族也早有祭天习俗。《金史》卷三十五《志第十六·礼八》记载,女真在岁时节日拜天:“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8](p.220)对于太阳崇拜,蒙古族、女真族、契丹族和汉族都有。对于兔、鹿、羊、鸟崇拜,也非北方民族独有,汉族也有。灵魂崇拜、万物有灵、占卜观念、星辰崇拜、感生神话、射日神话等,都具有人类思维的共性文化。尽管各族习俗稍有差异,但“文化之根”、“思维方式”有相同性。如人类关注自然、征服自然的愿望,是每个民族成长的共性,因而射日神话极具普遍性,据陈建宪先生的“中国各族射日神话”统计表发现,这一神话分布在我国汉、满、蒙、壮族等“27个民族”,其中蒙古族有乌恩射日的事迹[9](pp.155-156)。感生神话在蒙古族、汉族等族都有。元代盘古神话在其他少数民族神话中是否存在,不得而知,但现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也有遗存。汉族与北方民族分属不同民俗文化圈,但在民俗文化圈的跨地域传播中,以上民俗事象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渗透,逐渐趋同。据笔者统计,在《元曲选》中,日月神话有9剧、射日神话有2剧、感生神话7剧、嫦娥神话17剧,其他灵魂信仰、动物崇拜等民俗文化在元杂剧中也均有不同程度体现,此类与人类共性思维有关的民俗趋同,可以突破狭隘的民族和地域限制,成为元杂剧传播较广的又一内在动力。
正是元代打破了固有的民俗文化圈空间束缚,在广阔的疆域内民俗文化的传播中,在民族融合加速的前提下,各族人民对异文化的了解、接受、同化,对相似文化的包容性认同,才使得杂剧作家在民俗的选择上,体现出较强的民俗文化共性特征。这一选择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民俗认同的过程。
二、地域与民俗文化圈
如果不考虑民族的因素,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从地域上大致还可以分为江南民俗文化圈和塞北民俗文化圈。
元代大一统,打破了南北地域行政界限,使得南北文化差异凸显出来,而民俗文化首当其冲。饮食上南方多海鲜,北方多米面;南方多菜肴,北方多烤肉。即使肉食,中原多猪肉,北方多羊肉。宋代学者张师正《倦游杂录》引《类苑》记载:“杜大监植言:南方无好羊洎面,惟鱼稻为嘉,故南人嗜之。北方鱼稻不多,而肉面嘉,故北人嗜之。易地则皆然,不必相非笑也。”[10](p.747)因南北饮食文化差异而讥笑对方,宋人庄绰《鸡肋编》卷上也有戏言:“‘孩儿先自睡不稳,更将擀面杖拄门。何如买个胡饼药杀着!盖讥不北食也。”[11](p.4003)元杂剧肇始于我国北方,元杂剧中饮食文化首先体现的是北方饮食文化。北方饮食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面食与肉食文化。肉食在元杂剧中以“羊肉”为典型,如《伍员吹箫》《勘头巾》《黑旋风》《酷寒亭》《朱砂担》《儿女团圆》等剧,反映出宋元时期人们爱吃“羊头”的食俗。面食如蒸饼、旋饼、烧饼、馒头(即馍馍),如《气英布》有:“汉乾坤也做不得个碗内拿蒸饼。”米饭有白米焖饭、欢喜团儿、粥汤等,如《蒋神灵应》第一折:“白米焖饭吃二十碗”,《鸳鸯被》第三折:“我买欢喜团儿你吃”,《东堂老》第三折:“等我寻些米来,和你熬粥汤吃”。
由于民族杂居,人口流动,南北民俗文化差异,有时又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呈现出来,如杨显之《酷寒亭》第三折,江西商人酒店老板张保以南方人的视野看到回汉民族和南北地域饮食文化的差异。在元代南北交流中,南方人颇有经商头脑,尤其是沿海商业贸易的繁荣,而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使得北方人对南方商人颇有偏见,尤其在元代,除了汉人,还有回回等胡商,“回回商人在各地已成为巨商、富商和奸商的代名词”[12](p.609)。方龄贵在《通制条格校注》中解释,蛮子为“南人亦称蛮子”[13](p.80)。方先生对“蛮子”的注释是从民族和历史角度解释,固无不可。事实上,元代“蛮子”的文化意义不局限于此,在元杂剧中,表现为北方人把南方商人视为“奸商”的歧视,如《青衫泪》中江西茶商、《酷寒亭》中江西人酒店老板张保,都被称为“蛮子”。可见元杂剧中“蛮子”多与南方商人有关,且多为江西商人,这在民间传说故事中也多见,“蛮子”一词在对方看来是不敬之语或骂语。如《酷寒亭》第三折张保说:“他屋里一个头领,骂我蛮子前,蛮子后。我也有一爷二娘,三兄四弟,五子六孙。偏是你爷生娘长,我是石头缝里迸出来的。”总之,“蛮子”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在看待经商这一现象时,南北文化的差异。
北方天寒多火炕,也与南方水乡居住文化不同。最早关于火炕的文献记载,见于《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中记录了观鸡寺用火炕御寒。史卫民在《元代社会生活史》中指出:“大都和上都简陋的砖房和土房,应是黄河以北一般城市居民的典型住房。火炕的使用,自辽、金以来已经在北方地区普及,北方城市住房中有火炕,在元人眼中已不是稀奇之事。”[14](p.193)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政宣上帙三”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相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15](p.17)元杂剧《铁拐李》《东堂老》《救风尘》《岳阳楼》《生金阁》中的火炕、烧炭等取暖习俗的直接或间接描述,正是对北方生活的记录,也是杂剧早期在北方兴盛的民俗诠释。
当然,南北文化有差异,也有融合。宋元以来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吴松弟认为:“南宋时受北方移民影响,南方人也认为羊肉是最好吃的美味食品。”[12](p.508)元代居于南方的回回及南下的北方人把吃羊肉的风俗也带了过去。元代移民也使得北方火葬之俗在南方也产生影响。这种南北民俗文化的大势,使得元杂剧中关于“烧埋”、“羊”的描述屡见不鲜,显得合情合理。
总之,元杂剧中民俗元素出现频率较高的往往是各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反之,出现率低。元杂剧所反映的民俗文化有很大相似性,具备多民族共同的审美接受心理,这与元代多民族杂处、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环境相适应,为了争取更广的观众群体的民俗文化认同而采取的策略。这种增强民俗认同的策略就是在体现个性民俗的同时,不忘彰显共性民俗文化,充分考虑民族的、地域的民俗文化圈因素。元杂剧的这种民俗趋同品格,使得元杂剧在元代迅速传播,广泛扩布,兴盛成熟,并成为“一代之文学”,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马成俊.论民俗文化圈及其本位偏见[J].青海民族研究,2000,(3).
[2]陈华文.论民俗文化圈[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6).
[3]宋德金.金代女真族俗述论[J].历史研究,1982,(3).
[4]扎拉嘎.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J].社会科学战线,2003,(3).
[5]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M].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
[6]洪皓撰,阳羡生校点.松漠纪闻[C]//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顾韵芬,张姝.金代女真服饰文化的涵化[J].纺织学报,2009,(1).
[8]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9]陈建宪.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M].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张师正撰,李裕民辑校.倦游杂录[C]//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1]庄绰撰,李保民校点.鸡肋编[C]//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2]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3]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4]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作者系大同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成员)
[责任编辑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