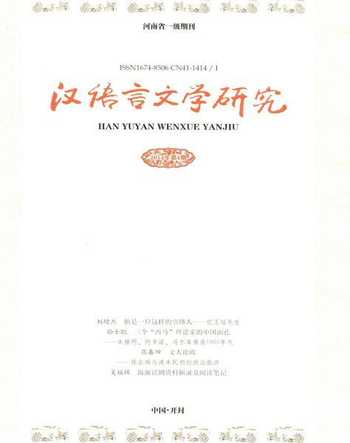文人论政
张春田
摘 要:以往的研究中,南社向以诗酒风流的旧派文人形象以诗歌鼓动“排满”与“革命”风潮,实际上,在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和社会事件面前,南社诸人也以各种政论文章提出过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不仅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而且积极地以言论介入政治讨论。作为南社发起人和中坚之一的陈去病,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对现实政治进行建言与批判的政论文章,其论题涉及政治体制、疆域设置、军事和经济建设以及宪法草案讨论等多方面,显示出当时中国文人的现代政治视野。
关键词:南社;陈去病;政论文章;公共领域
清末的重要文化团体南社在“排满”与“革命”的宣传上所起到的作用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南社人的政治兴趣当然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排满”和“革命”的热切呼唤上,但是他们并不只是以诗歌鼓动风潮。他们在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和社会事件面前,也以各种批评文章提出过自己的观点。这些政论文章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以至于南社人对现实政治的很多看法没有得到很好梳理,这反过来加固了公众对于南社人只是追求诗酒风流的旧派文人的刻板印象。事实上,他们不仅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而且积极地以言论介入政治讨论,对现实政治进行建言与批判,其论题涉及政治体制、疆域设置、军事和经济建设以及宪法草案讨论等多方面。
作为南社发起人和中坚之一的陈去病(1874-1933),与报刊传媒一直渊源甚深。不仅亲身参与了众多报刊的创办编辑,而且也极为主动地利用报刊发出批评的声音。1907年他南下汕头主持《新中华报》;1911年6月自杭州返回苏州后,办《苏苏报》;武昌起义后,又在江苏都督陈德全的支持下,办《大汉报》,鼓动革命舆论。在苏州独立后,他也通过报刊上的政论或时评文章,参与地方事务讨论。像他在1911年所作之《州县民政长之解决》(讨论苏州行政长之去留)、《吴中水利议》(讨论吴中水利事业)、《苏州宜改县矣》(讨论苏州行政设置)、《呜呼,苏苏其不复苏乎?》(讨论苏苏女校复校工作)等文章,都对地方公共事务有所建言和规划。而1912年1月,陈又与人在上海发起创办《黄报》,同月,赴绍兴任《越铎日报》总编辑,6月改任杭州《平民日报》总编辑。他的身份与工作,使得他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舆论能力。本文将以陈去病在清末至民国初建时期所写的一些政治或文化批评文章为例,讨论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思考,以展现南社人以批评建构公共领域的一面。
晚清的边疆危机是当时国人最为关注的。1904年陈去病在《论中国不与俄战之危险》一文中,对政府“中立”态度不以为然:
夫事为中国之事,己不能谋之,而他人代我谋之,抑已耻矣。乃谋之不下,以出于战。而开战之事,且不发于我,而发诸日本。呜呼!我中国之可耻,孰有甚于此乎?乃今者不惟其耻之为念,而日日以任他人之战争。……以为我能中立矣,我可以坐观成败矣。{1}
陈去病认为这是幻想。他鼓吹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对俄宣战:“如此,则中国可保,疆土可复,援兵得济,主权复还,而将来之独立,亦从此可期。”{1}否则,国权旁落,危机只会更深。这显示出陈去病对国际政治局势的深刻洞察。日本果然利用日俄战争,从此将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
1904年陈去病还撰写了《漠南北建置行省议》,纵论中国北方的政治建制。他对自己的方案很自信,说“有王者作,经营八表,必从吾言矣”。
一开篇他提出,蒙古幅员辽阔,“三百年来,屹然为中朝藩卫”。他把蒙古分为四个部分,指出“稽之载籍,则大漠以南,固我中国所有土也,开边置郡,筑城受降,其事至盛。……晚近以来,燕赵边外,东抵辽沈,始渐开垦,规为郡县。然意在苟安,无大兴革,终未见其裨补也”。陈去病认为对北方边疆不进行彻底规划,沿用朝贡体系将蒙古作为藩属对待,这是没有政治远见的行为。必须在长城之北设立行省,以更有效地加强管治:
举夫大漠南北,悉数囊括而隶司空之籍,更藩属之往制,夷穹庐为城郭,增置军备,拓为行省,慎简重臣,威镇其地,移民耕垦,以实边塞。夫如是,则国本固而敌亦知我之备,将北顾之忧,其稍纾乎?{2}
陈去病的建议显然是基于1903-1904年俄国和日本围绕中国东北展开的争夺而起的。他担忧目前中国对北方边疆相对松散的管治方式,会让“罗刹之众”迟早对蒙古下手。但我觉得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附属于朝贡体制的藩属制度的质疑:藩属制度在疆域上的松散和灵活的理解,在民族国家体系面前是不是失去了它所固有的优点,反而变成了可被其它国家利用的漏洞?在这个殖民竞争的时代,中国要保存自己并且参与竞争,就不得不实行中央集权,接受民族国家体系所假设的明确的疆域界限的划定。陈去病说,“今若弃蒙,吾无可言。否欲保蒙,则必置省”。这表明设置直接的行政管理是时势所逼,不得不然。
陈去病还认为,对蒙古加强管理,不是简单的建省,而是配合以一整套的规划。他具体分析漠南、漠北的地理、民族与文化情况,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步骤与方法,加以分别对待。“漠南卫中国,为十八省之附庸;漠北固边防,为新疆东三省之犄角”。③接下来,陈去病还设计了详细的官制,和行省下面的行政区划。在具体的治理政策上,陈去病也有两个建议:一是强调“威服之能”之外的“教育之功”,通过文化的交流来促进民族之间的理解。二是将“淮南北地”的“穷民之无告者”迁徙到长城以北,助其屯垦,“耕收于大漠之野”。既可补助驻军衣食,又解决了流民问题。{4}文章的最后,还附有一张“漠南北新建置总表”。
这里不去评价陈去病的方案是不是有可操作性,单从他的详细描述和讨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确实是意识到了作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之一的这一区域,{5}此后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而且,他并不是笼统地提出看法,而是做足了功课,建议提得非常具体和有针对性。这体现了晚清经世实学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知识分子面对新的民族国家体系在知识上的准备。民国成立以后,将内蒙古析为好几个省,实际也是基于加强国家治理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去病在清末提出的建议并不是一般的“书生之见”
陈去病关于加强边疆地区治理的建言,还有很多。如1908年所撰《南粤分疆设治议》。1912年陈去病在文后补记中说:“此丁未岁闻英法二国借口盗患,欲于西江流域有所侵越而作也。”⑥文中也是先勾画地理形势,特别侧重地缘政治的视角,比如他谈琼州海峡,“在无事,可通东西之邮;万一兵兴,则中国海军可从而树厥权于南海之南,以崇藩卫,抑又欧亚成败利钝之所系也”。他对广州湾被租借深感痛惜:“白人入室,租借约成,百年长弃。追维往事,能不痛心?何况法人据此,志不在小。卑哉一隅,而所包甚广。”鉴于如此形势,他建议:“析粤省西南地与桂省南部地,别建省曰广南”,给予特别重视;“以南宁为省政府主席以下官驻在地”。{1}陈去病后文还澄清了对设省以后、可能各自为政的担心,再次表示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有效地防范外患,“名为分枝,实属保全两广之策于其中也”。{2}陈去病在文后补记说,民国成立后,桂督果然移驻南宁,而孙中山也建议将琼州改分行省。对于自己此前的主张变成现实,他颇为自得。
这一类型的文章,在清末,还有《论筹防天山南路》(1908年),对新疆南部的区划设置、练兵筹饷,都有细致论述。③进入民国以后,作为原帝国所辖领土的辽阔的边疆民族地区被纳入民国法统,但局势也相当险恶。陈去病作《呜呼!边陲之风云急矣》(1912年),针对俄国借端图谋新疆一事,议论说:
记者既观时局,每以满蒙回藏危机四伏,辄窃窃焉,为之抚膺增痛。以为危迫如此,而当局犹不知戒备,恐非民国之福。……夫大好河山不能巩固,在满虏时代固不足责。若今者民国成矣,而四顾方隅,乃有岌岌可危之象。然则政府诸君,能诿其责而不自咎乎?{4}
他认为巩固边陲,乃是“巩固民国之初基”。鉴于“离叛日起,窥伺日殷”给西藏造成的威胁,他又作《西藏改建行省议》(1912年),强调“必先就其近者易者急植之基”:“余为藏计,拟先就康卫两部,力图开拓,而略择青海、后藏之要地,加以整顿。则西藏大局,亦自可观”。{5}在民初关于建都何处的讨论中,陈去病也有自己的意见。他既不赞同北京,也不主张南京或武汉,提出应该迁都正定(今石家庄),“统合枢机,建中立极”。⑥自然,经营西藏,或者迁都正定的计划,都是从维护中央集权的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着眼的。
民国建立以后,实行“五族立国”的政策,{7}继承了帝国的疆域与人口,以中华民族而非“汉族”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曾经倡言“排满”的陈去病,这时反倒格外注意维护多民族组成的“大一统”国家的法统。1911年他在《中华民国国旗纵论》中,以国旗为借端,虚拟“客”的口吻,质疑十八星旗只反映了十八行省,而忽视了更广阔的疆土,对维护统一国家不利:
此外,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四省同是中国领土,同列新政区划之中,不应轻易舍去,启人以觊觎之阶。况伪清往日尚有开拓蒙藏、康卫等部,改建行省之议。今既组织民国,何以恝然置之。{8}
陈去病回答说,十八星旗也只是“首先标识,扬独立之精神”,将来一定会改换的。至于“中华民国”的国号,也是“合乎古无悖于今”。他立论的主要用意正在于强调“民国”与之前的帝国在国际法意义上保持着主权的同一性。直到1929年,他还作有《中华民国释义》,探讨“中华民国”名称的来源,仍强调中国文明与国家的连续性。他说:
盖吾族之兴,托始昆仑,黄帝东来,犹梦花国。降逮汉世,而番兜开国之祖,犹奋然崛起于华胥故壤,建阿萨之朝,为一雄国(按“华胥”与“安息”为一音之转,“安息”与“亚细亚”又为一音之转。……当时欧洲诸国惟罗马最强,其属土踰地中海而东逾番兜壤地相接。而亚洲西部亦惟安息为盛,故其祖阿尔萨克自号为‘阿萨朝云),迄今声威所播。而亚细亚洲之称,遂为宇内所不废。然则吾华国家之震耀于坤轴也,非合古今中外而吻然一辙哉?{1}
陈去病援引各种古籍,努力在“华”与“夏”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语意关联,证明自古“华夏并称”,即“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存在:“故‘夏可以训‘中国之人,即‘华可以名‘诸夏之国,无异致也。……是故‘虞夏云者,乃‘华夏之音变,民主之权舆而中华民国之嚆矢也。”{2}他这样殷殷探问历史,看似依然着重文化,但其实反复强调“民主”与“中华民国”,已经预示了某些微妙的转变的发生,即目的首先是为了强化公民对共同体的政治认同:“斯诚不失其为大中华之民,而克副其为大中华之国矣。”
除了关注国家疆域和代表性,陈去病对清末立宪与国会问题也有很多评论。在《报馆之国会热》(1908年)一文中,一方面,是报界对于组建国会的热衷:“今日国会国会之声,猖狂洋溢,亦几几遍中国矣。言之者既舌敝而唇焦,闻之者亦瞀乱而失据。”但另一方面,清政府的实际行为无疑打破了这样的幻梦:
然而,天威不册,陈景仁则以电参于式枚而革职矣,政闻社则以良莠不齐而奉旨严拏伙伴矣。各省请愿之书,都察院且迟回,瞻顾欲上与不欲上矣。③
言下之意,即清政府的所谓“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场拖延的骗局。对于报界的一厢情愿,陈去病的笔调充满了反讽:“举世都不讲理而其人偏要说理,是谓不懂道理。……虽然,国会绝望如彼,人心之厌倦如此,而千理万理,缠绕不休,报往跋来,迄无其已。热哉热哉!”{4}显然,这里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立宪派,他希望他们能停止幻想。
另一篇《论建立国会之非易事》,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批评国会之议。陈指出,如果没有认真的准备,“无所筹划而徒大言以欺世,悬空名以遮人耳目,则标榜之行也”。{5}陈去病以为国会是“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之旷举也”,不可“摹仿仪型,掇拾牙慧”,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否则以后将纠纷不断。虽然清政府现在宣布了九年的预备立宪期限,但陈最大的担心在于人才:“担任办事之人才顾若何?”他接下来提出了四点疑问:第一,如果说国家已经有了实施宪政所需人才,那么这些人在这九年当中是否能不受阻挠,而且自身也能不阳奉阴违?第二,如果国家还缺乏这类人才,那么这几年应该实施的那些政策依靠什么人来执行?如果依靠法政讲习学校来培养,那么这些学校本身刚建立,如何保证培养出的都是有实践能力的英杰?如果还是依靠那些“疲癃老疾之绅宦”,那么不会有根本改变。第三,人民程度不齐,很多人罔顾公益,期待九年中尽变为开通,这是否现实?第四,短期内要办很多事业,财政如何保证?官员们会否借新政,搜刮民财?⑥陈去病深刻意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列出一个宪政时间表就行了。
在清末立宪与国会问题上,陈去病这些评论表现出一种有意的论述策略。作为曾经高呼“革命其可免乎”,并且与革命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他当然不希望满清的统治延续下去,更意识到清政府的让步是有限的,预备立宪敷衍的意味要大于实践的决心。但是这些评论大多又是他以记者的身份在《新中华报》上公开发表的。在言辞上,他尽力摆出一副客观的架势,提出很多现实例证与实际困难,甚至有时让人感觉好像是在为清政府谋划。但这种有意在语气和措辞上的伪装与含混(ambiguity),反而可以更好地揭穿幻象,达到反讽简单的立宪迷思的效果。
这样的论述策略还体现在《满汉畛域之见果可终泯耶》和《我固知之矣》两文。在前文中,他先指出朝廷“鉴于革命党之纷织”,希望通过立宪,调和满汉,和平解决,似乎是褒扬其一片苦心。但马上又以“侍御之人,职司风宪,顾亦暗于大势,不习世故,斤斤然犹存满汉之见,牢不可破”,重兴党祸一事,证明清朝权贵心里根本没有消除满汉的打算,再以担忧式的口吻表示,恐怕会“惹动天下之人愤激而灰心绝望于立宪之事业,或致转变其宗旨而入于猛烈之一途”。{1}事实上,正是在给读者一种情绪上的鼓动,促其转为激进。后一篇文章评论江苏咨议局的成立:陈去病先故意抬高调子,说以政府毅然筹备国会的决心,咨议局应该是很快就能成立起来的,但“月余矣,尚寂然”一句,马上将文气转折。接下来,以苏抚以断然下札的方式决定咨议局人选,“冀混成官绅之局”之事,揭示咨议局被政府操控的现实,再引出文章最后结论:
苏人之今方皇皇然骇且异也,然而吾则以为无异也。……国会之基础如是,他日之国会亦可想而知也。苏人毋皇皇为也,我固知之矣。{2}
“我固知之”这样故作豁达的感慨,显得比直接批判更有力量,易使读者对清政府彻底失望。
陈去病也接触到了世纪初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可以对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一种拯救,并且相信社会主义将作为替代性的方案“突现于中国”。比如,在《所谓富豪者听者,有心世道者亦听者》一文中,他预言:“社会主义磅礴郁积,行将突现于中国矣。”根据是,原先在欧美国家频繁出现的“联盟罢工诸事”,现在也在中国出现了。清政府本来担忧的是革命党的威胁,现在却也须面对工人的问题:“盖视中国政府官吏之苦革命党尤甚,当为诸君耳所熟也。比月以来,中国联盟罢工之事,亦竟迭见。”陈去病举出了当时岭东、江西、浙湖发生的工人事件,认为“是故社会主义之发端也”。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工人抗争。他认为这些现象在中国连续出现,不仅是各种环境的刺激所致,更重要的是反映出资本主义历史运动本身的辩证性后果:
然其实世之所以生此主义者,乃大势所趋。……中国近日则天灾如水火风旱虫,人事如各种抽捐,交迫而来,类皆足以直接间接而胎孕此主义者。况汽机之用,亦暂兴盛。嗟乎!数年数十年后,虽无人倡之而此主义亦岂能不轰然爆发哉?空言抑之,庸有济哉?③
陈去病还提出社会主义问题,不是政府官威所能压制,也不是慈善事业所能调和,而是要求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强权不除,阶级不去,共产制度不行,诸君其难一夕安枕于高楼大厦中矣。愿所谓富豪者听之。”同时他也希望关心中国命运的学者,要认真研究这一根本问题:“且夫此主义之势力,固决不仅及于富豪已也。惜今中国学者眼光如豆,只知埋头读甚么法政书,妄想专心致力于国家政府之小方面,而不知研究此人群最密切关系之一大问题耳,故曰有心世道者亦听之。”{4}
我们需要注意,陈去病的这番议论是1908年提出的。毕竟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思潮还没有像十年之后成为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话题,社会主义基本还没有进入中国知识人的视野。1907年6月刘师培和张继在东京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陈去病与刘师培关系不错,张继后来也加入过南社。陈去病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是否受到了刘师培等人的影响,尚待考察。但陈去病能从对地方事件的观察中,把这个重大问题提到知识者面前,其预见性与洞察力都是相当突出的。
同一年,他在《贻苏路股东书》一文中,再次引入社会主义概念,给苏路公司建言:“公司虽以营业主义为重,而亦不可不有国家思想隐然默寓其中。”{5}文章的核心是说大小股东在公司发展规划上都有同等的提出意见的权利,但作为股东之一的陈去病,注重的依然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对于资本兼并的抵制。他写道:
吾苏路公司者,固社会主义之苏路公司,而非兼并主义之苏路公司也。故当发起之初,定每股银为五元,且分析其缴股时期,俾无论何等人民皆得因其利便而争来认股,用意至为宏达。……夫唯实行社会主义,故其所定股东得被举董事之权,亦即以百股为限。良以百股之数,在兼并家视之为叹虽微,而就贫民以论,则此五百金者,亦必须锱铢积聚而成,固未可谓非辛苦事也。{1}
陈去病通过对苏路公司的观察,发现资本主义并不是像宣称的那样简单的自由市场和契约关系,相反,它更依赖于垄断机制和对弱势的排斥,并且把这种垄断推向社群生活领域。陈去病这里揭示私有产权的排拒本质,并且提出对立于兼并主义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止是对具体的不平等的抗争,更体现出重新把经济放到社会整体中来思考的可贵努力。从陈去病对于社会主义的使用中,正可以看出那时候的知识人是如何以开阔的视野去打量西方。他们在热切呼唤“十九世纪文明”的同时,却也在寻找着对于“十九世纪文明”的超越和替代的思想资源。
从以上陈去病的文本和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关心中国命运的南社人是如何介入清末民初的现实政治。他们努力把现实政治综合在不断变动的历史关联中。无论是建言还是批判,他们对国家认同与治理所作出的这些论述,可以证明南社人(至少一部分)并不是真的沉浸在“汉官威仪”的天真想象之中的。{2}“汉官威仪”之于他们更多是一种抒情表达,而非现实的政治规划。事实上,他们关于主权连续性、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思考,直到今天对我们仍有启发。
【责任编辑 付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