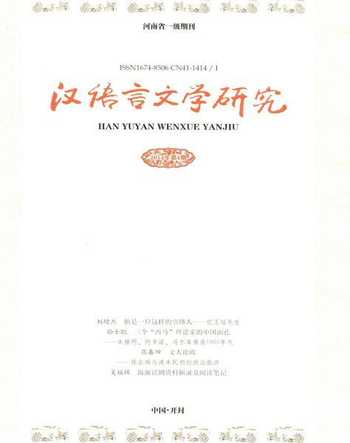宋濂文章的“体要”及其巧变特征
陈博涵
摘 要:“辞尚体要”,体现着儒家的雅正文学观。宋濂文章在“尊体”的基础上,文随其实,表现出中正典雅的文章风貌。他的诸种文体的写作,一方面突出文章的实用性,另一方面也没有忽视文辞、文气的审美意义。不同文体有着不同的文势与体貌,这在总体上会使宋濂的文章写作呈现出巧变特征。在实用中讲究辞章之美,是宋濂最为鲜明的文章观念。
关键词:文体;体要;宋濂;巧变;文章观念
宋濂的文章写作不仅有着雄健的体貌风格,其“真体内充”的道德修养又使其文章“辞尚体要”,郁郁文用,体现出中正典雅之美。“体要”一词源自《尚书》,其言曰:“辞尚体要,弗为好异。”后来刘勰用以讨论文章,“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1},“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2},所谓“体要”有“体之要”和“体其要”两层含义:“体之要”,“体”为名词,指文体,包括事义、文辞、情感、行文结构等几个层面。“体”给我们一个统观性视角,要求初学者明白文章写作在情辞、义理、结构上都有一定的规范性;“体其要”,“体”为动词,侧重体察文体中最为核心的几个层面,以呈现文体本色。杨勇先生在论述韩愈文章“体要”时,以清人方苞“文尚体要,各有所宜”为据,阐释“体要”含义,他认为“体”是一种组织、结构,需要作家经营布置,匠心独运,使文章思想表达得恰到好处;“要”是一种内容、思想,每种文体其重心不同,应该以最适切的语言去表达,除此之外,别无其它。即某一文体最宜表达某言为“体要”。他又认为方苞之说与《尚书》“体要”大体相似,其对韩愈文章体要的分析就是建立在此种理解基础上。③笔者对宋濂文章“体要”的分析,正受此启发。
一、撰写黄溍:同一对象,不同文体的体貌特征
“辞尚体要”体现出儒家的雅正文学观念,即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写作目的,所使用的文体、修辞、语气各有规范。宋濂的文章写作基本遵守文章体制,其公众化的写作更是如此。例如,他曾写过四篇关于黄溍的文章:《黄文献公祠堂碑》、《故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金华黄先生行状》、《金华先生黄文献公文集序》、《跋黄文献公送郑检讨序后》。这四篇文章的写作对象为同一个人,但由于文体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与风貌各有差异。
《黄文献公祠堂碑》是一篇碑文。明人徐师曾指出,碑文自秦汉以来有山川、城池、功德、墓道、托物等碑,“皆因庸器渐阙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4}可见这种实用性的文体主要是歌颂碑主功德,以寄托不朽。刘勰论碑之“体要”,认为其序文的风格应该类似史传,平实真切;正文应如铭文一样,义理宏深,言辞润洁,要在整体上把碑主的高风亮节呈现出来,以见其雄伟英烈。碑文写作的要点在于,“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1}如果不沿着“宏深”来行文势,那么所写的就不是碑文了。宋濂撰此碑文时,充分注意到写作中的“体要”。其序文首先叙述了黄溍的人文素养与化成天下的宏大功绩,有谓“轧摩日月,扶植鸿化,以震荡乎一世”之功。{2}其次写县侯胡惟信为黄溍立碑之事,描绘了邦里群彦共同祭祀的庄重场面。他写道,“侯具牲酒,盛服致祭”,众人“精诚格孚,契乎冲漠”;“祭毕而燕,笾豆静嘉,肴核维旅,鸿休诞昭,秩秩雝雝”。③县侯盛服致祭,说明官方对此事的重视,场面也相当隆重庄严。而祭毕之后的燕享,又无不井然有序。这样的叙述,照应着碑主的宏大功绩,是文章写作的得体之处。正文是一组七言诗,此诗以凝重的鼻音效果表现出一种回环、和谐的声韵之美,为一句一韵,类似曹丕的《燕歌行》,从而使这种凝重感贯穿全篇,为烘托碑主的功德打造声势。宋濂在诗歌中营构了两组意象:一组是来自大自然的高洁之物,如大星、日月、太清、雨露。另外一组是想象中的神圣灵物,如蛟龙、丹凤、幽灵、玄麟等。他将自然界的高洁之物与冥灵界的神圣之象拼接在一起进行歌赞,不仅增强了文辞的浪漫色彩,也使人对碑主的人格与功德肃然起敬。语音的凝重,意象的神圣,形成一种“宏深”之势,遂得碑文之要。
相比之下,宋濂为黄溍写的行状就没有碑文的凝重声势与溢美之辞,而显得较为平实、谨严。行状,按刘勰所说:“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4}徐师曾进一步阐述说:“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5}由此可知,行状以史笔行篇,其用或拟谥好,或录史书,或作碑表。总之,它是一篇由“门生故吏”记述死者生平的传记材料,真实性是不言而喻的。宋濂这篇行状写得洋洋洒洒,篇幅很长,大体可归纳为世系、生平、政绩、学问、出处等几个方面。世系、生平是行状文体最基本的要素,其它方面则因人而异。具体到黄溍,宋濂重点描述他的气节、学识与出处,这几点都体现出浙东学派的基本学统。元代婺州是浙东学派的一个重要区域,黄溍的学术宗旨体现着宋代以来该区域文道结合的事功传统。宋濂从气节、学识、出处上结构文章,显示了他敏锐的写作眼光。其文论黄溍事功“掌述帝制,劝讲经帷,嶷然独任”;论文章“天下学士咸所师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燿铿鍧,直与汉、唐侔盛”;论出处“其难进易退之风,真足以廉顽而立懦”。⑥这些评论就事而论,文随其实,黄溍或以致君仁政而出,或以尽善孝道而退,出处大义,鲜明可见。这种平实的叙述风格,有理有据,谨严得体。后来危素在给黄溍撰写神道碑时,就利用了这篇行状所提供的基本史料。由此可见,行状文体的撰写有其重要的实用价值。
第三篇是针对黄溍文集而写的序,它以议论的笔法呈现出“辩丽”的体貌特征。这篇序文重点论述黄溍文章得其“神”助。什么是“神”?宋濂开篇点题:“神者也,形之而弗竭,用之而弥彰。”{7}然后他从“形之弗竭”与“用之弥彰”两个角度来论述黄溍文章之“神”。首先,文推三代,六艺而兴,其文各有特点。三代而下,诸家之言又不曾因袭,而得“神”之变化之要,谓“形之弗竭”。自宝庆以后,文弊滋极,文人相互模拟而缺乏新意,故失文章之“神”。元大德年间,群士革伪趋真,到黄溍而文章极盛。这一层面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黄溍文章与三代之文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其次,就婺州的学统而言,黄溍的文章写作有着鲜明的事功倾向,宋濂说:“出用于时,则由进士第教成均,典儒台,直禁林,侍讲经帷,以文字为职业者殆三十年。”{1}这一层面从横向角度证明了黄溍文章的“用之弥彰”。如果说黄溍之文筑基于三代是在描述一种宗经观念,那么其文用于当下,则体现出浙东宗经与传道并重的学术理念。因此,宋濂在解释文章之所以“神”的原因上就要突出“学问”的意义。他指出:“师群经”、“友迁、固”故而得之。学“三代之文”,得人文之养,而后得之。宋濂的这种论证方式,前后衔接,纵横交错,非常符合“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的议论风格,是其“辩”格的体现。在修辞上,宋濂引譬喻、排比为文添彩造势,是其“丽”格的体现。其言:“三代以下,诸家言虽不能经,亦各以学鸣,龙门则异于河汾,河汾则异于昌黎,昌黎则异于庐陵,庐陵则异于伊洛。”又云:“蹄涔之水,其流不能寻尺;通江绝海,则涵浴日月,一朝而千变。土鼓之声,其闻不及百戍;迅风惊霆,则震撼万物,冲纵高庳,无幽而不被。无此他,神于不神也。”{2}这种文采与气势既使文章明朗有秩,又具有震撼与折服的魅力。
第四篇为一篇跋文。徐师曾说:“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③关于题跋文体,朱迎平先生曾以宋代为例,将其分为学术类题跋与文学类题跋,并认为,文学类题跋是题跋文发展中衍生出的变体,这类题跋与载体联系较为松散,载体在文中往往只是一种触媒,其主旨在于抒发作者性情。文学类题跋实际上已演变成一种新的随笔小品文体。{4}宋濂这篇关于黄溍书迹的题跋正是沿着宋代抒情的传统而来。其跋文写于黄溍亡后,因此,文章自然饱含着对老师的怀念,而以深情感人。文辞简约而有风力。其感人处首先在于以父待师,他说:“自古师弟子间,不翅亲父子然。传所谓‘父生之,师教之,其义诚一也。”以亲情拟友情,以激生文势,使其真挚情感得以呈现。其次,以感兴起笔,最为动人,如其言曰:“父没而手泽存焉,子或见之,则泣下沾襟。父师一也,孰谓为弟子者,有不然者乎?”{5}以亲情比拟起势,以人事感慨助势,师生真情于笔端处淙淙奔涌而来。再如《题黄文献公所书先府君行实后》、《跋〈张孟兼文稿序〉后》、《跋柳先生〈上京纪行诗〉后》莫不如此。
作为宋濂的老师,黄溍在元中期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宋濂在文章观念上大多继承了黄溍的文学思想。从碑文、行状,到文集序、序跋等文章的撰写,那种中正典雅的文风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也是浙东学派一贯的行文风格。
二、夹叙夹议:“序”文体的不同体貌
“序”文之体制,吕祖谦说:“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⑥徐师曾说:“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又谓之大序,则对小序而言也。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7}大体而言,文集序多为议论体,燕集赠序多为叙事体,但在实际创作中以二体的综合更为常见。宋濂的序文就呈现出此种特征。
《御赐甘露浆诗序》记载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于武楼便阁召见宋濂、陈宁二人,并与之共饮甘露浆的事件。事后宋濂有诗歌颂圣,众臣从和而成诗卷,故有此序。无疑,这篇序文的写作与皇上深有关联。皇帝乃天下之主,故而此篇序文的言辞丝毫不敢有轻佻之语,写得典雅庄重。如写煮甘露一段,从中贵人取膏露呈见于众,到用金杓炼水,以火烧水,再到皇上亲自启罂以投,调制甘露,整个过程写得有条不紊,不瘟不火。皇上赐饮二人甘露浆自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对此宋濂以雅驯之辞,表达了对圣德的颂扬,他说:“臣濂伏闻王者有德,上通于天,嘉气协应,鸿羡滋播。今甘露频降,大和坱圠,民物敉宁,洽于大康。是皆一人有庆,使臣庶永有攸赖。”{1}
再看《送赵待制致仕还乡诗序》一文,这是一篇写给同僚的诗序。赵待制是赵本初,洪武九年(1376)致仕,众友人有诗赠别,宋濂序其文。作为同侍皇上多年的臣僚,宋濂以得圣上之恩宠而鼓舞好友此去不要忘记圣恩,以忠孝宣导上德。言辞恳切,犹有自勉之意。他说:“先生之归也,见乡之子弟,导宣上德,俾习为孝弟忠信之行,出为时用,是亦报国之一端。若区区效贺季真,盘旋于鉴湖一曲间,自逸之计则得矣,岂士君子之所望哉?”{2}相较于上一篇,风格则大相径庭,因为序文对象发生了变化,语气言辞当然要有区别,这正是宋濂文章的得体之处。
同为鼓舞之辞,他对同僚好友的劝勉与对青年才俊的劝勉也有所不同。例如,《送东阳马生序》是宋濂写给东阳马君则的一篇赠序。当时,马君则正在太学学习,其才气横溢为时辈所称赞。宋濂朝京时,马君则撰长书以乡人之子拜访宋濂。对于这样一位积极于求知的后学俊才,宋濂无不感到欢心。因此他写这篇序文时,语气和蔼可亲,娓娓道来,充满了对晚学的劝勉与奖掖之情,成为后世劝学的一篇佳作。全文围绕“劝学”一词来写,现身说法,言辞平和,极富感染力与说服力。以宋濂幼时借书苦读,严冬不辍的经历最为感人,可谓开篇以势夺人,以求学之艰苦震撼人心。其次他从问学先达来写求学之勤奋,但其间甘苦是一以贯之的。他说自己问学时一旦遭到老师叱咄,便“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但等到老师高兴的时候,他又开始请教,如此反反复复,“卒获有所闻”。在这里,宋濂以冒雪求学,衣着朴素两个细节,表现出自得其乐,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而文章的最后一层正是以此种精神来劝勉后学的,他说今天的学生既无冻馁之患,又无奔走之劳,有书可读,问师必答,然“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③这种求学精神自古而然,宋濂以此激励后学,可见其修养之深。因此,此篇以真挚胜,既不同于赠序同僚的恳切,亦不同于序文圣德的典雅,它俨然有着自己的风格。
“序”作为一种文体,因不同的写作对象,而有不同的行文尺度。在送别序文中,叙述性的文字要多一些,它要述及与送别对象的诸种人事关系等等。至于文辞语气的轻重,还要看送别对象是长辈还是同辈、晚辈,因人而异。在诗文序中,宋濂《御赐甘露浆诗序》夹叙夹议的笔法,写得温柔敦厚,毕恭毕敬,因为他的言说对象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再如《应制冬日诗序》也是一篇类似的文章。而在上面所论及的师辈黄溍的文集序,我们可以看到宋濂议论笔法的精妙之处。实际上,在宋濂的很多序文中,要以议论诗文的题材更为精彩,例如《汪右丞诗集序》、《詹学士文集序》、《刘彦昺诗集序》、《华川文派录序》等等。这里讨论宋濂序文夹叙夹议的特征,重点阐述其文章写作的得体之处。
三、文风巧变:不同文体间的体貌变化
对于不同文体,不同对象而言,文章风貌的变化更为明显。比如宋濂在明初北伐战争中撰写的《谕中原檄》,其文刚健,气势迅猛,犹见风骨。先看檄文之体,檄文即军书,《说文》云:“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以号召;若有急则插鸡羽而遣之,故谓之羽檄,言如飞之急也。”{4}刘勰论檄文之要说:“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本源于用兵前誓师用的言辞,所谓“三王誓师,宣训我众,未及敌人也”。到春秋战国时,又增加了针对敌方的内容,故刘勰说:“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5}宋濂的这篇檄文兼而有之。其题为《谕中原檄》,所针对的对象是中原地区的士人与百姓,当然也有蒙元贵族,但以汉族居多。作为告谕汉族同胞的宣言书,其文的民族主义鼓动性是非常强烈的,如“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一语的提出,后来就成为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进而推翻封建帝制的重要口号。檄文开篇先明此意,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也。”{1}可谓事理昭然。然后以中华礼义之大防,辩说元朝社会之弊,所谓君者沉荒失道,臣者废坏纲常,朝廷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世间人伦更是大乱。言辞端直,义理中正,以骨力振作人心。因此,“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古训,才有可能为中原同胞慨然接受。接着,宋濂的笔锋转向对敌方的苛责,以其数典忘祖,假公济私,相互矜伐为要,指责其非为华夏之主,实为生民之巨害。这是一层。另一层是对己方美善清明的陈述,一是历数十三年的征战之功,以“奄及南方,尽为我有”为第一功绩;二是以兵精粮足,北逐群虏,拯救生民,恢复汉官威仪为第一目标;三是以严肃军纪,与民秋毫不犯为第一承诺。此三点并总群势,以明我方为济世安民者。前后对敌我双方的权衡利弊,人事审查,辞断而气盛,有犄角之势,迅猛之威。正如刘勰所说:“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2}这篇文字篇幅不长,却足见其刚健之力,当然也因此取得了它的历史功绩。③
与此文章风格形成反差的是宋濂的《蒋季高哀辞》。哀辞一体源自汉武帝,经过魏晋发展而定型,刘勰论其要曰:“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4}唐宋以来,韩、柳之作,或称诔辞,或曰哀辞,自曾巩、苏轼而统谓之哀辞。吴纳辩其体曰:“大抵诔则多叙世业,故今率仿魏晋,以四言为句;哀辞则寓伤悼之情,而有长短句及楚体不同。”{5}刘勰论诔辞之要说:“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悽焉如可伤。”⑥可见,虽然二者在情感基调上较为接近,但诔辞以颂扬为主,哀辞却以伤悼为胜,这个伤悼集中体现在“爱惜”一词上,宋濂这篇哀辞即是如此。他主要从德行、好学、才气三个方面构思文章,以突出失去蒋季高这个畏友的可惜。写德行曰:“季高恂恂儒者,非其道弗言也,非其道弗为也。言其事亲,则孝而恭;处伯仲,则穆而和;交朋友,则信而贞;遇族姻,则惇而庄;接闾党,则惠而慈。”{7}此处以失去美德之才而哀痛。又回忆与其初次见面的情景,可爱好学的季高给宋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时季高尚未冠,即能执经问难,进退雍容,肌肉若玉雪可爱。”{8}这一层以失去颖悟之才而伤痛。第三个方面写共侍黄溍时的同门之谊,这一次宋濂描写了一个出言雅驯、才华横溢的彬彬君子。黄门时的这段交往,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样一位青年才俊,深得宋濂敬畏,假以时日,其前途不可估量。而蒋季高英年早逝,不得不令人痛心。三个方面的描写,爱惜之中句句含悲。哀辞中又有伤痛之语:“岁几何,既哭其父,今又哭季高焉,则夫人世如传舍者,可不信乎!呜呼,悲乎!”{9}“呜呼,悲乎!”在文章反复出现,使得全文笼罩在一篇凄冷氛围中。尤其是哀辞一句一叹,音声回环不绝,情感似断非断,文情怊怅,恰如风云一般卷泪而至。如果说《谕中原檄》以刚健胜,那么这篇哀辞便以柔婉显,一刚一柔,写来从容得体。宋濂的好友王祎也写过一篇《祭蒋季高文》的文章,相比较而言,其文才气十足,不尽得体。虽然他在文中也不止一次的“呜呼季高”,也述其道德与才学,但文章几乎一半篇幅在谈“材”与“年”的关系问题,突出其“学行俱懿”,“没世有闻”,进而表达对好友虽死犹生的怀念。{1}其文哀痛不足,论辩有余,与宋濂文章的得体处稍有差异。
介于两种风格之间的文章写作,要属宋濂雍容典雅的颂圣之作了,或称为“台阁”体。例如《阅江楼记》,此记是奉朱元璋之命撰写的,旨在“便筹谋以安民,壮京师以镇遐迩”。面对圣命,其文辞固然要雅驯不佻,但讽谏之意又不能过于直白,因此“主文谲谏”成为此文一大特点,即寓讽谏于颂扬之中,寄劝勉于议论之间。“记”之为体一般为记事,但常常夹杂议论,至欧、苏之后,才有了专以议论为“记”的作家。宋濂的这篇“记”便以议论为主。全文以天下统一,广议君臣如何居安思危,思治报国。开篇以昂扬之势,将一股开国时的硕大情怀凸显出来,他自豪地说:“由是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道同体,虽一豫一游,亦思为天下后世法。”面临这种历史际遇,君该如何做?宋濂以登临思治展开了委婉的讽谏,说:“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其崇椒,凭栏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2}他从保土、安边、恤民三个方面进行陈说,言辞文雅,循循善诱:见城池之高,关阨之严而思疆域之完整;见蕃舶来庭,蛮琛入贡而思四边之安危;见耕人之苦,农女之勤而思万民之安抚。此一层是对君主言说,君主登临兴怀,不是贪图享乐,而是居安思危,这是迎合圣意而又出于含蓄之笔,可见宋濂为文之用心。另一层便是作为臣子的登临感怀。古人登临之作,常常缅怀今古,慨叹人事变迁,其情往往伤于哀思。作为儒者之文,其辞应该表现出中正之貌。宋濂刚要缅怀金陵往昔,便戛然而止,急笔转入鼓舞勉励之辞,说:“逢掖之士,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帝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③这正体现出儒者的修养。登临而思己任,忠君而报效国家,其意无不深合君主之意。全文借登临而沉思义理,行之以文,讽之以隐,构思巧妙,结言典雅,义理中正,足见其儒者气象与雍容风度。颂圣之作是宋濂入明后的一大手笔,他的《銮坡集》与《翰苑集》中保存了大量的“台阁”体作品,例如《天降甘露颂》、《龙马赞》、《恭题御笔后》、《见山楼记》、《恭题御赐文集后》等等。宋濂的颂圣之作,与他入明后的儒者期待有着很大的关联,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明初文坛的代表性地位。
从总体上看,宋濂的文章写作,或宏深、或平实、或辩丽,或典雅、或刚健、或哀婉,其体貌呈现出“巧变”特征。但这并不表示其文章观就是在追求辞章之美,在“文用”层面上,宋濂的文章写作有着鲜明的目的性。他为黄溍撰写的各种文章,一方面在于纪念业师的人品言行,以励后学;另一方面也有意“扶植鸿化”,以道德事功教化世人。其文章观正是建立在道德与事功基础之上,以达于用为核心的。但从辞章的层面上看,宋濂的文章就不仅仅在于说教,他同时还强调文气与文辞的表现,故文章可以因此而具有文学特征。尽管宋濂文章以“用”为核心,但绝不乏审美色彩。在实用中讲究文辞之美与感人之气,这正是宋濂最为鲜明的文章观念。
【责任编辑 王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