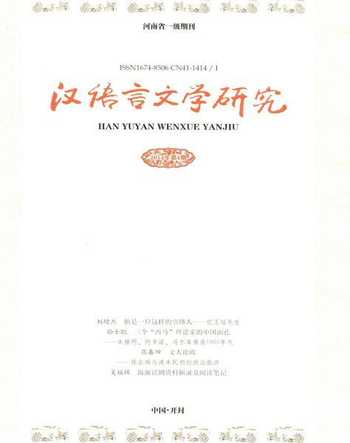论邵洵美编辑实践中的唯美主义倾向
费冬梅
摘 要:邵洵美在上海文坛虽以唯美诗人闻名,但由于出版诗集受阻,自己的唯美主义艺术理念也难以广泛传播,邵洵美便开始独立出版期刊以期解决这一难题。与此同时,他将唯美主义主张渗入到出版领域,这些理念具体体现在他主编的两本唯美主义期刊(《狮吼》半月刊复活号和《金屋月刊》)上,以此为阵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以邵洵美为核心的唯美主义群体。本文将从期刊编辑实践这一层面对邵洵美的唯美主义实践作一分析{1}。
关键词:邵洵美;《金屋月刊》;唯美主义实践
中国的“《黄面志》”和“《萨伏依》”
1925年,邵洵美在刘海粟做东的宴席上结识“狮吼社”{2}主将滕固,两人相谈甚欢③,从此邵洵美便加入狮吼社。邵洵美的作品最早出现在1925年8月的《狮吼社同人丛著》第1辑《屠苏》上。而后邵洵美于1927年开始相继主编了《狮吼》月刊、《狮吼》半月刊复活号以及《金屋月刊》。《狮吼》月刊的创办标志着“狮吼社”从以滕固为核心的早期阶段向以邵洵美为核心的后期阶段转变。后期的“狮吼社”以唯美主义作品的译介及创作、讲究形式美的杂志设计等诸多手段,形成了以邵洵美为核心的唯美主义文学团体。邵洵美以有产者的慷慨大方、亲切友善的性格,赢得了诸多同人的拥护。“狮吼社”的活动组织由最初的滕固、章克标、方光焘等人转为以邵洵美一人为核心。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刊物的撰稿人的改变上,也体现在杂志的趣味的潜移默化的转移上——由最初的偏重日本唯美主义向后期的偏于英法唯美主义转变,而标志性的事件便是《狮吼》半月刊复活号和《金屋月刊》的创办。
《狮吼》半月刊复活号和《金屋月刊》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借鉴了英国的两份唯美主义杂志《黄面志》(The Yellow Book)和《萨伏依》(Savoy)。《黄面志》的封面和插图由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绘制,文字方面的撰稿人有乔治·摩尔(George Moore)、道生(Earnest Dawson)、西蒙斯(Arthur Symons)等人,这份期刊的灵魂人物则是比亚兹莱。比亚兹莱以优美清晰的线条、强烈对比的黑白色块绘制了大量充满邪恶、颓废和色情气息的插图。这些插图如此著名,以至于因为王尔德被捕时身上携带一本《黄面志》,而使比亚兹莱受到了牵连,并最终从这份期刊中退出。而后,在出版商的支持下,比亚兹莱和西蒙斯一起又创办了《萨伏依》,在撰稿和编辑方针上《萨伏依》延续了《黄面志》的风格。
邵洵美在主持《狮吼》半月刊复活号和《金屋月刊》这两个刊物期间,发表了大量翻译或介绍“黄面志”、“萨伏依”作家群的作品。这些文章有:朱维基译的道生的小说《勃丽旦尼的苹果花》{1},比亚兹莱唯美主义风格的诗与画《理发师》{2},介绍摩尔纯诗理论的《纯粹的诗》③,描写一位有夫之妇私情的短篇小说《信》(Letters){4},摩尔《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Memories of My Dead Life)一书中的几个片断{5},小说《和尚情史》⑥和《George Moore》{7}等等。在编辑方针上,邵洵美也向《萨伏依》学习,在《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7期,邵洵美特意写了一篇《Savoy杂志的编辑者言》,介绍《萨伏依》杂志的编辑方针,并说“我们极愿也能达到他(《编辑者言》)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这主要体现在对其封面以及插图风格的模仿。
作为英国颓废主义的经典期刊,《黄面志》的封面和装帧设计相当考究,采用华丽醒目的黄色硬包装,看起来很像一本书。《金屋月刊》的命名和封面设计便是直接来源于《黄面志》。《金屋月刊》封面颜色模仿《黄面志》,在设计上于继承中又有所创新,去掉了《黄面志》封面上方的绘图,采用纯金黄色,以对比鲜明的黑体字交代刊名以及编者和卷期,显得简洁大方,高贵典雅{8}。据章克标对《金屋月刊》的回忆,“名字是洵美取的,我觉得过于富贵气了,不大合适,但在他可能是十分惬意的。英国有一种黄封面的刊物,就被叫成黄书,是唯美主义者的著名刊物,洵美的意思可能也想在中国来个唯美派的宣传,想把这个刊物作为中心,因而要袭用‘黄书这个名字,为适应中国用语情况,把黄改作了金字,又由金字想到‘金屋(因书店总有个店屋),就定了金屋书店这个名称”{9}。《金屋月刊》在二三十年代以封面闻名,被时人戏为“进香袋”,这个封面形式的选取正表示了邵洵美的艺术审美趋向。
《金屋月刊》第1卷第8期The Yellow Book第1期封面
章克标回忆,《金屋月刊》主要负责人其实是邵洵美一人:“《金屋》月刊的封面上,大书着‘邵洵美·章克标编辑,编《金屋》月刊每月一册,相当辛苦。实在因为撰稿同人不多,有点稿荒的样子。那时投稿的人也不多,外稿既少就难得有可以采用的了。洵美是主要的编辑人,我只帮帮校对,跑跑印刷所罢了。但有时也不得不勉力作文以凑足篇幅。洵美有时去联系好写稿人,以为确有把握的了,却常常到了要发稿还只字未写,所以刊物难以准时出版,常常脱期,这样就显得疲沓,没有精神了。这本月刊销路也不大好,印二千本常卖不完。”{1}稿源有限和出版不及时导致的这种销售的惨淡光景在杂志的“金屋谈话”专栏里也被屡屡提及,这是其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由此我们不难得出《金屋月刊》的“私人”性质——即这是邵洵美独立支撑的一本杂志,不仅撰稿同人不多,连编辑章克标也只是打下手跑腿的角色。这种为宣扬自身文艺理念和主要发表自家作品而编辑、出版刊物的形式在现代文学史上还不多见{2},也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邵洵美从事唯美主义实践的决心和苦心孤诣。
而在插图的选择上邵洵美尤其重视,在他的编辑理念里,插图和期刊本身联系密切,在风格上该保持一致。他选用的插图大多和唯美主义相关,有的是英法唯美主义诗人或画家的肖像,有的是唯美主义风格的画作。《狮吼》月刊第一期共采用了五幅插图,有置于目录前的,有在文章开头的,分别是散发裸身女子像、Sphinx人面狮身像、画家常玉作的裸体女人素描《NU》,以及插画《竖琴》、《眼泪》,另外还有一张唯美诗人史文朋的肖像画。在本期《编后记》中邵洵美特别提到了这期的封面和插图:
不过对于这期的封面和插图,我却要说几句。封面是江小鹣君制的木刻,这类的木刻,欧洲现在极得时,小鹣曾在法国研究多时,在本国这样的作品是少见的。还有一张插图是常玉君画的,他的素描以线条所表现的情致的丰富是早经艺术界所称许的了。他今年又到法国去继续研究,这张便是他送给我和佩玉作为纪念的。插图Sphinx是Franz Stuck氏画的,他是德国近代的大画家,他在一八六三年生于Pvaria的Tettenwise。他最初的得名,是因了他为Fliegende Blatter所画的插图。一八八九年他便开始研究油画。他的第一张出品《天堂的护神》,便是一张可以使他不朽的杰作。他的画大半取材于神话,最有名的《罪恶》、《战争》、《斯芬克斯》、《诱惑》等,将来有机会,再当在本刊刊出。③
从引文可知,邵洵美在本期插图的选用上对法国和德国流行画家很是在意,也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流行的艺术流派比较熟悉,邵洵美有意选用这些插图,正和他平日对英法唯美主义的喜好一脉相承。
《狮吼》半月刊复活号上的插图则多为卢世侯的黑白线条画,这些作品计有:为邵文《歌》配画、《迷》、《朋友的死》、《甜蜜的思想》、《诗人》。此外,还刊载过唯美诗人罗瑟蒂的自画像,A Beardsley的《梳装》{4},另外,还有为黄中《三角恋爱》的小说广告文所配插图,以及章克标的长篇小说《银蛇》的广告文配图。
卢世侯的作品很有比亚兹莱的感觉,也喜用黑白两色表达“爱”、“美”与“死亡”等主题,邵洵美评价“他可以用一种黑色来表示世界上一切的颜色”。卢世侯的作品擅用黑白色块和曲线条,他尤其喜欢以白色来表现裸体,并让其置身于浓郁的黑暗背景之中,给人以颓废的美感。比如《迷》,画中一个长发裸体女子仰面躺着,视线似与她右上方树枝上的猫头鹰相接,反复而交错纠葛的线条绘出了夜晚阴森的树木的轮廓,而与女子、猫头鹰构成一个平面的诸多环形曲线似水波一样由远方蜿蜒而来,是女子迷乱的情欲,抑或是对这夜色迷蒙的诸多幻想?画面总体布局像是装潢用的贴墙纸,人物、风景安排在一个没有深度的空间里;而《朋友的死》{1}更具代表性,此图似乎有点模仿埃弗雷特·米莱名作《奥菲莉娅》的感觉,画面中一个女子仰面合目躺在黑色缠绕的曲线条勾勒的棉被的包围之中,整个人只露出一张小小的雪白的脸和裸露的肩,眉毛、眼睛以及头发都和身边的黑暗融为一体,却更显得她白的触目。她的朋友跪在一侧,身体前倾,也是用白线条勾勒出的一个裸体形象,在他身后有一根高高的烛台,滴着蜡泪,而画面上方那些环绕的白色曲线似乎是正在奏着的升入天堂的音乐,那突兀地绕过画面的粗白线条则带着神秘而又鬼魅的感觉——这些画很明显受到先拉斐尔派以及比亚兹莱的影响,显示了《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的唯美、颓废的特色,也可以说是邵洵美唯美主义编辑理念的具体体现。
卢世侯《迷》 卢世侯《朋友的死》
值得一提的是,《狮吼》半月刊复活号上邵洵美选用了两幅与“蛇”有关的图画:《银蛇》广告图和《甜蜜的思想》。前者“蛇”蛰伏于花丛之中,后者“蛇”潜伏在人的眉梢之上。邵洵美对蛇极有好感,据他自己在散文中的陈述,他从小便与蛇有奇妙的缘分,他说自己看见蛇油滑而光嫩的身子时,“立刻会感觉到我的身子也变成一样的油滑光嫩,便是四周围的一切,怕是石头、铁、荆棘,也会变成一样的油滑光嫩,那种软,那种温柔,那种活泼,那种镇静与敏疾,实在太舒服了”{2},从这里似乎也看得出邵洵美的诗歌《蛇》的渊源,可以说,这两幅插图的选用和他写作诗歌《蛇》一样,都是出于一种独特的唯美、颓废的审美趣味。
章克标小说《银蛇》广告图 卢世侯《甜蜜的思想》
至于邵洵美翻译的比亚兹莱的诗《理发师》和配画③(邵误作《梳装》)则更为明显地模仿了《萨伏依》的风格。比亚兹莱的这幅画最先发表在《萨伏依》第三期,是比亚兹莱为自己的诗歌《理发师歌谣》所作的插图。这首诗讲了一个令人心灵颤抖的美丽而恐怖的故事。理发师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十三岁的公主,这公主的美貌让他觉得迷狂,痴愚而无力,最后他决心用破碎的香水瓶割断公主的脖颈,亲手毁灭了让他发狂的美而宁愿平静地接受死亡。这个故事和为了亲吻所爱者约翰而不惜割掉他头颅的莎乐美非常接近,邵洵美翻译这首诗并专门配了插图,可说是对比亚兹莱推崇备至。总之,无论编辑方针还是期刊内容,邵洵美主编的《狮吼》半月刊复活号和《金屋月刊》都可说是《黄面志》和《萨伏依》在东方的回音,可说是中国的“《黄面志》”和“《萨伏依》”。
比亚兹莱画作《理发师》
颠倒的经济逻辑
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论及文学场:“这个相对自主的空间(也就是说,同时显然是一个相对依赖的空间,尤其是依赖经济场和政治场)让位给一种颠倒的经济,这种经济以它特有的逻辑,建立在象征性财富的本质上,象征性财富是具有两面性即商品和意义的现实,其特有的象征价值和商品价值是相对独立的。”{1}在此基础上,布迪厄提出了文学场的两套经济逻辑,即“在一个极点上,纯艺术的反‘经济的经济建立在必然承认不计利害的价值、否定‘经济(‘商业)和(短期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赋予源于一种自主历史的生产和特定的需要以特权;这种生产从长远来看,除了自己产生的要求之外不承认别的要求,它朝积累象征资本的方向发展。象征资本开始不被承认,继而得到承认、并且合法化,最后变成了真正的‘经济资本,从长远来看,它能够在某些条件下提供‘经济利益。在另一个极点上,是文学和艺术产业的‘经济逻辑,文学艺术产业将文化财富的交易与其他交易一视同仁,看重的是传播,以及由发行量衡量的直接的和暂时的成功,满足于根据顾客先生的需要进行调整(尽管如此,这些机构与场的所属关系仍通过下面这个事实表现出来,即这些机构要想兼有一般经济机构的经济利益和保证知识机构的象征利益,只能拒绝唯利是图的最粗俗的形式,避免全部公开他们的有关目的)”{2}。
在邵洵美那里,经营书店、杂志,正是一种基于对纯艺术追求的“反经济”的经济策略,即布迪厄所说的第一种“颠倒的经济逻辑”,不计利害,不顾短期利益的回报,对体现自己文艺观和发表自己作品的杂志投入极大热情,因此常常亏本。他做生意亦像是作诗,目的在抒情,却不在乎家产的流失,为办出版“衣带渐宽终不悔”。从短期来看,这种个人化倾向极浓的杂志,除了自己的要求之外,不大考虑读者,但是它却逐渐朝着积累象征资本的方向发展。对于邵洵美而言,他的收获便是逐步制造出了一种声名,一个有名的不乏赞誉色彩的名字,循此发展,邵洵美由最初的不被文坛承认,到逐渐得到同人乃至文学圈子的认可,一步一步使得自己的作家身份得到确认,也使长远的经济资本的获取成为可能。
《金屋月刊》的广告在这个意义上是个值得关注的领地。和同时代其他杂志注重赢利不同,《金屋月刊》注重艺术审美而不太关心商业利益,刊物上没有商业广告,仅有的是金屋书店将出和已出的书目广告,偶尔还会有一些为《苦茶》杂志、《真美善》杂志登的书目以及广告,以及对同人的作品作简短的推介。这些广告在刊物内多有重复,占用了相当大的版面。而那些商业期刊却通常是利用这些版面来做商业广告,明码标价。《金屋月刊》对“非盈利性”的重视还体现在它对文稿的体裁选择上。通常来说,连载小说最容易赢得读者兴趣并从中获利。而且由于主题的通俗,情节的曲折变换,长篇小说比其他文学体裁需要更多地接触大众,得到大众认可,也反过来从大众读者那里获得经济利益。而报刊杂志为了赢利,也往往连载长篇通俗小说以吸引读者,增加发行量。《金屋月刊》是怎么做的呢?《金屋月刊》刊登的作品体裁主要有诗歌、短篇小说、文论、散文。其中诗歌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文论以及短篇小说。在前三期,《金屋月刊》曾刊载了郭有守翻译的哈代的长篇小说《无名的裘特》,但是连载至第三期就结束了,原因在于一封读者来信提议:“勿登长篇小说的译作,因为月刊刊登长篇小说他最大的目的,(恕我如此说),是在引诱读者续购下期……”{1},对此意见,邵洵美欣然采纳,答复道:“《无名的裘特》不再继续登下去,将来出单行本。”{2}以后《金屋月刊》便极少刊登长篇小说,即使有,也尽量在一两期内登完以致占了相当多的页面。
由此可知,邵洵美极力想摆脱为经济利益而出版的印象,那么邵洵美又为何要这么做?除了他本人资产丰厚以及上述分析的企图获取象征资本的因素,笔者认为,邵洵美作为唯美主义诗人的个人性情以及文学品味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在艺术理念上,邵洵美此时期坚持的精英品味和纯文学理念与走大众文学路线的左翼作家南辕北辙。与“革命文学”以普通大众为主要阅读对象不同,他对大众的态度是带着些微矛盾心理的。在消费社会中,销量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和价值的大小紧密相连。作家一旦和市场建立了联系,作品的销量、读者的多少都将在有意无意间制约着作者对大众的态度。邵洵美这个小群体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他们的文艺主张与革命文学的服务于政治以及通俗文学的服务于市场不同,邵洵美一直主张“唯美”、“为艺术而艺术”,讲究艺术的纯粹性,但明显的事实是,“输者为赢”的经营策略事实上已经是对经济资本做了秘密的妥协。
对邵洵美来说,他是其构建的艺术空间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身份在两个角色上轮换,一面是艺术家中的资产者,一面又是资产者中的艺术家。这是其身份特殊性所在。邵洵美的经商也贯彻了这一潜规则,他先是作为艺术商人存在,然后才是商人。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邵洵美要取得文学事业的成功,最快也是最好的途径便是通过艺术和金钱之间的运作,在获取文学事业成功的同时也在商业上盈利。而这双重身份的融合,使得邵洵美呈现出了不可消弭的矛盾。一方面是不计利害的艺术家的思维逻辑,这种艺术逻辑使得他仗义疏财,坚持为艺术而艺术,办刊“但求美观不计工本”,这使邵在当年的文坛环境下获得了大量赞誉,被称为文坛“孟尝君”;而另一面,作为贵族子弟,作为书店老板,杂志投资人,邵洵美对自身的商人身份不可能没有自我认知。在杂志编辑与书店老板之间转换身份的邵洵美,犹如《伊索寓言》里的那只取巧的蝙蝠,在艺术家群体中,他更多的是以资产者的身份被大家认同和尊崇,而在资产者的圈子里,他又以艺术家的身份而鹤立鸡群。邵洵美在这两种既态度鲜明却又犹疑不定的身份里徘徊,呈现出了一种暧昧的不确定性。在《金屋月刊》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两种态度的纠缠杂糅。一面是很无奈的感慨销量不佳,一面却又对读者的批评建议大都不予采纳,依然故我。
邵洵美本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与他人的理解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在诗歌《你以为我是什么人》里他对自己做了这样的剖白: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
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
你错了,你全错了,
我是个天生的诗人……③
邵洵美在这里把自己定位在纯粹的艺术家即“诗人”这个位置上,说自己“爱金子为了她烁烂的色彩”,“爱珠子为了她晶亮的光芒”,而在同时代人也是邵的朋友章克标眼中,他又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章克标对邵洵美做过这样一番评价:
我觉得洵美一个人有三个人格,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他一生在这三个人格中穿梭往来,盘回反复,非常忙碌,又有调和……这三个人格得以调和与开展,主要依靠金钱资财。大少爷要挥霍结交,非钱不行;办出版事业、开店当然需要资本,而且未必一定会赚钱,赔了本时,还得把钱补充、追加进去;做诗人似乎可以不要钱了,古时贫苦而闻名天下的诗人很多,但现代社会,做诗人要结社集会,要出刊物,印集子,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到处都得花钱。所以钱是最为必须的一种基础,基本的根基,有了钱才可以各方面有展布。{1}
在章克标眼里,邵洵美虽然同时占据着三个身份,但最根本的却是“大少爷”这一角色,如果失去了这一角色,那别的身份也将不再理所当然。章克标指出,邵洵美之所以能够协调三个身份,主要的是因为其拥有丰厚的资财。这便将邵洵美的文学艺术活动的“根基”剥落出来,相对邵洵美对自身艺术身份的推重而言,章克标这个“无产者”从自身角度对其进行观照,揭示出了更为深刻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发现了邵洵美身份的尴尬,发现了其自我认同与他人认知之间的罅隙所在。
【责任编辑 孙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