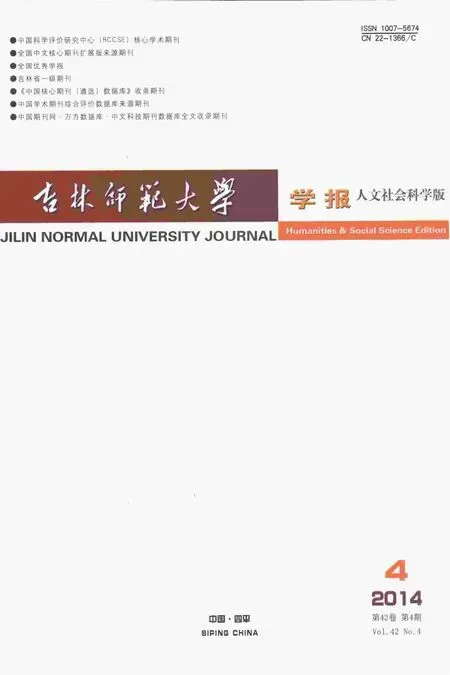先秦“蜡祭”考论
李强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2)
先秦“蜡祭”考论
李强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2)
蜡祭是古代农业祭祀一种,在每年的岁终举行,祭祀对象是“八神”,目的是为了感谢对农业生产有贡献和帮助的神灵,属“报祭”。本文通过整理传世文献中的内容来说明蜡祭“八神”中的“昆虫”是指蚕一类的有益昆虫,并试析蜡祭与腊祭是分属两种不同的祭祀,而蜡祭包括腊祭,两者从秦汉时期开始趋向模糊。
蜡祭;腊祭;蜡八
先秦时期的农业祭祀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这在《周礼》、《礼记》等先秦典籍中皆有所体现。而蜡祭就是其中一项。它表现了国家和民间对于农神和四方万物赐予丰收的感激之情,同时也体现了农业生产在国家统治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对于先秦时期蜡祭的问题已有所讨论,其中沈文倬先生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蜡祭属于“报祭”,而且蜡祭和腊祭是两种不同的祭祀,并讨论了关于蜡祭的祭服、音乐和祭祀对像等问题[1]。曹书杰先生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大蜡八”是祭路神。即“軷祭”[2]。詹鄞鑫认为蜡祭对象的八神是一种误解,“大蜡八”就是“大索于八方”的意思[3]。在总结和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笔者不揣庸陋,对于蜡祭的内容和与腊祭关系等问题上略述浅见,希望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祭祀特点和发展状况能稍尽绵力,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蜡祭本义
何为蜡祭。《礼记·郊特牲》篇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郑玄云:“万物有功加于民者,神使为之也,祭之以报焉,造者配之也。”[4]这说明蜡祭是主要祭祀“有功加于民者”的万物之神,即郑玄所云的“蜡八”之神。然曹书杰先生认为:“关于蜡祭的对象,郑玄所注的‘蜡八’之神,是一种误会,所谓‘蜡八’即‘蜡軷’、‘八蜡’即‘軷蜡’,八、軷同音假借。軷,祭路神也。由此可知,‘蜡軷’、‘軷蜡’的本义就是在道路、田野、村落等各处索求各种游神野鬼而遍祭之,或路祭之。‘蜡軷’、‘軷蜡’一变为‘蜡八’、‘八蜡’。‘大蜡’的本义就是‘国之大祭祀’时彻底清理环境卫生[2]389。”曹氏的观点有两处问题值得斟酌。首先,“蜡八”就是在蜡祭时祭祀八种有功于农事的八种神灵,而且蜡祭在国家祭祀体系中属于很重要的一种,《礼记·郊特牲》篇云:“天子大蜡八。”这说明大蜡之祭是天子所进行的,而曹氏说蜡祭是祭祀道路、田野、村落间的各种游神野鬼,这显然是降低了蜡祭的地位。其次,“大蜡”的本义并不是清理环境卫生。孔颖达云:“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对诸侯为大。天子有八神,则诸侯之蜡未必八也。”[4]孔氏所云证明了“大蜡”对于诸侯来说可以称之为大,而且上面又说到蜡祭是农业祭祀的一种,因此,其本义和清理环境卫生无关。
蜡祭不仅仅是天子可以举行,诸侯、民间都可以举行。这也体现了蜡祭是一种全国性质的祭祀。但三者的蜡祭是有区别的。天子的蜡祭是每年都举行的,而诸侯和民间并不一定。《礼记·郊特牲》云:“八蜡以记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郑玄云:“其方谷不熟,则不通于蜡焉,使民谨于用财。”[4]1080孔颖达云:“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记四方之国,记其有丰稔、有凶荒之异也。谓四方之内,年谷不得和顺成熟,则当方八蜡之神不得与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谨慎民财,欲使不熟之方万民谨慎财物也。四方之内有顺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与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蜡祭丰饶,皆醉饱酒食,使民歆羡也。”[4]1080总的说来,就是诸侯和民间的蜡祭要看当年的年成是否“顺成”。如果没有获得丰收或者出现灾荒,那就不能举行蜡祭。但是这条材料中所说的情况应该不包括天子。邢亚玲认为:“蜡祭通常选择在丰收的地区举行,具有欢庆丰收的意味[5]。”邢氏此言说的就是诸侯或者民间的蜡祭。因为天子的蜡祭不会去到诸侯国举行,如果天子每年都把蜡祭选择在丰收的地区举行,那岂不是蜡祭的场所要经常换地方?
蜡祭的场面是很宏大的,李慧玲认为,蜡祭是古代的狂欢节[6]。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但蜡祭确实体现了百姓劳作一年,丰收欢休的愉快心情。《礼记·杂记下》篇云:“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而所知也。’”孔颖达云:“言百日者,举其全数,喻久矣,实一年之劳苦也。今一日欢休,故恣其醉如狂,此是由于君之恩泽。”[4]1676子贡认为蜡祭时,国家的人像发狂一样,自己却不知道他们到底快乐在何处。孔子解释说百姓辛苦耕作一年,而蜡祭这天是国君赐予的恩泽。这说明蜡祭这天以后百姓可以获得休息,不用再劳作了。郑玄在解释这段经文时云:“蜡也者,合聚万物而索饗之祭也。国索鬼神而祭祀,则党正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于是时,民无不醉者如狂矣。蜡之祭,主先啬也。大饮烝,劳农以休息之。今一日使之饮酒燕乐,是君之恩泽。”[4]1675郑玄的此注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蜡祭这天确实“民无不醉者如狂矣”。其二,蜡祭之后党正要举行乡饮酒礼。孔颖达解释郑玄的注时说:“谓于时天子、诸侯与群臣大饮于学,于此之时,慰劳农人,使令休息。”[4]1676就是证明。而且沈文倬先生认为蜡祭毕,接着要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1]845因此,我们说蜡祭这天不但要蜡祭八神,而且在蜡祭之后还要举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
二、郑玄注引起的争论
关于蜡祭中所祭的八神,郑玄的注引起了一些争论。焦点在于“昆虫”。郑玄云:“蜡祭有八神: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先啬,若神农也。司啬,后稷是也。农,田畯也。邮表畷,谓田畯所以督约百姓于井间之处也。水庸,沟也。”[4]1072郑玄认为蜡祭的主要对象为八神,而《郊特牲》中只提到了七种。孙希旦认为:“八者,所祭有八神也:先啬一,司啬二,百种三,农四,邮表畯五,禽兽六,坊七,水庸八。”[7]王肃则认为无“昆虫”一项,把“禽兽”分“猫”和“虎”[1]847。宋人张载认为应该是“易以百种”[1]847。各家的矛盾之处皆在于“昆虫”的问题上。清人蔡德晋则认为无“昆虫”一项,他说:“郑成康蔡中郎以祝词中,有‘昆虫无作,草木归其泽’之语,因以为昆虫为一神,夫昆虫不当祭,若祭昆虫者,亦当祭除草木者而不止于八神矣。”[1]848同时他反驳张载之说,认为祭“百种”是祭“百种”之谷。那么,祭“百谷”则是祭谷神,这属于社稷之祭,并不是蜡祭[1]847。最后他把“邮”和“表畷”一分为二。蔡氏驳斥各家之言有可取之处,如“百种”一祭应该是没有的。但是,他把“邮表畷”一分为二应该是有些问题的。孔颖达云:“邮表畷者,是田畯于井间所舍之处。邮,若邮亭屋子。表,田畔。畷,谓井畔相连畷。于此田畔相连畷之所,造此邮舍,田畯处焉。”[4]1073沈文倬先生认为:“古时有田畯的制度,其使命是督约农人,教农人以耕种方法,所住的地方,是在田畔相连缀处,建造邮亭,亭外置‘表’,表上当然是颁布一些耕种方法。”[1]847这说明,“邮表畷”是“田畯”在田间督约农事时所栖身之所。而这种“邮舍”不仅“田畯”有,后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也有了,称为“田舍”。睡虎地秦简《田律》云:“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不从令者有罪。”[8]这些“田舍”可能是从“邮表畷”发展而来的,所以蔡氏之说有待思考。
从郑玄的注中我们可以看出“大蜡八神”中有七神是可考的。至于“昆虫”,郑玄并未作出解释。虽然《周礼》和其他先秦文献中不见有祭祀“昆虫”一说,但该是包括“昆虫”的,而且是指蚕一类的昆虫。众所周知,中国是最早进行养蚕业的国家,蚕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如《吕氏春秋·季春纪·季春》中记载:“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任降于桑。具栚曲筥筐,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堕。”[9]这段记载指出在季春之月,王后斋戒并亲自采摘桑叶以便养蚕,而且禁止妇女出游观赏,并减少她们的杂役,鼓励她们养蚕,还要考核她们的功效,最后把这些蚕丝都用来供给祭祀所用服饰的需要。祭祀“昆虫”和祭祀“禽兽”的思维和目的是大致相同的,即凡是对民有功的,人在用的时候一定要祭祀它的精灵。然“蚕”这类昆虫非常重要。所以,在蜡祭八神中,郑玄的解释大致是无误的,其中的“昆虫”就应该指“蚕”一类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有益的昆虫。
郑玄注引起的第二个争论就是关于“伊耆氏”何指的问题。《礼记·郊特牲》中提到蜡祭时说“伊耆氏始为蜡”。然“伊耆氏”到底何指,历代注家各有所云。郑玄云:“伊耆氏,号也。伊耆,古天子号也,或云即尧帝是也。”[4]1071孙希旦则认为:“伊耆氏,秋官之属。伊,安也。耆,老也。此官掌共杖,以安息老人为职,蜡息老物,故并使掌焉。始为蜡者,于将蜡之时,始命国人为蜡祭也。”[7]695这两家的观点有比较大分歧。郑玄在解释“蜡八”之神时,说先啬就是神农,如果“伊耆氏”是神农,那蜡祭所祭之神不就是首先祭祀自己么?这显然不合祭祀之制。金景芳先生认为蜡祭的年代一定很古。金老说蜡祭所祭祀的“禽兽”、“坊”和“水庸”都是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的遗迹,而以《明堂位》的记载作为旁证,那么伊耆氏的年代大概早于颛顼氏而为母系氏族公社时代的一个著名人物[10]。沈文倬指出:“伊耆氏一定是个部落的总号,后来进入氏族社会,这部落的后裔,就拿这总号作姓氏,姓伊耆的裔孙,其中有一人始为蜡祭而祭神农,所以传说上就称‘伊耆氏始为蜡。’周代又以此姓做官名,列于下士之间,而供王之杖。”[1]846沈氏此说应该已经接近事实。然《礼记·郊特牲》中的“伊耆氏”究竟何指,根据沈文倬先生说“伊耆氏”到周代从姓氏变为官名可以看出,所谓的“伊耆氏始为蜡”意思是说“伊耆氏”告诫人们祭祀时间快到了,要开始准备蜡祭的相关事宜。
三、蜡祭与腊祭
古典文献中关于蜡祭和腊祭的记载是比较混乱的。两者关系如何,是否属于同一个祭祀等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沈文倬先生认为两者的争论起于蔡邕的“四代蜡之别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曰腊”的说法[1]846。此说一出,异说迭起,有的人以为蜡就是腊,不过周曰蜡,汉曰腊,一祭二名。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认为“腊”有四义,一是祭名;二是同于蜡;三则引《风俗通》云:“腊者,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报功也”;四引郑玄注《礼记·月令》云:“腊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11]显然,段玉裁认为蜡祭和腊祭是同一种祭祀。而有的人则以为蜡、腊是两个祭祀。郑玄说:“腊,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五祀,门、户、中霤、灶、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腊’。”[4]726孙希旦云:“《月令》有腊而无蜡,秦制也,《郊特牲》有蜡而无腊,周制也。《月令》历言‘祈天宗,祠公社、门闾、腊先祖、五祀’,而无一语及八蜡之神,《郊特牲》历言八蜡之神,而无一语及天宗、公社等之祭。二《记》所言,不啻风马牛不相及,岂容牵合而指一祭乎?”[7]491由此可见,郑玄和孙希旦都认为蜡与腊是不同的祭祀。笔者同意这种观点。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腊祭并不是秦汉之际出现的改称,是之前就有的。《左传·僖公五年》中宫之奇说:“虞不腊矣。”这是指虞国即将灭亡了,宗庙将毁于一旦,不能如常的举行祖先之祭了,这并不是说因为年成不好而不能举行祭祀,这条材料不仅说明腊祭始于秦汉之前,更能说明腊祭与蜡祭是不同的两种祭祀。
蜡祭与腊祭混淆也不是偶然的。在祭祀时间上,蜡祭和腊祭的时间应该是在同一月。《四民月令·十二月》记:“十二月日,薦稻、雁。前期五日,杀猪,三日,杀羊。前除二日,齐、馔、扫、涤,遂腊先祖五祀……是月也,群神频行,大蜡礼与,乃冢祠君、师、九族、友、朋,以崇慎终不肯之义。”[12]此段文字史料说明蜡祭和腊祭是在每年的十二月。孔颖达云:“先蜡后息民,是息民为腊,与蜡异也。前‘黄衣黄冠’在蜡祭之下,故知是腊也。但不知腊与蜡祭相去几日。”[4]1081从孔颖达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知道腊祭是在蜡祭之后的。这两种祭祀在时间上应该是很接近的,更有可能是同日异时。因此,这可能就是后人把两者混为一谈的一个原因。
蜡祭与腊祭的关系应该是总体和个体的关系。曹叔彦先生认为:“祈年大蜡同时举行于郊,腊则日异时举行于庙,因为同日举行,所以总称大蜡。”[1]850沈文倬先生说:“大蜡是总号,蜡可以说腊,并非蜡即是腊,并且腊自能独立。不过二祭同日先后举行,所以称蜡即以包腊。”[1]850《礼记·月令》云:“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郑玄注云:“此《周礼》所谓蜡祭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腊’,互文。”[4]726孔颖达曰:“此等之祭,总谓之蜡。”[4]727综上所引,可以看出曹氏和沈氏的观点是正确的。沈文倬先生指出:“《明堂位》云:‘是故夏礿秋尝冬蒸春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从文气上看来,正是明言四时各种祭祀后,至孟冬而复总祭之。这就是祈年之祭,是附祭于大蜡的,所以大蜡中要包括‘天宗’以下的许多神灵了。而此等之祭,都是‘附祭’,与‘正祭’不同。因为‘天宗’自有它的‘王宫’,‘夜明’,‘幽宗’正宗,‘公社’自有它的‘社稷’正宗,‘门’,‘闾’正祭包括在五祀中,‘先祖’自有它的‘四类’正祭,本与蜡祭无涉,大蜡原为八神的‘正祭’。”[1]849沈氏这段论述相当正确,由此可以看出蜡祭是总祭,而腊祭是附祭。
蜡祭与腊祭虽分属两种不同的祭祀,却也存在着联系。但是到了秦汉以后,两者可能存在一种融合的趋势。《关沮秦汉墓简牍》中有一条记载:“先农:以腊日,令女子之市买牛胙、市酒。过街,即行拜,言曰:‘人皆祠泰父,我独祠先农。’”[13]这条简文中说当时人们腊日所祭之人皆为“泰父”,只有个别人才想到祭“先农”。 “泰父”一词整理小组注谓“大父”[13]132。即祖先的名称。“先农”整理小组注曰:“古代传说中始教先民耕种的农神。”[13]132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简牍》中所记的“腊日”当天,人们都祭祀祖先“泰父”,说明这天进行的就是腊祭。可见当时社会风俗中腊祭和蜡祭分属不同祭祀的情况依然是主流,然《简牍》所记的小农却想到要祭祀“先农”,这说明情况可能产生了变化,而蜡祭与腊祭的混淆可能也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
[1]沈文倬.菿誾文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曹书杰.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89.
[3]詹鄞鑫.神灵与祭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72.
[4]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071.
[5]荆亚玲.“蜡祭”考溯[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2):77.
[6]李慧玲.试说中国古代的狂欢节——蜡祭[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2):205.
[7]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694.
[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2.
[9]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4.
[10]金景芳.中国古代思想的渊源[J].社会科学战线,1981(4):155.
[1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72.
[12]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74.
[13]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2.
[责任编辑 薛柏成]
K22
A
1007-5674(2014)04-0081-03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4.015
2014-05-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礼》注所见汉代史料辑证”(编号:14BZX021)
李强(1985—),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