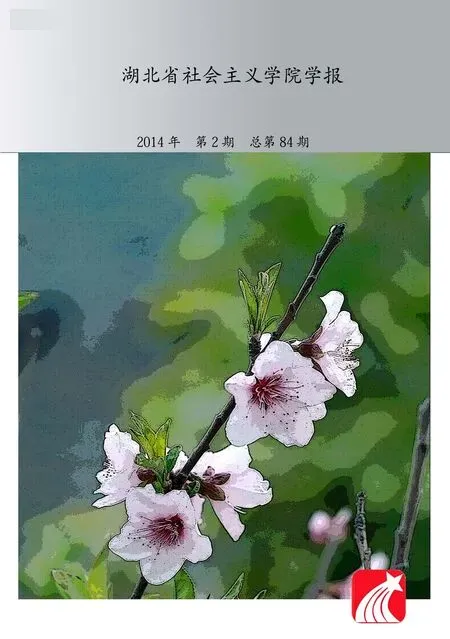朱熹之“天”和“天理”的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吴默闻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朱熹是宋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其思想无论是对当时社会,还是对后世的社会制度、观念、教育、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天”和“天理”的内容。天,既是朱熹宇宙观的主要范畴,也在其伦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代表性观点——“存天理,灭人欲”,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千百年来,朱熹的这一观点曾被广泛宣扬,也受到许多人的诟病。由此也衍生出许多问题,例如:朱熹之“天”的含义是什么?它在朱熹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朱熹为什么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对“天”的主张在其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朱文公文集》以及其弟子记录的《朱子语类》等著述中有怎样的体现?与他的思想又有怎样的传承关系?朱熹的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现在应当如何看待朱熹的这些主张?笔者试从《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朱文公文集》等文献的相关论述中,来管窥朱熹之“天”和“天理”的三层含义、主要内容及其价值取向。
一、朱熹之天的三层含义:宇宙之天、主宰之天、天理之天
天与理气、太极等都是朱熹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这从《朱子语类》第一卷开篇即为理气、太极、天地等内容可以得到印证。在《朱子语类》中,朱熹对“天”下了明确的定义。他在回答其学生关于《周易》经传中“天”的含义时谈到:“要人自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有说主宰者,也有单训理时。”[1](P5)可见,朱熹将传统经典文献中的“天”之含义划分为三层:一是指“苍穹”的宇宙之天,二是决定万物的主宰之天,三是“天地万物之理”的天理之天。这也可以理解为朱熹之“天”的三层含义。其中,朱熹所极力推崇的是“天理”之天。这里,首先对其宇宙之天与主宰之天作相应分析。
宇宙之天,在通常意义上,是指苍穹,即天空。朱熹在这里所说的“苍苍者”之天,通常与地相对而用。而对于天的宇宙论意涵,朱熹也有一定的阐述。“天地初间只有阴阳之气。……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1](P6)“清刚者为天,重浊者为地。”[1](P6)可见,在朱熹看来,天和地都是阴阳之气运行、转换的产物,其中,清者为天,浊者为地,两者相互对应。天地万物虽然各有区别,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太极,亦即“天地万物之理”或称“天理”。
朱熹哲学体系中有其独特的宇宙观:“天以气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气。天包乎地,地特其中一物尔。”[1](P6)可见,在朱熹的宇宙观中,天与地的方位是:天在外,地在中心,天围绕在地的周围,包围着地。太极,即理,是万事万物生长化育的根本,气则是直接作用者,清气为天,浊气为地。宇宙形成和万物化育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值得一提的是,朱熹的宇宙观不仅描绘了宇宙的基本格局,还涉及到对阴阳五行、黄道、经度、维度等专业问题的探讨,这些大都体现在《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下》中。
主宰之天的涵义,在朱熹之“天”中是非常突出的。朱熹所述的天人关系,往往蕴含着一种人被“天”主宰的意味。但是,主宰者不是天空本身,而是比天更加根本的理。天地万物因理而生、久远长存。“天地未判”时,“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万年,古今只不离许多物”[1](P4)。天是起主宰世间万物作用的上苍,但是它“主宰”万事万物的方式是自然而然的,正如朱熹引程颐所言:“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1](P4)朱熹所讲的主宰之天,是通过气运盛衰、天理循环来决定世间万物盛衰兴亡、新旧更替的。
天理之天既与天的前两层含义即宇宙之天、主宰之天相联系,又有所区别。天理贯穿于天地万物中,使万象万物运行周转,它就是“太极”。“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1](P1)没有太极,没有理,就没有天地和万物:“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1](P1)理是万事万物产生、成长和运行的根源,但是直接起作用的,是“气”:“有此理,便有此气流行发育。理无形体”[1](P1)。理是无形、抽象的,起的是根本的、决定性的作用。而“气”是有形的、实在的,起直接作用的。朱熹论太极,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若无太极,便不翻了天地?”[1](P2)可见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太极是天理或理的同义语。没有太极,也就没有了天理。没有天理,天地也无从出现。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正说明,太极是天地万物的秩序。
二、朱熹天理观的主要内容:理、气与天命之性
天理或理是朱熹思想的最高哲学范畴,天理论则是朱熹思想体系的核心。朱熹的天理论秉承程颐,并在程颐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使之更加严密、精致、深刻。
在朱熹看来,天理或理是宇宙的根源、根本。“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1](P2)可见,理是宇宙的根本。天地因理而化育,人与自然因理而生。天地、人和万物等等,都由最根本的理所产生、承载。有理就有气。气化流行,就化育万物。总而言之,天地万物,就是一个理。理无不包摄、无所不在。朱熹认为:“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在这里。”[1](P4)这是说,理是不随天地、时间、自然万物而变动的,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一言以蔽之,理是不依赖天地万物而独立存在且永恒的。
天在朱熹思想中的另一重要方面即是天命之性。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2](P2755)天地之间,一切事物都由理与气构成,理是事物的本质与规则,气是构成事物的材料,理属于形而上层面,气则属于形而下层面,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道家的“道”与“器”。天理被禀受到个体人、物身上所形成的本性,就是“天命之性”。人、物的本性秉承于天,在朱熹看来即是《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意义。人性除了禀受于天理外,也秉承气质。气质来源于理,然而气质有清浊偏正的不同,人性在形成的过程中,“天命之性”不可避免地受到气质的影响。于是,一切现实中的人性已经不全是“性之本体”的天地之性了,而是受到理与气两个方面影响之后而形成的两者的混合体——即气质之性。本来天理之性是纯善的。“‘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个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曰‘性’。只是这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1](P83)
朱熹认为,除天命之性外,人还禀受了气质之性。因此,人性有善有恶。“‘继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资以始。‘成之者性’,则此理各自有个安顿处,故为人为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有形质,则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做人物之性得。”[3](P1879)人性本善,天命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气质之性是天命之性受气质影响后的变化形态。“命者,天之所以赋予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禀受乎天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言之,则天以是理命乎人物亦谓之命,而人物受是理于天谓之性。自其气而言之,则天以是气命乎人物亦谓之命,而人物受是气于天亦谓之性。”“气不可谓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气杂而言之。”[2](P2688)“理”就是人的“天命之性”、“性之本体”。作为人的本性的天地之性,它是人的气质之性的本体状态,是纯然至善的。而作为天地之性受气质熏染而发生的转化形态的气质之性,是人的气质之性的现实状态,因而是有善有恶的。一切现实的人性,都是受到气质熏染的气质之性。这种气质之性中的浑浊、偏塞,造成了人的恶的品质、欲望、情感,“人欲”即是这样产生的。“人欲”与“天理”相对立的特征,在朱熹的“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4](P3)一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朱熹天理观的价值取向:追寻大学之道
如同历史上许多儒家学者一样,天的思想贯穿于朱熹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也蕴含在他对很多儒家经典著作的注释中,包含《大学章句》在内的《四书章句集注》便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大学》的主旨在于内圣外王的修养工夫,朱熹所作集注也主要是从伦理道德、治学修养等层面对《大学》一文加以解释。然而,无论是天理、天命、主宰之天还是自然之天,在《大学章句》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
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全文提及“天”的地方,只有引自《尚书·商书·大甲上》中的一句话:“顾视天之明命”。朱熹所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章句》,同样也只有几处涉及“天”。但是,这仅有的几处涉及天的语段,仍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朱熹的思想。另外,朱熹《大学章句序》虽然不是《大学章句》的正文,其中的内容也直接反映了朱熹对天的看法。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的“天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阐释上。朱熹指出:“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敝,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4](P3)在朱熹看来,高尚的德行,是人从天那里得来的。美好的德性,如同人性乃至万物之性的其它方面一样,因禀受天地之理而得。因此,明德可以视为天地之理的一部分。
显然,在朱熹看来,“天理”是万事万物(包括人)本来具有的本性,纯净而未受沾染,而人欲则是人的天地之性受浑浊、偏塞的气质所禀而出现的恶的杂质。人要回归本然的纯然至善的天地之性,就要清除气质之性中的恶的杂质即所谓“人欲”。君子正是要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来磨砺自己,变化气质,摈除人欲之私,使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天地之性完全展现出来,重新回到美好的本性,达到至高至善的境界,重归天理。而培养崇高的德行,革新民众的思想,都是要以达到并保持在至高至善的境界为目的,“明德”、“新民”都是回归天理、达到至善的必然要求。这也就是“大学之道”之所在。
此外,“天命”是《大学章句》中出现较多的一个与“天”相关的概念。《大学》原文引述《尚书·大甲》:“顾视天之明命。”朱熹解释道:“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4](P4)他在阐释《大学》所引用的《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时,也谈到“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4](P5)“受天之明命”,即禀承天理、修养德性。它并不是宿命论思想,而是与道德相联系的境界,它体现了天人关系中人的参与意识和担当精神。
作为化生万物的天,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思想史,在朱熹这里也不例外。“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4](P1)在朱熹看来,“天降生民”,人的存在来源于天,人的终极价值判断也来源于天。整个人世按照“天”所定的轨道前行,天也在默默地引导着人们,因此,历史上出现了一位又一位圣人秉承天道,修德立法,世间出现了各种礼乐制度和规范。这里的“天”崇高而深远,但并非是不可接近的。“天运循环,无往不复。”[4](P2)天运经年往复,引导着一代又一代人与万事万物,生生不息。
从上文对朱熹之天和天理思想的粗浅分析中,可以看出朱熹关于天的“苍穹”,即宇宙之天的含义,应当是从远古一直流传下来的,也是天之最根本、最原初的含义。而主宰之天的含义,则与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代表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朱熹在这里已经明确提出了主宰之天的概念,而不象《论语》、《孟子》等先秦著作中,只是含有主宰的含义,却没有明确地提出这种概念。而天理这一层含义,在先秦哲学中则少有涉及,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
[1]朱子语类: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朱子全书(修订版):第2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朱子语类: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