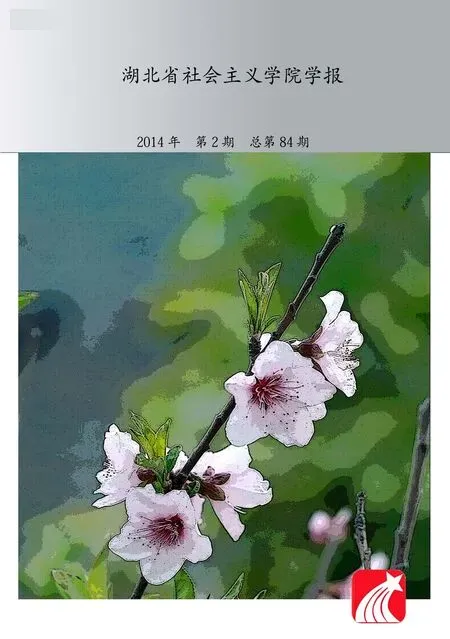刘禹锡朗州诗文与楚文化
刘云峰
(荆楚理工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文学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总是以特定的文化为背景,展现文化的本质内涵,文学作品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文化意蕴。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公元772年-842年)被逐出朝廷,远贬到了穷乡僻壤的巴蜀荆楚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刘禹锡23年(实为22年)贬谪人生的第一站,就是朗州(初贬连州刺史,未至而中道追贬为朗州司马),即今湖南常德。《旧唐书·刘禹锡传》:“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1](P168)朗州十年(公元805年-815年),刘禹锡留下大量的诗文,约占其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其中体现出来的骚怨情结、民俗风情,描绘的奇山异水,乃至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具有浓厚的楚文化色彩。研究刘禹锡,朗州十年颇为关键。
一、骚怨情结:刘禹锡与屈原
文人被贬谪由来已久,但对后世文人产生深远影响并形成了所谓“骚怨”传统的却是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一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遂将满腔的委屈与怨愤倾注于文学创作中,其代表作《离骚》开启了后世失意文人的骚怨情怀。刘禹锡与屈原遭遇相似,贬逐之地亦同,并曾住在当地百姓为纪念屈原而修建的“招屈亭”附近,这使他与屈原有了更多的共鸣,其在贬谪期间的文学创作也就带有更多更浓厚的逐臣情怀和骚怨意识。
贬谪,使刘禹锡“十年憔悴武陵溪”(窦巩《送刘禹锡》)。刘禹锡与屈原都怀有辅佐明君、济世安民的远大抱负,又都因奸佞当道而壮志难酬、远逐蛮荒,故《离骚》中蕴含的骚怨意识自然也渗入到刘禹锡的文学创作之中。久居蛮荒,仕途的蹭蹬,使得刘禹锡满腹愤懑,无时无刻不忘重返朝廷。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宪宗下诏:“左降官……刘禹锡……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1](P418)这无疑给了刘禹锡沉重的一击。到朗州不久,他就写下了《游桃源一百韵》,痛感于“巧言忽成锦,苦志徒食孽”的黑白颠倒而“北渚吊灵均”(本文刘禹锡诗文皆出自《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陶敏,陶红雨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版)。《谪九年赋》更是刘禹锡对长久厄运的质疑,以及对现实不公的愤怒追问。赋云:“古称思妇,已历九秋。未必有是,举为深愁”;“莫高者天,莫浚者泉。推以极数,无逾九焉。伊我之谪,至于数极。长沙之悲,三倍其时”。刘禹锡把自己比作是一位“已历九秋”的思妇,为贾谊在长沙贬谪时光的三倍,苍凉的语调中透出浓郁的愁怨和哀伤。
刘禹锡的作品中,学习、模仿或者涉及屈原者所在多有。《问大钧赋》结尾说:“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售。”《何卜赋》模仿《卜居》,借问卜抒愤懑之情。至于诗文中借用《楚辞》典故的地方就更多了,如《早春对雪奉寄沣州元郎中》“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醴有兰”,用《九歌·湘夫人》“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不敢言”典故。其《竞渡曲》“灵均何年歌己矣,哀谣振揖从此始……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表达了对屈原的深切怀念和巨大的孤独。屈原作品中的意象在刘禹锡的诗文中也经常出现:“逐客无印缓,楚江多芷兰”(《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楚水多兰若,何人事撷芳”(《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使幕》);“春还迟君至,共撷芳兰曹”(《别友人后得书因以诗赠》)等等。这种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刘禹锡离开朗州之后。
《何卜赋》是刘禹锡在贬谪朗州后期所写。楚人信巫神而好占卜,经历长期的贬谪而未有尽头的刘禹锡忍不住向卜者发问:“人莫不塞,有时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穷。人莫不病,有时而间,伊我兮久而滋蔓”;“极必反焉,其犹合符。予首圆而足方,予腹阴而背阳。胡形象之有肖,而变化之殊常?”慨叹人总有穷通之时,遵循物极必反的变化规律,可自己却是贬谪愈久,处境愈发困难;为什么我的形象与天地相似,而处境却如此反常呢?刘禹锡的占卜并非因为长期的谪居而相信并屈服于命运,而是藉此宣泄心中郁积的怨怼与不平。刘禹锡始终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谤,为谗言所伤:“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启》),直至他去世前所写的《子刘子传》中,依然自信地宣称,自己当年投身的那场革新运动“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这与当年屈原“信非吾罪而弃逐兮”(《哀郢》)可谓一脉相承。正因为有了屈原式的苏式独立的品格,刘禹锡才能在23年的贬谪生活里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精神,刘禹锡以自己卓然不屈的精神丰富了楚文化的内涵。
二、凄凉古竹枝
《竹枝》在楚地流传甚广,是其地方歌谣。刘禹锡善歌《竹枝》,他的竹枝词更是受屈原的影响,是学习楚地民歌创作的典范之作,甚至《竹枝词》11首与《九歌》的篇数也都一样。前人曾评曰:“刘梦得《竹枝》,亦骚之裔。”[2](P61)大和六年,白居易作《忆梦得》:“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注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此处刘禹锡所唱《竹枝》,或有其自创之词。刘禹锡写有两组《竹枝词》,其写作时地,自唐以来,多有争议。《竹枝词二首》与《竹枝词九首》声律不同,或非同时之作。据《新唐书·刘禹锡传》:“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怆伫,禹锡谓屈原居湘沅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于是武陵夷偶悉歌之。”[3](P168)明谓“《竹枝词》十余篇”皆作于朗州。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亦云:“《竹枝》本出於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调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於贞元元和之间。”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引: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
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证之以“引”中所提时、地及诗中地名如“白帝城”、“蜀江”、“白盐山”、“瞿塘”、“巫峡”等,《竹枝词九首》一般认为乃刘禹锡居夔州时作,《新唐书·刘禹锡传》所记错误,《乐府诗集》因之。而《竹枝词二首》,或谓作于夔州,或谓朗州,争议很大。二诗云: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
其中“巴”(巴山、巴人)字,乃问题之关键。巴是一个文明古国,早在商代已见称于世。在古代,以川东鄂西为中心,北达陕西汉中,包有汉水上游西部和嘉陵江以东地区,南极黔涪,包有黔中和湘西在内的一大片广袤的地域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族、巴国、巴文化等概念。[4](P54)而楚地疆域广阔,秦汉时就有西楚、东楚、南楚“三楚”之分。《汉书·地理志》亦云:“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5](P1665)。由于巴、楚之间长期的边际文化接触和交流以及频繁的和战兼并,导致了巴、楚之间风俗和精神文化的互融,因此取得最后胜利的楚国西境保留大量的巴文化要素本不足为奇。
要之,朗州是可以称作巴的。战国时朗州为黔中之地,而黔中乃巴之故壤,刘禹锡深谙于此,其《武陵书怀五十韵》引:“武陵当翼轸之分。其在春秋及战国时,皆楚地,后为秦惠王所并,置黔中郡,汉兴,更名武陵,东徙于今治所。”杜佑《通典》亦云:“秦昭王使将伐楚,略取蛮夷,置黔中郡。今武陵、澧阳及黔中五溪中诸郡地。”[6](P5041)刘禹锡另有《堤上行三首》、《踏歌词四首》皆提及竹枝词,这两组诗,其写作时地亦有争议,陶敏先生系之朗州。《堤上行三首》其二:“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踏歌词四首》其四:“日暮江头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自从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尽时。”而《阳山庙观赛神》是可以确认为朗州之作的,“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明言竹枝;《洞庭秋月行》“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巴童”与“竹枝”对举,可见在刘禹锡心中,朗州不仅可以称作“巴”,而且竹枝词在朗州流传甚广。《插田歌》作于连州,为刘禹锡贬谪的下一站,朗州之后,夔州之前,有“齐唱田中歌,嘤咛如竹枝”之句,足见《竹枝词二首》完全可能作于朗州,《新唐书》、《乐府诗集》所记虽然有误,却也事出有因。退一步说,正是由于刘禹锡在到达夔州之前就已经熟稔竹枝歌,甚至已经融进了他的生命,即便是《竹枝词》全部作于夔州,也不能抹杀朗州人民歌咏竹枝的风俗对其夔州《竹枝词》的重要影响。
三、刘禹锡与荆楚风物
刘禹锡晚年在《刘氏集略说》自叙云:“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者之比耳。”朗州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风土人情、地理物候等与中原地区迥异,刘禹锡详尽地描写了当地的山川形貌和风土人情,同时朗州独特的民风民俗又影响着诗人的心境,使他的诗文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意境。
(一)烧畲、渔猎、淘金、采菱
唐代的朗州属五溪蛮、武陵蛮之地,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刘禹锡对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很有兴趣,其《武陵抒怀五十韵》云:“户算资渔猎,乡豪恃子孙。照山畲火动,踏月俚歌喧。拥楫舟为市,连甍竹覆轩。披沙金粟见,拾羽翠翘翻。”描述了当地居民烧畲、渔猎、淘金的生活习俗。刘禹锡朗州诗文中,不止一次提到烧畲,如《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陆怅然有感》、《楚望赋》等,另有《畬田行》,写于何地何时有争论,有人主张朗州说,盖因朗州地区畲田之风炽盛。所谓“户算资渔猎”,谓武陵百姓平时的生计和税收主要是靠渔猎,渔业也是朗州人民重要的谋生方式,《楚望赋》中也有详尽的描写。朗州是全国有名的产金地,《楚望赋》、《浪淘沙词》其中真实地记录了朗州人民的淘金生活,兹不赘述。
《采菱行》描绘了武陵采菱女在秋天的白马湖上“争多逐胜”的紧张而又欢快的采菱劳动场面。纵观全诗我们发现,初贬时的那种强烈的忧怨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恬淡与平和。然而刘禹锡始终未忘记自己的逐臣身份,“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曲终人散之后是无边的凄凉和孤独,与《竞渡曲》心境相似。
(二)巫觋文化、神话传说及歌舞、赛舟
独特的民族心理造就了独特的巫觋文化。在楚国的神话与宗教中,沟通人神是通过巫觋来完成的。为了祈求福祉,感谢神赐,就要组织“赛神”,在隆重的祈祷仪式的同时,往往有歌舞活动,巫觋常常是赛神歌舞的表演者。楚地有独特的神系,又崇北方诸夏神,汉将梁松与成为江陵民众神祇的陆逊、甘宁等人一样,成为朗州民众的神祇。《阳山庙观赛神》序云:“梁松南征至此,遂为其神,在朗州。”此诗将赛神会写得栩栩如生,不仅使人感到楚文化中的那份“巫”气,更添加了几许神秘。“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还真切地再现了楚人热爱歌唱的风俗,与《洞庭秋月行》“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贾客吹羌笛”互相辉映。
龙舟竞渡,源远流长,楚地尤甚。《竞渡曲》详细地描绘了龙舟竞发,声涛拍岸的壮观景象。作者自注:“竞渡始于武陵。……斯招屈之意。”楚地有着多彩的神话传说,刘禹锡借之丰富了他的创作。《潇湘神·斑竹枝》写舜帝与娥皇、女英二妃的故事,思绪缠绵,哀怨凄凉,而其主旨则是借咏斑竹以寄怀古之幽思。《酬端州吴大夫夜泊湘川见寄一绝》亦将娥皇、女英的传说寓于其中,流露出异乡逐客的悲凉心情。
(三)洞庭湖、君山、桃花源等奇山异水
大自然是心灵最好的疗养所。刘禹锡于从政之余,搜奇访胜,游玩山水,足迹遍及朗州各地,岳阳楼、洞庭湖、君山、桃花源以及湘水、沅水等。奇山秀水以其独有的清丽、灵秀和神秘感染着贬谪中的刘禹锡。
刘禹锡往来洞庭,有文献可考者至少有六次。刘禹锡念念不忘山青水秀的洞庭湖以及湖中的君山,在前往朗州贬所经洞庭湖时写就《君山怀古》,借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尚且有受挫之时强自宽慰。《洞庭秋月行》则描绘出一派恬静幽美的人间仙境。刘禹锡另有一首《望洞庭》,写秋月与湖光山色。《历阳书事七十韵》序云:“长庆四年八月,予自夔州刺史转历阳(和州),浮岷江,观洞庭,历夏口,涉浔阳而东。”以时令观之,《洞庭秋月行》、《望洞庭》或亦有可能写于作者长庆四年(公元824年)赴和州任途经洞庭之时,但其中流露出的对洞庭湖的珍爱绝非一时之观感,其间一定凝结着朗州十年的复杂情感体验。
刘禹锡和桃花源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游桃源一百韵》是刘禹锡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叙述了他此次游览的经历,桃花源的传说以及独特的自然景观,也寄寓着自己的身世之感。他还写有《桃源行》、《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等诗,对桃花源可谓情有独钟。洞庭湖畔的奇花异草,月下荡舟的淡云轻风,桃源之侧的清猿哀鸣,一方面固然会引起诗人无端遭贬的无尽愁怨,另一方面,荆楚大地的丽山秀水也使他受伤的心灵得以平复和超脱。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凭借着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独具特色的楚文化所提供的丰富的养料,也凭借他极富个性化的创作天赋,贬谪的23年尤其是朗州十年反而成为刘禹锡创作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从政治中心到蛮荒之地,从改革派核心到戴罪之臣,是政治上的失意,玉成了刘禹锡文学上的成就。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翁方纲.石州诗话:卷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