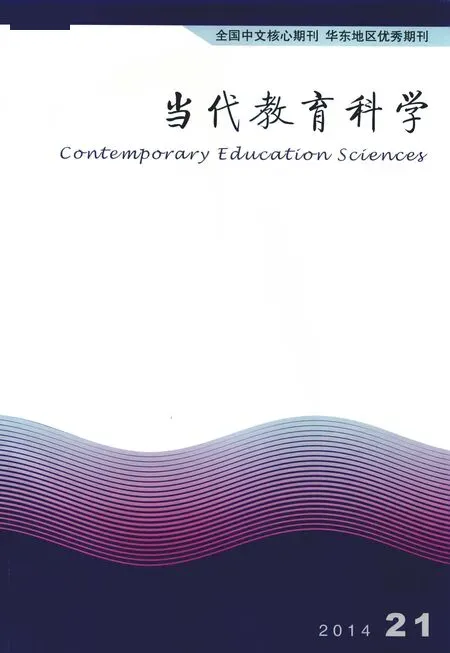“先学后教”模式在我国的百年演进及思考*
●刘秀峰
“先学后教”模式在我国的百年演进及思考*
●刘秀峰
新课改以来,“先学后教”模式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作为一种本土化的教学模式,“先学后教”模式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在我国建立之日起就开始在教学实践中慢慢探索。在民国初期、1920年代、1960年代、1980年代以及新课改以来,人们对“先学后教”模式的探索达到高潮。对“先学后教”模式的探索从根本上说是克服现代学校教育制度“重教轻学”之弊的历史使然,同时知识观的变迁也深刻地影响着“先学后教”模式的形成与内涵。
先学后教;演进;制度化教育;知识观
“先学后教”的基本意蕴在于通过改变教学中的师生关系,使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转变为指导者和辅助者,教学顺序改变为学生“先学”而教师“后教”,以保证教学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更具针对性。[1]“先学后教”一反传统教育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先教后学”模式,将学生的“学”置于教学的中心位置,可以说是对班级授课制以“教”为中心的教育体系的一种“反叛”。近些年来,在新课改的推动下,各地涌现出了不少突出学生自学的教学模式,最著名的有杜郎口中学的“10+35”模式、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模式和东庐中学的“讲学稿”模式。这些以学生自学为特色的课改模式,人们又将其统称为“先学后教”模式,并认为“先学后教”模式是一种带有原创性的、本土化的教学模式。[2]那么“先学后教”模式在我国有着怎样的探索历程?又是什么因素推动着“先学后教”模式的不断探索呢?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一论述。
一、近百年来“先学后教”模式在我国的五次主要探索
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是以“学”为中心的,“以学为本,因学论教”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教学的重要特征,自学也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当以班级授课制度为特色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嵌入”我国,并在我国逐步推广后,传统的以“学”为中心的教育体系逐渐被以“教”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所取代,“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重‘学’的特点及其合理因素也一起被抛弃了。”[3]学生的“学”由主动变为被动,自学精神得不到彰显,由此,“先学后教”模式开始了在我国的探索历程。纵观近百年来我国“教”与“学”的演进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先学后教”模式在我国的探索经历了五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民国初期,第二次出现在1920年代,第三次出现在1960年代,第四次出现在1980年代,第五次出现在新课改以来。
(一)民国初年的补偏救弊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培养具有自动精神的公民就成为当时教育的一大旨趣,尤其是受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及其德国哲学家倭铿、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影响,一股自动主义教育思潮开始在我国形成。这股强调自动的教育思潮对我国民国初的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孙世庆在《中国之初等教育》中写道:“因儿童自动主义学说传来,小学教员之思想为之一变。往日之教授法以教员之说明为教授之中心,此时则以儿童之动作为教授之中心。”[4]教育界开始对以“教”为中心的班级授课制度进行批判,并主张尊重儿童的自动力,倡导儿童自学,如署名天民的作者指出,“从来之教授法皆置教授之中心于教室,设活动之本位于教师。今则当移教授中心于自习室,置活动本位于学生。”“首宜减少教授时数,次宜编辑学生自习书。”[5]在教育实践领域,开始盛行自学辅导法,将学生的自学置于教学的中心位置,教师仅作辅导之用,但是此时的自学辅导法是为救复式教学缺乏师资之急,“仅是一种补偏救弊的办法”,[6]强调的自学也多为形式上的自学,对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强调并不多,正如吴研因等人的比喻,学生自学与教师辅导“好像工程师和工徒在一起建屋,工程师能明了一切,计划一切,工徒们不过做他的手足罢了。”“自学不过将现成的材料,受教师的辅导后,设法去学习。可说是部分的自学,是形式的自学,是受支配的学习,不是自己支配的学习。”[7]
(二)1920年代的兴盛与偏失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欧美新教育运动逐渐进入高潮,西方自动主义教育思潮已经由理念走向行动,各种批判传统教育,改革班级授课制度的新的教学模式逐渐形成,如帕克创立的“昆西教学法”、华虚朋创立的“文纳特卡制”、帕克赫斯特创立的“道尔顿制”、克伯屈倡导的“设计教学法”。此时的我国也正经历着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教育思潮的感知也甚为敏锐,在杜威诸弟子的鼓吹呐喊下,我国教学理念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革,教育的重心由教师转向学生,正如杜威所言,“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8]西方各种变革班级授课制度,倡导学生自学的教学模式在我国受到青睐,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等“先学后教”模式风行我国。但由于这些“先学后教”模式过分夸大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完全让儿童自主地去学习,未免高估了儿童的自学能力,如道尔顿制“没有班级、没有课程表、没有上下堂的分别,只是按各科设置若干作业室,教员在每一个月之初,把全月应当学习的功课指定好了,告诉学生,学生在规定作业的时间之内,可以随自己的高兴,自由到各作业室里学习,愿意先学什么就先学什么,不愿意学什么了就可以改做旁的功课,不受教员、课程表等的丝毫拘束,等到学习终了,教员考查成绩及格,便算完了这一个月的功课,再从新学习第二个月的功课。”[9]建立在儿童中心主义幻想中的这些“先学后教”模式,最终只能适得其反,阻抑儿童的学习成长进程,如道尔顿制被戏称为“逃而遁之”,设计教学法被戏称为“杀鸡教学法”。儿童的自学几乎成为儿童的“自由而学”,其偏失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三)1960年代的昙花一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将凯洛夫的教育学奉为圭臬,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民国时期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几种“先学后教”模式遭到了批判。建国初对民国时期这些“先学后教”模式的批评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对这些思想的否定缺乏辩证的考量,用简单的、阶级对立的思想对民国时期的这些教学模式进行了否定,造成我国教学关系由重“学”偏向重“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自觉主动性得不到张扬,使教学呈现出“少慢差费”的状况,造成课堂教学的呆板和机械。
1956年后随着中苏关系微妙的变化,我国开始反思学习苏联教育中的教条主义问题,意识到教学中只强调教师主导作用的弊病,开始注意到学生学习自主性的问题。随着大跃进逐渐渗透到教育教学领域,为解决教学领域的“少慢差费”问题,教育领域开展了对“量力性原则”的批判,加之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批判“注入式教学”,倡导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如1964年与毛远新的谈话中就指出,“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10]由此,各地进行了各种教学改革的探索,倡导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尤以上海育才中学的教改最为典型。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反思了过去教学不重视学生“学”的作用的弊病,提出要“让学生学会自己看书、自己练习、教师再加以指导”。[11]在育才中学进行“先学后教”的实验,如在讲授语文课《英雄列车》时,“教师开始并不讲解,而是让学生在课堂上读书,边读边议。读了一遍后,就叫学生自己讲解。除了几个难理解的地方外,学生讲得头头是道。讲完以后,教师抓住学生没有讲清楚的难点、作了画龙点睛式的讲解。整个课堂,教师讲的还没有学生讲得多,课后也没有给学生留任何作业。”[12]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彻底否定了以上课为形式、教师主导、知识授受的教学认识论,认为这种教学认识论是“扼杀学生主动性的洋八股”,学校教育制度遭到破坏,教师的作用受到鄙弃,“先学后教”突破了学校的范围,变成完全独立自主的学习。
(四)1980年代的模式多元
“文革”结束后,在揭批“四人帮”破坏教育秩序的罪行的同时,我国重建了教学秩序,重新提出学校教育要以教学为主的方针,为“先学后教”模式的重新探索提供了正常的教学环境。改革开放后,新的启蒙运动在我国兴起,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得到探讨,在西方各种倡导学生自学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教育界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予以了高度重视,在这种背景下,各地不约而同地开展学生自学的教学改革实验,并形成了几种有价值的“先学后教”模式。如,上海育才中学段力佩提出的“先练后讲”的教学模式,即“读读、议议、练练、讲讲”,因为这种教学形式中的学生有些像茶馆里的茶客,因此,也被称作“有领导的‘茶馆’式的教学形式”[13];江苏常州邱学华提出的尝试教学模式,主张让学生在尝试中学习,冲破“先讲后练”的传统教育模式,构建了“先练后讲”的新型教学模式;黎世法的异步教学法,将学生的“六步学习”和教师的“四步指导”结合了起来,“一上课,教师首先向全班学生布置本节课的学习任务,接着教师针对本节课要解决的学习问题进行启发,然后学生根据教师的启发,按照“六步学习法”(自学→启发→复习→作业→改错→小结)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独立自学,逐个地解决本节课所学新课中的问题。与此同时,教师走下讲台,来到学生中间,巡回走动。按照“四步指导法”(提出问题→启发思维→研讨学习→强化学习)对学生的自学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异步指导;[14]魏书生提出“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自结”的“六步教学法”。除此之外还有中科院心理所卢仲衡的自学辅导法、上海嘉定中学钱梦龙的三主式导读教学模式等。这些“先学后教”模式的探索尝试,对改进班级授课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由于这些尝试多以提高知识学习的效率为中心,将学生视为一个“知识的容器”,将课堂视为知识的转换地,无视学生的主体性、生命性,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五)新课改后的争议重重
进入19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主体性教育思想在我国形成,同时受西方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知识观的影响,现代知识观逐渐向后现代知识观转型,知识由以往客观的、中立的转向主观的、情境性的,知识观的这种转型使得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发生着改变,“学习不是知识由教师向学生的传递,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学习者不是被动的信息吸收者,相反,他要主动地建构信息的意义,这种建构不可能由其他人代替”,[15]学生成为一个知识的主动建构者。2001年开始的新课程改革,将“转变学习方式”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自主学习热在全国形成,洋思模式、杜郎口模式、东庐模式受到热捧,“还课堂于学生”成为一时风气,教学实践领域似乎正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但是与此同时,“先学后教”模式也有走向“唯自主化”的危险,一些学者将新课改以来出现的这种状况描述为“四个满堂”,即“满堂问”、“满堂动”、“满堂放”、“满堂夸”。[16]另有一些学者将新课改以来的课堂教学概括为“五个忌讳”,即“忌言讳讲”“忌讳批评”“忌讳管学生”“忌讳预设”“忌讳思考”。[17]一些学者对由“自主学习热”带来的“讲授法危机”进行了辩护。[18]学术界也就课堂教学领域“唯自主化”的倾向背后的知识观和教学观问题进行了争鸣,如“钟王之争”可以算作对“先学后教”模式争议的一个注脚。
二、对“先学后教”模式百年演进的思考
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在我国建立之日起,“先学后教”模式就开始了在我国的不断探索,究其原因,班级授课制“重教轻学”的痼疾是“先学后教”模式不断探索的根源,同时知识观的变迁影响着“先学后教”模式的形成与内涵。
(一)班级授课制“重教轻学”的痼疾是“先学后教”模式不断探索的根源
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最明显的特征是以班级授课制度取代传统的个别教学,试图实现“一个先生同时可以教几百个学生”[19]的愿景,它虽然适应了教育普及的需要,“把学生集体作为教育对象,开辟了从外延上提高教育效率的途径”,[20]但是集体集中式的班级授课制度却使有着生命的教学变成了一种工厂式的生冷的知识传授过程,强调教师的主导和将课堂教学模式化,使得课堂变得呆板机械,教师的“教”反而压制了学生的“学”,学生成了一个接受教师讲授知识的“受教育者”,成为了一个“被动的学习者”,学习者的学习能力逐步退化,自学精神日渐式微。如恽代英就认为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容易造成学生学习能力的“退化”,“学生太看重了教师。自己不能养成好学研究思考的习惯,所以离了学校,离开教师,便求不成学问。”[21]杨贤江同样指责班级授课制度下的学生“有受动而无自动。”[22]正是由于班级授课制度这种“重教轻学”“有教无学”的弊病,使得其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不断遭受批判和改革,“近代建立新学校采取班级授课制后,才出现了重教授轻自学的情况,因此不少教育家一直在纠偏。”[23]由此才有了“先学后教”模式的不断探索。
(二)知识观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先学后教”模式的形成与内涵
有什么样的知识观就有什么样的教学观、师生观和相应的学习观。正如石中英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中所言,“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师生双方对知识的性质怎么看,很自然地影响到各自的角色,影响到师生关系的互动,甚至影响到教学评价的模式。”[24]如当强调儿童经验知识最重要时,教育必然重视学生的自主探索、自学;当强调科学知识重要时,教学中教师主导作用将受到重视。当认为知识具有建构性时,必然会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当认为知识是客观不可变时,就容易造成教学中的灌输与对学生主体的无视。知识观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先学后教”模式的演进,如民国时期受欧美“儿童中心主义”的影响较大,强调儿童在活动中经验的获得,对系统的学科知识的学习有所忽视,认为儿童的成长是儿童在与外部环境的接触中,经验自然生长的过程,所以“教学为一种刺激和指导儿童的学习的活动”,儿童的学习“完全是儿童自己的事情,教师的教学不能够用来代替儿童的学习。在教学上,教师的任务,仅在于刺激和指导,至于儿童是否学习,完全要看他们做怎样的反应。”[25]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爆发,这一阶段对民国时期“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清算,代之以苏联教育学理论。否定了以儿童经验为中心的教育,确立了知识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认为教学过程就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必须居于主导地位,学生学习自主性得不到体现,“先学后教”模式遭到否定。当前知识观逐渐由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知识的情境性、体验性受到重视,与此相应,教学过程也不再是一种特殊认识的过程,而是一个由学习者建构知识的过程,“先学后教”模式成为这种知识观下的教学的基本样态。
通过对“先学后教”模式在我国演进的梳理,我们认识到“先学后教”模式不是新课改后才出现的一个新型教学模式,而是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在我国建立后就开始兴起的一种教学流派,它是以对抗班级授课制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面貌出现的。我们认为只要制度化教育没有丧失其存在的根基,对“先学后教”模式的探索也不会止步。制度从其起源和价值看是为保障自由的,但是当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走向“制度化”,发生异化,“制度的同一性、稳定性、规约性发挥到极致,就成为‘制度化’,它是制度的一种异化形式,是制度弊端的集中表现,任何一种制度运用不当都有可能沦为‘制度化’。”[26]“制度化”背离了制度设置的初衷,使得制度成为束缚人自由发展的“牢笼”。学校教育制度也是如此,从学校教育的起源看,学校教育是为满足人们求学的需要、实现学习者的学习自由,但是当学校教育走向制度化时,学校教育制度反而成了束缚学习者自由学习的羁绊。由此,在学校教育制度下,倡导学生自学,变“先教后学”为“先学后教”就成为课堂教学改革的一条主线,可以说,只要以班级授课制为核心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存在下去,对“先学后教”模式的探索也将继续下去。
[1]刘家访.先学后教运行机制的重建[J].中国教育学刊,2011,(11).
[2]屠锦红,李如密.“先学后教”教学模式:学理分析、价值透视及实践反思[J].课程教材教法,2013,(3).
[3]杜成宪.以“学”为核心的教育话语体系——从语言文字的视角谈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重“学”现象[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3).
[4]孙世庆.中国之初等教育[A].舒新城.中国新教育概况[C].北京:中华书局,1928,71.
[5]天民.中学校亟须改革之点[J].教育杂志,1918,(9).
[6]俞子夷.现代我国小学教学法演变一斑[A].董远骞.俞子夷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480-485.
[7]吴研因,沈百英.小学教学法概要[J].教育杂志,1924,(1).
[8]杜威.学校与社会[A].赵祥麟,王承绪.杜威教育论著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32.
[9]许兴凯.道尔顿制的实际[J].晨报副刊,1925,(12).
[10]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纪要[A].毛主席论教育革命[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22.
[11]段力佩.教海浮沉话甘苦[J].上海教育(中学版),1989,(3).
[12]张煦棠,刘文峰,沈景华.育才中学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J].上海教育,1964,(4).
[13]段力佩.领导的“茶馆”式的教学形式——读读、议议、练练、讲讲[A].段力佩教育文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70.
[14]黎世法.异步教学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23.
[15]陈琦,张建伟.建构主义学习观要义评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1).
[16]程少堂.第三只眼睛看课改[N].深圳特区报,2004-11-2.
[17]朱开群.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主导作用的缺失[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6,(12).
[18]参见陈振华.讲授法的危机与出路[J].中国教育学刊,2011(6)和丛立新.讲授法的合理与合法[J].教育研究,2008,(7).
[19]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10.
[20]陈桂生.教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9.
[2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恽代英教育文选[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138.
[22]杨贤江.学生自动之必要及其事业[A].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杨贤江教育文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2.
[23]钟秉林.自我教育是体现本质、真正生效的教育[J].中国教育学刊,2013,(1).
[24]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28.
[25]赵廷为.教材及教学法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7.
[26]刘国艳.制度分析视野中的学校变革[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55.
(责任编辑:孙宽宁)
*本文系四川师范大学2014年校级青年项目《“先学后教”模式在我国的百年演进研究》的成果。
刘秀峰/四川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和农村教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