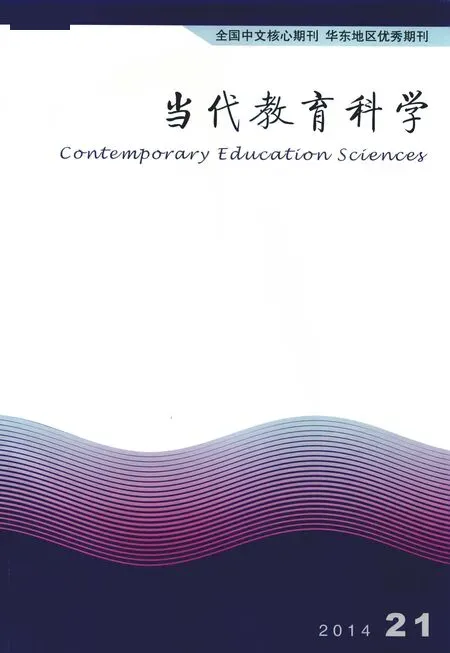行动研究的内在逻辑及其教育启示
●郭文良
行动研究的内在逻辑及其教育启示
●郭文良
行动研究与传统教育研究在理论基础、研究主体、研究场域、研究目的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行动研究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即“行动-研究”逻辑、“反思—行动”逻辑、“理性-反思”逻辑。行动研究与传统教育研究走向融合是教育研究范式的变革方向。
行动研究;内在逻辑;教育启示
行动研究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复兴的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1]由此行动研究再度兴起,并作为实践取向的教育研究范式弥补了教育研究的实践困扰,促进了教育研究的发展。
一、行动研究与传统教育研究的差异
行动研究与传统教育研究都是为了揭示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但两种范式又有着显著的差异性。
其一,理论基础不同。行动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反思理性,而传统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科技理性。反思理性有三个基本假设:一是复杂的实际问题需要特定的解决办法;二是这些解决办法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发展出来,因为问题是在该情境中发生和形成的,实际工作者是其中关键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三是这些解决办法不能任意地使用到其他的情境中进行检验。反思理性是行动研究的理论基础,它表达的是实践者的“实践理论”的显现过程。[2]传统教育研究以科技理性作为理论基础。科技理性是以数学或逻辑以及实证知识为基础的思维方法、手段及信念,其运行模式是一种“研究—开发—推广”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研究者和学校教师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者负责教育规律的研究与开发,然后由学校教师实践推广。
其二,研究主体不同。行动研究的主体是教育实践工作者,同时也是教育研究的应用者。教育实践工作者通过将研究和行动相结合,直接应用于自身研究成果,改进教学,提高教育质量,从根本上塑造了教育实践工作者的新形象。叶澜教授认为:“当教育研究主体深层次介入研究对象时,教育研究主体不仅研究对象,而且直接创造对象,主体不但不停留在‘说明’对象上,也不停留在‘解释’和‘理解’对象上,而是进入‘创造’对象的境界。”[3]进一步说,当教育研究主体成为了研究对象,成为了教育实践工作者,无疑对教育研究具有巨大作用。而传统教育研究主体一般为教育理论研究者,通过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教育理论的研究,以形成一定的教育理论规范,并通过教育实践工作者将教育理论规范付诸实践。
其三,研究场域不同。行动研究的场域是学校和课堂情境。教育研究场域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在哪里做研究的问题。以学校作为行动研究的场域,将学校最真实性的一面展现给教育研究者,不去控制、调节学校各因素,目的是通过对学校现实的描述、分析、总结,最后得出真实情境下的学校场域研究成果。同样,教育研究者以真实的课堂作为研究场域,不去干扰课堂各要素的设置,通过展现课堂真实的方方面面,就易得出真实情境下的课堂场域研究成果。与此对应的,传统教育研究场域往往是可控环境场域,通过对研究场域进行人为的设置与干预,得出普遍的教育规律。
其四,研究目的不同。行动研究的目的是理解现实教育情境、改进教育实践、促进教育变革,最终实现研究成果的小范围推广。在教育实践中研究实践,能够更深入理解现实教育情境中的教育现象、教育问题,针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做出具体地解释与指导。“改进”是行动研究的主要功能,它既能解决教育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也能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4]行动研究关注的不是教育理论问题,而是教育实践问题,并针对教育实践问题提供改进措施。行动研究让教师成为研究者,改变了教育研究的现状,实现了教育变革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行动研究是现场研究,因针对的是教育实践问题,故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种特点决定了行动研究的成果定位为小范围推广,即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当前的或相似的教育情境之中。相对而言,传统教育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教育规律、丰富教育理论、出版教育著作,实现研究成果的大范围推广。
二、行动研究的内在逻辑
行动研究作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教育研究范式,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般来讲,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行动—研究”逻辑
“行动—研究”逻辑主要涉及行动对研究的影响和研究对行动的影响。首先,就行动对研究的影响而言,行动让研究更为科学化、具体化。大卫·布鲁尔曾说:“对我们的思想进行构造和指引的都是一些观念,这些观念的真实特征也就是某一个社会模型所具有的特征。”[5]思想与观念的深化就是一种研究,而社会模型一般通过行动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研究的深入发展需要行动。因此,行动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直接指向研究的科学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性。其次,就研究对行动的影响而言,研究是借助于行动并为了更好地行动。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需要借助于具体的行动得以开展,同时,研究的重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行动,实现行动的完善与深化。从行动对研究的影响与研究的行动的价值看,这种逻辑性体现了行动与研究的和谐共生关系。
行动研究的内在逻辑包含着“行动—研究”逻辑,并以这一逻辑为理论基础,实现行动研究的真正价值。具体而言,“行动”和“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工作者那里,是两个用以说明由不同的人从事不同性质的活动的概念。“行动”主要指实践者、实际工作者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工作;“研究”则主要指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工作者、专家学者对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科学的探索。[6]行动与研究的结合,为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开辟了新的路径——既强调研究,又强调行动,用行动监督研究,用研究指导行动。
(二)“反思—行动”逻辑
“反思—行动”逻辑主要表现为反思对行动的作用。反思能够促进行动的规范化与合理化。行动可以拆分为行为和动作。帕森斯认为,一切行动都是行为,但所有行为未必都是行动,行为成为行动需要行动力。行动力是愿意不断学习、思考,养成习惯和动机,进而获得导致实现目标结果的行为能力。反思是对过去的思考,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促进行为的发展完善。行为要转化为行动需要行动力,形成动机需要,在此过程中需要反思并加以深化提升。可以说,反思是行动得以完善的条件,行动又是反思的结果和目的。反思对行动的作用,内在要求着行动与反思的结合。
行动研究的内在逻辑包含着“反思—行动”逻辑,体现着反思对行动研究的价值。首先,行动研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反思的深度。反思是针对现象或问题而进行的,这需要行动和反思的结合。如果是简单的思考而不是深刻反思,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在行动研究过程中,不仅需要反思,而且需要“思”的深刻,“思”到关键处,以促进行动研究向纵深处发展。其次,行动研究的程序包含有反思的环节,凸显出反思在行动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凯米斯认为,行动研究是一个螺旋式加深的发展过程,包括“计划—行动—考察—反思—再计划”的循环式过程。最后,有反思的行动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在反思中不断行动,凸显了反思不是空谈、空思,而是为了行动、在行动中进行反思,以促进行动研究的发展。
(三)“理性—反思”逻辑
要理解“理性—反思”逻辑,就需要深入人的理性世界。人性是理性的基础和前提。对人性的探讨主要存在两种基本方式:一是从形而上学的视角考察人之为人的终极本性,即理性本性;二是从人类现实活动的视角考察人之为人的特有行为,即符号本性。[7]从表现形式看,人性表现为理性本性,从表现内容看,人性表现为符号本性。事实上,人正是通过理性本性和符号本性来把握世界的。人的行为是在理性本性和符号本性的融合与相互作用中得以产生的。反思是连接理性本性与符号本性的桥梁,通过对符号本性的反思,以实现理性本性的发展,同时理性又作用于反思,让反思更有深度和效度。
行动研究的内在逻辑包含着“理性—反思”逻辑。根据反思时间的不同,可将行动研究中的反思分为行动中的反思与行动后的反思。行动中的反思是指在行动过程中针对其遇到的具体问题而进行的反思,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调整。行动后的反思有三类,一是对行动的“回顾”,二是对行动的“研究”,三是“再理论化”。[8]无论是行动中的反思,还是行动后的反思都离不开人的理性。理性提升了对实践反思的层次。行动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实践,正如埃利奥特所说:“行动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改进实践而不是构建理论,构建和利用理论从属于且依赖于这个基本目的。”[9]行动研究改进实践的主要方式是反思,反思的不断提升来源于人的理性的推动作用。
三、行动研究的教育启示
从行动研究的特点和内在逻辑出发,为教育研究范式的变革指明了方向。
(一)研究主体的融合: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合一
教育研究范式走向教育研究主体的融合,即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合一。传统教育研究的主体是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其相对应的是教育实践主体即教育实践者。行动研究将研究主体从教育理论研究者转向教育实践者,让教育实践者成为教育研究的主体。从教育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教育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经历了由合到分再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没有专门的教育理论研究者,人们的经验来自于实践,拥有实践经验的人被称为“专家”,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是合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导致了教育研究主体的分化。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正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10]社会分工使得研究者专门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教师专门从事教育实践工作。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是分离的。教育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的分离造成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在批判教育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背景下,教育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开始走向融合,即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合一。
(二)研究过程的融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统一
教育研究范式走向教育研究过程的融合。教育研究的过程经历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过程到自上而下的研究过程,再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研究过程的统一。在人类社会早期,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表现为传递生产与生活经验的活动,教育研究即是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研究,这种教育研究过程是沿着自下而上的路径发展的。所谓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是指教育研究从实践活动到经验的总结,并形成对教育的一般认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研究也在不断地变化,社会分工导致专门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人的出现。这一时期,教育研究过程开始从自下而上转移到自上而下地发展。所谓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是指教育研究从假设到验证再到推广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反映了教育研究科学化的进程,体现了教育研究走向对教育规律、教育真理地直接探索。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各环节的不断整合,促进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变革,教育研究过程走向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统一。
(三)研究结果的融合:普遍性与有效性的统一
教育研究范式走向教育研究结果的融合。从教育科学的历史发展看,教育研究结果沿着追求教育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到追求教育研究结果的普遍规律,再到普遍性与有效性的统一。在教育科学发展初期,解决教育中的实际问题是教育研究的客观需要,教育研究结果往往以有效性的方式呈现。随着教育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从教育研究结果的有效性转向了追求教育的普遍规律即教育研究结果的普遍性上。可以说,对教育普遍规律的探究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是教育研究科学化、规范化的标志。当过分强调教育规律的普遍性而忽视教育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就会产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范式走向教育研究结果的普遍性与有效性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一方面是教育科学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受到行动研究范式的影响。在为什么做研究中,传统教育研究范式侧重提出可以推广的理论、出版论著等,行动研究则侧重理解情境、改进实践和带动革新。[11]可见,传统教育研究范式强调追求教育的普遍规律,行动研究强调追求教育结果的有效指导实践,教育研究范式在这两种研究范式的比较中走向融合。
[1]钟启泉,张华.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
[2]陈向明.什么是“行动研究”[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2).
[3]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339.
[4]郑金洲,陶保平,孔企平.学校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241.
[5]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M].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78.
[6]郑金洲.行动研究:一种日益受到关注的研究方法[J].上海高教研究,1997,(1).
[7][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33-34.
[8]赵明仁,蔡瑞萍.教育行动研究的过程分析[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3,(5).
[9]Elliott,J.Action Rerearch for Educational Change,Open University Press,1991,49.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5-36.
[11]杨明全.行动研究与课程创新[J].教师教育研究,2004,(4).
(责任编辑:刘丙元)
郭文良/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