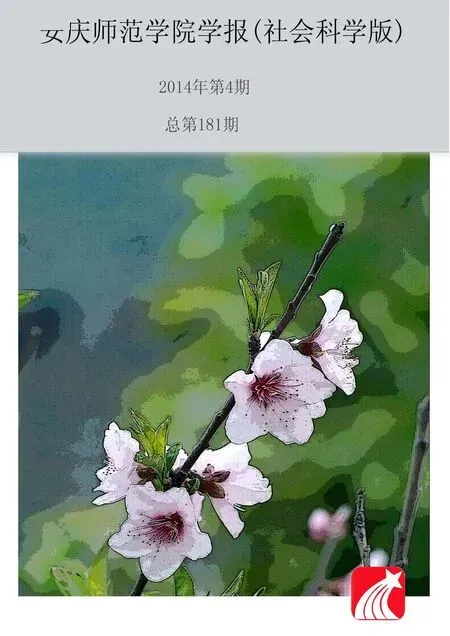郭象对《庄子·齐物论》的自然诠释
路 高 学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郭象对《庄子·齐物论》的自然诠释
路 高 学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自然”一词在郭象的诠释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郭象在《齐物论注》中,通过对“吾丧我”的自然诠释,展现了物自然其所然的形态;用物的自然之境来观照人,强调人的自生自是;用自然来诠释名教,强调人应“各当其分”;用自然来批判社会文化现象,否定社会文化上的是非纷争;用自然来诠释“道”,强调“道”之自然“独化于玄冥”。郭象对《齐物论》的自然诠释,是其自然哲学体系中的核心环节。
齐物论;物;自然;诠释;道
郭象的《庄子注》(学界对于《庄子注》的作者是郭象还是向秀存在着争议,本文无愿去考证其中的纠纷,默认今本《庄子注》为郭象作品)遵循道家“言不尽意”的传统,采用“寄言以出意”(《庄子注·山木》)的方法,在注解《庄子》的同时,阐发郭象自己的哲学思想。后世有言:“无者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大正藏·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今人刘笑敢认为,郭象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概念和命题”,赋予了经典“新的生命力和时代性”[1]。而《齐物论》作为《庄子》一书中最为艰深晦涩的篇章,自然是郭象诠释的重点。
一、自然:自然其所然
郭象在诠释《齐物论》的过程中大量使用“自然”一词,其思想主旨也被学者称为“自然的存有论”。[2]163因此,笔者拟以“自然”一词为切入点,对郭象对《齐物论》的诠释进行探究。在道家的思想体系中,“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其独特的含义,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自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如今我们所使用的“自然”一词多指与社会领域相对的自然界,具有浓厚的客观意义。而在中国传统道家的理论旨趣中,自然是指“精神生活上的观念”,“就是自由自在,自己如此,无所依靠”[3]。在魏晋玄学家那里,“自然”是与“名教”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人物之‘自生、自得、自由、自顺其性,而非由外物使其必然如此如此然’”的情态之辞[4]568。
郭象在注解《庄子》中多次使用“自然”一词,其中内七篇注中有64次,仅《齐物论注》中就有19次之多。而《庄子》内七篇中“自然”一词共出现2次,分别在《德充符》篇和《应帝王》篇。由此可见,“自然”在郭象《庄子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要理解“自然”一词,首先应从认识“然”开始。“然”,古同“燃”,是指燃烧的意思,后来又衍生出肯定、合理之意,也可以作为形容词词尾表示“……的样子”[5]。唐君毅根据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记载,认为:“此‘燃’之一字,依说文谓从肉(月)在火上,而犬在其旁,即有然悦、肯可之义;而火之炎上,即有生发之义。故用为‘火之始然’之然。”[4]567因而“自然”,顾名思义,即为自始之然。老子有言:“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这里所讲的“自然”应是人与万物“自顺其性”、“自生其所生”、“自由其所由、自得其所得”的“自然其所然”[4]567。而庄子所讲的“自然”,强调主体的普遍性、能动性。
庄子曰:“是非吾所谓调情。吾所调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
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汉,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
庄子注重人的心灵解脱,“恒指点吾人能不安不忍,于成心之茫昧陷溺中超拔出来,调适上遂,以安顿吾人之身心性命,自适其适,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一心之真淳彻达,是重主体实践的主要内容。”[2]164
“自然”一词在郭象《齐物论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有学者根据郭象所诠释的义理,把他的思想归为“自然的存有论”,认为他“论自然,除了老、庄所特重的自然之主体义之外,举凡命遇奇偶、才知之小大,运会之盛衰、事物之形势逆顺、伦常之尊卑分际等,率皆归属于自然”,远远地超越了前代[2]163。郭象继承王弼等玄学家关于“自然”的观点,通过注解《庄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强调人与物的特殊性和个性,摆脱了庄子过分强调主体而忽视个体的客体意义的束缚,注重个体各自的“自然其所然”。这种发展使道家的“自然”学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按钱穆的说法:“必俟有郭象之说,而后道家之言自然,乃始到达一深邃圆密之境界,后之人乃不复能驾出其上而别有所增胜。”[6]
从重心之主体义到重人、物的个体义,从重主体的能动性和普遍性到重个体的特殊性和限制性,道家的“自然”学说发展到郭象这里到达一个更为完满圆融的境界。郭象也正是以这种圆融的“自然”观来诠释《庄子·齐物论》。
二、“重明天籁”:对物的自然诠释
庄子在《逍遥游》中描绘了一个“游”的极致境界——“逍遥”,并把它归为自然而然的“道”,铸就了《庄子》一书的灵魂和基调。《齐物论》上承《逍遥游》之精神主旨,郭象以“吾丧我”的“天籁”之境中的“自然”旨趣为切入点,展开了对《齐物论》的自然诠释。
在进入郭象对《齐物论》中物的自然诠释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他对“齐物论”的解释。郭象言:
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恶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虽异而彼我均也。[7]48
郭象认为万物都有一种自我的中心主义:“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恶人”。这里讲的“物”应该囊括世间的一切,也包括人在内。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放大,人为地赋予了人外之物以人的情感,也是一种人作为主体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可是,郭象又说“是非虽异而彼我均也”,认为万物虽然有差异但都是一样的,明显是要万物破除“是非”的偏见,认识到它们本质上的一致之处。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恶人”都是万物都具有的,是不是一种“均”呢?要如何来破除呢?
庄子在《齐物论》中首先通过子綦和子游的对话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天籁”之境。子綦曰: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庄子·齐物论》)
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齐物论》)
庄子形象地描绘了风所产生的不同形态,用来表示万物产生的根源,指出了各种现象都是产生于物之自身的。冯友兰认为庄子的本意并不是要提出“怒者其谁邪”的问题,而是要取消问题,因为“‘自己’和‘自取’都表示不需要另外一个发动者”[8]。而郭象认为:
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而,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7]55-56
郭象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把物的“生”看成是其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且把这种现象称为“天道”。而实际上,“天籁”只不过是人的一种主观的“吾丧我”之后的精神状态,是意识的主观产物,并不能代表事实即为如此。郭象紧紧抓住了庄子讲的“天籁”之意,把它从一种个体的主观体验扩大到任何一物,认为物的存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天籁”,他说:
物皆自得之耳,谁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籁也。[7]56
郭象所理解的“天籁”和庄子的原意是有差异的。庄子侧重于主体主观上的境界感知;而郭象则侧重于个体的存在现象。
综上所述,《齐物论》是从对“物”的理解开始,把“天籁”之境看作是“物”自然而然的结果——无所生,也无所用。郭象也正从对“天籁”的“重明”进入到对人、社会文化以及“道”的诠释。
三、“言其自生”:对人的自然诠释
在郭象看来,庄子所言之“物”是包括世间一切的,当然也包括人及人类社会。这是道家学说一以贯之的观点。当然,如此之说并不代表道家不言人与社会。道家思想的一个传统就是以物*此物指与人和社会文化相对之物。之自然主义来观照人,来批判社会文明,来否定社会文化。
在《齐物论》中,庄子通过对“天籁”之境的论述转向了对人的理解,庄子曰: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执,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庄子·齐物论》)
庄子在这一部分对“大”、“小”两种人不同的心理情态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说明人虽有才智、德行等不同,但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莫知其所萌”。冯友兰认为庄子“是用形象化的语言写心理现象的千变万化”,讲的是人的主观世界[8]。而这种人之主观上表现出的“缦”、“窖”、“密”等精神情态,都必然会表现出差异性的恐惧之心、是非之心。这样的人就像自然之物到了秋冬季节就会衰败一样,最后都会衰亡;他们沉溺于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不能回复如初;他们“厌没于欲,老而愈恤”;他们有“耽滞之心”,心灵闭塞受到束缚而不能得到解脱。[7]59在庄子看来,这些“喜怒哀乐,虑叹变执,姚佚启态”的各种心理情态,就好像“乐出虚,蒸成菌”,而那些“大知”、“小知”之人却没有认识到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郭象基本上同意上述庄子对人的心理情态的描述,但是在如何破除这些情态的困扰方面两人的观点略有不同。郭象通过承认个体的差异性,强调个体的不同,正如其言:
此盖事变之异也。自此以上,略举天籁之无方;自此以下,明无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则形虽弥异,其然弥同也。[7]60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万物,变化日新,与时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7]60
郭象把人之个性、情态的不同,也看成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是谓“言其自生”[7]60。
郭象从庄子主观的否定态度转向了对个体存在的肯定态度,以“无方之自然”实现了对人之“形虽弥异,其然弥同”的自然诠释。郭象把世间的人与物都归为“自然”,同时也否定了个体的主观意志,就如其在对《德充符》注解中所说的:
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而横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7]205
郭象把生命中的一切都归为自然的结果,包括人的出生以及存在在内,都不是人的意志所能管控的。这是不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呢?
从表面上看,郭象的自然哲学在论述人的时候去除了人的主观意志,或者说把人的各种存在形态也看成是自然而生的结果,具有宿命论的倾向,但是他的根本旨趣是通过强调自然无为的工夫来达到某种玄冥的境界,是一种除却人之欢乐忧愁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不仅表现在对人事现象的认识上,而且更为突出地反映在对社会名教的诠释方面,而这才是郭象自然哲学的最终导向。
四、“各当其分”:对名教的自然诠释
在道家思想里,物性和人性是没有分别的,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郭象和庄子一样,从“吾丧我”的“天籁”之境来理解人的存在样态,把人看成是与物一样完全禀受自然之理的存在物,从而否定了个体的主体性。但所不同的是,庄子对名教也采取了完全否定的立场。而郭象却通过承认个体的特殊性对名教的存在进行了合理性论证,提出了“各当其分”的主张。
在《齐物论》中,庄子对是非彼我和现实的礼法关系持有一种批判态度,提出一种无是无非和无君的主张,其言曰: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庄子·齐物论》)
郭象认为,庄子所讲的“彼”为“自然”,而“自然生我,我自然生”,由自然而生的“我”完全禀受自然之理,并不受任何力量的支配;因此,人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7]62。正如成玄英所说:“信己而用,可意而行,天机自张,率性而动,自济自足,岂假物哉。”[7]62然而,人的这种“信己”而行是看不到的,所表现出来的只是“情智”。在庄子看来,人终生禀受自然之理,但是一旦有了是非之心而“与物相刃相床靡”就会“终身役役不见其成功”,就会“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这是非常可悲可哀的,这样的人活着和死了没有什么区别。而郭象则认为:“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7]63郭象也正是在这种“自然”状态下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他说:“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而他所反对的是臣妾不各安其才而“上下相冒”[7]63。
从郭象对名教的态度来看,他一方面承认自然的名教,并维护名教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批判异化的名教,反对名教的“上下相冒”,主张“各当其分”。郭象言:
皆说之,则是有所私也。有私则不能赅而存矣,故不说而自存,不为而自生也。[7]63
若皆私之,则志过其分,上下相冒,而莫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7]63
夫臣妾但各当其分耳,未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体,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7]64
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虽无错于当而必自当也。[7]64
在郭象看来,君臣、妻妾各有其位,各有等级的差别,都是天理自然的,是不能僭越的。然而,郭象不是对现实名教一味地肯定,而是主张“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主张在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才性之分,人人应各安于其性,而这种性是自然自生的。因此,从整体上来看,郭象所支持的是“贤者为君”;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不贤者就不能为君。从理论上看,这是郭象对名教的一种理想主义态度;而从魏晋时期的政治生态来看,郭象的名教思想又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可以说,郭象的自然哲学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集中反映,是以道家的自然主义精神对现实政治形态进行了一种合理性的证明,正如其言:
天下若无明王,则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实明王之功也。然功在无为而还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7]303
郭象一方面强调“明王之功”,另一方面又强调“无为”、“自任”,但是最终还是着重强调道家的“无为”。
综合前述,郭象的名教观和他的自然哲学是密切相关的。郭象的自然哲学一方面继承了庄子对现实礼法的批判精神,对现实名教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个体存在的特殊性而把名教中的伦常制度、礼节秩序看成是天理之自然,强调各依其才、各安其位,“无为”而“自得”,又为魏晋时期的政治生态提供了合理性的证明,已和庄子的旨趣十分不同。
五、“无是无非”:对文化现象的自然诠释
郭象在《齐物论注》中除了论述社会伦常的名教之外,对文化现象也进行了诠释。庄子在《齐物论》中把人看成是与物一样完全禀受自然之理的存在物,否定个体的主体性,并进而对文化现象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按照劳思光的观点,庄子是从“情意我”的角度对“认知我”进行了否定,认为知识的存在是无意义的[9]。而郭象则通过 “彼我”之“反覆相喻”、“相明”,论证了万物皆“既同于自是,又均于相非”,强调“万物各当其分,同于自得,而无是无非”[7]75,并由此指向了庄子“道通为一”的境界。
庄子把“言”与“吹”相比,认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庄子·齐物论》)。庄子是把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相比,用自然现象中物的“自然其所然”来观照社会文化。他认为社会上的各家各派都是以自家之说为“是”而以他派学说为“非”,如其言曰:“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他不但把儒墨各家的言论都看成是“浮辩之辞”,而且认为他们是违背“道”的结果,因此主张泯灭“是非”,对文化现象持有否定态度。而郭象没有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而是主张通过儒墨之“反覆相明”来宣扬“无是无非”,其言曰:
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无是无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无是无非也。欲明无是无非,则莫若还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则无非,非是则无是。[7]70-71
在郭象看来,是非之言皆是“彼我之情偏”的结果;有“彼我之情偏”,则有“我以为是而彼以为非”[7]68。如此,世界上就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言论。然而儒墨之士又据己之言以为有。郭象言:
夫小成荣华,自隐于道,而道不可隐也。则真伪是非者,行于荣华而止于实当,见于小成而灭于大全也。[7]70
郭象一方面肯定了儒墨之言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是“隐于道”的,不是真正的 “道”。如此,郭象就超越了社会文化的是非纷争,主张一种“无是无非”的文化观。
郭象所持有的文化观是对庄子文化观的一种诠释,是其自然哲学逻辑演进的自然结果,与庄子本人的观点有一定的差异。庄子曰: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
庄子认为物本来是没有是非之分的,但是人却往往各持己见,“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不能认识到各自只是偏安一隅、各执一词,由此也不能真正地理解“道”。在庄子看来,真正的“道”是没有是非纷争的,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准确理解和把握“道”,才能“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对此成玄英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是非两幻,凝神独见而无对于天下”,才可以“得道枢要”而“会其玄极”[7]73。而郭象则认为:“夫是非反覆,相寻无穷,故谓之环。环中,空矣;今以是非为环而得其中者,无是无非也。”[7]74在郭象看来,是非之争即为“环”,而作为“道”之“枢”的“环中”即是“无是无非”。郭象与庄子在文化观上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其特别强调“物”之“自是”,其言曰:
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则天下无是矣;无非是,则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也。[7]72
郭象把“物”之自是、自性普遍化、绝对化,强调个体存在的普遍意义,主张一种“无是无非”的“玄同”状态。从根本旨趣上看,郭象和庄子的文化观是一致的,都主张去除是非纷争,到达“道通为一”、“玄同彼我”之境。
由此,郭象的自然哲学从物的自然主义起,完成了对《齐物论》所论及的文化现象的自然诠释,进入到“道”的诠释。
六、“独化于玄冥”:对“道”的自然诠释
“道”是道家学说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代表了终极真理。与郭象重视个体自然的特殊性不同,庄子重主体普遍的能动性。庄子在《齐物论》中经过对物、人、名教和社会文化的论述之后,指向了对“道”的理解,主张“道通为一”。
庄子“道”的境界集中体现在“自得”一词。“自得”与“自然”意思相近,代表了庄子的逍遥之心:“逍遥游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庄子曰:
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庄子·齐物论》)
从中可以看出,庄子所讲的“道”是“已而不知其然”,即强调主体的主观感觉,通过主观破除“成”、“毁”之心,使主体从成心执着中超拔出来,认识到“物无成与毁”,也就是“道通为一”,也就是庄子《齐物论》的主要意旨。而在郭象看来,“道”是“不知所以因而自因”的[7]78,也是自然其所然的,其言曰:
夫莛横而楹纵,厉丑而西施好。所谓齐者,岂必齐形状、同规矩哉?故举纵横好丑、恢诡谲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则理虽万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为一”也。[7]76
由“理虽万殊而性同得”可知,郭象是从自然之性分来说齐一的。郭象认为,万物之“纵横好丑、恢诡谲怪”,都是自得的。因此,所谓“齐”或“道”之一,指的都是物物各是其所是,自然其所然。由此可知郭象与庄子二人对“道”理解的巨大差异:庄子“由心上做工夫,欲由成心之执超拔出来,无执无滞,则物论可齐”[2]174,强调的是主观上去除分别之心的“齐”,是一种“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而郭象则主张物性皆自然自得之“齐”,强调个体自然而然之“道”。
郭象对自然而然的“道”的理解,最突出地表现在“独化”一词。何为“独化”?万物“自然其所然”,即为“独化”。 郭象言: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得也。[7]117-118
“独化”在此处说得非常明白:第一,“物各自造”,没有一个造物者的存在;第二,物“无所待”,是共生共成的;第三,物是自然“独化”的,“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这也就是说,郭象否定了万事万物背后有一个创造他们的主宰之物,把物看成是自生的,而且万物之间也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共生共在的。犹如海德格尔把“存在者”看成是“涌现着的在场”的自然“存在者整体”,“让存在者是其所是”[10]。如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郭象的态度:他是把万物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自然的关系,强调个体的存在意义,以个体的论述为核心,认为应“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也就是“独化于玄冥”。
“道”在郭象的思想里不是一个“造物主”的形象,也不是一个空无的概念,而是指一种无能无为的存在样态。而“独化”,正是对这种存在样态的生动诠释。而对于“独化”与“道”的关系,郭象在《大宗师》中说的更为确切,其言曰:
道,无能也。此言得之于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为得也。然则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7]252
郭象把“道”看成是一个无能、无为的存在,但不是不存在,是存在的无;把物之“自得”称之为“道”的体现,但又不依赖于“道”,而是由“自得”而“独化”的。
郭象从“独化”的角度诠释了自己对“道”的理解,强调万物个体的自然之道。“独化于玄冥”所指向的即是万物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同时否定了事物外部有一个“造物主”的存在,也否定了事物自身可以有肆意妄为的情识之偏。
郭象在《齐物论注》中所诠释的哲学思想,是其自然哲学体系的核心环节。这也充分说明,郭象的哲学思想具有十分突出的个人特色,不能将它只视作简单的注解。
通观郭象的《齐物论注》,“自然”是其哲学思想中的核心概念。郭象的“自然”观与其对物、人、名教、文化、道的理解密切相关,彼此交融,贯穿了郭象思想的始终。而且在“自然”观的引领下,万事万物融为一体,最终走向了道之“独化于玄冥”的最高境界。
郭象由自然论齐物,就不可避免地强调个体的特殊性;同时,它也否定了个体具主体性的可能性。郭象一方面重主体之能动的普遍性而否定个体存在的主体性,是对庄子思想的一种继承;另一方面又承认个体存在的特殊性,强调个体存在的自然意义,是对庄子思想的一种发展。
[1]刘笑敢.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J].中国哲学史,2002(1) :32-40.
[2]庄耀郎.郭象《庄子注》的性分论[C]//洪汉鼎,傅永军.中国诠释学(第五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3]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03.
[4]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出版社,2006.
[5]王力,岑麟祥,林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22.
[6]钱穆.庄老通辨[M].北京:三联书店,2005:426.
[7]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冯友兰.三论庄子[J].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1(4):21-26.
[9]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7.
[10]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18-219.
责任编校:汪沛
2014-02-24
路高学,男,河南新郑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时间:2014-8-28 15:45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40828.1545.018.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4.018
B235.6
A
1003-4730(2014)04-0077-06
——王弼名教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