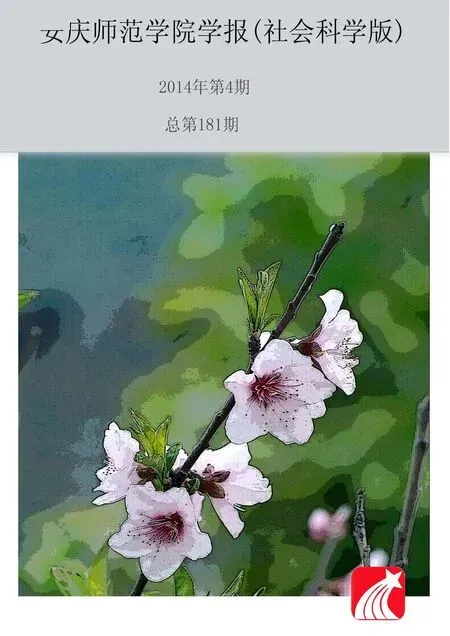社会主义荣辱观大众化的基本条件
罗 本 琦
(安庆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社会主义荣辱观大众化的基本条件
罗 本 琦
(安庆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有效的教育机制、过硬的精英群体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是实现社会主义荣辱观大众化的三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指向大众灵魂的教育,有效是荣辱观教育成败的关键;培育精英群体,以精英群体的道德实践彰显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导向,引导大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大众化的有效手段之一;人的复杂性及其趋利避害的本能决定了完善的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大众化的保障。
社会主义;荣辱观;大众化
荣辱观指人们关于什么是“荣”和什么是“辱”的根本观点和态度,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虽然“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但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都必然要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或者说主流的荣辱观,这是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主流荣辱观大众化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大众化的荣辱观才能成为主流伦理道德,才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发挥其社会导向的功能。所谓荣辱观大众化,不仅仅是让大众了解荣辱观的内容,而且还要求获得大众对这一荣辱观的普遍认同,使之成为人们普遍的内心信念或者信仰,使之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都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当代中国的主流荣辱观是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在理论上是没有争议的。然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大众化的使命远未完成。多年来久治不愈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特别是近年频频曝光的腐败现象、浪费现象,足以说明社会主义荣辱观大众化任重而道远。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荣辱观大众化?我们认为,有效的教育机制、过硬的精英群体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是实现社会主义荣辱观大众化的三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一、建立有效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机制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或者观念的大众化都需要借助教育途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大众化也不例外。但荣辱观的教育不同于一般知识或技能的教育。荣辱观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们掌握关于荣辱的理论——因为那本不是什么复杂的理论,而是要获得人们对特定的荣辱观的认同。这是一项指向大众灵魂的教育,有效性是荣辱观教育成败的关键。
荣辱观教育有效性的晴雨表是社会的价值导向和社会风尚。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社会价值导向就开始向物质倾斜,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开始滋生并迅速蔓延。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犯罪率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率大幅度上升,建国后一度消失的卖淫嫖娼及其副产品性病再度泛滥……诸多现象都印证了社会价值导向的变异,也映射了我国道德教育特别是荣辱观教育的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识之士呼吁要扼制道德滑坡现象。然而,长期以来,这种现象似无明显改观。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的复杂局面固然是重要原因,但荣辱观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应引起重视。
反思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实践,至少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没有正确处理好荣辱观教育与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的关系。以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取代荣辱观教育是我国过去思想政治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中有两种表现值得一提:一是改革开放前后(至少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直保持着每个星期三下午的政治学习传统,但学习的内容仅仅是读读有关文件,很少甚至没有把道德教育或者道德反省纳入学习范围;二是基层党组织生活也很少涉及伦理道德议题,即使是民主生活会充其量在工作领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至于伦理道德问题几乎成为人们不愿触及的禁区。第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都不同程度地受功利主义浸染。受物质利益诱导,社会上鼓吹得更多的是“事业的成功”、“财富的积累”,官场上晋升的快慢、商场上赚钱的多少成为荣辱的标志。看一看大量购物广告标榜的“尊贵”、“身份”、“地位”,听一听社交场合喧嚣的“升官发财”的问候,就不难感受到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严重背离。受社会风气影响,一度被认为远离世俗的学校也抛弃了曾经的清高,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不良荣辱观的侵蚀。家庭教育重视的往往不再是或者主要不是孩子道德品质,而是未来的前途。父母千方百计找关系把子女送到重点中小学、不择手段地把子女送到国外,并以此为荣耀。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向孩子们宣传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所有的传统美德都成为笑谈。可以说,整个社会没有形成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良性机制。
荣辱观不是什么精深的学问,因而它不一定需要教育者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基础,甚至对教育系统本身的组织结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荣辱观是人们对荣与辱的根本观点和态度,荣辱观教育的使命不仅仅要让大众真切地懂得什么是荣、什么是辱,更要求取得大众的认同。因此,荣辱观教育不仅对教育者的伦理操守有着异乎寻常的要求,而且对于教育手段的选择、教育系统的运作机制等等都有不同于一般教育的要求。显然,并不是什么样的教育体系都能够保证荣辱观教育的有效性。
什么样的教育系统才能保障荣辱观教育的有效率呢?
首先,应当保证不同教育渠道在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荣辱观导向的协调一致,即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高度协调。教育的有效性最基本的保证是协调,自相矛盾的教育是教育之大忌。荣辱观教育的目标是实现道德的内化,而环境是道德内化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或者是环境的产物。在道德内化的广义环境中,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发展水平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环境对人施加的道德影响。中国传统荣辱观教育或者说儒家荣辱观教育的成功经验之一就在于学校、家庭、社会的协调,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体化。儒家把自己的荣辱观渗透到家庭、学校、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得每一个人从幼儿时期就接收特定的荣辱观的洗礼,他们不但在学校能受到严格的伦理道德教育,在社会上也能体验到同质的荣辱观熏陶。因此,保证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有效性首先要规范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荣辱观教育,在教育系统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当融入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当然,学校教育各个链条中如何协调荣辱观教育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其次,应当保障教育内容的协调,即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政治教育等等协调。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本质上是伦理道德教育,它和政治教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不能相互取代。政治信仰的多样性与道德取向的多样性之间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同政治信仰的人可能会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伦理道德品质,反之亦然。但良好的道德品质对于政治信仰的巩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相对而言,伦理道德更具有基础性,道德教育较之政治教育亦具有基础性。因此,古今中外政治生活中对官员的政治信仰要求虽然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伦理道德品质要求。伦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这种关系,意味着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充分考虑包括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在内的伦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关系。至于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之间的关系,并无理论上的矛盾,但存在着观念上的误区和实际上的人为的冲突。表现为人们在追求知识教育的同时忽视道德教育,在选拔人才时重才轻德,唯才是举。如何使“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在教育与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中落到实处,是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二、培育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英群体
“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虽然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全体干部群众的要求,但要实现全体人民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目标,还需要精英群体的引领。培育精英群体,以精英群体的道德实践彰显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导向,引导大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大众化的有效手段之一。
发挥精英群体的作用是中国传统荣辱观大众化的经验。中国传统荣辱观主要指以儒家倡导的基本伦理范畴——“仁、义、礼、智、信、忠、孝、节、悌、恕、勇、让”等来表征的荣辱观。它是随着儒家的兴起和发展,并在秦汉以后融入百家思想形成的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荣辱观渊源于先秦儒家,基于春秋“礼崩乐坏”而对人性的深刻反省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中国传统荣辱观不仅是做人的基本目标,而且是治国安邦的基本要求,是儒者实现出世的动力。因此,历代儒家知识分子都把践行这一荣辱观作为基本义务,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线。由于儒家学说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国家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将“学而优”的儒家知识分子吸收到庞大的官僚队伍中来,并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彰显儒家荣辱观在国家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于是,形成了以官僚阶层、知识分子(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为主体的践行儒家荣辱观的精英群体。我们无意美化几千年封建社会中这一精英群体,但毋庸置疑,正是这一群体的以身体道才使儒家荣辱观普及到民间并世代相传,成为几千年中国社会最广泛的被认同的价值观,并维系着传统的中国社会。
发挥精英群体的作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欧洲文明孕育的理论体系。20世纪到来时,中国也不过若干有海外经历的知识分子知道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短短的几年内便蔚为显学,仅用了二十几年的功夫就席卷中国大陆,取得了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全面胜利”[2]。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依然在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飘扬,并且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迅速地中国化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有中国共产党人这样一个精英群体。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推进理论创新,从根本上保证了理论方向的正确性。因此,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都能够抵御来自党内外、国内外的压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历史证明,精英群体以身体道是特定荣辱观大众化的关键,精英群体建设得如何决定了特定时代主流荣辱观的命运,进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特定时代发展的前途。我们不但应当看到历史上精英群体在主流荣辱观大众化中的作用,也应当看到精英群体的没落对主流荣辱观的冲击。在中国历史上,官僚阶层的腐化以及由此带动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没落,往往是封建王朝走向衰落的前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党员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腐败蔓延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党的声誉和社会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因此出现一定程度的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明确宣示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英群体应当如何界定或者说哪些群体应当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英群体?我们认为这个群体应当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党员干部,泛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及其他机构领导岗位的干部和非干部岗位的党员;第二个层次是非党员、非领导干部岗位上的理论工作者(包括人民教师)。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英群体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较长时期荣辱观教育出现失误,人们(包括精英群体)的荣辱观在一定程度被扭曲,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还面临着消解错误的或者说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念的任务。
如何培育精英群体,取决于精英群体的性质。就上述第一层次精英群体即党员干部来说,所谓培育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英群体问题,就是党的建设问题,是党员干部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精英群体建设工作中两个环节是关键:第一,把好干部选用关和党员入党关。是否具有社会主义荣辱观应当成为一个公民能否成为这个党的成员或干部的基本条件。这在理论上似乎没有问题。然而,无论从观念层面看还是从实践层面看,我们吸收中共党员或者任命领导干部之前对这一问题都缺少足够的认知,更缺乏足够的保障手段。发展中共党员或干部后备人选时应当如何考察他们的荣辱观、用什么途径保障等等,都缺少科学的研究。我们认为,仅仅靠目前的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应当加强对建党对象和干部后备人选的行为研究。例如,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更具有实证性质的行为档案。第二,党员队伍的管理与教育问题。迄今为止的党员生活、干部教育体制都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导,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的学习与宣传,但对这种教育与宣传的效用缺少有力的保障。至于伦理价值的教育与检查,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有效的防控手段。我们认为,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更多地借助行政手段,对党员干部社会主义荣辱观进行监督是有必要的。
三、完善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制度保障机制
一种信仰的确立与普遍化,不是靠人们自觉的内省就能实现的,因此才需要有效的教育手段。但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说,教育的作用本质上不过是为人类选择信仰和行为提供间接的经验,精英群体的努力、榜样的力量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激励人们接受特定的荣辱观,但是并不能必然地使人们形成内心确信,更不能当然地决定人们的行为走向,这是人性使然!人是思想感情异常复杂的动物,从而决定了人的行为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权威——特别是规范性权威——对于引导、规制人们的行为选择具有不可取代的功能,对于人们信仰的选择和确立发挥引导和巩固作用。
趋利避害需要对行为后果有尽可能明确的预期,这种预期往往决定了人的行为选择,而人们对行为结果预测的依据必然是人们普遍认同某种权威。中国古代的榜样教育之所以能在荣辱观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作用,实际上是基于皇权的权威性。例如,封建王朝对德高望重的官员或民间以身体道的道德楷模的褒奖就是以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依托,而对于帝制时代的人们来说,皇权是最高权威,也是最可信赖的权威。在人们看来,凡是皇权(或者国家权力)肯定的行为就是应当效仿也是最值得效仿的行为。于是,一座牌坊就是一个荣辱观教育的基地,就会影响一方百姓几代人。而在当代社会,法律制度被视为最可信赖的权威。法律肯定的行为当然就是应当效仿的行为。法律还具有远甚于封建皇权的优越性,其表现之一就在于它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准确的预期,并因而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权威的力量特别是规范的力量通过对人们利益的处分进而影响人们行为的选择,对人们信仰的形成发挥作用:鼓励人们对践行某种荣辱观的行为的同时,惩戒人们违背特定荣辱观的行为。多年以来,我们相对重视对于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行为鼓励,诸如“劳动模范”的评选与表彰、“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与表彰、“道德模范”的评选与表彰,等等。但对于践踏社会主义荣辱观或者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不力的人和事的惩戒力度相对不足。许多党员干部在任职期间就有劣迹,因为没有引起重视以至于积土成山,到东窗事发时,已成大案要案。值得欣慰的是,近来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到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推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战略。
用制度维护荣辱观的权威并保障荣辱观大众化是中国传统荣辱观大众化的重要经验。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著称,“德治”被视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经典模式,传统荣辱观的大众化是这一治理模式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但古代中国人并没有放弃法律手段,而是创立了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中华法系在历史上不但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而且对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荣辱观的大众化也离不开法律的支撑。如果没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儒家荣辱观的普世化、大众化是难以想象的。中华法系“以礼入法”虽然从现代法治角度看有诸多问题,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类社会两大规范(指向思想的道德和指向行为的法律)体系关联,为主流荣辱观大众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从而保证了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使之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强有力的精神纽带。实际上,用法律制度维护包括主流荣辱观在内的核心价值的地位并推动它的大众化也是现代国家的通用手段。问题只在于如何实现法律的这一功能。
基于上述认识,完善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制度保障机制的基本任务是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融入制度体系,使之在最大程度上制度化、法律化。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20.
[2] 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5.
责任编校:汪沛
2014-02-15
安徽省高等学校思政理论课建设工程省级建设项目“社会主义荣辱观大众化研究”(20122013SZKJSGC7-2)。
罗本琦,男,安徽潜山人,安庆师范学院政法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时间:2014-8-28 15:45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40828.1545.001.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4.001
D64
A
1003-4730(2014)04-0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