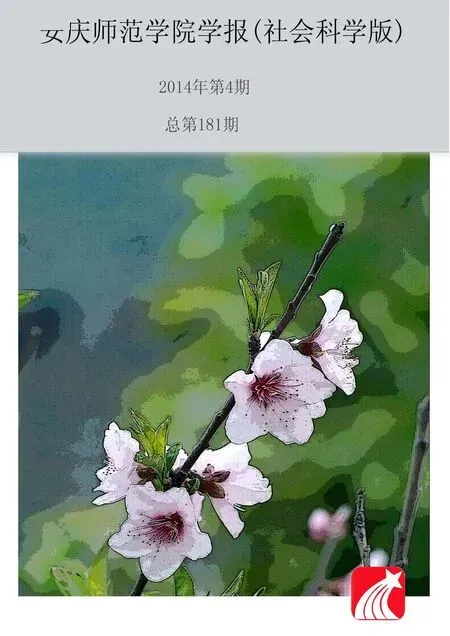“保底”与“跳级”:高收入高福利行业子弟回流就业行为的场域分析
刘 伟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保底”与“跳级”:高收入高福利行业子弟回流就业行为的场域分析
刘 伟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石化行业长期存在着员工子女凭借内部优惠政策“回流”至本行业就业的现象,其特征可概括为“保底”和“跳级”,即行业子弟在规避就业风险的前提下努力向更高层级行业流动。作为求职场域斗争妥协的结果,回流就业受到职业观念、行业归属感、子代教育水平和父代行政级别等因素的影响,反映了个人就业模式的变迁以及就业公平问题的复杂性。
高福利行业;子弟回流;就业行为;场域视角
当代中国社会的就业难问题人所共知,大学生就业则是其中的主要难点。国家垄断比例高、大型企业集中的石化、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凭借其特殊的归属身份和经济地位,几乎成为高收入高福利的代名词,受到广大毕业生的普遍关注。
但是,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这些高收入高福利行业中却长期存在着一条专为其职工子女服务的就业捷径,即企业员工子弟可凭借其血缘身份获得本企业的特殊就业权(如中石油系统)。为此,对这种“子弟回流就业”(本研究所称“回流就业”,是指依靠行业内部的优惠政策,某一企业员工的子女凭借子弟身份获得该企业就业权的现象,不包括员工子女到同行业其他企业就职的情况)的行为展开更具体的社会学观察与分析,将有利于认识并解决当前的就业不平等问题,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一、文献回顾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直接关注更多来自政治学和经济学语境下的概括性主张。这些学者认为,国企子弟先天优先获得国企就业权的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其成因在于国企企业性的凸显和国家性的弱化;并将相关的优先招录政策与凭借关系安排入职的现象统称为“职业世袭”,认为应从根本上约束权力、限制寻租机会,从而杜绝此类行为[1-3]。
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则主要来自职业代际流动与职业地位获得等方向。许多研究证明,以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经济收入、职业地位、政治身份等变量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因素,对子女的职业地位获得确有影响,并造成了社会地位差异在代际间的传递[4-7]。但是,由于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受到单位、区域等集体机制的影响[8],父代工作单位、父代所处行业等集体性变量可能更需要关注。对此,林南与边燕杰认为,在当代中国,父代工作单位对子代工作单位的获得具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传承是通过工作单位而不是职业进行的[9],其具体表现为:与父代务农的情况相比,其他单位向上的职业代际流动的机会都相对较大;父代单位级别越高,越不可能下降流动[10]。更详细的分析指出,对于优势阶层的子女来说,在只有低教育程度的条件下,有更多的机会避免从事最低的非技术体力的工作(“保底”);在拥有中等教育程度的条件下,则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专业技术等非体力阶层(“跳级”),很少掉到非技术体力这一城镇职业地位最低的阶层(“保底”)[11]。本文正是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父代工作单位和所在行业”这一重要却少受关注的集体性因素展开探究。
对于家庭背景影响子女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限制要素,则以对子代教育水平和父代行政级别的研究为主。相关研究指出,青年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是其能否进入精英阶层的关键所在,研究生学历是个人成为高级精英(特别是高级技术精英)的重要条件之一;父辈想要帮助子女获得中等级别的位置,则其本人的行政级别要足够高[12]。而子女的学业表现则是家庭教育背景对子女初职地位获得影响的中间变量[6]。
但是,以上绝大多数研究均使用量化的统计分析方法,缺少对个体主观意识与策略的刻画,没有也难以解释这一影响的过程机制是如何运转的;一些质性研究虽然指出回流就业作为单位意识的延续给企业和个人都带来了困扰,甚至指出了就业观的新变化[13],但并未说明这一趋向的生成机制;另一方面,回流就业始终是在相关企业优惠政策之下产生和运作的,企业对政策关卡的态度将显著影响着该现象的表征;而上述研究均缺少对这种相对公开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性的权力的介入考察。为此,本文将打破上述文献普遍遵循的个人属性的职业代际流动研究路径,增加机会阻隔路径和剥削支配路径意义上的分析[14],即将职业代际流动和阶层再生产视为充满主体策略性和运作性的过程。由于这涉及结构与运作两类要素的杂糅交错,本文借鉴以往文献[15],承认“关系”与正式渠道两种入职方式并存的现实,力求建立更明晰的逻辑框架。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场域理论是布迪厄最重要的社会学理论之一,也是其所主张的社会研究基本分析单位。场域可以理解为依附于某种权力(或资本)的各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或者结构,具有如下性质:场域的效果在其空间内得到发挥,并将影响所有对象的行动;场域中各种位置的占据者利用种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其在场域中的位置,在场域中展开斗争;场域通过一套结构性的预设或逻辑影响其中的对象,并以习惯的形式使影响内化[16]。因此,场域视角可以使分析者较容易地在多重诉求与策略交织的情况下,抽离出各方行动的内在机制。
场域视角下的子弟回流现象发生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期间运行着以行业内部政策为主导的各种逻辑,充斥着形式各异的资本或权力;另一方面,该场域又受到现实世界的深刻影响,被卷挟进入无止境的变迁当中。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各主体为保持并增加所掌握的资本(即实现自身诉求)而不断发生充满策略意义的斗争。
三、W公司子弟回流就业现象描述
W公司现为国有特大型炼油化工燃料企业,年原油加工能力为百万吨级,对W市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布局和社会心理均具有重大影响。公司共有在职员工15 000余人(2009年),包括退休员工、员工家属及相关服务业人员等群体保守估计不少于10万人,并围绕生产厂区形成了一个具备经济、教育、文化娱乐、公共服务等职能的综合性巨型社区。笔者在W公司员工子弟中采访了4位2013年应届本科毕业生A、B、C、D作为具体案例,另外还采访了一位退休工人E以了解政策沿革情况。
(一)W公司子弟回流就业政策的沿革与现实
石化行业的子弟回流就业优惠政策最早始于上世纪60年代大庆石油会战时期,随队家属被允许直接入职从事油田后勤工作,后来入职范围逐渐扩大到职工子弟;至上世纪60-70年代,随着社会就业压力增大,这一做法开始在包括W公司在内的石化企业广泛推行,称为“学大庆,让子女上班,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至上世纪90年代,W公司每年新入职员工几乎全部来自于厂办学校应届毕业生当中的职工子弟。但是,在经历了上世纪末的国企大改革和单位制弱化后,面对不容乐观的收支态势与人力资源现实,W公司对子弟回流政策做出了调整:“211工程”高校的理工科子弟全部接纳就业,非理工科子弟只接纳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一般高校则根据学校情况只招收化工、储运和装备制造等个别专业的子弟;三批本科院校毕业的子弟无论任何专业一律不予接纳。
(二)“保底”:W公司子弟对回流就业的态度
在上述政策改革的背景下,W公司子弟对于是否回流一般都已有较明确的立场;但是无论最终是否选择该途径,他们都试图将回流作为其他就业选择未能成功时的“留一手”,以保证最终结果不低于W公司。如就读于某高校重要工科专业的A君,始终把通过招聘会应聘企业作为求职首要途径,次之则有可能从事他喜欢的舞台设计等工作,如果以上计划全都落空,再考虑以子弟身份回W公司工作。又如已经回流与W公司签约的D君,她实际上从刚入大学起就有考研的打算,目前的回流签约只是为了万一失败后有一稳定工作,以便明年复考。
不难看出,不选择回流的W公司子弟其实并未在根本上排斥回流,而是将其作为无工作可聘时的一种应急方案;而已回流的子弟也并未将回流视为工作首选,而是作为保障最终发展目标的跳板。因此,这里不妨借用李煜的“保底”概念[11]来概括。这是为了保证就业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相对稳妥的选择策略,在相当程度上为子弟就业规避了风险。
(三)“跳级”:子弟们的近期职业规划
那么,既然回流到石化行业并非子弟们所热衷,他们更理想的职业又是何种模样?对此,调查材料显示,4位子弟无一例外对工程设计[2]410行业表现出明显的就业兴趣,而且4位子弟均有读研深造的计划。以A君为例,除了上述应聘对口职位和凭爱好自主创业等选择以外,他最理想的工作就是设计,并向笔者详细讲述了设计工作的优越环境;D君则干脆将考研作为进入设计行业的敲门砖,明确提出了“设计院>考研>回流就业”的倾向排序。
(设计院)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挤破头最想去的,无论如何,你一旦能进去,是所有人都会羡慕你的行业。工作稳定,事不多,工作条件极其安全,基本上属于按劳分配的,挣得真的是非常多。(访谈材料A20130131)
可见,尽管上述诸君凭借子弟身份可以较容易地在W公司获得一份相对不错的工作,但他们仍将在收入、职业地位、工作生态等方面更优渥的设计行业作为追求的新目标,即“跳级”概念:在能够获得确定工作的前提下,劳动者仍然具有向更高层级职业(行业)流动的倾向;“跳级”与“保底”相互配合,“保底”是为了能够实现“跳级”,“跳级”失败则可借“保底”实现就业;两者的实质都是为了获得就业利益的最大化。
四、场域斗争的演变——基于场域视角的分析
综上,W公司子弟的回流入职主要涉及W公司、子弟父母(W公司员工)和子弟本人三方主体,并在以W公司为核心的W社区中获得了运作空间——此处不妨称其为W场域,其特征除上文所阐述外还包括如下几点:第一,W场域结构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这会通过对行动者的习惯形塑而产生强大的历史惯性。第二,该稳定状态在最近遭到了明显破坏,很可能造成场域权力结构的失衡。第三,场域内各方力量对比并不均衡,相较于子弟本人及其父母,W公司的力量明显强势。由此,以场域斗争为分析核心,笔者对“保底-跳级”特征生成的原因作出如下解释。
(一)场域斗争的产生: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冲突
面对W公司的政策改革,子弟家长首先作出了反应,原因如下:第一,中国历来就有父母影响子女个人选择的文化传统。目前,为子女找到合适的工作已经内化为中国父母的典型角色期待。第二,许多子弟父母是经过了若干次职业流动后才最终在收入与稳定性均相对较高的W公司立足的,十分希望将该优势地位传承给子女。这体现了来自W场域的形塑作用。第三,W公司曾长期实行的宽松的回流政策使员工普遍认为公司对子弟就业应负有责任。这也是职工对传统单位制的一种路径依赖。于是,他们凭借公司职工的身份,借助“闹事”等舆论力量向W公司施压:
“为啥是装备二本肯定要,我们二本不要?上厂长办公室闹去呗。”(访谈材料C20130117)
作为回应,W公司一方面不再公开任命组织当年回流招聘工作的工作人员,以防个人寻租;另一方面严格保密当年回流招聘的专业要求,并尽可能缩短该政策的传达时间,一经公布立即执行,给潜在的“闹事”者以既成事实。于是,W公司与子弟父母形成了僵持对抗的局面。
(二)场域斗争的发展:代际间的变迁与对立
1.职业观念的代际变迁
就在此时,子弟本人的就业主张却逐渐开始异于其父母的想法:一方面,由于他们从小生活在发展水平较高的W社区中,与其长辈相比,向上流动的外界刺激更强,自我期望也更高;另一方面,职业在他们眼中被更多地赋予了丰富人生经历、体现生活态度的意义,特别是应满足个人在尊重和自我实现层面上的需求。因此,回流就业虽然能够获得较稳定且收入丰厚的工作,但由于上升通道狭窄、工作内容乏味,加之复杂的工作生态,难以得到子弟们的真心青睐。
2.行业归属感在代际间的弱化
子弟对石化行业归属感的明显滑坡是导致其对回流就业较低认同的另一重要原因。在缓慢却不可逆转的单位制消亡进程中,新一代石化子弟主张应以更强的自我意识来认识自身与这座工厂及整个行业的关系,石化只是“我爸妈的”行业,生活只是在此进行而已,W社区已不是他们的精神与文化依托:
它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个东西就像街边大马路上的存在而已……它顶多说和我父母有点啥关系,和我有什么关系?(访谈材料A20130131)
进一步讲,这种归属感的消亡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场域内文化资本代际传承的失效,也就是说,父代在职业生涯中积累的角色定位、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组织认同等文化要素已经很难传递给下一代。
(问:你爸妈平时和你聊不聊在单位的事?)我爸:“明儿有时间没?”“有。”“陪我打麻将去,三缺一。”我妈:“搞对象没有啊?哪儿的?人咋样啊?”不怎么唠工作的事。(访谈材料C20130107)
3.亲子角色差异与路径依赖
但是,文化传统一方面赋予父母以资源提供者的身份,同时也使其获得了对子女的天然优势。这不但体现在伦理和情感上,也体现在理性的计算上;而且由于亲子间影响的长期存在,子弟本人对父母长期为自己设计的学业及职业规划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很难予以抗拒:
我爸的决定谁也不能拒绝,你是不知道我爸,绝对全厂第一辩手……他不是强制,他是说服。(访谈材料B20130131)
而且还考石化吧。因为我要是别的专业挺难的,毕竟大学这个学着呢。(访谈材料D20130125)
最终,子弟本人与其父母在根本态度上形成了契合:子弟们并不否认“有饭吃”是就业的首要目的,亦不否认回流后将获得的正是这碗还算不错的“饭”。以至于B君就曾这样自我反思过:“(虽然)自己被安排、被建议,觉得不甘心,其实呢,我爸想的还是比我多,也为了我好,我没什么好抱怨的。”因此尽管工业设计等更高层级行业早就取代了子弟们心中“原本应该是”石化行业占据的就业首选,但在父母的压力下,他们终将有意无意地在就业选择中掺杂进后者的主张,“跳级”从此很难得以顺利实施。
(三)场域斗争的深化:三方主体的交互博弈
不过,此种亲子间的博弈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子代教育水平和父代行政级别的制约:一方面,W公司的新政策将子代教育水平视为重要的评价标准,成了回流路径中最“硬”的指标和最“窄”的瓶颈。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W场域在以回流政策为表征的常规逻辑背后,还存在着另一套难以为人所知的隐秘规则,即我们平时所称的“走关系”、“走后门”、“花钱(就业)”。在这套逻辑中,行政级别越高的行动者,其获取与调用资本的能力显然就越强,在公开规则外安排子弟回流的能力也就越强;由于倾向于让子女回流的员工往往处于行政序列的下层,因此父代行政级别在其中的限制作用实际上表现得相当强烈。其外祖父生前曾任W公司副厂长的C君就表示:“我姥爷要还在职的话,我还考研?!我都不念!兴许能费点劲,但肯定能进。”特别地,上述两个限制性因素的根源均来自W公司!这充分体现了子弟与公司间的隐性互动模式,说明场域作为一个运作空间总是能够对所有相关对象的行为有一定作用。
(四)场域斗争的妥协:对“保底”与“跳级”并存局面的解释
由此,该场域的三方主体既热衷于通过策略斗争为自身争取利益,又在这一过程中被场域的内在逻辑所形塑,被其他主体所影响。W公司的回流政策改革限制了子弟的大规模涌入,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职工的“闹事”隐患;子弟父母的主张能够充分影响子弟本人,但不能从根本上反对W公司的政策,同时又受到教育水平等要素的制约;子弟本人在就业观念与倾向上有着明确的个人偏好,但又难以完全违背父母的主张。
因此作为一种妥协,子弟们一方面考虑按照新政策的要求应聘入厂工作,但同时仍保持指向场域外的其他就业倾向,即形成“保底-跳级”并存局面。
五、结语
综上,石化子弟的回流就业现象呈现出“保底”与“跳级”并存的特征,即将回流与高层级行业岗位分别置于就业选择的末尾与首位,一旦机会成熟则放弃回流而向高层级流动。这既是个人实现就业利益最大化的主体策略,又源自维持就业场域斗争均势的各方妥协。期间,回流就业将受到职业观念、行业归属感、子代教育水平和父代行政级别等因素的影响,在就业机制上主要体现为:第一,文化资本的代际传承已经很难成为父代影响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方式;第二,父代的经济社会资本可能对子代就业观念的形成具有一定作用,并间接影响后者的职业地位获得(即“跳级”);第三,“回流入职”等就业优惠政策成为阶层再生产最简便直接的方式之一。三者综合反映了当今社会职业选择模式的变迁趋势:以文化和情感为纽带的原始职业选择已基本消亡,以单位和行业为中介的传统职业选择正逐渐弱化,但仍发挥一定作用,而突出主体意愿和个性的新式就业正在快速发展,“保底-跳级”的并存局面就是后两者间冲突的妥协。
从传统单位制企业的角度看,渐进的、调控的、策略性的改革确实有助于它们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推动人力资源转型。但是,由于难以完全摆脱职工的文化与情感依赖,现代管理制度发育不良,致使改革后的回流就业仍是一种凭借先赋身份和政策壁垒来挤压其他劳动者进入该行业的机会空间、最终实现规避就业风险和向更优行业流动的就业策略。可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职业地位差异仍将是个人属性与单位或行业集体阻隔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今后在国企转型和单位制解构进程中,应特别关注集体层面的就业政策改革,以便更有效地打破就业藩篱,推进就业问题的解决。
[1]胥仕元,李慕白.论国有企业职工子弟就业世袭问题——从国企的国家性和企业性矛盾谈起[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0(3):121-122.
[2]刘建明,张明根.应用写作大百科[G].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3]梁志全.论职业世袭对青年发展的重大影响——两代青年就业方式的比较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1(5):21-25.
[4]张翼.家庭背景影响了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获得[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4):82-92.
[5]王立波,马丹.转型期辽宁代际职业流动研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2-55.
[6]高舒.家庭背景对重点大学毕业生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D].复旦大学,2009.
[7]张瑞玲.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蔡寨村的调查[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6-41.
[8]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J].社会,2010(3):1-20.
[9]Bian Y.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M].New York: SUNY Press, 1994.
[10]李晚莲.社会变迁与职业代际流动差异:社会分层的视角[J].求索,2010(6):62-64.
[11]李煜.家庭背景在初职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及变迁[J].江苏社会科学,2007(5):103-110.
[12]张乐,张翼.精英阶层再生产与阶层固化程度——以青年的职业地位获得为例[J].青年研究,2012(1):1-12.
[13]周旋.当代单位意识的延续及困惑[D].吉林大学,2012.
[14]梁岩.职业代际流动研究路径与最新进展[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2(2):35-40.
[15]吴愈晓.社会关系、初职获得方式与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2011(5):128-152.
[16]乐国林,张丽.大学排名对高校影响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布迪厄场域、资本理论的探析[J].现代教育科学,2005(3):37-39.
责任编校:汪沛
“MinimumGuarantee”and“AdvancedPlacement”:AFieldAnalysisofReverseEmploymentofWorkers’OffspringinHigh-incomeIndustries
LIU Wei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China)
In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reverse employment, existing among workers’ offspring with internal preferential policies, is characterized by minimum guarantee and advanced placement, which means that the offspring try to move to advanced industries with the minimum employment risk. As a result of compromise over the struggle in the field of employment, reverse employment is influenced by the employment concept,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offspring and the executive level of their parents. It reflects the change of personal employment patterns and the complexity of employment equity.
high-income industries; backflow of the offspring; employment; perspective of field
2014-02-24
刘伟,男,辽宁锦州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时间:2014-8-28 15:45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40828.1545.004.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4.004
C913.2
A
1003-4730(2014)04-0014-05
——基于人力资本传递机制
——基于子女数量基本确定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