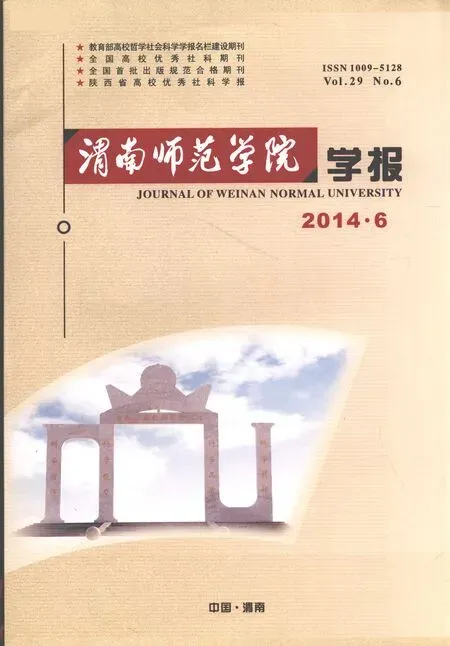论司马迁对孔子撰史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以“春秋笔法”与“书法不隐”为中心
李 波,赵 丽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泰安271000)
论司马迁对孔子撰史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以“春秋笔法”与“书法不隐”为中心
李 波,赵 丽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泰安271000)
司马迁撰写《史记》,效法孔子作《春秋》的撰述方法,借助历史表达褒贬好恶,宣扬政治理想,成其一家之言;同时,又摆脱了《春秋》“虚美隐恶”的书法限制,贯彻了史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由于他在撰史方法上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结合时代特征的新发展,从而使《史记》成为继《春秋》之后中国古代史书撰述的又一不朽典范。
司马迁;孔子;春秋笔法
司马迁作《史记》,是以做第二个孔子,写第二部《春秋》自居的。其父西汉太史令司马谈临终遗言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哉,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父亲逝后,司马迁接掌太史令一职。他谨受父教,承袭孔子“修旧起废”写作《春秋》的做法,把撰写新史书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自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3295-3296由此可见,司马迁创作《史记》,“成一家之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著述事业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司马迁撰写史书深受孔子的影响,本文从“春秋笔法”与“书法不隐”的撰述方法着手,试析司马迁对孔子史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一
所谓“春秋笔法”,也称之为“春秋书法”,它是由孔子在《春秋》这部书中所开创的一种记述史事的方法,并在后世成为中国史书撰述的一个重要传统。《左传》曾总结这种撰述方法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2]870《礼记·经解》则概括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撰写《春秋》,用辞凝练、取材慎重,他在行文中并不直接阐明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看法,而是通过对字辞和史料的斟酌取舍,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褒贬好恶。例如,《春秋》对以下史事的记载: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确立晋国霸业,天子周襄王也受召赴会。《春秋》则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周襄王因为遭到王子带与戎人的攻伐,仓皇外逃,避难于郑国的汜地。《春秋》则记载为:“天王出居于郑。”
吴国、楚国的君主原本为子爵,但随着势力增强自称为王。《春秋》仍然称其为“子”。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谈道:“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1]1944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他的写作态度显然是非常认真的。然而,从上文所举的历史事例来看,他在书中又时时处处地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难免存在诸多的“曲笔”,而他之所以会视《春秋》为其一生功罪之所系,概应由此而来。
若要了解《春秋》的“笔削”原则,首先须要明白孔子创作史书的真实意图。司马迁称“《春秋》推见至隐”,孔子作《春秋》是通过记述史事来传达“微言大义”。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讲:“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时期,周王室已经衰落,诸侯、卿大夫恣意妄行,整个国家制度崩废、战乱连绵,陷入了失序无道的状况。这种状况是孔子所不愿看到并且深为忧惧的,他编撰史书,“见之于行事”,就是为了匡正乱世,恢复礼仪法度,捍卫周代“王道”。即如司马迁借由壶遂之口所指出的:“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1]3297可见,司马迁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春秋》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它还是一种应然的政治理想,担负着赏善罚恶、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自序》等篇章中,用了大量的笔墨讨论《春秋》这部书的重要成就和价值。诸如在谈到《春秋》成书的背景和过程时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1]509在论及《春秋》的丰富内容时讲道:“《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因而,这部书的重要性非常明显,“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总之,在他看来,“《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1]3297-3298。
由上文所述,“《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乃“礼义之大宗”,其意义正如现代学者李长之所说:“《春秋》可以代表一种法制,——是禁于未然的法制,这也就是‘礼'。”[3]58如果深入考察,我们会发现礼不只是一些表面上的空泛的典仪形式,它有着实质的道德内容。《礼记·曲礼》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则认为:“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4]269礼作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于维护周代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一直起着不成文法的作用。孔子把《春秋》和“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制联结在一起,《春秋》作为“义法”就有了实质的内容,它就可以成为一种裁判的圭臬,一种是非的标准。
毋庸讳言,《春秋》中存在着不少“曲笔”,如果把它当作一部纯粹的史书来看,其中的一些记载无疑是违背事实的。但是另一方面,孔子又在倡导所谓“书法不隐”,强调作史者坚持“直书”原则。《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被赵穿杀死,晋国史官董狐却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他的理由是:“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他认为赵盾作为晋国的执政大臣,当事件发生时,虽然在逃亡之中但是尚未越过国境,与晋灵公的君臣之义依然存在,回到朝中后毫无讨伐乱臣的行动,因此应当承担“弑君”的罪名,这是按照撰史的“书法”决定的。孔子对董狐的做法十分赞赏,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2]662-663孔子以“书法不隐”来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显然,孔子在此所谓“书法不隐”,其实质仍是一种应然的理想发挥,他为了所谓“掩恶扬善”的“《春秋》之义”,不惜歪曲历史真相。而他所以这样做,就是要维护一种使“乱臣贼子者惧”的绝对价值,维护一种类似不成文法的“法”,尽管这种“法”只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并且在后世遭到无数“乱臣贼子”的篡改、玩弄。
董狐所遵循的撰史“书法”乃是依礼制定的,礼的功能即在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赵盾不讨伐杀害君王的乱臣,违逆了君臣之义,所以董狐认定其应承担弑君之罪。在礼崩乐坏、“事不稽古”的春秋乱世,政权下移,权臣操纵国政,手握生杀予夺之权,旧有的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然而董狐不惧杀身之祸,恪守史官职责,坚持传统的撰史“书法”,因此孔子对他大加赞扬,褒美其坚持原则的精神。所以,在《春秋》这部史书中,“春秋笔法”和“书法不隐”二者并不矛盾,它们和谐地统一于孔子的史学观念之中。
二
《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1]3310把孔子作《春秋》与汤武革命、陈涉首义并列,足见司马迁对这部史书的看重。他创作《史记》,“述往事,思来者”,“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不仅延续了孔子作《春秋》存“天下之史文”的撰史传统,而且发扬了《春秋》所表彰之“义”及“春秋笔法”所体现出的褒贬精神。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评论道:“(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1]1943其中的“据鲁、亲周、故殷”之说,是司马迁首先提出来的。“据鲁”,是孔子要把鲁国当做他政治理想的实践基地;“亲周”,是以周为天下宗主,体现了孔子政治上一统的思想;“故殷”,是因为孔子本是殷商后裔,以示不忘根本。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的整部《春秋》所体现出的即是这样一种政治上的向心力。深受《春秋》影响的司马迁,则把这种向心力发挥在当代,用来歌颂汉王朝的大一统。
司马迁生活在汉代盛世,西汉历经高帝、惠帝、文帝和景帝四代治理,到武帝时期全国一统,国力强盛。西汉经学家董仲舒发挥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宣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5]2523司马迁接受“《春秋》大一统”的思想,称述:“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1]3299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汉兴以来的整个进程,宣扬汉代一统带来的天下大治。如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他着重阐述了天下一统的道理,追叙了三代以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艰难历程,深深感叹:“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虽然秦朝命祚短暂,但他对嬴秦剪灭六国、一统海内的功业同样表达了认同,他撰写本纪,自五帝、三代至秦,将秦视作是承继周统而来的。对于秦朝采取的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他抱持着肯定的态度,在《礼书》中称:“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汉代制度即基本上承袭了秦制,“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改”[1]1159-1160。在关于汉代分封制的问题上,司马迁非常认可景帝与武帝采取的削藩政策,称赞这一政策使王朝呈现“强本干,弱枝叶之势”,从而实现了“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1]686、803。他在《袁盎晁错列传》中描写了汉初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的斗争,并肯定了晁错消减诸侯势力的主张。他对于拥护朝廷的诸侯,如楚元王刘交等,在书中都给予了肯定和赞扬,而对于发动叛乱的吴王刘濞等人,则将其不载入世家而贬入列传。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司马迁对大一统王朝的维护。
司马迁对于孔子“寓褒贬,别善恶”的撰述笔法有着深刻体会,并深受其影响。例如他在《吕不韦列传》中评价吕不韦之时,只用了一个字,即“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1]2514此处的“闻”字正是取自于孔子所说“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意指这种人表面上主张仁德,实际行动却背道而驰,但仍以仁人自居而不感到惭愧。因此李长之认为:“司马迁的精神,仿佛结晶在孔子的字里行间。”“司马迁的褒贬够经济!其养育于孔子精神中者,够凝练!”[3]41司马迁著史,可谓深获孔子撰述风格的神髓。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称:“《春秋》推见至隐。”在《匈奴列传》中则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法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1]2919不仅如此,司马迁还看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孔子记述与评判史事,主要还是为了服务现实,以建立一个合乎“王道”的理想社会。司马迁创作《史记》,就继承了这种批判形式下的建设因子,“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通过历史来总结统治经验,探求治国之道。
但是在司马迁这里,同样的“寓褒贬,别善恶”,表现与孔子有很大不同。他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赋予了《史记》文直事核的撰述风格。《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以人物为中心,十二本纪记载天子事迹,三十世家讲述诸侯事迹,七十列传叙列人臣事迹,这些体裁的不同称谓与结构形式所体现出的,即是帝王高居于上、人臣拱卫于下的礼法等级序列。但在这样的体例格局之下,司马迁又从历史实际出发,不仅给予了在当时不被学者认可的秦朝应有的地位,而且把项羽、吕后列入本纪,把孔子、陈涉拔擢入世家,这些都表现了他坚持实事求是、不惜“谬于圣人”的史家求真精神。
司马迁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盛世,但盛极而衰,汉代社会的许多阴暗面此时已经逐渐暴露出来,西汉王朝极有重蹈周朝衰亡道路的可能。有鉴于此,他对当时的一些人物包括最高统治者武帝刘彻进行了揭露和批评,继承了孔子“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的撰史精神,同时又摆脱了其“虚美隐恶”的书法限制。例如在《匈奴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韩长孺列传》等篇章中,他客观地描述了汉武帝发动对外征伐战争给广大民众带来的无尽烦苦。在《匈奴列传》篇末,他指出:“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1]2919对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及其任人唯亲、用人不当的品性进行了无情地揭发。再如在《酷吏列传》中对汉武帝所任用的酷吏作了集中的描写。张汤断狱完全依照武帝的意愿,“所治即上意欲所罪”,并且还迎合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审理案件时附会儒家经义,从而深获武帝的赏识;杜周亦是如此,司马迁通过他道出了武帝时期法律的实质:“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之是,何古之法乎?”任用酷吏导致了王朝吏治的败坏,对此司马迁慨叹道:“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寝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1]3153-3154又如《封禅书》,它可以说是汉武帝一生迷信、求仙和寻找长生之药一次次失败的记录。武帝信任骗子上郡巫师,司马迁则在笔下点出:“其所语,世欲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武帝至东莱山寻神,劳而无功,司马迁写他依旧不死心,“复遣方士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汉武帝屡次受骗,仍然执着地“冀遇其真”,司马迁就此饶有意味地写道:“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菜,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1]1403-1404此处正话反说,可谓极尽嘲弄、讽刺之能事。
综上所述,司马迁作《史记》,效法孔子作《春秋》的撰述方法,通过对史事的记述来表达褒贬好恶,宣扬政治理想,成其一家之言。然而孔子作《春秋》“是为万世做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做史,而纪实以征信”[6]23;司马迁作《史记》则是彻底贯彻了史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5]2738,客观地记载了历史事实。梁启超在比较这两部史书之后评论说:“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有忠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7]121正是因为司马迁在撰史方法上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结合时代精神的新发展,从而使《史记》成为继《春秋》之后中国古代史书撰述的又一不朽典范。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4]佛雏.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5][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7]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M].长沙:岳麓书社, 1985.
【责任编辑 王炳社】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us's of History Recording Method on Sima Qian
LI Bo,ZHAO Li
(College of Marxism,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an 271018,China)
Sima Qian wrote Historical Records to express personal views and political ideal by learning Confucius's method of writing Spring and Autumn.At the same time,he got rid of Spring and Autumn'swriting principles of enlarging beauty hiding evil, and carried out the spirit of historians to record the truth.As far as the history recording method,because he not only inherited something good from ancestors,but also made new development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times,so that Historical Records become another immortal example among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books.
Sima Qian;Confucius;Spring and Autumn Recording Method
K207
A
1009-5128(2014)06-0015-04
2014-03-03
李波(1978—),男,山东东平人,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赵丽(1979—),女,山东定陶人,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