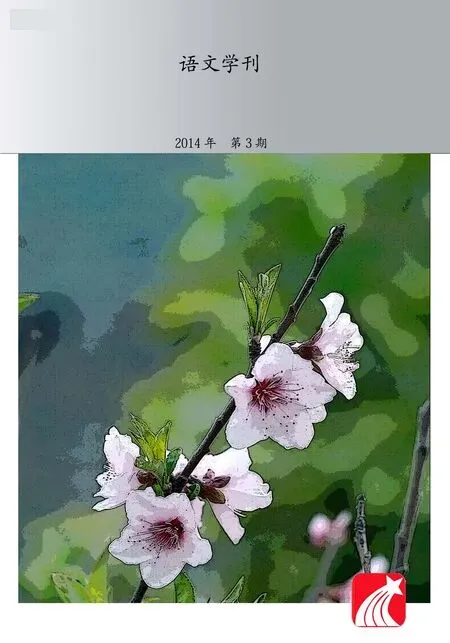颓废、压抑与毁灭
——论《废都》的性爱叙事
○ 宋桂友
(苏州市职业大学 吴文化研究院,江苏 苏州 215104;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13)
《废都》堪称是一部名字里就“包含有对传统文化断裂的隐忧,有失去人文精神倚持的荒凉感”的“东方式的《荒原》”[1]21,作者贾平凹采用了能代表中国古代市井和市井之徒特点的古典小说的语体[2]18,既不典雅又不流畅地讲述了一个虽是城市却是农业时代的市井标本的颓废寓言。
《废都》诞生在新时期文学的启蒙理想破灭之后的1993年。小说表现了叙述者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启蒙乌托邦相对于现实愈行愈远的心有不甘,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摈弃理想的庸俗化进程心存不满,对改变现实无能为力的只能进行自我作践的消极对抗。知识分子对抗社会的最好方式也许就是颓废,在传统文化的观念里,颓废之至就是性的放纵了。于是性起而“都”废。
一、性爱与颓废
《废都》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有一个背景交代,时间上就是思想文化不断变化的1980年代,这是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说其特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潮流不断地涌进来,以摧枯拉朽之势对两千多年以来形成的封建传统思想进行了毁灭性的冲击,其结果就是人的主体意识被唤醒;个体的人开始从群体之中走出来,独立自身,实现自我,甚或对抗群体。于是形成了理性与感性、欲望膨胀与人性压抑、个与类的对峙格局。那么,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叙事者又是怎样的态度呢?那就是性欲望对都市的威胁。
小说在叙述西京城里拆一个老房子时写道:从旧房子里飞出一种像人的头屑一样的东西在天空中四处乱飞,一旦落在人身上就使人奇痒难耐,庄之蝶就是受害者之一。后来经医疗部门检查认定,原来是盖房子时被封在墙壁里的臭虫。虽然早已被饿扁,但却没有死,释放出来,就百倍疯狂地咬人肉、吸人血。这是一个隐喻。臭虫其实是人欲的能指,人欲是臭虫的所指。人欲被压抑了几千年,就是一个饿扁了的魔鬼,它一旦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逃窜出来,不仅不能控制,而且还要控制人族。于是,整个西京城所指代的社会就陷入了空前的人欲灾难。
在人欲的展示过程中,性欲是表,是征,是这部“警世之作”进行文化反思、文化批判[3]68-69的形而上表述的形而下体现。先来看西京城男女的性观念。男人们的性爱观念之于传统伦理已经大为发展。孟云房的隔壁住着一个老头,这几年发财后就娶了一个小老婆。他说:“有了钱不玩女人,转眼间看着是好东西你却不中用了。”卖镜糕的老汉说:“古人说过,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现在,夫妻十个有九个是凑合着过日子的。”柳叶子男人对待男人们寻求新的性爱刺激下了这样的断言:他对收破烂的老头说:“如果你收旧女人了,我敢说这个街上没有一个男人不想把老婆去了旧换了新的。”男人们的这些观点概述一下就是“追求性爱”。具体是:(1)追求及时行乐。玩女人的条件就是只要具备条件具有性功能即为可以。若等到功能因年老而褪去,则令人遗憾。(2)追求新鲜刺激。性欲享受是最高境界。(3)追求女人的功能性物化:如果女人能像破烂一样处理该有多好。所有这些,男人对女人的性爱观都是生理层面、感官级别的。在此理论影响下,就有了西京男人的纵情声色的基础。女人们的性爱观以唐宛儿的话为代表,那就是“女人就是为男人贡献美的”。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贡献”一词已经点明了女性在男性面前的地位是从属关系的,“臣妾心理”根深蒂固。这样,女人就失去了独立人格,变成了男性附庸。其二,女人工具论。女人供男人享乐,成为男性工具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
在这样的性爱观念观照下,废都里的男男女女就有了这样那样的新关系。以西京城的四大名人为例,汪希眠、龚靖元的身边“总有赶不走的一堆女人”;乐团团长阮知非不仅在壁橱中的五层架子上放满了型号大小不一的女人鞋子还和她们有着一个个“美丽的故事”,随心所欲地“换班子”;阮知非老婆领了情人睡在卧室里而阮知非却像没事一样的坦然;著名作家庄之蝶更是与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汪希眠老婆和景雪荫等好几个女人上演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性爱大戏。
《废都》的性爱叙事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特地位来源于它的性爱叙事大突破。最突出的就是创造了那欲盖弥彰式的“天窗叙事”[4]74的暧昧技巧,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第一次疯狂地抒写生命体验。如:
唐宛儿这时候就却盼他一醉长年不醒,便趴近去解他的裤带,竟把那一根东西掏出来玩耍。□□□□□□(作者删去二十六字)不觉自己下边热烘烘起来,起身看那坐过的小凳子上,出现了一个湿湿的圆圈,就不顾了一切,□□□□□□(作者删去五十三字)她两条腿在地上蹭来蹭去,连鞋也蹬脱了。正得意忘了形状,脑门上梆地挨了一击,她猛地就爬起来,脸色顿时煞白。回头看时,身后并没有人,再转过来,庄之蝶挤着眼睛给她笑,唐宛儿立即双手去捂了他的眼睛,却也脏脚脏腿地上了床,压下去套上了。庄之蝶说:“你这不要脸的!”唐宛儿说:“我不要你说,我要你醉!”用嘴又堵了他的嘴。庄之蝶一下子翻上来狼一样地折腾了,一边用力一边在拧,在咬,在啃,说:“我是醉着,我还醉着!”□□□□□□(作者删去二百字)窗外的光线越来越暗了,庄之蝶瘫在那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吁了一口气,说:“天黑了,宛儿。”唐宛儿说:“是黑了,天怎么这样短的!”[5]311
对待这样的“天窗”,王富仁认为:“受人嗤笑的还有它删去多少字的方框。但我却认为它真是一种神来之笔。只要你从一种文学意象的角度考虑,你就知道它们真是妙不可言。这些方框不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一种现象吗?是在我们近些年的书籍中经常看到的一种东西吗?你不觉得它足以体现中国文化的一个方向的特征吗?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就是删去了中国人最感兴趣、最想看到但又觉得不够雅观的东西之后留下的一些雅观的文字。但这雅观的东西在总体的精神上却又是与那些不雅观的东西相通的,二者是一个浑然的整体。”[2]19-20温儒敏则认为,“庄之蝶和小说中其他男女角色的各种性行为、性心理、性态度、性感觉,包括许多病态、变态的心理行为,即是自然人性的表现,又无不反射出某种文化性社会性。”[1]25
在实际应用上,天窗叙事则恰如其分地完成了叙事任务,主要表现在通过对行动元的成功塑造而凸现主题上面。即:
“性”废“人”——“人”废“都”——“都”废“?”
这可谓一种非神圣忧思录。
二、压抑与毁灭
庄之蝶是《废都》的领衔主演,他虽列西京四大名人之中,但其深为声名所累,事业并不能有所发展,生活尽是不如意事,于是苦闷压抑。“尤其是近代社会似的,制度、法律、军备、警察之类的压制机关都完备了,别一面,又有着所谓‘生活难’的恐吓,我们就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总难以脱离这压抑。”[6]10“在内有想要动弹的个性表现的欲望,而和这正相对,在外却有社会生活的束缚和强制不绝地迫压着。在两种的力之间,苦恼挣扎着的状态,就是人类生活。”[6]11但是苦恼压抑着的生活不是自然状态的,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愈是旺盛,这压抑就愈是激烈。[6]14反之,就应该是愈是苦闷压抑,生命力就愈是需要喷发。所以,庄之蝶“他到女人群中寻求自己生命出路,庄之蝶对于女性的追求,其内在本质是对一种生命美的渴望。”[7]94因此,庄之蝶对于女人的性的发泄就成了他生活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借助其近乎变态的性爱来寻找出路。
庄之蝶和妻子牛月清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牛月清是思想上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女性,不仅以性为丑,就是偶有性生活也是被动应付,就连性事时的姿势也非要认定传统的那种,妻子的性冷淡事实上增加了庄之蝶的性压抑。
唐宛儿的出现正好给庄之蝶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唐宛儿是一个一直在追求心中的幸福却一直无门可走的青年妇女,她在社会的底层,指望嫁一个好丈夫,以便鸡犬升天,但天公不作美,她的丈夫性格粗鲁,生活邋遢,经常对她实施虐待,性生活自然不能得到满足与和谐。她心中对幸福的渴盼与追求在失望中愈益强烈,当遇到小城里的名人周敏时,她就不顾了孩子,与之从潼关私奔入西京了。但到了西京见着了庄之蝶,周敏又显然不算人物了。当她听周敏说庄之蝶早年的情人是景雪荫时,脱口而出:“景雪荫长得什么样儿?这般有福的,倒能与庄之蝶好?”这对景雪荫的艳羡和嫉妒的语句里已经有了对庄之蝶的向往与倾慕,也就有了相比之下对周敏的不满了。自然与庄之蝶一拍即合了。所以本文在行进庄之蝶与唐宛儿的性爱叙事时,极写庄之蝶与唐宛儿的曲尽于飞,性爱的疯狂。尤其是对性爱的渴盼的心理和对于传统而创造的新动作、新花样。这种性事的张扬,就唐宛儿来说,一方面写她对于期许的未来幸福的生活实现的信心,一方面又表现她对于个性主体表达的追求。这一点是和庄之蝶一致的。庄之蝶在这儿找到了“幸福”,他因现实生活的压抑而产生的旺盛的力比多(Libido)得以释放。但这又是他走向颓废堕落的开始。
与柳月的关系是深化庄之蝶人生走向的发展。柳月和唐宛儿有一个相同点,都出身卑贱,都向往走出山村奔向大城市,都采取了超常规手段,但二者又有不同。唐宛儿更多地带有理想成分,她的性爱里有着乌托邦的残渣。而柳月的“务实”造成了她的别样悲剧。她第一次和庄之蝶发生性关系是她看见庄之蝶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可就是这样,她还幻想主宰这个家。她的命运显然是不可改变的。柳月和庄之蝶的性爱关系还直接导致了庄之蝶的堕落的一大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对柳月的处置。
庄之蝶的堕落有两个事件:一件是画家龚靖元因犯罪被抓,庄之蝶出面相救的同时,让赵京五假托画商,以低价吞吃了龚靖元家里的珍贵藏品,导致龚在出狱后失望之极自杀身亡。庄之蝶的不光彩勾当充当了龚靖元之死的杀手。第二件事就是对决定柳月命运的人生安排。在和柳月的性爱中一直处于男权地位。他不仅把玩欣赏柳月的性器官,更是把梅子放在其中浸泡。在他的心目中,柳月就是一件物品,一个工具。他先是把柳月赏赐给了赵京五,后来又把柳月送给市长残疾的儿子大正做媳妇,以此换取自身的利益。
庄之蝶在与女人的性爱中完成了自己的堕落过程。但另一个女人的出现又给庄之蝶带来了一丝变化的机遇。阿灿是叙述者刻画塑造的一个拯救者角色。庄之蝶与阿灿的性爱里包含了庄之蝶灵魂受到触动以至震撼的叙述,但女人终久不能够拯救庄之蝶。随着阿灿的离去,庄之蝶最终走向了毁灭。在古城西京里,著名作家庄之蝶,在情欲场中和包括他妻子在内的众多女性——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汪希眠老婆和景雪荫等翻云覆雨,但最后却在他的城市里以失败告终。当妻子、情人都离他而去后,他则被迫在满城风雨中逃亡,死在了候车室的椅子上。完成了他的人生三部曲:
颓废—→堕落—→毁灭
人因性废,“都”因人废。从这里,叙述者在庄之蝶与多个女人的性爱叙事中明确地把叙事指向瞄向了文化、社会的堕落、颓废而给人的精神所带来的巨大损害的批判。社会批判主题深刻而震撼。
《废都》通过人之废来充分表达了都市之废。都市之废正好喻示了社会时代之废。为什么非要用都市来表达这个寓意呢?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80年前的英国作家劳伦斯在其名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面就是这样的书写。具有现代都市现代文明的拉格比庄园是阴森、晦暗的;工业化了的坦弗舍矿区是萧条冷落、死气沉沉的。而梅勒斯是和小树林以及小树林中的草地甚至小鸡一起诞生于叙事之中作为新生活的象征。小树林是自然与生机的形象化,身体健壮性能力极强的梅勒斯则是与克利福德截然对立的血管里涌流着人类生存热血翻卷着人性本质波涛的自然之子,是生命力的象征。他生活在大自然里面,融入在大自然之中。行文指向了融入大自然就是统一,就是和谐,就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这一蕴涵。在城市的庄园里,康妮没有办法和丈夫做爱,一点也享受不到性的快乐。雨天小树林里的极致的性快乐叙事,使梅勒斯与康妮都感到了空前的满足和诗意的快乐。并对富含象征的生殖器官进行崇拜叙写,梅勒斯则采来鲜花放在上面,并舞之蹈之,极尽颂扬讴歌之能事。这样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关系影响了《废都》的写作。贾平凹也是这样来刻画他的城市的:一步一步走向破败,尤其是文化的颓败,充满着肮脏和腐臭,到处游走着一群群的废人……于是,这个城市中的庄之蝶几乎没有了什么生命的信念,他的生活或曰生命就是和身边的女人做爱,而到最后在试图逃离这城市的路途上死去。这泛滥的欲望里其实表达了1990年代初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处境的失望和“农业精英心灵崩溃的历程”,而不甘死亡的知识分子发出了那个年代“性欲解放和道德反叛的第一声叫喊。”[4]74
城市往往就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主义的代言者,而国家主义向来视“性欲”为最大敌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于是,知识分子一旦拥有书面话语权力,他能采取的往往就是张扬“性”事,膨胀性叙事,以此来对抗或消解国家主义,尤其是在专制社会形态之下。
有人认为《废都》是“一部深刻的警世之作”[3]65,这自然是就其社会思想价值而言的。就文学价值而论,《废都》是新时期以来最早真正地从正面进行性爱叙事的小说,是真正正视人的自然属性,让性爱不是附丽在政治的道德的那个富丽堂皇的外衣下面的文本。脱掉了这些外衣,性变得纯粹也变得纯净。性回归了自身,文学也就找到了人性表达的正确渠道。还有一点,就是文本表达的女性主体性的悖论,或曰弔诡。女性自认是为男人贡献美的,是为男人而生,男性认为女人是玩物,这是女性失却了主体性的表现。而另一方面,女性自身对于性爱的追求,尤其是在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过程中并不考虑封建传统道德以及宗法观念、落后的法律制度对女性的束缚,这恰恰又是女性主体的寻找。如果女性的性爱真的变成完全由个人来主导了,身体是自己的,我的身体我做主了,那么,女性的主体性也就被进一步确认和尊重了。这一点,《废都》是超越了此前的性爱叙事文本的。
【参考文献】
[1]温儒敏.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扰[C]//孟繁华九十年代文存(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王富仁.《废都》漫议[C]//孟繁华.九十年代文存(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亚川.一部深刻的警世之作——《废都》门外谈[J].文科教学,1994(1).
[4]朱大可.“色语”的书写时代[J].东方,2003(11).
[5]贾平凹.废都[M].北京出版社,1993.
[6]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C]//鲁迅,译.苦闷的象征 出了象牙之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7]栾海燕.《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与《废都》比较谈[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