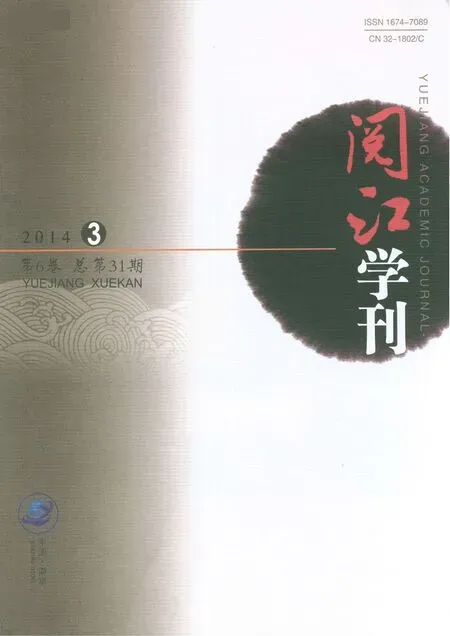回不去的故乡
——新世纪初农民工小说的“还乡”主题
葛亮亮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打工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进入了一个‘城市时代’:城市社会是当下中国社会的轴心,城市文化是当下中国文化的轴心”[1],数以亿计的农民以充满期待的心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个“轴心”。与此相应,出现了许多反映这一潮流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连同反映城市底层市民生活的文学,被称为“底层文学”。本文论述的,主要是有关农民工的小说。
农民渴望脱贫致富,义无反顾地走进城市。但城市作为区别于农村的异质性空间,和农民想象中的世界存在很大差距。离开贫瘠但熟悉的农村后,农民工面对的将是繁华现代却又新奇陌生的城市。在这个场域里,异质性的生活会使他们产生不适感,城乡两元社会结构也会使他们遭受轻视或排挤。在遭受挫折、感到失落之时,乡村①在此之所以用“乡村”而不是“农村”,是因为“乡村”一词比“农村”更带有“精神故乡”的意味。此时的“农村”已经不是实实在在的客体,而是成为思维主体精神“加工”之后带有美化色彩的想象之物。便会不由得浮上心头,心理或身体上的“还乡”②“还乡”是一个古老、永恒的文学母题。千百年来,人类渴望家园的心路历程始终不曾消失。“还乡”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隐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内容。就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向。即便对于那些成功融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还乡”也不可避免。在“离土不离乡”的户籍政策背景下,农民工和农村之间有着无法斩断的血肉联系,农民工的“根”永远在农村,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农村间往返迁徙。即使侥幸成为城市“新贵”,根深蒂固的“衣锦还乡”情结,也会促使他们带着“炫耀”心理回乡探亲。因此,“还乡”作为整个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与之相反相成的另一方面是“进城”),就成了农民工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新世纪以来作家笔下的农民工“还乡”主题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衣锦还乡”,即还乡主体在城市获得成功,荣归故乡,或虽不如意,却装出成功的姿态还乡;第二种是精神救赎式的回归,在城市受挫后主观上的退守故乡;第三种是“中性”的还乡,还乡主体在主观上对城乡并未做出道德高下的判断,只是客观上回到故乡,如逢年过节或家中有事返回农村。我们将仔细解读这三种还乡模式,看作家笔下的三种“还乡”模式是否成功,农民工的“还乡”是否可能。
一、“衣锦还乡”的黄粱梦
在这种“还乡”模式中,还乡主体一般在城市里取得成功。这种成功自然主要是经济上的,而且是相对于其他打工者或仍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而言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文化水平不高,外出务工前很少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不了解城市工业生产的基本规范。进城后劳动对象的改变,使他们必须从头学起(以前所积累的农业生产经验已经没有用处),这种天然的缺陷限制了他们工作的选择和成功的限度。于是,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技术简单的工作,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此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低层次的职业,“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5.7%,其次是建筑业占18.4%,服务业占12.2%,批发零售业占9.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6.6%,住宿餐饮业占5.2%。……变化较明显的是建筑业,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重在逐年递增,从2008年的13.8%上升到18.4%,从事制造业的比重则趋于下降。”见网页 http://www.gov.cn/gzdt/2013 -05/27/content_2411923.htm。农民工拿着低工资,干着最脏、最苦、最累、最重、最危险的活,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的岗位上。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悖谬现实,决定了他们只能是社会底层结构中廉价体力的出卖者和被盘剥者,几乎不可能取得巨大成功跻身社会上层。所以说,“衣锦还乡者”大多也只是获得经济上的微小成功,基本上不可能在政治、文化或其他领域取得成功。
山东作家张继的小说《去城里受苦吧》[2],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工“衣锦还乡”故事。农民贵祥是被“逼走”到城市里去的,因为长期遭受村长欺负,他忍无可忍进城,准备状告村长。贵祥是村里最微不足道的人,没权、没钱、没靠山,乡村权力的压迫让他卑微萎缩、尊严尽失,长期受欺而不敢反抗。进城后,他得到“城里女人”李春的青睐和帮助,迅速融入城市。还乡后的贵祥和村长的地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贵祥不再是那个任村长欺负的贵祥了,村长也不再是趾高气扬的村长,反而卑躬屈膝地讨好贵祥。贵祥以在村长院子里撒尿这一举动,宣告战胜了旧秩序的权威。回城时,村长求贵祥把村长女儿带到城里去,贵祥一口回绝村长。“衣锦还乡”的贵祥撼动了村长传统乡村权力中心的地位,成为村人新的崇拜对象和话语权力者,回到城市,享受一妻(贵祥的农村妻子)一妾(城里女人李春)的“齐人之福”。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意识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城乡之间不同文明模式开始交流互动,延续数千年的乡村秩序发生了变化。作家想努力写出这种变化,但遗憾的是,他的努力并不成功。且不说这个故事是否可能:即一个一无所长、猥琐卑微的农民工能不能获得城市女人(而且是漂亮、温柔、能干的城市女人)无条件的身体供奉和爱情馈赠;单说这个故事,本身就内蕴了一个有趣的悖谬。正如《阿Q正传》中阿Q进城归来,得到了未庄人的“新敬畏”一般,贵祥之所以动摇村长的权威地位,是因为他的城市经验。贵祥颠覆农村的权力结构的原因在于携“城市”自重。在这里,城市和农村既是空间的概念,也具有时间上、价值上的高下意义。城市由于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因而代表着“现代”、“先进”和“强大”;而农村则意味着“传统”、“落后”和“孱弱”。“传统”、“落后”和“孱弱”的农村,在“现代”、“先进”、“强大”的城市面前,自惭形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这也许是作者认为贵祥能成功挑战村长的理由。然而,这一逻辑的深层矛盾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了:既然农村在城市面前是天然地自惭形秽,那么,“孱弱”、“落后”、萎缩的农村男人怎么可能使“强大”的城市女人折服?城市女人会安于农村女人之下,以“妾”的身份,无怨无悔地向农村男人供奉身体和情感么?这实在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矛盾出现的原因就在于,乡村秩序变化的复杂进程被作者肤浅地简单化、片面化了。
乡村权力秩序持续了上千年,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在城市获得的“成功”,也许可以成为和乡村权威讨价还价的筹码,但由于乡村的天然自足性和权力结构的稳固性,颠覆它并不那么容易。作家阎连科的现实经验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对读的“文本”。阎连科说,“到今天,我五十几岁了,我们村的村长是个年轻人,我一回老家,村长还会传话说,让连科到我家里坐一坐。那么,我就只能主动到他家里坐坐了。”[3]一个功成名就、颇具社会地位的著名作家,在乡村权力面前尚且那么地卑微,靠一个“还乡”的农民工去撬动乡村权力秩序,更是痴人说梦。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乡村传统价值被逐渐颠覆或重塑,乡村秩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旧的秩序逐渐被打破,新的秩序逐渐被确立;但这一切变化,是潜移默化、缓慢微小的渐进式变化,而不是作家臆想的那样,权力秩序在瞬间就能被打破、颠覆。李泽厚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说过,“今天走向二十世纪结尾,现代生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打碎着种种古老传统,中国农村也在开始变革,但观念形态在这方面的变革速度却并不能算迅速。”[4]李泽厚的话今天依然适用。农村观念形态的变革并不能算迅速,农民工“衣锦还乡”只是一个黄粱美梦而已。作家想成功写出现代化大潮下乡村的变动,须要付出努力,深入思考,写出城乡文明博弈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避免片面肤浅。
二、逃回“乌托邦”
在作家笔下,每当农民工在城市遭遇到物质或精神上的挫败时,“乡村”往往就变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荆永鸣的《大声呼吸》中,打工的王留栓夫妇在城市频受伤害:王留栓处处被老板、工友欺辱捉弄,妻子被家政公司老板奸污致孕。经受了城市给予的累累伤痛后,王留栓决定带上妻子返回故乡,回到那片阳光灿烂的土地上:“离开城市的火车,逃跑似的奔驰在广阔的原野上,一直向西。”[5]“逃跑”这个词,形象地表达出了主人公的尴尬处境。对他们来说,“乡村”是“出征”的勇士失败之后的精神避难所,回乡是一条逃避城市压迫之路,只有“还乡”这味良药才能医治城市施与的创伤。《民工》里的鞠广大和鞠福生,在城市过着艰苦生活,因为回家奔丧,又被工头克扣全年工资。踏上故乡沟谷边的小道,他们瞬间变得十分陶醉,“父与子几乎忘记了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不幸,迷失了他们回家来的初衷,他们想,他们走在这里为哪样,他们难道是在外的人衣锦还乡?”[6]乡间田野竟然抚慰了主人公的丧妻和失母之痛,令他们欣欣然陶醉了。在作家看来,“乡村”真不愧是一剂有效的“麻醉药”,只是,这“麻醉药”麻醉的是农民工,还是肤浅的作家,要仔细讨论。
陈应松的《像白云一样生活》中,农村娃细满受钱财和手机的诱惑而杀人,不得不逃向城市。钱财和手机正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受城市文明的诱惑,细满走向城市,却忍受不了城市生活的冷漠,头脑里无数次浮现起家乡的美妙图景。他想,“假如没有发生那事”,他现在会“住在神仙住的地方,像白云一样生活”。他向恋人讲述自己的家乡时,“他发现他叙说的家乡是如此之美,像一个童话世界——他也第一次从自己的叙说中,从别人的聆听中,发现了自己家乡的美丽”,但家乡生活的环境的恶劣等痛苦回忆被他有意无意地遗忘:
山上有许多山蚂蝗,专往人的裤腿里钻,还有一种竹虱,往人的毛孔里钻,你若用手拍打,尾巴断了,头还在里面,要痒死你三天。……他没给她讲这个。山上会把人的鼻子冻掉,一年有五个月下雪,人不得出来,就像进了棺材一样。他把这些都忘了,只有蓝天白云,青草山坡,只有猪牛羊,桑麻茶。[7]
在他有选择的记忆和遗忘中,乡村贫瘠落后的一面逐渐退隐或被刻意忘却,代之以前所未有的纯朴和温暖,这种温暖对抗和反衬着城市的种种“丑恶”,掩盖了城市曾经诱惑人心的各种优越。乡村为受伤的游子们提供了母亲般的温暖胸怀,在真实的城市与想象的乡村的对比之中,现实中一路溃败的乡村忽然具有了巨大的优势与感召力。
颇堪玩味的是,在这些思乡、还乡的情节中,“故乡”是一种不在场的风景,也许正是因为其“缺席”的缘故,才能够承担起“舒缓”的重任,给那些在城市颓然失败的农民工提供一种“补偿”、“缓冲”的慰藉。他们所怀念乡村并不是真实的乡村,而是经过了头脑“过滤”、加工之后的乡村世界,在加工的过程中去掉了乡村不能忍受的贫瘠、艰苦、愚昧一面,突出了其宁静与温情的一面:尽管现实中的乡村生活并非真的就那么好,但至少缓解了城市里的压抑和焦虑。
在这些作家笔下,“还乡”被用来对抗城市文化和工业文化所带来的躁动,成为对抗“社会现代性”①现代性是一个意义含混、指向并不十分明晰的概念。但学界一致认为,存在着“两种彼此冲突却又互相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卡林内斯库把后一种现代性称之为“审美现代性”,国内有学者称卡林内斯库没有定义的第一种现代性为“社会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关注的是“现代性”设计中的社会制度层面,诸如国家组织、法律规范和经济体制,漠视了个体生命对现代生活的体验,而审美现代性更看重人的处境问题。参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顾爱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4页;陶东风《审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的一味良药。早在五十年前,夏志清在其著名的《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曾抱怨现代中国文学“宣扬进步和现代化不留余力”,不去“热切地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因而不够“现代”。他说,“西洋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品却对西方文明所代表的富强,表示反叛;他们着重描写个人精神的空虚,且攻击现代社会”,并援引黎昂卢·屈林(Lionel Trilling)的话说,“现代文学——至少是那些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文学——的特色,便是对文明本身所抱沉痛的仇恨态度”。[8]夏志清的遗憾在今天得以补偿,农民工文学的作家们开始反思“现代性”、“现代文明”的弊病,遗憾的是,这种反思过于肤浅。他们对远去的乡村文化怀有夸张的想象与回忆,在对传统的怀念和对现实批判的参照中,乡村的一切被涂抹、修改,变成了远离现实的“桃花源”。
在许多作家笔下,城市与乡村截然相反、相互对立,象征着不同的道德标准,前者是丑和恶,后者是美和善;他们在将乡村道德化的同时将城市污名化,对乡村世界诗化处理,建构起一个反城市文明、反现代性的乌托邦。于是城市就变成了让人堕落的罪恶之地,乡村则能对堕落的人性给予拯救;既然在城市遭遇丑恶,那么就可以借助“还乡”,在道德化的乡村寻找美和善,寻找灵魂的救赎。
刘庆邦的小说《神木》中,金钱异化了民工赵上河,使他变得贪婪残暴:他在矿井下杀死“点子”(骗来的农民工),伪装成井下事故,“然后以点子亲人的名义,拿人命和窑主换钱”。[9]人性的复苏是从还乡开始的。回到家乡后,和淳朴的乡亲交谈时,“不知为什么,他心情有些紧张,脸色发白,头上出了一层汗”。在“乡村”的感召下,他凶残贪婪的内心开始松动,负罪感油然而生。再次外出打工时,刚从乡村进城的“点子”以其善良纯洁进一步净化了赵上河的心灵,赵上河最终牺牲自己保护了“点子”。“还乡”是赵上河人性复苏的关键一环,通过“还乡”,赵上河受到道德洗礼,心灵得到救赎;刚离开乡村的“点子”,保留了乡村特有的淳朴和善良,这种淳朴和善良,更感染了赵上河,使他战胜了邪恶。
这种农村和城市“善/恶”“美/丑”的二项对立,自然是片面和武断的。有趣的是,在当代文学的源头“五四新文学”那里,乡村不仅不“美”、不“善”,而且是“丑”和“恶”的代名词。譬如鲁迅笔下,乡村文化落后、野蛮、封闭、沉闷,乡村居民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由于不同的“现代观”,“现代化的新文学倡导者们往往把前现代的乡土社会形态视为一种反价值。乡土的社会结构,乡土人的精神心态因为不现代而被表现为病态乃至罪大恶极”。[10]风水轮流转,到了21世纪,农村却因为“不现代”成为“善”和“美”的代名词。“面对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的压力,我们有时会把野蛮时代的单纯、宁静作为想象中的庇护所”[11]。对于远离“乡村”的作家而言,“乡村”也是不在场的风景。在对传统文明的怀念和对现实批判的参照中,不在场的“乡村”忽然具有了“失乐园”的意义和价值。作家们借农民工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以想象中农村的“超验世界”来对抗主流的现实“现代世界”。“乡村”成为疗救现代性的解毒剂,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神话”。“乡村”这个想象中的乌托邦,能否担当起反抗社会现代性、实施救赎的重任?我们在下文“中性”的还乡中再仔细分析。
三、“中性”的还乡
在作家笔下,农民工在城市里遭遇委屈时,常常会想起乡村。在真实的城市面前,想象的乡村显现出了巨大的优势与感召力。但是回到乡村后,面对真实的乡村,乡村的优势和感召力还存在吗?我们可以借助小说中“中性”的“还乡”来说明。
首先,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文明的反衬下,乡村是落后破败的。尤其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既在处于物质上的劣势,也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牺牲。中国乡村早已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环境优美、乡风淳朴的桃源胜地。仅就环境而言,已沦为工业化的牺牲品。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种与可持续发展观相背离的发展模式在当下农村相当普遍。“有河皆枯、有水皆污”,在过去我们很难把这句话与田园村庄联系到一起,而今天这句话却成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最真实的写照。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农村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交织,已经危及到农民的健康与社会稳定。农村不再是风光优美的桃源胜地,农民也并不像作家所想象的那样把乡村看成是自己的精神家园。
小说《长在城里的麦子》中,嫁给城里修锁匠的金麦孤独寂寞,抑制不住对故乡的想念,决定回乡寻找久违的亲切和温暖。但她已经不适应传统的乡村生活了。白天在乡亲们艳羡的目光中度过,晚上却感到了不适应。乡村里没有淋浴、软床和室内厕所,只有大澡盆、硬炕和茅厕。于是,金麦“开始想念城里的那个家”,“只在娘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登上了返城的火车。”[12]城市终究是让乡亲们艳羡的,城市以其“现代性”——仅仅是“卫生的现代性”,“物质的现代性”尚未出手——就以势不可挡之势击败了落后的农村。
小说《我们的路》里,民工大宝思乡情切,痛下决心,冒着损失两个月工钱并丢掉工作的风险,完成了一次回乡之旅。同他期盼回乡的热切心情相比,现实的家园是令人沮丧的。年轻的妻子面相衰老;自家的院子更破了;甚至连学校——这个现代文明的象征、未来乡村唯一的希望,也破烂衰败,迎着寒风瑟瑟发抖。思乡心切的大宝,踏进村里的第一步就丧失了久别重逢的喜悦,他的返乡之旅在故乡的贫瘠破落中很快结束,团圆的幸福与家的想象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又不得不踏上再次打工的道路。乡村和农民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土地和他们之间,又是怎么样一种关系?正如学者所说,对农民来说,“‘大地母亲’一类念头与他们无缘……土地之于农民,更是物质性的,其间关系也更功利性,他们因而或许并不像知识者想象的那样不能离土……”[13]乡村对于农民更是物质性的。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土地和乡村既养育他们,却又因落后贫穷限制他们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生活的压迫,他们不得不外出,但外出的最终结果只能使土地失去生命力。乡村的希望在于农民,但农民却因为乡村的贫穷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城市,土地愈发没有希望,乡村愈发破败落后。
其次,乡村是疗救社会现代性病症的有效解毒剂吗?还乡的失意游子,往往会发现乡村也会施予他们伤害。在作家笔下,乡村是精神皈依的象征,能够使还乡者产生对农耕文明的深刻眷恋,也使得他们对乡村的审美情绪发生质的变化。《民工》里奔丧回家的民工鞠广大,走进乡村后,丧妻的伤痛被故乡的自然风物抚平,“田野的感觉简直好极了,庄稼生长的气息灌在风里,香香的,浓浓的,软软的,每走一步,都有被楼抱的感觉”。[14]他对乡土的眷恋,不仅停留在对故土自然风物的亲近感上,更表现在对纯洁乡风的精神皈依上。然而,随着丧礼的进行,鞠广大明白了妻子的死因:留守的妻子耐不住寂寞和人偷情,事情败露羞愧自杀。“性”的开放靡乱甚至变成可购买的商品,这些现象常常出现在城市,是作家心中社会现代性的“病症”之一;而乡村在这一方面常常成为治疗社会现代性、拯救现代文明的最后良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最后的良药也有被失效的可能。小说中,城市是靡乱的,但乡村也未必干净;城市是势利冷漠的,但乡村也未必厚道温情。
亲情是农民工失意时的最后精神支柱,亲人给予归来游子最后的安慰和鼓励,但亲人对受伤游子的再次伤害,往往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魏微的小说《异乡》中,许子慧独自漂泊在北京,“父母、朴素的生活、爱”时时在她心中荡漾。踏上故乡的土地的时候,她有些惶恐:“她在外面遭了罪,她回来是为了得到抚慰,她能得到吗?她现在没一点底。”她的顾虑并不是杞人忧天。乡亲们在她背后指指戳戳,认为她是个在城市里从事皮肉生意的妓女,她的父母也这样猜疑。最终,父母在翻看了许子慧的皮箱之后,“宣判”女儿是妓女。乡村的伤害让许子慧欲哭无泪,她几次推开窗户,“把半截身子探到窗外,试了试,然而这是二楼”。[15]窥私欲、流言蜚语,以及父母的不信任,这些人性深处根深蒂固的“恶”击碎了她的还乡美梦,她甚至决定以死来抗争乡村对她的伤害。
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农民工(抑或作家?)对乡村的诗意想象会被现实乡村一点点侵蚀和消解,乡村真实而狰狞的真相会逐渐显露出来。乡村依旧破落,乡亲依旧愚昧,人性依然丑恶。这时候,那些曾经出现在想象里的美好画面,刹那间荡然无存,精神家园轰然倒塌。事实上,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化以疾风暴雨之势洗涤乡村,乡村逐渐被同化为城市的另一镜像,不仅城市文明会传入乡村,同时现代化病症也会传染给乡村;另一方面,千百年以来的乡村文化也有其劣根性,使得它无法承担起疗救社会现代性病症的重任。
“乡村”是想象中的乌托邦,对于渴望回到传统,回到纯净,回到纯洁的主体来说,“还乡”是无法实现的。在有些作家们看来,“乡村”是对抗现代文明病症的有效工具,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他们笔下的“大地崇拜”和“乡村崇拜”又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神话”,这种“神话”的建构是不成功的。正如著名作家贾平凹在《高兴》的创作后记中说,写作中曾几易其稿,“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16]这一创作自白无疑折射出作家复杂的无法摆脱“乡村神话”的复杂心态,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作家,贾平凹也要和“乡村神话”斗争,更何况其他不成熟的作家。萨义德在描述西方对东方的认识时,有这么一个著名论断,“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达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而这些表达依赖的是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而不是一个遥远的、面目不清的东方。”[17]之所以说作家们的认识是肤浅的,是因为,正如“西方”一般,他们“依赖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甚或自己的浪漫想象,去建构“乡村乌托邦”,在他们笔下,“遥远的、面目不清的农村”被浪漫化、片面化、本质化了。
我们必须承认,以农民工为写作题材的作家们用心良苦,他们能够关注底层,关注农民工,以文学介入现实,本身就是一种责任的担当,也是对现代文学精神的继承。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作家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抗并不是指向速度、效率,能量和机械化的现代文明,而是指向社会现代性对个体生命、尊严的漠视。作家们希望建构一个纯净美好的乌托邦,守住人类灵魂的栖息之所。但和宏阔深远的时代大潮相比,他们的思考显然远不够成熟和深刻,因此他们的笔触注定是犹疑不定的,注定无法为社会现代性的病症开出一味真正有用的药方,于是,在一阵风似的“书写苦难”、回望“故乡”之后,他们发现,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找到真正纯洁的“故乡”来疗救现代化进程中的病症。由于他们的思考不够深入成熟,既没有写出城乡两种文明冲突中的农民的精神焦虑,也没能用笔真切记录下转型时期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农民文化心理的艰难蜕变、农村现代化的艰难进程。因此,这种寻找“乌托邦”的写作难以为继,短短三五年之后,农民工文学,甚至包括底层文学的写作就烟消云散了。
(论文写作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哈佛大学招生与经济资助委员会的资助,在此谨致谢意)
[1] 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J].当代作家评论,1998,(3).
[2] 张继.去城里受苦吧[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3] 阎连科.没有尊严的生活和庄严的写作——在台湾东海大学的演讲[J].当代作家评论,2013,(5).
[4]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84.
[5] 荆永鸣.大声呼吸[J].人民文学,2005,(9).
[6] 孙惠芬.民工[J].当代,2002,(1).
[7] 陈应松.像白云一样生活[J].芳草,2007,(1).
[8]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460-461.
[9] 刘庆邦.神木[J].十月,2000,(3).
[10]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87.
[11][美]威尔·杜兰特.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M].王琴,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07.
[12] 常君.长在城里的麦子[J].鸭绿江,2008,(1).
[13]赵园.地之子[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86.
[14] 孙惠芬.民工[J].当代,2002,(1).
[15] 魏微.异乡[J].人民文学,2004,(10).
[16] 贾平凹.高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46.
[17][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