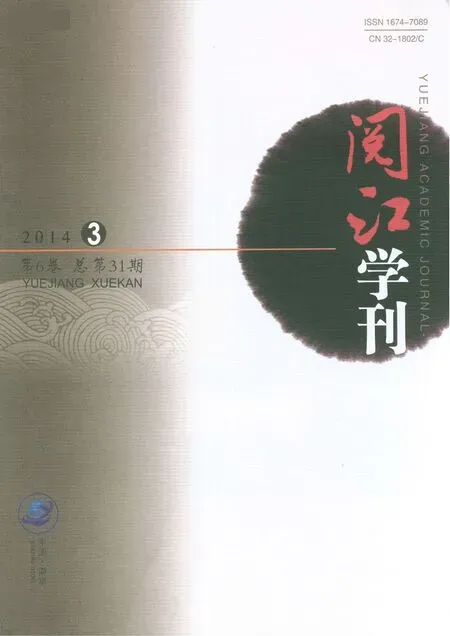文学语境的实践表征
徐 杰
(西南民族大学,成都 610041)
一、文学活动的语境实践
文学语境是在文学经验、文学传统、文学知识和文学批评理论等文学场域之中达成的一种动态性共识的范畴。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交往活动),我们都能体认到语境的存在。
第一,文学创作活动中的语境表征。文学创作的过程是伴随着主体语境、社会文化语境和文本自身形成的语境而不断生成的。在中国古代就有“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方法,这也恰恰说明了语境在文学创作过程之中的重要性。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作家自身的写作风格、人生阅历、审美趣味等等都直接影响着文本的产生,也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生产语境。作品写作过程之中,文学文本会自我生成语境,使得文本具有一种逃脱作家预先控制的力量。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在谈到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安娜最后卧轨自杀,完全出乎作者的预料,因为人物命运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作者的设想而进行下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本在被作者创作出来一部分之后,具有一种未完成的自我生命力量。首先是文学之中事件具有自我生发力。沃尔夫感觉,“这条激流般的力量流过了我,将我挟带而去,我没有办法不写。关于那最初的一段时间,我想我现在能说的就只是,那书是它自己写出来的。”[1]其次,文学之中人物的失控状态。格拉斯发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人物会“捍卫自己,不听作者任意摆布,他们不容对他们施加暴力”,也就是说,“他们迫使作者跟他们对话。”[2]小说之中的人物不再是作家笔下任意支配的对象,而具有平等甚至反叛的力量。安德烈·别雷说,“主题声音产生的形象并不服从指挥,而我则先验地想让它们服从这种抽象方法。我以为:主人公应该是这个样子,可他一再推翻我的想法,迫使我跟着他亦步亦趋,情节也打乱了。”[3]诗歌之中也具有相似的情况,兰瑟姆就说很多真正的诗歌“开始时是一个有待于发展的主题而起始于诗人的头脑中,但人物和情节却在那里发展得比主题快。而且是自动地发展的。”[4]从作家亲身写作的经历来看,笔者认为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命运在两个维度的力量之中博弈——作家对文本的控制和文本上下文的自我调整。
第二,文学阅读活动中的语境表征。文学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形成阅读主体语境。萨特认为阅读的过程包含着预测和期待,预测着接下来会读到什么,同时期待证实或者推翻自己此前的预测,从而经历着希望和失望交织的奇妙过程。读者总是在当前阅读的未来之中品味、思考和预测着,“逐页后退的未来”形成了变换着的主体阅读语境。[5]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费力去识别和区分话语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因为文学作品经过出版、评论和再版,读者已经确信作品值得一读才去阅读它。不管作品中有多少艰难晦涩和与题无关的东西,他们都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对于读者来说享受着一种“超保护的合作原则”(hyper-protected cooperative principle)。所谓“合作原则”指的是在日常交流中,相互配合是我们确立的基本原则。比如,我问你乔治是不是好学生,你说他平时都很准时的。我会认为你是在配合我,肯定回答了我的问题的,而由此去理解你的话。文学便是在这种“超保护”的语境之下使得读者将其当作文学来研读的。“大多数情况下是那种可以把一些文字定义为文学的语境使读者把这些文字看作文学的,比如他们在一本诗集、一份杂志的某一部分,或者图书馆和书店里看到的那些东西。”[6]文学的保护语境赋予了作品被作为文学接受的强大力量。读者的阅读是将自我语境与作品语境融合的过程。当作品进入读者的视野的时候,已经脱离作者原初的意愿,可以被读者进行创造性地阅读了。这也是埃斯卡尔皮“创造性背离”的意图。比如《格列弗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前者本身是建立在对哲学讽刺的基础上的;后者则是为殖民主义歌功颂德的。结果到现在两本书都被作为儿童文学来阅读了。[7]所以,读者语境与作品语境之间并非完全吻合,而是一个不断协调的过程。读者语境表征为四个层面:读者自身主体语境;读者所处时代语境;读者与其它时代语境;读者与其它地域语境。首先,任何读者都是作为一般主体存在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人生阅历、价值判断和审美经验,所以,在接受一部作品时,一定是带着自己的主体语境进入的,并从自己的角度解析和体会作品,即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次,如果读者阅读的是本时代的作品,发生共鸣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比如前些年流行的六六的作品《蜗居》,就是对中国近十年来房价暴涨下小市民艰辛生活的写照。这样的现时代的现实性作品必然带来无数读者和大众的共鸣。还有,当读者的目光触及到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作品时,原作品本身所携带的审美元素和文化基因会因为时代语境不同被读者遗落,但是其核心必然被当代读者重新审视、解读和进行意义充实。在阅读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印第安人的营地》和《乞力马扎罗山的雪》时,我们并不能让自己真正进入到当时时代语境和文化氛围之中,但是作家对“死亡”“痛苦”的文字思考却能让生活在其它文化之中的后世人读出生命的深度。
第三,文学交往活动中的语境表征。文学的交往活动主要呈现在文学话语的语境本体属性之中。话语的生命在巴赫金看来是“在于从一张嘴到另一张嘴、从一个语境到另一个语境、从一个社会群体到另一个社会群体、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转换。因此,词汇不能迷失自己的方向,归根结底不能摆脱它所处具体语境的制约。”[8]也就是说,语言是具有生命的,这种生命和功能是建立在与他人话语(或泛音)的对话的基础之上的,将他者意向和声音内化到自我当下使用的语言单位之上。语言穿梭于不同主体的言说语境之中,当言说者使用词汇时,“词汇是从另外的语境进入他的语境的,渗透着他人的意蕴。他本人的思维发现词汇已是被进入了的……当没有自己的‘终极’话语时,每一个创作意图,每一种思维、感觉、体验,都应该透过他人话语、他人文体、他人方式的语境而被折射出来”。[9]因而,巴赫金眼中,语言的存在和交流都是以语境作为自己依附的背景的。当然,这种文学活动之中的交流本身就是一种语境性的表现,因为纯粹的形式意义上分析的文学语言是不具备文学交往性质的。
当我们在使用“文学语言”时,已经是一个不恰当的术语了,因为文学的“语言”主要是从形式逻辑角度去分析文学;但是作为与文化共在的文学显然应该从语言的使用角度去探讨,即从文学“话语”、“言语”来分析。正如杜夫海纳所说,“当语言在创造行为中被使用时,它已不再是语言或者还不是语言。因为,在艺术中,创造就是话语……艺术是话语……不是语言。”[10]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语言艺术,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具有一种主体间的对话性和交流性。文学话语中的对话性不一定像日常生活的对话那样具有符号化的实体性,可以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回应或交流,“对话关系不是存在与具体对话的对语之间,而是存在与各种声音之间、完整的形象之间、小说的完整层面之间(大型对话),而同时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次感受中,都有对话的回响(微型对话)……所有精神上的关系(和所有被意识到的关系,正在被思考的关系),都是对话性的。”[11]因此,文学话语一定关涉到文学活动之中参与者,从而形成各个元素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文学交往活动主要涉及六个方面:创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或事件的互动对话;阅读者与作品中的人物或事件的互动对话;作品内部人物或事件的自我互动对话;创作者与阅读者之间的互动对话;创作者与创作者之间的对话;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源自于创作者写作过程之中,大脑中一定不停地盘算着读者会是哪一类型的人,怎么写符合他们的口味,应该怎么写才能将更多的人纳入自己作品的读者群之中来等等。像白居易经常将写完的诗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就一直改,直到能听懂为止。所以,白居易的诗歌写作过程之中,读者意识特别强,从而形成了浅显易懂的文风。关于读者之间的对话,首先可以达到文学交流的作用。[12]接受者之间的同一性的形成是在作品基础上的,“作品强迫我们放弃我自己的差异性,迫使我变成我的同类人的同类人,像我的同类人那样接受表演规则,去观看甚至去欣赏。”[13]因此,作家、读者、作品、作品人物等等之间的对话将文学的语境性彻底地表征了出来。
二、文学话语形式和意义赋予的语境实践
语境的功能随着所处的语境层次的不同而不同,“言内语境具有制约功能、协调功能,言伴语境在这两种功能之上还具有过滤功能、补充功能,言外语境则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引导功能和生成功能。”[14]总的来说,语境具有制约和创新功能。文学语境是作为语境的特殊形态,自然也具有上述多种功能,只不过表现不同。文学语境能够保证语言使用的合理化,同时又能促成语言搭配的超常规化。
第一、文学语境与文学话语形式层面。文学语境决定着字词和句法结构的选择。字词和句法结构的选择和组合都浸润于文学语境的同化力量之中。语境同化着词语,使得它具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功能的特殊性又决定着词汇的选择。“每个词,当它进入文学的时候,都被文学所同化,但要想进入诗歌,其词汇特征则应在文学当中获得结构性的意识。”[15]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并非所以语言词汇都特别适合进入文学诗歌,一定有一些相对来说更适合文学语境,而另一些则更适合生活语境或者科学语境。进入文学语境的字词选择和排列以及句法结构都需要作家的细心考量,而这种考量不是以语法规则作为标准,而是以语言产生的审美效果和新鲜感为首要考虑的。比如我们熟知的“僧敲月下门”的“敲”字、“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和“大漠孤烟直”的“直”字,诗人有无数的语言选择机会,但最终确定为这些词,主要是由于它能给人以一种“陌生”的审美感。同时对语词的选择也尽力挑选饱含无尽文化意味的单位,比如“梧桐”“柳树”等,带有着无穷体验和感受的文化情感积淀。句法结构的安排在文学语境之中也不是以逻辑至上的,而是寻求最佳的情感效果和审美效应。比如《伤逝》结尾:“子君却不再来了,永远、永远地。”当然,字词选择也好,句法结构安排也好,其过程也伴随着音律、节奏的安排,不能全然分开。因此,常常会出现一种情况是,为了上下文语境的需要,改变句法结构以适应押韵的需求。
第二、文学语境与文学话语意义。首先,文学语境在保证文学话语基本义不受歪曲的情况下,保持着语言的多义性弹力。日常话语语境重视语言横组合的句段关系,抑制纵聚合的联系关系,因此,语言的意义一般是呈现为明确的涵义的;文学话语语境既重视语言横组合关系,更重视纵聚合的联想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一对多”的潜在意义功能。也就是说,语言只有在文学语境之中才能将潜在的多义性激发出来,成为作为文学语言的优势或特性。“红杏枝头春意闹”,多义性造成了文学语境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张力。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对多的关系,在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语境中,为了追求语言的准确性和单一性,这种一对多的关系受到抑制,正如利科所认为科学语言“要消除歧义,要使一个符号只具有一个意义,要使人们不能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同一符号”[16];但是,在文学语言语境中,一对多的辐射关系不仅不受到限制,反而常常被故意地和充分地使用。科学语境与日常语境的作用主要是限制语言多义性的产生,尽量让意义单一化和明晰化,从而避免误解的产生,而文学语境则试图更多地挖掘语言的多义性。但是,由文学语境带来的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必须遵守“有效性”原则,也就是说,带来文学审美感受的多义性必须是有效的,而不是歧义性的。如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读者可以感受到表层义下面的扩展义,而不像“鸡吃了吗?”这样的歧义句导致接受者无法理解。所以,文学语境中,文学语言语音能指可以指向多个所指意义,是建立在类比的基础之上的,而非逻辑推理基础之上的。其次,文学语境带来文学“意味”。文学语境可以使语言摆脱概念意义的约束,从而具有具体、特殊的涵义。单独的词语只具有词典意义,但当被放入文学语境之后便会产生鲜活的、意想不到的个性涵义。“涵义与意义不同,意义所表示的只是语词与其所指称的事物固有的客观联系,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时固定的;而涵义所反映的却是在感性活动过程中,事物、对象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个人对于语词内容的一种主观体验。”[17]“言外之意”就是语境意义。如《文心雕龙》中的“隐”“隐以复意为工”,司空图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皎然的“但见情性,不睹文字”,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圣俞之“必能状难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诗乃佳尔”,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诗无言外之意,便味同嚼蜡”等。语言本身具有言外之意的性质,所以,这并非文学语言独有的特质,只是文学家有意增强话语言外之意的效果。这种对言外之意的挖掘使得文学话语充满了意味隽永、韵味无穷的审美效果。另一方面,言外之意意味着对原初语言环境的偏离和违背。格莱斯认为,言外之意是为了在话语交流过程中达到某种目的而故意对合作原则的违反;普拉特认为,特别是在文学中,“由于文学被看作是作家静心创作以词做事的方式,因此,文学作品中所有违反合作原则的现象,无论是人物的对话,还是作者提供的信息都必须看作是有意的,是故意要产生某种言外之意的。”[18]“让他去死吧!”狄德罗《论美》一文对这句话的分析,单独看这句话,我们不能体会到它的涵义,因为这句话仅仅表达了让某人死的意义,如果将这句话置于关系祖国荣誉,个人生死的战斗语境之中,老父亲的三个儿子有两个都在保卫祖国罗马的战争中牺牲了,他毅然将剩下的唯一的儿子去战斗,在这种场景下说出“让他死吧!”在这种语境中话语的突破自身字典意义的丰富的庄严、凄美的意味逐渐展示出来。当然如果将这句话置于意大利舞台司卡班口中,也许就成为滑稽幽默了。[19]
三、文学审美效果的语境实践
文学话语区别于日常话语的根本在于文学话语所蕴含的基本语义之外的审美感知,因而文学话语构成的文学语境必然具有强烈的审美创造力倾向。文学语境之中的审美效果生成主要来自于文学语境内部要素之间所形成的语境差。文学语境之间的不平衡带来审美效应。语境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是语境差,它“可能出现在作品语符层面的各语境因素之间,也可能出现在作品人物与读者语境之间,还可能出现在创作与读解语境、读解与读解语境之间。”[20]语符层面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文学话语对语言的语法规范和文化习俗规约的打破,并进行重新组合和链接,于是将语言之中蕴含的丰富的审美经验和感受深度挖掘出来,也就是说,文学语境既可以使文学语言使用它固有的形态和意义,又可以使其偏离常态,造成组合上的新的规约,达到文学表达上的审美效果。作品人物与读者语境的不平衡源自于创作者的语境与阅读者语境的不同,作家将自身的语境信息投射到作品之中,读者面对的不是作家,而是作品文本,于是读者只能带着自己的前见语境进入文本,从而形成语境差。当这种语境差由于时间和空间距离的拉大,比如一个美国读者去阅读屈原的诗歌,肯定会形成语境差。审美效果的产生就源自于这个语境差的形成、协调乃至平衡的过程之中。“文学作品中的语境差具有特殊的审美效应,这一审美效应体现在语境系统内的自我调适。有了语境各因素间的调节,不平衡就可以转化为平衡,并生成美学信息。”[21]这种文学语境的不平衡性常常会形成反讽、张力、悖论、朦胧等效果。如语言系统和文学语境的之间故意的错误置放,会产生反讽的修辞效果,像王蒙小说《说客盈门》、《莫须有事件》、《活动变人形》、《名医梁有志传奇》等等一系列作品之中都存在着大量的反讽。他将60、70年代的一些政治辞令植入80、90年代的叙事语境之中,造成表层涵义与深层的表达之间的不协调,从而产生反讽、诙谐的语言效果。同时,文学语境自身也可以通过变化产生一种语境反讽。比如王朔的三部系列小说《顽主》、《一点正经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之中,主人公都是同一批人。在《顽主》中,这些人从事替身的工作为人解决难事,到《一点正经没有》中,这些人又明目张胆地成为了作家——“流氓”的实践者,最后在《你不是一个俗人》中,这批人重新回到公司干起了新的项目,吹捧他人。这种通过小说语境的转移和对比制造一种荒谬和离奇的效果,产生语境的反讽。
同时,文学话语进入文学语境能够使得自身音响性、图像性和情感性更加鲜明而具更强美感。语言本身就具有感性审美特性,语言从产生就具有诗性。当人试图理解这个陌生的世界,维柯认为,初民是通过“移情作用”将世界隐喻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或身体的感受。“把爆发雷电的天空想象为一种像自己一样有生气的巨大躯体”,[22]甚至磁石吸铁这一现象,他们也将其视为磁石对铁的情欲和恩爱。无生命的事物是用人体各个部分或感觉来隐喻的。而在这个内化的过程中,诗性语言起到了重要作用,它通过隐喻——以己度人和殊相喻共相的方式为人类和各民族造就了一个能为人所理解和把握的世界,诗性语言也就成为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
赫尔德认为,语言不是一种来自本能刺激的发声,也不是任意的约定形成,而是人自己和自己心灵之间的协约,来自人的精神创造,心灵的产物,是人内在的迫切需要,即“悟性”。“语言的全部构造方式正是人类精神的发展方式”,[23]语言的分类,语言从动词发展成名词等过程都反映出人类精神发展的图景;人与世界的关系,因为人类原初的爱憎情感,从而在语言上表现为语法的性,比如事物被分为男性、女性,善良、邪恶。因而,人心中的感觉浸润到所有的物体之中。也就是说,从语言的诞生开始,它就具有非概念、非逻辑的诗性内涵,难怪克罗齐得出语言的本性就是美学性质的说法。[24]既然所有语言就其起源来说都具有一种诗性特征,那么,文学语言独立于一般语言的美学特质又是什么?怎么产生的呢?我认为,文学语言与一般语言并非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而是语言进入文学语境之后产生出的差异。在文学语境之中,语言的审美感性特质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如果真正要对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作区别,我宁愿认为,现在的生活语言才是真正被扭曲异化的语言,因为语言产生之初的那种诗意和韵味在生活语言的实用性之下被消弱了很多。所以,虽然语言在早期是与感性经验共生的,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之中,语言的抽象性和逻辑理性被强化,而将具体性、感受性和经验性的任务扔给了文学。在文学语境之中,作为抽象共义存在的语词、句子和段落所拥有的具象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这种被充分发掘的具象性根据英伽登的“字音层”、“意义组合层”、“客体再现层”和“图式化观相层”[25]表现为语言的音乐性、图像性和情感性。
那么,文学语境怎样将语言具象性的这三方面渲染到极致,从而产生文学的审美感受的呢?
第一,文学话语讲求一种音律美,这种音律美不能像音乐那样通过乐器呈现,只能通过文字发音的组合(包括字音、声调、节奏和韵律等)来形成美感。语言通过人的声音传达出来,本身就具有音律性,刘勰就说过“音律本于人声”的观点,只是我们习以为常或没有刻意为之。但凡语言进入文学语境之后,要达致其美感,务必需要在音律上更为仔细地雕琢。中国古代诗歌所讲究的双声、叠韵、平仄、对仗、押韵等,就是在总结了无数诗歌语言之后得出的最美的表达形式。如帕克所说,“如果绘画中同一色彩或线条的重复,音乐中同一乐音的重复能够使我们感到愉快的话,同一字音的重复为什么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愉快呢?”[26]诗歌对节奏的突出呈现,而小说话语之中的音乐性更多的是体现在结构之上。[27]也就是将音乐之中的“对位法”,将各自独立的音调组合到一个统一的结构之中去。小说中经常会打破单一线性的叙事模式,采用多种视角、多条线索的叙述方式,从而形成类似音乐之中的复调的艺术结构。比如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灵》、《“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和《吉姆爷》等都模仿音乐中的复调技法,从故事情节到叙述视角都实践着主题和形式的复合、缠绕与协调之美。无论是诗歌语言上的音律追求还是小说结构层面上的复调运用,都能看出文学的文体语境决定着对语言的特殊要求,同时,创作主体语境的内心情感和情绪状态也对节奏、音律等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所谓“元韵之机,兆在人心,流连泆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乐,必永于言者也。”[28]
第二,图像美。语言的诗性本性是从人类最早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中就具有的,语言本身就具有情感性和感觉性。语言的感觉色彩就包括语言给人带来的触觉、听觉、视觉等联想。语言从一产生就是伴随着符号所指向的对象的图像表征的。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认为,原始人的思维处于主客不分的混溶阶段,[29]因而,总是会陷入对象的性质和对象的形象纠缠“互渗”之中。卡西尔就说过,“在魔法领域内,语言魔力处处都由图像魔力陪伴着。”[30]比如,说到“太阳”,其圆形、明亮等图像特征就自然复现在我们眼前,更别说像汉字这样的象形文字,更是在字形上就具有对人视觉起到牵引的作用。就像魏姆塞特所说的“言语图像”[31](verbal icon),语言成为世界的镜子,不是因为它为世界带来了意义,而是因为它成为唤醒世界的形象。文学语境与原始世界存在状态接近,都能为语言提供非概念、非逻辑的感性世界。因而,语言符号在原始状态下所带有的图像色彩在文学语境之中也能轻易地被表征出来。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诗句以意象并列非逻辑的组接方式生成,“枯藤”、“老树”和“昏鸦”将一种死亡、没落和沉寂的意味传递出来,带有一种冷色调;“小桥”、“流水”和“人家”更有一种小巧、灵动和生机于其中,带有一种暖色调。诗句纯粹是一种意象和图像的并排和渲染,并将图像所直接带给人的冷暖色调通过文字表现出来。
第三,文学语境强化情感色彩,产生更强美感。语言自身具有情感因素,当语言进入文学语境之中,这种情感性会被有效地展示出来。因为文学语境与前反思性、非概念性的语言原初场景相似。在语言产生之初,主体的内心感受和情感冲动在语言之中凝聚起来,从而得到客观的表现。所以,语言天生就具有一种情感性和直觉性。后来由于理性语言的发展,使得我们将语言的概念性视为语言的正宗。实际上,理性逻辑性只是语言的特殊运用而已,语言的概念性也是源自于经验。而文学语境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感觉和情感之上的场域,区别科学和理性建构的理论世界。当已被概念化的语言进入文学语境之后,其原初本性就会得到最大化的释放。文学语境对语言情感性的激发具有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实现。首先,文学语境使得语言意象和意象组合方式倾向于包蕴的民族文化的情感体验,比如古诗之中经常用“杜鹃”表达悲苦与思念,“杨柳”表达送别与不舍,“流水”表达伤势与惆怅,“落花”表达生命流逝与伤时等等。因此,在表达同一种感情之时,古代诗人更喜欢用长亭、夕阳、飞絮、春花、芳草、西风、落叶、寒蝉、归鸿等等意象来构筑自己的诗歌,因为这类意象携带着的不仅是个体独特体验,更多是整个民族通过几千年形成的文化心理。从而使得这类文学具有让读者产生共鸣的基础。其次,文学语境要求的主体叙事视角对情感传达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着控制效应,像第三人称叙事就比第一人称叙事具有更少的情感表露可能性。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发现,“五·四”时期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作品较之传统全知叙事多了许多。这就和“五·四”时期整个时代都主张个性张扬、表现自我和抒发个人情绪等等社会风气有关。因而当情感需要得到宣泄的时候,文学中的叙事视角转移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手段。另外,文学作品所展示出的人物和事件等发生的语境可以以情感效应为目的进行自我调整和改变,以求将同样的感觉和感受在文学中给人以最大的震撼。同样是写元音辅音,日常生活中谈到人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肯定是在学声上有哪些缺陷。而我们再来看看王小波《革命时代的爱情》,在描写一红卫兵被长矛扎穿而疼得呃呃直叫的片段时,叙事者心里想着:“瞧着罢,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同样对元音和辅音的使用,在文学语境之中可以达到一种令人极其震撼的情感感受。还有,文学语境中,话语追求音律性和节奏性使得情感具有爆发性和回味性,如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叠字和双声字改变舒缓的节奏为急促的节奏,从而达到凄婉、悲怆的感情效果。小说中则通常通过故事情节的节奏变换,使得叙事在文学语境之中达到最佳的艺术审美效果。如《水浒传》中写武松的片段,即是从喝酒的“松”到打虎的“紧”,从打虎的“硬”到遇到嫂子潘金莲的“柔”等等效果。
总之,文学语境是在文学经验、文学传统、文学知识和文学批评理论等文学场域中达成的一种动态性共识的范畴。在此场域之中的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交往活动,文学话语形式生产和意义赋予以及语境差带来的文学音乐、图像和情感性审美都是对文学语境的具体实践。文学语境的此种具体实践所趋向的目的正耦合了康德对艺术审美判断“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思想。
[1] [美]托马斯·沃尔夫.一部小说的故事[M].黄雨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46.
[2] [德]格拉斯.谈文学[A].吕同六,编.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256.
[3] [俄]别雷.我们怎样写作[A].吕同六,编.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203.
[4] [美]兰色姆.诗歌:本体论札记[A].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66.
[5] [法]萨特.萨特文论选[M].施康强,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17.
[6]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M].李平,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28.
[7] [法]罗贝尔·艾斯卡尔皮.文学社会学[M].于沛,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37.
[8][9]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221.
[10][法]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M].孙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9.
[11][俄]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M].白春仁,晓河,周启超,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53.
[12][德]尧斯.接受美学与文学交流[A].张廷琛,编.接受理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201.
[13][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M].韩树站,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94.
[14]王建华,周明强,等.现代汉语语境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80.
[15][俄]尤里·梯尼亚诺夫.诗歌中词的意义[M].张惠军,方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52.
[16][法]保罗·利科.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A].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98.
[17] 王元骧.文学语言[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3).
[18] M·L·Pratt,Towards a 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178.
[19][法]狄德罗.狄德罗美学论文选[M].张冠尧,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8-29.
[20]祝敏青.文学言语的多维空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50.
[21]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55.
[22] Giambattista Vico,New science:principles of the new science concerning the common nature of nations[M].New York:Penguin Group,1999:146.
[23][德]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1.
[24][意]贝内代托·克罗齐.美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M].黄文捷,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54.
[25] Roman Ingarden,The Literary Work of Art: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orderlines of Ontology,Logic,and Theory of Literature[M].Evanston and 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30.
[26][美]H·帕克.美学原理[M].张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59.
[27] Watt,Conrad,The Modernist Novel[M].New York:Routledge,1997:430-431.
[28]王夫之.姜斋诗话笺注[M].戴鸿森,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上.
[29][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0.
[30][德]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张法,刘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14.
[31] Wimsatt·W·K.The verbal icon: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M].Kentuc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5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