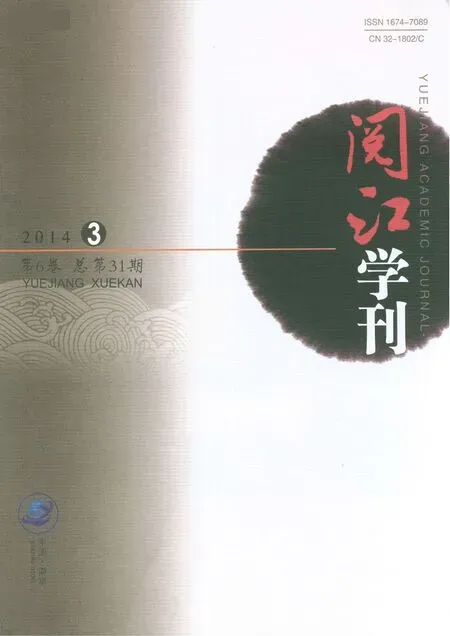缪荃孙文化播迁中的学术思想研究
米彦青
(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 010070)
缪荃孙是晚清民初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博学多识,在诗文著述、藏书、教育诸多方面皆有可观成绩。治学领域由经史诗文、书目碑刻,至近代史料、方志丛书以及日常用书等。正是因为缪荃孙在众多学术领域的突出成就,清末民初,缪荃孙与王壬秋、张季直、赵尔巽齐名,被誉为“四大才子”。作为晚近民初的重要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缪荃孙一生都以学术的薪火传承为念,研究他在变动的时代风云中心灵和学术思想的变迁,对于更好地掌握那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嬗变有着广泛意义。
一、缪荃孙文化播迁概览
缪荃孙一生中对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纵观他的学术研究方式有如下两种:一是为己之学,一是为人之学。作为一代学人,缪荃孙的学术视野宽泛而博杂。他在文、诗、词乃至经史研究方面皆有建树。其“论文奉桐城文学为古文正宗,其古文亦治用桐城义法。”[1]缪荃孙的传世诗稿,早年作有《萍心集》、《巴觎集》、《北马南船集》、《息影集》,中晚年作有《辛壬稿》、《乙丁稿》、《癸甲稿》,后分别录入《艺风堂诗存》及《艺风堂文漫存》中结集刊刻。《萍心集》乃缪氏少年离家漂泊之作,《巴歈集》和《北马南船集》是缪荃孙青年求官、应试的奔波之作,而《息影集》则是释褐后之作。《艺风堂诗存》是缪荃孙以诗笔写就的人生大半岁月之心路历程,由于他在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遂有着他集不可替代的作用。邓之诚先生于戊寅(1938)冬为此集作序云:“艺风先生尝刻所为诗,毁于辛亥国变,后复手订诗,凡四卷。曰《萍心集》、《巴觎集》、《北马南船集》、《息影集》,附《碧香词》一卷,未及授梓,遽于戊午冬下世。后十年,令子子受始再刻之,而未印行。前年之诚为作介,以畀燕京大学图书馆,属中原板荡,艺风堂书版庋存国学图书馆者已不可问,此集岿然独存,不可谓非厚幸也。先生负海内盛名,于学无所不窥,著书满家,乾、嘉经儒老寿犹存者,尚及亲见而师之。同、光之际,考据词章一时称盛,遍交其魁硕,博搜图籍碑志,以为金石目录之学。多闻旧事,明习典故,以为掌故之学。大要嫥长于史,晚更与修清史,发凡起例,成就独多,一生与刻书为缘,孤本秘籍赖以流传,尤有功文教。故先生不仅以诗文传,即以诗论吐属蕴藉,不失先民矩矱。视才气陵厉,谬附名家者,或若不逮,然正唯一世皆噍杀之音,而后觉和平中正者为尤难得可贵。”[2]对缪荃孙的诗文作品及学术生涯作了全面而公允的评说。
缪荃孙的为人之学,更显示出他的宽广胸怀。他的为人之学,始于目录学,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目录学。缪荃孙生活的清朝末期海禁已开,当时部分奋发向上的士大夫,在文明的冲撞中渐渐意识到华夏文化亦有卑弱之处,对于外来文化开始容纳、吸收。缪荃孙早年为功名奔走,在京师作学官,进入中年后,思想有所觉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他掌教书院多年,培养国家有用之才,东渡日本考察先进的教育制度,回国后创办学堂,主持编译馆,出版新式教科书和翻译国外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推动文化,启迪民智,他参与创办了我国南北两大图书馆,即今日南京图书馆的前身江南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成为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奠基人之一。
缪荃孙古籍方面的重要建树反映在他参与了《书目答问》的编撰。近代版本目录学中,缪荃孙无疑是最有影响者之一,广为人知的《书目答问》,实际上就是出自缪荃孙之手,“同治甲戌(1874),南皮师相督四川学,诸生好古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者为善,谋所以嘉惠蜀士,并以普及天下学人,于是有《书目问答》之编。”[3]虽然后来陈垣先生力排此说,但张之洞此书很大程度上得力於缪荃孙当是无疑,至缪氏晚年,其学术成就更是远远超出了张之洞之上。缪荃孙的后人曾回忆说,缪荃孙“光绪二年,三十二。八月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4]缪荃孙的学生柳诒徵也说“(缪荃孙)为张文襄公《书目答问》一手经理……”[5]柳诒徵是缪荃孙最得意的门生,为人持正,又是他的朋友,对缪氏生活中的许多琐事记忆都很准确。因此,他所说缪荃孙经理《书目答问》一事当无疑义。此书共收图书2000多种,以经、史、子、集、丛5部34类加以组织,是一部中国旧学书籍的综合性选目,刊行后,风行海内,称誉儒林。《书目答问》介绍推荐古籍二千多种,多为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典籍,因而《书目答问》起了举历代典籍之要的作用。这部书问世以来,直到民国末期,一直被人们视为读书治学、举业成才的重要工具,翻印重刻不下数十次。《书目答问》不论类目设置还是著录内容都颇具特色,显示了缪荃孙的学问功底,在学界初露头角。
缪荃孙入仕后,在目录学上所做的主要工作是《艺风藏书记》三编的编撰。缪荃孙早年从广东藏书家李文田习版本目录之学,从此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以后南来北往,遇书辄购。在京师任职时,缪荃孙常去海王邨书肆搜访异本,又与许多藏书家往来,互相抄校考订,学问亦随之日益博通。缪荃孙一生以藏书、传书为业,至庚子年(1900),五十七岁的缪荃孙,经三十多年的努力收藏,使缪氏艺风堂藏书积累了十余万卷的孤本秘笈。也就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举国震惊。当时,缪荃孙主讲于钟山书院,鉴于历史上人亡书散的教训,他担心天下大乱,自己的藏书不能保,遂编撰了第一部藏书目录——《艺风堂藏书记》,并于辛丑(1901)十二月钟山讲舍住宅饱看山簃写下了这部藏书记的缘起:“旧刻旧钞,四库未收之书,名家孤传之稿,共十余万卷。甲午初夏,与掌院徐相国议不合,投劾归,遂乞祠禄,辇书自随。庚子夏秋间,京师变起,南中亦岌岌,如李易安所云四顾茫茫,盈箱溢箧,知其必不常为己物矣。秋日酷暑,移笔砚于深竹阴中,清风泠泠,洒我襟袖,因思勒成一书,遂按藉编目……他日书去,而目或存,挂一名于艺文志,庶不负好书若渴之苦心耳。”[6]缪荃孙根据藏书编《艺风堂藏书记》8卷。本着“慎择约举”的原则,《艺风堂藏书记》仿《孙氏祠堂书目》之例分为十类,著录图书六百627种、10962卷,从中挑选,按藉编目,尽录题跋、印记,略举人之仕履,书之大意,缪氏在《藏书纪缘起》中自认不敢与瞿、杨、丁、陆四大藏书家相比,但足与吴骞的拜经楼和孙星衍的平津馆相伯仲。缪荃孙苦心经营的藏书业同史上的藏书家一样,为时代学术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藏书家是学术研究的首要条件之一。他们收藏、出版史料,向有关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文献。在17、18世纪兴起的图书收藏热中,藏书家和实证研究关系十分密切。没有这些藏书,文献考证家就无法获得研究必需的材料。江南图书楼的长足发展、雕刻及善本翻刻业的进步,使学术交流更为便利,还为之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7]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缪荃孙的藏书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庚子后,缪荃孙东游日本,得暇即搜罗旧书。在国内,又观书于四明天一阁,并曾先后担任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监督之职,及寓居上海,托日本人将原先藏书四百箧转运上海,所得之书与庚子藏书相埒。1912年,缪氏依前书体例,在上海聊珠楼成《艺风堂藏书续纪》8卷。在这段时间里,缪荃孙由于没有收入,只能以书易米,但仍自鸣旷达,以“书去目存”自慰。此后,虽政治上失意,经济上拮据,而嗜书之癖依旧,遇好书,必“损衣食之费用而置之”,但数量并不多,且“旋收旋散,有若抟沙”,晚年又成《艺风堂藏书再续记》2卷,以版本组织,分为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旧钞本、校本、影写本、传抄本七类,著录所藏旧本百馀种。在《艺风藏书记》书成的十几年中,缪荃孙在先后编成的《艺风堂藏书续记》8卷,《艺风堂藏书再续记》2卷中,把自己所藏图书分门别类、逐一记录下来,并对“四库未著录者,略举人之仕履,书之大意”,以此流传后世。实际上,这些并不就是缪荃孙的全部藏书,据郑逸梅回忆,“缪筱珊晚年,有日记三巨册,记各种版本及轶闻,遗命其子禄保,不许刊本。”[8]缪荃孙对学术的追求是严肃认真的,他认为,要刊本的必须是确有学术价值的东西。
洪亮吉《北江诗话》将藏书人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等五类,掠贩家自与缪荃孙无涉。更为重要的是,缪荃孙与一般藏书人还有着近乎本质的不同,那就是他对于中华文化的一种深挚的爱。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缪荃孙应两江总督端方之聘,创办江南图书馆,任总办,为江南图书馆的创立与发展而奔波于江浙藏书之家。当时海内藏书家有南北四大家,即江苏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浙江归安陆新源皕宋楼、浙江钱塘丁丙八千卷楼,其中尤以丁氏八千卷楼最为著名。此时陆氏皕宋楼之书已为日本人以重金全部购去(现藏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而丁氏亦家道中落,其后裔正欲将所藏“八千卷楼”善本书卖给日本崎岳的“静嘉堂文库”。缪荃孙认为,这些书是国家的宝藏,不能再流落异邦,他在端方的支持下,紧急筹措七万三千元巨款亲赴杭州与议,将全部藏书60万卷悉数购回。此批书极为珍贵,据柳诒徵所撰《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中有关书目统计,宋版书40部,1845卷,元版书98部,3981卷,其他还有四库修书底本、名人稿本等。缪荃孙随即将书运到南京,就在清凉山附近前任两江总督陶澍所建的惜阴书院旧址建造大楼,将“八千卷楼”的图书连同捐购之本贮藏其中,编写了《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并撰有《八千卷楼藏书志序》。为纪念这件文化盛事,端方的幕友们建议将大楼命名为“陶风楼”。后又充入武昌范氏月槎木樨香馆藏书4557种,故江南图书馆藏书在当时为全国之冠。宣统元年(1909),军机大臣张之洞掌管学部,奏请创办京师图书馆,荐调缪荃孙任图书馆正监督(馆长),时图书馆尚未建造,暂借城北积水潭广化寺为储书之所。缪荃孙督基建,聘馆员,分类清理书籍,并从内阁大库检出元代蒙古人从临安(杭州)南宋秘阁所收的珍本,即加集刻为《宋元本书留真》,并重价购买姚觐元的私人藏书,充实馆藏,一手创成京师图书馆。
缪荃孙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仅以目录学而言,除上述《艺风堂藏书三记》外,较著名的还有《艺风堂金石目录》18卷、《艺风堂读书记》4卷,又曾辑有《荛圃藏书题识》10卷,还曾为盛宣怀编有《盛氏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主持编撰《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等。缪荃孙所编的另一专题目录是《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这一书目于辛亥革命前夕编成,计4卷,共录省府州县方志1676部,其中明志224部,不全者360部。这虽非我国方志目录的首创,但为公共图书馆方志目录的滥觞。
缪荃孙又喜刻书,除了为他人校刻过各种书籍外,自刻有《云自在龛丛书》、《对雨楼丛书》、《藕香零拾》、《烟画堂小品》等。田洪都序《艺风堂藏书再续记》评论缪荃孙说:“一生与刻书为缘,孤稿秘籍,多赖流布,广人见闻,裨益文化之功,可谓至巨。”清代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张海鹏曾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更广耶?”[9]好读书的缪荃孙,继承了先哲之精神,以先藏书既而又刻书的形式,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古籍汇总编纂者。缪荃孙又以收藏金石碑名,他的云自在龛藏碑帖近12000种。光绪二十二年(1896),江南藏碑大家沈树镛旧藏散出,缪荃孙卖田买碑,一下子购进3000余通,收藏金石之最,遂属缪荃孙。缪荃孙的《艺风堂收藏金石目》,是他在专题目录学方面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几次由川入京会试途中,他“每逢阴崖古洞,破庙故城,怀笔舐墨,手自椎搨,虽极危险之境,甘之如饴。”[10]其后供取京师及主讲济南泺源、南京钟山书院时,一方面尽力收购,一方面募资派人往拓京畿、山右、山左、大江南北及皖中碑刻。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苏州又以重价收得曾为刘燕庭所藏的拓本3000余种。于是按代编目,凡伪造摹刻,无地可考者皆不录,共得10800余种,为18卷。这就是缪荃孙竭三十余年精力收藏,花了三年多功夫编撰而成的《艺风堂收藏金石目》。后又续得千余种,藏本之富,为前代金石家所未有。
清亡后,缪荃孙住在上海虹口联珠楼,彼时,“艺风堂”藏书已达11万卷,收藏金石古董11000件,自著书达200卷。“古今经籍之传,由竹简而缣素而楮墨而椠刻,日趋便易。至丛书之刻在艺苑已为末事。然萌于宋,绳于明,极盛于我朝。乾嘉之间,大师耆儒咸孜孜焉弗倦。校益勤,刻益精,藉以网罗散逸,掇拾丛残,续先哲之精神,启后学之涂轨,其事甚艰,而其功亦甚巨。”[11]“续先哲之精神,启后学之涂轨”,这是缪荃孙一生读书治学、传播图书之思想精华所在。他在《江阴先哲遗书序》中说:“士大夫居乡收拾先辈著作,寿之梨枣,以永其传,有三善焉。一邑读书之士能著述者不过数十人,著述而能存者不过数人,吉光片羽,蟫杰为巢及今传之,俾不湮没,其善一也。土风民俗之迁革,贤人才士之出处,贞义士女之事实,耳目近接,记载翔实,是传一人之诗文即可传数人之行谊,其善二也。乡曲末学,志趣未定,贻以准则,牖其心思,俾志在掌故者,既可考订以名家工于词章者,亦能编纂而成集佩,实衔华闻风兴起,其善三也。”[12]在缪荃孙看来,人生最大的乐事,莫过于藏刻古籍、研读古书、习治古文了。居金陵时,他曾自撰联语:“饱暖自矜稽古力,萧闲天与著书年。”[13]广博的兴趣,在成就了缪荃孙宽泛的治学之路的同时,也把他培养成了一个杂家,一个文化名人。著名学者李审言就认为缪荃孙是治杂家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①“李审言不清许人,惟对王晋卿颇致钦佩。……又对于冒鹤亭亦有好评,如云:‘鹤亭,子部杂家之学,与陈石遗等,信缪艺风、沈乙庵后一人。’”(参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3页)。
缪荃孙的为人之学并不仅限于此。他曾历主南菁、泺源、龙城、钟山等书院讲席。清光绪十四年(1888),时任国史馆总纂的缪荃孙因继母病故,离任服忧,奉柩归里。应江苏学政王先谦聘为南菁书院院长。南菁书院系清光绪八年(1882),江苏学政黄体芳在两江总督左宗棠支持下于驻节地江阴创建的一所全省最高学府。南菁书院的办学方针同谈程朱理学的书院及一般应付科举考试的书院完全不同,它重在经史词章的实实在在的学问,反对士子耽于科场利禄。崇尚朴学,不教八股之业。缪荃孙与著名学者、定海黄一周分任经学、词章,并主编《南菁书院丛书》144卷、《南菁讲舍文集》9卷。三年后,继母丧期满除服,继而又因父丧,不能回朝,去往山东济南掌教泺源书院。清光绪二十年(1894),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将缪荃孙聘为南京钟山书院山长,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缪荃孙还兼领常州龙城书院山长之职。讲学之外,编刻丛书,日事校勘,抢救古籍,成绩斐然。光绪二十七年(1901),为推行新政,张之洞集东南名流于武昌讨论,决议在南京设立江楚编译局,由缪荃孙主持局务,介绍外国书籍。同年改钟山书院为江南高等学堂,由缪荃孙任监督,兼领中、小学堂。为改革教育,缪荃孙于12月亲赴日本考察学务。归来后,亲自参与商定课程,编写课本,中西之学兼重,访聘真才实学的教员,讲求教授管理之法。第一届毕业生颇有明达通才,为士林所敬重和取法。江南高等学堂(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是我国创办最早的近代高等学校之一,因缪荃孙初创之功,清廷特诏加四品卿衔。
二、缪荃孙的学术思想流变
缪荃孙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中西之学兼重的教育家,更是名重士林的藏书家、刻书家。纵观缪荃孙的藏书与治学,还不仅仅是为自己,更是为国家、为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对学者而言,其学术史与心灵史总是紧密联系的。缪荃孙的晚年生活在思想界发生急剧变革的20世纪初期,无论如何,革命还是导致了一个新社会的开始。社会的革命往往带来人们思想态度的改变,而这时期显然表现出来对过去传统的唾弃。比如采用西元纪年,外交上穿西洋礼服,政府采用西方组织形式等等。在遗老们眼中,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改变就等于承认西方胜过东方。因此,思想阵营中革命派与保守派立刻形同水火,而保守派就一直采取自绝于仕进之途、遗世而独立、按照自己的理想方式读书生活创作的守势。这是旧瓶和新酒之间,社会现实和社会理论之间,茫然莫知所以的旧一代和茫然莫知所以的新一代之间,荒唐滑稽对照对比的一个阶段。可是在文人的心灵中,这样的时代变化无疑是性命攸关的。在新的时间和进步观念影响下,未来变得很必要,但在晚近民初的过渡时期,这种时空转化在士人心理上实难接受。换言之,身处的现实情境逼使晚清士人憧憬未来,但在不可知的迷乱中他们也有着太多的惶惑。
其实,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传统人格时,大致有三种状态:一是调和态,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出入自由,心境平和。二是分离态,他们在外来文化的压力下,失去调和传统精神的文化氛围而陷入矛盾中,于是或在困惑中回归传统,或在分离中走向“中西化合”,实现一种新的整合。三是抛弃态,他们摒弃传统人格价值观,而一味地从外来思想中寻找人生的准则。[14]处在调和态和抛弃态的士人,无论处在哪一种情态下,虽有时代带来的痛苦,但都可以暂时偏安于心灵的一隅,只有行走在两者之间的分离态者,才会有学术文化、道德修养、生存理想间的依违两难之苦痛。不幸的是,缪荃孙正是这样的士子。因此,他的学术文化走向既有固守传统的执持,也有洋为中用的调和。
缪荃孙的学术文化,无论是内省式的为己之学,还是外倾形的为人之学,都始终反映出变革时代中的文化特征。变革时代的功利性,不仅冲击着缪荃孙,也冲击着每个士子的人生追求、道德理念和文化信念。墨守陈规的士人往往被套牢在岁月的彀中虚耗时日,而少数试图超越现实束缚的士人才能够摸索到一些突破策略。应该说,缪荃孙在他的为人之学中体现出了他的这些突破策略,无论是讲办学堂还是创建图书馆,都是为了在新旧交汇、观点丛出、思想纷扰的时代中开启民智,走出浑蒙。这些文化建树,一方面反映出缪荃孙的思想有进步的一面,另外也可以看出他保存和传播儒教文化的良苦用心。对他而言,即便翻译国外著作,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其它国家的思想文化脉络,利于在变革的时代中找出应对之策,以期留存中华文化。因为在现实中缪荃孙已经感到,当建立在利益推动精神上的西洋文明把几千年国人沉静迷梦打破的同时,自然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孔门伦理的基础。此时的缪荃孙的思想相当矛盾,他所能做到的,仿佛就是在外侵日重的形式下,尽己所能的做些抢救民族文化的工作,而且这也是他的心性之所在。所以,缪荃孙保护了大量古籍、古董,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精神财富,而且在校勘刻印珍贵古籍、研究版本目录学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缪荃孙的为己之学又在很多时候牵制了他,每当反省时代,反省人生的时候,缪荃孙就又无法走出自己的精神窘境,他成为时代夹缝文人中的一分子,留恋传统文化、不想改变相对幽闭文化氛围中的古诗文辞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理念。“近顷以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阶级渐渐得势,颇苦于古文学之不能尽量自由发表其思想,于是有打破旧形式的束缚的新文学之出现。梁启超《新民丛报》的报章文字倡于先,《新青年》的白话文字继于后,现今我国文学界,可说是此二种文字的势力。”[15]梁启超派的“报章文字”风行于“戊戌变法”后,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正处于对立时期,士大夫阶级中的进步分子想要“从八股文外延长他们政治上学术上传统的特权”,而豪绅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则想“从地方势力握得中央势力”。[16]无论是哪个阶层中的进步分子,都发现报章文字最是合于他们通情达意的一种东西,所以,这种文字形式很快就流行起来了。“五·四”前后,又有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的突破旧文学的束缚而得解放的自由的文体——白话文字代报章文字应运而生。这种种的变化,皆极缤纷奇诡之观,虽是代表了社会的进步势力,但并不是生活在时代夹缝中的文化人所都能从容接受的。
缪荃孙在他的诗词作品中多处抒发个人在变革时代中的茫然心绪、浮沉仕路,一种欲吐又吞的情怀,他的《拟玉溪生有感二律》:“海内原无主,冲人敢自专。虞宾方敛抑,赵肉荷矜怜。庶乎风尘起,浑如梦呓然。钩陈临左辅,天策握中权。云雨相翻覆,裳衣太倒颠。东都摧柱石,北阙集戈鋋。机括凭徐穉,纵横属李全。桐宫终不返,流涕旧山川。”“不解扶持苦,惟闻责备深。赤熛方肆怒,黄屋遂消沉。擢发应难数,羞颜恐不禁。彼苍无可问,毕世效聋瘖。”[17]就是借李义山式的绵邈诗怀展示个人婉曲心灵、悠长情思的典型作品。作为一名清朝官员,缪荃孙身遭鼎革之变,面对礼崩乐坏,世事难如己意的时世,他的内心时时有着不忍想起又不能忘记的感喟,故此,缪荃孙在模拟前朝诗人诗体诗风时,很容易就想起了李商隐。这一特点在他的《灵鹊》诗中表现得更为充分。除了李商隐,对清末曾接受义山诗风的黄仲则、樊增祥他也有和诗,“眼前不改旧山河,往事凄凉付逝波。轴覆枢翻腾铁骑,天荒地老泣铜驼。还家深恐难全璧,阅世浑疑欲烂柯。龙汉劫中余一乐,异乡偏聚故人多。”[18]虽然诗中的“眼前不改旧山河,往事凄凉付逝波”语出晚唐赵嘏《经汾阳旧宅》中的“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但颔联所叙的“轴覆枢翻腾铁骑,天荒地老泣铜驼”的黍离之悲,才是诗人想要表述的诗心,李义山曾于《曲江》诗中悲慨“死忆华亭闻鹤嗅,老忧王室泣铜驼”,缪艺风翻用其典,其意依旧在“夜月啼鹃悲故国”。[19]
综观文学史,文事之兴无不与政事并进。清末大地云扰,变乱丛生。在此人心浇离之际,缪荃孙等遗民坚守儒教伦常,鼓动文人艺士并不就是全然落后的。文学是合文字、思想两大要素而成,旧思想尚存,自然就有寄托旧思想的旧文学存在。据郑逸梅《艺林散叶》载,辛亥革命时,缪荃孙参加众多流寓沪上的遗老组织的“超社”,彼时已经七十岁矣。[20]
缪荃孙的思想虽然守旧,同样打进了时代的气息。他和同时期的很多遗民以一种“拒新恋旧”的理念引领,沉湎在传统的学术氛围之中,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孽臣孤忠”式的时代共感。面对目不暇接、风云变幻的现实他们感慨万分,痛心疾首:“神州扰离,风雅弁髦,明教扫地,吾人今日处境之难堪,有甚于零丁孤露,饮冰茹蘖。”[21]这种易代之感,借用胡薇元的话来说,就是那种“心与境异”的“岁寒”之味。①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自序》云:“于骄阳烈日炎威溽暑中,而曰岁寒,心与境异也。”(参见胡薇元《岁寒居词话》,1934年铅印本)此“心与境异”的“岁寒”正是遗老们心灵的真切感受,是社会变迁在他们心里烙下的深痕,传达出遗老心灵与新时代之间、个体生命意识与传统道德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不仅有对旧时代逝去的无奈,也有对新时代到来的恍惚。在个人无能力作为的情况下,惟有“时时以共保此岁寒为念”。不管时代怎么变,在那些静穆自在的心灵中,“风雅”、“名教”仍然辉煌博大,充塞天地,反映在缪荃孙的诗词中,便是频繁出现的“故国神思”以及遗老孤愁之感。虽然清廷朝政也曾使他不满,并曾有消极隐退之念,但鼎革之变还是让他无法接受,矛盾的他既曾接受新教育思想,然而又曾拒绝使用新式机器刻书,并且还选择“逃命天涯”的生活方式。“少年遭难离乡曲,中年服官麋廪禄,老年革命逃海角。装无陆贾之金,怀抱卞和之玉,天禄读未见之书,明夷无待访之录。叹世事兮茫茫,逐风尘兮碌碌。是耶,非耶,有靦面目。”[22]而事实上,他的这种逃命,更多的是心灵上的被放逐。缪荃孙曾作有《减字木兰花》:“江湖浪迹,头白无家仍作客。岁岁他乡,烟雨天涯总断肠。不如归去,杜宇声声啼不住。放棹江南,仕隐机关我总谙。翀霄无力,屈指人才薪样。沧海横流,埋骨何方胜一邱。平生知己,南海李候今已矣。华屋犹存,雪涕西州白板门。松楸手植,扫墓归来无几日,大好溪山,自葺茅庐昼掩关。朝耕暮读,小隐无妨江海曲,北郭梧溪,前辈流风,续旧题长亭怨慢。”[23]有感事变人非、江山空劫的茫然心情,通过“头白无家仍作客”的形象特写,把身世之感规范于家国之念,在一己身世之感中寄托着儒教伦理情怀。
“在中国,19世纪90年代开始了思想的风云激荡过程,这不仅产生了变法维新运动,也预示了一个社会文化变化的新时代的到来。”[24]在缪荃孙眼里,革命带来的思想上的变革几乎是扫荡性的,“宣统辛亥,君令渭南变起殉难。呜呼!盗起一隅,多方响应,如狂飚之乱卷,如野燎之四起。甫及四月,遂移国祚。稽诸史册,亡国未有如此之易者。……盖自戊戌变政,新党首倡破坏三纲,十余年来邪说渐渍人心,忠臣义士之气因此少衰。”[25]“近来三纲沦斁,踰闲荡检,名为倡明女学,实则破坏家规,借异域之行为,师桂寇之往迹,几不知世间有节义事。”[26]他无法适应这种文化上的变革,他早期也曾借助西学新思想所建构的为人之学,但是,在时代变革的加剧中,在人生岁月的衍流里,已渐行渐远,留给心灵深处的是越来越沉重而守旧的思想,他在自己生命的余年只爱故国的古文化。“野鹤闲云伴此身,惊心岁月去如尘。空怀抗手千秋想,已是平头六十人。薄海难求安乐土,余生自署葛天民。屠鲸射虎非吾事,只愿紬书葆性真。”[27]1919年,在新旧交替的思想惝恍中,缪荃孙病逝沪寓,终年七十六岁。
[1] 刘声木.桐城渊源考[A].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国朝鼎甲征信路[Z].台北:明文书局,1985.
[2] 邓之诚.艺风堂诗存跋[A].缪荃孙.艺风堂诗存[M].北京:中国书店,1939.
[3] 缪荃孙.半崖厂所见书目序[A].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A].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Z]. 台 北:文海出版社,1985:卷五.
[4] 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Z].1936年家刻本.
[5] 柳诒徵.缪荃孙与盛宣怀书跋[A].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劬堂题跋[M].台北:华正书局,1996.
[6] 缪荃孙.藏书记缘起[A].缪荃孙.艺风藏书记[M].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
[7] [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M].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01.
[8][13][20] 郑逸梅.艺林散叶[M].北京:中华书局,2005:73,24,343.
[9] 张煜明.中国出版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159.
[10]缪荃孙.王仙舟同年金石文钞序[A].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Z].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卷五.
[11][12] 缪荃孙.积学斋丛书序[A].缪荃孙.艺风堂文集[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Z].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卷五.
[14]杨柏龄.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361.
[15]仲云.通过了十字街头[J].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
[16]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3.
[17][18][19] 缪荃孙.乙丁稿[A].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M].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卷一,卷一,卷一.
[21]况周颐.《莺啼序》(音尘画中未远)词序[A].况周颐.蕙风丛书[Z].陶凤楼刊本:第六卷.
[22][25] 缪荃孙.癸甲稿[A].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M].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
[23]缪荃孙.碧香词[A].缪荃孙.艺风堂诗存[M].北京:中国书店,1939.
[24]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22.
[26]缪荃孙.乙丁稿[A].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M].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卷二.
[27] 缪荃孙.息影集(下):六十[A].缪荃孙.艺风堂诗存[M].北京:中国书店,1939: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