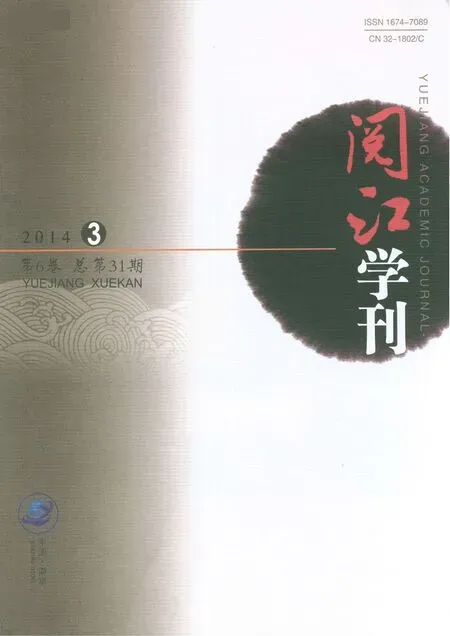语言流中的文学语言
秦晓伟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语言学转向以来,对语言的考察成为各门人文科学的重心。文学研究领域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成为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主调。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到法国结构主义甚至后结构主义,都是以索绪尔语言学为依据,侧重对文学语言的形式分析,并发展出文学符号学;英美新批评也是以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为分析对象,当代美国文论融汇解构主义的语言策略与言语行为理论为一体构建出行为论的批评模式。形式主义及后来的结构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的初衷在于探索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建构一门独立的文学科学,从而摆脱文学的外部研究模式,摆脱传统工具论语言观对语言的钳制。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差异就成为他们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出发点。在此,我准备考察几种有代表性的区分方式,不过这种考察将突破语言研究的静态模式,置于动态视域下进行。
一、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常与反常的变奏
关于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最早最著名的区分来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他发表于1917年的文章《作为手法的艺术》正是围绕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差异展开。将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区分开并非什克洛夫斯基的首创,形式主义阵营的另一理论家列·彼·雅库宾斯基在他之前提出了诗歌语言规律与日常语言规律相悖的观点。事实上,形式主义理论家们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他们普遍认为日常语言奉行省力节俭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有其自身的独特规律。
什克洛夫斯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区分的两个标志性概念:自动化与奇异化(又译陌生化)。自动化是日常语言的特征,与感受力的惯性有关,是无意识的表现,也是用符号取代事物的代数思维方式的体现。“在用这种代数的思维方法时,事物是以数量和空间来把握的,它不能被你看见,但能根据最初的特征被认知。事物似乎是被包装着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从它所占据的位置知道它的存在,但我们只见其表面。在这种感受的影响下,事物会枯萎”,因为“在事物的代数化和自动化过程中感受力量得到最大的节约:事物或者以某一特征,如号码,出现,或如同公式一样导出,甚至都不在意识中出现。”[1]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日常语言的这种无意识的自动化很可怕,他引用托尔斯泰的一则日记证明这种危险:“如果许多人一辈子的生活都是在无意识中渡过,那么这种生活如同没有过一样。”[2]自动化令人们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在抹消事物存在的同时,抹消生命的存在。也就是说,不留痕迹,稍纵即逝,旋生旋灭的日常语言吞没一切,不能为存在提供见证。因此,为了挽留存在之痕迹,感知生命之分量,有必要借助能唤起存在感的语言,那就是“奇异化”的艺术语言。
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3]
在他强调“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时,就在同传统认识论基础上的语言工具论划清界限,他认为,艺术语言的目的在于感觉体验而非知识。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文人绘画的旨趣相契合:中国文人山水画要求可行可望可游可居。①宋代画论《林泉高致》有言:“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见郭熙,郭思.《林泉高致》,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载,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632页)不过区别在于,中国文人画是从道家美学出发对艺术提出要求,是拒绝刻意地留下痕迹的淡漠之迹;而什克洛夫斯基要求的“可观可见”的“奇异化”的艺术语言,则显示出一种语言自我彰显的特征。奇异化,或陌生化的语言,是通过反常的自我凸显来挽留目光,标识在场,通过言语的阻挠引发人们穿越事物的表面,深入事物,细致周全地察知事物。虽然什克洛夫斯基声明其目的不在可认可知,不在制成之物,但客观上这种语言的功能必然导向更深入的认识。换言之,奇异化的文学语言,以凸显语言本身为目的,同时凸显语言所描述之物。
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什克洛夫斯基归结托尔斯泰的奇异化手法“在于他不说出事物的名称,而是把它当作第一次看见的事物来描写,描写一件事则好像它是第一次发生。而且他在描写事物时,对它的各个部分不使用通用的名称,而是使用其它事物中相应部分的名称。”[4]简言之,也就是通过搁置约定俗成的命名,换个视角对事物进行再度感知体验;通过这种有别于常态的言语体验使我们再度看到由于司空见惯而变得熟视无睹的事物,发现寻常事物的不寻常之处。在这种从寻常中勘探不寻常的语言手法的尝试中,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就不再是泾渭分明的对峙关系,而开始相互转化。奇异化的文学语言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沉淀为寻常之语,而寻常的日常语言也会在长久的遗忘之后再度恢复奇异化的功能。而且,“我们翻开任何一本书,在书中我们首先看见的是引起注意的愿望。从普通的事物中刻画出不同寻常的事物来。为此又要把不寻常的事物表现为寻常的。”[5]在此,发生的不是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势不两立,而是二者的互渗互溶,是常与反常的变奏。
二、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规范与越轨的张力
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论语言观被认为抛弃内容只论形式而频频遭受批评。对此,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认为,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概念并非是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而是包涵文学作品全部容量的形式;并且,什克洛夫斯基强调形式至上正是对前一时期内容至上观念的纠正,是用一种片面性纠正另一种片面性,纠妄必须过正。①参见周启超.《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114页。事实上,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所举的托尔斯泰奇异化手法的范例,如关于鞭刑的描写,关于马对私有制的感受等,恰恰证明了语言形式的丰富内蕴。在语言的奇异化过程中,不管是搁置共名去描述事物,还是从陌生的视角来审视熟悉的事物,平常所建立的词与物的关系都遭到质询。奇异化手法,在凸显语言自身的同时,悄悄地动摇着既定秩序和惯常观念的基础。这当然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论语言观。也就是说,穆卡洛夫斯基从历史语境方面解释了什克洛夫斯基形式论语言观的有效性。他在《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一文中,承续什克洛夫斯基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并大大拓展了思路,用“标准语言”取代了“日常语言”,用“结构”置换了“形式”概念,从而将对文学语言特性的研究导入结构主义的轨道上来。
穆卡洛夫斯基从标准语与诗语言的关系入手,认为诗论家与语言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着眼点不同:诗论家关注的是诗人是否受制于标准语的规范?规范在诗作中以何种方式存在?而语言学家关注的则是:“一首诗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作认识这种标准语规范的材料?”即“诗的语言的理论的根本旨趣在于标准语言和诗的语言之间的差异,而标准语的理论却侧重于它们的共同点。”[6]由此可以明了:一个奉行差异化原则试图在语言作品之中立定自身,一个采用同一化原则从语言的整体中抽取本质;一个排他性地构建差异,一个简约化地构建同一。但事实上二者并不矛盾,标准语的同一性正是诗语言与非诗语言之间构建差异的前提条件,而诗语言强调差异也是为了确立自我同一性。因此,这里讨论的不再是标准语与诗语言的差异,而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二者在整个语言系统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及功能。
二者的密切联系存在于如下事实里:对诗歌来说,标准语是一个背景,是诗作出于美学目的借以表现其对语言构成的有意扭曲、亦即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有意触犯的背景。……正是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有意触犯,使对语言的诗意运用成为可能,没有这种可能,也就没有诗。一种特定语言中标准语的规范越稳定,对它的触犯的途径就越是多种多样,而该语言中诗的天地也就越广阔。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规范的意识越薄弱,对它的触犯的可能性就越小,而诗的天地也就随之狭窄。[7]
原来,标准语作为诗语言的背景,作为诗语言发生扭曲的条件,为语言的奇异化、陌生化提供可能。诗的审美空间的营构正来自于对标准语规范的触犯,来自于越轨的冲动。这种越轨的冲动,破坏规范的冲动源于诗意地、审美地维护“真”的目的及组织审美形象的意图。标准语中规范的力量愈强大,诗语言越轨的冲动也就越强烈,由越轨而拓展的诗意空间也就越广阔;标准语的规范性越弱,诗语言就越难以找到逾越对象,也就越不能与标准语所指涉的世界区别开,因此,也难以营构超越性的审美空间。说到底,诗语言就是与标准语作对的语言,就是对标准语的逆向运用。穆卡洛夫斯基考察到,在诗作内部,标准语也仍是作为背景存在,目的是要突出被扭曲的那一部分诗性语言。因为,全部使用被扭曲的语言就会使诗作失去可读性——我们无法进入一个完全陌生无法识别的文本空间。
从宏观层面来说,标准语构成诗语言背离的对象,也是诗语言活动的主要背景,虽然是以否定的、与此作对的方式;从具体方面来看,文学作品内部对语言的运用就既有符合规范的一面,又有偏离规范的一面。虽然说偏离规范的语言才更接近文学语言的本质,但也正是规范的标准语那一部分作为背景,才指明、彰显了这种偏离现象的存在。相对于标准语的“背景”功能,穆卡洛夫斯基把诗语言对标准语的偏离、扭曲、自我彰显称为语言的“突出”(foregrounding,又译“前推”)功能。诗语言是能最大程度地“突出”言辞的语言。在对突出的界定中穆卡洛夫斯基沟通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自动化”和“奇异化”的概念。
突出是“自动化”的反面,即是说,它是一种行为的反自动化。一种行为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受意识支配的成份也就越少。突出的比例越大,受意识支配的程度就越高。客观地说,自动化使一事件程式化,突出则意味着对这种程式的破坏。[8]
在诗的语言中,突出达到了极限强度:它的使用本身就是目的,而把本来是文字表达的目标的交流挤到了背景上去。它不是用来为交流服务的,而是用来突出表达行为、语言行为本身。[9]
突出是反自动化的,是破坏规范和程式的语言功能,这种功能的实现恰恰是什克洛夫斯基提倡的“奇异化”或陌生化手法的结果。突出和奇异化都强调意识的主动介入,强调语言的自我彰显,都是拒绝语言的交流功能而注重语言的审美功能。奇异化相对于日常化、自动化而言,通过反常而凸显,是以日常语言为背景;突出相对于规范化、程式化而言,通过越轨而实现,是以标准语为背景,“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歪曲正是诗的灵魂。”[10]因此,可以说,标准语与诗语言之间呈现为一种规范与超越规范的张力关系。甚至在诗语言内部,如果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也同样存在规范化与超越规范的冲动。
在将“突出”与“奇异化”作比较中,一个一开始就存在的、含混暧昧的问题浮出水面:穆卡洛夫斯基的“标准语言”与什克洛夫斯基的“日常语言”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等同的吗?为什么自动化成为二者共同的特性?它们作为非文学语言存在何种差异?这种差异是人为建构的还是客观事实?美国文论家斯坦利·费什(Stanley E.Fish)曾在《普通语言有多普通?》一文中对普通语言或标准语言表示质疑,进而质疑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界划的合理性。①see Stanley E.Fish,“How Ordinary Is Ordinary Language?”in New Literary History,vol.5.No.1.1973.普通语言(ordinary language)这一概念暧昧地囊括着日常语言和规范化的标准语两个向度。
我的看法是,穆卡洛夫斯基的“标准语”概念来自语言学,是符合某种语言标准、规范的语言;这种语言标准和规范是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抽象分析与归纳总结的产物,是依据语言要素的沉淀而人为构建出来的语言结构或语法体系。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诗语言)都可作为构建这一规范的材料,反过来,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又都受到这一规范的约束。标准语言与日常语言都会在惯性作用下导致自动化的发生,在这种意义上它们一起站到了反常的、奇异的、突出的诗语言的对立面(甚至诗语言内部也会发生陈辞滥调现象,这时所谓的奇异化就可能借助日常语言而与自身的自动化语言拉开距离);不过,从规范性的程度来说,时常越轨、偏离规范的诗语言(尤其是书面文学语言)却常常比日常语言,尤其是口头语,更符合语言规范,从而成为建构新的语言规范的主要依据。换言之,日常语言更不符合规范,不过这不是有意偏离或越轨的结果,而是语言的个体性差异与即时性语境导致的结果。因此,不管是日常语言还是文学语言,都是现实的语言现象,但并不存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标准语言或普通语言,标准语只能是一种建构,并潜在地发挥作用。
三、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逻各斯与神话的互补②这里也许用“科学言语”和“诗歌言语”更为合适,因关涉到的主要不是普通语言学问题,或一般语言学中不同部分的结构关系问题,而是针对语言的特殊使用中的差异性问题,属于语用学意义的考察。因此,用具有个性化意味的“言语”概念来取代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语言”概念更好。在下面的讨论中,瑞恰兹提出语言的“情感用法”实际上已经表明诗歌语言中主体的在场。利科也是在“言语”的语言学框架内展开对科学与诗歌的思考。不过,利科最终将二者沟通起来。这就重新使“语言”概念变得可用。
英美批评界从语用学理论出发,认为并不存在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分,存在的不过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用法而已。因此,语言作为一个先在的同一性范畴,为建构不同言语(或语言的不同用法)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合法性。即以同一性为前提,从质疑差异、否定差异的立场出发,其结果反而肯定并确证了差异。一旦从个别性概念“言语”而非集体性概念“语言”的视角看过去,差异就变得理所当然。瑞恰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在其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批评原理》中较早谈及这一问题。瑞恰兹认为,语言具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科学用法,一种是情感用法。语言的科学用法以确凿真理为旨归,以客观世界为指涉对象,“可以为了一个表述所引起的或真或假的指称而运用表述”,强调指称性和确定性;语言的情感用法以情感态度为旨归,是“为了表述触发的指称所产生的感情的态度方面的影响而运用表述”,虽然其中不排除指称性,但“在这些情况中指称是真是假根本无关紧要。它们的唯一功用在于引起和支持成为进一步反应的态度。”[11]语言的情感用法具有虚构性,重视溢出指称物之外的意义向度。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两种语言用法的真实性问题。科学语言之真,要求符合现实逻辑,得到事实的检验,拒绝指称的差异性,因为科学真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情感语言或文学语言之真,则意味着“可接受性”,是“内在必然性”或情理真确性在起作用。[12]与指向外部世界的明确清晰的科学用语相比,以情感为主导的文学用语具有虚构性、意向性、内指性的特征,会导致语言意义的含混不清。
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正是从“一词多义”现象切入对科学与诗歌之语言效力的思考。德国19世纪语言学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将“言语力量”界定为“有限工具的无限运用”,这一界定将“语言”(有限工具)与“言语”(无限运用)关联起来,为利科提供了考察科学言语与诗歌言语之间能力相互转化作用的出发点。利科认为,符合“有限工具的无限运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语言游戏,一种是一词多义。语言游戏中结构规则的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无限只不过是列举的无限,而一词多义现象中的无限则是构成上的无限,基于支撑无限意义的词汇本身,具有开放性和生产性。词典是一词多义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场所,但只有在具体的言语之中,一词多义的效力才能得以实现。在一词多义现象中,语义的丰富性表现出双重效果:从积极方面来说,它以有限涵盖无限,具有简约经济的效力;从消极方面来说,它制造歧义,导致误解发生,给言语活动造成困难。面对歧义,利科提出,
在一系列可能的解决方案的一端,我们有科学语言,它可能定义为系统地寻求消除歧义性的言论策略。在另一端是诗歌语言,它从相反的选择出发,即保留歧义性以使语言能表达罕见的、新颖的、独特的,因而也就是非公众的经验。[13]
这是两种对立的语言策略:科学语言致力于消除歧义,维护一词一义,从而维护专业术语系统的稳定性;诗的语言不是消除歧义,而是保护、利用甚至制造歧义,以隐喻思维为主导展开多重的意义网络。因此,一词一义的科学语言并不能“说明语言的所有力量”,[14]而诗歌语言才能最大程度上发挥语言的效力。在此,似乎可以列举二者之间一系列对立项:科学语言具有单义性、精确性、指称性,服务于信息传递;诗歌语言具有多义性、含混性、抒情性,服务于情感表达。
不过,发现二者的差异并非利科探讨一词多义现象的初衷。利科从诗歌的情感导向出发,重申诗歌作为一种诗性存在方式的价值,重申诗歌与真理之间的古老联系,从而揭示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之间对立互补的关系。科学语言以一种精确性和可证实性建构人与物质世界、现实世界的关联,诗歌语言以一种意义的丰富性和不可证实的真理性建构人之存在的意义空间。二者的对立互补才构成语言的完整效力,即逻各斯(logos)与神话(mythos)的协作。这与马丁·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对语言的本源性考察相沟通。
四、文学语言:文学与语言之间的叠合
苏轼曾形容自己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15],当代作家汪曾祺也提到,“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中国人说‘行文’,是很好的说法。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16]语言的内在流动性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再流动的语言就是一种死语言,失效的语言。因此,对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任何界划与区分,都避免不了语言流动性造成的冲击与破坏,从而使任何明确的界划都成为不可能。形式主义关于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差异性研究,并不能取消语言在常与反常之间的变奏,事实上,自动化与奇异化概念揭示的恰恰是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相互转化的规律;布拉格学派关于标准语与诗语言的分析,更是致力于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及这种关系所引发的语言变化态势的研究;从语用学视角对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的划分,最终也走到逻各斯与神话互补共生的道路上来。可以说,流变性是整体语言流的特征,也贴切地描述了语言流中形形色色的言语支流聚合分散、汇流分流的现实情状。我认同洪堡的看法,“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的,而是只能在连贯的言语中为人感觉到或猜度到(这一点更能够说明,真正意义的语言存在于其显示发生的行为之中)。”[17]从发生学视角看,语言就是那种在持续流动中减损消逝并增补更新着的事物,其不竭的动力源泉来自人们言说处于流变中的事物的根本需要。文学语言在语言流中,时而沉潜汇融而了无痕迹,时而奔腾跌宕而先声夺人。
关于文学语言,有把它视作文学的质料,是与文学形式相对而言的混乱素材;有把它看作文学的形式,通过自我凸显来确立文学是其所是的本质;有把它限定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以作品的物性存在为其划界;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文学语言是具有文学性的语言,它也可以存在于非文学作品之中。在此,我把它作为一种文学活动中的语言现象来看待,它涵盖了文学活动与语言活动相交接的全部现象。从这种宽泛的文学语言视野出发,能将前面几种不同层级的文学语言观念囊括其中,而且可以避免片面分化的危险,尽可能地顾及文学语言运作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依据下图,可以获得对文学语言流变规律的相对直观、动态的理解。

在上面这组图中,每组由两个虚线圆环构成。一个表示语言活动的范围,一个表示文学活动的范围。由于这两种活动都不是封闭的,其边界都存在位移和张缩,故用虚线勾勒。语言活动和文学活动的叠合地带就是文学语言安身立命之所在。图二所示,文学语言恰好处在语言与文学的之间,是文学语言存在的正常状态。它可以向语言活动区域扩张自己的领地,在此演化过程中语言活动区域与文学活动区域渐趋重合汇融,文学语言的特性几乎消融殆尽,如图一所示;文学语言也可以为了标识特性,确立自我同一而尽可能地远离语言活动区域,导致语言活动与文学活动交叠地带渐趋缩小,如图三所示:文学语言由于拒绝平庸,抗拒规范,甚至抗拒意义的负累,兀自耸立在语言和文学的接合点上,也是危险的临界点上。这种状况恰如纯粹的语言游戏,是文学语言本质纯化的一种极致状态,也是语言活动和文学活动分离的极致状态。正如二者完全重合,成为语文学,是一种假设的理想状态;二者分裂到唯一的接合点,成为空洞的语言游戏,也是一种不可能状态,面临着文学的彻底消失。不妨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于文学语言之不可能性的临界试验,是科学主义的文学语言研究或诗学研究走入穷途末路的标志。人们对文学语言的认识,一般来说,经历了从图一所示,语文学的混融状态中出发,达到图二所示正常状况,而后在科学性诉求的推动下遭遇图三所示的危险的临界点,然后重又复归正常状态。语文学的状态和几乎完全分裂的临界状态,最广阔最丰富但缺乏自觉性与最狭小最贫困但自我同一的两极,构成了文学语言运动的张力,也标示了其活动的极限;在此范围内考察文学语言边界的游移变化,更能全面了解文学语言的运演规律。
[1][2][3][4] [苏]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第二版):上[M].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10,10,11,12.
[5] [苏]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第二版):下[M].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388.
[6][7][8][9][10][捷]简·穆卡洛夫斯基.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A].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414,415,416,417,424.
[11][12][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M].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243,245.
[13][14][法]保罗·利科.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A].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三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95-296,298.
[15]苏轼.苏诗文集(第五册)[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069.
[16]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A].邓九平,编.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23.
[17][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A].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