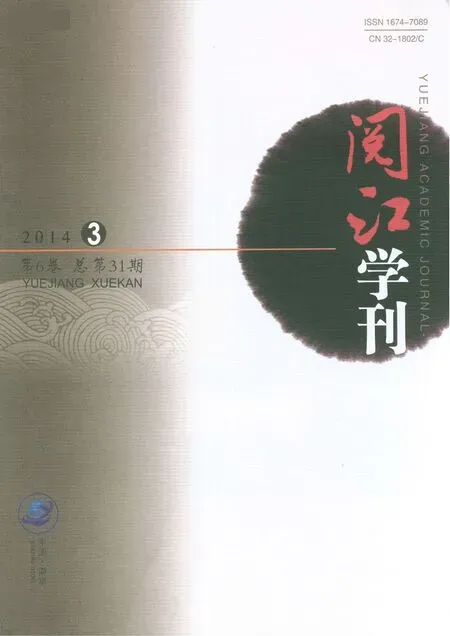气候变化冷思考
史 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 210044)
对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媒体普遍持有这样一种假设:科学已经证明,全球变暖的唯一原因就是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这一过程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并一直持续至今。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信仰者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但是事实上,科学并非如此简单,科学结论也不具备如此的确定性。既然气候变化事关每一个人,人们就有权利听到“不同的声音”,以确保正确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作为“门外汉”,我们至少可以向科学家请教以下几个递进的问题,以便较为系统地理解和质疑“权威的”气候变化事实及其影响。
第一,气候是否在变暖?或许气候并未变暖,或许气候变暖已经停止,未来的气候可能会变冷。
第二,是否存在稳定的气候?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实现气候稳定或气候平衡,可什么样的气候才是稳定的或平衡的?如果气候稳定或气候平衡这一目标根本不存在,那么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就显得有些荒谬。
第三,气候变化是否与人类活动有关?虽然气候在变暖,但气候变暖或许与太阳黑子活动或宇宙尘粒等其他因素有关,而与人类活动无关;即使与人类活动有关,但人类活动的贡献或许可以忽略不计。
第四,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而言是否是消极的?气候变化一定是坏事吗?即使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有关,气候变化也可能带来远远超过损失的收益,因此,气候变暖可能对人类有益。
第五,为什么关于支持全球变暖的声音如此地一致?科学总是在不断的争论、质疑和证伪①例如,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所创立的证伪主义理论。波普尔从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的归纳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普遍命题,认为科学理论不断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而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都能证伪普遍命题,即如果根据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假的,其前提必假。在他看来,一种理论所提供的经验内容愈丰富、愈精确、愈普遍,它的可证伪度就愈大,科学性就愈高。中前进,但质疑气候变化的声音却越来越少,这其中或许另有隐情。
正是对世界上确定事物的理性怀疑,科学家们才能够使人类的认知不断发展。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就是对反对观点进行不断的争论和试验,直到这个观点最终被证明是真的或是假的。怀疑既是一种哲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态度。为了真理,让我们向气象学家(以及相信气候变暖的气象经济学家、气候政治学家等)提出我们的质疑吧!
一、气候是否在变暖?
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气候变化结果:变暖、变冷以及不变。气候变冷说和气候不变论都是对气候变暖的质疑。实际上,科学界内部对气候是否在变暖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
在一些科学家论证气候变暖及其带来的可怕后果时,在各类媒体热情报道国际社会围绕温室气体减排付出的努力时,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也如影随形,那就是全球气候变冷说。实际上,这种观点比全球气候变暖论的历史更为悠久。
在19世纪,科学家们担心的问题是全球变冷。他们认为,在宇宙中,各星球的温度极低,而且在宇宙中长期保持均衡低温,所有的生物都无法生存。19世纪末,瑞典化学家斯万特·奥占斯特·阿累尼乌斯对温室效应很感兴趣。他计算发现,到1896年,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全部消失的话,地球的平均温度将降低21℃。他还评估了人类活动特别是燃烧煤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活动是有益的,加强了温室效应从而延迟了冰期的来临![1]他提出了为世界气候前景和短期世界命运做决定的重大问题,因为和现在的科学家一样,19世纪的科学家之间同样存在高度的共识,而且他们的官方地位和当代科学家也是一样的(阿累尼乌斯于190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虽然这些科学家和当今的科学家一样,都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并享有同等的科学权威,但他们预测的结果却恰恰相反!
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担忧的问题也是气候变冷。一些科学家从地球运转轨道周期变化规律出发,提出了盛极一时的气候变冷说,认为地球将在21世纪进入“小冰河期”。1974年,一批欧美著名学者在美国布朗大学举办了一个专题研讨会,他们在会上举例证明地球气温已开始下降,表示距最近一次(15世纪)的地球小冰河期已有约500年,如果人类不加以干涉,当前的暖期将会较快结束,全球变冷以及相应的环境变迁很快就会来临。忧心忡忡的两位会议发起者甚至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写信,发出小冰河期临近的警报。
气候变冷说的声音几十年来从未沉寂,只是常常被“屏蔽”而越来越难以被公众接收到。早在1998年,日本学者槌田敦就提出,环境问题不是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暖的问题,而是气候变冷与经济行为带来的森林、土地的丧失问题,因此,关于气候变暖的对策研究毫无意义。[2]该观点最新的变体形式是,承认地球在过去的世纪里变暖,但变暖的趋势在1998年已经停止;甚至还有极端观点认为,地球自1998年进入了新一轮的降温过程,并且可能进入冰期。即使其后并未出现与1998年相同的高温情况,也并不代表全球变暖的过程已经停止。地球不仅正处于长期的变暖过程中,并且每一年全球的平均气温都因厄尔尼诺效应以及其他气候现象的影响而波动。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已经达到每10年约0.2℃,折合每年约0.02℃,而年与年之间平均气温的变化幅度为0.1—0.2℃。例如,Joe D'Ale运用高度精确的卫星数据,考虑轨道漂移和其他因素后,认为在过去29年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已经减缓,在21世纪头10年变暖趋势明显下降;Qian Weihong等探讨了1850年—2008年的全球温度变化的长期趋势和多时间尺度周期性波动,认为最近10年际暖期是3个周期性正位叠加的结果,属于自然界内部变化范围之内,并由此推测21世纪30年代会出现一个冷期。[3]
气候变冷说也得到了部分冰川学家的支持。据俄罗斯《今日报》报道,俄罗斯、法国、美国的冰川学家到最靠近南极点的俄罗斯的东方站进行超深钻探,分析钻取的岩芯中的氧同位素含量,发现在过去的42万年中,全球气候变冷和变暖相互交替,有明显的周期性。他们认为,地球气温变化的一个完整周期为10万年至12万年,而最近一次地球气候变暖的高峰约在1.7万年前,现在已开始降温,人类活动以及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都不足以改变地球气候变化的总趋势。无独有偶,丹麦科学家丹斯加德等人发表的格陵兰冰芯氧同位素分析成果表明,地球气候有10万年的轨道周期变化,其中9万年为冷期,1万年为暖期。据此推算,目前气候的暖期已接近尾声,全球气候变冷将是主流。采加诺夫在俄罗斯科学院的网站上报道:俄罗斯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俄罗斯水文气象局中央高空观象台及莫斯科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的合作研究表明,全球平均温度在2005年达到峰值之后,已经下降了0.3℃,回到了1996年—1997年的水平。科学家相信,到2015年平均温度还将下降0.15℃,与20世纪80年代初相当。2020年的气温将使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居民回想起1978年—1979年的严冬,到2040年地球开始“冻结”,温度可能比现代低0.5℃,大体上处于1880年—2006年的中间值。这些研究结论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IPCC)发布的报告观点完全不同。
气候变冷说的支持者似乎还在现实中找到了证据。近几年,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大面积持续的极寒天气。比如,2012年底,大范围寒流横扫北半球,一些地方的气温甚至创下几十年来的最低纪录。被认为气候变暖最明显地区之一的阿拉斯加,在本世纪的10余年间年均气温已经降低了1.3℃,西部的半岛地区甚至降低了2.5℃。此外,2013年8月北极冰盖不仅没有像预言的那样融化消失,而且面积大幅增加了60%,以致一支期待在冰雪消融之际,开辟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北极西北航道的船队被冰雪围困。
2012年1月27日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Allegre等16位科学家联合署名、题为《对全球变暖不要惊慌》的文章,认为近10年来地球气候没有变暖,呼吁不要压制气候变暖怀疑论者的声音。[4]质疑者提出,如果温室效应理论是有效的,那么,在两极地区,气温应该因人为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而大幅上升。换言之,气候变化应该开始于极地地区。但是在南极,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量的地面监测站和卫星观测的数据表明,只有指向阿根廷方向的南极半岛,其气温在上升,而超过南极大陆面积98%的地区,其气温在缓慢地下降。在北极地区,仅阿拉斯加的许多地方有变暖的趋势,这可能是对发生在1976年—1977年太平洋10年涛动的反映;而在北极其他地区,目前并无迹象表明气温在变暖或冰盖在融化。格陵兰岛也是越来越寒冷,特别是在格陵兰岛的西南沿岸地区。[5]
在1974年4月15日的联合国演讲上,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倡议进行更多的研究,以应对气候变冷的威胁。同年,气象学家得出了一个现在看来令人颇为吃惊的结论:自然气候以每年0.15℃的速度变冷,因此会在2015年降到0℃;接着会出现20年—30年的轻微变暖,约在2030年左右达到每10年上升0.08℃的峰值;之后的一百年变化甚微;一百年后气温将再次下降。[6]
历史是一面镜子,气候变冷说以及人类应对气候变冷的历史也是当代人必须了解的历史。即使历史更为悠久的气候变冷说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近40年的气候变暖论就一定是真理吗?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同一个声音”表明科学家的自信显得过于盲目。
二、气候稳定是否存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二条声明,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稳定在某个水平,以防止人为危险地干扰气候系统。”这一提法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气候稳定或气候平衡是存在的,或者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就是使气候不变。然而,气候稳定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怎样的状态才是稳定的?无论是《公约》,还是《京都议定书》都没有声明,什么样的温室气体水平是稳定的。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詹姆斯·汉森写道:全球变暖使地球陷入了“能量不平衡”。[7]但是,他却忘了精确地告诉我们,怎样的气候才是他所认为的“平衡的”气候。换一个提问方式:人们最喜欢什么样的气候,或者什么样的气候最适宜人类生活?我们常常发现,人们虽然来自气候差异巨大的不同地方,但被问及最喜欢的气候,许多人还是认为家乡的气候最好,原因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即使是他人认为不好的气候。
对地球约45亿年的漫长历史而言,截取近100年的时间段来衡量考察,进而得出全球变暖的结论可能是片面的。实际上,地球气候有冷暖变换的周期。全球气温在1℃左右的变化,在过去5 000年中极为普通,不能作为气候变暖的证据,依据这种极为普通的温度波动而得出结论,可能纯属杞人忧天。17—18世纪,地球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19世纪末以来地球温度的上升可能只是这次小冰河期的结束。一些科学家认为,目前的气候变化属于自然界内部正常的波动。Ian Plimer根据冰芯数据对全球大气温度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发现百万年来气温存在23次明显的波动,其中明显的增温现象仅有4次,亚冰期与间冰期之间的年平均温差为±4℃左右;最近1万年来属于第四纪冰期中的间冰期,是处于亚冰期之后的气温回升阶段;最近1000年来属于间冰期范围,仍然具有明显的波动特征,20世纪后期的气温变化没有超过间冰期的正常波动水平,甚至还相差甚远,气温波动幅度在±1℃范围内。[8]
全球气候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系统,当给定初始状态的二氧化碳浓度时,并不能预测未来气候系统的具体状态。目前所有气候模式给出的二氧化碳浓度倍增时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将上升2℃的模拟结果,只是未来全球气候状态中的一种可能。有研究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与气温曲线的变化并不一致。1940年前的气温升高,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完全没有关系。紧接着,20世纪50年代初人类又经历了一次气温下降的过程,而此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在增加。20世纪晚期所记录的地表气温上升,或许是由于数据采集地出现了问题——大部分气象站位于城市或城市开发区,这些城市化地区因自然植被地面被混凝土或其他人工材料覆盖而出现了城市热岛效应,因此采集的数据并不具有代表性。①同样,设置在环境优美的自然景区或城市公园的环境监测设备所采集到的PM2.5数据也不能真实反映大气污染状况。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气候部门负责人乌里希·贝纳尔指出,气候从来不是稳定不变的。贝纳尔认为,科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只关注温室气体,并企图以此阻止气候变化的做法是错误的。当前的人类能够像生活在公元900年—1100年气候条件绝佳的中世纪的人类一样,适应不断改变的气候。[9]
如果气候稳定并不存在,那么人类不断努力并投入惊人的巨额财政资金以防止气候灾害,并使气候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可能就是一个虚幻的目标。全球各国政府会不会正在采取一些可能无法获得成功的战略和举措并为之倾注数以亿计的巨额资金与气候变化作斗争,而最后不得不向全世界人民宣布“很遗憾,这场战争,我们输了”?[10]
由于地球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整体,并作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系统而不断进化。从地球形成开始,在过去45亿年中,气候一直都在变化,即使人类不存在了,气候将来仍然会继续变化。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气候从来都是不平衡的,因为所有的气候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只能将气候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界定为一种平衡状态。[11]人们试图实现的可能不是稳定的气候,而是人们所熟悉的气候。
三、气候变化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
《公约》在第一款中规定,气候变化专指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气候变化。然而,气候系统十分复杂,影响气候系统的因子众多,是自然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大还是人为因素的影响大?人类活动(主要是温室气体排放活动)是否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1990年IPCC发布的第一次评估报告,向人类警示了气温升高的危险,并促成了《公约》的出台。在1995年的第二次评估报告中,清楚地表明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并为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铺平了道路。在2001年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中,IPCC以更详实的证据表明全球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有关,全球变暖“可能”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可能”表示66%的可能性。在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IPCC列举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气候变暖已经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人类活动“很可能”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很可能”表示90%以上的可能性。
造成地球变暖的因素很多,包括太阳的活动、宇宙射线的变化等等,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些质疑。第一,IPCC宣称的人类活动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这一论点是否得到了证实?第二,当代的变暖或许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太阳和地球系统的振荡才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第三,人类或许根本没有对大自然产生重大改变的能力,因此所谓人类活动改变气候不过是一种妄自尊大的说法。
有俄罗斯科学家研究发现,宇宙尘粒是气候变化的原因:落入地球的宇宙尘粒使地球的云层增厚,反射回宇宙的太阳辐射通量增大,从而使气候变得越来越冷。[12]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太阳辐射是地球的根本驱动力,太阳活动对地球温度的影响远远大于人类活动。在太阳黑子活动最弱的1640年—1710年,正是小冰河期里最寒冷的时期(即蒙德极小期)。50年前,科学家们认为,太阳系是稳定的,太阳是地球热量巨大的、不变的来源。但是,最近几年,科学家们对冰芯的同位素变化、树木年轮以及海底沉积物的研究都已经证实,在1 500年的气候循环之间,地球气候和太阳活动的小波动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北极冰盖面积持续缩小,可能是地球在向下一个冰期过渡所产生的自然现象。科学研究发现,史上因太阳活动规律性变化而导致的4次冰期,其间的每一次过渡,都存在升温现象。
二氧化碳的变化是否能说明我们已经知道的地球发生过的气候变化,包括罗马暖期、欧洲中世纪冷期、中世纪暖期以及小冰河期?全球气温与太阳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可能比与二氧化碳之间的相关性要大。在过去的2 000年里,最温暖的时期是罗马帝国时期和中世纪,尽管当时的二氧化碳水平比较低,但是当时的气温比现在还要高。中世纪暖期甚至比今天更为温暖,而这显然不能归因为矿物燃料的消耗。温室效应理论似乎也不能解释最近的气温变化,当前的气候变暖大多数发生在1940年以前。之后,虽然空气中有人类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但地球温度却在下降,直到1975年还是如此。现在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还在大幅度地增加,但整个地球的平均气温仅仅出现微小的上升。显然,这些事实和温室效应理论是背道而驰的。在全球变暖的过程中,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或许只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
贝纳尔也是持气候变化由自然原因所致的观点的人之一。他认为,地球目前正处于一个较温暖的阶段,气候变化的真正原因在于太阳黑子——它控制了地球上的天气变化,而非二氧化碳的排放。他指出,二氧化碳只占整个大气的0.03%,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仅占全球二氧化碳释放量的1.2%,其余都是由自然界产生的;而且,人类活动制造的二氧化碳,绝大部分来自热带的火耕地区,并非欧美先进的工业国家。[13]贝纳尔也提醒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即使气候变化是人为的,是否有可能与人类的其他活动而非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更为密切?人类的其他活动包括土地使用的变化、过度放牧、森林砍伐等。
质疑者认为,相对于自然界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言,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是微不足道的,把可能的气候变暖归咎于人类活动是武断的。如果全球变暖(或者全球变冷)仅仅是一种永不停歇的、周期性的自然现象,与人类活动无关,且并不像公众害怕的那样危险,那么是否需要大幅规范人类活动以应对气候变化就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四、人类活动总是消极的吗?
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有两种:自然的和人为的。气候可能变暖,也可能变冷。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也有产生变暖与变冷两种结果的可能性,于是可能有以下四种结果:A自然地变暖,B自然地变冷,C人为地变暖,D人为地变冷,如表1所示。

表1 气候变化的各种结果
气候变化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出现四种结果:AC、BD 和 AD、BC。
AC组合表示自然因素导致气候变暖,人为因素也使气候变暖,人类活动加剧了气候变暖;BD组合表示自然因素导致气候变冷,人为因素也使气候变冷,人类活动加剧了气候变冷。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活动“恶化”了气候的自然变化趋势,因而有可能需要受到控制。但问题在于,人为的因素究竟占多大比例?如果所占比例甚微,则可忽略。如果自然因素所占比重为99%,而人为因素所占比重不到1%,那么,控制人类活动的意义就不大。只有当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都使气候变暖且人为因素所占比重较大时,控制人类活动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是相反的,人类活动恰好“中和”、“缓和”或“平衡”了气候的变化,因而是积极的。在AD和BC组合中,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正好相反。AD表示自然因素导致气候变暖,而人为因素却使气候变冷;BC表示自然因素导致气候变冷,而人为因素却使气候变暖。在这两种组合中,人类活动都“减缓”了气候变化,因而是积极的,是值得鼓励的。
如果自然因素一直在导致气候变冷,那么中国人几千来种植水稻所产生的甲烷和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反而都是有益的,推迟了新一次小冰河期的到来,可谓在无意中“拯救”了人类!
通过以上分析,只有当自然的气候也在变暖,并且人为因素所占比重较大时,当前我们所担忧的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暖,才是理性的。因此,《公约》仅仅关注人为因素——“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气候变化”——明显是不合理的。
当然,如果自然的气候确实是平衡的或稳定的,即自然因素既不使气候变暖也不使气候变冷,那么,就只有人为因素会“扰乱”自然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像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那样,仅仅通过控制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活动就可以减缓气候变暖。但是,正如上一节所分析的,自然的气候并不是稳定的或平衡的,如果自然因素使气候变冷从而导致世界陷入灾害性的冰期,那么人为因素所导致的变暖就抵消了变冷趋势而使人类因祸得福。因此,只有将自然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进行对比研究,才能得出具有实质意义的结论。
五、气候变暖一定是坏事吗?
即使气候变暖是无需质疑的事实,并且人类活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也被证实是引发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我们依然可以继续追问:气候变暖就一定是坏事吗?
道家主张“祸福相依”,凡事都是付出成本与获得收益并存的。气候变暖会带来损失,但也会带来收益,然而,IPCC报告和其他大部分气候变化报告却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损失,对全球变暖,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所带来的收益几乎只字不提。如果气候变化的收益远远超过损失,那么气候变化或许会是一件好事。
历史事实、科学研究和人们的直觉都证明,寒冷比温暖更可怕。
首先,从气候与人类文明的历史来看,变暖比变冷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兴盛。人类文明正源于全新世的气候变暖,“全新世的全球变暖为先进文明铺平了道路。”[14]在古罗马、中国以及中世纪的欧洲历史中,在1 500年的气候循环中,最后两次变暖阶段,对人类来说都是繁荣时期。罗马帝国和中国都在2 000年前的罗马暖期处于繁荣时期。在人类历史上,像中世纪那样的暖期是一片繁荣的场景,而后来的小冰河期的特征则是饥荒、瘟疫与社会混乱。程明道通过对两千余年中国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关系机理的研究发现,“一方面,气候变化(降温趋势)可能引发朝代更迭、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有破坏力的外族入侵和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民众起义等。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升温趋势)可推动社会繁荣。”[15]虽然不能据此得出气候决定论,但在气候变暖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联系。至少在农业生产中,“历史上在温暖的年份,农业一年可种植两季,单位面积产量获得很大的提高。”[16]
其次,从生物学来看,即使气候变暖会带来许多灾害,但气候变冷所带来的灾害可能更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早已使全球植物大幅增加,包括许多环保主义者所关心与珍视的热带森林。温暖的气候不仅适宜植物生长,可能也更适宜人类生存——有研究表明,在欧洲大多数国家,死于冬季低温症的老人,远远多于死于或者可能死于夏季脱水的老人。以英国为例,在2003年热浪之后,卫生署一项使用了哈德利中心气候模型的研究表明,到21世纪50年代,预计每年与炎热有关的死亡会增加2 000例,而与寒冷有关的死亡则会减少 20 000 例。[17]
最后,从人们的自然喜好与直觉来看,每年都有许多人自愿重新选择居住在气候适宜的南方温暖地区。即使是那些担忧世界变暖的人们,也喜欢去热带海滨度假。例如,马尔代夫、泰国的普吉岛、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中国的三亚、越南的美奈、马来西亚的沙巴等度假胜地都位于热带地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3年9月于莫斯科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开幕式上曾说过:“如果全球温度升高2至3度并不可怕,甚至可能是件好事,我们可以省下一些花在毛皮大衣上的钱。”[18]
小幅度的气候变暖确实有可能给一部分地区带来益处。例如,有人估计,全球1/4尚未开采的石油,埋藏在北极的冰盖之下,气候变暖以后,这些石油会更易于开采;俄罗斯北部拥有大面积的冻原,目前人们因寒冷而无法居住,也许气候变暖以后人们能够在那里生活。虽然马尔代夫等低海拔地区可能因气候变暖而被淹没,但面积更大的格陵兰岛等地区却可能适宜人类居住。可以想象,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加拿大北部、中国的青藏高原等世界上寒冷的地区或许因为气候变暖而成为适合农作物生长的良田。从整个地球来看,由于地球上寒冷地区的陆地面积远远大于热带地区,因此,气候变暖的收益或许远远大于损失。但问题在于,受损者和受益者不是同一群人,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如果气候变暖的收益与损失并存,那么气候变化就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全球分配正义问题。[19]
或许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气候变化本身,而是人类设计与运营的社会制度阻碍了人类对自然气候变化的适应,剥夺了人类在变化的气候中过上更好生活的权利与机会。在没有国家与国界阻止人类自由迁徙的时代,远古人类无需护照就可以自由地离开因气候变化而环境恶化的非洲大草原,人类因此寻找到更广阔的适宜居住的地区。但是,当前的国际政治制度既阻止了利益的全球共享,也阻止了损害的全球分担。
六、是否一切负面问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
2012年10月底,飓风“桑迪”登陆美国并袭击了包括纽约在内的东部地区,导致70余人死亡。然而,飓风还没有过去,许多气象学家便找到了一贯的“元凶”——全球变暖。[20]缓慢发生的气候变化何以如此迅速地产生影响?
在当前全球变暖的警示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把所有负面的气象事件,甚至农业、生态和人类的健康问题都归因于全球变暖,并且将它们视作有必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证据。实际上,很多事件与气候变化可能毫无关系,有些事件完全是局部性问题,或者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与全球气候变化趋势没有必然联系。
比利时神学家弗朗索瓦·浩达在谈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时指出:“太平洋上的好几个岛屿的人民正迁往新西兰,岛上人口开始下降。”[21]可是,他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人口迁移是受“气候变化逼迫”,而不是因为岛上工作机会减少、社会环境变化等其他原因呢?我们是否能将中国数百万农民工从寒冷的北方地区到炎热的南方地区工作归因为气候变化呢?①笔者曾在课堂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你更喜欢寒冷的北方,还是温暖的南方;更愿意去三亚,还是去哈尔滨?结果来自北方的同学强烈地表达了对寒冷北方家乡的热爱。这个小调查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类具有很强的气候适应性。或许只需10—20年时间就可以让一个人喜欢并适应截然不同的气候环境。“在1900—2008年全球十大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中,中国就有三次:1909年的传染病、1928 年的旱灾、1959 年的水灾。”[22]但是,这些灾害与当前的全球变暖有关系吗?
对于许多报告中提及的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我们似乎都可以对这些不利影响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提出质疑。例如,在《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提到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各地区的影响,[23]但这些“影响”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
在华北地区,气候变化“加剧”了水资源紧张态势,“引起”浅层地下水位不断下降。但是,华北地区的地下水位下降是否与浪费性的农业灌溉、北京等大城市的过度扩张等关系更为密切?即使气候条件变得更好,该地区原有的淡水储量恐怕也早已不能满足大幅增加的城市人口的用水需求。当前的人口比古代增加了多少倍?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比古代增加了多少用水量?被水泥覆盖的路面使多少降水无法渗入地下?
在华东地区,气候变暖常伴随热浪发生频率及强度的增加,“导致”人体心血管、脑血管及呼吸系统等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增加。然而,气候变暖对中国其他地区居民的健康就没有影响吗?这些健康问题是否与当前的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以及人们正在改变的生活方式等因素关系更大?
在华中地区,气候变化“引起”该地区洪涝灾害加剧,“导致”湿地面积不断减小。然而,洪涝灾害加剧与湿地面积减小似乎是矛盾的——洪涝灾害加剧意味着更多的降水量,更多的降水量怎么会导致湿地面积减小?湿地面积减小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水土流失加速湖泊淤积、房地产开发①参见武汉沙湖被房地产围剿的例子。武汉沙湖被房地产开发蚕食 湖景蜕变湖景房[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3/29/c_122903278.htm.与围湖造田。同时,洪涝灾害加剧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缺乏更多、更坚固的堤坝和更有效的白蚁防治技术。
在华南地区,气候变化“导致”登陆华南的热带气旋数量减少、强度增大、登陆时间偏早、移动路径变复杂。按照这种逻辑,或许相反的现象——热带气旋数量增加、强度减小、登陆时间推迟——也可归因于气候变化。热带气旋对发达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越来越大,或许主要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迁移到更具有吸引力的沿海地区,尤其是那些易受风暴袭击的海滩地区。在发展中国家,通讯不发达、建筑物脆弱、交通设施匮乏等因素严重地制约了沿海地区的热带气旋预警工作。
在西南地区,气候变化“引起”干旱、洪涝灾害频次增多、程度加重,山地灾害呈现出点多、面广、规模大、成灾快、爆发频率高、延续时间长等特点,气候变化“加剧”了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退化、岩溶地区石漠化。然而,西南地区的山地灾害是否与滥采矿山、植被破坏、贫困、应急管理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关系更为密切?人们为什么要居住在这些生态脆弱地区?另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可能与非法捕猎、野生动物保护不力等关系更大。②电影《可可西里》揭示了盗猎是藏羚羊种群数量减少的最直接原因。
在西北地区,气候变化对西北地区的水资源造成严重“影响”,冰川退缩,地下水资源总体呈减少趋势,一些地区土地沙漠化问题突出。然而,该地区的干旱、土地沙漠化可能与过度放牧、草原生态平衡被破坏等关系更大。“文明人跨越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24]
继续分析人们常常见到的气候变化对农业、公共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第一,对农业的影响。当提到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时,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结论:气候变化导致病虫害种类和世代增加、危害范围扩大、经济损失加重;气候变化造成人们对化肥、农药等的投入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增大;气候变化导致干旱,造成农作物减产。实际上,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是利弊共存的。例如,北方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会由于气候变暖而有所扩展,在加拿大和俄罗斯平原北部,气候将变得更加温暖,这样便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另外,农作物也能够适应气候的变化,农民需要根据气候变化种植适宜的农作物。相对于气候变化,田间管理和农业科技对世界粮食产量的意义更大。现代科学可以提高热带地区农业的技术水平,现代交通也能从世界其他地区运输更多的粮食到印度、尼日利亚等缺粮地区。因此,“造成的任何饥荒,都将是人类的过错,而不是气候是过错。”[25]从历史上看,人类的粮食产量在全球变暖期间都是持续上升的。21世纪的饥荒不能归咎于气候,而只能归咎于“政府失败”。1984年—1985年,埃塞俄比亚遭遇粮食歉收后,该国虽然收到了西方国家捐赠的大量粮食,但是政府将其中的大部分供应给军队,最终导致大面积的饥荒。因此,在研究饥荒时,不能仅仅研究气候变化因素,还要对比政治、经济、军事等人为因素。如果许多国家都同时经历了同样的极端天气,只有个别国家出现了大规模饥荒,那就说明其他因素可能更为关键。
第二,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我们常常听到热浪导致许多人死亡的报道,气候变化确实会增加各类疾病的患病风险。然而,我们既需要知道每年“热死”了多少人,也需要知道每年与寒冷相关的疾病减少了多少。结果可能是极寒比酷热杀死的人要多得多。全球变暖的提倡者提供了一个相当简单的理论,即温度升高会引起更多的极端天气事件,这些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加人类的死亡率。但是,总体上来说,严寒比热浪更易致人死亡。从1979年到1997年,美国死于极端严寒天气的人数比死于热浪的人数多两倍。由于空调的普及,热浪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小。导致现代人死亡的很大原因是心血管问题,寒冷天气对于那些患有心脏疾病的人来说更加危险,寒冷还会增加呼吸系统疾病。研究发现,每年与寒冷有关的死亡人数几乎比每年与炎热有关的死亡人数多10倍。[26]2003年夏天席卷欧洲的热浪导致法国数千位老人因酷热天气和脱水而死亡,但为何在气候相似的奥地利、德国或瑞士等国却没有发生这么多的悲剧?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主要原因并非气候变化,而在于法国没有类似于奥地利、德国或瑞士等国那样完善的社区护理体系。[27]如果年轻人都去度假了,留下没人照顾的老人在家,那么无论是热浪还是严寒,对这些老人的威胁都是一样严重——热浪对空调房里的人或海滩上的人而言威胁不大。
2001年的IPCC报告重点关注了变暖所导致的疟疾发病率的预估上升。实际上,疟疾的蔓延或许与气温毫无关系。直到17世纪后期(即使在小冰河期),疟疾一直是欧洲的一种地方流行病,并且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疟疾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世界上第一种大型传染病——黑死病——爆发于中世纪冷期,而不是中世纪暖期。在小冰河期,阴雨绵绵,人们居住得拥挤不堪,衣物潮湿,卫生条件恶劣,再加上营养不良,燃料缺乏,最终导致疾病滋生。至于通过蚊子传播的疾病,例如疟疾和黄热病,应该由窗纱和杀虫剂来应对,而不是依靠寒冷的天气。然而,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使用滴滴涕运动所制造的普遍恐慌,正是发展中国家每年约200万名儿童死于疟疾的主要原因。[28]
第三,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一些物种的退化甚至灭绝也常常与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因为气候变化会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我们仍需追问:在导致物种退化与灭绝的原因中,有多少是自然因素,多少是人为因素?如果其他面临相同气候变化的国家没有此类问题,可能就需要另找原因。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可能是人为因素,而不是气候因素。[29]致使北极熊、鲨鱼等物种退化的原因或许不是二氧化碳排放,而是人类的捕杀。人类在百万年的进化历史中,捕猎任何能够捕猎的物种,如果某一物种灭绝了,人们会继续捕猎其他的物种。近代以来,农耕和城市开发侵占了大量动物的栖息地,使其无处藏身。当然,人类也会有意识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例如,如果没有人类的刻意保护,像大熊猫这样的物种可能早已灭绝。
或许许多物种比人类更能适应突然的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气候变化在1 500年的周期中是经常发生的。世界上的物种,在过去的100万年中,已至少经历了600次气候环境暖期和冷期的交替。全球变暖的主要效应将增加物种的多样性,因为大部分植物、动物都可以扩大其生存范围。有些生物学家声称,如果全球气温进一步上升0.8℃,将摧毁数千个物种。然而,发生在8 000—5 000年前的气候变暖,当时地球的气温大大超过了全新世期间气候最适宜期的气温,但并没有已知的物种因气温升高而灭绝。
如果气候变化并非一切负面事件的“元凶”,那么,为什么许多人总是直觉地将这些负面事件归咎于气候变化?难道这其中存在不可告人的秘密?
七、气候寻租
“小冰河期是真实发生的。它们也是遍布全球范围的。20世纪不是气候最温暖的。为什么最近的媒体却歇斯底里地认为20世纪是最近1 000年里气候最暖的呢?”[30]科学家、政治家和其他学者在还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时,就迫不及待地将各类负面事件归咎于气候变化,这难免会引起人们的猜疑:或许这样做对他们更有好处。好处是什么呢?
对于科学家而言,由于当代科学研究已经不再是古典的个人兴趣式的探索,而成为一种体制内的社会建制。①社会建制是指为了满足某些基本的社会需要而形成的相关社会活动的组织系统。在建制化的科学研究时代,科学家从其他社会角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角色,集合为有形的或无形的科学家共同体。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应当是非功利的——目的在于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职业”科学家却将从事科学研究当成谋生、获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手段。当目的变成了手段,科学家所追求的就不再是科学真理,而是经济利益。由于科学家共同体的研究非常依赖来自政府或企业的资助——气象学家也不例外,因此,科学研究就可能变成“谁出钱,就听谁的”。如果这就是科学真相,那么,科学还值得信赖吗?如果科学家可以为了经济利益而说谎,那么他们的行为也是一种腐败或寻租行为——科研经费就是租金。
气象学家也可能为了获得政府和企业的科研投入,或成为媒体与公众关注的焦点而夸大事实甚至说谎,以获取“气候租金”。无论是支持气候变暖还是反对气候变暖,似乎都能获得租金:支持气候变暖的人认为反对者从化石能源企业等利益集团获得了资金,而反对气候变暖的人则认为对方通过宣传“气候变化威胁论”获得了巨额的科研经费等利益。媒体也成了利益集团之一,它们通过无休止的炒作和耸人听闻的新闻吸引读者。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暖”成为竞争研究资金的有力武器,因此,一些气象学家的危言耸听让我们觉得半信半疑。
经济学家总是在股市、楼市等经济现象的预测上争吵不休,但气象经济学家却出奇地和谐,扮演着全球变暖宣传机的角色,难道他们也是气候变化研究的受益者?美国企业研究所是智囊团之一,该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接受了来自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大量资助。它拥有很高的公共地位,能够挑战人类行为引起气候变化等舆论意见。尽管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已经判断出人类的生存空间有90%的可能性会陷入困境,但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机构以及从这些机构获得金钱的“科学家们”,却建议我们依赖那不到10%的“无可避免的不确定因素”,继续原有的高排放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收取利益集团的金钱,散布混淆全球变暖问题的言论,这类似一种职业公关。就像一些不讲道德的律师,利用专业知识帮助委托人违法,或不讲原则的会计师帮助他们的客户逃税。再如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美国烟草研究所和烟草业研究委员会,都不遗余力地对任何质疑吸烟影响健康的研究提供资金并大力宣传。[31]
政治家们也能从气候变化问题中受益。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与好莱坞明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一起驾驶昂贵的混合动力汽车前往他们的私人飞机停机场,乘坐私人喷气式飞机宣传环保主义和气候变暖的威胁,这一行为本身就要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是导致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的奢侈性消费。政治家们发现,宣传环保主义和气候变暖的威胁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收益:阿尔·戈尔与IPCC的科学家共同获得了2007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是,阿尔·戈尔竟然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公然撒谎,引用子虚乌有的专家之言,耸人听闻地预测北极最快在2014年将不再有海冰。当然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还因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邮件被窃取而引发了“气候门”事件,更是令人震惊不已。难怪有人直指IPCC是一些国家、组织和个人牟取利益的工具,气候变暖论本质上是“世纪大谎言”,其背后隐藏着国际发展权之争,夹带着牟取碳交易利益的私货。
IPCC还提出了海平面上升的问题:1990年—2100年,海平面将上升0.09—0.88米。前海平面委员会主席,瑞典地质学家尼尔斯·阿克苏·莫纳则认为这完全是伪造的科学观测数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海平面几乎没有变化,并且在21世纪根本没有办法科学地预测海平面的上升。他的研究甚至认为最近马尔代夫的海平面在下降。[32]IPCC为什么要“伪造”数据?塞文斯马克和考尔德指出:IPCC和世界各国政府坚持温室气体排放正在加剧全球变暖的一致立场,其原因是政治的而非科学的……采用这种假设的人是想制造一种恐慌气氛以加强国家对企业和个人的监管权力,同时阻止第三世界国家享受矿物燃料带来的发展,而在西方这些发展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改善了个人的健康状况。[33]
全球有多少人在从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研究?①笔者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全球有多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研究机构?每年有多少人参加各类气候大会?他们的经费从何而来?在这样一个科学建制化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科研伦理要求科学家们抛开利益、追求真理、造福人类,但在现代建制科学中,要真正遵守这些基本要求却很难。作为气候科学的门外汉,至少我们应当保留对大多数人“公认”的气候事实提出质疑的权利——真理也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八、气候罪
气候变化问题也受到了神学家们的特别关注。神学家们发现,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危机与基督教的许多教义出奇地一致。首先,全球变暖会使海平面上升,淹没地球上的许多地区和物种。基督教神学家认为这与《圣经》中关于诺亚方舟的描述是一致的,或者就是预言的证实。几个世纪以来,深植于人们灵魂之中的某些东西让人们很容易就接受了那些灾难性的警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充满了内疚感。基督徒习惯于将极端天气事件解释为神对人类的惩罚——旧宗教很快就与气候变化的新宗教结成了联盟。其次,基督教认为每个人都有“原罪”,这是人类自身无法摆脱的罪过,只能寄希望于上帝的救赎。在全球变暖的时代,由于没有人能将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至零,因此,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因排放温室气体而犯了“气候罪”。如神学家约翰·霍华德·约德所批判的:现代人企图“掌控历史”,即避开神圣造物主对地球和人类历史的统治权,这反映了一种狂妄自大的意图。[34]于是,气候变化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宗教问题,教徒们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他们坚定地相信人类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是有罪的。
即使是一些非宗教的环境理论,也具有神学的倾向或特征。例如,生态中心主义具有泛神论的倾向,它取消人的主体性,捣毁人的创造性,将一切罪恶归因于人类。生态原教旨主义,特别是全球变暖专制主义为人们提供的是替代传统宗教信仰的宗教抚慰和价值观。[35]一些环境虚无主义者也有着宗教的背景。例如,在美国政府中,有超过200名共和党议员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所属的教派认为地球的未来无关紧要,因为地球没有未来。他们生活在“末世”,“末世”之后上帝之子就会回归。环境破坏应受到欢迎,甚至应当加速,因为这是天启即将到来的标志,到那时,他们就会进入天堂,而罪人将会面对永恒的地狱之火。[36]
在这个全球变暖的时代,所有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利己主义者还是利他主义者,都因排放温室气体而变得有罪了。其实,神学家给人类“定罪”的传统从中世纪就开始了。他们害怕人类揭开宗教的面纱,害怕科学占据宗教的领地。即使最为糟糕的气候变暖发生了,科学也比宗教更有可能拯救人类。“难道因为担忧全球变暖,我们就得放弃在20世纪已经取得的先进科学技术吗?而这些科学技术曾使人类的预期寿命整整延长了30年!”[37]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全球真的变暖,人类也会在21世纪享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长的寿命——除非对气候变暖的恐惧使人类社会闲置或者放弃通过各种丰富的、廉价的能源以及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带来的经济繁荣。
九、结 语
人类可以在零下40℃至40℃的温度范围内正常居住和生活——例如北极圈内的挪威和赤道地区的新加坡都能实现经济繁荣,那么为什么地球平均气温小幅上升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科学家提供了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地球的升温幅度不是全球同步的,而是相反的。平均气温升高0.75℃可能引起局部地区升温2℃—3℃——如西伯利亚地区。另一种解释是平均气温上升会导致严重的气候灾难——如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换言之,气温的上升会扰乱自然气候系统,破坏自然界的运行机制,并使其超过人类的可控范围。
尽管科学家在尽力提供各种解释,但并非所有人都对他们的解释确信无疑,有些人还对IPCC的结论提出了各种怀疑。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经验和感受的作用和影响不像疾病和战争那样直接和强烈,而且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和专业性很强的科学问题,因而,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产生怀疑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在IPCC发布其研究报告之后,就一直存在质疑的声音。有媒体声称,该报告关于喜马拉雅山冰川面积萎缩、气候变化对亚马逊雨林的威胁、非洲农作物减产等结论涉及引用文献不严谨、缺乏科学研究支撑等问题。[38]
虽然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性的质疑,但无论气候变化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我们都必须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在国家层面,由于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以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为由拒绝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并且不受国际气候政治与经济政策的影响。
如果气候变化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且气温大幅升高的风险被证明是比较低的,但人们已经削减了排放,那么人类还是能够受益。因为无论气候变化是否是伪命题,资源与环境危机早已被证实,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带来的绿色转型,正是一次革命性的机遇,是另一种“无意识的后果”:以应对气候变化开始,以绿色转型结束。我们将拥有一个能效更高、空气更清洁、生物种类更多样的世界。如果气候变化的结论是科学的,但人类拒绝采取行动,那么,当人们认识到犯了错误的时候,还有机会改正吗?人类可能已经继续大量排放了30年或50年,温室气体存量可能已达到足以导致危险的气候变化的高风险水平。那时再努力脱离这种处境,代价将极其高昂,或者已不可能。
[1] [法]帕斯卡尔·阿科特.气候的历史——从宇宙大爆炸到气候灾难[M].李孝琴,译.北京:学林出版社,2011:246.
[2][3][8] 李廉水,等.应对气候变化研究进展报告[P].北京:气象出版社,2012:18,59,59.
[4] Allegre C,Armstrong J.S,Breslow J.No need to panic about warming [EB/OL]. http://online. wsj. 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4301404577171531838421366.html.
[5][25][32][37][美]弗雷德·辛格,等.全球变暖:毫无来由的恐慌[M].林立鹏,王臣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57 -58,33 -34,67,19.
[6][11][14][27][德]贝林格.气候的文明史[M].史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19 -220,242,45,45.
[7] James E.Hansen.Earth's Energy Imbalance:Confirmation and Implications[J].Science,2005,(308).
[9][13][德]弗里德黑姆·施瓦茨.气候经济学[M].郭晗聃,译.北京:气象出版社,2012:29 -30,29 -30.
[10] Mutsuyoshi Nishimura,Akinobu Yasumoto.碳预算为基础的全球排放贸易计划如何能拯救地球并使全球经济保持繁荣发展[A].潘家华,主编.碳预算: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构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99.
[12]王绍武,黄建斌.宇宙尘粒是气候变化的原因[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2,(4).
[15][16]程明道.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32.
[17] W.Keatinge.Seasonal mortality among elderly people with unrestricted home heating[J].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86,(293).
[18]何一鸣.俄罗斯气候政策转型的驱动因素及国际影响分析[J].东北亚论坛,2011,(3).
[19]史军,卢愿清,郝晓雅.代际气候正义的陷阱[J].阅江学刊,2013,(3).
[20]数名气候学家分析称全球变暖可能壮大飓风[EB/OL].http://discovery.163.com/12/1101/10/8F7FI4MV000125LI.html.
[21][比]弗朗索瓦·浩达.作物能源与资本主义危机[M].黄钰书,黄君艳,安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8.
[22]胡鞍钢,管清友.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61.
[23]《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P].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4][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表土与人类文明[M].庄峻,等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5.
[26] W.R.Keatinge.Heat Related Mortality in Warm and Cold Regions of Europe:Observational Study[J].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0,(321).
[28] P.Reiter.Malaria in England in the Little Ice Age[J].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2000,(1).
[29] I.M.Goklany.CO2and biodiversity:Does the former affect the latter?[J].CO2Science,2002,(5).
[30] Willie Soon,Sallie Baliunas.Recent Warming Is Not Historically Unique[J].Environment News,2001,(1).
[31][加]詹姆斯·霍根,理查德·里都摩尔.利益集团的气候“圣战”[M].展地,译.北京: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21.
[33][英]诺斯科特.气候伦理[M].左高山,唐艳枚,龙运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78.
[34] Michael Northcott.An Angel Directs the Storm:Apocalyptic Religion and American Empire[M].London:I.B.Tauris,2004:166.
[35][英]奈杰尔·劳森.呼唤理性:全球变暖的冷思考[M].戴黍,李振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19.
[36][澳]希尔曼,史密斯.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M].武锡申,李楠,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5.
[38]王子忠.气候变化:政治绑架科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