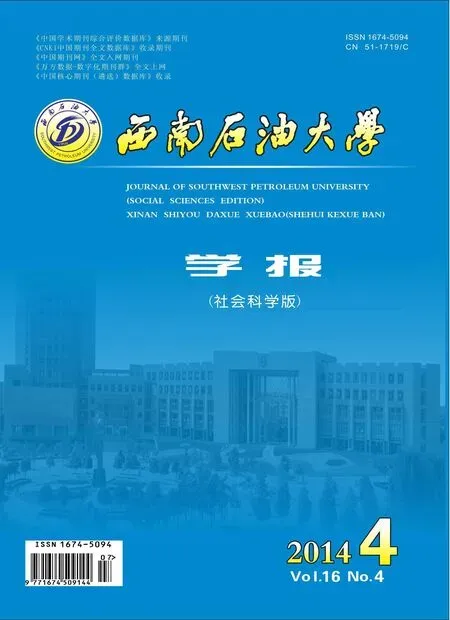论AID知情同意书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法律效力*
陈传荣,杨 芳
(安徽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
论AID知情同意书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法律效力*
陈传荣,杨 芳
(安徽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
AID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不育症夫妇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AID子女亲子关系认定尤其突出。明确AID子女与相关当事人的亲子关系,对保护AID子女利益至为重要。根据各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裁判,知情同意原则在认定AID子女亲子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由于法律缺失,仅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作为AID子女亲子关系的认定依据是不够的。建议以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指导思想,在未来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和提升知情同意书在AID子女亲子关系中的地位,将AID知情同意书作为认定生母之夫为AID子女法律父亲的事实依据。
AID技术;知情同意书;亲子关系;遗传父亲;法律父亲
陈传荣,杨 芳.论AID知情同意书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法律效力[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4):57-61.
1 问题的提出
生育子女,传宗接代,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源泉。不育症严重影响不育症夫妇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和谐,治疗和解决不育症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辅助生殖技术①辅助生殖技术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的简称,指采用医疗辅助手段使不育夫妇妊娠的技术,包括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AI)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及其衍生技术两大类。试管婴儿就是使用该技术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方法生育的婴儿。世界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被誉为继心脏移植成功后20世纪医学界的又一奇迹,激发了全球许多国家研究这一高新技术的热潮。的应用,使生育子女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通过性交受胎的自然繁衍方式。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Using Semen by Donor,以下简称AID)②AID,供精人工授精,人工授精根据精源不同,分为夫精人工授精(AIH)和供精人工授精(AID)2种。前者用其丈夫精液进行人工授精,后者采用精子库的冷冻精液。是丈夫在无生育能力或完全没有精子的情况下,用辅助生殖技术将丈夫以外的第三人提供的精子注入妻子体内,使妻子怀孕分娩的非自然生殖技术。AID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不育症家庭带来福音,但其所涉及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1],表现在亲子关系问题上,主要是AID技术造成遗传父亲和法律父亲分离,因此,从法律上厘清AID子女亲子关系,对AID技术的健康应用和AID子女权益的保护至为重要,但我国立法并未跟上医疗实践的步伐。
我国长期缺乏关于AID子女亲子关系的法律规定。自1991年河北省王某与杨某争夺AID子女抚养权案发生后,司法界意识到厘清AID子女法律关系的重要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从保护子女最佳利益的角度出发,发布《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该复函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将AID子女视为婚生子女,确定生母之夫为AID子女的法律父亲,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此后辅助生殖技术飞速发展,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复函的精神却迟迟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导致医疗实践中AID子女权益因受术夫妻反悔而得不到保障。当事人若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能走司法程序,既耗时费力,也浪费司法成本。2006年南京再度发生AID子女遗产继承风波就是最好的例证。本案中,丈夫在遗嘱中以子女为AID受孕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为由翻悔,导致遗腹子继承权被剥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时,依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复函的相关规定,以及夫妻双方在知情同意书中的约定,认为实施人工授精是两人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的一致意见,丈夫对实施AID技术具有积极的意思表示,不得再提起婚生否认之诉。因此,丈夫在遗嘱中否认其与AID子女亲子关系内容无效,AID子女依法享有相应继承权[2]。本案中,当事人虽然消耗了时间、精力和财力,欣慰的是,AID子女权益毕竟得到法院支持,而对那些缺乏权利意识或没有勇气诉诸法院的AID子女命运则可能完全不同。
毫无疑问,知情同意书在AID子女亲子关系之争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如果没有AID知情同意书,法院无相应事实依据判定实施AID技术是夫妻双方一致意见,则最终只能依据丈夫生前遗嘱判决遗嘱生效,这显然不利于AID子女权益的保护。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未来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和提升知情同意书在AID子女亲子关系中的地位。
2 知情同意在辅助生殖医疗中的法律意义
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为不育症家庭带来了生育子女的希望,但其存在的潜在风险仍然不可忽视,如人工授精后妊娠以流产告终,出现妊娠和分娩并发症,第三人的精子携带有遗传病或传染性疾病,或实施辅助生殖可能会对后代产生严重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损害等情况。此时,医师应当尊重不育症夫妇的知情同意权,在充分告知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存在的利弊以及可能影响不育症夫妇做出选择的实质信息后,由不育症夫妇自主做出选择——同意或拒绝实施辅助生殖技术。
知情同意作为一项重要的伦理原则,根源于一个坚强的信念,即任何个体都有权依照其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自主决定怎样处理自己的事务[3]。
在临床医疗中,不育症夫妇受不育症困扰,无论是心理、医学知识还是社会地位,与医师相比,均处于弱势地位,世界各国之所以纷纷立法确立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实际是对患者弱势地位的矫正。不育症夫妇知情同意权的实现离不开医师告知义务的如实履行,医师履行告知义务的过程,实际是与不育症夫妇沟通、交流、理解与合作的过程,这有利于增进医师与不育症夫妇之间相互信任[4],减轻不育症夫妇心理压力,从而有利于辅助生殖技术顺利实施。而且不育症夫妇在医师充分告知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存在的潜在风险后,仍然坚持选择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因非医师过错而妊娠失败,不育症夫妇不得将责任归咎于医疗机构和医师,不育症夫妇与医师所签订的知情同意书可作为相应事实凭证。在辅助生殖医疗中遵循知情同意原则,体现的是医师与不育症夫妇之间相互尊重、信任、理解和合作,是对不育症夫妇自主权的尊重,是医患关系和谐的最佳境界。
为了保障不育症夫妇知情同意权的实现,2001年卫生部(即现在的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当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此后,2003年卫生部又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均强调知情同意书应当在不育症夫妇双方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签署。所以,在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前,医师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后,不育症夫妇仍然坚持选择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夫妇双方应当签署书面的知情同意书。
3 AID知情同意书的主要内容
3.1 知情同意权主体
毫无疑问,如果不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受术主体加以限制,单身女性、同性恋者可要求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正常夫妻也可要求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筛选胎儿性别,这些都将导致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在我国,依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技术规范》和《人类辅助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中的规定,辅助生殖的受术主体仅限于不育症夫妇,医疗机构和医师在实施AID技术前,应当认真检查不育症夫妇的身份证、结婚证和计划生育证,只有三证具备并符合实施AID适应症的夫妇才可以实施AID技术。此外,医疗机构和医师实施AID技术还应当严格遵循知情同意原则,由不育症夫妇双方共同签署知情同意书。所以,对于是否实施AID技术的知情同意权的主体亦仅限于不育症夫妇。
从法理学角度看,不育症夫妇作为知情同意权的主体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不育症夫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育症夫妇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自愿。知情同意是不育症夫妇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是否同意实施AID技术的决定,这是一项重要的意思表示,要求不育症夫妇双方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后果,故不育症夫妇双方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5]。
根据《民法通则》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相关规定,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不育症夫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生育目的的实现,必须有夫妻双方达成生育愿望的契合,所以,是否通过实施AID技术生育子女,应当由不育症夫妇双方共同决定,任何一方不得单独决定实施AID技术[6]。所以,不育症夫妇作出同意通过实施AID技术生育子女的决定,是不育症夫妇双方协商一致、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
3.2 知情同意书的主要内容和条款
因辅助生殖技术的知情同意书不仅涉及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还涉及辅助生育子女亲子关系的约定等问题,因此,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知情同意书予以监督和指导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卫生部在反复征求生殖医学、医学伦理、医学法律和卫生管理专家的意见,多次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后,制定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知情同意书参考样本,以使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至于违反公序良俗、显失公平和危及后代子女利益等。
虽然AID技术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影响妊娠的因素复杂难测,其存在的潜在风险仍然不可忽视。因此,在AID知情同意书中应当列明实施AID技术存在的风险以及可能影响不育症夫妇作出选择的实质信息,如受精后不一定能妊娠成功、通过AID技术生育的子女可能出现身体或智力缺陷、授精成功后妊娠可能以流产告终,可能会发生妊娠和分娩并发症,该技术不能绝对避免传染性传播疾病的危险等以及为降低这些风险所采取的措施,该机构实施AID技术稳定的成功率、每周期大致的总费用及进口、国产药物选择等其他可能影响不育症夫妇作出合理选择的实质性信息等。
AID技术的使用割断了两性结合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使传统的基于血缘关系作为认定亲子关系的方式受到置疑,造成AID子女的遗传父亲和法律父亲相分离,使得AID子女的法律地位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卫生部在制定AID知情同意书参考样本时,依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保护后代的原则”,明确不育症夫妇是AID子女的法律父母,AID子女应当与自然受孕分娩的后代享有同样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包括AID子女的被抚养权、继承权、受教育权和赡养父母的义务等,不育症夫妇对AID子女负有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7]。
4 AID知情同意书亲子关系条款的法律效力
因各国文化背景、宗教信仰、AID技术应用程度以及对AID子女认识程度不同,各国关于AID子女亲子关系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但落实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许多国家人工生殖子女亲子制度的基本指导思想。
美国早期判例均判决AID子女为非婚生子女,但1948年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关于斯坦德案件的判决对AID子女的法律地位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该法院站在道德的高度,从保护AID子女最佳利益的角度出发,判决斯坦德夫人的丈夫具有探视权,承认AID子女为婚生子女[8]。此后,美国经历过漫长的讨论、实践和研究,在1973年颁布的《统一亲子法》中规定:如果已婚妇女经使用第三人的精子通过人工授精怀孕,且经过丈夫同意,由有资格的医生实施手术,该子女即被视为其丈夫的婚生子女[9]。
1979年,以色列卫生部也发布规定,明确实施AID技术必须有夫妻双方的书面同意书,丈夫必须公开承诺对孩子负有法律责任[8]。
1983年,澳大利亚《家庭法修正案》规定,根据丈夫同意或按照法律规定而实施异质授精的,丈夫为AID子女的法律父亲[10]。
在瑞典,1985年《瑞典受精法》和修改的《瑞典亲子法》规定:妇女之人工授精若曾得其丈夫或永久同居者的同意,而子女之受孕和出生为该人工授精之可能结果时,则该子女视为婚生子女[10]。
于2009年完成修订的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规定,妻子经丈夫同意接受丈夫以外的第三人捐精实施人工生殖技术时,丈夫是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父亲。
法国的《亲子关系修正法案》第14条规定,夫于怀胎期间,因隔离之理由或依确实方法经医学上证明之理由,证实生育子女为不能时,得否认婚姻怀胎之子女,但无论子女属于夫或属于第三人,依夫之书面同意,以人工授精方法怀胎者,不问以任何方法为证明,均不许否认[11]。此条款实际是将AID子女视为婚生子女。
在丹麦,根据人工授精法案,在丈夫同意情况下出生的AID子女,具有婚生子女身份[8]。
关于AID子女的法律地位,我国一直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作为判决依据,至今尚未出台相关法律,这使得AID子女相关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但根据我国目前的司法裁判,我国已将AID知情同意书作为认定AID子女亲子关系的重要事实依据。将AID知情同意书作为认定AID子女亲子关系的事实依据,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依据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AID知情同意书是不育症夫妇自愿缔结,不损害他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得到国家承认的法理基础[12]。
其次,AID知情同意书涉及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医师可以作为第三人见证丈夫是在真实自愿的基础上作出同意妻子通过AID技术生育子女的决定,而并非妻子单方面决定实施AID技术。
最后,依据英美法提出的“禁反言原则”①禁反言一词来源于法语单词estoupe和英语单词stop(停止)。禁反言是人们在进行民事活动、民事诉讼行为时,应对自己以言词做出的各种表示负责,不得随意做出否定在先言词的言论或行为。一般而言,禁反言是指:禁止一方当事人否认法律已经做出判决的事项,或者禁止一方当事人通过言语(表述或沉默)或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做出与其之前所表述的(过去的或将来的)事实或主张的权利不一致的表示,尤其是当另一方当事人对之前的表示已经给予信赖并依此行事的时候。,丈夫在明知知情同意书中有关其作为AID子女法律父亲的相关约定,仍坚持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的行为引致其妻子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并实施AID技术的行为是可合理预见的,且的确导致其妻子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并实施AID技术,如果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可避免不公平结果产生,则该知情同意书上的所有条款具有法律拘束力,丈夫不得再提出相反主张[13]。即丈夫不得对AID子女婚生子女地位提出否认之诉,否则,不仅不利于保护AID子女利益,而且违反了民法中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14]。
综上所述,我国虽未同其他国家一样,直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AID子女的法律地位,但根据我国AID知情同意书中关于AID子女亲子关系的约定以及其在司法裁判中的广泛应用,可见我国亦是严格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将AID子女视为婚生子女,确定生母之夫为AID子女的法律父亲。因此,未来立法应遵循这一传统,进一步明确和提升知情同意书在确定AID子女亲子关系中的地位。
5 结 论
我国辅助生殖技术虽起步较晚,但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该技术的应用,对不孕不育症的治疗以及维护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具有一定作用,但是,我们应当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辅助生殖技术,在看到其带来的有利方面的同时,也应当正视其带来的伦理和法律问题,特别是防范受术夫妻翻悔危害未来孩子的利益,积极构建妥当的AID子女亲子关系制度。在当前关于AID子女身份认定法律缺失的情况下,建议以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指导思想,在未来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和提升知情同意书在确定AID子女亲子关系中的地位,将AID知情同意书作为认定生母之夫为AID子女法律父亲的事实依据。同时,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加快辅助生殖立法,以加强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使辅助生殖技术可以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1] 应锋,王建华,徐华伟. 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与原则[J]. 中国计划生育杂志,2002(3):191-192.
[2] 南京婚姻家庭律师网. 李梅、郭重阳诉郭士和、童秀英继承纠纷案[EB/OL]. (2008-11-06)[2014-3-11].http://www.njlh110.com/ShowArticle.shtml?ID=2008 116182438881380.htm.
[3] 杨芳,姜柏生. 死后人工生殖的民法问题研究[J]. 河北法学,2006,24(11):111-114.
[4] 杨芳,潘荣华. 病人知情同意权的法律分析[J]. 中国卫生法制,2001,9(3):28-32.
[5] 许莉,供精人工授精生育的若干法律问题[J].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4):31-36.
[6] 杨芳,姜柏生. 辅助生育权:基于夫妻身份的考量[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7):34-36.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知情同意书参考样式[EB/OL]. (2005-11-30)[2014-3-11]. www.moh.gov.cn/uploadfile/20051130171237791.doc.
[8] 刘成明. 论体内异质授精子女的身份确认[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6):113-118.
[9] 夏吟兰. 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18.
[10] 邢玉霞. 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中的热点法律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174.
[11] 冯建妹. 生殖技术的法律问题研究[M]//梁慧星. 民商法论丛:第8卷[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8.
[12] 李志强. 代孕生育的民法调整[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8(3):21-25.
[13] 刘根. 英国法中的诚信原则——关于禁反言若干问题的研究[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1):130-136.
[14] 张燕玲. 论人工生殖子女父母身份之认定[J]. 法学论坛,2005,20(5):66-75
On the Legal Effect of AID Informed Consent on Parentage Identification
CHEN Chuan-rong, YANG F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2, China)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AID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a donor) technology brings both a lot of benefit to the infertile couples and a series of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especially in parentage identification of AID-children. Identification of the parentage between the AID-children and the relevant parties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AID-children. According to legal provisions and judicial adjudica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arentage identification of AID-children. Due to legislative deficiency in China, the reply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serves as the only evidence for parentage identification of AID-children, which cannot serve as an ample evidence. The present paper recommends that the future legislation should further clarify and enhance the status of informed consent in parentage identification of AID-children under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respect for party autonomy, making it a factual ground that affirms the husband of natural mother as the legal father of AID-children.
AID technology; informed consent; parentage; biological father; legal father
10.11885/j.issn.1674-5094.20137531
1674-5094(2014)04-00057-61
DF552
A
编 辑:余少成
编辑部网址:http://pxsy.cbpt.cnki.net/WKC/
2014-04-01
陈传荣(1991-),女(汉族),安徽六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伦理与法律。
*通讯作者:杨芳(1971-),女(汉族),安徽宿州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涉医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