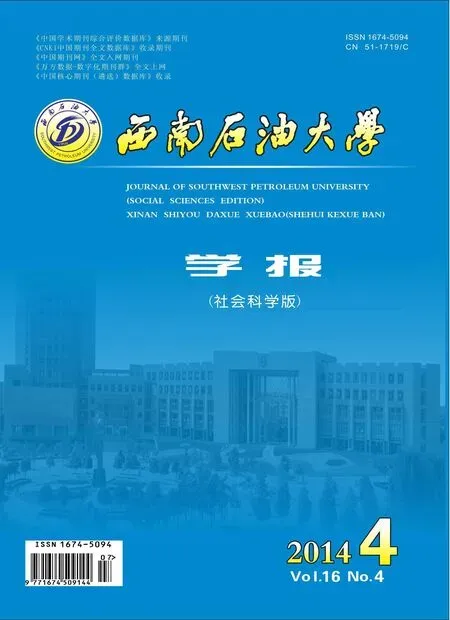论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
孙道锐
(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论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
孙道锐
(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我国的器官移植法规赋予了器官捐献人对其已作出的器官捐献意愿以撤销权,但若从民法理论上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界分,则应称此项权利为“撤回权”。器官捐献的撤回非是使器官捐献不生效力,乃是停止对器官捐献意愿的追求,该项权利的行使只能是捐献主体在其生前或器官植入受体之前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行使。赋予器官捐献人撤回权在于尊重其自我决定权及体现民法所蕴含的价值。器官捐献者行使撤回权后,在活体器官捐献中捐献人恶意撤回致使受体死亡或严重身体损害时需要赔偿损失。
器官捐献;活体器官捐献;遗体器官捐献;器官捐献撤销权;器官捐献撤回权
孙道锐.论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4):62-66.
引 言
我国《器官捐献条例》第8条赋予了器官捐献人对其已作出的器官捐献意愿以撤销权,在其他各器官捐献法规之中也皆将此项权利称之为撤销权。但若从民法理论上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界分,则称之为“撤回权”更属妥实。本文在赋予器官捐献人此项权利以“撤回权”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就器官捐献人对该项权利的行使以及权利行使的结果进行论述,希冀能够对我国的器官捐献立法、器官捐献人权利保障以及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进步有所裨益。
1 器官捐献人撤回权的法理基础
1.1 撤销权与撤回权的界分
要准确地将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界分,需要从源头上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梳理,佐以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方能无误地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区分。在罗马法上,撤销权与撤回权的行使多发生于债的领域,如债权人撤销权为大法学家保利(Paulius)所发明,亦称“废罢诉权(也称保利安之诉)”,即债权人为保全债务人的财产得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对其财产的处分行为。债权人行使废罢诉权须具备以下四项要件:一为有减少债务人现有财产之效果,二为有使债权人蒙受损害之效果,三为债务人于行为时有损害债权人权利之故意,四为第三人明知债务人之行为系出于损害债权人权利之故意[1]。撤回权多产生于要物契约之中,在罗马法上契约分为要物契约与诺成契约,要物契约的成立较诺成契约而言多一个交付标的物的要件,契约的成立须在合意和交付两个要件同时具备时方可成立,要物契约在实物交付前当事人可撤回其同意[2]711。可见,在罗马法之中已经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了区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于权利人意思表示的对象是否为已生效的法律行为,对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权利人行使撤销权以前已成立生效,撤销权的行使在于使已成立生效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归于消灭;而对于可撤回的法律行为,在行使撤回权以前则尚未生效,撤回权行使的目的在于阻止尚未生效的法律行为发挥效力。撤回权的行使是在于否定尚未生效之行为而使其不生效,撤销权的行使是通过否定生效行为而否定其法律效力,可撤销的行为是生效行为,未生效行为不存在撤销的问题[2]28。
近代以降,受罗马法影响的德国民法典,深谙此民法理论,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了严格区分。例如在《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20条、第123条分别规定了因意思表示的错误、误传和因欺诈、胁迫而生效的法律行为可予撤销。在第2253条至第2258条对被继承人订立的遗嘱可以通过订立新遗嘱、销毁或变更遗嘱证书、从官方保管处取回遗嘱的方式予以撤回。遗嘱是被继承人生前订立的处分其身后遗产的行为,遗嘱的生效需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方生效,在立遗嘱人尚生存期间,该遗嘱未正式生效,不发生撤销问题,而只能撤回。在我国现行的民法之中,也同样规定了众多可以撤销的对象,撤销权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一方面反应了可归入撤销权的制度可谓内容丰富,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在法律的制定中,对“撤销权”与“撤回权”不加区分地以撤销权代替[3]。例如在我国《继承法》第20条中规定了立遗嘱人有权撤销其所立的遗嘱。在法理上,立遗嘱人不能对其所立的遗嘱予以撤销,而是只能撤回,其撤回所订立的遗嘱,乃是使尚未生效的遗嘱不发生效力。
1.2 赋予器官捐献人撤回权的合理性
我国的器官捐献、移植法规无一例外地将器官捐献者的此项权利称之为“撤销权”,实属错误。器官捐献分为遗体器官捐献和活体器官捐献,因此器官捐献意思表示的生效须区别加以认定。遗体器官捐献的意思表示在捐献人死后方生效,在器官捐献人生前,任何机构或个人无权以任何理由摘取其活体器官,只有在其身后方可根据其生效的捐献意愿摘取其器官;活体器官捐献的生效为在器官摘取并植入受体体内成为其身体的一部分时方生效,在器官摘取前,捐献人享有撤回权自不必言,在器官摘取之后植入受体之前,捐献人对其器官享有返还请求权,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地要求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挽救他人,应尊重其私人自治,器官捐献人亦能撤回捐献。唯在器官植入受体体内成为其身体的一部分之后,捐献人对于其器官完成了现实的占有移转,该器官成为受体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为保护受体的生命健康,器官捐献人既不享有撤销权,也不享有撤回权。因此,器官捐献人在其生前或者所捐器官植入受体之前,对于其作出的器官捐献意愿只能撤回,不能撤销。器官捐献人行使撤回权,非是使器官捐献不生效力,乃是停止对器官捐献意愿的追求。若谓之此项权利以撤销权,则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实属不妥。赋予此项权利以撤回权之谓在其他国家已早有先例,例如,在《欧洲人权与生物医学公约》第5条第3款、第6条第5段规定了成年人或无同意能力之人对于其作出的器官捐献同意可随时自由撤回,赋予了器官捐献人任意撤回权[4]。在大陆法系中,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亦肯定了处分人身行为的可撤回性,自然人可随时撤回处分其身体之全部或一部分的行为,该处分行为的执行在处分人生前或死后进行,在所不论。
器官是维持人体机能正常活动,保持人体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器官不具有可再生性,显得弥足珍贵,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在损害其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捐献其器官以拯救他人。追求更高程度的幸福生活,享受身体完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当然,法律也不反对一个拥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为拯救正因器官衰竭而饱受折磨的灵魂而捐献其器官,对不违反法律的自我决定权的尊重是民法的应有之义,加之器官捐献遵循无偿捐献的原则,其器官捐献的意愿不能因其作出这样的意思表示而成为其必须履行的义务,相反,器官捐献是自然人所享有的权利,肯定器官捐献人器官捐献的权利,并且赋予其任意撤回捐献的自由,使器官捐献人能够处于一个无因捐献而给其压力的环境之中,不至于为其所作出的器官捐献意愿所困,我们相信,在法律祥和的阳光下,器官捐献的关爱之树必成长得参天茂盛,结满爱心的果实。因此赋予器官捐献人以撤回权颇值肯定。
2 器官捐献人撤回权的行使
2.1 器官捐献人撤回权行使的主体
我国的器官捐献分为遗体器官捐献和活体器官捐献,而遗体器官捐献又分为捐献者生前作出捐献意愿及捐献者生前未明确反对器官捐献,在其身后由其近亲属代为做出捐献意愿的。一般而言,器官捐献人撤回权的主体为器官捐献者本人,在由近亲属代为做出捐献意愿的情形下,其近亲属可以撤回其之前的捐献意愿。
2.2 器官捐献人撤回权行使的对象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公民捐献其人体器官应当有书面形式的捐献意愿,虽未明文规定捐献意愿的作出对象,但规定了具备相应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因此,医疗机构既是器官捐献意愿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器官捐献者撤回权行使的对象。《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第12条、第16条规定“市红十字会及其委托的区县红十字会是人体器官捐献的登记机构,在捐献意愿登记后,本人可以要求变更或者撤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及时予以变更或者撤销。”《贵阳市捐献遗体和角膜办法》第4条第2款、第8条规定“市、区、县(市)红十字会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捐献遗体和角膜的宣传、咨询、协调、登记工作。变更、撤销捐献遗体或者角膜登记,应当到原登记机构办理手续,登记机构不得拒绝。”《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第11条、第14条规定“区、县红十字会和接受单位是本市遗体捐献的登记机构。办理遗体捐献登记后,捐献人可以变更登记内容或者撤销登记。”在其他器官捐献、移植法规中,类似地规定了红十字会或医疗机构作为器官捐献意愿的登记机构,因此器官捐献者撤回权行使的对象为上述红十字会或医疗机构。
2.3 器官捐献人撤回权行使的方式
我国的器官移植法律文件未明文规定以何种方式行使撤回权,笔者认为,器官捐献人可以以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行使其撤回权。器官捐献人能否以单纯沉默的方式或者以其行为行使撤回权?笔者认为,无论是器官捐献人单纯的沉默,还是器官捐献人以其纯粹的外在行为均不能行使撤回权。器官捐献人以单纯沉默的方式不能行使撤回权,因为撤回的意思表示只有在产生停止捐献的动机之后,经过其行为的外化并向登记机构作出,才能产生撤回捐献的法律效果,所以单纯的沉默,不能得出器官捐献人撤回器官捐献的内容。至于器官捐献人以其行为能否发生撤回捐献的法律效果,笔者认为结论同样是否定的,权利的行使应当向特定的对象予以作出才能实现其权利,器官捐献人虽然通过其行为予以外化,但同样不能准确的反映其内心的动机。例如一器官捐献者作出身后捐献心脏的意愿,一段时间之后,捐献者刺破心脏自杀,我们不能得出捐献者以其行为行使了撤回权,因为我们更倾向这样的推理:其刺破心脏只是为剥夺其生命,而非以自杀行使撤回权。
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属于形成权,依照器官捐献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就能够实现撤回器官捐献意愿的效果,作为器官捐献的登记机构负有容忍及协助捐献人行使该项权利的义务。该项权利属于形成权,形成权的行使不得附条件以及附期限,唯在权利的行使主体上须是作出器官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有权行使。器官捐献撤回权的行使在捐献者生前或者器官植入受体之前均享有撤回权,在时间上仅存在生命时间的长短和摘取及移植器官时间长短的问题,亦不受除斥期间的限制。撤回权人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行使其权利,在其意思表示到达医疗机构或红十字会时,撤回的意思表示生效,产生撤回器官捐献的效力。
3 器官捐献人行使撤回权的效果
要分析器官捐献人行使撤回权的效果,就需要对该项权利设立的目的予以剖析。罗马法时期未将自然人一视同仁地视为权利主体早已一去不复返,人人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法律之中予以体现。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以权利为本位是现代私法体系构建和制度完善的基础之所在。个人主义的精神理念是民法的发祥地,民法的最基础理念是以承认个人对自由、生命、安全和秩序等最基本的本能和需求为基础的[5]。康德哲学中的“主体——意志——理性”在现代民法,尤其是在器官捐献移植法规中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一个有理性的主体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构建自己的权利义务,法律不仅要保护这种可能性,而且要保护其真实性[6]。在私法领域,法律不知晓谁是农民,谁是手工业者,谁又是企业家,是抽取了财力及社会地位的外衣而存在,人生而取得权利能力,在到达一定年龄及智力能力健全便享有民法上的行为能力,能够独立从事民事法律活动。民法肯定一个法律上的人是思辨理性之人。民法在肯定自然人具有理性能力的同时,也不排除感性的存在,在器官捐献上尤为如此,特别是在活体器官捐献中,在面对近亲属因为器官衰竭,在病床上无奈的透支生命时,感性往往会战胜理性,这就需要在活体器官捐献中给予器官捐献者一定的考虑时间,并且使其达到对于摘取器官进行移植知悉的程度,若仓促摘取器官捐献人的器官进行移植,可能捐献者会因为对捐献认识不足或者心理准备不足而嗣后难以接受,悔之晚矣。因此,法律赋予器官捐献者器官捐献意愿的撤回权,既肯定了其器官的捐献意愿,也同样不反对其不捐的意愿,每个理性之人都是其最佳利益的判断者,尊重其自我决定权。
器官捐献人享有撤回权毋庸置疑,那么捐献人撤回权的行使是否需附加一定的条件?市民社会的法是肯定个体存在及其思辨、行为的差异性的社会规则,以其所体现的自由、正义、秩序等价值指引社会步入文明。不把人当做手段,是康德对自主性原则最为经典的描述。在英美法系中,依据宪法,个人在私生活而非财产规则的名目下被授予对其身体的自主权,私生活理论许可对身体进行轻微侵入,甚至不要求支付公正的赔偿,但国家不得为抢救一个人的生命而要求另一个人让自己的健康或生命处于危险中。每个人必须被视为目的,不得用来作为服务于他人的手段。若对人体器官捐献人行使撤回权附加一定的条件,那么无疑是将器官捐献这样的高尚德行绑架在了鄙俗的木桩之上,让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止步。因此,器官捐献者对于其所作出的捐献意愿享有自由的、任意撤回权。
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属于形成权,一经行使则产生撤回捐献的法律效果,若器官捐献人撤回其之前所作出的撤回捐献的意思表示,则效果如何?笔者认为,器官捐献者之前撤回捐献的意思表示已将捐献的意愿归于消灭,后作出的撤回先前撤回捐献的意愿不产生撤回的效果,可视情况而定,视为新作出的器官捐献的意思表示。
在器官捐献者行使撤回权之后,躺在病床之上需要器官的病人能否起诉其“缔约过失”或者要求承担损害赔偿?韩大元教授指出:“在器官捐献和移植前,当事人的承诺撤回是绝对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履行承诺,也不能基于捐献志愿书、移植请求书诉求他的‘缔约过失’责任,因而,这一界限更多的是以事前预防的角色发挥效力的。但如果供体虽然承诺提供器官,但潜在目的是损害受体的生命健康,致使受体丧失了最佳移植时机或因此造成了伤害,那么供体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乃至刑事责任。”[7]彭志刚认为,因由法律规定捐献行为可以撤销的条件和时机,对违反法定条件而给受益人造成损害的,受益人可以要求捐献人负赔偿责任,具体而言:(1)承认活体捐献人撤销捐献行为的绝对性,若接受人为此进行了必要的准备而造成损失的,需承担赔偿责任,或者是恶意撤销捐献行为致使受益人丧失寻找器官的最佳时机,致使受益人死亡的,受益人家属可就物质损失及精神损失请求赔偿;(2)对于死体器官的捐献,不管是基于死者生前的明示同意还是基于推定同意而由家属做出的捐献决定,同意一旦做出,就应该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不得随意更改[8]。
笔者认为对于因捐献人撤回捐献是否需要赔偿,应区分遗体器官捐献与活体器官捐献,不能一概而论。对于遗体器官捐献,我国大部分的器官捐献法规均规定器官捐献实行登记制度,建立统一的分配制度,因此,遗体器官捐献一般而言受体不特定,在捐献者行使撤回权的条件下难谓造成损害或是“缔约过失”,因此就遗体器官捐献者而言,捐献者撤回捐献无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活体器官捐献而言,《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0条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活体器官捐献的受体仅限于上述四类人员,器官捐献的供体以及受体均特定,若是供体以捐献器官之名行欺骗之实,最后恶意撤回捐献意愿,使受体因信赖供体的捐献意思表示而丧失寻找其他器官源的机会,致使受体死亡或者遭受其他严重身体损害,其本人及其近亲属有权要求赔偿损害。
器官捐献人在行使撤回权撤回捐献之后,作为登记机构或红十字会应当对已登记的捐献意愿及时注销,并进行保密,避免对其造成负面的影响。
4 结 语
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属于其自我决定权的范畴,器官捐献与否属于器官捐献者的权利,其有权以其人格完整为目的而对其个人事务予以处置,并不受公权力的干涉。近代以来,民法传统上的绝对理性人向有限理性人发生转变,每个人因智力水平、学科专业、理解差异等不同而存在认识的盲区,不存在绝对理性的法律主体。在器官捐献之中,器官捐献者亦是一个有限理性的主体,可能因其捐献时的思虑不周全而作出捐献的意愿,并在作出捐献意愿之后因对捐献性质、后果等认识发生变化而撤回其捐献意愿。人的存在本身即是其目的,应当受到尊重[9]。不论器官捐献人作出器官捐献或是撤回器官捐献,法律均应当尊重并保障捐献者该意愿的真实性。
[1] 陈朝璧.罗马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62-163.
[2] 周枏.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 李锡鹤.论民法撤销权[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02):28.
[4] 欧洲人权与生物医学公约[J].赵西巨,译.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02):156-157.
[5] 马黎.民法目的性价值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2.
[6] 李永军.民法上的人及其理性基础[J].法学研究,2005(05):24.
[7] 韩大元,于文豪.论人体器官移植中的自我决定权与国家义务[J].法学评论,2011(03):31.
[8] 彭志刚,许晓娟.器官移植受益人的权利保护及其限制[J].法商研究,2007(03):74.
[9]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119.
On the Organ Donor’s Withdrawal Right
SUN Dao-rui
(Law School,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Regulations on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give the organ donor the rescission right to cancel his organ donation intention, but according to civil law theories, this “rescission right” should be named “withdrawal right”. The withdrawal of organ donation is not to make the organ donation void, but to stop the pursuit of organ donation.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can only be implemented in written or oral form before the death of the donor or the transplantation of the organs. Giving the organ donor the withdrawal right is to respect his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embody the value of civil law.In living organ donation, after organ donor exercises the withdrawal right, the donor should compensate for the losses if malicious withdrawal results in death or serious body damage to the recipient..
organ donation; living organ donation; cadaver organ donation; rescission right of the organ donation; withdrawal right of the organ donation
10.11885/j.issn.1674-5094.20137475
1674-5094(2014)04-00062-66
DF523.9
A
编 辑:余少成
编辑部网址:http://pxsy.cbpt.cnki.net/WKC/
2014-03-04
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3DXS010),贵州民族大学科研院所、基地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孙道锐(1988-),男(汉族),云南宣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