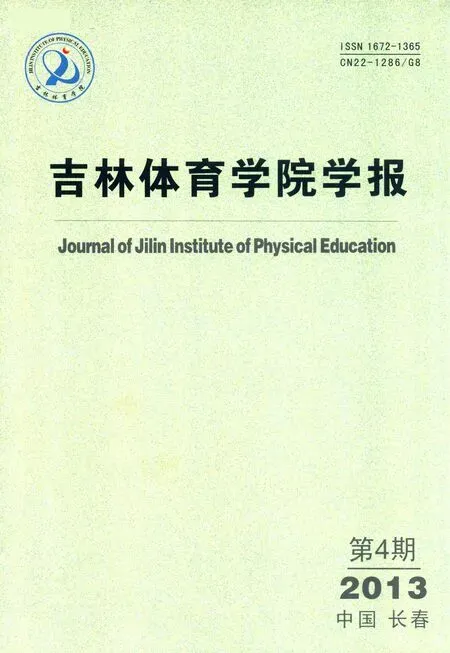论“内圣外王”与中华体育精神的契合
李 波 沈乐群
(1.南京大学体育科学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93;2.南京大学体育部,江苏南京 210093)
1 前言
经过无数先哲睿智的思索,汇聚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历经两千年的磨炼和洗礼,儒家文化被积淀并融入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但随着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发展,其腐朽、消极、过时的成份逐渐被暴露出来,其文化价值及存在的社会意义开始被人所怀疑,甚至遭到唾骂和摒弃。但当我们顺着历史的长河,审视这一融入了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时,其骨子里所蕴含的积极、健康的东西以及永恒、普适的意识形态,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导引着我们的价值观、规范着我们的行为、树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内圣外王之道”,其所关涉到的价值取向、人格及社会政治理想,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离的部分。而中华体育精神的形成和构建也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文化,其从内而外散发的正是中华民族文化所特有的气节和精神,我们对于中华体育精神的认识、构建和发扬,都应该不断汲取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正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体育健儿在竞技场上的优异表现,中国体育在世界体育领域地位的不断提升,这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正是影响世界最重要的内容。而儒家文化“内圣外王之道”与中华体育精神的契合,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正是中国体育魅力之所在。
2 “内圣外王”的传统内涵与中华体育精神的契合
2.1 成己成物
儒家对于理想人格的认识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最终被高度概括为“成己成物”。“成己”是通过一定修养从而使自己成为具有道德完美的人。儒家学说始终认为心性与人格修养是紧密联系的。人的心性是先天条件,它影响着人格的修养,心性基础好,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就大,反之亦然。但儒家并不认为其是决定性因素,而是认为人后天的修养更为重要。这与中华体育强调身心统一是不谋而合的。人的先天身体素质固然重要,但优异成绩的获取、健身、健体目的的达成还需后天的努力。然而身体的强壮、成绩的取得并不是中华体育追求的全部,更确切地说中华体育是以身体锻炼为手段、强身健体为目的、修身养性为追求的。“身体锻炼为手段、强身健体为目的”看似平淡无奇,但真正践之以行动时,一切却并非唾手可得,其间所面临的各种困难、生理及心理的考验、智力的挑战,也绝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之人所能胜任的。而儒家的“立志、为学、力行”似乎是对此最好地阐释。儒家的“立志”表现为自立、自强、自信、自尊、自勉等精神。既而克服身体锻炼、强身健体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为学”则体现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驾行之。”即是说,为学应该广泛地学习、仔细地求问、小心地思考、明白地分辨、笃实地实践。既而做到巧妙地行事,科学的锻炼,实现“下学上达”。
《中庸》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仁”、“智”、“勇”三者兼备,“修身”之功也就体现出来,“成己”之道也就变成规实。然而“身体锻炼、强身健体、修身养性”实际讲得是自我完美,自我价值的实现,即是“内圣”。然而中华体育除了健身修心这一功能外,它还具有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所以《中庸》说:“夫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儒家的“成己成物”说,实际上讲的是人生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
2.2 修己治人
“修己治人”原本是儒家“内圣外王”在政治层面上的一种思想理念,不可避免的带着封建思想的意识存在。但是当它与当今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发生交融、碰撞后,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中华体育与之依然能够擦出智慧的火花。《尚书·五子之歌》指出:“民惟邦本,本国邦宁”。民本思想经过儒家的发扬,终于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主流思想。儒家的民本思想主要还是反映了当时封建主义等级关系的烙印,而当今的中华体育精神则将其升华到“民主”的层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个体角度而言,体现“以人为本”。即从人最根本需求出发,满足每个人的身心健康需要,倡导无歧视、人人都能参与的民主氛围。并在参与的过程中,体会到理解、包容、团结、协作、拼搏向上、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和内涵。第二,从国家和民族的全局角度考虑。王安石曾说过:“百姓所以养成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成百姓也”(《王安石全集·再亡龚舍人书》)。即体育的发展要“以民为本”,无论竞技体育、群众体育还是学校体育,我们都必须抓住“民”本身,它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本,也是体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离开了这一基石,体育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算有一时辉煌,也只能昙花一现而已。第三,以全球观的视野来看中华体育。“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中华体育人文内涵在世人面前最好地展示。充分体现了中华体育用自己人格力量影响天下,由修身达到家齐,由家齐达到国治,由国治达到天下平的海纳百川的体育精神。它通过“修己”,创造一个不分民族、种族、肤色,平等和谐的大体育观,展现了中华体育的“内圣”,又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展现了中华体育特有的“外王”内涵。
2.3 明体达用
这里所说的学问是“明体”,事业是“达用”。儒家文化强调将学术研究、道德修养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统一起来,从而建立了以“实用”、“实功”、“实理”、“实行”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学以致用,是儒家的基本宗旨和一贯传统,这与中华体育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内涵是相吻合的。儒家学者研习经典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也就是要把学到的经术运用到社会现实中,以求开物成务、利国利民。这在当时虽然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但它所蕴含的“理论到实践”的文化精髓即使是现在,其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中华体育而言,“内圣”是理论,“外王”是实践。“内圣”功夫只有见之于“外王”事业,才是真正的“圣”,同时“外王”也只有以“内圣”作为指导,才能成就真正的“外王”事业,如果偏重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
3 “内圣外王”在当代中华体育精神中的价值
3.1 体现并提倡自我实现与社会实现高度统一的体育主体精神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与美国“个人英雄主义”不同的是,中华体育在强调个人“修身”、“成己”的同时,更关注群体和社会。《中庸》说:“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道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成己”必须“成物”,立必俱立,成不独成。两者虽有内外之分,但其道为一。正是受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华体育从发展、复兴到强盛,个人的命运始终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塑造了我们集体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世界观。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华体育崛起之时,无数地体育健儿能够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人利益,在艰苦环境中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同时在他们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和人民无私的支持和激励。当第一块奥运金牌挂在徐海峰的胸前,当刘翔在雅典奥运会刮起中国风的时候,时间跨越了几代体育人,但梦想却是未曾改变,当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赛场,我们看到的是中华体育的辉煌和亿万中国人的骄傲,这就是最具民族的,因此,这种民族文化造就了独特的中华体育精神,而这种体育精神也让个人与集体相融合,造就了中华体育的辉煌,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和谐。
从中华体育发展的整个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固然重要,但自我实现与社会实现如果不能高度统一,那么仅仅是“成己”而已,这种价值实现只能满足自我的相对完善,只有将个人价值转换为社会价值,才更有意义。姚明在NBA实现了个人的价值,但这也是国家和人民培养的结果,当雅典奥运会他率领男篮获取实现中国男篮最好成绩时,他个人价值也获得了升华。所以,个人的“内圣”只能确保一时的荣耀,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最终促成中华体育真正做到“外王”,这种荣耀才是长久和永恒的。
3.2 体现并发扬“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的体育博大精神
北京奥运会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宣传语,向世人展示了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通过体育这一窗口,世界了解了中国的开放和接纳、包容和个性、进取和创新。春秋时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国语·郑语》)的观点。即是说,只有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结合,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仅有相同的事物简单累积,是无法产生新的事物的。中华体育在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固步自封、闭门造车,而是将民族体育、民族文化向世界输出和传播,太极拳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同时,我们也积极地将世界优秀文化借鉴和引入,让中华体育真正做到即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在借鉴和学习时,我们也看到,在一段时期内,我们传统的东西在被人遗忘,甚至抛弃。针对这一点,孔子早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于路》)的思想。即,借鉴不等于无条件、无原则的全盘接受,脱离了民族根基的体育,最终将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其发展将岌岌可危。
中华体育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强调人格独立的同时,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文化理念。虽然儒家提出的“天下、世界”和我们现在的概念有所区别,但在思想理念上是一致的。中华体育的发展就是要通过体育这一途径和手段,“强世人之身、健世人之体、育世人之心”,为创建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而努力。因此,北京奥运会将目光投向了世界,并将世界的绿色发展作为自己的责任,在一些国家不友好的举动面前,我们处世不惊,不仅展示了我们不畏的气节,也践行了我们的和平、发展的使命,真正体现并发扬“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的体育博大精神。
3.3 体现并践行循序渐进的体育实践精神
从中国在奥运会获得金牌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华体育从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开始,并没有好高骛远,而是一步一步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经过体育人几十年的奋斗,从悉尼到雅典再到北京奥运会,我们从第三、第四军团,直到迈进第一军团。当然,获取金牌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成绩的取得体现了中华体育脚踏实地、立足现实、循序渐进的体育实践精神。也是儒家文化“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中庸》)在当代体育实践中的验证。当然,我们目前还称不上体育强国,无论是竞技体育、群众体育还是学校体育,我们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只要践行循序渐进的体育实践精神,那么最终会成就“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的境界。
4 结语
儒家“内圣外王”学说在中国社会走了近两千年的历程,而中华体育本身也源远流长,两者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着碰撞和交融。在这通过现代诠释和梳理,去除其腐朽部分,重拾蕴含在中华体育骨子里的文化经典,对于重新认识和塑造中华体育精神都是值得去尝试和努力的。同时,这也赋予了儒家“内圣外王”学说新的内容,并具备了当代价值,对于丰富和充实其内涵都是有益的。
[1]阎钢.内圣外王:儒学人生哲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75-199.
[2]程梅花.内圣外王:儒家的社会哲学[M].济南:泰山出版社,1998:325-338.
[3]李坚.内圣外王儒道思想的发展[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147-163.
[4]王斌.礼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4,28(5):44-46.
[5]刘介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6-111.
[6]宁陶,谢有长.内圣外王思想的源流及发展历程探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9):18-21.
[7]雷信来.解析“内圣外王”与“外王内圣”的思想悖论[J].世纪桥,2009(10):60-62.
[8]李进.“内圣外王之道”的衍化[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