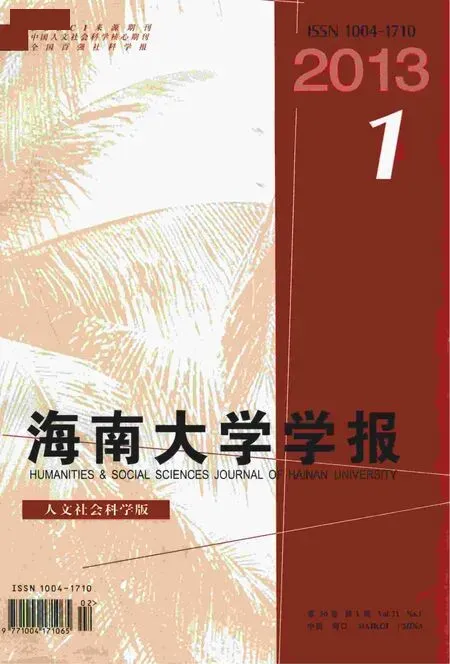尼采《偶像的黄昏》与形而上学问题
刘 振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尼采在世之时,始终没有出版那部他一再提到的《权力意志》(Willen zur Macht)。何以如此?或许有几种可能的原因。要么,尼采确实有出版《权力意志》的计划,然而由于中年以后精神状况日渐恶化,以至于无法摆脱严重的精神疾病,尼采最终没有完成这部作品;要么,在尼采发表过的作品中,《权力意志》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已然得到呈现,因此无须另行出版一本《权力意志》。事实上尼采也透露过,《偶像的黄昏》(Götzen-Dämmerung)、《敌基督者》(Der Antichrist)等作品正是《权力意志》的部分。
一、用锤子创造
或许,尼采最终受制于某些重大思想问题,无法建成《权力意志》这座哲学思想的“正厅”。这种可能意味着,既然尼采已经出版的部分作品出自《权力意志》,人们应该能够从这些作品中发现“权力意志”学说的困难。除此之外,最令人费神的一种可能也许是,既然尼采自己认为所有“改善”人类的哲人和教士都在讲“虔诚的谎言(pia fraus)”,因此所谓“权力意志”或许正是尼采的一个“谎言”。这种可能甚至意味着,即使尼采在世时将《权力意志》公之于世,人们也不能轻易认定这部作品表达尼采的真实想法,而且人们还不得不就此提出如下颇费思量的问题:尼采为何说谎,尼采的“谎言”究竟是什么?
不论如何,解开上述问题的惟一门径只能是从尼采发表的作品中探寻踪迹。因为,哲人的精神状况必然首先基于其哲学思想的状况,同时,既然有些已经发表的作品出自《权力意志》,其中必然会透露尼采思想的困难,至于尼采为何说谎,当然要听尼采自己“如是说”。因此,不妨尝试像尼采一样“打听底细”,小心地打听《偶像的黄昏》的底细。
尼采这部作品的主标题是“偶像的黄昏(Götzen-Dämmerung)”,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副标题——“人如何用锤子哲思(Wie man mit dem Hammer philosophiert)”。就主标题而言,尼采所说的“偶像”有两类:一类是西方传统哲学,更确切地说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尼采将这一传统追溯到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直至苏格拉底之前;另一类则是西方传统道德政治学说,在尼采看来,这些道德政治学说实际上基于上述形而上学。因此,“偶像的黄昏”这个标题似乎意味着,西方的形而上学与道德政治学说即将走到尽头。可是,这两类“偶像”必须经过一个重大思想事件才会走到尽头,这个事件就是重估(umwerten)一切的价值,尼采把促成这个思想事件看作自己的任务。不过尼采清楚地意识到,一切真正的重估都不可能仅仅是“否定和拒绝”,因为,倘若没有先行看到那个应该建立的东西,一切重估都无从谈起;换言之,那个应该建立的东西恰恰是据以重估一切的东西,是一切重估的根据。尼采认为自己的任务正是“创造(beschaffen)”那个应该建立的东西。
应该建立或创造什么?从这两个标题中看不出来。不过,尼采用这个副标题揭示出创造的工具——钻石制成的最坚硬的锤子。在《偶像的黄昏》之《锤子说话》一节中,用来制造锤子的钻石这样责备软弱的煤:
倘若你们不愿成为命数、变得无情:你们如何能够与我一起——胜利?倘若你们的硬度不能发光、剪裁和切割:你们如何能够与我一起——创造(beschaffen)?也就是说,所有创造者都是坚硬的。将你们的手按在千年(Jahrtausende)上犹如按在蜡板之上,你们必须以此为至福——在千年的意志(Willen)上犹如在青铜上书写,以此为至福,——比青铜更坚硬,比青铜更高贵。只有完全坚硬的东西才最高贵。①本文所引尼采原文皆出自卫茂平译《偶像的黄昏》,卫译不当之处,据德文改动。[1]191
尼采要用锤子创造什么?在这则寓言中,创造者要在“千年的意志上书写”,也就是说,创造者要为人类的意志立法。不过尼采说,创造者的立法必须以一场“胜利”为前提,因为,既然人类的意志之中写满了种种错误、可鄙的东西,创造者必须首先战胜他的各种敌人。然而,谁是创造者的敌人?
二、敌人与形而上学
显然,迄今谁在人类的意志中书写错误、可鄙的东西,谁就是创造者的敌人。这无异于说,创造者的敌人同样为人类的意志立法,创造者的敌人正是从前的创造者,而那个“最高贵”的真正的创造者则属于未来。尼采把从前的创造者称为人类的“改善者(Verbesserer)”,他们是“哲人和教士(Philosophen und Priester)”。因此,尼采的敌人似乎是从前的哲人和教士。然而,创造者为何必须与从前的哲人和教士为敌?在《人类的“改善者”》这一节中,尼采揭示了一个“骇人的问题”:
这个重大、骇人(unheimliche)的问题,我探究得最久:人类“改善者”的心理学(Psychologie)。一个细小而且根本不起眼的事实,所谓虔诚的欺骗(pia fraus),给了我理解这个问题的第一通道:虔诚的欺骗,所有“改善”人类的哲人和教士的遗产(Erbgut)。无论摩奴、柏拉图、孔子还是犹太和基督教的教师,都从不怀疑他们说谎的权利(Recht)。[1]91
看来,创造者之所以必须与从前的哲人和教士为敌,是因为从前的哲人和教士用谎言搞欺骗。“遗产”这个字眼或许表明,尼采认为自己不在“所有‘改善’人类的哲人和教士”之列。尼采的修辞是否意味着,未来的创造者与从前的哲人和教士的重大、骇人的区别在于,未来的创造者不再说谎?倘若如此,无疑意味着谎言对于尼采不再是正当的东西(Recht)。那么,尼采是否从不说谎?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人类的“改善者”为何说谎。就在尼采揭示这个“骇人的问题”之前,他明确说到,人类的“改善者”说谎是“为了创造道德(um Moral zu Machen)”。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尼采特意用斜体字强调这里的“创造(machen)”一词。这难道意味着,既然从前的“改善者”用谎言搞欺骗,那么所谓“创造”其实是凭空“编造”,他们宣称的道德不过是捏造出来的道德?
无论如何,尼采的修辞使得这里的情况变得十分复杂。既然问题在于为何人类的“改善者”要说谎,那么,不妨先搞清楚他们的“谎言”是什么。至少从表面上看,尼采严厉地指责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似乎这正是人类“改善者”的“谎言”,是哲人们“为了创造道德”而捏造的东西。可是,形而上学为何是“谎言”?在《偶像的黄昏》之《哲学中的“理性”》一节中有一则格言,其重要性在尼采作品中很可能难有其匹,尼采在其中说:
我怀着崇高的敬意把赫拉克利特(Heraklit)的名字拿到一边。倘若其他哲人族(Philosophen-Volk)指责感觉(Sinne)的明证,是因为它们显示复多和变动,那么他指责感觉的明证,是因为它们显示事物(Dinge),俨然它们具有持续性和一致性。赫拉克利特对感觉也不公平。它们既不以埃利亚学派相信的方式说谎,也不以他相信的方式说谎——它们根本就不说谎。我们从它们的明证创造(machen)出的东西才带来了谎言,比如,一致性的谎言,物性、实体、持续性的谎言……“理性”是我们篡改感觉明证的根源。只要感官展示生成(Werden)、灭亡,变动(Wechsel),它们就没说谎……不过在这一点上赫拉克利特将永远正确,存在(Sein)是个空洞的虚构。“表面的(scheinbare)”世界是惟一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仅仅是编造的(hinzugelogen)……。[1]55-56
尼采在这里同样用到了“创造”这个词,似乎让人茅塞顿开。在这段话最后,尼采明确说“‘真实的世界’是编造的”,“编造的”这个语词的词源正是说谎(lügen)。根据尼采的说法,“表面的世界”是感官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则是哲人从感官的明证“创造”出来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哲人的“谎言”,是一个虚假的世界。尼采这里的修辞让人突然想到,当他说未来的哲人“创造”千年的人类意志时,所用的语词是“beschaffen”而非“machen”。倘若确如尼采所言,从前的哲人“为了编造道德”而“编造”虚假的世界,那么,如果未来的“坚硬的创造者”是“成为命数、变得无情的”创造者,他们似乎必须与从前的人类“改善者”为敌,从他们那里“胜利(siegen)”。但是在此之前,尼采必须先证明,从前的哲人创造的世界为何是虚假的世界,或者,形而上学的世界为何是虚假的世界。
尼采的说法是,因为哲人用“理性”否定“事物(Ding)”。是哪些哲人在“否定”?尼采在这里谈到两个哲人族(Philosophen-Volk),一个是埃利亚的哲人,另一个是赫拉克利特,这两个哲人族共同的错误是:否定感觉事物。在尼采看来,埃利亚的哲人编造“存在(Sein)”概念——帕默尼德(∏αρμενíδηζ)的“存在(ο’uσí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正是这一类哲人的传人,这个哲人族用他们编造的“存在”否定事物,因为他们认为凡是“复多和变动”的东西皆无“存在”。所以,另一类哲人反对他们的意见,代表人物就是赫拉克利特。尼采对赫拉克利特的看法具有双重性。尼采肯定的是,赫拉克利特洞见到“存在”是个空洞的虚构,“在这一点上(damit)”他“永远正确”;但是,尼采批评赫拉克利特“对感觉也不公平”,因为赫拉克利特同样否定感觉事物,换言之,由于赫拉克利特否定任何相对的“持续性和一致性”,所以在他那里同样不存在所谓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既讨论主张“存在”的埃利亚学派,也讨论主张“流变”的赫拉克利特学派,因此,尼采这段论述的核心观点乃是:作为形而上学两端的“存在”与“流变”都是理性的编造——哲人的“谎言”。似乎感觉事物才是真实的:“它们既不以埃利亚学派相信的方式说谎,也不以他(赫拉克利特)相信的方式说谎——它们根本就不说谎”。
但是,尼采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工作依然只是“拒绝和否定”,他否定两个哲人族的形而上学,将其看作哲人的“谎言”,但是他始终没有明确表示自己是否也会“说谎”。可以设想,倘若尼采自己所说的话同样是哲人的“谎言”,那么他所否定的形而上学“谎言”岂不恰恰是真理?但是,如果这些形而上学“谎言”是真理,尼采为何又要否定它们?
三、形而上学与灵魂论
至少从字面上看,尼采从未肯定形而上学是真理。所以首先需要搞清楚,这些意在“改善”人类的哲人为何谎称形而上学是真理。这个问题尼采似乎已经回答过——从前的哲人编造形而上学是“为了创造道德”。这个说法表明,从前的哲人意识到一个事实:道德观念必须有其根基。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才以形而上学作为道德观念的根基。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从前的哲人“从不怀疑自己说谎的权利”,他们很可能十分清楚自己的形而上学是谎言,可是他们依然向世人宣称这些形而上学,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能的情形似乎只有两种:其一,人类生活本没有道德,一切道德究其根本都是谎言,哲人编造形而上学只是为了用形而上学的谎言为道德上的谎言奠基,因此,人类其实生活在双重谎言之中;第二,哲人编造形而上学只是为了宣扬某些特定的道德观念,这意味着,道德观念并非必须以形而上学为根基,或者说,人类的道德观念至少有两类,一类以形而上学为根基,另一类则不以形而上学为根基。
尼采想说的是哪种情形?目前看来似乎是后者。因为尼采似乎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道德,不仅如此,尼采给未来的立法者设定的任务就是在人类的意志中书写最高贵的道德。那么,尼采的说法看起来是:从前的哲人编造各种形而上学只是为了宣扬某些特定的道德观念。这样一来,尼采无疑是在揭示形而上学的最终根源。因为,在《偶像的黄昏》之《哲学中的“理性”》这一节中,尼采说形而上学的根源是理性的编造,现在,尼采进一步揭示了这个编造的根源——从前的哲人信奉某些特定的道德观念。也就是说,形而上学本来只是一个谎言,从前的哲人之所以宣扬他们的形而上学,是基于某种道德观念。
什么道德观念?据尼采说是宗教救赎、自由意志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既然形而上学背后的根源是道德观念,现在的根本问题当然在于认识这些道德观念,如此一来,人们就能彻底认识迄今出现的种种“偶像”。如何认识?尼采的说法是,继续打听这些道德观念的底细。因为,哲人的道德观念同样有其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哲人的灵魂。因此,尼采一再说他从事的是一门心理学(Psychologie),不过,尼采的心理学其实是一门古老的技艺,恰当的名称应该是灵魂论,因为尼采所说的Psyche(心理)显然是希腊人尤其是柏拉图的ψυχ'η(灵魂)。既然尼采认为道德观念的最终根源是哲人的灵魂,那么,形而上学的最终根据自然就是哲人的灵魂。因此,问题就归结为:从前的哲人有什么样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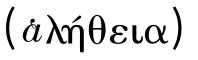
看来,尼采现在可以自信地说,灵魂的真相已经得到澄清,未来的创造者可以用他发光的锤子在意志的蜡板上立法了。人们似乎也可以得出结论,尼采与摩奴、柏拉图、孔子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士不同,他否定说谎的正当性,拒绝“虔诚的欺骗”。
事实是否如此?毫无疑问,尼采挑起了一场至关重要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尼采自己,另一方是从前的哲人。这场争论的主题则是:什么是灵魂的真相。既然尼采有权“拒绝和否定”从前的哲人,或许尼采也应该允许从前的哲人“拒绝和否定”他自己。然而,从前的哲人如何否定尼采?
尼采说他发现了灵魂的真相,可是,发现灵魂的真相自然意味着发现什么是(ist)灵魂,或者说,这必然意味着发现灵魂的“存在(Sein 或ο’uσíα)”。
但是,尼采明确说过,所有“存在”本质上必然借助“理性”,那么,如果不借助某种向内的“理性直观”,尼采如何发现作为内在事物的灵魂之“存在”?或者,如果“理性直观”只是哲人的编造,尼采如何能说清楚什么是“灵魂”?这种问法意味着,真理的发现似乎离不开以“理性直观”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因此,发现灵魂的“真相”离不开形而上学的“内在直观”。那么,难道形而上学并非“谎言”,而是出于真理本身的要求?
可是,真理本身的同样要求基于整体认识部分。认识灵魂既非认识灵魂的“理性”,也非认识灵魂的狄奥尼索斯冲动,而是认识灵魂的“存在”或灵魂的“秩序(πολιτεíα)”。然而,认识灵魂的“秩序”,意味着认识人的“自然(φ'υσιζ)”或“正义(δικαιοσ'υη)”。同时,离开作为人的整体之城邦的“秩序”,同样无法认识人的“存在”。可是,尼采也冷静地看到,认识城邦的“秩序”最终意味着认识存在者的整全(Ganze),亦即作为“自然”本身或“宇宙(κóσμοζ)”的“存在”;但是,这意味着认识一个比整全更大的整全,尼采在这里看到问题的根源——“可是整全之外一无所有”[1]88。
无论如何,尼采十分清楚,形而上学既是真理的要求,也是真理的深渊。除非人们能够认定,即使没有洞见真理的整全,人们依然可以获得真理明确显现给自己的东西。这意味着尼采哲学中或许隐藏着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或许通往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哲人,根据这条道路,尼采相信狄奥尼索斯冲动正是那个显现出来的、确定无疑的真理。不过,这个显现出来的真理依然在既作为真理、又作为深渊的形而上学中摆动。
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尼采相信人世的生活离不开道德,道德的根基是哲人的立法;可是尼采同样相信,所有关于内在灵魂的知识本质上离不开形而上学或者关于整全的知识,然而关于整全的知识就其根本而言乃是深渊。因此,为了保留立法的意志与立法的可能,既有必要公开地取消形而上学,又有必要隐秘地保留形而上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了使未来的创造者坚定地行使立法意志,尼采小心地隐藏了他的灵魂论的形而上学本质。尼采努力使他刻薄的言辞看起来指向形而上学本身而非某些形而上学,以免他的灵魂论“再次陷入形而上学或诉诸自然”[2]。或者说,尼采努力地想让他的哲学躲过那些过于形而上学的后现代哲人的眼睛,目的在于保留一个至少最明白的真理——人世的生活需要高贵的礼法,尽管何为高贵需要探究,然而探究好于根本不再探究,或者,严肃的探究好于随意的探究。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尼采精心地将真理与谎言混在一起,他并不急于宣布自己的律法,他相信形而上学的双重性必然要求永恒者的不断复归,过去的东西会在未来不断出现。因此,不论人们发现尼采竟然多么接近柏拉图,都不必感到惊奇。
[1]弗里德里希·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STRAUSS Leo.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