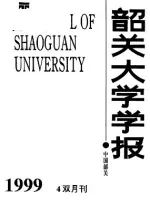从最佳关联性看英文电影字幕翻译效度
(广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西方视听翻译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1991年Luyken的《跨越电视语言障碍:着眼于欧洲观众的配音与字幕译制》首次探讨了影视的语言转换模式。1995年以后,欧洲视听翻译研究协会(ESIST)建立,Target,Perspectives,Meta等国际翻译期刊不断关注该领域研究性成果,以字幕翻译的描述性研究最为显著。领军人物有YvesGambier(芬兰)、Henrik Gottlieb(丹麦)、Jan Ivarsson(瑞典)、Jorge Diaz-Cintas(西班牙)等,他们试图利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建立影视翻译理论框架,研究对象涉及配音译制、字幕译制、画外配音和为残障人士提供的无障碍传播等多种语际或语内翻译形式,并从单纯的语言研究,发展到影视翻译与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等多方面的关系研究[1]。近年来,国内官方译配的影视作品呈多维态势发展,网络字幕翻译组亦拥有庞大的受众市场,在引进的各语种影视作品中,市场份额最大的还是英文电影,而汉语字幕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影视作品的接受度。我国的视听翻译研究相对滞后,多见于翻译技巧的探讨,如用目的论、系统功能理论或翻译生态论等文学翻译理论探讨字幕翻译策略,但是对字幕译文的效度研究尚未引起关注。本文拟从最佳关联性视角,分析英文电影汉语字幕的翻译特点,从认知视角解读字幕翻译效度的影响因素,探讨在特定翻译方向下如何提高字幕文本的翻译效度。
一、英译汉字幕翻译的特点
英译汉字幕翻译的特点源于两方面:一是翻译方向;二是文本因素。从翻译方向上看,由形式化程度高的语言译为形式化程度低的语言,隐化现象递增[2]。英文电影的汉语字幕正是从语言形式化程度高的英语,翻译为语言形式化程度低的汉语,因而汉语字幕的语篇衔接具有隐化趋势。这是因为,英语电影对白的形态功能较强,语法意义常由明显而规范的形态变化来表达,如连接词、功能词、分句和从句等,其结构完整,以形载义;而汉语字幕体现意合特征,构句采用无痕连贯,以语序或词汇调度来彰显事理逻辑,如零形式衔接(或隐形衔接)在汉语字幕中较为常用。此外,对于汉英在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方面的差异,应尽量使用符合汉语规范的语言形式,例如,四字格、俚语、主题句和无主句等浓缩性语段出现频率很高。简言之,英文电影的汉语字幕追求表达明确、措辞简化、衔接隐化、句法范化和文化专项显化。
从文本因素上看,字幕译文是辅助译语受众理解影视原声的特殊文本,和其它文学翻译相比,字幕翻译具有更高的综合性、浓缩性、市场性和科技性。第一,字幕翻译具有综合性和互补性,影视作品是多模态综合性艺术,具有图像、文字、声音等多重表意符号,翻译对象不是孤立的人物对白,而涉及多重符号的配合,字幕的言外之意有表演、画面或者配乐来充实辅助。第二,字幕翻译具有浓缩性和瞬时性,影视画面的空间局限、瞬时切换和语速快慢都会制约字幕符号量,通常一块字幕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为1到7秒,每块字幕的字符数(连标点和空格)不超过37个[3],以达到和画面动态和谐。第三,字幕翻译亦带有明显的市场性和商业性,译者有必要预测目标受众的知识结构和审美倾向,既要满足对异质文化有习得经验的受众需要,又要回归大众艺术的雅俗共享。第四,字幕翻译具有科技性,没有译配软件的实战经验,不能公正评价字幕译文的效度,通常译者在转码前反复揣摩剧情、表演和画面,在人物原声的自然停顿处标记文稿分句,并做好时间轴,再使用软件添加字幕,并对着画面反复修改。这些都和普通的文学笔译有所分别。
二、关联理论下的字幕翻译效度
关联理论从认知视角解释人类语言交际活动[4]。翻译是涉及三元关系和两种语言文化的交际活动,是遵循最佳关联原则的双重明示-推理过程,也是语言释义和翻译产出的两段过程。然而在产出阶段,普通文学由译者充当交际者,而字幕翻译中影视作者和译者同时作为交际者,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原影视制作者提供多模态影视符号作为表达意图的交际线索,字幕译者根据这些符号线索,结合双方共有的认知语境推断出影视作者的交际意图;第二阶段,译者提供承载原作意图的译语字幕,影视作者提供声画符号,共同形成交际线索,而译语受众根据这些综合线索,结合自己的认知语境,推断出影视作者的交际意图。在这两阶段,各种符号表征和交际者真正要表达的意图之间并不是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有着多种可能的理解方式,而交际对象总是倾向于选择和自己的认知语境具有最佳关联性的理解方式,期待能以适度的认知心力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如同,“估算生产率一样,要考虑产出和投入之比。”[5]
在关联视域下,翻译是一种跨语际的阐释性运用,是用另一门语言再述原文的信息和意图[6]。因而翻译效度,作为译文质量的重要表征,有两个参考值:趋同度和趋异度,和趋同度成正比关系,和趋异度成反比关系[7],其参照物为原作交际意图,而原作交际意图的实现要看译文与受众是否具有最佳关联性。字幕翻译的效度就是对影视作者意图的实现程度,因而译语字幕是否和目标受众具有最佳关联性尤为关键,“翻译的表达方式既要给译文读者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又不要让译文读者付出任何不必要的努力”[5]107。这也受影视作品的市场性影响,票房决定了受众中心论。字幕译文和受众的关联性越强,和影视原作意图的趋同度越高,翻译效度就越高;相反,关联性越弱,和原作意图的趋异度越高,翻译效度就越低。字幕译者的任务就是识别原影视作者的意图,分析译语受众的认知语境和认知特点,以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译文有效地传达原语作者的交际意图。最佳关联性的寻找,成为译者提高字幕翻译效度的必然途径。
三、英文电影中翻译效度的实现
奈达认为,尽管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文化存在差异,它们也惊人地相似,相似度甚至可达九成,而相异度不过一成[8]。对于相似部分,翻译时只需再现原文的语义表征,便可生成趋同度较高的译文;而恰恰是相异的那一成,构成了对译者的最大挑战,是指针翻译效度的关键区域,其动态转码方式因文本、译者而异。于字幕文本而言,尤为体现明示-推理过程中的读者导向,注重语言形式的浓缩性和易解性。译者在翻译决策时对影视作品核心意图的领悟,对观影者认知语境的总体预测,影响着字幕译文的效度。以下就从语言和文化两个维度,探析字幕译配中对相异部分的处理思路,寻求提高翻译效度的有效途径。
(一)语言维的翻译效度
首先,在语言衔接方式上,汉语字幕倾向隐化思维,以提高译文效度。英语使用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衔接手段,如逻辑衔接和语法衔接,常以语法功能词和虚词来体现;而汉语青睐隐形连接,语序和零形式很大程度上担当了衔接功能。由于字幕作为特殊文本,具有高度经济性,应该尽量使用汉语衔接的内隐策略,避免句式上的陌生化手法,产生妨碍解读的翻译腔。以下通过字幕译例,分析如何有效地处理逻辑衔接和语法衔接,提高翻译效度。
(1)This is my kingdom.If I don't fight for it,who will?这是我的王国,我不为它而战,谁为?(《狮子王》)
(2)The wise never marry,and when they marry they become otherwise.聪明人从不结婚,结了婚就再难聪明。(《加菲猫》)
(3)It takes a strong man to save himself,and a great man to save another.坚强的人救赎自己,伟大的人拯救他人。(《肖申克的救赎》)
(4)Sometimes people think they lose things and they didn’t really lose them.It just get moved. 人有时会以为失去了什么,其实没有,只是被移开了。(《第六感》)
先看逻辑衔接的字幕翻译策略,例(1)和例(2)分别是条件和时间关系从句,其衔接词“If”和“when”在原语中显化,其实从语义本身即可感受其逻辑关系,汉语以零形式译之,以意统形,既节约了字幕空间,又传递了原作意图,让观影者以较少的解读心力,获得了趋同于原作的语境效果,体现了翻译效度。类似的,增补、原因、条件和转折等各种逻辑关系从句,只要不改变原作意图,衔接词都可视字幕空间而隐化。再看语法衔接的字幕处理策略,例(3)中先行词“it”的后向照应功能在汉语中较为陌生,且不具备概念意义,因而可省,译文句式更为匀称,节奏前后呼应;例(4)中后两个代词“they”和“them”指代不同对象,如果直译为“他们其实没有失去它们”,罗嗦而致歧义,索性归纳为“其实没有”,无形胜有形,凸现了核心交际意图,又与原作趋同,是效度较高的传译手段。
其次,在非衔接功能的语言形式上,汉语字幕倾向简化思维,以提高翻译效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借助四字格、主题句、无主句等浓缩性语码,使字幕凝练;其二,对语义晦涩部分简化,使字幕明晰;其三,对语义重复部分隐而不表,使字幕精要;其四,当语义对应空缺,实施替换,使字幕连贯。如此,译语文本重点突出,可读性强,受众节省了认知努力,仍能借助电影的多重表意符号,推理出丰富的语境效果,相对于仿译,其交际线索经济而有效,翻译效度更高。例如:
(5)People die,but real love is forever.人会消陨,真爱永存。(《乌鸦》)
(6)We’re all just floating around accidentally―― like on a breeze.我们只是随风四处飘摇。(《阿甘正传》)
(7)It just means that your subconscious is attracted to their subconscious,subconsciously.那只是意味着你们两个在潜意识相互吸引。(《西雅图不眠夜》)
(8)Do you have a plan? 你有 计划吗 ?I don’t even have a‘p1’.八字没一撇。 (《老友记》)
分析发现:第一,浓缩性语码在字幕中出现频繁。如例(5)对称的四字格,浓缩凝练,字字玑珠;又如《乱世佳人》把“winning a war with words”译为“纸上谈兵”,《西雅图不眠夜》把“Destiny takes a hand”译为“命中注定”,都能有效拉近受众,提高译文效度。第二,对语义晦涩部分简化。例(6)若仿译为“我们都在偶然地四处漂荡,随风一般”,有翻译腔之嫌,“我们”其实隐含群体之意,所以“都”字可省,“偶然地”也可因“随”字而隐。如此调整语序和适度精简,使受众在解读字幕时,以较小的努力获取最佳语境效果。第三,某些原文有同义反复现象,出于字幕空间限制,可使用压缩手法。如例(7),若将后半句仿译为“你的潜意识,正无意识地被他们的潜意识吸引”,受众会为文字游戏付出额外的认知心力,相反,笼统地译为“你们两个在潜意识相互吸引”,更为言简意赅,可读性强,交际有效。第四,某些语码无法激活译语受众的认知语境,可隐去原文,替之以语义表征完全不同而交际意图异曲同工的语码。如例(8),字母“pl”意图表达“一个计划的开端”,所以采用汉语俗语“八字没一撇”形象贴切,受众能积极推断出与原语受众相近的语境效果,貌似不忠原文,实为凸现核心意图的更高层次的忠实。
(二)文化维的翻译效度
如前文所述,翻译过程分为释义和产出两个阶段,整个过程体现了交际主体的接力关系,即由原作者到译者,再由译者到译语受众。然而,字幕翻译不同于普通文学翻译:普通文学翻译的第二阶段通常由译者担当交际者,译语受众作为交际对象;然而字幕翻译中,第二阶段的交际者身份是由两个主体同时承担的,即影视作者和字幕译者同时向译语受众明示交际意图。这种交际局面给译者既带来了约束,也带了优势。其约束体现在字幕空间局限、不可复看性、与声画同步;优势是译者可以借助于影视画面的演绎,适当减轻描述的负担,当某些文化现象可以通过画面补充时,译者可以通过异化手段编码,以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分享于受众。异化的编码方式和原作的趋异度最低,可达翻译效度的制高点。例如:
(9)Magic Eight Ball,should I never see Rachel again?神奇8号球,我永不再见瑞秋吗?(《老友记》第五季第四集)
例(9)的影视场景是:剧中罗斯的妻子要求他再也不见前女友瑞秋,否则就离婚,罗斯无奈之下只能乞灵于“神奇八号球(Magic Eight)”。蕴含的语境预设是:“Magic Eight Ball”是美国特高玩具公司(Tyco Toys)制作的一款玩具,人们可以向这个“神奇八号球”提出任何问题,然后摇动一下,答案选项就会出现在球的小窗上。影视原作通过涉及 “Magic Eight Ball”的影视对白和画面信息,向译者明白展示其信息意图,译者结合语境预设,推理出原作交际意图:罗斯惧怕妻子埃米莉离去,也害怕失去好友瑞秋,左右为难,无计可施。虽然译者直译为“神奇8号球”,辅以“罗斯叩问8号球显灵”的影视画面,但汉语受众结合其认知语境,如魔镜、魔盒的乞灵场景,不难推理出原作的交际意图。这是对文化现象的异化处理,也是字幕翻译的综合性和优越性所在,源于影视艺术的多重表意符号,画面、配乐和其它影视符号共同牵引观众对译语字幕的认知过程。
然而,由于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规范之间的张力,原文中某些明显带有独特文化特征的文化负载词,在译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项或者与对应项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在原文中的功能和涵义转移到译文易产生翻译壁垒[9]。这种影视画面无法辅助解决的翻译障碍,隐译难以攻克,归化更难化解,于是显化应运而生,将原文中通过预设才能认识到的信息在译文中加以明示。由于显化易于造成译文冗长,与字幕简约性相悖,因此要有利有节地运用,“有利”是指要以提高翻译效能为宗旨,“有节”是指不能过度使用,以免受众因聚焦字幕而疏忽画面,错失影片整体传输的交际线索。显化思维的常用策略有阐释和替换。例如:
(10)Don’t be silly.Ben loves you.He’s just being Mr.Crankypants.别傻了,本他喜欢你,他只是爱发牢骚而已.(《老友记》第一季第六集)
(11)Loose the cannons,you lazy bilge rats.快把炮绳松开,你们这群懒猪。(《加勒比海盗》)
例(10)的影视场景为:莫妮卡每次抱起侄子本,本就哇哇大哭,莫妮卡手足无措,于是罗斯说出了例(10)中的劝慰之词。如果按字面译为“怪癖裤子先生”,这就与原作意图相去甚远。“Mr.Crankypants”是一个著名的美国卡通形象,他经常说的两句话是“别烦我”和“别碰我”,此处言外之意是:孩子正在叛逆期,并不针对姑姑。考虑到汉语受众不熟悉该卡通形象,有限空间容不下长篇注解,受众无法调用该卡通人物相关的语境预设,所以译者把言外之意和盘托出,有效实现了原作意图。这是一个常见的字幕阐释过程,通常用来处理那些受众认知语境中缺失的概念,虽然失去了生动的喻体形象,但是根据最佳关联性原则,减少了受众不必要的字幕处理时间,保证了对画面情节的注意力,翻译效度较高。
例(11)的“lazy bilge rats”,原指“懒惰的舱底老鼠”。在两种语言中影射的文化意象颇具差异,“老鼠”在汉语受众的认知语境中多为猥琐、肮脏、狡诈的象征,如果仿译,受众调取的是错位的语境预设,因为不熟悉英语中某些喻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并质疑其语言文化中所不存在的逻辑,直译法可能导致语境效果南辕北辙,所以代之以新的文化意象“懒猪”。这种替换殊途同归,虽形式叛离,但本质指向一致。在该影片中,类似的译法还有“a sitting duck”,原指 “坐着的鸭子”,译为 “瓮中之鳖”;“the snake pit”,原指“蛇洞”,译为“虎口”。替换的前提是原语语码和译语语码之间潜藏着隐含意义的共性,比如“the snake pit”和“虎口”在两种语言中的认知途径异曲同工。此法点燃了译语受众的语境认同感,可事半功倍地获得语境效果,忠实的叛逆,也是高效的译文。
四、结语
综上所述,英文电影的汉语字幕翻译,是译者依据字幕文本特质,以传达影视原作的交际意图为宗旨,关照受众认知而进行的动态转码过程。字幕翻译效度是影片交际意图的实现程度,译文意图和原作越趋同,效度越高,相反效度越低。效度实现的可靠途径,也是最佳关联性的寻找过程。在语言维度,汉语字幕应追求措辞简化、衔接隐化、语法范化;在文化维度,可借助影视多重表意符号的互补性,适当异化,但对于没有声画提示的文化障碍,应考虑受众的文化体验,明确精炼加以显化。译者需深谙中西文化,丰富语言储备,着眼于字幕的文本接受,展现出汉语的字字珠玑,以最佳关联的语言体现,让观影者积极回应,让两种文化融汇升华,实现字幕翻译的至高效度。
[1]董海雅.西方语境下的影视翻译研究概览[J].上海翻译,2012(1):12-16.
[2]柯飞.翻译中的隐和显[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4):303-307.
[3]Cintas D.Teaching and Learning Subtitle in an Academic Environmen[A].In D.Cintas.The Didactics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C].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8b:97.
[4]Sperber D,Wilson 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1995.
[5]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5-206.
[6]Gutt-August Gut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2004:27.
[7]Chesterman,Andrew.Memes of Translation[M].Amsterdam:Benjamins,1997.
[8]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1:45.
[9]Aixelá,Javier Franco.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A].In Román Avarez and M.Carmen-Africa Vidal(eds.).Translation,Power,Subversion[C].Beijing: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200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