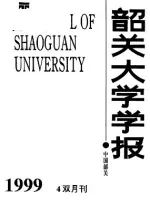评《侵权责任法》第87条——从侵权责任法立法利益衡量视角
(韶关学院 法学院,广东 韶关512005)
一、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是指对相关利益进行考量、评估,侧重某种利益或对相关利益进行取舍,以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法学中的利益衡量,既是法解释学的方法和法律适用的方法,也是现代立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利益配置机制。立法中的利益衡量是指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对各种利益进行识别、界定、整合,以平衡各种利益的一系列活动。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多变化和冲突化的社会,法律作为定纷止争的工具,立法者必须在立法过程中对多元、多变的利益进行识别、界定,对冲突的利益进行调整,对相关利益进行整合,以使法律制度的设计对各种利益进行有效调控,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受害人(或潜在受害人)权益保护与加害人(或潜在加害人)行为自由之间的矛盾是侵权责任法调整的一对基本矛盾。这对基本矛盾实质体现的是受害人群体的生存、健康、稳定等利益和加害人群体的行为自由、经济自由、发展等利益的矛盾冲突。侵权责任法对行为人的行为限制少一些,则其他人因相应的行为而利益受损的可能就大一些,反之亦然。到底在侵权法的法律制度设计中是给予人们更多的行为自由,还是对可能受损的利益给予更多的保护,这就需要立法者对相关利益进行衡量,以在立法中有所侧重和取舍。现代侵权法立法中的利益衡量即是要对受害人群体和加害人群体的各种利益进行识别、界定、整合,以通过制度设计平衡各种冲突的利益,在对受害人实施法律救济与保障人的行为自由之间实现利益平衡。
侵权责任法立法利益衡量的主要路径有一般利益衡量和特殊利益衡量[1]。侵权责任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平等在民法上既有抽象意义上的平等,也有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一般利益衡量是着眼于所有民事主体民事权利能力平等的抽象平等的基础上,即一般利益衡量的运用是“将每一个人视为同样的人,使每一个参与分配的人都能够在利益或负担上分得平等的份额”[2]。特殊利益衡量着眼于实质的平等,即在进行利益衡量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人群进行分类,对特殊人群在利益分配上进行特殊倾斜性保护。现代民法既强调民事主体抽象的人格平等,又注重民事主体间实质意义的平等。可以说,侵权责任法立法的特殊利益衡量是对一般利益衡量忽视民事主体实质地位不平等而造成实质上分配不均的缺陷的弥补。侵权责任法立法的一般利益衡量的适用具有普遍性,而特殊利益衡量通常只有在必要时,如在涉及企业主与劳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等之间的利益衡量时才适用。侵权责任法中的一般利益衡量在制度构建上主要体现为,侵权法通过过错归责原则、自己责任原则、构成要件、抗辩事由等制度设计在受害人(或潜在受害人)民事权益保护与加害人(或潜在加害人)行为自由维护之间实现利益平衡。侵权责任法的特殊利益衡量主要通过无过错归责原则、规定过错和因果关系推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对特殊利益进行倾斜保护,以实现利益平衡。
二、高空抛物侵权关系中的利益冲突和第87条的调整思路
高空抛物侵权关系当前通常指高楼住户从高空抛掷物品,致人损害而产生的侵权关系。高空抛物侵权关系中的基本利益冲突为抛物人行为自由和受害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此种利益冲突是产生于平等个体之间的普通损害赔偿关系,通过侵权责任法一般利益衡量机制调整即可,即通过过错责任、构成要件、抗辩事由等制度,追究抛物人的责任,救济受害人的损失。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见,第87条并非对高空抛物侵权关系的一个简单规定,而是对高空抛物关系中,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时,受害人权益如何保护作出专门规定,并把其中的利益冲突扩展至高空抛物人所在建筑物的其他使用人。第87条立法是在侵权法实践的推动下产生的。侵权责任法出台前,司法实务中一系列的高空抛物伤人案件,如深圳“好来居”玻璃坠落伤人案、重庆扔烟灰缸致人受伤案、济南扔菜板致人死亡案等,都在裁判过程中因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而对如何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产生了争议。上述案件最终都采取了倾斜保护受害人的做法,即判决由相关大楼的其他住户共同承担侵权责任。针对这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曾表达过意见:“从社会效果来考虑,也应该由被告举证(证明其未实施侵权行为),如果被告举证不能,就应共同承担责任,否则不利于对受害人的及时救济或对受害人家属的赔偿,不利于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社会善良风俗的建立”[3]。应该说《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做的利益选择是以侧重保护受害人利益的思路,将利益衡量的天平向受害人方倾斜。这种利益衡量方式并非侵权法立法中的一般利益衡量,也不完全符合侵权法立法中的特殊利益衡量,而是采取了一种分配风险,转嫁损害的思路。立法直接将侵权人无法查明的高空抛物受害人的损失在可能致害的所有住户间进行分配,将受害人的损失转嫁给建筑物其他住户,将高空抛物致害的风险直接规定由建筑物所有住户承担。这实质是一种分配正义的立法思想。王利明教授认为,现代社会风险无处不在,“如果无辜受害者的损失得不到补救,则社会正义就无从谈起”。应该以救济法为中心,构建我国侵权责任法体系,基于此定位,“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应坚持有损害必有救济,则侵权责任法的适用对象和范围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扩大,其具体制度设计也相应改变”。同时,就高楼抛物致人损害而言,王教授认为:“全体业主与受害人相比较,业主的损失分担能力更强,由其分担损害后果更能实现对受害人的保护。”[4]第87条即是从上述“侧重救济,分配正义”的思路对相关利益进行调整的。
三、从立法利益衡量视角对第87条的评价
《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产生有其立法背景和立法思路。与既存侵权法立法利益衡量方式相比较,第87条立法在利益衡量时采取了比较特别的方式,这也使得第87条在立法过程中引起了一些争议。笔者欲从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就第87条的立法阐述个人看法。
从侵权责任法的理论来看,如前所述,侵权法的立法利益衡量主要有一般利益衡量和特殊利益衡量两种方式。一般利益衡量表现为一般侵权制度设计,通过过错责任、自己责任、构成要件、抗辩事由等法律技术调整侵权人和受害人的利益。特殊利益衡量主要表现为特殊侵权制度的设计。从正义的类型上而言,一般利益衡量主要表现为矫正正义的调整思路,而特殊利益衡量主要表现为分配正义的调整思路。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是亚里士多德在理想的城邦政体中,实现具体正义的两种具体措施。分配性的公正,是按照所说的比例关系对公物的分配(这种分配永远是出于公共财物,按照各自提供物品所有的比例)。矫正正义,是指城邦中的公民为了私人的利益而相互交往时,对私人物品以算术比例原则进行分配的一种正义[5]。亚里士多德认为矫正正义为审判正义,即针对违法行为所采取的救济原则,所确定的是“一个人是否实施了非正义,另外一个人是否遭受了非正义,以及一个人是否实施了伤害,而另外一个人是否被伤害”[6]。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理论是侵权法正义理念的基础模型,在侵权责任法中体现为追究加害人的过错责任,使受害人的损失得以填补。而近、现代以来,由于生产作业的机械化和高科技化,很多损害无法用侵权法的一般利益衡量机制来解决,为实现社会公平,分配正义理念在侵权法中日益受到重视,主要体现在一些特殊侵权关系中,立法通过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因果关系推定等法律技术使得受害人的利益得以特殊保护。
如前所述,第87条对利益的调整实质是为了侧重救济,采用了分配正义的思想。分配正义理论在侵权法中的应用,体现在对特殊侵权关系中利益的分配上。特殊侵权是指欠缺一般侵权行为所要求的基本构成要件,由法律直接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侵权类型。特殊侵权类型以法律的特别规定为前提。特殊侵权通过规定过错、无过错归责原则以及举证责任倒置等制度,使得受害人的利益得到特别保护。但是,法律对特殊侵权关系的规定并非任意的,立法对行为人自由的限制必须有一定的理由,否则难以服众。特殊侵权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的理由(或说归责原因、归责基础)主要有:行为人开启或制造了某特殊危险;行为人与实际侵权人存在特殊的牵连关系;行为人和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为公平起见,由双方分担损失。第87条用分配正义的思想,侧重救济受害人而将对行为自由的限制扩大至可能致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但是该条规定对可能致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归责理由却无法用既有特殊侵权的理论来阐释。首先,可能致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是普通的高楼住户,他们并未制造或开启任何危险,住高楼本身并非法律上禁止的危险行为,不能因为他们住高楼而要求他们承担责任;其次,可能致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与抛物人(真正的侵权人)通常只是恰巧为同一高楼的住户,他们之间没有法律上的监督与被监督和管理与被管理的特殊牵连关系,不存在适用替代责任的基础,要求同一高楼的住户为抛物人的致害行为买单没有理论基础。最后,高空抛物侵权关系中,抛物人是过错侵权人,而公平责任适用于行为人和受害人都没有过错的场合,可能的致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并非行为人,他们没有实施任何致害行为,不存在有没有过错的问题,因此也不能适用公平责任使他们承担责任。可见,虽然第87条适用了分配正义理论,但是它突破了既有侵权法理论对分配正义理论的适用模式,导致其所规定的责任承担没有侵权法理论上的依据。虽然分配正义理论在侵权法中日益受到重视,但是作为私法,侵权法的理论基础仍然为矫正正义。“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应当有各自适用的制度边界,纠正强弱非均衡格局的分配正义的法律父爱主义措施应当主要体现于社会性立法之中。”[7]分配正义在侵权法中的过度扩大适用,可能危及侵权法的私法属性。
从实践角度来看,第87条的利益分配方式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影响法律权威。依第87条规定,高空抛物致害的责任由其他可能致害的无辜建筑物使用人分担,这实际是强加给了他们一个无法完成的义务,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一个人只有在没有尽到他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时,才承担责任,如果这个义务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或他已经达到了应当注意的程度,法律就不应该再对他科以责任。对于一个普通住户而言,他对于一个与他不相关的同一建筑物住户的行为往往不可能有预见的能力,也不存在应尽的注意义务,让他为该某住户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难言公平。立法基于一种分担损失的考虑,认为多数建筑物使用人比一个受害人更有分担优势,将损害在建筑物使用人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就独立个体而言,并不一定每个建筑物使用人都比受害人更有损失分担能力,这种比较会加剧处于经济劣势地位的人对法律公平性的质疑,导致法律执行困难,影响法律权威。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已经出现,重庆烟灰缸案中被判承担经济责任的无辜住户多数不服判决,四处上访,其中不乏有经济境况比受害人还糟糕的住户[8]。
四、结语
侵权人不明的高空抛物受害人的救济通过《侵权责任法》来解决或许并不合适。每一部法律都有其基础性法理、自身的体系和运作的疆界。“无损害,无救济”是侵权法救济的基本特征,然而“有损害,有救济”却是侵权法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第87条立法扩张了分配正义在侵权法中的适用,这种法律父爱主义在侵权法中的过度扩张必然冲击侵权法的既有框架,侵蚀侵权法的私法属性。侵权法是一部关于救济的法,也是一部关于责任的法,“它用自己全部的原则、规制,以至于全部的精力来处理行为自由和权利救济的问题,但是,侵权法中一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还需要在侵权法外去寻找”[9]。
[1]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的利益衡量[J].中国法学,2009(4):176-190.
[2]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5.
[3]杨立新.侵权法三人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24.
[4]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体系构建——以救济法为中心的思考[J].中国法学,2008(4):3-15.
[5]孙文恺.亚里士多德正义分类的理论与现实基础[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95.
[6]苗力田.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4.
[7]李霞.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法律救济——以《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为中心[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13-119.
[8]陈晓军.高空抛物之法律探析[J/OL].[2013-01-12].http://www.studa.net/minfa/090527/16382214.html.
[9]王成.侵权责任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