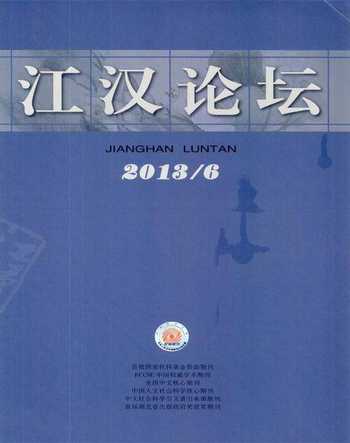当今边疆地区环境史视野下的“瘴”研究辩析
刘祥学
摘要:环境史是当今史学研究中的热门。在对边疆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尤其是在对“瘴”的研究上,很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但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往往持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取向,违背史料运用的基本原则,在论证过程中,其逻辑思维本身是矛盾的,得出的结论不少与科学原理、生活常识相悖。
关键词:边疆地区;环境史;瘴;史料运用;逻辑思维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6-0077-12
在环境问题曰益突出的当代,环境史研究无疑是当今史学界研究的热门,其相关成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由于史料中有关“瘴”的记载极为丰富,且存在的时间长达近两千年,很自然成为边疆地区环境史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十余年来,众多学者倾力研究,或侧重于瘴的名称及含义解释,或侧重于瘴区的历史变迁,或侧重于从疾病医学角度以及文化学、传播学、地理学、景观学等角度来研究瘴,已取得了不少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颇值得指出的是张文的《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和张轲风的《从“障”到“瘴”——“瘴气”说生成的地理空间基础》③两文。前者认为瘴乃古代的文化概念而已,是统治者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地域歧视的重要表现。后者主要从词的释义角度考证了“瘴”字的演变过程,认为瘴的广泛使用,体现出中原汉文化的强烈意识。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不少研究者往往以一种先人为主的思维取向从事研究,在史料的分析与运用上,违背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以致在研究中常出现逻辑自相矛盾的现象,这一现象是颇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在“瘴”研究已持续一段时间并取得相当成绩的情况下,很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总结与争鸣,才能推动“瘴”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此,笔者对于瘴气、瘴疠等历史名词、概念不作具体的辨析,只从史学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近十年来以边疆地区环境史为视角的瘴研究,阐述自己的一孔之见。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尊重诸多学者所付出的努力,所提出的不同见解,丝毫没有贬低已有成果之意。只是从反向思维的角度。对现今的瘴研究进行必要的学术争鸣。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瘴”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近世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就曾明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④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学者也持相同的论点,认为“没有史料,没有历史”⑤。在史学研究中,史料正确与否,不仅决定史学研究结论的正误,同时也决定着研究本身的价值。中国史料浩如烟海,又往往真伪并存,故史学研究对史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忠实、准确。在征引史料前,对史料本身进行必要的考证,信而后引,这也是最基本的原则。但近来的边疆地区环境史研究,特别是对“瘴”的研究上,不少研究者却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数端:
1 盲信所谓的原始记载。直接引用明显具有逻辑矛盾的史料
关于“瘴”的最早记载,一些学者认为出自东汉,《后汉书》是首部记载瘴的正史。⑥仅《马援传》中就有3处明确提到瘴。其一是记载马援南征交阯,斩征侧、征贰,班师回朝。因其有功,东汉封其为新息侯。马援于是“击牛酾酒,劳飨军士”。在宴会中,马援谓官属曰:“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又言“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这里显然是指瘴气,瘴气的杀伤威力已然超过了手持武器的敌人。其二载“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其三,云阳令朱勃上疏为马援伸冤,声称“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其中尤以马援声称的“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为后世津津乐道,奉为圭臬。以此为发端,有关瘴的记载才逐渐多了起来。先不论此条史料存在的问题。即使为真,也只能说明东汉时期在交阯才有所谓的“瘴”存在。然而。让人不明白的是,何以自东汉后,瘴气会蔓延到交阯以外的整个中国广大南方地区?所有的研究者对此均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仅从《后汉书》记载的这条史料本身看。至少也是存在明显问题的。笔者认为:这条史料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自相矛盾,缺乏可信度。试想,按马援描述,交阯的瘴气是如此之毒,能够“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说明是近距离观察了。问题是在弥漫着巨毒的“瘴气”熏蒸之下,既然飞禽之类的生物,立刻堕毙水中,而同样作为生物体的亲历者,又怎么能安然无恙?更何况马援叙述此事时,是在犒劳士卒的宴会上,也就是说纯属酒后“真言”。酒饱饭足之际,对部属吹嘘一下自己的战功,与所经历的危险故事,本是一种正常行为,但却不能将这些酒后真言当作信史看待。在他之后,其他人所提到的“瘴”,也是根据马援所说的“瘴”加以陈述的,并非亲身经历。还有就是“瘴”一出现便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从史料记载看,既具有“气”的属性,即为自然界散发的“有毒气体”。又具有“病”的特征,所谓“瘴疫”。不论史料描述的瘴为烈性有毒气体,还是疾病,士卒染瘴而死者均在十分之四、五左右,但如从《后汉书》“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的记载来看,瘴并非毒不可治,其时人们显然已掌握了食用薏苡以胜瘴气的办法。问题是既然人们已找到战胜瘴气的办法,士卒又为何还有死亡十分之四、五的高死亡率呢?而且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这个士卒死亡的比例,到魏晋南北朝再至宋代都是如此!如《南史》卷66《杜僧明传》载,梁大同年间,杜子雄率军讨伐叛军,士卒中瘴毒,“至合浦,死者十之六七”;《宋史》卷348《王祖道传》载“祖道在桂四年,其地瘴疠,戍者岁亡十之五六”;文彦博疏称:“北兵往戍,不习水土,每至岁满,戍还,瘴死者十有三四”。由此可见,自汉以来,中瘴死者的比例多在十之五左右波动,当然也有一些人宣称“岭南外区,瘴疠薰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生”。而同样的,至少在宋代,时人已掌握应对“瘴”的办法了。也就是说,从史料记载的源头看,士卒染瘴的高致死率从一开始就与其时人们的认识与防治是自相矛盾的。
自马援描述瘴气之毒后,广为后世史家所引述。至宋代时,在史料记载上,对于其所说的看见飞鸟堕地的地址至少出现了相互矛盾的两处。其一为广西容州。史称“此地多瘴气,……江水即马援云仰视鸟鸢跕跕堕水中,即此地也”;其二为广西合浦。史载“春,青草瘴;秋,黄茅瘴。元和郡县志云:自瘴江至此,瘴疠尤甚,中之者多死。举体如墨,春秋两时弥盛,春谓青草瘴,秋谓黄茅瘴。马援所谓仰视鸟鸢跕跕堕水中,即此也。”同一作者写的同一部史书,对此记载即出现了矛盾的状况,说明史料记载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即后代存在套用前代记载的情况。
又如有关“瘴母”的记载,其实源自西晋时期的“鬼弹”,其中干宝的《搜神记》卷12有载。称“汉永昌郡不违县有禁水,水有毒气,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辄病杀人。其气中有恶物,不见其形,其似有声,如有所投击。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土俗号为鬼弹。”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条材料,一些学者竟深信不疑。稍具史学常识的人,即可知道,《搜神记》作为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所载皆多怪异。作为史学研究者,是不应该将其所载内容视作史实对待的。更何况“鬼弹”,“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威力如此巨大,凡人自是难以接近,旁观者又如何能够逃脱?
2 没有注意到史料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重复”性
不可否认。自东汉后,有关“瘴”的史料记载,越来越多,有一个曰渐丰富的过程。如以瘴的史料记载多寡而论,大体是隋以前属萌芽期,隋唐时属发展期,宋至清中叶则属爆发期,这一时期有关“瘴”的史料记载丰富程度达到顶峰。清末以后为衰落期,史料对瘴的记载才渐渐减少。
然而,在这些“丰富”的史料中,只要细心考察,便可发现,不论是正史、私人笔记还是地方志,其所记载的史料均有相当的“重复”性。即不少所谓的史料完全是后人“抄袭”前人史料的结果。这是从事瘴研究不能回避的事实。这样,史料层层相因,无疑给人“瘴”气极盛的深刻印象。
如前述之“鬼弹”与后来的“瘴母”的史料流传就很能说明问题。关于“鬼弹”,西晋干宝《搜神记》与《左思别传》均有提及。《左思别传》称“初,(左思)作《蜀都赋》云:金马电发于高冈,碧鸡振翼而云披,鬼弹飞丸以礌礅,火井腾光而赫曦”。左思所处年代略早于干宝,考虑到《左思别传》为南朝人注引,且版本文字并不相同,并不能排除后人添加的可能。故谁是“鬼弹”的最早提及者,实已难详考,但最早出现于西晋应是没有问题的。自此之后,关于“鬼弹”的史料记载开始多了起来,且有所变化。先是晋代佚名所编《南中八郡志》作了摘录,其后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卷38《若水》以及萧统在《昭明文选》也都作了摘引。宋以后的史书、医书皆引用不断,但多以引《南中八郡志》为主,其书佚失后,宋代《太平御览》卷15《天部十五·气》即作了摘引,并进一步作了发挥,称“《南中八郡志》曰:永昌郡有禁水,水有恶毒气,中物则有声,中树木则折,名曰:‘鬼弹。中人则奄然溃烂。”北宋时伪托晋人李石所撰的《续博物志》卷2对“鬼弹”的记载称“先提山有钧蛇,……水傍瘴气特恶,气中有物,不见其形,其作有声,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名曰鬼弹。”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42《虫部》附录《水虎·鬼弹》将之列为“溪毒”之类,也是引用了已佚的《南中八郡志》,称“其气有恶物作声,不见其形,中人则青烂,名曰‘鬼弹”。至清代医书所引,皆不出此内容。
至于史书中的“瘴母”即由“鬼弹”演义而来。晚唐时,瘴母之说开始流行,先是刘恂在《岭表录异》卷上载“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唐人郑熊《番禺杂记》中有关“瘴母”的记载,从文字到内容与此完全一致,因郑熊所处年代略晚于刘恂,故应是摘引《岭表录异》之故。其后陆游在《避暑漫抄》中又作了摘引,“瘴母”之说遂逐渐流传开来。至明代,邝露在其《赤雅》卷下,再对“瘴母”作了更加具体、形象生动的描述。称“瘴起时,望之有气一道,上冲如柱,少顷散漫,下似黄雾,空中如弹丸,渐大如车轮,四下掷人。中之者为痞闷,为疯痖,为汗死。人若伏地,从其自掷,则无恙。”由于作者出生于广东南海,且有游历广西民族地区的亲身经历,故他所述,总能给人场景逼真的感觉。晚明汤显祖的戏剧《邯郸记》第二十二出也有这样的描写:
过了连州地方与广东接界。……[童]脑领上黑碌碌的一大古子来了。(生]禁声!那是瘴气头,号为瘴母。[叹介]黑碌碌瘴影天笼罩,和你护着嘴鼻过去。(走介]好了,瘴头过了。[童]又一个瘴头。[生]怎了,怎了,这里有天难靠,北地里坚牢,偏到的南方寿夭。
至清代,史家及西南各省方志所载“瘴母”,皆与前述大同小异。惟文字不同而已。
又如关于“瘴”的种类,也有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较早以植物命名的瘴,是在晋代。其时史料有载“芒茅枯时,瘴疫大作,交广皆尔也。土人呼曰黄茅瘴,又曰黄芒瘴”。之后,在唐代开始盛传开来。在唐人所修的《陈书》、《南史》中均有记载,称“时春草已生,瘴疠方起”。其时民间已有“青草黄茅瘴,不死成和尚”的谚语,《元和郡县志》也载“青草黄茅瘴,……瘴疠尤甚”。至宋代开始,种类又进一步增多了。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杂志》记载的植物瘴已有数种之多,称“邕州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其后,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风土门》按发病症状将瘴分为冷瘴、热瘴等。邝露《赤雅》卷下所录之瘴,皆采自《桂海虞衡志》,清代闵叙《粤述》在原有基础上,又新增了桂花瘴、菊花瘴。至于以动物命名的瘴,则始自唐代,较早的记载有“瘴广之南新、勤春十州,呼为南道,多鹦鹉。……食木叶榕实。凡养之俗,忌以手频触其背,犯者即多病颤而卒。土人谓为鹦鹉瘴”。之后,这一史料开始为宋人所引用。范成大则作了更进一步的描述,称“南人养鹦鹉者云,此物出炎方,稍北,中冷则发瘴,噤战如人患寒热,以柑子饲之则愈,不然必死。”明人王圻所纂《稗史汇编》卷159《禽兽门·禽上》也作了摘录。
以上记载中,尤以《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赤雅》等私人著述广为广西、云南等地方志以及医书所引。只要仔细检阅,便可发现自宋以后,“瘴”这一名称有一个明显的丰富、发展过程。在原有植物命名的瘴上,甚至出现了黄瓜瘴、芳草瘴。以动物为名的瘴中,有虾蟆瘴、朴蛇瘴、蚺蛇瘴、孔雀瘴等,甚至还出现了人瘴。林林总总,无不是不同朝代,不同作者之间不断转述、渲染的结果,从而导致有关瘴的史料记载,在不同作品间,不同地区间均出现了高度一致的状况。正如史料所载:“人有恒言,五岭之外多瘴,今广之东西是也”。这个“恒言”,正说明了所谓岭南多瘴系由历代人士反复重述而来这个事实。如果对这一问题不从史料学上深加辨析,而是以此作为研究基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科学、不可靠的。
从最原始的史料记载看,不少载“瘴”的古籍都有“述异”、“志怪”性质。经过一代代作者的反复转引、添补,最终成了“史料”。但近来的研究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3 只摘引于己有用的史料,回避于己不利的史料
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历史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复原客观真实的历史。要求研究者在众多的史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现实是近来部分研究者在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的瘴时,在史料运用这个原则问题上,却持一种先人为主的思维取向。采取了厚此薄彼的态度,甚至只摘引于己有用的史料,回避不利于己的史料这样的治学态度,因而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全面的。
诚然,历史上关于“瘴”的记载,委实不少,可称俯拾即是。但是否有瘴,即使在古人看来也是大有分歧的。尤其是宋以来,对瘴之说表示怀疑、甚至断然否定其存在的,也大有人在。这样,在史料中,常常出现较为明显的相互矛盾的记载。
如桂林,唐诗人许浑在《送杜秀才归桂林》中称:“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白居易则称“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白居易(772年846年)与许浑(生卒年不详,史载其于唐文宗大和六年即公元832年中进士)生活的年代,大体相近,何以在一人嘴里称有瘴,在另一人嘴里则称无瘴了?至宋代《桂海虞衡志·杂志》又载“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宋代的昭州(今平乐县),宋时一些人称其为“大法场”,邹浩称其为“昏昏瘴海”,庐陵人徐俯则称“两岁昭潭无瘴疠,清秋郁郁望神岗”。海南岛,宋代周去非称“海南之琼管,海北之廉、雷、化,虽曰深广,而瘴乃稍轻”,说明海南是有瘴气存在的,只不过程度轻微一些而已。但宋代赵汝适却称海南气候虽与中州异,但“地无烟瘴水潦之患”。同样是同一地方,究竟是有瘴还是无瘴,同时代人的看法并不相同。至于后代,持异议者更是多见,如民国《贵县志》称“昔之所谓瘴者,不独桂林无之,梧、浔以上之郡县皆无之,极之泗城、西隆之崇山峻岭,人迹罕经之处,亦无之,旧通志谓草木壅翳,蛇虺出没者,概乎其未之见也。至闵叙《粤述》谓地卑土薄,阳气常泄,人居其间,腠理不密,肤多汗出,往往致病。夫阴阳疵疠,何地无之,而且归咎于其地之气候,殆亦不必然也。”
还有就是,瘴既然毒害巨大,有瘴之地显然是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可事实上,有史以来,边疆地区所谓的“瘴乡”、“瘴海”,却是古人类的故乡。目前已有的考古发掘中,已知的就有云南元谋人、广西柳江人、广东马坝人等,近来在广西古代号称“重瘴区”的百色市辖区内,就发掘了大量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明遗址与遗物。说明在很早时期,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明代,郁林、苍梧等地,为史料记载有瘴之地,可却是当时广西人口最为稠密之地。为解释这个问题,古人也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史料记载。一为土著居民适应当地环境了,具有免疫力,所谓“土人谙则不为病”;“盖身居覆载之间,曰食动植之物。凡往来岭南之人,无不病且危殆,何也?若所谓南人生长其间,与水土之气相谙,外人之入南者必一病,但有轻重之异,若久而与之俱化则可免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论北人与南人,皆无法免疫。如宋人李璎绍兴年间寓居苍梧,“见北客与土人,感瘴不幸者不可胜数”。甚至还有人认为,“夫瘴,亦天地之气也。元气固,虽曰当之,无伤也。不然,郁林、苍梧之境,户不下数百万,彼人之生屯林立者,将藉养于他方乎?”
以上这些具有异论性质的史料,并非毫无价值,然而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不少研究者在研究中对这些于己不利的史料却不够重视。如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一文中,从文化视角人手,阐述瘴疾与华夏文化扩散的关系,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论述岭南地区的瘴疾时,却只取前人史料中与自己观点吻合的史料作支撑,而对同一书的另一说法未予重视。甚至在其所引的同一篇目中即有“且此病(指瘴疾)之作也,土人重而外人轻,盖土人淫而下元虚,……外人之至此者,饮食有节,皆不病”这样的记载。
再者,在缺乏仪器检测的古代,断定所处环境究竟是有瘴还是无瘴,主要还是以个人对环境的感知为主。这类记载有较明显的好处,即所记多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说服力较强。但缺陷也显而易见,就是环境感知者难以摆脱自身认识的局限,更主要的是个人对环境的感知,终究是要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同一个人,处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心境并不一样,对所在环境的感知认识,前后也会出现差异。一般而言,作为谪宦,他们或因犯罪被贬。或因得罪权贵被迫离开权力中心,被发配到地理位置极为偏僻,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边疆民族地区。他们悲苦失意的心情,多体现在南行途中的诗作中。再者被贬时多已有一定年纪,在赴谪所的途中,如若染上疾疫,身心痛苦与政治失意的苦闷交织,这时他们诗作中有关瘴的渲染就较多。在此,笔者以宋代的苏轼与李纲为例。他们都是宋代名臣,且都有被贬海南,后获皇帝恩赦,返回内地的经历。仔细对照他们的年谱与文集,便可发现他们的诗作,在贬往海南与返回内地的途中,对所经环境的描述,前后即有明显的差异。
根据《苏东坡文集》记载,苏轼最初被贬至广东惠州,南行路线为:自江西翻越梅岭,到南雄、韶州、曲江、清远、广州、惠州,之后被贬海南,行进路线为:由惠州、广州、梧州、藤州、过雷州,至海南,最后到达贬所儋州。获赦后返回路线为:从海南至廉州、郁林、容州、藤州、广州、韶州,越过梅岭,返回内地。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59岁的苏东坡先被贬英州,旋又被贬宁远军副使,安置惠州。他一路乘船南行,未受风寒之苦,在清远,即作《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这里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都十分适合他,初到惠州,失意的他就受到当地吏民的热情接待,心情大好,被贬斥后的心态也归于淡定。他作诗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他在《答陈季常书》中称:“轼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其后在绍圣三年(1096年)四月,他于归善县买地数亩,修筑房舍。其游罗浮山时作《荔枝诗二首》,其第二首云:“曰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表明了他在遭受排挤、贬谪后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并有在此终老的思想准备。这·时期,在他的诗作中,涉及瘴的极少。其间只在登游白鹤峰,所作《丙子重九诗》中偶有涉及,即诗中所称“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绍圣四年(1097年),因为朝内党派之争,苏东坡再被贬为琼州别驾,居昌化(儋耳)。这个诏令给他以沉重的心理打击,他由原来乐观、淡定,迅速转向悲观、迷惘,以为自己不久将死于贬所,在《与王敏仲书》中声言:“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别,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从昌化军谢表云》称“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臣孤老无抚,瘴疠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从惠州起程到赴海南谪居之所,苏东坡所作的诗文中,涉及瘴的篇目才又多了起来,根《苏东坡集·后集》统计,即有《江月五首·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薏苡》、《夜卧濯足》、《独觉》等篇目。所述之“瘴海”、“瘴雾”、“瘴疠”皆为泛指,或在追述前人时抒发。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苏东坡对海南地理环境并不了解,在赴谪所前深受海南“瘴毒”传说的影响。而当他真正到达谪所儋州后,随着他对当地自然环境有了亲身的体验与了解,以及亲见“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者”,与原先听说的瘴毒弥漫,人民“早天”之地,完全不符。为此,他大发感慨,“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心态重又趋于淡定。故在海南谪所生活的三年间,苏东坡写下了不少诗文,但涉及到瘴的篇目极少。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病逝,其弟赵佶继位,苏东坡获赦移回内地安置。其返程途中心情与初赴海南时自有天壤之别。故经过的廉州、容州等史籍记载的瘴毒地,在他所作诗文中,对瘴均没有提及。惟一一处提到瘴的,是在经过藤州之时。其有诗文称:“峤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霜风扫瘴毒,冬曰稍清美”。究其原因。可能与他在郁林途中。得知好友秦观在藤州中暑,卒于光化亭,心情伤痛有关。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他把好友的病亡归因为染上瘴痢。他在《与范之长书》中称“到容南(容县),知昆仲皆苦瘴痢”。
北宋的另一大臣李纲于靖康二年(1127年)被贬海南,其南行的主要路线为:自湖北蒲圻,经临湘,过岳阳、澧阳、益阳、湘乡、邵阳,至广西全州,经桂林、阳朔、修仁、象州、贵州、郁林州、雷州,最后至海南岛。建炎四年(1130年)获赦返回内地,回程路线为:海南、海康、雷阳、陆川、郁林、北流、容州、藤州、苍梧、封川、肇庆、广州、循州、惠州、潮阳,然后经福建返浙江。
与苏东坡不同的是,在李纲的诗作中,自从进入岭南后,几乎无处无瘴。路过桂林时,他有诗云“时危远谪堕南蛮,犹在乾坤覆载间。瘴雨岚烟殊气候,玉簪罗带巧溪山。”过修仁县时,有诗称“夸妍斗白工夫拙,辟瘴消烦气味长”。过象州,他有诗云:“山鸟不知兴废恨,岭云自觉去来忙。炎荒景物随时好,何必深悲瘴疠乡。”其后抵达贵州(今广西贵港市),所作的《次贵州二首》、《伏读三月六曰内禅诏》、《即事三首》,经郁林州所作的《端午曰次随林州》,南行至雷州时所作的《赠峤南琮师》,都涉有涉及到瘴的诗句;最后到达海南后,他还有诗称:“当茶消瘴速,如酒醉人迟”。可以说,他进入岭南后,在一路南行的路途中,几乎是无瘴不成诗。但当李纲获赦返回内地时,他沿途所作的诗文尽管也还提到瘴,但数量明显少了很多。具体提到的只有三处,一是返至雷阳时,诗曰:“风烟萧瑟黄茅瘴,山路崎岖赤脚蛮。……万里得归辞瘴海,三年奔命厌征轩”。之后是在北流时,“宿瘴须寒压,消愁欲醉逃”。其后是他回到广东循州之时,他写的几首诗都有。如称“峤南瘴毒地,乃尔气候清”;“只愁青草黄茅瘴,敢意好风佳月天。山顶蒙蒙遮薄雾,江心跕跕堕飞鸢”;“深入循梅瘴疠乡,烟云浮动曰苍凉”。
对比两位谪宦在不同时期所作的诗文,便可发现具有相同的规律,即在赴贬谪地途中,所作诗文中涉瘴较多,返回内地时所作诗涉瘴较少。似乎没有研究者认真考虑过,在短短的三年左右时间里,何以会有如此变化?再就是两人在岭南地区的返程路线大体一致。如在北流与藤州,何以会出现一人称有瘴,另一人则绝口不提的现象?这些都说明,判定一个区域是否有瘴,主要还是经历者自己的内心感受不同。且诗文中提到的瘴,多为泛指,或重述前说,甚至只是自己不满情绪的宣泄,是根本不应该用做判定某一区域是否存在瘴气的依据的。但一些研究者却只注意到诗文中有瘴的一方面,却有意无意地把无瘴的另一方面给忽视了。
笔者认为,在瘴研究中,之所以在征引史料时会产生顾“此”失“彼”的现象,当然与研究者持有的先入为主的思维取向有密切关系:为了自圆其说,只好对史料有所取舍了。
二、瘴研究中存在的逻辑思维矛盾现象
不可否认,当今以边疆地区环境史为视角的瘴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人们正确认识边疆地区环境变迁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考。但由于不少研究者在研究中,带有一定的先人为主的思维取向,对材料采取有目的的取舍,最终导致研究过程中,常出现逻辑思维上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现象,甚至得出的很多结论经不起反证,这是颇为引人注意的。
1 因果关系的错位
关于“瘴”的产生原因,不论是从史料记载看,还是从近来研究者得出的结论看,其因果关系均明显存在错位的现象。从史料记载看,最初的瘴,是指自然界存在的一种有毒气体。之后又演变成为一种医学疾病上的瘴。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瘴,其产生的原因,按史料记载,多因气候炎热、潮湿之故。如在岭南地区,《后汉书》卷24《马援传》称“下潦上雾”,唐人刘恂《岭表录异》卷上载“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宋人周去非也称岭南“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曰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记“广右石山分气,地脉疏理,土薄水浅,阳气易泄,顷时晴雨叠更,兼之岚烟岫雾,中之者谓之瘴虐”。其余南方地区,起瘴的成因基本相同。然而,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如以自然气候而论,尽管岭南、西南各地部分地区地处热带、亚热带,多数地区气候炎热,但气候是受海拔高低、季风影响的,并非所有地区一年四季皆是炎热。古树参天的山区与海风吹拂的海边地区,气候其实还是较为宜人的。如岭南的桂林,山青水碧,杜甫有诗称“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融州,“气候与荆湖不殊”;钦州,“早温,昼热,晚凉,夜寒,一曰而四时之气备”。广东的肇庆府,气候“隆寒盛暑,与中州不相远,但晴则暖,雨则寒”;连州则被称为“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0;琼州,气候“夏不至热,冬不至寒”。至于云贵高原,因为海拔较高,年平均气温较之岭南,还要低些。如一些史料所载“云南最为善地,六月如中秋。……四季如春”,可能并不能代表云南全省的气候状况。但海拔较高的云南北部地区平均气温较低,也是事实。丽江、永北、鹤庆等府、州,飞雪严霜现象时有。即使在滇东南的广西府,“虽盛夏,雨即清凉”,师宗州则“气候多寒,冬则大寒”,各地气候也有明显差异。但仔细分析史料对瘴的记载,却发现瘴的有无与气候并不完全相关。唐时桂林。气候宜人,但在一些史料中记载是有瘴的。至于贺州、融州等地,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瘴的记载;钦州一带,尽管属海洋性季风气候,还是重瘴区;至于桂西地区,“邕州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前述之气候多寒的师宗州,每年四月至九月多瘴。更为重要的是,据竺可桢先生研究,我国历史气候自宋以来逐步变冷,至明清时为我国气候最为寒冷的时期,1400—1900年间,还被称为明清小冰期。受此大势影响,广西气候也呈变冷趋势。作为边疆省区的云南亦同样受到影响。令人奇怪的是,从史料记载看,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多,这显然是与气候炎热与否无关的。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当地人类活动不断增多,对瘴的问题发现较多,记载随之增多了的缘故。然而这必须要考虑到“瘴”本身所具有的“剧毒”特征,以及史料所记载的遇瘴九死一生的描述,大量的陌生人口到达瘴区后,必然会伴有较高的死亡率。应该说,清康乾时期是汉族人口向西南、华南等边疆地区迁移的高峰,但至少在这一时期所修撰的地方文献上还找不到这样的记载。偶尔发生的一些导致人口死亡较多的瘟疫,并不是发生在瘴气弥漫的原始林区,而是汉族人口大量聚集,林木遭到大量砍伐,开垦过度,瘴气没有产生基础的城乡地带,因而这些瘟疫是不应与瘴疠相等同的。同时还需思考的是,人类对于环境是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的,对于危害生存的环境,总会本能地选择逃避。又怎会常年不迁以慢慢适应“瘴气”?从记载看,没有当地居民大量外迁的记载,相反是移民不断进入。
一些研究者根据田野调查还认为,瘴气一般产生于气候炎热的低海拔地区,而在气候寒凉的高海拔地区,瘴没有产生的条件。因而瘴气成为影响民族分布的重要因素。称“在低海拔瘴气产生区聚居的民族主要是傣族,还有部分哈尼族、基诺族、壮族、苗族等。很多民族如景颇、阿昌、彝、回、汉、傈僳、拉祜、独龙、怒、德昂等则居住在高海拔的、寒凉的无瘴地区”。事实上,根据史料记载又有“冷瘴”(又称寒瘴、雪瘴)存在,作者也认为这是因气候过于严寒,或者是常年积雪不消而产生,主要产生于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这就让人难以明白,瘴的产生与海拔高低究竟有无因果关系?再者,即使不考虑高海拔地区的“冷瘴”因素,居住在高海拔区的民族也不可能不下山与其他民族交往,过封闭的生活,他们下山也同样会接触到所谓低海拔区的“瘴气”。事实上,分布在低海拔“瘴”区的民族人口数,远比分布在高海拔无瘴区的民族多得多。
总之,从现有研究成果对瘴的产生机理解释看,与气候并无紧密关联度。在边疆地区,气候炎热地区有瘴,气候严寒地区也有瘴。不可否认,现在对瘴的研究,成果是有不少,但瘴到底是因何产生的,至今仍莫衷一是。
也许是意识到瘴气的炎热气候产生学说存在明显的缺陷,故在古代即有人又将之归结为自然的地形地貌因素以作补充,所谓地形闭塞,空气不流通,或是森林密布,空气不通畅,郁积而生瘴气。如宋人周去非又称“尝谓瘴重之州,率水土毒尔,非天时也”。清人称“瘴疠之气,则山泽为之,非气候之过也”。闭塞的地形是致瘴的因素,明人称“岭南群山四固,故广西多瘴”。这一说法,也是得到很多研究者认可的。如一些学者论述云南腾越等地的自然环境时,称“腾越位于高黎贡山之西,……未深入开发的河谷低地山区、平坝区,地处极边,进入的汉族人口相对较少,动植物数量及种类保存颇多,自然生态环境较为原始。这个山泽之气不通、阴阳变态各异的环境成为瘴气孕育的温床”,所依史料即为光绪时刘毓珂等纂修的《永昌府志》卷2《天文志·气候》,当中有“大体山太高,水太深,则山泽之气不通,郁蒸而为瘴”这样的文字记载。众所周知,在岭南与西南广大地区的低山丘陵、平坝地区,适宜开垦的耕地主要集中于此,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古代,人们是不可能舍弃耕种条件较好的坝地,而率先去开垦陡坡山地的,因而平坝地区历来是人口的聚集之地。后来迁入的人口,只有在平坝地区没有容纳能力之后,才不得已向耕种条件相对较差的山区迁移发展,这也是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尤其是在桂西的左右江流域与红水河流域,岩溶广布,石山高峨险峻,石厚土薄,山上难以开垦,其间的低洼地,即为溶积平原,地下伏流多从此涌出地表,流经其间。因便于生活、灌溉,同样也是人类聚落的首选地,古代“蛮夷”所居之“峒”即此。如存在此种严重危及人类生命的剧毒的“瘴气”,人又如何生存?事实上,广西及西南地区有人类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坝子、“蛮峒”哪一个不是山泽之气不通之地?而从史料记载看,瘴气的分布地与山泽不通并无必然关系,在濒海地区,地势低平,四周没有山脉环绕,且常年受到海风吹拂的廉州、高州与琼州等地,皆为瘴气,且为史料记载的重瘴区。
2 忽视史料记载本身存在的逻辑矛盾,以致研究结论也无法避免逻辑矛盾
关于瘴的产生原因,尽管众说纷纭,但无一例外地,都与森林茂密有密切的关系。不论是从史料记载,还是从研究者的认识看,瘴多产生于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之中,即常称之“山毒”。一些研究者也认为古代生态系统高度复杂,在各种生物、动物等相互作用中,就会产生毒害人体健康的瘴气。问题是既然瘴气多产生于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之中。那些弥漫的瘴气如何能被人发现?是那些史料记载的作者亲身经历的吗?既然瘴气潜藏于原始森林之中,古代行军打仗的士卒,为何会有高达十分之五左右的死亡率?他们的行军征战难道主要不在城镇、聚落附近,而主要在林海中行军而感染的吗?
3 一些研究推论明显与生活常识、已知的科学原理相悖
由于史料记载的瘴,具有极大的神秘感与恐惧感,且多混杂,向呈众说纷纭之势。一些研究者在研究瘴的产生原因时,除不对史料本身进行辨析外。还依据一些没有仔细考证过的史料,进行推断,致使相关推论明显有悖于生活常识与科学原理。如在岭南及西南地区,不少学者对瘴的产生除了气候炎热这一因素外,还从瘴的孽生环境人手加以考察,试图探寻瘴的产生与自然生态环境中植被、动物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植被状况而言,边疆民族地区开发滞后,地广人稀,生态环境良好,地表植被十分茂密。对此,史料多有描述。其基本特征是:凡有瘴之地,必为树林翳密之区。如宋人周去非称广西“初春百卉荫密,枫槐榆柳,四时常青。草木虽太,易以蠹腐”;明代广东“郡邑之依山者,草茅障翳,炎气郁蒸,故为害也”;滇东南的广西府一带,“山峻、水冽、箐密、林深”。等等。从现有学者们根据史料得出的观点看,瘴的孽生原因无非有如下几方面:一是树叶枯腐,产生有毒气体,甚至渗出有毒液体,污染水体。宋代即有这样的记载,称广西“昭州有恭城,江水并城而出,其色黯惨,江石皆黑”,对此学者深信不疑。稍具科学常识即知,在没有工业污染的宋代,江水如墨,流染江石,其上游地区需要有多少枯枝落叶集中发酵沤腐?何况河水颜色变化毕竟与所在流域的水土流失程度相关,土壤颜色才是影响河水的最重要因素。在植被茂密,缺乏黑壤的恭城,为什么看到的江水是黑色的?这个答案恐怕只有周去非本人才能回答了。金强、陈文源在《瘴说》一文中,也认为:在炎热气候,山峦叠障,树林茂密,空气不通的环境下,植物落叶易于腐烂,产生的岚雾瘴气郁结,不能稀释,最终为害。按此逻辑,原始森林地区,树荫浓密,落叶相因,均具有产生“瘴气”的环境基础。其实根据现有科学实验得知,植物树叶在有氧环境腐烂后,可以产生二氧化碳,如果周围有产甲烷菌的话就会产生甲烷,就是俗称的沼气。二氧化碳与甲烷对人体确实是有危害的,前者主要是刺激人的呼吸中枢,导致呼吸急促,空气中超过一定浓度后,可致人呼吸困难,甚至死亡。后者对人体无毒,但浓度过高时,会使空气中氧含量降低,从而使人窒息。问题在于如果原始森林中空气不通,两种气体浓度必然不断升高,单位含氧量必然不断降低,不仅人类无法生存,就是所有生物也缺乏生存的基础。更何况南方热带、亚热带自然界中,植物以常绿植物为主,落叶只是一小部分,同时自然降水与地表的浸水,也会对树叶腐烂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气体起到一定的稀释作用,从而保持天然的生态平衡,为各种生物生存繁衍创造条件。与当今工业社会产生的温室气体相比,古代社会原始森林中产生的少量温室气体,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实上,原始森林地区,动植物种群也是最丰富的。二是缘于有毒植物。这在史料中也有相当多的记载,如周去非说广西“地产毒药,其类不一,安得无水毒乎”。一些学者遂根据自然界中的植物中,存在不少有毒植物,如断肠草、金钢纂、毒蘑菇等,认为这些有毒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释放剧毒气体与液体至自然界中,从而产生瘴气。事实上,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有毒植物,远比这要多得多。古代医书、植物学著作均有大量记载。但要形成危害,肯定要有一定的生长密度与一定的生长面积,其挥发的有毒气体与流出的毒液才能达到危害人的浓度。排除人为因素,自然界中是不可能只存在单一有毒植物或有毒植物聚集情况的。不然,就不是生态平衡了。从动物生态学看,边疆地区开发较晚,地广人稀,植被茂密,因而成为动物的乐园,动物种群十分丰富。也许是为了完善瘴的产生学说,古人又常归因于一些动物身上,这在古代史料中亦有不少记载,所谓的蚺蛇瘴、蚂蝗瘴、孔雀瘴、蜥蝎瘴、蛤蟆瘴、鹦鹉瘴等。致瘴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动物的粪便污染、呼出的有毒气体污染空气。如史料记载哀牢山附近的毒溪,称“或谓夷多孔雀,其粪遗归溪流,乃至此”。一些学者遂据此认为有毒动物及其分泌、排泄物散发在河、湖、潭、泉、溪、涧等水流及其经过的土壤岩石、植物花草上,繁生了众多含毒的微生物,空气、水源及阴暗潮湿处遍布了众多毒素,在气温适宜时发生各种生物化学反应,产生对人畜伤害更多的瘴毒素。应该说,即使完全排除自然界的分解作用,某一种动物分泌出的毒液,排泄的粪便,要对人类形成危害,肯定要有相当的量的。但从已有的一些科学实验可知,提取的蛇毒常温下易腐坏失去活力,酒中的酶也能破坏蛇毒。而且它们的毒液主要是通过血液作用,破坏动物的神经系统、呼吸系统与血液循环。正常情况下,动物受到其攻击、咬伤,才会产生中毒现象。至于孔雀,作为南方分布的一种鸡形目中的大型鸟类,现在的科学也已证明,在养殖过程它有啄食自己羽毛、粪便的习性,其胆汁有微毒,而传说中的“孔雀胆”虽是一种剧毒药剂,但并非孔雀的胆。明代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49《禽部·禽之四·孔雀》中称“山谷夷人多食之,或以为脯腊,味如鸡,能解百毒”。
又从瘴的产生时节看,一些学者力图摆脱传统文献古籍的束缚,尝试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采访民族地区群众,以求取得研究上的突破,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过分注重现场口述,而不能深加思考,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仍然无法摆脱矛盾的状态。如通过调查瘴区群众,一致认为:瘴气主要存在于春季、秋季、夏季。冬季是瘴气收敛及隐藏期,也是非瘴区民众到瘴区生活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最佳时期。姑且不论采访对象的出生年代,与瘴气存在的时间是否相符,稍具生活常识即知,在四季分明之地,冬季绝非最佳的农作季节,除了一些采集活动,很多经济活动都难以在一个季度完成的。更何况瘴气如此之毒,遇到瘴气九死一生,他们又是如何提前知道并有效地规避的?
也许一些学者认为,南方生态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与古今之间的巨大变化,不能用现代的“科学分析”来证明,但如果不能通过已有的科学实验去验证,瘴气研究只能从神秘走向神秘。
三、研究结论的局限性
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分析问题。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虽然迄今为止,众多学者对瘴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从现有的许多研究成果看,其得出的结论也还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
1 瘴为什么在魏晋之后才横空出世?
根据史料记载。“瘴气”作为南方地区自然界中存在的对人类生命有巨大危害的有毒气体,为什么在魏晋前的史书无载?虽然说史学研究说有易,说无难,但中原人士进入岭南,至少可以追溯至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代。其后中原汉人的足迹更是遍及海南、岭南,如果自然界中存在“瘴气”,不论以什么形态、什么名称出现,在史书中都应有所反映。对此问题,有关研究还很薄弱。
2 “瘴”概念本身的模糊性
瘴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无疑是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由于史料记载不仅杂乱,且多柢牾。原因在于记载者记载时多凭自己的主观感受,或并未亲身体验,或道听途说,或沿袭前说,以讹传讹,有些根本就是文学上的语境表达。这样,就造成“瘴”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可以说,“瘴”自从出现历经近二千年,后人不断给它增加了许多符合其时代的“新”内容。一些研究者没有对史料进行详细的梳理与辨析,往往将其混为一谈。这样,在论述时难免会出现自说自话的局面。笔者以为,考虑到史料对“瘴”记载的复杂性,需要根据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朝代、不同领域加以区别开来,分别进行研究。如岭南地区的“瘴”与西南地区的“瘴”是否相同?汉唐时期记载的“瘴”,是否与明清时期的“瘴”完全一样?尤其是医学层面的“瘴”与文学层面的“瘴”更是应该严格加以区分的。即使是医学层面上的“瘴”,不同区域之间,环境不同,史料上的“瘴”所指可能也不一样。在一些地方可能是指“疟疾”,在另一些地区可能是指“伤寒”。需要细加思考的是,象“疟疾”、“伤寒”等疾病,不独南方民族地区有,北方也都存在,为何在南方则称为“瘴”了。由于现有的一些研究常常是把它作为一个对象来加以研究的,就难免出现你所述之瘴与我所述之瘴可能并非同一概念的现象。虽然名称相同,然表述的内容各异,讨论起来,自说自话也就不足为怪了。
3 结论的现实矛盾性
可以说,从史料记载看,瘴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就已消失了,瘴正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历史名词。但为害甚烈的瘴是怎么消失的?原因何在?应该说这是边疆地区环境史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近来不少研究者对瘴作了研究,但对瘴的产生原因研究多,对瘴消失的原因研究严重不足,而且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医学知识普及与文化原因。张文认为:随着近代医学知识的普及和中国文化优势意识的减弱,瘴气与瘴病的概念才渐趋消失。二是人类的生产开发活动影响。龚胜生在《2000年来中国瘴病的分布变迁》一文中认为,考察“2000年来中国南方的土地开发史和瘴域变迁史,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显然言下之意,是认为人类的开发活动,最终导致了瘴气的消失。对此,周琼也持相似的观点。她认为:随着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深入开发,以及医学疾病学的发展,瘴气存在的自然生态基础逐渐消失,瘴气区域随之发生了变迁。此外,尚有一些学者认为“瘴气由气候和环境的恶劣而产生,而最终又随着气候的变迁和环境的改善而逐渐地消减、消亡”。三是微生物医学的进步。一些医学工作者从传染病病理学的角度,也对瘴的消亡作了探讨,认为:看不见的“瘴气”从传染病学中消失。主要是西方科学家通过检测到可以目证的病原微生物的结果”。
在以上诸说中,第一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历史时期汉族的文化优势意识而言,它不会只针对某一特殊区域,对周边各族、各国,实际上也是持有的。历代统治者长久不懈地推行“以夏变夷”政策,改良民族地区的社会风俗与文化,本质上也是出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民国年间仍然存在,广西的新桂系当局统治时即曾组织人员编辑刊行过《改良风俗的实施》一书,对改良风俗的方法与途径提出了若干建议,并附有《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这些“规划”其实也是文化优越感的体现形式。更何况,出于统治与政治上的原因,政府层面的文化优越感消失了。民间层面的文化优越感并不一定随之消失。因此,仅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解释“瘴”的消失,是不够的。
如果瘴是一种疾病,它的消失肯定与医药技术水平提高密切相关。而不应该把它归为环境变迁因素。故在上述诸说中,第三种说法是有较强说服力的。论者把“瘴”作为一种疾病来看待,通过科学手段对疾病的病原体进行检测,发现了其间的致病原因,并找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弥补了传统中医学认识上的不足,引导人们把“瘴”从传统中的无形不可视,向现代有形可视方向进行思考,是大有裨益的。不足之处在于,传统的“瘴”包含的内容过于庞杂,并非医学一个领域,更有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的内容,只从一个学科解释其消失原因,并非完整。
从现今的研究成果看,认为人类的开发活动是“瘴”消失的原因明显占据多数,但这一说法也是最为矛盾的。持此论者,主要是缘于头脑中的固有思维取向作用,盲从所谓的史料,固执地认为原生态环境下是瘴产生的原因。原始森林是瘴产生的原罪,因而认为只有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砍伐掉了森林,破坏了这一生态原貌,瘴的存在基础才不复存在,实际上所持的就是一种“人进瘴退”的思维。岭南、西南民族地区自古即有土著居民在生息繁衍,从事开发活动,为何非得汉族移民进入之后,才能开发,并战胜瘴气呢?一些学者在经过田野调查后,认为:瘴气不仅危害外来人群。也对长期在本地生存的土著民族有巨大危害。瘴气使瘴区民族人口长期徘徊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数额内。这不仅与原来史料所述的土著人对瘴有适应能力相左,而且违背了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就是决定一个区域人口多寡的是环境容量的大小,以及受生产力水平、卫生习惯、医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沙漠地区,人口肯定聚集在绿州,那里人口的多寡肯定与绿州的大小、肥沃程度密切相关。而在山地,耕地有限,生产力水平有限,不可能容纳过多的人口。如在广西金秀大瑶山地区,在环境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当地的坳瑶为了维持本民族的生息,“在没有任何避孕措施的前提下,为了限制人口的增长,多生养的孩子就要通过人为的方式将其杀死,有的用水溺死,或者用毛巾闷死,也有的父母把婴儿挂到树上饿死。……除个别较为富裕,田地稍多的家庭,在父母高兴之时可以留三个以上小孩,其他的往往会毫不留情地把小孩杀死。”庞新民在《两广瑶山调查》中,也明言“因瑶山可耕种土地有限,对于生育子女皆极端限制,故瑶人以子女各一为合意,至多者二子一女,因子女过多,将来成人之后,无从安插也”。正是基于环境容量有限这一严峻现实,当地瑶族才有强烈的控制人口的自主意识,并形成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使本民族的人口数量始终保持在与当地环境容量相当的水平。而在平原地区,环境容量较大,生活在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亦较庞大。广西的壮族就是典型,即使是号称一年四季皆瘴的左右江重瘴区,壮族人口在很长时期内都远远多于汉族。可见,认为瘴气的存在导致人口发展缓慢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四、余论
综上,笔者以为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土著居民,或缺乏本民族文字,有的民族有文字,但较晚。而有关“瘴”的记载,主要是以汉籍史料记载为主的。目前的有关瘴研究,也主要是依据这些汉籍史料记载。对于经常生活于瘴区的土著居民而言,没有他们的话语,要对瘴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这些土著居民,祖辈生活在瘴区,与瘴接触机会较外人多,对瘴的认识也较外人深刻。少数民族自己的记载才是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材料。一些学者已意识到汉籍史料记载的不足,开始走出书斋,深入民族地区调查,这是可喜的一步。至少是从研究上开始倾听少数民族自身对瘴发出的声音了。但迄今为止,从少数民族流传的歌谣、故事、民间传说以及有关古籍记载中,还鲜有这样的记载出现。这是值得研究者充分注意的。
有些学者认为,瘴是对南方陌生环境的人而言的。事实上,迁人“瘴区”的,不仅有汉族人口,也有少数民族人口。以广西为例,瑶、苗、侗、回等族,皆为历史上从周围省区迁入,其迁移、生息也是在瘴区进行的。但在这些民族的有关典籍、口传歌谣故事中,同样少有瘴的记载。
既然瘴气的产生与炎热气候有关,那就不可能只会局限于中国的国境线内,也需要把目光放大至越南、老挝、缅甸等国之内,看看他们的记载是什么样子。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限于篇幅,笔者不打算作进一步的展开。
由于边疆地区地理上与内地相隔较远。内地人士了解有限。在历史上,看不见,摸不着的“瘴”,往往又成为一些人谎报军功、推诿失败责任的借口,因而在记载中难免夹杂着传说、流言传播的成份,史料本身虚妄、荒诞与真实参半。从“瘴”自身的含义看,也有一个由“气”向疾病发展,即由无形向有形发展的过程。但在文人墨客的渲染下,呈现出有形与无形反复纠葛的特征,并表现出很强的神秘性。对瘴的研究,不论从哪个角度展开研究。最终还需回归本位,首先要对其史料进行全面的辨析与梳理,找出其间的内在联系,根据相关学科理论从不同学科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笔者以为,既然周去非已明言“南方皆病,皆谓之瘴”。那从疾病的角度去加以研究,或许更能接近历史真实。但不论瘴是病是气,其消失主要与人们对瘴区的了解增多有关。随着内地对边疆民族地区了解的不断深入,原先虚妄的成份,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人们对原先所说的“瘴”,已不再迷信。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现实的生计问题,看不见摸不着的瘴自然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了。
——基于扩展的增长核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