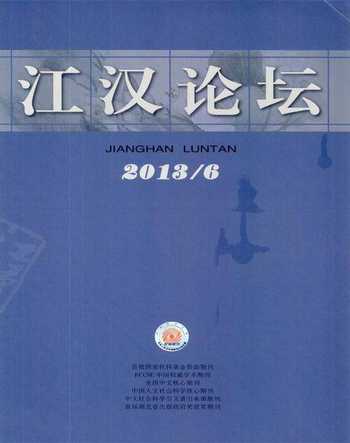中国符号与荣格的整体性心理学
范劲
摘要:荣格对于道教和《易经》的兴趣,体现了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的一种潜在趋势,即由孤立的个体分析转向宇宙性关切。本文通过细读荣格的两个重要文本,阐明荣格如何将中国精神融入心理学,以激发新的意识形式的过程。而在“道”、“金花”、“阴阳”等象征物或《易经》卦象中,他也经历了自身的无意识的意识化,自我在中国符号导引下得以超越传统的西方概念框架,在和新的当下世界形势的协调中,领悟整体性之大道。
关键词:整体性;心理学;道;逻各斯;共时性
一、心理学和汉学的接近
荣格将中国智慧称为“中国心理学”,这种不自觉的误用包含了一个宝贵的启示,即技术性、分析性的心理学的人类学化乃至宇宙化的可能。只有从人作为宇宙一分子,且和宇宙分享同一节奏韵律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个体心理的成因,这一点也正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所蕴藏的革命倾向。
从意识形态上说,心理分析以恢复被排斥意识为己任,东方正是西方历史上最大的被排斥者。从内容上说,东方的冥想即深层无意识的涌现,天人感应即人类意识中最深处的先在联系,构成了人性的无意识基座。按照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说法,儒家无为和无言之教的秘诀就在于,通过有意识和超意识的连接、配合而达到对人人心中的下意识的影响,因为超意识和下意识本来就同沐于宇宙潜流,两者不过是天与地的另一称谓而已①。
1920年,在沙龙哲学家凯热林的智慧学派开幕式上,荣格认识了卫礼贤,1923年又邀他到苏黎世讲演《易经》。荣格对卫礼贤评价极高。荣格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处境孤立,经常引卫礼贤为支援。而实际上,这是一个由互文而达成的话语策应:卫礼贤希望由西方无意识研究强化“中国”理想的合法性;反过来荣格感到,“中国”实践为他的意识模型提供了佐证。荣格和卫礼贤最重要的相通之处,即对于“异”的委身。一般正统学者拒斥东方智慧,是因为占卜等神秘观念同科学信条相抵牾,可精神分析恰是一个极开放的学科,愿意聆听和理解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荒诞不经的事情。
集体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暗示了两种解释学原则。如果说弗洛伊德是科学的、分析的,荣格就是浪漫的、综合的。像谢林那样,荣格视精神和物质为一体,在他的《艾翁:自性的现象学研究》(1951)中,清楚阐明了心和物相互参与、相互循环的整体性原则。②在《论无意识心理学》(1917)中,荣格称自己的释梦方法为“综合建构法”,以区别于弗洛伊德的“分解简化法”,后者建基于“因果还原程序”,“将梦和幻想分解为某些记忆成分和某些潜在的本能过程”,却不适用于集体无意识的意象。③弗洛伊德发现了个人的梦境。而荣格回溯至一个更广阔的语境,将弗洛伊德的原理由封闭的、笛卡儿式的语言系统发展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学。由此,他体现了20世纪人文科学的一种潜在趋势,即由孤立的个体分析转向宇宙性的关切,在委身他者的过程中实现一种整体性。
这正是东方智者走人西方知识分子视野的恰当时机:人和宇宙万有的和谐,是他们一致的渴求。荣格坚决不同意把中国思想看作形而上学,而主张作为心理学来对待,因为中国古代智慧是完全现实可触的形态,注意力也全在内在性一面,而心理学对荣格来说。就意味着可体验的、真实具体的内在性。荣格倾心于中国的整体性精神,乃基于一种新的文化意识。过去考沃尔德等人论荣格所受的中国影响的论文。往往忽视了卫礼贤的中介作用④。造成疏漏的原因和方法论有关,他们的考察重点落在了荣格对中国思想的接受,而非他的二度符号化操作本身。这一操作的基本前提,正是卫礼贤对中国文本的精神化。
二、“金花”的秘密
在卫礼贤译作《金花的秘密》(1929)中,荣格的“欧洲评论”占了近半篇幅。卫礼贤的底本为中国密教团体翻印的《长生术·续命方》。他的翻译本身已是一种选择性的符号转换,将成分芜杂的中国养生秘笈化为一个普遍性的精神化文本。荣格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心理学化,熔铸成一部全新作品,这才是《金花的秘密》畅销一时(前后共5版)的真正原因。显然,这里并不涉及误读与否的解释学问题,而是图像生长为意义、胚胎展开为理论的具体过程。
符号化的依据对荣格来说是本体论的,集体无意识概念先验地决定了中西互通的可能。在《金花的秘密》中,他再次强调:“……心理也拥有超越所有文化和意识差异的共同基础,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而卫礼贤的依据看来是历史性的,他声称,吕祖的改革已将炼丹术符号变为心理过程的象征,密巫之书顿时具有了心理学和宇宙论意义。他也相信,金丹教的形成和景教有着密切联系,故吕祖的教导和基督教如此相似。然而说到底,无论崇尚神秘的荣格还是前青岛传教士卫礼贤,都有一种潜在的宗教性冲动。宗教作为无限憧憬和真正自由的象征,意味着整体性的实现,也把东西方、汉学和心理学连成一体:整体性的和谐是中国长生术的秘密,也是治疗现代人精神疾患的最终药方。
在卫礼贤极具个人特色的译文中。中国养生术已演成一个典型的“施洗和重生”故事:中国圣人(吕祖)教导说,原初的整体就是道,道以魂和魄的形式现象化为个体。魂寓于目,是明亮的、轻清上浮的阳的力量,和“元神”相联系。魄居于腹,是阴的力量,代表身体和性的能量,和“识神”相联系。在自然情形下,能量由上往下流动,魂的理性能量为魄的激情意志所役,最终元精枯竭,归于死亡。禅坐修炼则是对生命过程施行“逆法”,通过内观反照,将阴或魄的性能量转化为阳或魂的精神力。生命力不像平常那样消逝,而是在内化上升的过程中孕育了纯精神性的生命体。这一新的自我就是“元神”,它制服了“识神”,标志着自我从尘世纷扰中脱颖而出,达于身心两忘之境。从纯精神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肉身消退、神体诞生的过程。从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来说,就是放弃对自我和意识的执著,唤出一个新的生命中心,亦即自性。
如何实现极端的心理类型之间的平衡,是自始就困扰荣格的问题,这一问题将他引向了中国思想,也说明他是由自身的轨道而趋近卫礼贤的。早在写作《心理学类型》的时期,荣格就十分关注“道”的概念。“道”是中国哲学中的统一性象征,即对立面之间的中点。荣格引用了多达十余段的《道德经》译文,对“道”的属性作了全面阐述。“道”就是“对立面的非理『生联合,有和无的象征”⑦,是平衡对立者的冲突的“非理性的第三者”,因为其非理性,故不能由意志的“有为”达到,而必须通过中国式的“无为”。荣格相信,“道”还带有些许的实体性,故而可以译为“上帝”。圣人和道合一,故能摆脱对立面的冲突,认清万物的联系变化,达到婴儿的纯真,获得天国的福乐。“道”就是人和自然、天和地、男性和女性的和谐无间。它逐渐发展为荣格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型意象。
卫礼贤用阿尼姆斯(Animus)来翻译中国字“魂”,用阿尼玛(Anima)来翻译“魄”。人死后,灵魂分为两部分,阳性的、较高级的魂向上升,归于神,阴性的魄向下沉,沦为鬼魅。阴阳、鬼神并无正邪之分,而是生命力的扩张和收缩的两种形式。荣格很欣赏卫礼贤的译法,因为它凸现了无意识的两大特征:人格和性别。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也是荣格的无意识中的两个原型人物,共同构成心灵的“内貌”。中国思想中阴、阳的法则,荣格同样不陌生,他的《心理学类型》提及:“根据道教的中心原则,道分为一对基本的对立者,阳和阴。阳代表温暖、光、男性,阴代表寒冷、阴暗、女性。阳也是天,阴则是地。从阳的力量中生出了神,即人的灵魂中天国的部分,从阴的力量中生出了鬼,即地的部分。人作为小宇宙,他是对立面的调和者。”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由他的治疗经验来说明,狂躁型男人往往具有女性特征,这一心理学事实印证了中国的“魄”的观念和他本人的阿尼玛概念,阴性名“阿尼玛”正好代表了男性意识的女性母型。而阿尼姆斯意味着女性中的男性母型,即是说,女性人格的本质恰是男性的,是一种较低级的精神/逻各斯。如果说,个人性的冲动成为阿尼玛的基础,则非个人性的群体的意见或偏见构成了女性心灵的原型阿尼姆斯。有人指责说,荣格将无意识人格化的做法。使心理学沦为了神话学,但卫礼贤转写的中文词的人格特征,支持了荣格的这个观点。荣格相信,只有最彻底地承认无意识的人格性,才能从一个更高的立足点将其制服,“制魄”无非是精神对阿尼玛的统摄。
荣格不但由中国文本汲取了新的神话资源,还得到了理论上的印证。《太乙金华宗旨》将“识神”和“魄”相联系,“魄附识而用,识依魄而生。魄,阴也,识之体也”。卫礼贤译为:“阿尼玛作为意识的效用附着于意识。意识依赖于阿尼玛而得以诞生。阿尼玛为阴,是意识的基体。”荣格由此得出结论,东方人的心灵建立在无意识的基础之上,因为他们把意识看作是阿尼玛的效果。而西方人总是将心灵等同于意识,即便是弗洛伊德,也仅是将潜意识看作意识的产物。反之,荣格不但坚持梦、神话、无意识的真实性,而且强调它们在人类心灵结构中的中心地位。
荣格进而建议,若要更清晰地揭示“魂”的理智德识的阳性特质,不如用“逻各斯”来取代卫礼贤的“阿尼姆斯”译法。了解了荣格的基本立场,就不难理解他这一修正的用意。在荣格看来。中国哲学建立于男性世界的基础上,不需要像西方的心理学家那样关注这一概念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女性心理。但是,心理学家必须考虑到女性独特的心理,他把“魂”译作“逻各斯”,原因就在这里。逻各斯的表达包含了普遍性存在的概念,是非人格和超越个体的宇宙原则。而魂正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和理性光芒,来自作为宇宙生成原则的“性”,在人死后回归于“道”。这样,魂和魄的区别就更明显了,魄是以完全个人化的情绪来表达自身的个人性的魔鬼,正体现了无意识的人格特征。也是通往无意识的桥梁。严格说来,“魂”对应于“性”(卫礼贤译为逻各斯),是区别于性的认识,故而女性中的阿尼姆斯作为低级的逻各斯就是无所联属的偏见,或者全然脱离了对象本质的意见。“魄”对应于“命”(卫礼贤译为厄洛斯),是联系、交织,联系的功能由情欲而实现,故男性中的阿尼玛就是这样一种低级的情欲。在荣格看来,魂和魄的区分成为了理性和无意识的区分。
修行的目的是重返于“道”。然而,“道”不可道,对于“道”的需要,其实是对于象征物的需要。对荣格来说,对立面的统一,绝非理性或意志的事情,而是一个由象征物表达出来的心理过程,故而幻想总是围绕一些抽象图像产生。如果将内心的幻觉描绘出来,就是东西方都存在的曼荼罗图形。曼荼罗是一种围绕中心旋转的图像,显示了一种走向中心的心理过程,在此过程中,自性将内在和外在领域同时纳入自身。荣格认为,发现自身的曼荼罗对于自性的生成至为关键,因为它就是心理整体的密码。《金花的秘密》巩固了他对于自性、曼荼罗的观点:金花就是一种象征自性的卓越的曼荼罗,在其中,无意识和意识得以统一。巫术的目的无非是要将注意力重新引到内在的神圣区域,这个区域是灵魂的起源和目标,包含了曾经拥有又一度失落的命与慧的统一。
宗教的核心也是要借助象征的力量重现整体性之大道。在荣格看来,对意识的独尊就是宗教上讲的对神缺乏敬畏。现代意识排除神祗(即原始图像),被排除的神祗只能以恶魔的形式出现,即疾病。而荣格所理解的耶稣是认识到并实现了大道的高尚者,“人子”就是新生的精神体一金刚不坏之身或金花。事实上,在荣格眼里,阿特曼、道、金花、曼荼罗、基督都是整体的象征,其作用都是将内在的自性和宇宙的生命原则相调和。在他的独特的耶稣象征中,东西方汇聚一处,由东西方的联结而达到人类意识的高级发展阶段。西方习惯于从外部来看待中心的象征,故而强调耶稣的肉身化,甚至耶稣的历史性,将其置于超越的上帝之下,而东方强调无始无终、内在于人的道本身。荣格相信,新教徒终将会让耶稣的外在象征内化于自身中,这一刻,亦是东方的神人、真人的心理状态真正为欧洲人领会之际。这实际上是在以整体性眼光塑造新的宗教意识。
三、《易经》和共时性
“道”意味着整体性。可是,“道”的具体运作形态、它和人的联系方式是怎样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易经》对于荣格具有了特别的价值。荣格很早就读到了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易经》译本,但他认为理雅各未能触及中国心灵的深处,惟有卫礼贤才敞开了神奇世界的大门。1923年,荣格委托他的美国女弟子贝娜司把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文转译为英语。英译本历时20多年才完成,出版后风靡一时,而荣格为1950年《易经》英译本而作的序言也成为他最有影响的文本之一。
1 《易经》:整体性之具体化
荣格眼中的《易经》乃是一个精巧的心理学系统,它组织原型间的互戏,沟通意识和无意识。它把占问者置于整体性的宇宙背景中,从而让现实情景的隐蔽意义得以凸显。在占卜过程中,占问者走出理性的自我,接受外在世界的偶然性——由揲蓍变易之数所代表——的侵入,又借助卦象重建和无意识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自我就让位于一个和宇宙相关联的自性,“个体化”的过程就实现了。换言之,《易经》成为包容意识和无意识的整体性的参照系,帮助个体在一个超越主客体的立场上认清自己所处的真实状态。
为了向读者形象地演示《易经》的效用,荣格把自己设想成是占卜者,《易经》则是他要叩问的人格对象。对于心理分析家来说。这个类似智慧老人的占问对象自然也是自性的投射。荣格占了两卦,但毋宁说,他讲述了两个关于无意识的故事,或演示了两次心理学的“积极联想”。荣格真实的目的,其实是要借助《易经》的象征模式去暗示整体空间中意识和无意识的具体交流情形。
首先,荣格要占问新译本在英语读者中的命运,他求得了《鼎》卦。按卫礼贤的精神化译解,此卦为文明和上层建筑之象,即精神性的营养。在荣格所得的《鼎》卦中,二、三爻为可变之阳爻,其意义对于吉凶判断尤为重要。《鼎》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荣格说,这是《易经》在示意,它包含了精神性营养,而妒忌者企图掠夺或毁坏它的意义,但终归没有得逞。《鼎》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卫礼贤评述道,这表明一个人受到社会的漠视,但只要坚守内在的精神财富,发挥作用的时机终将来临。荣格利用德文的构词特点。进一步缩短意识(西方)和无意识(中国)的距离。这里的关键是对“耳”的理解,卫礼贤译“耳”为“Henkel”,是“用来提起鼎之处”,贝娜司转译为英文“Handle”,而荣格有意识地改译为“Griff”,从而在当下语言系统中造成了一个具有增殖能力的“耳”的衍生符号。“Griff”不仅和德文“Begriff”(概念)、“Begreifen”(理解)相关联,而且经由拉丁文“Concipere”(放到一起,综合)可联系到英文“Concept”(概念)。这一符号是无意识和意识在《易经》的象征空间内协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协同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它来自无意识,因为它源于中文的语言系统,代表一种陌生的古老用具:它来自意识,因为它的生成受到西方概念系统的引导;这种引导性意识本身又出自无意识,即西方的语言习惯。荣格说,“耳”(Griff)就是鼎的可供把握之处,因此就是“概念”(Begriff)的本义,即人们关于《易经》的概念。概念随时代变迁发生了明显变化,以至于今天的人们不再能“理解”(Begreifen)《易经》。我们失去了卦爻辞的智慧的支持,无法在命运的沼泽中寻得自己的道路。美好的精神粮食不被理解,就如废弃的鼎无人使用,但终将恢复其应有的尊严。可见《易经》在抱怨自己遭遗弃的命运,但它对前景充满信心。五、六两爻中的“鼎黄耳金铉”、“鼎玉铉”,都意味着《易经》由新译本焕发新生,成为新的“概念”,因为较之于意识、理性的僵硬态度,《易经》和无意识的关系显然更为亲密,而现在的英译者也恰是一位女性,给予它母性(无意识)的关怀。荣格总结自己的故事说,应答者把自身看作盛食物的容器,食物用来供奉无意识的力量。无意识力量被我们投射为神明,是让它们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对个体生命发挥引导作用。《鼎》二、三爻变为阴,就生成了《晋》卦。《晋》六二:“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大母神或女性祖先在心理分析理论中代表着无意识,于是荣格将其转述为:女性心灵即男性的无意识原型,这意味着,《易经》即便被意识拒斥,也会受到无意识的接纳。
他的第二卦是占问自己作为评论者的行为本身,这一次得到了《坎》,六三为变爻。坎为水,为险,就是心理分析中的无意识深渊(精神病人的幻觉中往往有水的意象),荣格认为这正体现了他战战兢兢的危殆之感。可是危险中又含有希望,六三一变而为《井》。《坎》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人于坎,窖勿用”,《井》九三则为:“为我心恻,可用汲。”和《坎》中的水坑一样,井也指《易经》。井容纳了生命之水,但是人们没有适当的取水工具,即没有合适的“概念”(Begriff)去把握它。荣格说,这里仍是《易经》在言说自身,表明自身是生命的水源。《坎》描述偶然跌入水坑者的危险,他必须挣扎出来,然后发现那是一口废弃的旧井,为泥浆淤塞,但是完全可以加以疏浚使用。落入井中的人就是荣格,他陷入《易经》的迷宫,处境维艰,但终究领会到,这就是古老的生命之泉。
占卜意味着以外在程序压制主体的意识强力,让个体透过潜意识这一存在的共同深渊去同他者交流。故这里不是通常的文本阐释,而是借助图像重新获得和无意识的联系。
2 共时性:宇宙性联系的法则
《易经》体现了一种新的思维原则,那就是非因果性的“共时性”。真实世界由偶然或几率而非因果律所决定。面对这一世界,更高明的态度是对于情境的模拟。这种模拟把主体和客体、意识和无意识都同时包容在内。荣格相信,《易经》是中国特有的、无法为西方科学的概念所把握的科学,却更符合现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共时性原则”的概念,最早是他在1930年悼念卫礼贤的演讲中提出的。它成为荣格后期思想的一个关键词,用以说明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巧合以及心灵感应等超自然现象。他还将同一原理用于原型概念,原型在外部世界以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同时,还能在内部以心灵形态表现自身⑧。荣格认为,这种思想在欧洲自从赫拉克利特以来就消失了,仅有蛛丝马迹残留于西方星相学中——诞生于另一时刻的人或事。也具有另一时刻的特性。
共时性即整体性,即道,荣格说过:“我把道称为共时性。”共时性意味着:一种现象的出现只是从表面上看是某种物理性的因之果,根本上却由宇宙整体所决定;时间并非抽象的、死的媒介,而是一个有机的连续体。某一时刻已经内在地包含了一系列性质和基本条件,这些性质和条件可以在这同一时刻展开于不同地点。这种基于“时势”的共时性体现了生命的同构。《易经》的卦爻(原型)能和成卦时的具体心理情境相契合,原因即在于此。共时性是内在和外在相连结的关键。由于共时性的作用,原型才能被提升到意识层面,人格重心才得以由自我转移到宇宙性的自性。作为超越了物理性的因果联系的本体关联,它必然就是阴阳交替的“道”。共时性暗示,在理性的分析工具建立的因果网络之下,还有一个更深层、更宏大的操控网络。其作用无处不在,以同样强度、同样的不可抗拒性体现于最隐秘的角落,使得个体心灵哪怕最微妙的波动也是大宇宙的韵律的表达。这在先前的德国浪漫派那里成了自然和精神的类比的依据,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因为同源而可类比,这个可感而不可知的源头即荷尔德林所说的“存在之一般”。在后来的罗兰·巴特那里,就成了基于语言性(这不过是继“世界心灵”、“宇宙自我”或“道”的另一说法)的社会、文化、文学、语言学的同构性。《易经》的作用,不过是再次提醒荣格回到世界的一体性原则。如果真能以共时性思考。则精神病问题可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因为这就意味着人和自然恢复了往日黄金时代的和谐。
四、中国符号和精神分析学的自我超越
“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历来就是整体性的代码,因为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是天人合一、物我交融,西方人有时称为“宇宙主义”(高延、福兰阁),有时称为“文化主义”(费正清)。早在19世纪初。黑格尔就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文化所推崇的精神与自然的直接合一。但对他来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混沌,混沌来自于理性的蒙昧未彰,因为理性意味着主客体的严格区分。于是中国(连同印度)被贬为自然实体精神,被踢出世界历史的进程之外。然而荣格视中国整体为最高级的调和,是从混沌到有序之后的无序之有序。西方人为了一个主体性的有序,付出了从精神到肉体的巨大代价,只有进入同时包容意识和无意识的新的整体性,才能将撕裂的伤口缝合。
按照一种简单化的“后殖民”思维,荣格的中国符号或许仍然是西方的权力意识的产物,亦即西方为确认自我身份而设立的对立面。于是荣格也将被归于“东方主义者”。但这种解读的弊病在于,它把符号完全看成是单义的主体意识的产物,而忽略了符号象征对于荣格的特别意味。按照荣格的理解,象征之所以为象征,首先在于它是意识和无意识的合一,而非单纯的意识的产物;其次,它总是超出了单一意义,为多种意义的并存提供了空间。荣格所诟病于弗洛伊德的,是后者将梦、心理异常仅仅视为意识的产物,被遮蔽的真相的征兆,而他要求把梦本身看作更高一级的真相。它超出了理性认知的范围,却是意识得以形成的基础。真正的符号如基督、金花、八卦乃是“基于最早的人类梦境和创造性幻想”的集体无意识的积淀,产生于一个比意识形态、权力意识更为深广的层面。而文化的产生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符号来发展“异”的因素:“我们的意识的扩展不应以牺牲其他的意识形式为代价,而应通过发展那些我们心灵中与异域心灵中相似的因素来实现……”换言之,真正的中国符号处于比一切政治意识乃至可以探测的政治无意识都更深的层次上,它是整体性的集体无意识空间的隐喻。对于荣格来说,这一异域符号的引导作用无疑是具体而真实的。正因为如此,他才称中国精神为一个足以改变西方的传统世界图像和心理态度的“阿基米德点”。
荣格相信,治疗的根本就是生活本身。生活承认一切对立面,新的生活的开始就是对“如此之在”的承认。从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平衡来说,中国并非处于人类文明阶梯的开端,而恰是在未来。原始人完全依附于一些无意识图像(神祗),以此维持心灵的完整,同时却趋向于保守。更高一级的意识倾向于自治,并回过头来反抗自己的旧神,力求摆脱无意识的原初图像。现代人独尊意识,现代宗教的实质是“一种意识的一神教”,“一种对于意识的痴迷”,可是这种“傲慢”(Hybfis)也可能使人陷人失去本能的贫瘠状态,最终结果是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缚于高加索山巅,万劫不复。荣格说,这就是中国的阴阳转换、物极必反之理。中国人的高明之处即在于,从未脱离中心,从不摒弃悖论和对立面。卫礼贤强调,《金花的秘密》中的修行方法乃至中国的全部哲学,都立足于一个前提:“宇宙和人遵循同样的法则,人就是小宇宙,没有任何固定的藩篱将他和大宇宙分隔开来。……心理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因此。人从本性上参与所有的宇宙事件,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都和宇宙交织在一起。”因此,中国的“性”和“命”两个原则都是超越个体的。对于荣格来说,这就是关于中国整体性的权威看法,也是对他的整体性心理学最有力的支持。中国人视片面为野蛮,由天人合一的立场超脱了是和非、彼和此的对立,这正是《易经》以不变的宇宙框架,以各种原初的卦象包容天地间变化之深义。心理疾患者如果能被引导着超越一己的孤独与不幸,找到和整个人类命运相联系的方式,就会得到安慰。而意识和无意识、阳和阴的双重存在,只有借助符号、宗教、神话、艺术才能实现,心理分析则是这一存在形式的科学表达。由心理分析唤出的本能对智性的反抗,代表了西方文化在20世纪的巨大突破和对精神的重新认识:“……精神是某种高于智性之物,因为它所包裹的不仅是智性,还有情绪。它是一个方向,一种生命的原则,此生命竭力向超人的、光明的高处奋进。”
就心理分析所处的形势而言,一方面,形而上学在真实的生命之外设置一个无可经验的神性;另一方面,经验性的心理主义又走入另一极端,把自治的心理情结乃至神性通通归于机械的因果法则。荣格的心理学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既是形而上学又是经验科学,却模拟了真实世界的含混本相。似乎惟有借助中国符号,才能厘清这一切背后的真实意义,获得一个有效的解释框架——这就是“道”的总体框架和阴阳转换的宇宙流程。这种对异者的容纳却绝不意味着放弃自身的心理和感知传统,恰恰相反,越是忠实于自身在历史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潜意识,就越能同异者沟通,因为无论自身的还是外来的神祗。无论基督、佛陀还是罗马诸神都是集体无意识这同一渊源的投射。所以荣格说过。能否接受东方的异质思维其实是一个内部的事情。中国的启示不在于提供了什么具体的东西,而仅仅是展示人的存在之深化和丰富如何可能,指示人们如何达到宁静和自足。由此而获得从内部去影响事物的力量。
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出版后,批评者质疑他是否把两件从历史渊源和意识形式上南辕北辙的东西硬扯到了一处。然而,荣格、卫礼贤等中介者的具体经历表明,道和逻各斯的融合并非没有可能,因为无论东方的道,还是西方的逻各斯,都不是绝对不变的存在物,而是在无数次的引用和转述中随时变换更新自身,以便和当下世界形势相吻合,而推动这种变换的力量,就是人类共同的无意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