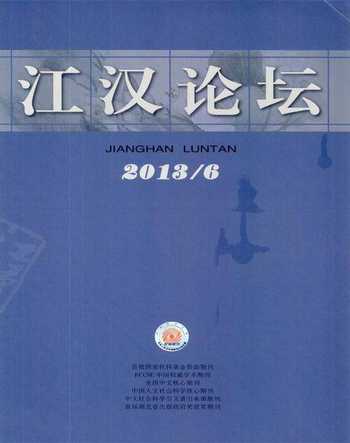论胡适对中国文论的科学化改造
夏宏
摘要:五四前后,胡适通过对中国文论的科学化改造,开启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转向的一条道路。科学方法论是胡适学术思想的核心,他对中国文论的革新主要在于将科学实证的方法论运用于中国文论,演绎与归纳并用,从而建构起新的文论框架,转换了中国文论的理论视野。但是这种单向性地从西方引入的学术方法,同中国的传统有着内在的差异性,以致胡适在对中国文论的改造中出现了冲突和偏差现象,体现为“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科学认知与审美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关键词:胡适;中国文论;科学方法论;实证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6-0122-05
在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进程中,胡适是一位核心人物,他破除了中国文论的传统思想标准,开启了以“科学方法”论证白话文学的合法性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方法论变革,将以直观、体悟、点评为主的传统文论之“术”转换到逻辑的、系统的、实证的科学化道路上来。学界对胡适将科学方法运用于文论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科学方法与考据的联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等方面展开①,关于胡适对中国文论进行科学化改造及由此带来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科学方法论意识的建立
对方法论的重视是胡适学术思想的核心所在,他对中国文论的改造集中体现在对科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运用上。其科学方法论意识的建立过程,可以分为留学前后两个时期。
在留学美国之前,胡适接受了晚清启蒙知识分子译介、转述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其中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影响尤甚⑦,前者传递了物种进化的科学观,后者启蒙了他的现代政治观和学术史观。但是,留学前胡适所受到的科学方法的影响是潜在的。
在第二个时期,即留学美国期间,这种潜伏的影响在实用主义哲学的直接教化下鲜明地显露出来,他在研习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觉的方法论意识。1911年,胡适在康乃尔大学从农学院转入文学院,改修哲学、经济和文学,也就是从自然科学转向了人文科学。1914年,胡适在“道”与“术”之间作出了选择:“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之言,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晚清以来,中国被迫向现代国家转型,启蒙知识分子对西学的研习、引进,立足于拯救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危机和思想文化危机,胡适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中寻求如何借西救中,其重心不在于研究西方现代思想的真理性何在,而在于如何将其拿来改造中国的社会和思想文化,有着鲜明的实用倾向。他认为科学的“三术”才是“起死之神丹”,同他对思想学术本就抱持的实用目的有关,对他来说,“有何用处”的价值意义远远大于“这是什么”的本体意义。可以说,胡适自此立足于中国的现状,从价值论的取向上来看待和吸收英美经验主义哲学中的方法论。
在初步接触杜威学说的1915年,胡适开始以实证方法来判断中西学术思想的正误,比如在8月15日的日记中他对“证”与“据”的差异进行了思考辨析,以实证的方法论为标准对中西传统上的权威思想进行批判,并进而以此标准对如何有效地应用西方思想作出了分析。他认为所谓“据”就是“据经典以明其说也”,而“证者根据事实。根据法理,或由前提得出结论(演绎),或由果溯因,由因推果(归纳):是证也”,“吾国旧论理,但有据而无证。证者,乃科学的方法,虽在欧美,亦为近代新产儿”,他依此而批评说:“今之言论家,动辄引亚丹斯密,卢骚,白芝浩,穆勒,以为论理根据者,苟不辅以实际的经验,目前之时势,其为荒谬不合论理,正同向之引‘诗云‘子曰耳。欲得正确的理论。须去据而用证。”显示出他推崇科学的方法,而不迷信于经典的内容。
直接受教于杜威之后,实证的方法论便逐渐成为胡适学术思想的中心。他在晚年总结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⑤在杜威实用主义学说的影响下,实证的方法论不仅成为胡适用以思想的形式,而且成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方法论与真理观在其思想中互为表里。1921年,他剖析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胡适本人的影响,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要在历史背景中探究学说与制度发生的原因,在评判标准上要“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也就是说任何学说和制度并非天生合理,它们在特定的历史中才有其价值;实验的方法至少有三个特性:一是“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是“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是“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⑥。对胡适来说。所谓“真理”都是历史的产物,没有经过实用和实证的学说只是假说;作为中国传统王道思想学说的“诗云”“子曰”和西方传统神学的《圣经》神言,在现时只能算作没有经过论证的“据”,是靠不住的假说。在思想学术上,若以这些没有经过证实的假说作为理论前提,只会得到荒谬的结论:在实用中,若这些学说思想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那么就是没有价值的。由此,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之本的圣贤之说,作为西方传统思想学术之本的宗教神言,在胡适这里都不能当作思想学术的合理根据。
在具体的学术方法上,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就是演绎和归纳并行,这是他从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中学习到的真髓,表现出科学观与方法论合一的特点,他说:“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研究一个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⑦简而言之,胡适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就是“假设”加“求证”,或者说是为假设而求证。
二、科学方法论下的白话文学理论
在认定理论的正误要以实证的科学方法来检测的前提下,胡适不仅用实证的方法来瓦解中国传统思想的合理性,也用实证的方法来看待西学在中国的实用性,所以他对西学中形而上的理念内容并不关注,只确信科学方法论是能够在实用中解决中国问题的,这便是他改造中国文论的思想之本。以此为根基。他用科学方法论来改造中国文论的路数,同粱启超从新民出发的政治现代性改造路数、王国维从绝对理念出发的审美现代性改造路数相并而行,又有着明显差异,他没有以哪一家西方学者的政治学说或美学理论为准则来改造中国文论,而是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来论证他的文学改良主张,倡导白话文运动,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同时,他对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提出了假设和求证,以“白话”为中心重叙中国文学史,建立起“白话”与“文言”相并列的双线文学史观。
一方面,胡适采用了演绎法来论证其白话文学观。在论证中,他以语言文字与现实的对应关系为准则,以“科学”的历史观——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前提。他认为:“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表情达意;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⑨而语言文字又是在历史中动态发展的,如果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那么旧有的语言文字便不能反映出新的现实。在晚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的事实面前,文学的语言形态必须相应地进行变革,“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非用白话不可”。
另一方面,胡适又采用归纳法来论证白话文学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于中国来说,早在明清白话小说出现之前,佛书的输入是以浅近文字来达意的,唐宋时期白话就入了诗词,至元代戏曲,几近言文合一,“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以元代为最盛”;于欧洲来说,但丁用意大利俗语取代拉丁文写作,路德用世俗德语翻译《圣经》,开辟德国文学的新路,“故今曰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曰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
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以“文言一白话”为双线,对中国文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重叙,提出了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主流和正宗的惊世骇俗之说,而论证过程就是对他所理解的“假设加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的运用。胡适将杜威的方法论分作五步:“(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简括起来,就是“质疑——问题难点——假定解决方法——对假定选择——证实或证谬”五步,在最为关键的“假设”这一步上,胡适持以文学进化论的观念,将文学史上不断发生着文言一致的白话文学现象视为中国文学进化的一面。这种假设还不同于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体变化说。而是以语言形态的世俗化为进化标准的。第一步的质疑是:中国文学到底是如何进化的?第二步的难点是:如何在正统的文言文学之外找到突破口?这两步都是为了引起“白话文学中心说”的假设。接下去,假定可以从朝代、文体、语言形态等方面来研究文学的变化,他用演绎法提出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可以代表时代精神,用归纳法将不同时代的俗语文学现象联结成一条完整的白话文学演进史。最后得出结论:在文言文学之外,中国传统文学中不仅有着白话文学发展的历史,而且是历史进化的自然趋势。这个结论意味着五四文学革命中的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文学进化的必然结果。在整个论证过程中,由于他的“假定”是要凸现出“白话文学史”,所以文言文学史这一脉只是作为与前者并行、对立的现象而被叙述的。
在对中国文学史的重述中,胡适将“历史是怎样”的问题转化为“历史应该如何演进”的论证,其中难免有偏颇和矛盾。比如若认定白话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那么为何直到晚清才会发生以言文一致为核心内容的文学革命呢?但是应该看到,评价胡适对中国文论的现代性改造,关键并不在其观点的正误上,他已经表明任何思想观念都只是历史情境中的假设,他假定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白话文学史的完整线索,并抬高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有意为之的,是为了对当时的白话文运动进行合法性论证。胡适对中国文论的革新在于文论方法上,他将科学实证的方法论运用于中国文论,演绎与归纳并用,从而建构起新的文论框架,转换了中国文论的理论视野。
胡适运用科学方法论而建立起来的白话文学理论,相对于中国传统文论有了断裂式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首先是思想资源的变革。中国传统文论的思想资源是农业文明背景下的儒、道、释思想,从中孕育出文以载道论、意境论、性灵论等文学理论;胡适引入了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背景下的科学理性思想,其中蕴含着人对自然、社会和自我进行改造的动力,同中国文化传统上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明心见性的整一性思想观大相径庭,这为中国文论的革新提供了思想动力。
其次是思维方式和文论方法上的差异。中国传统文论主要采用直觉思维和类比思维的方式,论者用感应、体悟来把握文学作品,寻求批评者和作家在感悟上的同一、批评和创作的融合,而不是将作家和作品当作异己的对象来进行解剖分析。胡适的文论引入了西学中理性分析的思维方式,不仅将作家和作品当作实证分析的对象,而且建立起了一套注重理性逻辑的推演方式。在文论方法上,胡适所采用的演绎、归纳法,同中国传统文论惯用的“体悟”式的批评大相迥异。
再次是理论术语的更新。在中国传统思想、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传统文论中的概念、术语大多取自对自然和人的描述,呈现出生命化、人格化的色彩,反映了生命和物象的感性特征。在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中,关键术语大多属于理性范畴,比如方法、经验、结构、形式、内容、制度、背景、进化、遗形物等,具有理性思维的抽象化特点,这些术语的运用,让中国文论的话语逐步走向了现代学科的理性表达方式。
三、文论科学化改造中的冲突
胡适对科学方法论的引入,目的在于改造包括中国文论在内的传统学术,使其发生现代性的转变,但是他又常常因为这种现实需要而有意误读中国传统学术的历史事实,比如他以西方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比中国传统朴学的方法,武断地认为:“科学上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甩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
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胡适就认识到,“现在,中国已与世界的其他思想体系有了接触,那么,近代中国哲学中缺乏的方法论,似乎可以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今天已经发展了的哲学和科学的方法来填补”,这就说明他那时就已经明知科学方法论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本来没有的,但是接着他又提出了这种“填补”所带来的一个大问题一“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国外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它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显露出胡适在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科学化改造时的矛盾心理:这种现代性改造是后发的、被迫的,会带来中国文化和学术主体性的丧失;但如果不进行这种现代性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就会在以西方为主导的“新世界”里消亡,这可以说是胡适一代学人的现代性焦虑。胡适提出以“中西互释”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如果用现代西方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西方的科学方法论是其现代文化整体构架中的一种系统理论,那么在单向性的输入中,必然会将中国传统学术纳入到它的体系之内进行改头换面的“手术”,而不是相反。林毓生认为胡适的文化综合论充满矛盾:“胡适有时也主张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应该加以综合。但这同样是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花言巧语的说法。如果本民族文化充其量只存在不如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其余都在摒弃之列,那么,这种综合能说得通,能实行得了吗?胡适提不出论据能说明杜威需要学习中国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以提高他自己的科学方法的理论和实践。既然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毫无裨益,那么他的关于综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建议,本身就是—个矛盾。”
这种矛盾与冲突体现在胡适对中国文论的科学化改造上,具体表现为递进的两个方面:
一是“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的矛盾。这一对概念是费孝通提出的,他这样界定它们:“在人类所知的范围里本来可以根据所知的性质分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化的伦理社会,其知识主要是维护这种伦理秩序的规范知识,比如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缘情说”和“言志说”这两大主流理论,看起来差异很大,但都属于规范知识的范畴,“情”和“志”都是在对社会伦理进行规范的礼仪纲常中展开的;胡适所认定的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中的“科学”,属于自然知识体系,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将自然物种作为实验考察的对象而非社会规范对象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胡适认为实用主义的实证方法就是进化论在西方现代哲学上的应用。“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判哲学上的问题,拿来讨论真理,拿来研究道德。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规范知识是在一种稳定的文化传统形态中发挥阐释功能的,比如从焦循到王国维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都没有脱离开文言文学的诗文传统,只是以文学体例分类来看诗、词、曲、小说在不同时代的相继出现;胡适以进化论的自然知识观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假定白话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再以举证、归纳方法展开论证,而不承认文言的诗文是中国传统文学主流的事实。实际上,他认为文学是像自然物种一样进化的。并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论证白话文学是对文言文学的进化。客观地说,胡适用自然知识范畴中的科学方法来重叙规范知识范畴下的中国诗文传统,是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事实不相符的。
二是科学认知与审美的矛盾。胡适以西方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元方法,将文学研究科学化,忽略了文学表达人生在世感受的审美特质,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学和文论注重人的主观感受。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审美表达,与西方认知论意义上的理性活动分属于不同的领域。用科学的理性认知方法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学,就容易出现偏差。比如《红楼梦》这部小说,是在传统的“人世”与“出世”这两种相互依存的人生体验中来展开故事的。王国维用叔本华的意志论来解读它的悲剧性,是拿西方美学理论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学,以人的审美感受力为研究核心的德国近代美学,同《红楼梦》所表达的人生欲念和“生与死”的感受主题,有着一定程度的切近性。王国维之所以偏爱德国近代美学,将其引入用于研究中国文学,是因为他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审美和想象。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他将科学与文学分列为属性不同的学科:“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也。”而胡适主要是在实证的方法下,对《红楼梦》的作者展开考证。在文学研究中,从文献学和考据学的角度来展开作家、作品研究,本也是一种可取的方法,但胡适的目的是要通过对作者的考证,来论证《红楼梦》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他将小说内容与曹雪芹的家世材料相互印证,认定曹雪芹“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宝玉的底本”,认定小说里的甄家与贾家就是现实中的曹雪芹家。在以表述与事实相一致为原则的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下,讲究想象、虚拟的文学作品被胡适解读为一本纪实性的家谱,显示出胡适将文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不尊重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偏失。胡适不仅将文学作品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当作科学实验来做,面对白话文学的反对者,他表明文学创作同科学试验是一样的:“我们对于这种怀疑,这种反对,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对付,只有一个法子,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科学家遇着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只认可他做一个假设;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我们主张白话可以作诗,因为未经大家承认,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的实地试验。”
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学,一方面让胡适建立起系统化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偏颇。在此,西方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科学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被转化为科学化的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诗文观的矛盾,也可以说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矛盾。梁启超在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批评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同样,胡适用假设与求证的方法来论证其白话文学史观,的确给时人“石破天惊”之感,一旦他用此方法来研究存在论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便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学赖以生存的文化世界,产生了认识上的谬误。
对其将科学方法论引入到文学研究中而产生的偏误,胡适在晚年有所体会。如他晚年把“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研究”分列为不同的研究,可见胡适已经意识到文学有着自然科学方法所不能认识的性质,他悬置了“应该采用什么方式来研究文学作品”这个问题,显示出他这位科学方法论信奉者终于在“文学”面前承认了科学方法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