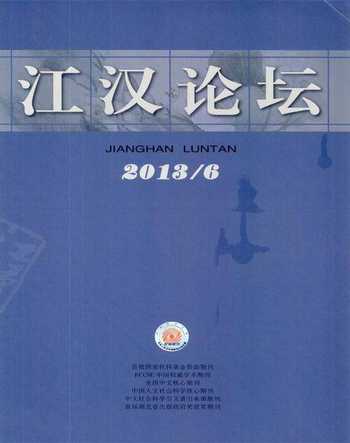试述楚人的联姻风习及其历史嬗变
刘利
摘要:婚俗既是社会风俗和伦理关系的重要表现,又是内涵深广值得认真研究的基础科学命题。由于楚国社会直接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所以,它比中原地区保留了更多的原始社会的习俗。其奇异的婚俗和充满浪漫的情调与中原地区大异其趣。特别是楚人在婚姻方面能打破繁琐的礼节,比较尊重人的个性。这在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楚婚俗;伦理观念;独特形态;神韵风采;历史嬗变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6-0089-05
婚俗既是社会风俗和伦理关系的重要表现,又是内涵深广值得认真研究的基础科学命题。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一定的地理、气候条件,制约着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当然也就会形成相应的文化环境,生长出独具特色的文化果实。楚地物产丰富,山雄水秀,云烟多变。客观环境造就了楚人奔涌跌宕,神秘浪漫的心理结构。但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只能是一种启迪,真正决定这一社会文化面貌的,是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变幻多姿的自然条件,天造地设的山川逶迤之态和风物灵秀之气,南北混融、多族杂居的生存状况,使楚人的生活色彩异常丰富。楚地的文化土壤既受过华夏文明的熏陶,更直承南国蛮风越雨的滋润。与中原文化相比,楚文化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气息、自然色彩、神秘意味和浪漫精神,表现在婚姻方面就是比中原人显得开放、自由、充满浪漫的情调。特别是楚人在婚姻方面能打破繁琐的礼节,比较尊重人的个性,这在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楚人的婚姻观念及其独特形态
中国古代婚姻重礼轻爱。举行正式仪式的婚姻才被社会和家庭认可。古代的婚姻礼仪,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与中原诸夏相比,楚人不仅在婚姻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在婚姻礼仪和嫁娶方式上也大异其趣。这是古代婚姻文化的差异性特征。
楚国与对男女交往限制严格的中原在婚俗方面的差异十分显著,浪漫气息浓郁,男女交往不受礼法限制。楚人在婚姻方面与中原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不大注重婚姻仪式。《仪礼·士婚礼》对从求婚到成亲的每一个环节(“六礼”)都作了极细致、具体的规定。所谓“六礼”:一曰纳采,即男方送彩礼给女方;二曰问名,即男方派人去询问女方的姓名;三曰纳吉,即占卜婚姻是否吉利;四曰纳征,即男方送现金给女方;五曰请期,即选择结婚的曰期;六曰亲迎,即男方派人到女方家中去迎亲。楚人从订婚到结婚却没有如此复杂。就通婚的彩礼而言,中原地区要隆重其事,需要纳彩礼。由此可见,古代婚姻文化的经济性表现得比较突出。男女双方在选择配偶时大多考虑双方家庭财产多寡。婚姻在缔结过程中非常注重聘礼,聘礼越重,女子的身价筹码越高。而女子出嫁时陪送嫁妆,也体现了婚姻当事人的经济动机。清代赵翼谈及古代婚姻时说:“凡婚嫁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恬不为怪。”根据史载规定,“先纳聘财而舌婚成”,“入币纯帛无过五两”②。彩礼的数量虽然有限,但在恩格斯看来,这是对偶婚中,女方氏族向男方氏族索取女儿赎金习俗的残余③。而楚婚俗则不拘这些礼仪,男女之间有情是以随身穿戴的衣物、装饰物作为定情之物的。《离骚》:“解佩壤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九歌》也写道:“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襟兮醴浦”(《湘君》)。“佩壤”是男子腰间装香料的袋子,玉环有缺称块(块古音同缺、袂,象征缺偶),为男女随身饰物。楚人通常以自己穿戴的物件赠送情人,用以向对方表示自己对婚姻的看法,因而湘君、湘夫人所弃的块、佩、袂、襟(指衣物)都是当时楚国民间的定情之物,而不是彩礼。在“六礼”中,楚人最多选择二、三项,甚至有时完全撇开这一套。在许多情况下,男女之间只要相中,就可以托人说媒,或直接向对方提亲。甚至跑到对方家中成亲。据《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楚子之在蔡也,郧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杨伯峻注:娶女不依礼曰奔,犹近代之姘居)“郧阳封人之女”爱上楚平王,便不顾一切地私奔到平王身边,结为夫妻。郧阳封人之女私奔楚王,不仅没有遭到拒绝,受到轻视,反而被楚平王立为夫人,所生之子建立为太子。太子建的母亲后来因为楚王另娶秦国之女赢氏而回了娘家。
在周代,“聘者为妻,奔者为妾”。而楚人置若罔闻,并非楚人有意违背周礼。只能说氏族社会的遗风在楚人的婚俗中还有较大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中原人的婚仪是十分周到的,纳徵亲迎之礼和嫡庶之分都是十分清楚的。在楚国,则还没有意识到礼仪的重要。《左传·昭公五年》记晋国韩宣子如楚送女一事,楚灵王想趁晋国上卿、上大夫来楚之时,侮辱他们,但为蔫启强所劝阻。与韩宣子同行的上大夫叔向说:“若奉吾币帛,慎吾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从而不失仪,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训辞,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国。”这番议论,说咀晋人恪守礼仪。楚王起初根本不重视这一套,然而,最终却不得不屈从了,待韩宣子等人以厚礼,并且在第二年命“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④当然,随着楚国与中原各国交往的曰益频繁,中原的部分礼法也逐渐为楚人所接受。《左传-定公五年》记:“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妻钟建,以为乐尹。”楚昭王的妹妹逃难时让一个叫钟建的男子背过,后据理提出要嫁给钟建,其理由是:女子之所以为女人,就是要远离男人,既然钟建已经背过我,我就应当属于他了。于是楚王把她嫁给钟建,让钟建做了乐尹。表明楚人已渐趋重视礼仪和贞节。
当时。中原各国在婚姻方面是非常注重名分的,男子的多偶制虽然存在,但在宗法名分上,男子却只能娶一名妻子。妻与妾在名分上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同时也是与其出身和所受教养的程度密切相关的。楚婚俗与之稍异,一男可娶二妻。这可以在史籍中找到佐证。《战国策·秦策》载:“楚人有两妻者,人祧其长者,詈之,祧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祧者曰‘汝取长者乎?少者乎?‘取长者。客曰:‘长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为取长者?曰:‘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我詈人也。”楚人可有两妻,此文最明。《淮南子·说山训》载楚申喜寻母故事亦云:“老母行歌而动申喜。精之至也。”注云:“申喜,楚人也。少亡二母,听乞人行歌声,感而出视之,则其母也。”此二母恐是申父的两个妻子,故申喜以母视之。《汉书·地理志上》荆州条下云:“……其利丹银齿革,民一男二女”。汉去楚不远,汉志载楚俗又最详,其说足以为据。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楚国当时这一习俗必然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屈原能够在《九歌》中写进《湘君》、《湘夫人》,至少可以表明一男娶两女为妻之类是楚国较为流行的传说故事。⑥在《离骚》、《天问》中也可以得到明证。《天问》中屈原曾问到:“舜闵在家,父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朱熹在《楚辞集注》中释前句为“问舜孝如此,父何以不娶乎?”闻一多在《楚辞校补》中释前句“闵”为妻,“父”为夫,郭沫若从之。从朱说,屈原的意思是舜的父亲应为舜娶尧之两女为妻;从闻、郭说,屈原的意思在责舜不应称鳏夫,因为舜原有妻登比氏⑦。无论从何种解释,屈原对舜娶两女子为妻一事均无异词。从后句来看,屈原责问的对象也在“尧不姚告”,不在同嫁二女。《天问》是屈原疑古最强的作品,凡是他认为与俗不合,与理难通的神话传说。他都要质疑。他对男子娶两女为妻一事不以为然,这就间接表明楚国当时有男子可娶两女为妻的习俗。
而在楚国统治者或贵族之间则是实行多妻多妾制。恩格斯说:“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⑧楚国的君王除了有正妻以外,还有妾多人。而且她们之间似乎也相处得很好,从楚庄王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庄王夫人樊姬已经习惯了这种关系的存在。据《列女传·楚庄樊姬》记载:楚庄王“尝听朝罢宴,姬下殿迎曰:‘何罢宴也?得无饥倦乎?王曰:‘与贤者语,俱不知饥倦也。”樊姬听了不以为然,她举例对庄王说:“妾执巾栉十一年,遣人之郑卫求美人于王,今贤于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岂不欲擅王之爱宠哉?妾闻堂上兼女,所以观能人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见,知人能也。妾闻虞丘子相楚十余年,所荐非子弟则族昆弟,未闻进贤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贤路。知贤不进是不忠,不知其贤是不智也。”意即我为了大王您的高兴,每每看到有美貌的女子,都要把她纳为您的妾,为的是能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而您的令尹却从来没有为您进献过一个有用的人材,这怎么能说得上是一个有用的人呢?樊姬的这番话反映出当时的楚国女子对于纳妾之事能够泰然处之,甚至于能够去为丈夫物色合适的女子作为她的妾。其实楚庄王在即位不久时,年纪还很轻,就“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了。这说明楚国的纳妾之风兴起得还是很快的。
纳妾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它的起始应该是从男子在婚姻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开始,但是最初以一定的法规来确定它却是在周代。周代记载礼仪的《曲礼》上规定: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妾被排在最末的位置上,可见地位之低。而楚人并不把名分看得过分重要,出身高贵的女人可以作妾,出身低微的女人也可以立为妻。据《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楚平王就曾把“郧阳封人之女”立为夫人,并且立其子建为太子,而把出身于秦国王族的赢氏纳为妾。《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适也。”太子壬是赢氏之子,子常的话,说明赢氏终平王之世非正夫人。又据《史记·楚世家》载,楚国著名丞相春申君黄歇曾将自己一个叫李环的侍女送给楚考烈王为妾。楚考烈王不仅没有因为李环出身卑微而鄙视她,相反倒十分宠幸她,以后又被立为王后。当然,说楚人不太注重名分也不尽然,《国语·楚语上》载:“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访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对曰:‘……君子曰:从而逆(从,从其欲)。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进退周旋,唯道是从。……子期乃止。”楚司马子期曾欲以妾为妻,问于左史,旋为左史制止。《韩非子·奸劫弑臣》载:春申君黄歇“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君前。妾以赐死,若复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黄歇妾余又欲杀前妻子甲而以己子为嗣。“因自裂其亲身衣之里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曰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戏余,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杀甲也。”春申君之爱妾想代正妻,欲杀前妻子甲而以己子为嗣,采取自伤的办法诬告正妻才得逞。然而这只是少数现象,一般情况下,楚人是不把名分看得过分重要的。楚人既允许多妻,又不怎么注重名分,这表明楚个体家庭的组成形式比较特殊。
楚国也实行媵婚制。媵婚制是始于周代的一种特殊的嫁娶方式。《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载:“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女。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按照周王朝规定的媵的作法来解释,即送女子出嫁之人。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如果要娶一个诸侯国的女儿,必须有两个同等诸侯国派女儿前来相送。后来发展到一个诸侯国的女儿出嫁到别国去,也必须有两个同姓诸侯国的女儿送新娘前往夫家。这些送嫁女子的身份就是处在陪嫁者的地位。也就是说能够有被人送的资格的,当时是具有同等地位的贵族女子。最初,对于陪嫁者的姓氏还有很严格的规定,只有同姓诸侯国才能成为陪嫁的“媵”,她们或者是妹妹,或者是侄女。到后来,异姓诸侯国的女子也可以成为媵婚者。这种陪嫁出去的女子,其身份就不仅仅限定在侄女或妹妹的范围内,只要是未嫁的有一定家庭背景的女子,都可以去送嫁。这些陪嫁到别国去的女子,其身份是作为出嫁女的陪嫁,这种陪嫁者所具有的地位可以是奴仆,也可以是待嫁的后备人员,也可以随后就成为男主人的妾或者是身份高于妾的偏房。有的媵婚者在正妻死了之后,就由偏房或者妾的地位上升到正妻的位置,她们较一般的女子而言,更容易取得正房的位置。媵的意思在后来也有了一些改变,最初媵只是指陪嫁的女子,到后来,人们把媵婚的人不仅仅局限在女子这一部分人了,还有一些陪嫁的男子也称为媵,陪嫁的伶人也可以成为送嫁者。甚至有一些陪嫁的物资也被称为媵,如一些青铜礼器等等。楚国既接受别国来媵的女子,也接受别国其它的来媵之人或来媵之物。《史记·楚世家》中就有“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媵”的记载。这件事所反映的是楚国当时不仅在陪嫁女子方面随了周礼,而且在媵婚的一切形式上都遵从了周礼。
,
在古代,以物为媒。即以某种约定俗成的物品为中,介,作为传递爱情的信物在各民族的婚姻生活中广泛存在着。楚国民间男女互恋时以花草赠人,如《山鬼》中女巫拿的“三秀”、“芳馨”,《湘夫人》中的“杜若”,《大
,司命》中的“瑶华”。《礼魂》中的“春兰”、“秋菊”等,这一表达情谊的行为方式反映了楚人的联姻风习。据《九歌》所载,灵巫们均为少年艳丽之女,他们与中原诸夏不同的是,竟以同神恋爱的方式祈神、媚神、悦神,求其赐福。与此同时,也使自己得到神灵的钟爱。瞿兑之在《释巫》中说:“众聚焉则必求所以相娱悦者,……其始也,以人之道事神;其继也,以事神之道娱人,固理之所必然而势之所必至也。九歌为礼神之曲,而并多男女爱悦之词。……然古昔先民固如是也。士女……目挑心招,式饮式食,既醉既饱,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巫在其间的作用是“为之导示,为之左右,期于洽比其邻,既安且宁。”这种风俗的根本目的就是男欢女爱,两性合好,繁衍后代。楚人就是这样,在一片充满神秘色彩和生命激情的热土上,在一种宽松而活跃的多元信仰氛围中,以自己对自然万物的独特理解。营造出一种人、鬼、神和谐共处。神话与现实交融互渗的、亦真亦幻的精神天地。
古代对婚期的选择一般都是由卜筮决定,这是由巫师掌握的一项专门技术。与婚仪严格的中原诸夏相比,楚人在婚姻问题上个人有较多的自主权,因而楚人婚期虽用卜,但卜婚定情约期之后还有轻易改变态度不受巫祝支配的情况出现。《九歌》中湘君、湘夫人遗袂、遗块以及山鬼等待情人失约的故事就是临时变卦的写照。这一现象在婚仪严格的中原诸夏是少见的,恐怕与他们自由恋爱的风气不无关系。
结婚何时为最佳?相传古人有在仲春三月会合男女的风俗,这一风俗成为联结婚姻的好时机。《周礼》引《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之时。”《周礼·地官》亦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在每年农历二月春暖花开的季节,由官媒组织青年男女举行一次露天舞会。在这样的舞会上,男女青年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恋人,甚至当场私奔也没有人禁止。《诗经·郑风·溱洧》、《鄢风·桑中》等篇中,也都记载了先秦时期这种比较自由的恋爱习俗。朱熹在《诗集传·周南·桃夭》注中说:“桃为有华,正婚姻之时。”《白虎通义·嫁娶篇》也说:“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据此二说,周代婚姻大抵都以春天为正时。当然,也不排斥其他时节,由于古代男女恋爱场合往往是与民间的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而祭祀时间一般又通常在春秋两季,最普遍的是在春季(古代农事一年的开始)约婚,秋季(古代农事的终末)完婚,故而年终结婚也是一个重要的季节。《诗·氓》载:“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衍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九歌·礼魂》载:“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千古”,但从九歌反映的物候来看,楚国男女相会并不限于仲春三月或春秋二季,地点也并不限于云梦一带,这和楚国男女交往自由,具有区别于中原的独特的婚姻观念和方式有关。
二、楚婚俗的神韵风采和历史嬗变
楚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音乐舞蹈之邦,这种传统在故楚之地依然有着生动的体现。楚民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楚人的浪漫气质还表现在以歌舞求得联姻。性爱是人类的本性。大概男女双方都想极力求得对方的喜悦,因以活泼的姿态、美丽的声音,努力去表演,借以引起对方的注意,遂导歌舞的先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杜注:“万,舞也”。)楚令尹子元以“万舞”蛊惑其嫂,借万舞以撩拨文王夫人的春心,以实现非分之念,达到淫事的目的,则可见万舞可能非常热烈。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极具刺激性的意味。《诗·邶风·简兮》曰:“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方将万舞”,“公庭万舞”,闻一多先生由此推定“爱慕之情生于观万舞,此则舞之富于诱惑性。”《九歌》中所祭之众神不仅大多是与人的生活关系密切的自然神,而且都是人格化的靓男美女。他们有七情六欲,需要爱情。以“人神恋爱”而著称的楚人,踩着鼓点,“安歌”以和,“缓节”、“应律”而舞。身穿姣服的美丽女巫,在“芳菲菲兮满堂”的祭堂之上,以悦耳的乐曲、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和妩媚的神态酣歌醉舞,使神享受到了更大的快乐。
楚人以歌舞取乐求爱在《招魂》、《大招》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大招》云:“姱修滂浩,丽以佳只。曾颊倚耳,曲眉规只。滂心绰态,娇丽施只。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袂拂面,善留客只。……丰肉微骨,体便娟只。”《招魂》以“盛需不同制”、“长发曼需”、“弱颜固植”、“姱容修态”、“埃光眇视”来描绘巫女的婀娜多姿。楚楚动人。唐人诗句中曾描绘巫女的形貌神韵,韦应物《龟头山神女歌》中有“巫女南音歌激楚”之句。款款灵巫,纤腰轻飏,长袖飘逸,纵情声色。在这样的氛围里,神与人的距离消失了,人间之美和神界之奇合二而
一,幻化出楚巫女歌舞艺术最美丽迷人的魅力。
以歌舞为媒缔结婚姻的习俗在秦汉以后的汉族地区由于生产的发展和受封建礼教束缚及其媒妁婚的盛行而趋于消失,然而在故楚之地的南方诸族却较为完整地传承下来。许多文人墨客曾有十分生动的记载。据《炎徼记闻》卷4载:苗人跳月,“未婚男女吹芦笙以和。”《黔书》载:贵州荔波县水家苗,“每岁首,男女成群连袂歌舞相欢者,遂为婚姻。”陆次云的《跳月记》、田雯的《苗俗记》里,都记述到苗民舞蹈的情况,说是每当春月,群集未婚男女于草原上,吹笙摇铃,并肩舞蹈,男女相悦,夜间各择爱侣以去。又据《太平寰宇记》载,宋代广西有些地方还有普那路亚婚制和对偶婚制的遗俗。每月中旬,不同姓男女青年盛服吹竹,在明月下联情,二更以后,互相喜悦的便两两相携而去,野外同居。明代邝露所著《赤雅》中描写侗族青年男女对歌求偶:“歌唱为乐……春歌正月初三,三月初三,秋歌中秋节。”又记:“侗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箫笙于名山。五丝刺同心结百钮鸳鸯囊,选侗中之少好者,伴侗官之女,名曰天姬队。余则三三五五,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亦三五群,歌而赴之。相得则唱和竞曰,解衣结带,相赠以去。”赵翼《檐曝杂记》载粤西边地风俗说:“每春月趁墟场唱歌,男女各坐一边,……若两相悦,则歌毕携手就酒棚并坐而饮。彼此各赠物以定情,订期相会。”沅湘之间“走歌圩”、“歌为媒”的习俗沿袭成风,常盛不衰。对民俗主要是对湘西民俗事象作多侧面、多角度反映的著名作家沈从文曾说湘西苗族男女青年,“热情多表现在歌中。”他在《龙朱第一·说这个人》一文中,说湘西的男人,“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是真实热情的歌。”它是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独特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近代以来二些地区这种习俗已发生了变化。如现代壮歌的歌圩,已经不完全是古代社会那种面貌。一般相邀对歌,都有邀请歌、询问歌、爱慕歌、交情歌、深情歌、送别歌等程序。往往第一次歌圩只是初交,到第二次、第三次歌圩时,互相进一步了解后才能到“深交”,而誓约终身。
依吹笙跳月、连歌哒舞表达爱情、选择配偶是原始自由婚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后来的媒妁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记当时瑶族婚期时写道:“瑶人,每岁十月旦,举山同祭都贝大王,于其庙前会男女之无夫家者,男女各群,联袂而舞,谓之踏摇。男女意相得,则男咿嘤奋跃,人女群中负所爱而归,于是夫妇定矣。”《虞初续志》载:“苗人之婚礼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而跳,跳舞求偶也。”若跳月之时,男女相悦,则“渡涧越溪,选幽而合。解锦带而互系焉。……而后议聘”。《滇黔土司婚礼记》载贵州苗族婚俗:“以跳月为婚天夕立标于野,大会男女,男吹芦笙于前,女振金铎于后,盘旋起舞,各有行列,讴歌互答。有洽于心即奔之。越曰,送归母家,然后遣媒妁。”《云南方志》载云南楚雄地区,男女“婚姻不先媒妁,于每岁正月择地树芭蕉一株,集群少吹芦笙月下。婆娑起舞。各择所配,名曰扎山。两意谐和,归告父母,始通媒焉。”可见,以上这类婚姻在通媒之前男女已通过跳月选定了终身。
不可否认,随着北方中原文化统治地位的建立,孔孟之道对妇女的种种约束,同样强加于楚地的妇女。在中国南方一些官府官军的驻扎地旧址,从残存在节孝牌坊和家族族谱上的节妇烈妇名单的只字片纸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一统汉儒文化对妇女的残害。然而,正因为这里毕竟不是中原,这里的妇女,尤其在民间的妇女,免不了有一些对孔孟之道的所谓“妇道”阳奉阴违,在父母包办明媒正娶的婚姻关系中也难免给人一点混水摸鱼的暖昧与涣散。以至于至今湘西北、广西省境苗、瑶民族的歌圩,“还黑祖愿”祈神仪式中的“舞娘子”,尚存春月集合青年男女,歌舞择偶之古俗。在湖南的湘西苗族、土家族和侗族的聚居地,仍然有祖辈相传的对歌自由恋爱的习俗。在赶歌场的时候,年轻的姑娘们用一种微带抑郁的情感唱她们迎接神的歌子,总是能让人联想到两千年前的伟大诗人屈原到湘西来所听到的那些歌。照历史记载,屈原著名的《九歌》原本就是从楚地流传的酬神歌曲衍化出来的。
据有关文献记载,直到18世纪,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由土司制“改土归流”之前(即自远古至明清),当地的少数民族青年男女自由婚姻带有原始的气息。男女青年的社交和恋爱都是相当自由的。当时,土家族的自由婚姻在史籍中被认为“迥异华风”,有别于中原早已僵化了的封建婚姻制度。而且,能歌善舞的土家族男女青年都是用情歌来追求爱情的。土家族的歌谣反映在婚姻和恋爱方面有“家曲”和“山曲”。家曲是在迎亲嫁女和宴请宾客时唱的,山曲是男女青年恋爱时唱的。山曲可分为初恋曲、赞美曲、结交曲、深情曲、相思曲、离别曲。有意男女一曲曲唱下来,便可私定终身。土家族舞蹈,最为热烈壮观的是摆手舞。摆手舞也是明清之前土家族青年男女进行恋爱和建立婚姻关系的一种方式。明清之后,随着汉族商人和农民大量迁人湘鄂西地旷人稀地区,土家族社会形态迅速由封建领主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发展。尤其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封建地主经济确立。封建礼教和婚姻也迅速地统治了土家族婚姻。摆手舞的庞大场面直至现在还保留在湘鄂西土家族聚居区,但是,过去摆手舞中男女青年订婚的形式却不复存在了。
据史籍所载,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集团往往以联姻作为巩固相互之间政治联盟的一种手段。楚国也不例外,自春秋中期以后,楚国王族的婚姻已逐渐打上政治烙印。如楚国和秦国联姻,楚国和齐国联姻等,就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楚和“蛮夷”诸侯的各国间也是互通婚姻的。如《国语·周语》中有“庐由荆妫”之句,韦昭注:“庐,妫姓之国;荆妫,庐女为荆夫人也。”楚共王曾“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告其五子曰,当璧而拜者立为嗣君。巴姬直接插手楚王室继承一事,反映了通婚对楚政治生活的直接影响。其后,巴在“战国时尝与楚婚。”《左传·文公元年》载,潘崇曰:“享曰芈而勿敬也”,杜预注:“江芈,成王妹,嫁于江”,并有“楚女嫁于江者”之说。到战国时期楚国王族婚姻就带有更浓的政治色彩了,已经非常明显地以联姻作为一种联系的手段。《史记·楚世家》记:“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寡人与楚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以相亲久矣。”《史记·张仪列传》亦记:“秦欲伐齐,齐楚从亲,於是往相楚。……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於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这种政治联姻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个人爱情为代价的,但毕竟在客观上对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据有关文献记载,清代鄂西土司之间往往利用通婚结盟。如容美土司田氏与五峰土司张氏“世为姻娅”。这种婚姻关系。甚至延伸至两湖土司之间,据《容美纪游》中盟书曰“祖宗以来世为姻好”。
值得指出的是,婚俗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当人类社会的婚姻和家庭前进到一夫一妻制状态时,许多古老的婚俗也随之以变形的形式保留下来。其中有良俗,也有陋俗。春秋战国时代,南北文化交流频繁,可楚人的某些婚姻观与北方迥异,而与故楚之地的南方诸族何其相似。应该说,这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存在源与流的关系,而主要是两者的社会中都保留着较多的原始社会残余所致。我们可以将之解释为在相似的环境、情况下可以产生同样的文化特征。但是,楚国当时雄踞南半个中国,正如有关文献中所记载的:“楚地南卷沅、湘,北饶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缘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楚悼王二十年(公元前382年),以吴起为令尹,“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等等,这一切。充分显示出当时楚国版图之广阔。因此在婚俗文化上与楚境其他民族婚俗文化也不无相交通的可能,不仅有相互吸收、融合的性质,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有其分化、传播的特点,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