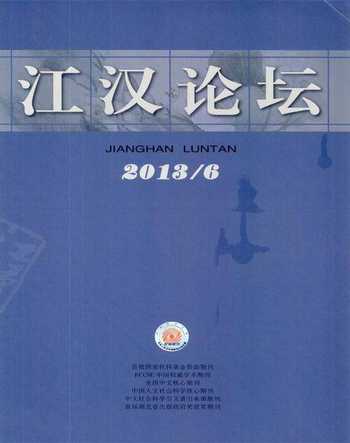个人权利是必须的吗?
[美]克雷格·K·伊哈拉
一、从不宜谈个人权利的地方说起
本文拟从一些我们熟悉的语境谈起,在这些语境中,权利话语,尤其是那些彼此责难的权利话语,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1 以体育团体中的篮球队为例。团队中每个人的天赋不同,承担的角色分工也不同。负责发起进攻的防守队员最重要的责任是持球跑动进攻、运球、发球以及传球给处于有利位置的队员。中锋(通常是最高的队员)负责控制篮下阵地、抢得篮板球、阻止对方投篮、以及篮下得分。假定在一次比赛中,某队的中锋站在对方的蓝板下面。没有对手严密防守,而该队负责发起进攻的防守队员却未能将球传给中锋,人们会怎么说?说防守队员犯了一个错误,做了错事,没有做该做的事,没有尽职尽责,把事情搞乱了或者说把局面搞糟了。无论什么原因,如果他经常性地错失这样的机会,他可能被视为一个能力不够的甚或是拙劣的防守,很有可能丢失这一位置。该队其他队员有理由抱怨他的不称职、缺乏球场意识或者指责他自私,尽管就团队精神而言他们不应该急于批评。
借用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术语来说,我们在篮球或其他相似的比赛中从事的是一项业务。在这项业务中,参加者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遵循游戏规则中的好坏标准,接收大量的评判性回应。在这样的业务中,参与者承担着角色职责意义上的义务,但我认为,他们并不享有个人权利。
为什么说他们并不享有个人权利呢?首先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关于权利的语言根本不在篮球比赛中使用,尽管它应用于比赛之外的职业合同谈判或其他属于法律范围或准法律范围的场合。如果负责发起进攻的防守队员未能将球传给中锋,我们通常不会说他不尊重、侵犯了或者是妨碍了中锋的球权。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赋予中锋一定的权利,除了说防守未能尽职,做了错事之外,我们还能说什么?我们可能会说在这一情形下,只有中锋享有球权,而防守未做应做之事,便意味着他剥夺了中锋的这一权利。因此对他构成了伤害:防守不仅做了错事,他亦伤害了中锋,侵犯了他的权利,并且剥夺了他的应得权益。所以,中锋比其他队员更有理由要求补偿。我认为,这样的一套篮球或其他体育比赛理论至少是古怪的。再严肃点说,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比赛的性质,它会将个人而不是团体,视为最根本的要素,从而重新定义比赛本身。
当然,队员们,即使同队的队员们,彼此间会产生不满。在上述情境中,如果中锋比其他队员对防守更加不满,那也不足为奇。毕竟。由于防守的错误,他才错失了一次轻易得分、帮助该队取胜的佳机。但是,尽管情理上可以理解,我们却不能说中锋的权利受到了防守的侵犯。而且,如果中锋不是因为防守的所作所为使团体失去了获胜的机会,而是因为防守的错误伤害了他自身而严斥防守,他也会因缺乏团队精神而受到谴责。
体育比赛中还有各种各样的例子可说明权利语言的使用至少是不正常的、不必要的。这些例子涉及的是犯规,而不是未尽职的问题。如同大多数体育比赛一样,篮球赛有许多关于队员在比赛当中可做和不可做的规定。队员违反了规定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而这些处罚通常情况下都不会涉及到权利侵犯之类的话语。举例而言,持球走(有时称走步)是一种犯规,会导致球权转入对方手中。很多犯规行为——自由投球当中的越线或替换犯规——皆是如此。它们并不直接涉及一个与之相对的队员,所以无法从权利的侵犯来解释或定义。
在篮球比赛其他一些犯规的例子中,关于权利的话题虽然并非难以提及或者说令人尴尬,但依然是非正常的,亦是不必要的。比如一个队员被对方队员犯规。这种情况下,该队员会屡次向裁判员申诉,而实质上他所要表达的就是“难道你没看见他(对我)做了什么吗?”如果这样说只是为了指出犯规行为,该队员的申诉并无不妥之处。任何人,包括粉丝在内,都可以这样做。关键的问题是这一申诉是否必须从侵犯权利这一角度进行。
例如,一个防守队员抱住对手以阻止他拿到篮球是一种过错;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对对方犯规,破坏了规矩,做了不被允许、不该做之事,或者违背了比赛规则,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说他侵犯了对手的权利。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这样去界定,而是这样界定没有任何意义。显而易见,如果防守队员犯规应该给他以处罚。如果裁判员没有裁定处罚,包括粉丝在内的任何人都有理由进行抗议。但是,他们喊的会是“犯规”,甚或是“他被犯规”,而不是“他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请务必注意,就是“他被犯规”亦无须界定为一种权利侵犯。“他被犯规”可被解释为“他受了委屈”,可被比作一种我们非常好理解的事情,一件无须援引权利概念,甚至无须理解权利概念就可以理解的事情。只要明白犯规者做了根据规则本不该做的就足够了。引人权利观念只会转移对团体的关注,对于比赛而言也是不必要的。
2 再以舞蹈这一语境为例。在芭蕾舞剧中,演员都有自己的角色,他们每人都应该表演一系列的舞步。然而,尽管《天鹅湖》中的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特定的角色与责任,但如果认为这一场舞蹈中舞蹈者彼此间享有权利,在我看来却是概念性的错误。
首先,芭蕾舞中没有可以产生个人权利与责任的规定。其次,当有人未能尽职时,其他人不会说他们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如果我忘了自己的舞步,可以说我跳得差。我甚至可能觉得有必要向我的舞伴或者整个团体道歉。然而,如果因为一个舞步上的失误,我未能帮你完成单脚着地旋转。却并不能说我侵犯了你的权利。我或许令你沮丧,使你生气,让你失望,而你也有充足的理由批评我的表现,或要求我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但却无须从侵犯了你的权利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批评和要求。
当然,你可以有权利期望我按照你所知道的舞蹈设计去表演。但是,你存此期望却并非说明我对你有应尽的义务。这里所说的权利是认知性的,它表明你的信念,即你对我的期望,有它合理的基础。换句话说,就理性的正当性而言,可以说你有权利指出我的失职。而事实上,其他任何一个看见并意识到我的错误的人都享有这一理性的正当性。但这并非意味着犯错即构成了对你的权利的侵犯。
3 再考虑另一种语境——典礼。典礼或许更像舞蹈表演,而不是竞争性比赛,但与两者都有基本上的相似之处。一方面,如芭蕾舞一样,其中的每个参与者都承担着某种角色,每种角色都有其既定的责任。正如在舞蹈中,成功依赖于一种协作。这种协作是一种共同的努力,其中一个人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其他每个人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个体的目标很大程度上与所有人共同的利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如竞争性比赛一样,典礼常有其规定,虽然其规定不同于比赛规定。举例而言,国宴有其特定的礼仪要求。典礼这一语境,因其角色责任与行为规则,较之其他语境更像儒家的社会理想。
至此,我想说的是,在上面提到的以及一些其他语境中,讨论个人权利至少是非正常的、不必要的。后文中我还会指出这些活动与儒家的社会理想有某些根本上的相似之处。它们所描述的都是无须谈及个人权利的语境,其中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一个人拥有特别的可能被他人侵犯的道德权利。说了这么多还未正式进人主题,如此行文主要是希望以上例子及对它们间不同之处的讨论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参照,以便能对下文有更好的理解。
二、关于个人权利重要性的-Lq论
最近几年,研究儒家哲学的重要专家们,如杜维明、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安乐哲(Roger T.Ames)、陈汉生(Chad Hansen)等,都声称传统儒家思想中没有权利观念③。尽管这一声称本身是有争议的,而且有关讨论还远没有结束,我还是敢断言大多数儒学哲学家们会赞同这一说法。我还有这样的推断:专攻其他非西方思想的哲学家们很可能对他们各自的道德传统持有类似的观点。
与此同时,研究英美道德哲学的重要人物,如德沃金(Ronald Dworkin)、费因伯格(Joel Feinberg)、阿兰·葛维慈(Alan Gewirth)、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麦尔登(A.I.Meldon)和马奇(J.L.Mackie),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有力地强调权利的根本性意义,而且他们所说的根本性意义不仅仅是针对西方的伦理理论,而是针对任何一个哲学上可被接受的道德伦理⑤。正如阿兰·葛维慈所说:“对人权的认可和保护是所有社会道德合法性的必要条件。”
看起来。如果这些儒学专家是正确的,亦如他们所说儒家思想中不存在权利观念,我们就会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儒家伦理从根本上而言具有道德上的缺陷,要么西方权利倡导者在某处出了问题。从本部分开始,我将通过分析费因伯格著名而颇有影响的文章《权利的本质和价值》中的论点来讨论这一两难问题。
在此探讨费因伯格观点的目的是想表明,英美的权利倡导者们过分强调了他们所谓的权利,而事实上,即使没有个人权利这一概念,儒家伦理也并非如费因伯格所暗示的,是站不住脚的⑦。
三、费因伯格的“无何有之乡”及其含义
在《权利的本质和价值》一文中,费因伯格让我们想象一个“无何有之乡”,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彼此间不能有任何道德上的主张,也就是说,他们不享有权利,但是这个世界有如下特色:
1 人们的道德高尚至极,同我们所知的人性本善相吻合。
2 人们对任何没有特殊关系的他人和集体不具备完善的责任(如慈善)。
3 人们对于“甜头”(dessert)的意识比较薄弱。他们会认为一定程度的奖惩是合理的,比如最佳竞赛者之获得奖赏,但当一名雇员因特别出色的工作而主张额外的报酬时,就不能认为是合理的了。
4 为了具备诸如资产、信诺与契约、协议与买卖、约定与贷款、婚姻与伙伴等制度,“无何有之乡”拥有它的“君主权利垄断”。所有上述提到的机制的运行都非权利而不可实现,而在“无何有之乡”中,所有的权利则尽属君主一人所独占⑧。
在费因伯格看来,尽管没有权利概念的“无何有之乡”在道德上已至极高之境,但它还是有所缺失的。他说:
“无何有之乡”和我们的最大差别……与(依据权利提出)主张的活动(the activity of claiming)有关⑨。
这将我们引到以下问题:费因伯格所说的“(依据权利提出)主张的活动”是什么意思?假如没有权利,我们就真的不能提出主张吗?果真如此,它为什么如此重要?看起来,试图维护儒家伦理的专家要么证明即使没有权利概念,儒家思想提出主张也是可能的,要么证明缺乏主张的理论并非一个道德体系的致命缺陷。而我想说的是,能够向他人提出个人主张并非一个可行的道德体系的必要特征。尤其是儒家这样的道德体系。
为了清晰阐明自己的观点,费因伯格进一步对主张(claiming that)和提出主张(making claims)做了区分:
关于权利(或主张)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只有拥有权利的人才能主张权利。当然,每个人都可以主张(claim)这把伞是你的,但是只有你或你的代表,才能真正拥有(claim)它。……因而合法主张(claim to)与主张(claiming that)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前者是合法的作为,可以产生直接的合法结果,而后者常常只是说明性的语言,不会产生法律效力。从法律角度而言,主张本身可使事情得以发生④。
费因伯格含蓄地将他关于合法主张的论断扩展至道德主张。显然,提出道德主张是一个道德行为,可以产生直接的道德结果,本身可使事情得以发生。而声称某事如此或并非如此常常只是事实上的语言说明,并不具有任何道德力量。
费因伯格接着又进行了如下粗率的推断:在一个没有权利概念的社会里,提出主张是不可能的。而如果没有提出个人主张的能力,就不可能具有“某某东西是我的”的意识,因此(1a)没有什么伤害可构成申诉的理由,而且(1b)任何予以他者的益处是不必要的(道德上不被主张);(2)我们缺乏人类尊严、自尊和平等。既然这些在道德和哲学上都使人感到不快,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抵制任何不具备个人权利的社会或道德观。正如费因伯格所说:
这些关于权利享有的事实绝好地证明了权利的至高无上的道德重要性。所以,我最想说的是,这些事实说明“无何有之乡”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上文提到的儒家学者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轻易地得出结论:个人权利的缺失就是儒学思想或其他没有权利基础的传统问题之所在。
四、对费因伯格的回应
现在我们更详细地讨论一下费因伯格观点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他说:
“无何有之乡”的居民,即使受到了极端的歧视,即使他们的需要无入理会,甚至即使遭到不堪的对待,也不会想到要站起来提出正当的主张@。
这段话无形中使我们面临一个谬误的两难之境:要么我们拥有主张权,要么我们就被动地丝毫不加反抗地接受一切形式上的虐待折磨。但是,正式承认或表达对他人的不满并非离开权利概念就无法实行。这里,我们以对违背某一传统文化所信奉的禁忌为例进行说明。这一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并可能抗议违禁行为。但抗议的根据不可能是违禁行为侵犯了其他居民的个人权利或甚至其他居民的集体权利。比较可能的情况是。这一违禁行为侵犯了某一超自然法令。这种情况下,抗议的居民并不仅仅是在声称(claiming that)某事正在进行,而是进行的事情触犯了一项禁忌,他们还在提出主张(make a claim),而这一主张“可以使得某些事情得以发生”。当然,这种主张并非费因伯格意义上的主张,因为它并不是由权利被侵犯的特定的人所提出。但是这些居民能够断定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亦有能力对这一行为作出抗议,而且能够将这一能力付诸实践。
这些居民可以提出抗议,同样的事情也可发生在无何有之乡。费因伯格规定无何有之乡的居民可以:
彼此间承当义务:但这些义务……并非直接为受约人、债权人、父母等诸如此类的对象而尽,而是只为上帝而尽,或为某一精英实力集团的成员。或为神祗之下的独一无二之君而尽。
但是,果真如此的话,请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某人A向君主承诺他不会违逆他人意愿而夺取他人之物,而事实上他却做了这样的事,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被A夺取了物事的某人B显然会意识到允诺者违背了他向君主所做的承诺。并且很可能要求允诺者要么物归原主,要么接受惩罚,甚至二者兼之。这就说明即使是无何有之乡也并非如费因伯格所设想的那样被动顺从。在这个地方因为人们彼此之间不能直接提出权利方面的申诉(例如“你伤害了我”),我们可以说它没有权利概念,尽管如此,此处居民依然可能提出可以“使事情得以发生”的主张。无何有之乡可能是一个没有权利主张的世界,但它不可能是一个不能辩识背弃诺言和契约或者说无视如此行为的一个世界。
以上众多例子中的两例表明,没有彼此间的个人权利,不意味着没有不道德的行为,也不意味着抗议不道德的行为不会出现。其他例子包括了由角色支配的活动——如前面分析的篮球赛、芭蕾舞、典礼等等。再以礼节为例。有违礼节不会被界定为侵犯行为,如用小刀吃豌豆不会对其他就餐者构成侵犯行为,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识别这一行为的不适宜性,并不妨碍我们对之提出抗议。
棒球比赛中,假定二号守垒员将跑垒员推离二垒之后再将其触杀,依照规则,这一行为是被禁止的,所以跑垒员可以据此提出抗议。如果裁判员同意,跑垒员就可以留在二垒。那么如果跑垒员坚持说“我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会出现什么情况?不仅规则手册里对“权利”没有明确的提及,而且这样的说法也未免古怪异常。但是无论我们认为跑垒员或甚至整个团队有无权利,我们都无须为了对这一行为提出申诉而以权利概念来界定这一违禁。对于申诉而言,必要的就是权威性的规则和职责。二号守垒员违犯了规则,做了一个二号守垒员不该做的事,这就足以构成理性抗议和寻求官方补偿的基础。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关于运动和礼节的例子是琐碎的,因而并不中肯。道德是严肃的,而当我们的争论点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如人类生活时。关于权利的语言则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这一反对意见,我做出如下三点回应。首先,和道德相比,比赛和礼节的确显得琐碎,但是我们并不能轻易否定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的一些结构上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是否具有重要意义,部分取决于一个人的道德观念,但我认为这些相似之处可以启发我们对规则、角色责任以及权利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并且启迪我们从崭新的角度审视道德。尽管这些例子不够严肃,但它们却有另外一个优点:比更严肃的例子更少争议性,更少受到情感上的攻击。
其次,无论其有何种普遍意义,这些例子的提出主要是针对费因伯格观点的回应:无论受到何种虐待,无何有之乡的居民也不会想到抗议。后者作为一个例子与任何比赛之例一样是琐碎的。当然,一个例子的琐碎性并不能表明另一例琐碎性的合理性。不过,如果我所举的例子可以提供具体而又颇为大家所熟悉的语境,其中一些行为可以被认为是错误的,可以被抗议,而不必依赖或使用权利概念,那么这些例子理应和费因伯格的无何有之乡之例具有同样的分量。
最后,更加严肃的例子并非没有。然而,要举出没有争议的例子却不容易。这至少可以归因于以下两点。其一,在我们这个竞争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体系中比较难以提取严肃的实例。比如,从比较严格的科学的观点来看,一队受聘于类似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可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例子。因为他们从事的就是我所主张的无须权利话语的合作性事业。然而。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这一合作性事业中。知识产权是必须考虑的。这一反对意见背后存在着一个预设:这一合作活动的背景是一个较大的市场体系,而这一市场体系正是科学家们非常关注的。而且,还存在另一个假定:除了市场体系,没有其他的公正途径可进行金钱或其他利益的分配,因此一个人的自我保护也就等同于某些权利的主张。
列举更加严肃的例子的第二个障碍是,很多人倾向于用权利话语界定一切重要的人类关系。而这样做往往是行不通的,其中争议最少的严肃的例子就是传统家庭,尤其是亚洲的传统家庭之例了。我们常用天然的、有机的单位来界定这样的家庭。这种家庭最重要的目的是家族的延续和发展。它们是一种统一体,时间上前可追溯至远祖,后可延伸至子孙后代。在这样的家庭中,角色和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人都有该做的一份工作,而且每个人一生的主要目标中至少有一条就是做好那份工作。一个经常忘记给孩子做饭的母亲不是一位好母亲。但是无须将她的行为界定为侵犯了孩子的饮食权。一个没有按照父母意愿照顾兄弟姐妹的兄长是做了错误的事情,但不能说他侵犯了兄弟姐妹的权利。
与上文所举之例相似的例子也可表明费因伯格第一个论点第二部分(1b)的问题:没有权利概念的人们必定会将他们得到的利益视为赏赐或是统治者的分外之举(acts of supererogation)。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社会,人们认为统治者在春季必须履行一定的祭祀之礼从而保证好的收成。就统治者而言,履行祭祀之礼并非分外之举,而是其角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职责。如果未能履行这一职责,统治者便会遭到指责;而对这一职责的履行。甚或是值得赞扬的过度履行,根本不会被视为过分之举。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人民都没有被授予权利,尽管他们才是最为获益或最为受损的一方。
棒球中的巧胜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击球员一个好的短打使得跑垒员能够完成角色职责实现目标。跑垒员依赖击球员的作为,从击球员的作为中受益。但就跑垒员而言,赞扬击球员并非不可。而感恩却属异常。就像上文提到的统治者,击球员所做的并非分外之事,而是他作为击球员的职责所在。他只是做了他应做之事,而不是为了跑垒员轻轻触球。这就与费因伯格的观点——没有主张权。获益就会被视为统治者的分外之举——相抵触。
最后。再看看以无何有之乡为背景的一例。如果无何有之乡的君主要求所有的夫妇都要彼此关心爱护,那么丈夫关爱妻子是他对君主应履行的责任,而妻子关爱丈夫也是她对君主应尽的义务。而根据费因伯格的假定,无何有之乡的夫妻彼此间没有主张权。但是,夫妻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也不会视对方的尽职行为为异常,为分外之举,就如同棒球运动员不会对队友间的相互依赖感恩戴德。
五、个人权利和儒家的人类价值观
面对上述例子,费因伯格或许会不情愿地承认,尽管没有个人主张权,无何有之乡的居民也能够向不端行为提出抗议,能够接受一定的利益而不将其视为赏赐。但他又可能坚持认为,无论是抗议还是接受都并非基于适当的理由,即遭受损害或获取利益的人民的道德状态。换句话说,他们的回应并非立足于这样的事实:他们本就是理应得到尊重和尊严的人。而这实质上又促使我们分析费因伯格关于权利价值的第二个观点。下面是一段详尽的引用:
当然,拥有权利使得提出主张成为可能;但是,正是提出主张赋予权利以特别的道德意义。就某种程度而言,权利的特点有些像我们惯常关于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的讨论。拥有权利使我们能够“像人一样地挺立”,能够坦然地正视他人,能够从根本上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视自己为权利的持有者并不会导致过度的骄傲,而会使人感到适度的自豪,自豪于拥有那借以获得他人之爱与尊重的最低限度的自尊。事实上,尊重人……或许就是尊重他们的权利,因此人与权利不可能被割裂开来;而所谓的“人的尊严”或许就是公认的提出主张(assert claim)的能力。因此,尊重一个人,或者认为他拥有人的尊严,也就是将他看作一个潜在的主张者,权利声称者……这些关于拥有权利的事实很好地证明了权利至高无上的道德意义。这里,我最想说的是,这些事实道明了无何有之乡的问题之所在。
我们从上述引文中可看出费因伯格两个极其不同的论点。起初他就表明“主张能使我们‘像人一样地挺立”等等。换句话说,他认为提出主张本身足以使人“像人一样地挺立”,或者说它至少是使人“像人一样地挺立”的部分充分条件。而承认这一观点并非必然要批判儒家思想或其他不谈及权利的道德体系,因为除了主张权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保证人之为人的尊贵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然而,接下来他又强烈地暗示,他人拥有权利,即拥有提出主张的能力,至少是尊重人的尊严的一个必要条件,甚至说二者本身就是等同的。尽管费因伯格用或许(may)做了程度上的限定,这一观点对他的权利辩护观而言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观点,权利不会是“最为重要的”,而是可以不被涉及的。而无何有之乡也未必如他所说是一个有缺陷的社会。
但是,如果说权利是平等、自尊、尊重人、人格尊严的必要条件,那么费因伯格不但向无何有之乡,而且向诸如儒家任何_个没有认可或者说特别重视权利的道德哲学发起了一个极其猛烈的挑战@。
应该从何处着手来回应费因伯格的第二个论点呢?首先,我再次着重强调一下我一直坚持的观点:费因伯格不仅仅是在赞美可理解为主张的权利德性(vinue of right),而且包括个人的权利和主张的概念。换句话说,不将权利和主张归属于个人,它们在概念上依然是可能的。相反,权利或许只能被归属于诸如家庭之类的团体,比如德川日本的情况。而情况果真如此,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费因伯格的言论。他依然还会说人们能够享有平等、尊严、自尊以及其他的感受吗?
一方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人们就不会因个人享有权利而享有这些,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拥有如此权利的团体才享有它们。那么,个人拥有主张权对自我价值感和尊重他人意识而言就并非必须的了。而事实上,费因伯格的例子都是关于个人与个人权利的,所以。他是根本不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思维。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假定团体权利不足以使人感到自我的价值、人格的尊严。果真如此的话,必须的并不仅仅是权利,而是个人享有的权利。事实上,我坚持认为这点正是费因伯格论点所预设的。他的分析以及关于权利的很多哲学文献,都声称其为之辩护的是权利的价值,而实际上却是个人权利的价值。
其次,如果费因伯格是正确的,那么他必须承认任何一个道德体系要么必然具有权利观念,要么其中的人们就不可能享有“平等,最低的自尊,热爱、尊重他人,敬重人或人的尊严的感受”。而这些论断的谬误与真实都是就定义而言的,而并非事实上的判断。
费因伯格曾断言,视自己为权利的享有者是借以获得他人之爱与尊重的最低限度的自尊的必要条件。这里,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一论点。如果将“自尊”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最明显的事实就是,一个人最低限度的自尊主要指的就是获取他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对他的爱与关心的机能,尤其是在孩提时代。然而,下面假定似乎不合情理:爱的基础,尤其是家庭之爱的基础,是“视自己为权利享有者”或“视自己的孩子为一个潜在的主张提出者”。而且,他人的尊重往往取决于什么被其所处的文化重视,它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向他人提出主张的能力。所以,一个人在没有自我是个体的权利的享有者的观念时,也很有可能受到他人的尊重,并拥有自尊。费因伯格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并不视自身为权利的持有者而断言,这些人不可能真正地尊重自己。然而,这种论点不仅看起来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的结果,而且,在费因伯格所说的“最低限度的自尊是获取他人之爱与尊重的必要条件”的假定之下,这种论点必然导致如下观点:这种社会中无一人“值得他人的爱与尊重”,但费因伯格根本不可能主张这一观点。
我们再从儒家的视角看费因伯格的另外一个观点:能够提出主张是人的平等、人格尊严、尊重他人的必要条件。儒家所说的世界是为天所安排好的秩序井然的宇宙的一个部分。在这一宇宙中。每一事物都有其根本天性。都有其需要扮演的特征角色。当每人每物都能履行其职责时,一切都会如其所是地顺利、和谐地进行。这是一个秩序的世界观。与今天的观念相比,它更像科学革命以前的西方观念。
在儒家看来,人类是自然秩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然的状态,即使就人类而言,也理应是和谐的,而不是混乱的。和谐社会中的生活既是人类最适宜的生活。也是其天性最向往的生活。儒家的人人平等观念来源于人人生而具备同情、尊重、礼节等道德情感能力,并在其基础上建立人际关系能力的信念@。传统儒家思想的基本信条就是“人性本善”,认为人生而具四种情感,并且这四种情感便是四种德行的始端(《孟子·梁惠王下》)。正因为这一点,才使得人类具备值得尊敬的道德地位,而并非人是权利享有者或潜在的主张提出者使然。
赫伯特·芬格莱特用另一种相关的方式描述了儒家思想中的人类平等及价值。在其著作《孔子:即凡而圣》中,芬格莱特将儒家的人类生活观比作一场神圣的礼仪。人如同“神圣的礼器”,因为在礼仪中人人有其扮演的角色。芬格莱特努力地指明。人类拥有内在的价值,并非因为他们是个体的权利持有者,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内在的价值整体的构成部分。人类有其价值,并非因为他们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因为他们是互相关联的。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对儒家还可以另外描绘一个形象,与芬格莱特神圣礼仪的观点非常接近:生活如同一场神圣的人人出演的舞蹈,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其唯一的成就之路就是成功地表演。人人都是生活之神圣舞蹈的参与者,他们出演孩子、父母等角色,他们具备人类特有的彼此相处的能力,因而他们值得尊重。在这一场景中,人们在两个显然不同的层面上值得尊重,享有尊严:(1)从外在观察者的角度看,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拥有内在价值的整体——神圣舞蹈——的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2)从内在其他参与者的角度看,因为我们都是同一家庭的组成部分,类似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彼此间需要尊重。在这一场景中,平等来自我们共同的成员身份。来自我们在自己特别的环境中达到卓越之境的平等潜力。尽管就舞蹈者之间彼此的权利和责任来界定芭蕾舞等舞蹈是可能的,但如此对待舞蹈者的舞蹈的思维方式还是比较奇怪。而且,这样的界定是没必要的。就舞蹈的目标而言,权利根本远非首要之事,充其量它也只是次要的,而且甚至可能妨碍目标的实现。
上述这一显然比较粗略的场景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尽管儒家从未提及权利,它对人的平等与价值却有着重要而令人关注的概念。我们似乎可以将尊重他人与适宜的自豪归因于人的能力及他们对该能力的实践,虽然他们并非被视为潜在的主张提出者。
相对于费因伯格基于权利的观念,儒家关于人的价值观是否令人满意呢?如果这一问题可以理解为“儒家关于人的概念能够为人们拥有自尊、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适宜的自豪、平等、尊重他人等情感提供一个令人关注而又合乎道理的基础吗”?那么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如果问题意为“儒家关于人的概念能否产生与个体权利享有者观念非常一致的概念?”答案就很值得怀疑了。当然,即使答案是否定的,它也不足以构成谴责儒家观念的原因,除非我们已经认定基于权利的概念是唯一可接受的概念,人必须被视为个体权利的享有者。而认定这个思想之前,我们首先得接受如下观点:人在本质上是个人(individual),他的人性通过理性和自主得以界定,人性得以受到尊重则需要承认个人向他人提出主张的权利。
然而,关注个人,关注个人的理性与自主,关注个人向他人提出主张的权利是西方特有的关怀。传统社会,如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甚至启蒙运动之前的西方社会。显然是从另外的角度理解人之为人的道理。费因伯格可以径直断言这些角度的理解是错误的,权利视角才是正确的,但这样做却显得有些自行其是。
费因伯格自始至终都在论证,没有权利概念,就不可能有人的尊严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尊严”究竟何指。一种似乎有道理的解释是。人的尊严可被理解为对人之为人的内在固有价值的认可。这种价值与纯物体的价值分属不同的体系。如果这样理解,没有权利概念的儒家和其他传统文化,就它们具有自己的人的价值概念而言,同样具有人的尊严概念,借用康德的术语,它们认为人之价值是超越于价格的。
然而,如果人的尊严必须以个人及其权利,或者以人的自主与理性的角度进行分析。那么儒家及其他传统思想或许真的不存在人的尊严概念,但或许也并不会因为这一缺失而损害其伟大性。换句话说,如果费因伯格为之论证的是没有视人为权利持有者的概念做基础。我们就不可能具有关于人之尊严的正确概念,那么他首先必须更加清楚地阐明一个令人满意的尊严概念需要满足的条件,而且必须提供更多的论据来证实此概念的独一无二性。
可以看出。儒家关于人的价值概念是否比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人的价值观更为可取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任何一种答案看起来都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从一个儒者的角度而言,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就一个浸染于个人权利传统的个体而言,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而第三种可能性,即致力于某种跨文化的协议,目前还遥不可及。既然如此,唯一明智的做法或许就是:不排斥任何一种承认人的价值的道德体系,即便其价值不是建立于个人权利之上,而是建立于不同的人的观念之上。
总而言之,我对费因伯格第二个言论的反应是:我并非主张,在我们多元而又破碎的现代社会,成为权利持有者不是建立并获得人的价值意识的一种途径。我认为是错误的,也一直反对的,是把视自身及他人为权利的持有者看做是人的平等、尊严、自尊以及其他价值的唯一途径的观念。我的言下之意是,其他道德理论可能亦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可以支撑起人之为人的尊严意识而无须依赖于个人权利观念。
六、个人权利的价值
最后一章的主要内容,是我关于个人权利之实际价值的一系列思考。再次以篮球赛为例。在篮球赛中,规则话语是重要的,而个人权利话语却是非正常的,没必要的。然而,谈论个人权利却并非不可能。我承认,我们能够将权利引入篮球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或许会想要这么做呢?
原因之一,当队员、教练、粉丝或裁判值得信赖,尽心尽责,能够确定、处理违背规则或角色的行为时,我们无须谈及权利。授予违规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例如投篮时被违规的队员)以特权是没必要的,因为它不可能增加比赛的公平性。投篮队员不可能是客观的、值得信赖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力图保护的是什么?规则的设定既是为了组成比赛,也是为了改进比赛,使其更具有竞争性,因而更具有刺激性和趣味性。而欲达到这些目标,最为根本的是要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其中尤其包括规则的公平应用。
这一认识或许可以启发我们关于权利话语及其重要性的讨论。如果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处理竞争。尤其是个体间的竞争,那么保护竞争者,使其免遭不公正对待便是非常重要的了。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具备基本的合作精神和诚实感,比如在篮球赛中,具备某种可信赖的公正的机构或机制,那么从个人权利的角度界定这一比赛,给个体以特别的提出主张的能力,就不会很重要,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另一方面,假如我们不具备上述元素,那么给予个体以具备自己的主张、坚持自己的主张的能力就是极其重要的。
或许,与上述竞争之例不同的例子也可说明这一问题,比如公司或家庭,一个通过践行角色责任而运行的合作性整体。当一个团体是一个奋斗目标一致的共同体(community)时,权利话语是不需要的,也是不适宜的。事实上,它可能是破坏性的(deleterious)。尊重、平等和尊严都可以根据作为对社群(community)有贡献的成员来理解。该社群依然存在规定与界限,但它们的存在不是因为社群中的个体拥有权利,而是因为为了使社群能够有效地运行、不断地进步而不得不对角色进行界定。此外,当一个社群解体之时,当一个社群没有共同目标,当一个社群中的成员致力于个人的升迁或其他形式的竞争时,每个人都想要且需要个人的保障措施或个人权利。
有时人们认为,尤其是问题家庭中,家庭成员一直拥有权利,而当家庭关系和睦时,生活本身就认可并实践了那些权利,因此它们无须被提及。这是一种界定方式,但是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界定。这种界定同样易于理解,或许更容易理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界定比前一种更少形而上色彩。这种界定就是:家庭中的权利,比如说儿童权利,是为了裁定问题家庭中存在的分歧而设置的社会概念。所以说,不是儿童们一直拥有权利,而是他们在出现了很多问题严重的家庭的社会中逐渐拥有了权利。因此,如果家庭不能履行它照顾好孩子的本职功能,视孩子为权利的拥有者有时就有它的必要性。而问题的根本是孩子会受到怎样的对待、确立权利观念能否促进问题的解决都要依赖于家庭的运行情况。
我一直主张的是,在没有个人权利观念的情况下,人们亦能够保证规则的执行或角色职责的履行,也可以具有人之为人的尊严感和价值感。在我看来,个人权利的价值在于其可以改善其他一些公平机制,而这些机制的设立则是为了保障对规则、角色的遵从,或是为了裁定冲突,或者为了保护个人免受那些拒绝履行责任者(包括国家)的侵害。在任何团队比赛(如篮球赛)中,如果裁判公正不偏,那么面对队员的申诉,他可以以是否违规来裁决,果真有违规现象,就可以按违规程序处理。而如果裁判是众所周知的不公者,那么个人权利就可能是纠正裁判之偏的一种途径。如果家庭沦落到孩子无亲情可依的程度,那么儿童权利话语的引入便可能成为不愉快的必然。
在我们越来越多元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之一或许就是我们太过分裂,以至于看起来除了私利之外我们再无其他利益可以依靠,我们也不可能依赖诸如社群压力等非正式保护措施来保护私利。诉诸权利,亦即在制度内给个体特殊的地位,是确保个人利益得到重视,违规行为被识别并被严肃处理的一种手段。果真如此,我们就会明白在特定的当代语境下,权利观念为何会如此有用武之地。权利能给个人主张以独有的强调;就人权而言,它赋予个体超出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之外的重要意义。
在我看来,倡导个人权利观念是否有意义取决于特定的环境是否需要给予个人主张以特别的重视。假如根本不涉及个人权利观念的道德体系能够同样或更好地服务于人类,那就不应该倡导个人权利观念。
考虑到现代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许多人认为诸如儒家等传统道德体系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即使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不实用于现代社会却远非如费因伯格等人所主张的——意味着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