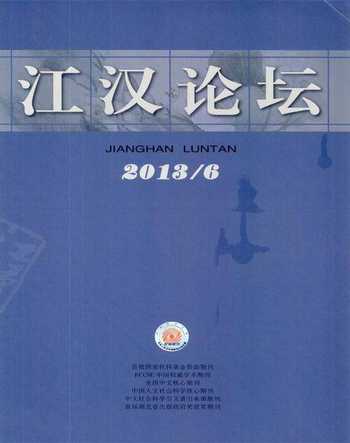以礼仪为权利
[美]安乐哲
一、礼仪之内
礼的概念非常广泛,包括了从风俗习惯到交往礼节,再到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所有方面。它是儒教文化的限定性结构,甚至还界定了社会一政治秩序。礼仪实践当然不是中国的发明,但是它作为稳定社会的重要工具和法律体系的主导因素,使得礼在中国具有了某种独特的含义。
当代中国的人权观念深受西方影响,趋于政治化和国家中心化。与此不同,我探究“礼”这一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组成社会的古老而重要的社会机制。我会揭示礼如何发挥人权观念的效用,如何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接纳人权信条。
“礼”这个字通常翻译为“rites”,“ritual practice”或者“propriety”,在人际关系(bonding)上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礼字与“体”字同源,意为“履也”(embody)、“体也”(to constitute a shape),也指“节文也”(organic form)。礼仪实践也可看做是一种演出:通过规定的仪式影响人际关系的社会实践。英语单词“rites”和“ritual”的词源是引人深思的。拉丁文中“ritus”源于*ri(计数;列举),也是对*ar韵脚的扩展(“加入”,就如“arithmetic”或者“rhyme”)。礼仪实践是社会的韵律。
把“礼”翻译为“propriety”亦有其合理性,它指出了礼仪实践的功能属性(proprietorial implication):使个人融入共同体。实践礼仪,一方面得以按其要求融人社会整体,由此被塑造、社会化;另一方面,个人也参与造就了礼仪所限定的人际关系模式,并且对社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份贡献与参与,“礼”并没有诸如肤浅、形式主义、非理性这些在西方理解中总和礼仪联系在一起的贬低含义。礼并非对外在模式的消极遵从,而是造就社会(making of society),需要个人的投入以及意识到个人的重要性。
虽然礼仪实践最初引导人们进入合法的、确定的社会关系,但它们并非只是根植于文化传统的刻板的行为标准。礼仪实践还有个人创造的一面,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更多是一种倡导而不是禁止。礼告诉参与者何种行为对他或她而言是合适的。在固定的社会模式之外,是一个开放的、个人化的礼仪结构,容纳了每个参与者的独特性。礼是一个柔软的实践体系,显示了个人的重要性。它是君子真知灼见的载体,使其最大程度在传统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礼仪实践的个人化程度各不相同,且其确立的角色是等级的,这些角色形成了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通过协同式的敬重(deference)产生意义(meaning)。对这些角色的扩展、深化过程为其带来了极大的成就感。因此,个人自主(individual autonomy)对于礼治社会来说是遭唾弃的,被视为是极度愚蠢和非道德的。对社会的冷淡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就是那些世代传承、饱含深意的全套礼仪。礼仪传承文化,使人们社会化,让人们融人群体。它给予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念。让人们得以通过继承、发扬群体生活的方式融入社会。
孔子曾宣称,礼仪实践关系到社会和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仪活动在孔子眼中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因为从定义来讲,礼仪不仅允许而且要求个人化。这种和谐认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应该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保持着这种独特性。缺乏个人特色的形式化的礼仪是空洞无物且破坏社会和谐的。
在礼治社会,共同体的定义基于一种彼此尊敬的人际关系模式,这种彼此尊敬是内在呈现的而不是外在强加的。具体的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由创造力而不是权力决定。这种创造力与权力的区别对于理解由礼仪活动所构成的共同体至关重要②。这种共同体是开放性的。个人完整与社会整合的不可分割打破了手段/目的的二分,使得共同体中的每个人既是自身的目的,也是他人实现自我的手段,其模式是相互性的。这种共同体是纲领性的——个不断追寻的未来目标,而不是眼前的现实或固定的理想。这是一个开放的美学成就,像艺术品一样取决于某些特定因素或灵感,而不是公式或设计图的必然结果。
二、权利之外
人权、礼仪实践都是建立、界定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关系限度的社会概念。英语中的“礼”通常是贬义的、形式的,与之相对,中国的礼概念则相反。权(rights)通常意味着力量(power),不是指褒义的合法权威而是一种源于特殊情景下的暂时优势。
19世纪中期,中国人创造了“权利”一词来翻译“人权”(human rights)这一理念,但大多数中国人开始时对这个词语极为困惑③。然而,这一对人权不恰当的翻译不但从此正式进入汉语世界,而且在本世纪颁布的众多法律中反复出现,成了著名的术语。即便如此,这个词在西方政治学中的含义对于中国大众来说仍然是十分陌生的。中国对于人权理念的抵触更多出于其他因素而不是劣质的翻译。西方传统意义中的“人权”与中国的社会情况在很多方面是互相冲突的。
历史地看,我们的人权观念受到小家庭共同体与现代城市国家断裂的影响,在前者,是风俗与传统维护着基本尊严,而在后者,流动的、原子式的人口必须向非人化的、时常是压制性的政府机器主张人权。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工业革命改变了我们对于共同体的理解,故而需要人权保护个人价值。
从传统出发,对于中国古典人性概念做出深入阐发的是孟子。在盂子看来,人的存在严格地说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行动之后取得的成果。“性”的概念——一般译为“nature”——源自对“生”的提炼。“生”是生物的出生、成长、灭亡的全过程。孟子认为。人类自从出现在世界上开始,就处在一种不断变化的与各种关系交错的体系中。这种体系决定了人的本性;它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并贯穿人的一生。对于人而言,它更接近于“性格”、“人格”或“体格”(constitution),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nature”,也不是physis或natura。
孟子认为人是作为自发的、不断变化的关系基质(matrix of relationship)来到世界的,人经由此,通过一生的时间,确立了自己的性。就这一情感纽带(bonds)可以对既定的家庭、共同体秩序做出回应而言,其最初的性情(disposition)是善的。这些情感纽带根据程度不同的灵巧和风格得以培养。培养这些原初的纽带(primordial ties)使人得以为人,超越于禽兽之上。
对于人性概念,孟子没有试图区分作为一个人的实际过程的人性,与作为人之为人过程之能力的人性之间的差别。一种理解关系性人性概念的方法,是考察“性”与其同源词“姓”的共同内涵,后者表示“家族或宗族的字”。与人性概念一样,一个家族的姓为一群人所共享,既规定了他们,也被他们所规定。它表示了一系列的条件,使得每一个成员享有以特殊方式得到培养的可能和机会——如姓所表示的。将一个人的名附属于其后的机会。不论姓还是性都不是一种本质的、先天的能力,二者都是一个人进入关系的焦点。
受以上所论孟子式性论的影响,中国传统中不存在分裂的个体观,这一事实对于中国移植人权的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将自我看做是独立于且先于社会的利益中心(locus of interest),是毫无哲学基础的。在对人性关系性理解的支配下,个人、社会与政治的实现往往被设想为是相互性的。
一些——如果不是多数的话——关于中国对于人权态度的看法不断重复着一种自我牺牲(selfabnegation)或者“无私”的根本成见,一种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空洞人”(hollow men)诠释的当代翻版⑥。然而,将无私归于中国传统,是以不恰当的方式加入了公共/私人、社会/个人的划分,削弱了我们关于中国传统中人(person)是不可化约的社会性的主张。做到孟旦(Munro)所设想的“无私”,首先要有一个个体的自我存在,然后是为一些更高的利益作出牺牲。不论是对个体还是社会而言,认为存在着“更高的利益”,就偷偷地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对抗关系。
无论古今,将无私归于中国传统,都是源于对自私、无私的模糊、含混的理解。在儒家看来,既然自我实现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担当,那么自私的考虑显然是有碍于自我实现的⑦。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义利之辨。“利”造就小人,而“义”成就君子。
将无私的理念赋予中国传统的西方诠释者,往往将国家与个人看做是对立的,这一观念使我们将自由民主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家区分开来。但是这个模式很难照搬到中国,对中国人而言,自我实现既不需要高度的个人自由(individual autonomy)。也无需屈从于公众意志,而是成员间的一种互利互惠,他们处于相互忠诚与责任之中,被这种忠诚和责任所环绕、激励,并确保了个人价值。
在质疑了“无私”是中国人的理想的观点之后,我们必然要考察与之相关的一个论点。即自我实现是通过“服从……主要相关权威”来完成的⑧。每一权威之上都有一更高者,一直到中华帝国的皇帝。如果这一“无私”和顺从的混合是真实的话。那么它与黑格尔对中国极权主义的描述便非常接近了。
这种“自上而下”(top-down)的理解由于相对缺乏公私利益对立的压力而得到鼓励,同时也受到杜维明所描述的“信赖社群(fiduciary community)”中的个人与国家基本信任关系的支持。这种强有力个人与强有力国家密切相连的中国模式,与自由主义西方限制国家权力的想法形成鲜明对比。
在中国,一种传统的看法是,个人秩序(order)与公共秩序是相互作用的,大的结构(configuration)往往来自于当下的和具体的(immediate and concrete)。当国家濒临崩溃时,君子要回到他们的家庭或社群,重新塑造新的秩序。因此,当孔子被问及为何不愿为政时,他回答说处理好家庭秩序本身就是更为广泛秩序的基础。在家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等差之爱的核心原则,决定了直接、具体相对于普遍之原则和理想的优先性。
中国传统对于当下和具体(substantive)的偏爱阻碍了任何普遍的人权概念。同时,也不允许限制国家的绝对权力。在经典政治理论中,政府与民众的共生关系被看做是民为贵的民本。自下而上出现的秩序具有参与和容忍的特点,可以从内部对极权主义做出抑制。因此,在中国,从古到今的冲突几乎总是通过调解、劝慰等非正式的机制来化解的@。这种自我管理的社会只需要一个小政府就可以了。
在中国,政治命令通常以宽泛、抽象的口号形式由公共机构和报刊发布。这些政令在诠释和应用于社会时出现的分歧并不明显。思想、舆论的传播是通过具体的机制,其与由自主个人构成的社会特性相比,远没有后者抽象。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人性观念中没有预设任何超越于共识秩序(consensual order)之上的道德秩序以蛊惑人的诉求或个人良心的诉求,而这样的秩序是有可能破坏共识的。
中国传统中,道德是民族精神或社会性格的文化产物,体现于行为礼仪规范之中。在道德形上学保证自然权利概念的地方,有一个开放的道德论域,在这里对于什么是自然的问题,是可以协商的。鉴于已有秩序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各种具体境况使得普遍性千变万化,所谓可普遍化(universalizability)的概念早已遭到质疑。事实上,中国人对待普遍性原则一向小心翼翼,从文化的根本上讲,他们不愿为了尝试接近先验原则而放弃更为可靠的直接经验。这种偏好的证据在文化中随处可见:产生于具体历史事件的神话传说,由个人精神直接扩展而来的神圣概念@,产生于追求具体历史事件的合理性并得到其支持的理性概念,可用具体历史典范人物类比说明的道德概念,与实际功效密切相连的知识概念,只关注自身(inward-look-ing)近乎排外的自生的文化身份,等等。
中国人排斥普遍性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证据,是他们难以接纳我们所理解的平等观念。我们如同计量单位的个人概念使得数量意义上的平等得以存在,相信拥有等价的本质特性或属性就可以被视为是平等的。如此数量化的平等概念使得平等作为一种质量评估(也就是“好于”)的概念显得不太可靠——如果不是令人反感的话,从而可能导致利己主义、性别歧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等。我们承认人们在等级、尊严、权力、能力、卓越方面的差异是与本质的平等观对立的。
中国将人看做各种角色的特殊基质(matrix),自然无法接受西方所宣扬的生而平等(natural equality)。然而,还有另一种相关的(relevant)平等。尽管人们所处的等级关系反映了他们之问的巨大差距,但是礼仪实践起码在几方面体现了性质上的(qualitative)对等(parity)。首先,人的角色的动态性质意味着其在共同体中的权利与义务在其一生中是基本持平的。一个人作为子女的义务会被其作为父母的权利所平衡。个人的关系领域随着时间推移会在其人际关系中产生一定程度的对等,这种人际关系往往被视为人类最重要的资源。其次,平等(equality)概念如同身份(identity)一词一样是多义的:它可以指两者或多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当被用于一个事物时。它可以指对其他事物而言,使其成为自己,而不是其他事物者。因此,调和(accommodation)也是一种平等。平等的第一层含义源于对相同之处的共鸣,第二层含义来自于对不同之处的欣赏与宽容。平等的重要内涵就是虽然万物皆不相同,但是都允许实现自己。这种平等或对等,不是绝对利他的;事实上,由于一个人所处环境中的各种因素都贡献于其可能的创造,它明显是利己的。在以权利为基础的秩序竭力保障最低限度也是最重要的同等(sameness)之时,以礼仪为基础的秩序则在尽力维护宽容。因为这是和谐的基本性质,也是礼仪实践的志向,被其丰富而协调的内涵所强化。长期以来,这种重视具体超过抽象、重视眼前超过普遍的倾向,使中国人对普世人权的奇怪幻想有一种天生的排斥。
三、宪法或礼典?
黎安友(Andrew Nathan)写过一本关于中国宪法的书,该书的内容是我们分析讨论的突出重点。他注意到,比较美国与中国的宪法就会发现,“广义上修辞的相似而价值观与实践上深刻的差异,是一种很难对付的结合”。这些深刻差异表明,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仰仗礼仪实践来做事,而这些事在我们的社会中则是由保障人权的原则来处理的。
自上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先后公布了不下12部正式宪法,还有数不清的这样那样的宪法草案⑩。由于在中国人传统中,无论是“人性”还是其界定的社会秩序都不是静止的,所以宪法必须保持开放以适应特殊环境中的特殊选民。
具有适应性的中国宪法的另一个相关特征是,它不仅界定了现行的社会政治秩序,而且“计划性地”(programmatic)为进一步的成就提供蓝图⑩。如同礼仪实践一样,这些宪法不要求落实普遍有法律效力的理念,而是从更具体的方面探寻和谐、完善的变动结构(configuration)。任何宪法都只是党的政策与愿望的最新宣言。宪法的改动是具体的,绝非旨在阐发不变原则的修正案。考虑到礼仪共同体(community)对于普遍秩序的抵触,其宪法对权利的保障与我们的情况不同,不是对制定法律设置界限(“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相反,变化着的社会秩序要求法律和党的政策全权处理共同体中变化的权利与义务。
中国的宪法与其说是一个政治文件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文件,其基本功能是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调解纠纷、消弭争端。例如,孔杰荣(Jerome Cohen)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宪法时明确说,它与我们所说的宪法一词不相干。它是“现行权力结构的一种形式化。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制度框架,用于调节竞争权力的各种政治力量”。美国的宪法是立法的依据,而中国的宪法主要是制定礼仪。也就是说,中国的宪法使地位、特权和义务定型化,这样做的假定是,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存在这样的假定,即加强共同体的权威便会削弱构成共同体的具体个人的选择权。因为宪法基本是一个合作的协议,建立在个人与共同体的信任之上,而不是潜在对抗力量的契约,因此没有独立的条款以强化对于国家的权利主张。这样做的假定是,通过共同体对于环境更为直接的非正式压力,以及允许民众的参与,秩序将会形成并得到保障。作为最后的一招,宪法确实规定了可以求助于国家机关,但正如传统中国社会中对法律的求助一样,这是一种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行为。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身处这样的处境本身就暗示了自己有罪。
最后,另一个中国宪法的特征是,权利完全是从一个人作为社会一员的资格派生而来的。在我们的传统中,个人的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权利奠定了个人的社会、政治关系观念的基础。而在中国的环境中,人的存在完全处于共同体的范围之内。权利是从社会派生而来的行为规范(proprieties),而不是源自个人的行为规范。这些规则显然主要被表述为社会福利的赢的权益(entitlement),而不是个人的政治权利。如果人只是社会的存在,那么就可以设想中国的情况:不参与到共同体中去,就使自己失去了享有权利的资格。这种对人的极端社会化定义从中国法律文件中权利与义务不可分这一点上反映出来,在那里即便是教育权这样的积极权利,也同时包涵个人权利和社会义务。
作为独立的文献,宪法正式而抽象。但是即使在抽象的层面对中美宪法做对比,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文件是服务于不同社会的。
黎安友“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家……改造外来思想以适应其熟悉的思想模式”的论断是有道理的。事实上,通过比较中华帝国传统中正式礼仪规范的语言、功能与美国宪法,就能看得出中美宪法间很多类似的深层差异。从这点上说,当代中国宪法可以视为中国维持社会秩序的传统策略和西方法律表述的结合体。
其实,大卫·麦克米伦(David McMullen)早已对传统礼书之一的《大唐开元礼》(公元732年)做了许多重要研究工作。《大唐开元礼》和中国20世纪宪法在形式、功用上的吻合部分可以概括如下:
一个变化的社会需要正式文件使其成为政策一致性的根源,同时需要具有适应性以符合实际的管理政策。《大唐开元礼》以一个王朝的统治阶段命名,是唐建国100年来的第三部礼典,既与过去的礼法一脉相承,也有反映变化的社会倾向的创新。例如,除了包括传统人物外,它还广泛地包括了相关的唐代受祭者,这样礼典既继承了古老身份,又拥有了唐代化的新身份。而且《大唐开元礼》是纲领性的。例如,它将古代军事家姜太公提升到与孔子同样的地位,就是一个具体的创新。它标志着大唐发展军事实力的决心并使之合法化。
尽管《大唐开元礼》是正式的官方文献,却有着基本的社会功能。许多既定礼仪通过现存的等级制度不断重复,既树立了朝廷的典范,也反映了地方的特色。这种吸引社会各阶层成员参与的礼仪模式,是增强个人与共同体关联性的一种好方法。就这样,《大唐开元礼》尽管以抽象的形式主义处理事务,但其内涵却是从共同体的具体成员身上吸取而来,并服务于它所构建的共同体。
四、以文化为中心的人权
中国人对西方思想是非常重视的,但我们并不清楚西方人是否对中国思想也非常重视。现在,我暂且不讨论中国的思想,而是来看看中国模式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强我们的人权概念。
无须赘述我们尊崇人权的种种益处。在今日的世界这些好处既明显且重要。我更愿意去讨论权利理论的一些缺陷。
首要问题是构成权利理论基础的个人的定义。罗斯文(Henry Rosement,Jr.)曾在一篇文章中用一章的内容来讨论这个定义。儒家传统中有丰富的资源可供我们重新审视自主个人的概念(autonomous individuality),尤其是个体优先于社会、环境的一面,实际使情景(context)成为个人目的的手段。这里一个明显的缺点是将个人自由优先于对社群、环境的责任。
一个更情景化的人(person)的定义必然会让我们思考使用个人权利去维护个人应得一切的诱惑。个人自主并不必然提高人类尊严。事实上,如果尊严是有价值的,对个性的夸大可能会阻碍人权的最终计划,而这一计划恰恰可以保护和培养人的尊严。中国的人(person)的概念在区分个人自主与自我实现的差别上是很有价值的。
同样的,我们总爱赋予人权过度的情感意义也要求我们能更好的把握分寸。将人权说成维护人类尊严的重要方式显然有些夸大其词,除非人类尊严是指最基本的生存。将人权看做社群中可能的生活质量的标准,就像将最低健康指标看做宾馆质量的通用准则一样。作为法律的人权是最低的标准,是最后的诉求,这一乞求(invocation)是共同体的巨大失败。
儒家的选择表明几乎所有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实际权利与义务都是由超出法律权限的(extralegal)制度、惯例来维持,并由社会压力而不是处罚来强化的。事实上,依靠应用法律和从属于法律的人权绝不是保护人类尊严的好方法,它从根本上消磨了人性,破坏了我们相互协调、妥协以确定恰当行为的特殊责任。义务的引进调和但同时也限制了关系创造的各种可能性。相比之下,对礼仪的强调能够使这些可能性得到最充分的实现。中国模式显示了非法律机制也能够化解争端。它提供了其他的理性选择从而降低了人们运用法律手段的热情。离开正式程序也就意味着趋向更多的实用性。
一些人对人权的基本批评就是,人权仅仅挑选了人之存在的某些特殊方面加以强调,这种批评忽略了文化环境和人权抽象定义的可变内容之间直接且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指定的(given)权利会因为相关因素的影响而不断重新定义,如各式各样的社会、政治压力。一个变化的人权定义是现实的(realistic),不仅作用于我们的文化发展,也有益于我们对文化差异的理解。
中国对西方模式的学习使得他们对于本国的社会政治秩序有了更加正式和清晰的指导原则。借鉴中国模式也能够使我们对以礼仪为基础的人权有更清楚的认知,对于文化差异有更多的包容:这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有关人权的各种狭隘观念(parochialisms),但它们作为我们人权的实质性内容也应当得到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