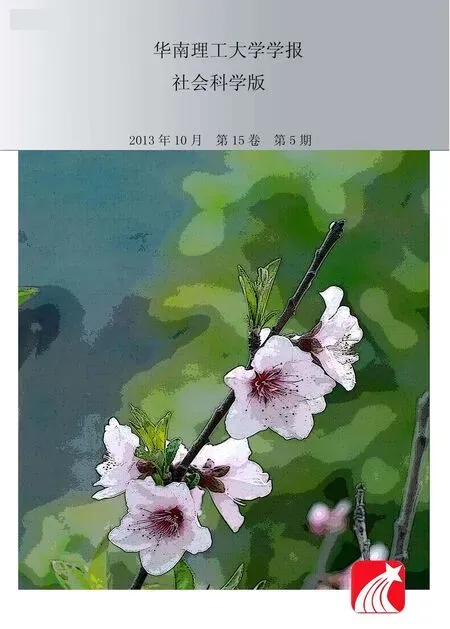试论 《九歌》与 《天问》中矛盾的婚恋观
卓 雅
(贵州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4)
古代文学史讲述中国神话,总要提及屈原在神话思想史上的地位与成就。这与其在中国诗歌史上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相比,同样重大而辉煌。屈赋中大量的古代神话与传说,是直接采自楚地民间,其时楚地仍旧还保存有原始文化遗风。而诗人又以开放的精神与博大的胸襟,突破地域和民族间的局限,使这些古代神话传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楚辞》神话体系。从《楚辞》神话中,于外可以了解到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特征、审美习惯以及原始形态的宗教习俗,巫术礼仪;于内也可以了解作者本人那渗透理性思考的世界观,体味诗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大胆的批判精神。但这还不是全部。在对屈原的两部作品《九歌》和《天问》的分析中,还可以窥见些许诗人所持有的对待爱情、婚姻、家庭的观念。
一、神话可以反映个人的婚恋观
神话作为在特定的远古时代和原始环境中,人类的特殊思维方式及该种方式下的文化产物,反映了彼时的文化规范或思维模式下人们活动的基本形态。其主要功能有二:认识功能和非认识功能[1]12-15。
神话的认识功能,基于原始先民有自己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原始的“互渗律”。他们用“以己度物”“以类度物”的直接方式去推测和解释世界,进而借助想象去征服和支配自然。这种朴素的哲学认识功能,解释了关于世界的普遍本质和宇宙起源等问题,帮助人们认识原始的世界及其历史。神话的非认识功能又有两种表现方式:其一,体现为特定的巫术、宗教类的文化价值。在神话思维中,思维主体和观照对象的不分化性使神话具有不自觉的物我同一、天人感应的特征。此背景下,神与人具有同一的情感、意志。其二,体现为道德与法规的规范功能。“德”与“法”是人类行为规范中最基本的范畴和观念,是一定社会群体为了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行为约束力。道德伦理既然是以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为目的,而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神话所提供的爱情与婚姻的准则无疑也是一个被社会认同、为群体所承认和接受的规范。同时,这种共识的婚恋准则又不乏个体特征:这种相对固定和规范的集体意识需要个体在交互作用中传承。但传承过程中又并非一成不变。传播主体会根据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以其个人观点对神话加以再解读,神话中所渗透的规范会被个人重新定位思考。个体与神话间不断实现个人意识的社会化和社会意识个人化的双向作用。因此,《楚辞》神话中所反映的婚恋观也会打上鲜明的个性化烙印。
针对屈原作品中关涉男女恋爱的情节段落,后人多接受王逸之说影响,通常认为是诗人借助男女情爱之名来隐喻自己与楚怀王的君臣关系,婚姻与恋爱不过是爱国和忠君的代名词。很少有人认为《离骚》中的求女就真是诗人对爱情执着的向往和追求。古人对屈原作品的繁多注疏中,很少透露诗人个人生活的信息。在《史记》本传中也丝毫没有体提及屈原的婚姻生活。因之,后人心目中的屈原一直是忠君、爱国、忧民的一位伟大诗人形象,可缺少了爱情婚姻的“生气”,颇似文革样板戏中“高大全”类的主人公。这样的人物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自然,屈原绝非虚构形象,作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或因中国正史史家不屑于记录男女情爱之类不登大雅之事,以至相关于屈原其人的日常生活史料极其匮乏;又或因历代治《楚辞》学者多秉从儒家思想,绝不从男女之情方面考虑阐发,才使后人几乎看不到诗人的个人生活。所幸近现代学人已经突破思想方面的囿限,在对《楚辞》的重新阐释与演绎中,同时发掘出诗人个人生活的蛛丝马迹。如姜亮夫先生的《女嬃考》就一改前人屈原之姐说或屈原侍女说,认为女嬃是屈原的侍妾[2]61。其他楚辞学者虽未完全认同姜先生此说,但此例可以证明,诗人作品是可以反映诗人自己的个人生活,以及自己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的。因之,本文也做管中窥豹,从诗人的两篇保存神话传说最多的《九歌》与《天问》中,一察屈原对爱情婚姻的某些观念。
二、《九歌》中的情爱观念
《九歌》之作,谱写的是一组情韵哀婉的情歌,具有浓郁的民俗风貌,神奇的宗教背景,深厚的历史渊源,及复杂的思想感情。并不仅止诗人对当时当地祭神歌舞之词“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朱熹语)[3]29,也不仅止诗人寄入自己忠君爱国的情愫,更有男欢女爱的细腻描摹。《九歌》共十一首,闻一多、姜亮夫、苏雪林均认为其中有八首是恋爱篇。这八首是:二《湘》,二《司命》, 《东君》,《云中君》,《河伯》与《山鬼》。不过苏女士认为这八篇写的是“人神恋爱”[4]99,而姜先生则认为写的是四对夫妻神,也就是“神神爱恋”[2]38。其实,无论是人与神的恋爱也罢,神与神的恋爱也罢,楚地诸神在《九歌》已经人性化了。诗人着力深入挖掘诸神的内心世界,细腻地描写他们的心理活动,写的虽然是神,却处处渗透着人的情绪爱憎,人的悲欢离合,有一股浓浓的人情味,这些恋爱诗篇明显反映出了人的爱情经历与感情纠葛。
《湘君》、《湘夫人》是九歌中的双璧,二湘分明是一对恋人在无尽的相思中等待,在失约的怨望中倾诉。《湘君》像女神湘夫人写给湘君的情诗,诗中诉说了自己对夫君的思念:我在沅湘之上徘徊寻找你呀,我那“蹇留中洲”的夫君。我修饰起美丽的容貌,乘上桂木龙舟,止息了江上的风浪,盼望着你,可是你却没出现。循环往复疾走的龙船象征我那焦急的心情,连身边侍女也垂泪叹息。你失信爽约,“告余以不闲”,使得我把定情的信物“袂”与“佩”负气地投入水中,姑且以“逍遥容与”打发时光吧。但我心中何曾丝毫忘却了爱人?《湘夫人》是男神湘君写给夫人的情书:我在洞庭湖边眺望,希望佳人在傍晚能如约而至。为了这次约会,我作了多少准备,一大早就奔走在江边,傍晚才回到岸旁。我“筑室兮水中”,用荷叶作顶,香草作壁,紫贝铺院,芳椒成堂,薜荔为帏,白玉为镇……这一切都为了夫人你的到来。但是九嶷山的仙灵来了而你却未到。我也一样负气地把“袂”“褋”投入水中,怅然若失地徘徊容与。“这两首像热恋中男女往来情书的诗,使人们整体地感受到了两人一波三折的约会,体会的是热恋中情人忧心忡忡的疑虑,展现的完全是现实化、生活化的爱情故事。湘君与湘夫人因对方失约的赌气举动和自我解嘲的心理,都和几千年后现代青年的不差分毫。试想,诗人若没有源于生活的现实体验,即便再修饰以华丽浪漫的辞藻,也只能使诗篇徒具文彩,如何能够细腻地表达出热恋中人们的真性情呢?”[5]177
湘夫人“在斫冰兮积雪”努力开辟航道,表明了她追求爱情的执着。外界坚冰积雪的恶劣环境是不能阻止两人的相见,关键的是两人心灵上的契合:“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决”,“交不忠兮怨长”。诗人在这几句诗中表述了这样一种观念:两情相悦、两心相爱的基础是心、恩、忠。相恋的人要有心灵的契合,若两心不合,即使有媒人也是徒劳;还要有深深的恩爱,若恩爱不深就会轻易分手;更要有对爱人的忠诚,若交往不忠诚就会导致深深的抱怨和猜忌。心、恩、忠,这三者促成的恋人间的互相信任,才在爱情中起决定性作用。两心若是同床异梦,做出再大的努力也只是徒劳,没有深切的恩情,也就容易放弃。湘君与夫人有着心灵上的契合,忠诚的恩爱之情,即使两人约会失误,未得相见,只能造成轻微的伤害,虽然两人都是敏感而彷徨,但又能把这一切的失误调和弥补。所以,两篇的结尾虽有二人自我解嘲的借口,但读者却没有感到两人绝望的放弃与决裂,相信真爱可以弥补失误,两人最终一定重逢。[5]178
湘君与湘夫人是一对配偶,已为学者所公认。大司命与少司命是否为一对配偶神,学界还有争议。若承认二者也是一对夫妻的话,则《大司命》《少司命》两篇勾勒的爱情故事又是另一番景象。大司命是人类生命的主宰之神,大权在握——“何寿夭兮在余”,诗中他的出场有点阴森可怖,以“飘风”“冻雨”为先驱;但又气度非凡地亮相—— “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更让凡人神秘莫测—— “众莫知兮余所为”。
这样一个掌握生杀大权、严肃高傲的神却恋爱追逐着一位佳人。他要“析疏麻兮瑶华”献给那“离居”中的意中人,并且“结桂椒兮延竚”,怀念着恋人,直到愈是相思愈愁煞,最后以“愿若今兮无亏”来祝福远方的爱人。比起大司命的阳刚之气,诗中的少司命则具阴柔之美。她是保护幼小的司爱女神,她倏忽而来倏忽而逝,入不言出不辞,忙忙碌碌地“为民正”。她降落在厅堂之上,“满堂兮美人独与其目成”。这里的“目成”是眉目传情的爱意,一个“独”字就表明了少司命的爱是情有独钟的,是一见钟情的。在这第一眼的接触中感到了“新相知”的快乐。
诗的结尾写到她的离去,由于“司命”之职的繁忙,又让人感到“生别离”的悲伤。在二司命是为配偶神的前提下,可以假定少司命钟情的对象就是她的夫君大司命,于是这两首互文性的诗篇就构成一个狂傲的大丈夫气概的男子与秋兰麋芜般的女子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相聚总是短暂的,各自的工作总让他们聚少散多,他们惆怅着思念对方,想着有一天一起“沐兮咸池”,“晞发阳阿”。在二《司命》中,诗人精准地刻画了男性在恋爱中的心理:因大权在握而倨傲的大司命,原来也为相思所苦,看起来冰冷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炽热且温柔的心,在愁苦的相思中默默地等待,为所爱之人祈福,祝愿她身体无亏。如此这般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诗人对此是持赞许的态度,丝毫没有后世道学家以谈儿女私情为耻的虚伪与做作。诗中还明确提出这样的劝诫之言:“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要趁这青春年少,多和爱人亲近,否则岁月流逝,相爱之人会渐渐疏远。当然,这里的亲近不一定局限于肉体的亲密接触,还应该指两人心灵的沟通与思想的交流。远隔两地的恋人即使看不到对方,接触不到对方,但通过心与心的交流、亲近,爱更浓,情更深[5]178。
除了二湘、二司命外,《河伯》、《山鬼》两篇诗中的恋爱情状也非常明显。作者描写了两种截然相反不同的爱恋行为:河伯是“与子交手”“游兮九河”的欢乐,山鬼是“思公子兮然疑作”的怀疑。情人携手共游河川,享受的是爱情带来的快乐;情人失约未至,心中疑云顿生,忍受的是爱情带来的酸楚。但这不同效果均是建立在真挚互爱的基础之上,诗人能创作出如此高于生活的艺术典型,其创作体验必是根植于生活的。读者从这明显地表现爱恋的六篇中,可以感到屈原本人的某些爱情观,也隐约地辨识出诗人的意识深处似乎倾向宣扬一种情感至上的非理性文化。
三、《天问》中的婚恋观念
气势磅礴,构思奇特的《天问》共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涉及宇宙时空、社会历史、个体存在等多个方面。屈原对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构成、思想的各个领域进行反思,对既有知识提出强烈的质疑,对公认规范给予强力的冲击。从其中的一些提问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诗人对婚姻家庭观念的思考。
在对神话传说中半人半神的圣王们的婚姻状况,屈原是抱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的。
他对禹和涂山氏的关系提出质问,表明他对正式夫妻关系的崇尚。实际上,传说中禹的时代正处于原始部族社会时期,男女两性关系自由松散——只要双方愿意,就能“桑间濮上”地自然结合,不需要媒聘之礼,婚姻大典。大禹治水忙忙碌碌地四方奔波,有可能与涂山女情投意合地在台桑结合,新婚四天后便匆忙离开,这样迫不得已的“新婚别”并不是“嗜不同味,而快朝饱”。屈原以他那时的婚姻伦理观念为准则来批评禹,用“通”字来暗示涂山女非禹明媒正娶。在他看来,圣人化身的禹应该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何况刚从天上下来正怀着“伤念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的哀痛呢?
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人物,羿的神格是自相矛盾的。在不少上古文献中,零星散落有关羿的事迹。有的传说他为民除害、射落九日,是一位英雄;有的传说他淫游射猎、夺人妻室,近似一个无赖。在这些文字中,有的地方用“羿”字,有的地方用“后羿”,以至有后人辩争羿与后羿是不同的两个人。在《天问》中,羿“射夫河伯”、“妻彼雒嫔”,古代学者这种行为抱持肯定态度,连天帝都认为是河伯的不对[6]70;或认为河伯危害人民,羿拔箭以射……实则他们均在为羿粉饰其圣人形象。屈原却敢于持否定态度,大胆指责羿夺人妻室,实在太不象话。其实,以现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羿的事迹,我们就易于理解羿矛盾的神格。后羿应当是原始社会的一位英勇的部落首领,他为自己的部族除害,射落危害人民的“九日”。羿射河伯,可以解释为后羿部族与河伯部族之间的原始部落战争,雒嫔作为河伯的配偶,在部落战争失败情况下,作为失败者的财产理所当然归胜利者所有。成为羿的配偶了。于现代人很容易理解的事,于处于战国时期的诗人就是不合伦理的了。
再来分析诗人对舜的婚姻的指责。因鳏而闵忧在家的舜,年纪很大了,父亲为什么不替他张罗婚事?而如果“尧不告舜父母而妻之”,男方父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尧的两个女儿又怎能和舜成亲?孟子曾为“帝之妻舜而不告”的不合礼法的行为辩解过,而屈原对舜这段“没有告知父母就擅自婚配”的传说表示怀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发生的。可见大家都认为“娶妻如何,非媒不得”,婚姻的前提是父母之命,这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极度有损圣王的光辉形象。
诗人把救民于火热的羿、救人于水深的禹、孝亲悌弟的舜的婚姻加以比照,说明他们的婚姻很值得怀疑。其目的是怀疑这些古代神圣帝王是否具有高尚的人格,要求理性地去思考其传说中的本来面目。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他衡量这些圣王是否具有高尚人格,选择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他们的婚姻。神圣的先王应该合乎“神圣高尚”的婚姻准则,即娶妻应该合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礼法,这礼法正是从周公礼乐一路延续下来的儒家礼法。
屈原对传说中的女性的婚姻也采取同一种标准来衡量。
“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无论他问的是女神还是星宿,都是以人类社会为参照。早在商周时期,人类社会就已从以部落为社会基本单位进入了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体系时代。夫妻是家庭的基本构成元素。无论是一夫一妻制还是一夫多妻制,若缺少夫、妇中任何一方,家庭都是不完整的。屈原认为女岐应该是有夫的,才能生九子,焉知女岐传说当产生于母系社会,人类处在“民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群婚阶段,所以那时的神话中不知道九个儿子的父亲为谁是不足为怪的。诗人看来,女岐应该是有个配偶、组成家庭的,否则那九个儿子便成现今所谓“私生子”,这是违反当时婚姻道德规范的。
另一个女岐与前一个女岐不是一人。一说女岐即浇嫂,一说女岐是女艾[7]。
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身?女岐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女岐身份并不重要,可她与浇的关系总之是不正当的,若为叔嫂关系,那是绝对不允许二人之间有所暧昧的。即使是无夫女子,也不应该“馆同爰止”,住宿在一起。最后诗人写出了这样做的后果,女岐勾引浇,致使后者“颠陨厥首”,她自己也“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考察西周早期时代,烝报的婚姻制度还存在,兄死嫂嫁叔的事是正常的。但随着社会进步到了东周时期,这类事多为人们所不齿。屈原对浇与其嫂的越轨行为的责问,恰好表明了诗人对当时婚姻伦理观的认同。
诗中还问及了吞卵生子的简狄,平胁曼肤的有易女,汤的吉妃有莘氏以及妹嬉、褒姒、妲己等女子。屈原都是以其为男子附庸身份来观照这些历史上有名的女人的。说到简狄,是作为帝喾的妻子、契的母亲来问“喾何宜”,如何生契?说到有易女,是把她作为勾引王亥的工具来问“何以怀之”?说到有莘女,是把她作为成汤吉妃来问“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这里说有莘女是伊尹的陪嫁倒比说伊尹是有莘女的陪嫁更妥当些。诗人提到桀、幽、纣的三个红颜祸水的宠妃,说这些女性不是君王的好配偶,而是亡国的祸首,她们是男性的附属品,男性在她们身上得以体现德行的高尚与否。
要之,在《天问》中,男女性爱已为既定的社会秩序所强制,受社会伦理观念强烈的挤压,使文本风格更倾向于一种理性至上的非感性文化。而诗人对神话人物们两性关系的责问与非议,就彰显出屈原对东周时期婚姻礼法的认同感。
四、矛盾的婚恋观形成原因
从上述分析中,读者看到的是两种相抵牾的爱情婚姻观念。
屈原在《九歌》中极力赞颂美好的爱情。他不止改动了楚国祭神之歌的文词,更重要的是赋予了楚神人类的思想感情,把凡人爱情生活中种种微妙复杂的感情假托在神的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了爱情生活中的境遇和情感,追求的期待和焦灼,成功的欢乐与幸福,失恋的痛苦和忧伤……。 《九歌》不但是颂神祭神之歌,也是歌颂爱、祭祀爱之歌。诗人把爱情理解为一种超拔于社会现实上的单纯理想,情爱的自由没有礼教的拘限。爱的基础是“相知不渝”,两心相悦后是情感的升华。即使湘君、湘夫人作为夫妻亦是靠相知的情感彼此吸引,而不用婚姻来维系,这种相知的吸引力亦使河伯、山鬼沉溺于爱的欢乐与痛苦中。[5]178。
相反,诗人在《天问》又极力而冷静地强调婚姻伦理。虽然他是在对世界、宇宙、历史、现实进行深刻的思考,批判善恶是非的错位与颠倒,在当时具有超前意识和进步意义。但是由于时代限制,诗人无法了解历史是从低级社会到高级社会逐步发展的,也无从拥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辨证观,所以拿战国文明时代的婚姻礼制来衡量原始社会时期的群婚行为和对偶婚制,故先古圣王的婚姻在他眼中便成了违反道德礼仪的放荡行为了。《九歌》中对两性爱情的承认在《天问》中被抛却,注重把两性关系放在厚重的周礼婚制约束模式下承认,强调符合礼法的婚姻,个性情感则忽略不计了。一方面强调“心相知”的感性爱情,一方面强调“合礼法”的抑制情感,这就是屈原对待两性关系的矛盾的爱情婚姻观。这种情况的原因正在于诗人深受楚国巫风文化和中原理性文化的双重影响。
不同的地域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大风格。不同文化大风格影响下的文学作品就有不同的艺术品格。《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曾根据地域特征和民俗差异对各地文学的特征略作提示,郑玄也在《诗谱》中联系各国自然条件和风俗制度论诗之思想与风格。楚民族由于地域、气候、风俗、政治、宗教、历史等原因而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思想意识、心理特征和审美习惯,学界称为巫风文化。巫文化是楚国音乐、舞蹈等艺术的源泉,也渗透到文学中,形成了文学艺术中的楚风。同理,各个民族文化对待两性关系的婚恋观也未必同一。巫风文化的内核——宗教祭祀活动给了楚人爱情的摹本,也催生了楚人自由奔放的情感。正如朱熹所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用男女之情相诱以娱神的巫术思维动机,使得情感在这过程中得以放肆宣泄。虔诚的宗教情感投入,运用歌舞致情达意,生成了一个充满自由的恋爱空间。这个空间没有世俗社会的干扰,没有婚姻家庭人伦道德的束缚,再加上楚国礼教文化落后于北方,战国时期楚地男女还保持着淳朴的恋爱风俗。这种不同于中原礼教的婚恋观念就不自觉地在文学作品上反映出来。一方面,长期浸淫在巫风文化中的屈原,其作品势必具有感性的浪漫主义特征。《九歌》在形式上把楚地这种淳朴恋情如实记录,在内涵上更加以作者自我的理想化——即在第二节中提到的,爱情要以“相知”来彼此吸引,以“恩” “信”来彼此维系,强调“心相知”的爱情观念,从而把原始以性交、生殖为目的纯生理的两性关升华为以心灵相通为基础的两性关系。这种爱情观正是构成现代社会文明婚恋的基础。在这一点上,诗人有着超越时代的进步。[5]178。
另一方面,《天问》代表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理性现实主义。北方中原各国,自西周以来,都以宗法家族制度为社会基础。姜先生在《简论屈子文学》中曾详说:“北方文化至殷周以后已固定。至周初,宗法制度建立后,北土先受此一制度影响。其文化以家族为基础。大宗、小宗、祖庙、郊社等礼俗,将全国社会整体,置于此一准则规律之中……”[7]223因此婚姻制度只是宗法制度的一个体现而已,虽然有《周礼·媒氏》所谓“奔者不禁”,但更注重《礼记·昏义》中的“昏礼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8]179的纯粹政治目的的婚姻。男子是为了事宗继后而娶妻,感情是次要的、被排斥的。女性呢?则根本无权去要求什么,更别说爱情。屈原在接受北方文化理性精神熏陶的同时,此种在以后禁锢了中国几千年的婚恋观也必定对他有所影响。如第三节所述,因为时代的局限而缺乏历史进步论的观点,对原始婚姻状态缺乏了解,拿后世婚姻礼制来评价前人,从而对其人的道德人格加以怀疑抑或否定的作法是不妥的。尤其在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反思中,“兹细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之兴亡作骨,其所以兴在贤臣,所以亡在惑妇”[9],就落了后世道学先生的窠臼。
总之,《九歌》与《天问》都是诗人在战国时代南北文化大融合背景下保有神话原形的作品。在作品中诗人倾注着自己的感情与思考,透露出了两种不同的婚恋观念:一个理性,一个感性;一个拘束,一个自由;一个落后,一个进步……这种矛盾的表现正显示了诗人对南北文化“兼收并蓄”的博大襟怀与开放的精神,其小小的缺憾并不影响后人对屈原伟大人格的崇敬。
[1]赵沛霖.先秦神话思想史论 [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2]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3]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苏雪林.屈原与《九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4]洪兴祖.楚辞补注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卓雅.从《九歌》看屈原的婚恋观 [J].重庆:知识经济,2008(07).
[6]闻一多.天问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郑玄.十三经注疏[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林云铭.楚辞灯[M].林氏挹奎楼刻本,清康熙二十四年.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