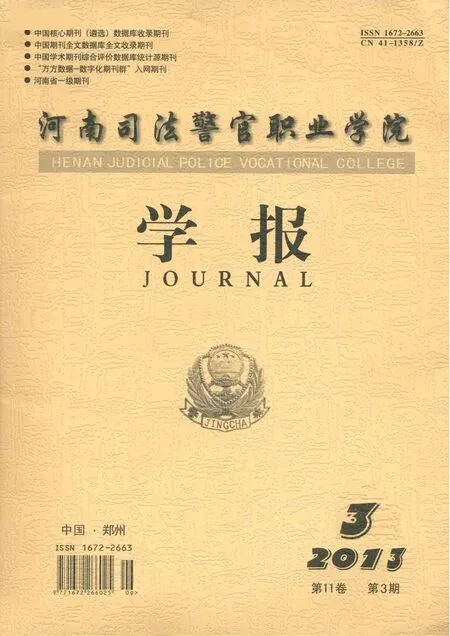期待可能性的本质与妨害司法罪的认定
马荣春,徐晓霞
(1.扬州大学 法学院,江苏 扬州225009;2.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检察院,江苏 溧水211200)
一、期待可能性的本质
按照普遍的理解,源自德国“癖马案”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概念,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刑事违法行为时,还有被期待或被信任不实施该刑事违法行为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期待可能性问题的论述可谓连篇累牍,但期待可能性的本质是什么却未见有人予以深究。在笔者看来,期待可能性的本质可从不同的层面上予以把握:从法学层面上,期待可能性的本质即法益尊重的可能性。在任何一个可用期待可能性来解释某种犯罪的成立或不成立的场合,如果某种犯罪被期待可能性解释为成立,则其所对应的行为便被认为具有法益尊重的可能性;如果某种犯罪被期待可能性解释为不成立,则其所对应的行为便被认为不具有法益尊重的可能性。用法益尊重的可能性从法学层面上解读期待可能性的本质,正好解答了为何具有期待可能性的刑事违法行为最终不是阻却违法性而是阻却有责性。从哲学层面上,期待可能性的本质即相对的意志自由。有人说:“自由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自然界和社会力量以及自身力量的支配,这种支配以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为前提。”〔1〕正如我们所普遍接受的,人所具有的自由是相对的意志自由。在实施刑事违法行为和不实施刑事违法行为之间,当行为人选择了前者,则通常应被看成是相对意志自由的结果。而正是基于相对的意志自由,支配刑事违法行为的主观心理活动才有了道义上的色彩而成其为罪过,正如有人指出:“期待可能性不是罪过心理以外的独立构成要件,也不是罪过形式本身的构成要素。期待可能性无非是意志自由程度的外在形式,是评价行为人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大小的根据,是罪过心理产生的前提。”〔2〕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刑法学中的期待可能性,便是指行为人支配自己实施适法行为的可能性。由于支配行为的是人的(相对)自由意志,故刑法学中的期待可能性便最终发端于意志自由,而这个作为发端的意志自由便构成了期待可能性的最中坚、最内核的东西即本质,正如有人指出:“期待可能性理论正是借助于相对的意志自由科学地说明了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这是其获得强大生命力的最主要原因。”〔3〕那么,当我们说某种行为因仍然具有期待可能性而成立犯罪,则意味着行为人没有发挥或把握好自己的相对的意志自由,从而对法益造成了本可避免的侵害或践踏;当我们说某种行为因根本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因而不成立犯罪,则意味着行为人无力把握自己的相对的意志自由,从而对法益造成了无可奈何的侵害或践踏。
对于作为犯而言,期待可能性实质即“不作为的期待可能性”;对于不作为犯而言,期待可能性实质即“作为的期待可能性”。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期待可能性,我们都可用法益尊重的可能性与相对的意志自由分别从法学层面和哲学层面予以审视和把握。
除了在紧急避险上有着典型的体现,期待可能性在妨害司法的相关具体犯罪上也有它的运用与体现。
二、期待可能性与妨害作证罪的认定
张明楷教授在讨论妨害作证罪时提出:“问题之一,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本罪行为的,是否成立本罪?一种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采取非法手段妨害作证的,也构成本罪。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一般的嘱托、请求、劝诱等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以妨害作证罪论处;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并不缺乏期待可能性,宜认定为妨害作证罪(但可以从轻处罚)。至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实施本罪行为的,则应认定为具有期待可能性,应以本罪论处。”〔4〕张明楷教授显然是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并列在一起而与刑事诉讼作相对应的讨论,并在刑事诉讼中又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嘱托、请求、劝诱等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和采用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予以区别对待。如何透彻地解读张明楷教授的“基本观点”呢?首先,为何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同样的妨害作证行为因具有期待可能性而可构成妨害作证罪?在笔者看来,其原因在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诉讼结果所关涉的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因最终体现为财产性利益而显得相对不重要或不重大,而当事人尚不至于被这样的切身利益“威逼”到必须妨害他人作证的程度或地步,故才有当事人具有不妨害他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期待可能性一说,进而其行为应以妨害作证罪论处。相比之下,刑事诉讼的诉讼结果除了关涉当事人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通过罚金所体现的财产性利益之外,主要关涉的是当事人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较为重要或重大的自由甚或生命这样的切身利益,而在这样的利益所“威逼”之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取一般的嘱托、请求、劝诱等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实属“趋利避害”的本能所致,故言其缺乏不妨害他人作证或不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期待可能性,从而其行为不构成妨害作证罪。但为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又言其并不缺乏不妨害他人作证或不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期待可能性而宜认定为妨害作证罪(但可以从轻处罚)呢?笔者的理解是,当他人还可被通过嘱托、请求、劝诱等方法来阻止作证或作伪证,则说明他人还是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留下“可乘之机”,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不具有不妨害他人作证或不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期待可能性,故其行为不宜以妨害作证罪论处。相比之下,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时,则说明他人没有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留下“可乘之机”,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也就变成了“强人所难”,于是其不妨害他人作证或不指使他人作伪证也就具有了期待可能性,故其行为宜以妨害作证罪论处。
“问题之二,共犯人阻止同案犯作供述或者指使同案犯作虚假供述的行为,是否成立本罪?这不仅与期待可能性有关,而且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有关。本书认为,同案犯的供述,对于其他共犯人而言,就是证人证言。因此,共犯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同案犯作供述,或者指使同案犯作虚假供述的,符合阻止他人作证、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条件,因而可能构成妨害作证罪。但如果采取一般的请求、利诱等方法阻止同案犯作供述,或者指使同案犯作虚假供述的行为,则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宜以犯罪论处。所以,对于同案犯之间的串供行为,不宜认定为妨害作证罪。”〔4〕显然,共犯人采用请求、利诱等方法阻止同案犯作供述或者指使同案犯作虚假供述与采用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同案犯作供述或者指使同案犯作虚假供述,被张明楷教授作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予以对待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么,又如何来透彻地解读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呢?犯罪人本来都负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当同案犯还可被通过嘱托、请求、劝诱等方法来阻止作供述或作虚假供述,则说明同案犯还是给共犯人留下“可乘之机”,于是,“趋利避害”的本能便使得共犯人阻止同案犯作供述或指使同案犯作虚假供述,仍不具有不妨害他人作证的期待可能性,故其行为不宜以妨害作证罪论处。相比之下,当共犯人采取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时,则说明同案犯没有给共犯人留下“可乘之机”,而共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同样也就变成了“强人所难”,于是其不阻止同案犯作供述或不指使同案犯作虚假供述同样也就具有了期待可能性,故其行为宜以妨害作证罪论处。
三、期待可能性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认定
案外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行为的定罪问题。张明楷教授在讨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时指出下列行为均属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第一,行为人单独为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第二,行为人与当事人共同毁灭、伪造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与当事人并不成立共犯;第三,行为人为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是帮助犯,而是正犯;第四,行为人唆使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是教唆犯,而是正犯。”〔4〕论者所列举出的第一种情况是最明白不过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行为类型,而第二、三、四种之所以属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行为类型,且在行为人与当事人并不构成共犯的前提之下而由行为人直接成立“正犯”,在根本上是因为当事人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令其自身行为难以成立犯罪。其实,案外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类型还有一种情况,即案外人或行为人接受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教唆而为其毁灭、伪造证据。特别是第四种情况,作为刑事案件当事人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身或亲手毁灭、伪造证据尚且缺乏不去毁灭、伪造证据的期待可能性,则其教唆他人为自己毁灭、伪造证据便更缺乏这样的期待可能性了,但案外人或行为人却因具有期待可能性而成立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案外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较为复杂的情况如张明楷教授指出:“在刑事诉讼中,由于举证责任在公诉一方,而公诉方也有义务收集被害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因此,即使经过犯罪嫌疑人同意,帮助其毁灭无罪证据,也妨害了刑事司法的客观公正性,应当认定为帮助毁灭证据罪。但是,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由于举证责任在当事人,当事人放弃自己的利益,法院作出了不利于当事人的判决裁定时,法院的判决裁定也是客观公正的。另一方面,毁灭证据的行为人得到了当事人的同意,也没有侵害当事人的利益,所以,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帮助当事人毁灭有利证据或者伪造不利证据的,不宜认定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4〕这一论断也可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予以解读。具言之,在刑事诉讼中,由于举证责任在公诉一方,且公诉方也有义务收集被害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故即使经过犯罪嫌疑人同意,则帮助其毁灭无罪证据的行为仍然具有不予帮助毁灭的期待可能性,故仍然可成立帮助毁灭证据罪;而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我们本可用被害人承诺(损害)的理论来理解,为何得到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承诺而毁灭对其有利的证据或伪造对其不利的证据的行为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我们也可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解答问题,即当当事人甘愿放弃自身的利益,则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便不具有不去帮助毁灭、伪造的期待可能性,故难以成立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更为复杂的情况如张明楷教授指出:“毁灭、伪造自己是当事人案件的证据的,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而没有被刑法规定为犯罪(在此意义上说,本罪构成要件要素是客观的责任要素)。”〔4〕“问题是,自己的刑事被告案件的证据,同时也是共犯人的刑事被告案件证据时,行为人实施毁灭、伪造行为的,是否成立本罪?”〔4〕对此问题,张明楷教授介绍国外的学界观点是:“第一种观点认为,共犯人的刑事被告案件,也应视为他人的刑事被告案件,故上述行为成立本罪。因为‘共犯人’不是本人,只能属于‘他人’。此观点受到的批判是,如果是单独犯则不处罚,然而因为有共犯关系则受处罚,这是不均衡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共犯人的刑事被告案件,应视为自己的刑事被告案件,故上述行为不成立本罪。理由是:犯罪人毁灭自己的犯罪证据而不可罚,是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而毁灭共犯人的犯罪证据与毁灭自己的犯罪证据具有共同的利益,也缺乏期待可能性。但是,共犯案件的证据,对每一个共犯人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该观点忽视了这一点。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专门为了其他共犯人而毁灭证据,就属于毁灭他人刑事被告案件的证据,因而成立本罪;反之,如果专门为了本人或者既为本人也为其他共犯人而毁灭证据,则不成立本罪。其中,有的学者提出的理由是,毁灭自己的证据之所以不可罚,是因为考虑到其处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地位,所以,专门为共犯人毁灭证据的,应评价为毁灭他人的刑事案件的证据。但是,这种观点是用犯罪的主观内容来限制‘他人’刑事被告案件,在方法论上不能令人满意。”〔4〕张明楷教授原则上赞成第三种观点:“当行为人与其他人均为案件当事人时,如果行为人所毁灭、伪造的证据在客观上仅对(或者主要对)其他当事人起作用,或者行为人主观上专门(或主要)为了其他人而毁灭、伪造证据,则由于存在期待可能性,应认定为毁灭、伪造其他当事人的证据。在我国,采纳第三种观点也不存在‘方法论’问题。因为刑法第307 条第2 款所规定的‘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本身就包含了主观上为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意思。”〔4〕在笔者看来,行为人所毁灭、伪造的证据在客观上仅对(或者主要对)其他当事人起作用与行为人主观上专门(或主要)为了其他人而毁灭、伪造证据,是两种不同或对立的情况,那么,认定后一种情况即主观上专门(或主要)为了其他人而毁灭、伪造证据具有期待可能性,是妥当的;而认定前一种情况即行为人所毁灭、伪造的证据在客观上仅对(或者主要对)其他当事人起作用也具有期待可能性,则是欠妥当的。仅仅“帮助”一词,就让人们从常识、常理、常情上难以接受行为人毁灭、伪造证据在客观上仅对(或者主要对)其他当事人起作用系出自“过失”即出于一种“认识错误”,却依然成立帮助(他人)毁灭、伪造证据罪。那么,当行为人毁灭、伪造证据虽在客观上仅对(或者主要对)其他当事人起作用,但在主观上是专门(或主要)为了自己,则仍应认为行为人不具有不去毁灭、伪造证据的期待可能性,故难以成立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将行为人毁灭、伪造证据在客观上仅对(或者主要对)其他当事人起作用而不分行为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则难免有客观归罪之嫌。我们不能期待共犯人在“趋利避害”本能驱使下毁灭、伪造共同犯罪的证据即既是自己又是同案犯的犯罪证据时,还能够清醒认识到或准确把握其所毁灭或伪造的证据究竟是对自己还是对同案犯起主要作用,或曰作出这样的期待是不切合实际的。
四、期待可能性与窝藏、包庇罪的认定
一般的案外人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主动予以窝藏或为之包庇,显然因具有不予窝藏或包庇的期待可能性而可成立窝藏、包庇罪。一般的案外人接受犯罪的人的教唆而对犯罪的人予以窝藏、包庇,则犯罪的人因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难以构成犯罪,但接受教唆者因具有不去窝藏、包庇的期待可能性而可构成窝藏、包庇罪。国外学者认为,犯罪人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的,成立伪证罪的共犯;但教唆他人窝藏自己的,则不成立共犯。〔5〕显然,教唆者即犯罪人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难以成立犯罪,故才有教唆者即犯罪人不成立共犯之说。至于犯罪的人的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对犯罪的人予以窝藏或包庇,在立法没有除罪规定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仍可认定成立窝藏、包庇罪,但可将期待可能性作为一个酌定情节,即以期待可能性减弱为由而给予从轻或从宽处罚,即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对犯罪人的近亲属实施的窝藏、包庇行为,原则上应认定为缺乏期待可能性,不宜以本罪论处。即使构成犯罪的,也应从宽处罚。”〔4〕
对照共犯人与同案犯之间所发生的妨害作证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情形,则共犯人与同案犯之间所发生的窝藏、包庇行为也应成为一个较为复杂或更加复杂的问题而予以讨论。对此问题,张明楷教授指出:“犯罪的人窝藏、包庇共犯人的,应具体分析。如果专门为了使共犯人逃避法律责任而窝藏、包庇的,成立本罪;反之,倘若专门为了本人或者既为本人也为共犯人逃避法律责任而窝藏、包庇共犯人的,则不宜认定为本罪。但是,如果明知共犯人另犯有其他罪而窝藏、包庇的,应认定为窝藏、包庇罪。”〔4〕如何解读前述论断呢?在笔者看来,由于窝藏、包庇的性质并不亚于共犯人以暴力、威胁或贿买等方法阻止同案犯作证或指使同案犯作伪证,当后者并不缺乏即具有期待可能性,则前者也不缺乏甚或更加具有期待可能性,故共犯人窝藏、包庇同案犯专门(或主要)是为了同案犯(包括受到同案犯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诱惑)的情况,仍应或更应成立窝藏、包庇罪。倘若共犯人专门为了自己逃避法律责任而窝藏、包庇同案犯的,则仍可认为缺乏或不具有不去窝藏、包庇的期待可能性,从而不宜认定为本罪。共犯人与同案犯之间的相互窝藏、包庇行为还有一种情形,即共犯人受到同案犯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胁迫而窝藏、包庇同案犯的。对这种情形,由于窝藏、包庇同案犯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共犯人本人,又外加共犯人受到同案犯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胁迫,故应认为共犯人缺乏或不具有不去窝藏、包庇的期待可能性,从而不宜认定为本罪。
五、期待可能性与脱逃罪的认定
对于脱逃罪问题,有人指出:“如果是看守人员私放罪犯,而罪犯借机脱逃的,该脱逃人是否成立本罪?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人认为,此种情况下,应对看守人员定私放在押人员罪(《刑法》第400 条),同时对脱逃之人定本罪。我们认为,此种观点难以成立。处理该案时,对看守人员定私放在押人员罪即可,对被私放人犯的脱逃行为不应定罪。其理由是:此种情况下在押人犯不脱逃不具有可期待性,因而,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其脱逃的行为不具有刑事归责性。”〔6〕在笔者看来,在看守人员与在押人犯直接有通谋或经由第三人而有通谋的情况下,看守人员打开监室之门或提供其他机会让在押人犯脱逃的,则看守人员与脱逃人犯或定脱逃罪的共同犯罪,或按私放在押人员罪与脱逃罪分别定罪。在看守人员“单方”即在没有通谋的故意之下打开监室之门或提供其他机会,而在押人员“纯粹”借机脱逃的情况下,才产生脱逃者的脱逃行为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而是否论以脱逃罪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即便在前述情况下,如果认为脱逃者的脱逃行为已经不再具有不脱逃的期待可能性,从而论以无罪,则是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一种滥用。在前述情况下,至少不能认为脱逃者不脱逃的期待可能性已经荡然无存,即在仍应认定其脱逃行为构成脱逃罪的前提之下而以其期待可能性有所减弱而给予从轻或从宽量刑。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看问题,如果在前述情况下以脱逃者已经全然不具有不脱逃的期待可能性而论以无罪,则是在相当程度上变相地肯定看守人员的私放行为具有某种合法性。一个观点或命题如何,假设时常是一种有效的检验方法。
但是,如果是非法关押或根本无罪而被错误关押,则情况截然不同,正如有人指出:“我们认为,所谓‘依法被关押的’,应当是指依据事实和法律、按照正当程序应当被关押(的人犯)。因此,如果那些被非法关押或者根本无罪却被错误地作为犯罪嫌疑人而加以关押者从被关押处所逃逸的,就不能按犯罪论处。”〔6〕如果是非法关押或根本无罪而被错误关押,则在押者的脱逃行为便具有不脱逃的完全的不可期待性,而应论以无罪。对前述问题的解答,其道理正如在妨害公务的场合,之所以要求公务行为本身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实质上和形式上都合法,乃是因为妨害不合法的公务行为将因缺乏不予妨害的期待可能性而不能论以妨害公务罪。当然,如果妨害不合法的公务行为造成明显过当的结果,则有构成其他犯罪如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可能。
诉讼结果直接关涉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从而“趋利避害”的人之本能在妨害司法罪中的体现更加直接和明显,进而直接受制于“趋利避害”本能的期待可能性便在具体的妨害司法罪的成立上发挥着独特的解释力。在妨害司法罪的成立上接受并运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可以看成是司法人性化的一种生动体现。
〔1〕叶敦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3.
〔2〕姜伟.期待可能性理论评说〔J〕.法律科学,1994(1):26.
〔3〕李立众,刘代华.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J〕.中外法学,1999(1):33.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83-784.
〔5〕〔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285-290.
〔6〕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628.
——以被告人翻供为主要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