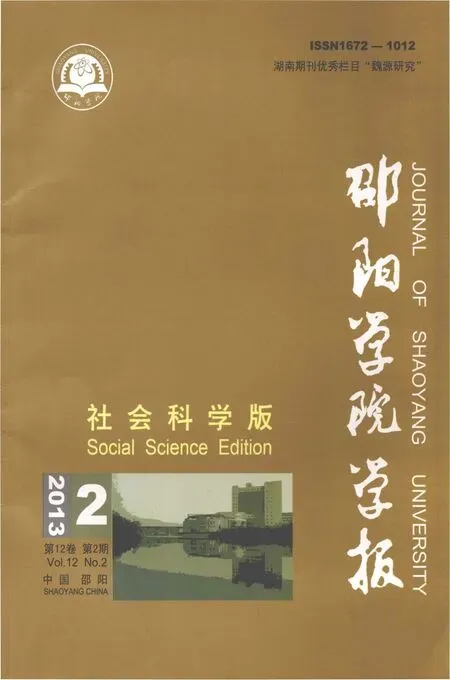试论王充与东汉批判思潮
颜 为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东汉一朝,批判思想尤为显著,代表人物有王符、崔寔﹑仲长统等。崔寔针对时局“上下怠懈,风俗雕弊”提出了改革意向,仲长统著《昌言》在天人关系﹑历史治乱﹑政治批判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见解,王符著《潜夫论》对东汉社会的政治、边事、风习、教育等方面提出了批判。虽然他们的批判对于针砭时弊起到过一定作用,但并未如王充《论衡》那样细致而全面地对整个东汉社会的弊病而加以批判。王充①学界对于王充的思想研究相对比较成熟,主要著作和代表性论文有:蒋祖怡的《王充卷》、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王举忠的《王充论》、徐斌的《论衡之人—王充传》、朱绍侯的《论王充对孔子及儒家学派的评价》等。在民风、士风、官风三个领域分别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乱象,开启了批判思想的先河,从而引领了整个东汉社会的批判思潮。
一、王符、崔寔﹑仲长统的批判思想
史载王符“耿介不同于俗”,仕途郁郁不得志,因此“以讥当时失得”[1]王符的批判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一,对东汉社会弊政的批判。针对当时弊政百出,腐败不堪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了“上医医国,其次医疾”[2]的观点,并指出政治得失的症结所在:“违背法律,废忽召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3]、“贪残专恣”、“侵冤小民”。[4]对此贪赃枉法、盘剥百姓之举,王符进一步指出:“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5]其二,王符对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提出了批判。针对豪强一族兼并土地、鱼肉百姓的现象,王符尖锐地指出:“宁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6]另外,他还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主张,如:论富民: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论求贤:“国以贤兴,以谄衰”[7]的用人主张;论边事:积极实边的政策;论谶纬:不迷信的无神论;论正学:以“正学为基”的教育主张。由此可以知,王符著《潜夫论》虽对东汉社会的政治、边事、风习、教育等方面提出了批判,但其批判并未完全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和揭露社会乱象丛生的本质。
《后汉书·崔寔列传》说:“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8]崔寔“少沉静,好典籍。”自小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深感百姓之疾苦,崔寔的经历使他深知国家治乱与人民安康之间的关联,因此他在对社会的批判中,对下层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改革尤为关注。对当时社会上土地兼并、苛捐杂税、流民倍增的现象也提出了批评,故而有“指切时要,言辩而确”之称。他的主要批判思想有:其一,反对宦官、外威专权,主张君主亲政,求治在民的思想。崔寔认为君主必须亲政,只有牢牢掌握国家权力方可避免宦官、外威或大臣利用职务之便行一己之私,一旦权贵得势势必造成政治上的黑暗。其二,反对崇古,提倡关注现实。他认为天下之治理应当因时制宜,政策的制定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反对盲目信古,否则将酿成“贤佞难别,是非倒纷”的悲剧;在社会问题上,他认为存有三患之弊:一曰奢侈浪费,二曰财富匮乏,三曰厚葬害民。无疑,崔寔的批判是有力的,只是批判的对象有显零散,未能形成完整的批判体系。
据载仲长统善文辞,颇有文名,为人“耿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9],故而有“狂生”之名。其批判思想主要表现在:其一,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主张。对东汉以来的天道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从而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彰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谶纬经学妖言惑众的假象。其二,对外戚宦官乱政现象的批判。东汉和帝之后,外戚、宦官乱政,争权夺利之势使朝野混乱不堪。对此,他提出了“政务十六端”,但多为空洞的复古思想。另外,仲长统的人生观也表现出了其思想矛盾的一面。他主张以儒家学说为尊,同时也提出了歧视天下士人的“三俗”、“三可贱”、“三奸”之说,这一点与王充相比颇有几分相似但不如他深刻,而且其思想的主观性颇强从而降低了可操作性,显得迂阔。
综上所述,王符、崔寔、仲长统作为东汉社会批判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于揭露东汉衰败的社会政治、浮华的社会风气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们的批判范围相对较窄且不够细致,对于东汉社会—官风腐化、民风浮华、士风日丧等乱象都未能全面揭露其真相、分析其原因、透析其本质。因此,这表现出了其批判的局限性,相反,王充的批判却更显得全面而透彻。
二、王充对东汉社会的批判思想
(一)对东汉社会民风的批判
民风可谓是衡量社会兴衰的晴雨表,民风淳朴则是国家兴盛的表现,民风浮华则是社会衰竭的征兆。王充针对社会上鬼神论蔓延﹑忌讳四起以及盛行厚葬的习俗而加以批判,表现在:
其一,对鬼神论﹑忌讳的批判。“人死为鬼”在当时成为一种公论,各种关于鬼的传说层出不穷,针对此,王充进行了一一考订。他指出:人死不为鬼,反对死人的精神能变鬼之说,他主张:“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10]究其所以是“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之故。与此同时,社会上忌讳也大肆泛滥,盛传四种忌讳:“一曰讳西益宅;二曰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三曰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四曰讳举正月、五月子。”[11]王充指出:“忌讳非一”,忌讳的本质即假托神怪,借死人之亡灵以恐吓世人,使“世人信用畏避”。世上本无“鬼神之害,凶丑之祸”,忌讳无非是为了“教人重慎,勉人为善”罢了。王充的此番见地开启了东汉一朝破除迷信的先声。
其二,对于厚葬习俗的批判。王充一贯反对劳民伤财的厚葬并指出厚葬是个人虚荣心驱使的结果,即“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他认为:“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厚葬与否与恩义无关,“今厚死人,何益于恩?倍之弗事,何损于义?”而儒家提倡的“不明死人无知之义”的厚葬,将给社会造成“财尽民贫,国空兵弱”,甚至“国破城亡,主出民散”的悲剧。如:“论死不悉则奢礼不绝,不绝则丧物索用。用索物丧,民贫耗之至,危亡之道也。”[12]《潜夫论·浮侈篇》中也有关于厚葬习俗的记载:“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此无异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今天下浮侈离本,僭奢过上,亦已甚矣。”[13]当然,他也明确告知世人,厚葬恶习是由于人们对“死人无知,厚葬无益”这一道理的认识局限所致,显然,这一主张有益于民智的教化。
(二)对东汉社会士风的批判
诚如《荀子·儒效篇》中所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14]然而东汉一朝“公侯已下,玉石杂糅,贤士之行,善恶相苞”[15]这不得不引起身为士人身份的王充诸多的愤怒和不安,“论汉晋之际士大夫与其思想之变迁者,固不可不注意士之群体自觉,而其尤重要者则为个体之自觉。” 王充正是“个体自觉”的一个代表,表现在:
其一,对于谶纬迷信妖言惑众的批判。史载光武帝“尤笃信其术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17],汉儒也追随其后争学图谶之学,使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鱼龙混杂。和帝﹑安帝之际,“浮华交会之风”[18]更是盛行一时,“在那时,一个‘士’的阶层,有两条可以通向统治阶级的道路:一条是通过科举制度,另一条是从事于谶纬迷信。”[19]《潜夫论·务本篇》中也提到:“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20]这与王充所思所想不谋而合,正因如此,造成了社会上“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萤惑百姓。”[21]对于那些无德薄才、愚弄百姓的“佞幸之徒”王充批判其为“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而那些妖言惑众的俗儒一旦得志,对于国家和社会无异于一大祸害。
其二,对于学风不端迷信权威的批判。由于社会上“传书之言,多失其实”因此让人“多所不安”[22]。对于迷信权威之风,王充首先向孔子发难:“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23]而王充提出批判和反对迷信权威的真正原因在于:“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为学之道:“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因此,王充的的批判无疑起到了净化学风的作用。
(三)对东汉社会官风的批判
由于社会上流行着重文吏、轻儒生的一种官本位之风以及官员贪赃枉法之流弊,而王充其人又是一个“仕不急进”、反对官员以权谋私之人,因此,他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不满,表现在:
其一,对重文吏,轻儒生﹑官本位思想的批判。“社会的复杂化,使各种社会要素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以等级性的社会分层和政治文化上的正统相继为基础的封建礼法……它已不能适应不断变迁中的社会形势了。”[24]所以,社会的复杂化使儒生和文吏出现职业性分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王充认为儒生与文吏各有所长,只是分工各异,所谓儒生不如文吏一说是一种谬论。他认为,在追求目标上:“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儒生治本,文吏理末”。在道德情操上:“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在与当政者的关系上:儒生显得“安分守己”,而文吏则变得“机灵乖巧”。之所以造成这种风气,王充把它归之于纲纪的败坏和学风的不正,即“徇今不顾古,超雠不存志,竟进不案礼,废经不念学。是以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25]
其二,对官员贪赃枉法﹑残害忠良的批判。王充在仕途生涯上坚持“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26]他痛恨并揭露了官员为谋求升迁所表现的丑陋行径。如:“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27]他认为官员“庸人屈起”的出身很难保证为政官员不贪赃枉法及自身名节的“贞洁”,即“世俗之所谓贤洁者,未必非恶;所谓邪污者,未必非善也。”[28]由于当时选官制度存在着“以名取人”“以族取人”[29]的弊端,即“黑白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30]因此官员选拔的公正性却备受质疑。首先,那些具有大才之人被拒之于门外。他论述:“圣贤务高,至言难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而对于那些有志于改变社会的贤良之士却屡遭陷害,如“奋志敖党,立卓异于俗,固常通人所谗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损。”其次,期待有所作为的官员会遭到“群起而攻击”。如:“动百行,作万事,嫉妒之人,随而云起,枳棘钩挂容体,蜂虿之党啄螫怀操”最后:环境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善恶。如:“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31]、“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32]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唯有世俗圆滑的“乡原之人”方可苟且偷生,因为“乡原之人,行全无阙,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也。”所以他直言不讳:“今则不然,作无益之能,纳无补之说,以夏进炉,以冬奏扇,为所不欲得之事,献所不欲闻之语。”即很多人为了一己之私而陷国家于不义。然而,王充认为造成这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权者的随心所欲,他说:“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圣主之民如彼,恶主之民如此”。[33]《潜夫论·贤难篇》中却认为:“今世主之于士也,目见贤而不敢用,耳闻贤则恨不及。虽自有知也,犹不能取,必更待群司之所举,则亦惧失麟鹿而获艾猳。奈何其不分者也?”原来正是因为当权者的“小肚鸡肠”,故而造成了君臣离间、荒于政事的悲剧。一言以蔽之:“上梁不正下粱歪”。
三、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东汉社会的批判思想,王符、崔寔﹑仲长统虽独占一席,然而王充却占据了主导﹑开启了先河,从而引领了整个东汉社会的批判思潮。
[1][17][清]赵翼撰.廿十二史劄记[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3.
[2][3][4][5][6][7][13][20][21][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崔寔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仲长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11][12][15][22][23][25][26][27][28][29][30][31][32][33]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8]孟繁冶,夏毅辉.汉末衰征:“浮华交会”之风[J].殷都学刊,2007,(2),55-60.
[19]蒋祖怡.王充卷[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24]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