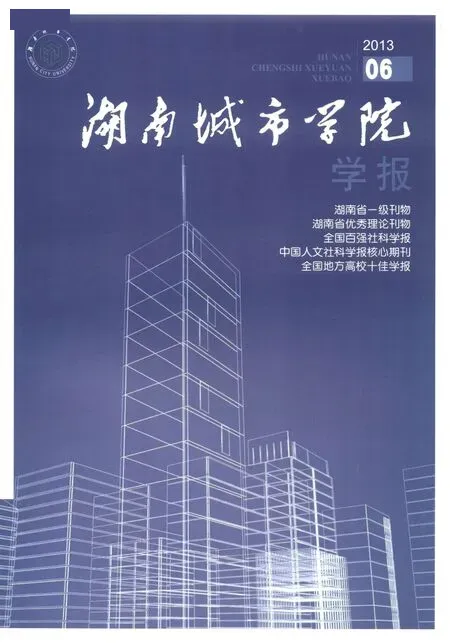“经世致用”与“通经致用”观念再议——以晚清湖南今古文经学论争为考察
张利文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长沙 410003)
传统中国是一个重视“实用”的社会,孔子弟子子夏所说的“君子学以致其道”、“学而优则仕”这些名言,已蕴含了古代知识分子“学以致用”、“救世济民”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子夏这一精神的来源,若不必追溯更早,至少是发轫于孔子的。学问必欲表达政治述求或经济关怀,肇始于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后《春秋》尊王攘夷、拨乱反正等微言大义的经学思想,经过秦汉乃至唐宋历代儒生的阐释与发挥,形成了儒家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主流传统。尽管这一以学术为治术的治学路数在近代遭受到一定争议,如梁启超批评说:“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1]31但可以明确的是,“通经致用”始终是贯穿在晚清今古文经学论争,尤其湖南近代经学发展史中的一个共通的“目的”。
一、“致用”观念之回顾
子贡曾问孔子:“有美玉於斯,韫椟而藏诸?求善沽诸?”孔子回答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2]91在孔子看来,儒者之学应当是付诸实用、待沽而售的。藏于书斋、无补于世的是无用之学,纵使闭门著书卷而怀之,也只能是无道之世下不得已的权变。“经世致用”的观念经过历代士大夫的宣讲,渐成一种民族意识。
“致用”一词之源,首见《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杨伯峻注曰:“致用,板、臿、梮诸用具置之于场地。”[3]244-245意即火星出现时,应置土木工具于场中而待用。《易·系辞上》有:“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4]340然而《左传》与《系辞》此两处“致用”之“用”主要是“物用”、“器用”的层面,与孔子所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经世层面上所说的“用”还不完全一样。[2]182后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5]2519《魏书》中说“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6]2864这些“致用”之“用”才更多地倾向了儒者治国治民的层面,也就是说带有了孔门“致其道”的经世意味。
“经世”二字大概首出《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7]83这里的“经世”,王先谦释为“经纬世事”。[8]21秦汉以降的史书中出现“经世”一词,则不胜枚举,如《后汉书》有:“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9]2901《宋书》说:“安不忘虞,经世之所同”。[10]95王宏斌先生在《关于“经世致用”思潮的几点质疑》一文中认为:
在古人心目中,“经世”本来就是具有实践意义的“用”……现在把“经世”、“致用”两个词语重叠在一起,不仅语义重复,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在古籍中凡是“经世”出现的地方,不必出现“致用”;同样道理,凡是“致用”一词出现的地方,“经世”一词也绝不出现……“经世”……本来就是行政之“用”。“经世致用”一词的使用者开端于梁启超。[11]106-114
笔者完全同意王宏斌先生关于“经世”即“致用”的观点,也认同古籍文献中大多数语境下,“经世”与“致用”语义等同,且罕见并列使用。但不甚赞成作为同义词的“经世”与“致用”不可以重叠使用,同义复合词并不会造成“概念的模糊不清”和“词义的不严谨”。而且“经世致用”一词早在清初就已出现,如孙奇逢在《四书近指》中说:“诵诗读书所以经世致用,嘘古人已陈之迹,起今日方新之绪,方是有用之学。乃有诵诗三百而诎于言,所谓儒生俗士不达时务者耳。”[12]725古籍中虽少有“经世致用”连用者,但在明末清初,这一思想已是士大夫中的普遍意识了。
值得指出的是,即便被清初诸儒指谪为空疏之学的“王学末流”,似乎也不是不讲经世致用的。且不论王阳明本身就是平定宸濠之乱的事功大儒。其大弟子王畿也再三强调“儒者之学,务于经世”,[13]1200王畿求道并不废主事,这是他自认为“吾儒”别于佛、老的地方。 当万表编辑《皇明经济文录》商榷于王畿时,王畿亦首肯此书“不可不备”。[14]8王学传人管志道也说过“德以忠信进,不以入虚入玄进”。[15]9-24后来冯应京编撰《皇明经世实用编》更体现出王门后学学风中固有的经世一面。玄谈心性是否果然会导致政务上的“空疏”无用,顾炎武对三王“清谈、新说、良知”误国的指责是否确然无诬,[16]1032也许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但可以确定:明末清初标榜“实学”之诸儒与王门后学对何谓虚实、何谓经世、如何经世的理解存在着差异。用传统术语说,就是内圣外王是儒者共通的主张,但对内圣的体认差异,可能导致外王述求方式的不同。
梁启超注意到了顾炎武等明末清初知识分子提倡经世致用后,此一思想在晚清再次复活的现象:“这些学者(笔者注:梁氏后文指名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朱舜水等人) 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 因为时务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 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 他们对于明朝之亡, 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 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 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 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 是为政治而做学问”,[17]16“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18]71-72正如梁启超所说,清朝晚期“经世致用”的提出相对于明末清初是一次“复活”,中间间隔了一个时段“经世致用”的低谷,这个低谷期便是乾嘉考据学派兴起的一百余年。
经历了乾嘉汉学而复活的经世致用,在“通经”的述求上更为强烈,这时的致用思想更多地表现为“通经致用”。前文已述“经世”与“致用”是一对同义复合词,经世即致用,致用即经世,因此可以说“通经致用”比“经世致用”更多了一层“通经”的内涵。“通经”说在西汉立五经博士时就已流行,《汉书·艺文志》载:“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19]3594五经者,《易》、《书》、《诗》、《礼》及《春秋》,通一艺即通一经,凡博士弟子能通经者,不仅蠲其徭赋,而且还可补“文学掌故”官职之缺。这大概是“通经致用”较早的形态,或者严格说是一种“通经致仕”的现象。较之“经世致用”,“通经致用”更强调源自“经典”的意义,这个“致用”不是空穴来风的,必以经典为依据,至少主观上应该如此。尽管东汉古文经学与西汉今文经学在“通经”的方法上存在不同,但通经致仕或通经致用是其共通的述求。北宋王安石也主张“通经”与“经世”结合,他说:“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所赖焉”。[20]1915至于陆王心学,我们说同样具有“经世致用”的外王述求,然而却未必恪守“通经”的原则。如陆九渊曾说“吾人皆士人,曾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岂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无事,优游以食,亦可为耻,乃怀安非怀义也”,[21]457尊王攘夷之春秋大义跃然纸上,不可谓陆九渊没有“经世”情结;但陆九渊又说:“六经注我,我(何)注六经?”[21]399所以我们说陆九渊有“经世致用”的抱负,却难说有“通经致用”的观念。“通经致用”是一个外延比“经世致用”更狭窄的概念。至于“通经致用”一词较早的完整出现,也是在明末清初,与孙奇逢、顾炎武同时代的朱鹤龄提出:“今也专奉四大儒为祖祢,而孔、毛、马、郑十数公尽举而祧毁之,何怪乎通经致用者之世罕其人乎!”[22]489这句话也道出了朱鹤龄对短于“笺解名物、训诂事类”的宋儒不能“通经”的指责。
二、清代“经世致用”与“通经致用”观念的流变
宋代刘彝说:“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23]25按照刘彝的看法,儒家之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体、用、文。所谓文,即包括经典、训释、辞章等一切垂法后世的文本,是“文以载道”的载体;而所载之道,则是儒家“历世不变”的道体,所谓“君臣父子、仁义礼乐”者,宋儒的“天理”、明儒的“良知”或清儒所说的“义理”,皆属于此范畴;所谓“用”,则是指明体而后润泽斯民的功用,儒家所谓“康济小民”或“经世致用”,其述求就体现在这一方面。后来,一代鸿儒曾国藩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24]442不过是从“文”之一面,独立出了“考据”的内容。
宋明理学家,不论是程朱或是陆王,都追求“体”上见道,大多也不忘经世之“用”,但在“文”或“考据”上,不甚重视。虽然朱熹多讲“道问学”,略重名物,但与汉学家相比,毕竟要疏略许多。清初学者,如顾炎武,重“文”轻“体”,其“理学经学也”这一命题剥落了理学形而上的追求,[25]58将目光回落于考据与世务之中。顾炎武指责宋学为“虚”,标榜自己是“实”,然而不论从顾炎武本人之事功,或是以顾氏为鼻祖的乾嘉朴学而言,所谓“实学”均未实现“经世致用”的原初目的,实际上反而走向了“华而非朴”的反面。[26]174-274顾炎武对明王朝覆灭于“玄虚”、“清谈”的指责恐有错误历史总结的成分,梁启超指出顾炎武轻易否定理学的失误在于“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18]10华山也指责说:“顾炎武的哲学思想是比较贫乏的……主要由于他的狭隘的经世观点使他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花劳力,同时他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也限制了他在丰富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做理论的提高。”[27]56-62
稍后的颜李学派标榜“实用”,更加极端。他们不仅把汉唐笺注训诂视为“无用”,更抛弃了宋学对“性理”的追求。颜元说:“千余年来,率天下人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28]251“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28]78在颜元看来,经世致用的知识并不源自书本,而是来自于“习”。所谓“某谓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28]54颜元致力于“礼、乐、农、兵”之用,[28]51-52反对从经典中或从本心中发明本体,他强调的是“临事”而“习”的经验实践。剥落了性理与经典之后,颜李学派“实学”最终的落实处无外乎“礼、乐、农、兵”四大要目。也就是说颜李学派在“体、用、文”三事之中只认可了当下的“用”,对性理之“体”与典章之“文”均给予否定。此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之学”既无补于世,也是无法流传长久的。
乾嘉考据学派对“经世致用”态度略微复杂,如戴震“抱经世之才”,“论治以富民为本”,[29]259汪中“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30]291然而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考据之学,无论吴派还是皖派,都丧失了清初顾炎武等学者倡导的“致用”述求。即便如“抱经世之才”的戴震,在说到“三不朽”时,也暗示了“立言”高于“立功”的价值倾向。王引之更是直截坦言:“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31]147相对于顾炎武批评的王学末流,乾嘉学派对“经世致用”的主动疏离更加明确。这不仅将顾氏黜宋崇汉,讲求“实学”经世的设想付诸东流,也偏离了传统儒家学以致用的本怀。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使得乾嘉学派的学术走向了与治术相分离的独立道路,开启了近代中国纯学术研究的序幕。学术研究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既不为干禄之工具,亦不侈悬更高更美之目的,使其治学的态度与成果都更为精审与科学。就“体、用、文”三事而言,可以说乾嘉学者在主流上放弃了“体”与“用”两个方面,惟在“文”上下足了功夫。乾嘉学术自身成为后来今文经学者眼中“无用”之学的现实,反证了顾炎武重文轻体,诋尽空谈的思路并不能带来济世之实用。
复兴“通经致用”思想的主要还是道光以后崛起的今文经学家,常州学派的魏源说:“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 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 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32]24魏源给予“通经致用”一个明确的说明性表述,即“以经术为治术”,也就是说以六经为蓝本,“形为事业”,直接为经世济民的治国之术服务。鸦片战争以至甲午战争之后,内忧外患的外缘性因素促使崇尚致用的今文经学由复活而高涨,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并以此为理论开展戊戌变法,将近代的“通经致用”观念推至极致。从魏源“出使专对”、“以经术为治术”,到康有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33]19可以看出今文经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高度提倡“通经致用”,要求学术直截地服务于治术——尽管其学术在原典忠实性上遭到了古文经学家的猛烈炮轰,但出于对经典诠释方法的差异,今文经学家常常并不以古文学家的指责为然。今文经学家从自己的立场阐释六经、发扬春秋大义,并积极地为其维新变法的政治述求做理论铺垫,成为引导清末民初思想巨变的先声。
三、清代湖南今古文之争中的通经致用观念
了解了“通经致用”学风在有清一代的演变,然后我们把眼光聚焦在近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湖湘一地,可以发现在新旧思想激荡的背后,始终涌动着一股“通经致用”的原初动力,而不论他们的知识背景或政治述求有何不同。
湖南一省,学问重于经世,是有历史渊源的。自南宋胡安国、胡宏、张栻确立湖湘学派,就为湘学奠定了“得其体必得其用”的理学经世派学风。[34]131清初王夫之、道咸时曾国藩,都以推崇经济、主张事功的理学名世。罗克进曾说:“湖南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35]523湖湘理学的浸淫使湖南学风对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问窗外事的乾嘉朴学心存抵触。叶德辉曾说:“乾嘉以后,吴越经学之盛,几于南北同宗,湘人乃笃守其乡风,怀抱其忠义。经世之作,开风气之先;讲学之儒,奏戡乱之绩。流风广衍,本不以考据为能。”[36]176
说湖湘学术“独立自由”(钱基博语)也罢,说“不入流”(罗志田语)也罢,[37]51-83乾嘉汉学风靡全国时,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是确实的。待到汉学在湖南略成规模之时,已是王先谦、皮希瑞、叶德辉等人活跃的清末之际了。此时江浙间经学大家虽不乏其人,然而与乾嘉盛世相比已是余波,全国范围代之而起的“显学”已是亟求变革的公羊学或鼓吹欧风美雨的西学了。尤其在陈宝箴、江标、徐仁铸、黄遵宪等地方大吏的支持下,经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中的躬身推行,康有为的公羊学在湖南大行其道,这与迟到却仍欲登上经世舞台的湖南古文经学势必发生冲突。今古文经学之争在湖湘一地的表现也就带有了清末民初学术演变的痕迹。
此中最重古文经学的人物是仰止许慎、自号郋园的叶德辉。叶德辉,字焕彬,清末民初长沙人,祖籍江苏吴县。其祖避太平军战乱迁居湖湘时“除衣箱外,皆书簏,大抵均江浙乾嘉诸儒先之书”。[38]45-49叶德辉17岁入岳麓书院,接受传统的理学、时文教育外,也跟随宁乡崔识学习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39]23-24在崔识的引导与家藏经书的熏陶下,叶德辉对《说文》等文字训诂学问逐渐发生了兴趣,23岁因“登乡荐,北游京师,于是日与日下知名之士文酒过从;又时至厂肆,遍取国朝儒先之书读之,遂得通知训诂考订之学。”[40]252以古文经为旨归的叶德辉对今文经学,尤其《公羊学》素无好感。且其性最好詈骂,除对庄存与略存敬意外,对今文经学家几乎无人不骂,如其诗曰:“公羊肆流毒,经亡国亦亡。祸首两礼部,刘龚扬沸汤。变法托改帛,大义日晦盲。”[41]383被目为公羊学“流毒”、“祸首”的两礼部正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人刘逢禄与开拓者龚自珍。此今文经学“流毒”之愈下,叶氏之攻讦则愈烈,其评价又说:“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宋翔风倡为今文之学,摭拾西汉残缺之文,欲与许、郑争席,至康有为、廖平之徒,肆其邪说,经学晦盲,而清社亦因之而屋焉。追原祸始, 至今于龚、魏犹有余痛。”[42]420
清代今文经学自庄存与开始就试图摆脱“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纯粹训诂学风,发扬公羊学的经世义理。龚自珍、魏源沿着庄、刘开辟的路径继续前行,在鸦片战争前夕,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迫切要求,重举公羊学旗帜,以通经的名义,呼唤变法。如龚自珍从“张三世、存三统”的传统公羊学观念出发,倡言变法先声:“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43]319魏源痛斥乾嘉学术之无用:“以训诂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32]24其代表作《默觚》分《学篇》与《治篇》,由学而治的意图十分明显。魏源与龚自珍相应共唱变法之先声,他引《诗经》“物其有矣,维其时矣”,而主张“变古愈尽,便民愈甚。”[32]48盖学风之转变,“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44]1-35由庄、刘发微,龚、魏推衍的清代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学风,到了清末康、梁之时,终于发展成声势浩大、托古改制的变法潮流。这些呼唤变革的种种言行,在宗奉古文经学,且思想保守的叶德辉看来,不仅学术而且治术上都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也便有了叶德辉以龚、魏为“余痛”,以康、廖为“邪说”的猛烈抨击。
自幼受学于岳麓书院,又长期浸淫于湖南学风熏习下的叶德辉,尽管自称“半吴半楚之人”,身上却也带有湘学浓厚的“康济时艰”的先天烙痕。考察叶德辉的著作及书信,叶德辉虽然不满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但他并不否认《春秋》等儒家六经有“大谊”的存在。叶氏在辛亥前后编成的《经学通诰》经学教科书中,讲到了如何治经的方法,即“五通”:通章句、通校雠、通小学、通大谊、通政事。[42]431-437由“章句”至“小学”当属音韵训诂的乾嘉“通经”之学;由“大谊”至“政事”则明显是“致用”之学。叶德辉“以学术为治术”的通经致用目的非常明确,他虽主汉学,却不像乾嘉诸儒那样仅仅满足于饾饤训诂,如他在贬低却不甚攻击皮锡瑞时说:“鹿门在汉学中,所谓章句之儒,性情尤为敦厚”,亦可见一斑。皮锡瑞虽主今文,却持论较为平允,大部分时间从事于著述讲学,不像龚、魏那样侈言大义,更不如康、梁一般政议激烈,所以叶德辉抑之以“章句之儒”;但可以估计,假若皮锡瑞也如康、梁一般“通大谊”、“通政事”的话,恐怕叶德辉就不会谓之“性情敦厚”了。叶德辉继而又说:“六经而无实用,则圣人为空作矣”。[42]436在这种通经致用观念下,叶德辉甚至对西汉以降,今文经学家屡屡言及的“禹贡行河”等迂阔之说也全盘接受。如他在《经学通诰》中说:“董仲舒以《春秋》决狱事;王式以《三百五篇诗》当谏书;平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兒宽通《尚书》,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载在《史》、《汉》纪传,成为美谈。”[42]437他在1915年上书袁世凯当局《学校中之读经问题》一文中也主张:“中学必读《尚书》,使知行政大纲……更读《左传》,俾知外交专对。”[45]可以这么说,在通经以图致用的目的上,同受湘学沾染的叶德辉与魏源等人并无二致,甚至其通经致用的说辞都非常相似。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他们“治术”上的对立呢?叶德辉在“通政事”一段文字中,对王莽、王安石的评价也许可供我们参考:“王莽、王安石伪托《周礼》,惑古殃民,此其人于经术本无所所知,仅乃拾其鳞爪皮毛,为饰奸文过之计。其不能以一二人之私慝,玷及圣经,明矣。”[42]437显然,康、梁托古改制,在叶德辉眼中无疑也是不能“以私慝玷及圣经”的,六经也只能以其叶某认可的训释为“致用”。
不同于今文经学家的大义在于黜周王鲁、托古改制,叶德辉的大义则是另一番图景。他在“通大谊”中说:“大义虽乖,可以随时匡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之谓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谓之谓不乖”。[42]435可见叶德辉通经而起的大义是要维护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亦即“中国四千年之史迹,五伦首在立君”。[45]如此就不难理解叶德辉在清末民初屡次政治风波中始终固守着保皇保教的立场,而与新政治、新伦理水火不容了。在今天看来,叶德辉的这种“致用”之治术在那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与其说是“不入流”,毋宁说是一股“逆流”了。
中国传统社会注重学问必“致用”、务“实用”,尤其在近代社会内忧外患的现实刺激下,反思学术史,谋求学术“致用”的责任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晚清湖南今古文经学争论中,魏源、梁启超以及叶德辉等人都以“通经”为手段,“致用”为目的;以学术为起点,治术为终点,积极阐述各自主张。他们的政治蓝图之所以南北异辙,只能归结于他们对学术的不同理解;或者说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差异,造成了湖南新、旧二派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激烈的思想冲突。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73.北京:中华书局, 1989.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第1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周易正义[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班固.汉书: 第8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6]魏收.魏书: 第8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7]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 上册[M].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8]王先谦.庄子集解[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 中华书局,1987.
[9]范晔.后汉书: 第10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0]沈约.宋书: 第1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1]王宏斌.关于“经世致用”思潮的几点质疑[J].史学月刊,2005(7): 106-114.
[12]孙奇逢.四书近指[M]//文渊阁四库丛书: 第2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3]王畿.重修白鹿书院记[M]//王龙溪全集: 第三册.台北: 华文书局, 1970.
[14]万表.皇明经济文录序[M]//张寿镛.四明丛书: 第7集.第40册.
[15]方祖猷.实学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C]// 宁波文化研究会论文集: 2002卷, 2003.
[16]顾炎武.陈垣.日知录校注: 第18卷[M].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
[1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9]班固.汉书: 第11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0]王安石事迹: 上[M]//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第4册.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21]钟哲.陆九渊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2]朱鹤龄.愚庵小集: 第10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3]黄宗羲.宋元学案: 第1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4]曾国藩.劝学篇[M]//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 岳麓书社,1986.
[25]顾炎武.与施愚山书[M]//顾亭林诗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1959.
[26]陈澧.陈兰甫先生(澧)遗稿[J].岭南学报, 1932.2(3).
[27]华山.论顾炎武思想: 下[J].文史哲, 1963(3).
[28]颜元.颜元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29]洪榜.戴先生行状[M]//赵玉新.戴震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0.
[30]汪中.与朱武曹书[M]//王清信.汪中集.台北: 中研院,2000.
[31]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M]//龚自珍全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32]魏源.默觚: 上[M]//魏源集: 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33]康有为.教学通义[M]//姜义华.康有为全集: 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4]胡宏.与张敬夫[M]//吴仁华.胡宏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7.
[35]罗克进.湘潭罗府君行状[M]//续修四库全书: 第1530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6]叶德辉.叶吏部答友人书[M]//苏舆.翼教丛编.上海: 上海书店, 2002.
[37]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J].近代史研究, 1998(5): 51-83.
[38]张晶萍.省籍意识与文化认同:叶德辉重建湘学知识谱系的努力[J].湖南大学学报, 2008(2): 45-49.
[39]张晶萍.守望斯文:叶德辉的生命历程和思想世界[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40]叶德辉.与罗敬则大令书[M]//印晓峰.叶德辉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1]叶德辉.日本三君咏[M]//印晓峰.叶德辉诗集.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2]叶德辉.经学通诰[M]//郭齐勇.儒家文化研究: 第2辑.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43]龚自珍.上大学士书[M]//龚自珍全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44]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J].汉学研究, 1997.15(2): 1-35.
[45]叶德辉.学校中之读经问题[N].上海: 时报, 1915-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