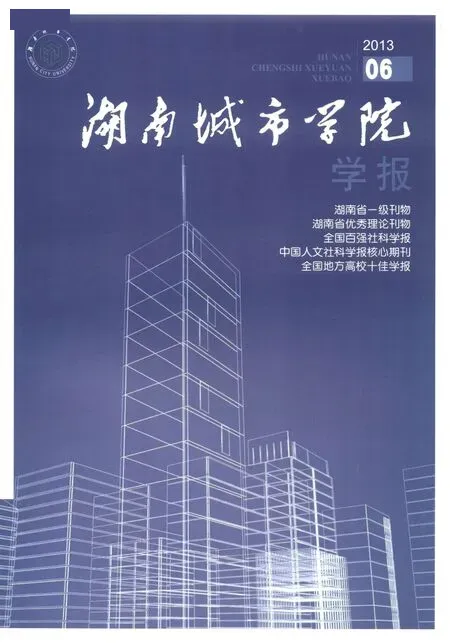再现、权力与文化政治——萨义德文化批评略论
管 勇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500)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于当下学界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然而,萨义德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及其为世人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直至今天依然是人们争相话说却又人言人殊的论题。在笔者看来,文化政治学(cultural politics)的视角不失为一条重新审视和观照萨义德文化批评实践与理论的新路径。
一、变革与脉络:文化政治的理论渊源
何谓“文化政治”?若从词源学上进行考察,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最早把“文化政治”作为一个复合名词提出来的是葛兰西,[1]14但它的所指意义显然只是“文化”与“政治”内涵的本义叠加。而从语义学的历时演变来看,“文化政治”内涵的发生和固定与人们对文化和政治概念在认识和理解上的转变紧密相关。在传统观念中,文化与政治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虽同属于上层建筑但却是两个迥异的领域。文化带有形而上的意味,文学艺术是其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具有超越性、自律性和审美性的特征。政治则带有形而下的意味,主要涉及党派组织、政治制度、政治斗争、政治管理等不同的方面,而权力始终居于政治范畴的核心地位。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则被看作是互相独立的实体,两者各有不同的运作法则和规律,两者之间处于一种上下位平行运作的状态。但是,这种认识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期开始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文化与政治的分立状态被打破,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从疏离、对立走向了联系、融合甚至同一,“文化政治”便从一个隐而不现的潜在问题变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课题。文化不再被看成是一个独立自在的理想王国,其中政治始终存在并从未缺席。而政治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党派政治、阶级政治、国家政治等传统政治范畴,而是从特定的所指转化为泛化的所指,囊括并覆盖了所有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领域。因而,文化政治的产生实由文化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文化化这两个双向互逆过程共同催生出来的,这其中自然包含着“文化政治”得以产生的两条思想脉络。首先,从文化的政治化过程来看,主要存在于文化研究的政治化转向中,尤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代表。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要获得成功并不在于暴力夺取政权,而是无产阶级自身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因而,他主张应当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作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基础。葛兰西则认为“政治社会”主要通过强制实现统治目的,包括军队、监狱、行政机关以及法庭等国家机器,而“市民社会”主要通过认同实现统治目的,包括学校、学会、教会、新闻媒介、艺术团体等民间文化机构。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主要在于“市民社会”的认同,因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应当把意识形态领域视为主战场并争夺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直接成为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后来在1960年代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的思想资源。不仅如此,以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和以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为代表的英国左派文化研究理论家也都纷纷聚焦在文化的政治性问题上。他们认为,文化不仅只是经典马克主义理论中从属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不仅只是对社会现实的被动反映,其本身能动地参与了社会的构形,也是权力施展拳脚的重要政治场所:“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2]31其次,从政治的文化化过程来看,主要是受到后结构主义哲学理论的影响,尤以福柯的微观权力论为代表。政治在通常的意义上往往是与国家、政党、阶级、国家机器等概念紧密相连,政治权力则往往指向压迫、统治、暴力等政治行为的强制性和宰制性。然而福柯给出了对政治和权力的另外一种理解。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只是一种社会政治或宏观政治,权力的意义因而也就被缩小成为一个特指,其实不然:“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3]161福柯意义上的权力把社会政治语境中大写的、单数的、单向的、强制的宏观权力改写为小写的、复数的、多样的、渗透的微观权力:第一,权力无处不在并且具体入微,弥散性地存在于社会不同维面和各个角落,在传统的理解中与权力不相干的性、性别、身体、话语、民族、种族等等其实都渗透着权力因素;第二,权力不是像财产或财富那样可以据为己有,也不只是单向性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以一种关系网络的形式运作;第三,权力是匿名的、无主体的,而每个人只是权力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他可能同时扮演着权力施为者与受与者的双重角色,权力则是统摄这一切关系的生产性机制。因此,通过福柯后结构主义哲学对权力的微观化处置使得“‘政治’的含义就扩展到了包括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关系,而不仅仅是阶级关系。”[4]229政治因此摆脱了社会政治的狭隘理解,走向泛化的、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而权力也成为一种既笼罩在普罗大众之上也暗伏于关系网络之中且抽象性与实存性兼具的微观化权力。
简而言之,文化的政治化使文化突显政治意味,政治的文化化使政治携带文化色彩,两者合力促成文化政治从潜隐的常识化状态走向显豁的问题化状态,其核心所指实为以微观形式存在的文化权力。格伦·乔丹和克里斯·威登所言极是:“权力处于文化政治学的中心。权力是文化的核心。所有的指意实践——也就是说,所有带有意义的实践——都涉及到权力关系。”[4]229换言之,在文化政治学中万变不离其宗的正是对文化权力的聚焦和关注,文化不是远离政治的神圣殿堂,而是权力操演的重要场所,反过来看,权力所表征的支配、宰制、控制以及所导致的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等征象同样存在于文化之中:“正因为与权力相关,‘文化’政治才成其为文化‘政治’。”[5]因此,文化政治学实质上所要讨论的正是文化中的权力问题。
二、继承与创新:文化间性的批评转向
从思想谱系来看,萨义德的文化批评风格和策略尽管独具一格,但这依然不能否认他的批评思想是一种批判性继承。萨义德从未承认过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未把自己定位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之中,甚至把马克思的理论也归入到他所批判的东方主义话语之中,但他却公开宣称自己受到了马克主义者的影响,尤其是他所崇敬的葛兰西和威廉斯等人。同时,萨义德尽管在后期明确地与福柯告别,但不可否认在其产生世界影响的东方主义话语批判中却从方法论上主要参照了福柯微观权力论的解构路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实践浓缩和集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化和后结构主义政治文化化的智识成果。所以,当他谈到文学研究时,他认为:“文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使命,而不仅仅是审美研究。我依然相信审美的独特地位,但是,那种关于‘文学是一个自治领域’的认识是过分简单的错误认识。一种严肃认真的历史研究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即文化完全卷入了政治之中。”[6]尤其是“文化完全卷入了政治之中”的有力论断与当下仍然活跃的两位著名文化政治批评家杰姆逊和伊格尔顿的名言几乎异曲同工:前者说过“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7]11后者也曾高论“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8]246显然,这里的“政治”已不是指向社会政治或宏观政治,更主要是指向文化政治。如果说,这一论断可看成是萨义德对文化政治的最基本理解和最集中概括,那么,其关于文化概念的理解和表述则将文化政治置于更加具体同时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专属萨义德的独特视角:“我将使用文化一词来表示一种环境、过程和霸权”,“文化并不是仅仅用来标志一个人所从属的某种事物,而是他所拥有的某种事物,而在拥有的过程中,文化也指称一种边界,凭着这一边界,外在于或内在于文化的诸概念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文化还依靠它的崇高或优越地位,而拥有赋予权威、主导、使之合法化、贬谪、限制并确认的权力:简言之,即文化充当它领地内外的强烈分化的施动者,抑或是主要中介的权力。”[9]13-14不难看出,萨义德已经开始进入文化间性视域,即从跨文化的角度审视不同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他看来,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而且本来就是一个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力量相互较量和角逐的舞台甚至战场。他以文学和文化经典为例进行说明:无论是美国、印度还是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在文化接受和传承过程中,都要赋予本民族或本土经典的优先权甚至特权,而且在要求欣赏并且不加批判地忠诚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还要贬抑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经典并与之斗争。我们认为,正是文化间性的视角转向使得萨义德的文化政治理解及其文化批评实践彰显出独特的思想光芒:第一,从批评对象上说,萨义德并不是指向文化本身而是文化权力。是故,萨义德明确表态从未反对西方或西方文化,这绝不是狡辩而是对文化与文化权力的明确区分,权力或曰文化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才是其批评的对象而文化本身。因此,他既对西方殖民文化进行犀利批评,因为权力是暗藏其中的灵魂,也对第三世界殖民地民族主义文化提出批评,因为其中权力的阴影仍未散开。第二,从批评立场来说,萨义德既不是西方立场,也不是东方立场,既不是殖民统治者的立场,也不是殖民地人民的立场,既不是第一世界的立场,也不是第三世界的立场,而是始终站在权力的对立面,是坚守一切被权力遮蔽、宰制、压迫、得不到再现者的立场,是坚持为之发声和代言的立场:“在思想上,他是‘精神贵族’,蔑视一切形式的思想束缚;在政治上,他是‘孤家寡人’,不和任何势力合作和妥协。他支持的不是巴勒斯坦、东方人、第三世界,而是一切弱势、边缘、得不到再现者。他反对的也不是美国或西方,而是一切霸权、控制和对‘他者’的意识形态误现。”[10]196第三,从批评视域看,萨义德是世界主义的国际视野,而不是地方主义的保守视域。这一点和萨义德本人作为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的散居经验密切相关,无论是与母国文化还是与移居国文化之间都保持着联系却又从不完全从属于任何一个,这就造就了萨义德开阔的批评视野。因此,伊格尔顿称“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用世界主义的眼光去批评殖民权力,他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11]第四,从批评思维来看,萨义德扬弃了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而强调反本质主义思维。他曾反复重申,既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东方,也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西方,这都是人为建构的特定历史产物。而他的路径正是逆向解构文化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下想象构造物何以产生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何以生成。第五,从批评目的来看,尽管在批评方法上萨义德借鉴了后现代理论的解构策略,但他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却并不是后现代性而是现代性。他企图通过对文化政治之核心即权力的揭露、解构和抵抗,打破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窠臼,消除二元对立所引发并顽固存在的对抗和敌视,通过文化权力的消解达到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交流、对话和融通,进而撬动不同文化共同体在社会政治层面已经固化的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抗和敌对,以重塑和形构全人类启蒙与解放的现代性理想追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启蒙运动的儿子”。[11]胡赛因则直接将萨义德与威廉斯、乔姆斯基等人并置,认为他们都是力图为现代性阐释提出洞见的现代思想者。[12]303而萨义德自己也承认“转来转去又回到了解放与启蒙”。[13]312
三、还原与解构:文化再现的权力生成
更为关键的是,萨义德基于文化间性视角而展开的文化政治批评,并不是一种凌空高蹈式的理论分析,也不是枯燥乏味的空头说教,而是抓住并紧扣文化研究核心范畴即再现(representation)进行由点及面的辐射性论述和阐发。因为在他看来,“再现的研究是重大的文化议题”,[14]107“是所有批评和哲学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9]355丹尼·卡瓦罗拉认为:“任何文化产品都可以理解为一种表征(即再现,引者注)形式,这种表征形式为文化信念系统、文化的现实解释以及文化将实际情境和虚构情境转化为意象的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线索。”[15]45雷蒙·威廉斯梳理了该词的词义演变过程:该词出现在14世纪的英文里,最初的含义主要是象征或代表,到了17世纪“代表他者”的意涵开始以各种不同方式出现。[16]406-409约翰·费斯克把再现视作“一切有效的意指系统内形成意义的社会化过程”。[17]241霍尔则认为:“在文化的意义过程的核心,存在着两个相关的‘表征系统’。……各种‘事物’、概念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生产的实质之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联结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之为‘表征’的东西……意义并不内在于事物中,它是被构造的,被生产的。它是指意实践,即一种产生意义、使意义具有意义的实践的产物……意义是被表征的实践和‘运作’产生出来的。它经由意指(也就是意义的生产)实践而得以建构。”[18]1克里斯·巴克明确指出:“所谓再现,指的是客观世界被我们以社会的方式建构、并且对我们重新展示的过程。的确,文化研究的核心,是将文化当作再现的种种表意实践来研究的……”。[19]9廖炳惠认为,意义往往需要通过叙述或意象来表达,传统意义上“再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治的代表,另一种是文学的叙事表现,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再现”不只是修辞行为,更是政治性活动。[20]219从上述观点来看,“再现”虽为传统术语,但其词义却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在文化研究兴起之后,把再现看成是文学或文化对客观世界镜子式的被动反映过程这一现实主义观念已经显得过时和陈旧。事物并不具有一个先在的意义实体,经由再现的工具性转换就可以将其“真容”再次呈现于我们面前并且被我们加以掌握和理解,而是我们通过对作为“文化信码”的语言符号进行组织、操控和运作进而赋予事物以特定的意义。因而,事物的意义世界不是先验性的而是建构性的、生产性的,再现也就不是一个反映和呈现意义的客观工具性过程,而是一个赋予和形塑事物意义的意指实践过程。在文化研究理论中,尽管“再现”的词义变化仍然纷繁复杂,但基本可以把“再现”的含义概括为:主体通过语言、文字、视像等文化符码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而生产、流通、获取关于事物意义的意指实践过程,具有显著的社会性、建构性、能动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权力就有了发挥的空间和滋生的土壤:谁来再现、谁能再现、再现谁或谁不被再现、如何再现、给谁再现等等一系列存在于意指实践过程中的意义争夺已不再可能被当成是常识或客观知识来加以接受,而是成了值得怀疑、追问和揭示的攸关权力的政治性问题,而这正是萨义德文化批评题中应有之义。在他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再现的世界里。而再现——包括它们的生产、流通、历史和阐释——正是文化的真正元素”。[21]75-76因此,无论是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等理论色彩稍显浓厚的著述中,还是在《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充满激情的批判论说中,乃至在以知识分子再现的政治伦理为主要讨论内容的《知识分子论》(英文标题“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台湾中译本即为“知识分子的再现”)中,再现都是其念兹在兹的主题。台湾学者单德兴认为,“再现”对萨义德而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综观萨义德多年来的论述,包括学术著述、政治评论、教学、演讲以及媒体采访,若说“再现”为其主要观点实不为过,甚至可以说他无时无地不在关切再现的议题。[22]而再现与权力是意义生产的一体两面,在意义生产过程中与再现同时生成的权力问题理所当然就成了萨义德文化批评的重要着力点和立足点:“我的批评的前提是,所有再现在性质上都有缺陷,以及它们如何密切连接着现世性(worldliness),也就是,连接着权力、地位和利益。……在牵连到权力、地位和利益的时候,不管它是不是它们的牺牲品,它早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沾染。”[23]57可见,萨义德认为文化再现从来就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知识获取过程,而是充满着选择、筛除、歪曲、遮蔽、扭曲等人为建构行动的意义争夺和权力生成过程。在文化间性视域中,再现不仅关系到文化主体的自我再现,而且更重要的还有对文化他者的再现:“再现(因而是化约)他者的行动几乎总是涉及对再现对象的某种暴力……再现的行动或过程暗示了控制、暗示了积累、暗示了监禁、暗示了再现一方的某种疏离或失去方向。”[24]56那么,对于权力始终居于其中的文化再现,我们可以完全消解或者完全拒斥,还是只能对其中的权力进行祛魅、抵抗和消除以达到一种转换形式的再现?在一篇访谈中,萨义德给出了答案。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文化再现在文化生产、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传播以及参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构形中的基础性地位,其对于人类存在的重要性和语言可以相提并论:“再现多少是一种人类经济的形式,对社会中的生活是必要的——就某个意义来说,对不同社会之间的生活也是必要的。因此我认为没办法摆脱他们——它们和语言一样是基础。”同时,萨义德指明了通过对权力的揭示、解构和抵抗所要实现的目的:“应该消除的再现系统,是带有一种压迫性权威的再现系统,因为它不允许或保留那些被再现者介入的空间。”而值得我们不懈追求的“另类的选择就是一种参与式的、合作式的、非强制的再现系统,而不是从外面强加的再现系统……我们必须指认出在制造再现时,哪些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形成(social-cultural-political formations)能够促成消减权威,增加参与,然后从那里开始前进。”[24]57
[1] 葛兰西. 论文学[M]. 吕同六,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弗兰西斯·马尔赫恩.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M]. 刘象愚,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 福柯. 权力的眼睛[M]. 严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 阿雷恩·鲍尔德温. 文化研究导论[M]. 陶东风,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5] 姚文放. 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J]. 文学评论,2011(3): 17-25.
[6] 塔里克·阿里.纪念赛义德[J]. 于冬云, 译. 国外理论动态,2004(1): 35-37.
[7]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M]. 王逢振,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8] 伊格尔顿. 文学原理引论[M]. 刘峰,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9] 萨义德. 世界·文本·批评家[M]. 李自修, 译. 北京: 三联书店,2009.
[10] 朱刚. 萨伊德[M]. 台北: 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7.
[11] 伊格尔顿. 赛义德、文化政治与批评理论[J]. 吴格非, 译.国外理论动态, 2007(8): 48-53.
[12] Abdirahman A.Hussein. Edward Said:Critism and Society.London: Verso, 2002.
[13] 赛义德. 赛义德自选集[M]. 谢少波,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4] 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2009.
[15] 丹尼·卡瓦罗拉. 文化理论关键词[M]. 张卫东,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16] 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 译.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17] 约翰·费斯克.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M]. 李彬,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18] 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 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9] Chris Barker. 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M]. 罗世宏, 译.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10.
[20] 廖炳惠. 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21] 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 译. 北京: 三联书店,2003.
[22] 单德兴. 代表/再现知识分子:萨义德之个案研究[J]. 华文文学, 2011(5): 5-22.
[23] 萨义德.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M]. 朱生坚,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24] 薇思瓦纳珊. 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M]. 单德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