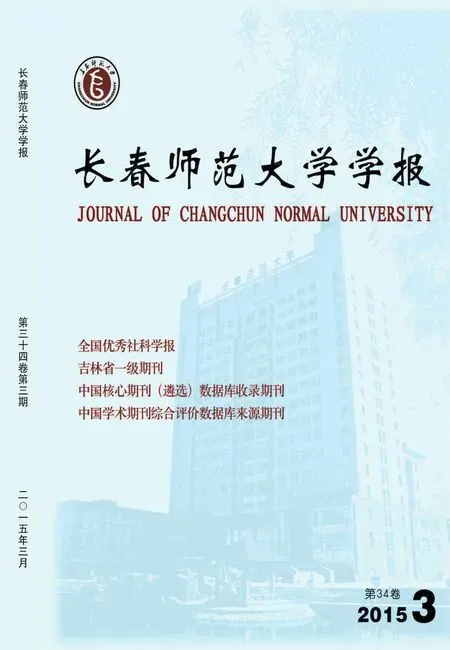论《格格不入》中萨义德的自我身份
潘婷婷
(特种作战学院四系,广东 广州510500)
有别于尽数童年、青年、成年和老年时代模式的传统自传,爱德华·萨义德的《格格不入》(Out of place,1999)[1]主要讲述了从1935年出生到1962年他大致完成博士论文间的生活,是他青少年成长时期的一次绵长回忆。它是局部的、分散的记忆,从自己的角度观察和记录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描写最多的是折射大局的小环境:家庭琐事、学校见闻和家乡变故。萨义德后来为巴勒斯坦解放问题的辩护、对“东方主义”的批判等都不在本书的叙述范围,但其根源已经萌芽于此。
虽然回忆录所涉岁月不足三十年,但萨义德在其中将其自我身份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紧扣两条主线:一是巴勒斯坦失陷与以色列建国、埃及君主制度结束、黎巴嫩内战等背景下的流离生活,以及这种生活下的身份危机和焦虑感让他强烈感受到的自身和世界的格格不入;二是阐述父母对其性格的塑造以及对其自我意识形成带来的影响,从而更集中、紧凑地突出了萨义德自己最看重的身份——无根的流亡者、软弱的恋母者。本文拟从离散角度和恋母情结考察萨义德在回忆录中的自我身份,探讨它与萨义德后来所从事活动的关系。
一、自我身份
《格格不入》以萨义德的自我经历为中心进行叙述,适用于自传的“身份理论”。正如传记家在写作前必须确定传主身份一样,自传者在写作前必须确定自己的身份,才能回顾过去,对无数的材料进行选择和扬弃、使用和安排、解释和说明。他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都同他对身份的自我认定有关[2]311。也就是说,萨义德总是在以一定的身份在写作,试图让读者接受他的“自我身份”,实现证明他的“自我身份”的目的。“自我身份”是指所有人在他们作为人的能力范围内一个关于自我的独特概念[2]18,这一意识贯穿在回忆录写作之中,萨义德在自我身份的引导下进行自我塑造。依据这个身份,萨义德向读者再现自我,选择和使用的材料也是为这一身份服务的。萨义德竭力把自己的形象同他的自我身份连接起来,尽量达成一致,这个过程也正是他自我解释和自我认同的过程。
《格格不入》的自我身份意识贯穿于全书。萨义德将自我身份定位为“无根的巴勒斯坦人、在父权打压下懦弱恋母的儿子”。萨义德先是分别勘定了父母的身世:“她母亲穆妮拉是黎巴嫩人,她是巴勒斯坦人,在拿撒勒出生……”;“他1895年在耶路撒冷出生……”[1]5-8萨义德强调的是自己的母亲和父亲都是巴勒斯坦人,不言而喻自己当然也是巴勒斯坦人。《格格不入》里的萨义德虽然有多重身份,但“巴勒斯坦人”就是他的基本身份。巴勒斯坦是萨义德“视为理所当然的地方,出身的国家,亲人与朋友安然不假思索存在之地”[1]21。他强调自己是巴勒斯坦人,这有丰富的含义和暗示:他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埃及人。他的父亲在一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后回到巴勒斯坦结婚生子,他也因为父亲的缘故一出生就持有美国护照,童年也有很长时间在埃及开罗度过,但他打心底认定自己是巴勒斯坦人。他接着解释为什么“我想我们家族在耶路撒冷说得上世泽绵长”[1]7,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这个身份的确认对萨义德意味深长。正是因为萨义德的内心深处坚守巴勒斯坦人这个自我身份,他在巴勒斯坦亡国后才一直感觉飘泊无根。他以“无根的巴勒斯坦人”的视角讲述他的求学经历,展示他的漂泊流亡的青少年时代。
自我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萨义德将自己描述成什么样的人。萨义德认为少年时代的他是一个备受压制的儿子,每天生活在父亲为他制定的条条框框之下,就算遭受暴打也不敢抗议还手。父亲之暴与母亲之慈造成了他的性格缺陷,形成了今日的他。
“爱德华”首先是儿子,其次是哥哥,最后是那个上学并努力遵守(忽略或回避)规则但并不成功的男孩[1]19。这里,儿子照父母心中的模型被打磨出来,他自己无力反抗,不得不无奈接受打磨。整部回忆录里弥漫着萨义德对父权的恐惧和对母爱的渴求,体现了他最为隐私的一面,是一个压抑的小男孩的心灵独白,哭诉那些年他的压抑和渴望。父亲的强势、自我的弱势直接导致了他转向母亲寻求温暖。《格格不入》除了多处直陈他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外,更直言对母亲超乎寻常的爱慕:“回顾我与母亲坦白而且——尽管年纪悬殊——深刻的爱恋……”[1]57。这些经过筛选的记忆更加明确了他的自我身份:那个备受压制的男孩。而恋母厌父的萨义德则是由这一身份的升级,更具有代表性。作为一个备受压制的儿子,萨义德在父亲的阴影下永远不得要领,一直处于下风,只能在母亲那找到一丝慰藉,他的自我身份随之发展为在父权打压下懦弱恋母的儿子,并在此视角下展现他的家庭生活,记录父母对他性格塑造产生的影响。
二、流亡与公共知识分子
一个人拥有多重身份,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作者确认的自我身份只是其中最为重视的身份中的一个或几个,所以可能与社会所认定的身份不一致。这个无根飘泊的游子、恋母厌父的男孩,和那个被誉为“向权力言说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人”[3]90的萨义德又有何关系?萨义德在回忆录中实质上已经给出了答案:流亡者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别称,萨义德的流亡状态供给着他成长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养分。离散、流亡的状态给萨义德提供了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理性与感性兼具的人文视角。
《格格不入》中萨义德的第一个自我身份是痛失祖国、四处飘泊的学子,亦即是无根之人。无根是一种无奈,亦是与母体撕裂的切肤之痛;萨义德却将其转化成得天独厚的优势。一生飘泊的萨义德是无根的,而“离散”就是造成他无根的直接原因。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以及1967年的以阿战争造成了大量的巴勒斯坦人被迫迁徙或被逐出巴勒斯坦。自此,巴勒斯坦人家破人亡、分崩离析,使巴勒斯坦人产生数个流离群体:一是约旦西岸、迦萨走廊,二是以色列境内,三是阿拉伯国家,四是西方国家[4]90-108。虽然散居各地,但是他们的“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却始终没有消失过,甚至更为强烈。
流离失所、矛盾重重的生活让萨义德痛苦不堪,他的人生经历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乐园”——田园诗式的开头,然后遭受残暴的打击。萨义德父亲经营文具生意,家产丰厚,所以他幼年的生活非常安逸。但是从十二岁开始,萨义德一家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开罗。十五岁赴美读书,再次遭受被放逐的命运,此后他就一直处于流亡的状态。这正是整个巴勒斯坦民族的缩影。
萨义德后来之所以极力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摇旗呐喊,尖锐谴责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的美帝国主义,与离散造成的流亡他乡息息相关。八岁的萨义德在埃及开罗念吉西拉预备学校的时候,受到一个英国男教师的体罚,使他头一遭体验到“英国人以一个殖民地事业为形式的有组织体系”[1]42。对幼小的萨义德而言,这学校(大部分学生和老师都是英国人)没有学习场所的趣味,只给了他和殖民地权威的第一次长期接触,就像是一颗种子,播在了被殖民者的心田,等待着日后的生长发芽。在萨义德心中,那些英国孩子和他隔着一条无形界限,他们是有家的,而最深意义的“家”却一直是他无缘的东西。无处为家的飘泊反而促使萨义德要寻求自己的一片净土——不是社会领土,而是思想疆域。
萨义德所找到的净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常态——“流亡”。流亡者不愿适应权威,宁居于主流之外,不被纳入,不被收编。与诺诺之人相反,他们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1]48——这一定义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不谋而合。对于萨义德来说,流亡不再单纯是命运的无奈,反倒成为了他的一把利器。放逐者的思维方式使萨义德面对阻碍时依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1]57。处于局外或边缘、拥有“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反而可以使流亡者摆脱主流文化的控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思考的精神。作为一个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他游离于多种文化之间,绝不墨守成规、跟随大流;他更广阔和多元的视角使他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开拓性,使他就算在民族、国家、传统等宏大集体概念笼罩之下,仍然能无时无刻地维护自己的独立性格和批评精神。正是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使萨义德处事冷静而客观。萨义德曾担任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独立议员达14年(1977-1991),并长期在西方社会为巴勒斯坦代言,但他不能简单地被概括为一名巴勒斯坦“斗士”。他从未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反西方论”的言论,却曾尖锐批评巴解组织内部的专制和腐败。
三、恋母厌父与后殖民理论奠基人
《格格不入》中萨义德的第二个自我身份是逆来顺受、备受压抑的儿子,他无力反抗父亲的霸权,却深深地迷恋着母亲。书中大段与母亲暧昧关系的描写反映了萨义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对父权的憎恶更深化了他对母亲的依恋,为萨义德成年后的反抗埋下伏笔。
萨义德的父亲对其实施“维多利亚式”的教育,给童年的萨义德留下深深烙印。父亲为他制定了严格的作息制度(上学、放学、钢琴课、体操、主日课、骑术、拳击、课程补习),让萨义德每天疲倦不堪,远离一切诱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大众娱乐场所闲逛,更别说出门找女孩了。进入青春期,父母费尽心思地让萨义德远离“性”,禁绝性的存在。父亲发现萨义德自慰后,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让他再次感受到父亲令人畏缩的父权压制,让他不自觉地压抑自己对母亲的情感,根本无法想象父亲要是发现自己对母亲的感觉、对女性亲人暗含的欲念,会作出何等激烈的反应。
在父亲的高压管理下,母亲是萨义德逃离压力的温暖港湾。回忆录中满是萨义德对母亲超乎寻常的爱恋和依赖:他早年没有同龄朋友,却自认和母亲心有灵犀,从来只向母亲寻求思想和情感上的依傍;直到萨义德二十岁,母亲才不过四十,她在萨义德心中一直以世界上最美丽的女神形象出现,操控他、诱惑他,让他迷恋不已,深陷其中。萨义德童年经常玩的小把戏更能够说明他对母亲的依恋:到了公园的关门时分,小萨义德总是藏在里面,享受母亲的呼唤——“Edward这个英文字飘过薄暮的空气传来……享受被呼唤、被需要的愉悦”[4]2。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或恋父情结,尤指男孩恋母厌父的情感。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俄狄浦斯情结潜伏于婴儿的无意识中,随着年岁渐长,这种冲动因受到社会道德的约束而无法满足,就在意识抑制下形成了“情结”。人全部行为的动机源于这种情结,因为它从无意识深层影响着人的心理[3]264-265。萨义德和母亲忽明忽暗,细致、敏感的母子情显然符合弗洛伊德的定义,这种感情也确实影响了萨义德后来与女朋友的交往方式,不自觉地支配着他的行为:他们复杂的关系在萨义德即将离开开罗赴美留学时达到高潮,在共同聆听贝多芬交响曲的一个下午,他和母亲心神领会,产生共鸣,俨然象征着两人形成一种不容侵犯的结合,这种象征甚至还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成为他成年后和别的女人交往时的障碍。
弗洛伊德认为,本能冲动受到自我的抗拒而被压抑到无意识系统之后,并不会就此消失,反而会寻找别的释放途径[5]112-113。成年后的萨义德没有选择继承父业,而是成为了一名文学教授,后来更不听家族劝导投身政治。以美国公民身份为豪,认同美国基督教文化的父亲对萨义德的严苛,使他萌生了对“西方殖民霸权”的敌意;而与萨义德关系非同寻常的母亲则是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信徒,至死都未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代表着“弱势的东方”。萨义德毫无疑问地倾向母亲,后半生为巴勒斯坦奔走呼喊,带着强烈的亲阿拉伯情感著成《东方学》(1978),奠定后殖民研究范式,开创了一种极具文化穿透力和颠覆性的研究方法。
萨义德将“东方主义”(Orientalism)定义为西方对于东方的解释,是外界强加的术语,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却掩埋了东方的真实面貌[1]30-64。父亲的强势和苛求,如强势的西方压制弱势的东方,任意解释、定义东方,扭曲萨义德的本我,用条条框框规约萨义德,使之成为他心目中的那个儿子。“东方主义”的理论是萨义德迟到的“叛逆”,是他反抗父亲对他长达二十多年的“殖民式统治”,是对父亲的“报复”,更是自我的解放:“他去世二十年,我才惊觉,我们前往美国的时间前后相隔足足四十年,但到美国之时的年纪几乎完全相同,他到美国追求他的人生,我到美国演出他为我写好的人生剧本,只是我后来挣脱,决定自己要走的道路”[1]8。
四、结语
萨义德在《格格不入》中的自我探索像是一幅大历史流变的个人拼图:动荡的世界、相融而矛盾的文化使萨义德深感与周遭格格不入,但“流亡”的状态却又为他提供观看事物的异类视角,超越过去与现在、他者与此地,成为他成长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必要因素;他在父亲的严厉和母亲的暧昧下成长,其俄狄浦斯情结昭然若揭,对父亲强权的逆来顺受和对母亲爱恋的渴望甚至决定了萨义德成年后的思维模式,间接激发了他对后殖民理论模式的思考。他的回忆录实质上已暗含着答案,早年的经历和记忆并没有消散,而是潜移默化地成为了启动行动的基因,最终成就了他的社会身份:身体力行的公共知识分子,深具批判意识的后殖民理论先行者。
[1]Said Edward W.Out of Place:A Memoir[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9.
[2]杨正润.现代传记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Said Edward W.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The 1993 Reith Lectures[M].New York:Pantheon,1993.
[5]赵山奎.论精神分析理论与西方传记文学[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3):111-117.
——《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