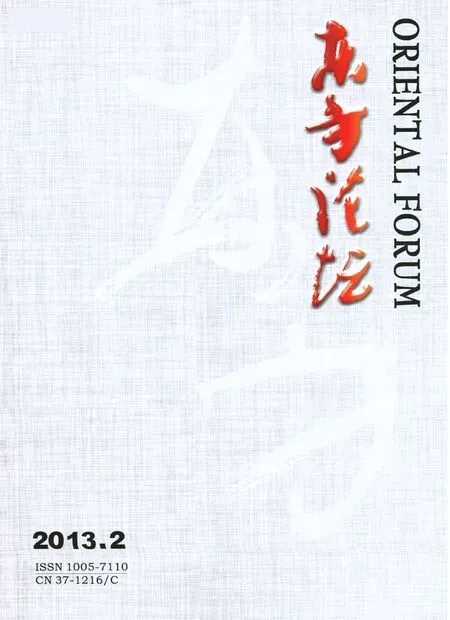论《文心雕龙》与写作过程中的文体感
赵红梅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写作活动是一项复杂、综合性的创造活动,文章是其最终成果的体现,即写作载体,这个载体又是以一定的体式呈现的,此即我们常说的“文体”,但文体概念在传统文论中具有更为丰富、多层次的内涵。在写作教学中,文体是一个不能不涉及的重要方面,如何有效开展并切实提高学生实际写作中的文体把握能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教学课题。作为一部研究“为文之用心”的理论专著,《文心雕龙》近年来受到写作学界的高度重视。“文体”亦是《文心雕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丰富的文体论思想为今日之写作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文心雕龙》中的文体思想是体现于全书的,而尤为可贵的是其写作活动过程中对文体的动态把握。因而,本文在把握《文心雕龙》之“文体”观的基础上,聚焦于写作过程中的“文体感”,并结合《文心雕龙》之相关篇目进行了更为细化的分析,旨在吸取传统文论精华,反思并改进高校写作中的文体教学。
一、《文心雕龙》之多层级、整体性的文体观
单从字面上来看,据有关学者查考,《文心雕龙》中“文体”一词出现过8 次,“体”出现190 余次(既是论文,则“体”亦多指“文体”)。①参见杨东林《开放的文体观——刘勰文体观念探微》(《文史哲》2008年第4 期第122-129 页)及王毓红《中国古代诗学语境中的文体概念——从刘勰〈文心雕龙〉谈起》(《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1月第24卷第1 期第5-11 页)二文。可见,“文体”或“体”是《文心雕龙》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1950年代以来,对刘勰文体观的研究一度引起关注,并引发一场跨世纪跨海峡的学术论争。②李建中《龙学的困境——由“文心雕龙文体论”论争引发的方法论反思》(《文艺研究》2012年第4 期第51 页)一文说:这场学术论争,从徐复观的“主观情性论”文体观,到龚鹏程的“客观规范论”文体观,再到颜昆阳的“辩证性的文体观念架构”,以其革命性、批判性和建构性,对《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研究乃至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学者们从各自角度,对《文心雕龙》中“文体”的内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也有不同的声音。归纳起来,其共识是“文体”具有多重内涵,不能简单等同于文章的体裁。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上世纪50年代徐复观先生提出《文心雕龙》之文体有体裁、 体要、体貌三个层次,而以体貌为文体概念之最终依归;其后龚鹏程先生针对徐文发表不同意见,强调文类,反对做近乎现代风格学上的阐释;颜昆阳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辩证性的文体观念构架”;内地学者中,1960年代陆侃如先生提出文体包含体裁与风格二义;1980年代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体包含体裁、体貌;1990年代童庆炳先生提出文体概念的三个层次:体裁、语体、风格等。[1]理论的辨析无疑使我们对“文体”这一术语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这也彰显出传统文论批评的特色,往往一字具有丰富之内涵且有时随文见义,难以用准确的现代术语加以替换。这里,我们取其共识,并对不同的内涵层次做综合的理解:“文体”是刘勰对待写作载体——文章的一种整体性看法,既包括体裁之形式特点,也有其他内容风格等方面的附加之义。总之,是一篇文章的整体面貌、有别于其他的质性所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管刘勰从怎样的角度去把握体概念,而由人体概念引申出的体的整体性和直观形相性,则是刘勰对文体认识的基础。”[1]“文体范畴的含义还可进一步表述为具有各种特征和构成的文章整体。”[2]这里,我们亦对“文体”这一概念做整体性理解,并着眼于写作活动,考查写作过程中对文章整体的一种多层次的把握。《文心雕龙》中对文体问题的处理与把握值得我们在现今的写作教学中加以充分借鉴。
一般认为,《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即是上篇中的二十篇“论文叙笔”。这部分篇幅之重占全书的近一半,而且下篇的创作论诸篇正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归纳阐发,可见刘勰对文体问题是非常重视的,是建构其创作理论的基石。与同时期的其他理论著作相比,这部分内容体大虑周,力图对所处时代的各类文体做出全面之归纳,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前所未有的文体总结范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分类体系以及各体文的具体阐述对当今之写作教学仍有较大借鉴意义,尤其在专门文体的教学方面。但文体分类随时代而变,在内容的借鉴之外,更应吸取其驾驭各类文体的胸襟眼光及方法。《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之所以达到时代之最详备者,正因其开阔的理论视野。纵向上,追根溯源,挖掘探寻各体文的发生发展及变异消长;横向上,文笔兼收,充分吸纳时代之各类文章样态,涵盖各种正体变体。在文体探析中,刘勰创造性地运用了“原释选敷”的研究方法,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3](P682)文随世变而方法可通、原释选敷的研究思路,对今日之文体研究仍切实有效,尤其“原”、“选”之法在今日之文体教学中亟需加强。
《文心雕龙》对“论文叙笔”部分的极大重视、对各类文章的条分缕析、宽阔的文体视野以及独特的“原释选敷”之法,都对今日之文体写作教学有较大启发。
详析“论文叙笔”的这部分内容,侧重类的辨析,注意归纳各类文体的特征规范,求同辨异。虽分类较细,但亦有相近文体的归并,从篇目安排上还可见出有些相近文体应是刻意相邻而排。《宗经》篇中亦曾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参照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刘勰的文体分类呈现出较为严谨的系统性。天下文章纷繁庞杂,种类繁多,但本同而末异,从某种角度可以归并为更为简约的大类,这样各依其类、以简驭繁,可以达到较系统全面的把握。由此,笔者曾提出立足于某些“基本文体”来开展教学与写作训练,可以较好解决写作教学中(尤其基础写作教学)文体需广泛涉猎又难以各个展开的矛盾。这里的基本文体,就是指相近而归并的文体大类。当然归并的角度不尽相同,笔者曾尝试结合表达方式加以归并,如叙述描写与叙事文、议论与论辩文等。这样以基本文体中的典型代表(具体文章)为依托,可以将普适意义的文章之体的要求、类的规范性体现于具体文本,在阅读与写作实践中把握“文体”的创造,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于各种具体文体的自主学习与掌握的能力。[4]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可以较好地打通点与面,使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既体会到不同文体之差异,又有较全面的文体把握,从而实现文体教学的铺展与深入。这应是《文心雕龙》之文体论给我们的又一启发。
姚爱斌先生曾撰文提出基本文体、文类文体、具体文体的概念,认为文体之创造不是其内部结构层次的逐级升华而是这三种不同层级文体的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由潜在到现实的过程。①姚爱斌《论徐复观〈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的学理缺失》一文提出基本文体、文类文体、具体文体的概念,认为“文体的生成的确有一个逐层升华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不等于文体结构的三个层次,而应该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由潜在到现实的过程”, 该文中说:从逻辑层面看,文体的生成或升华会经过三个层次和两个环节。这三个层次分别是作为所有文章范型的基本文体、作为某种文类范型的文类文体和作为现实具体的个别文体。两个环节分别是:先由基本文体转化为文类文体,再由文类文体落实为具体个别文体。因此,所谓文体的升华过程,可以理解为包含一般规定和特征的基本文体、文类文体,在实际创作中转化为包含具体规定和特征的个别文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遵循的是体用规律。……人们也只能通过种种具体的文类文体(末)来体会、认识文章之“本”,……文类文体又必须通过无数具体的个别文体作为其现实存在。……文体创造应该是文类文体的规范性与个别文体的多样性结合……《文心雕龙》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体发展和创造过程中的体用关系,但是其思想方法完全与体用论契合。其“基本文体” 指“所有文章范型”,亦即普适意义的文章之体的要求,与我们所说的出于教学考虑而进行文类归并的“基本文体”概念指向不同,但其逐层升华论无疑使我们对文体之生成有更为清晰的认识。由此我们也可以归纳:《文心雕龙》中的“文体”,包含了刘勰对普适意义上的文章之体、某类文章之体、具体文章之体等多层级看法,但无论哪个层级,都是将“文体”视为具有多重结构内涵的文章之整体,写作过程中正是一直秉承这一“整体”观念而不断加以矫正(遵守或突破),从而实现文体的实施与创造。
基于这样多层级的整体的文体观,刘勰对文体之重视与把握显然并不仅仅局限于论文叙笔之中,而是贯穿于整个探讨“为文之用心”的全过程、贯穿于全书的。从全书纲目看,“文之枢纽”五篇,《序志》中曾概括为:“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 无论“本、师”亦或 “酌、变”,其依归之中心乃是“体乎经”,可见,《宗经》是枢纽论的核心,宗经思想更是笼罩《文心雕龙》全书的主导思想。①关于《宗经》之主导意义亦可参见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 版)第964、965、976 页。而宗经实是宗经之体,从《宗经》篇内容可以见出,《文心雕龙》所关注并强调的,是其“禀经制式”的文体意义。[5]
“论文叙笔”部分前已详述自不赘言。下篇的“剖情析采”之创作论,笔者以为其实更为鲜明地体现了刘勰的多层级整体的文体观。创作论建立在各体文的归纳之上,力图通过对各类文体的全面把握,探讨普适意义的文章写作的一般理论,而这些写作的一般理论又体现于写作过程中对具体文体的把握,因而,紧密结合实践的创作论,打通了普适意义上的文章之体、文类文章之体、具体文章之体的多层级界限,在过程中具体体现了文体的生成转化和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写作活动中,每一个文本就是一具体“文体”,成功的文本应具备普适意义的文章之要求、文类的规定性,同时又是独特之创造,自成一体。在这过程中有由隐及显的文体层级转化但最终体现为具体文体,有文体内部多层结构的分别把握但以整体之面貌展现,所以就显像的具体文本而言,创作论中以贯穿写作活动始终的文之整体观彰显其对文体的高度重视。
按照通行之纲目,创作论包括《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术》等凡十九篇。②《物色》篇有过争议,但学者多认为保持原纲目次序为宜,暂不论。从真正论创作的十八篇来看(《总术》篇除外),前五篇无疑是“务先大体”的文章整体之要求,其后十一篇分别涉及了实际写作过程的诸多方面,最后的《养气》、《附会》两篇则又以文章整体之眼光对前面的论述做了有益的补充发挥。行文纲目的“总—分—总”的视角特点,正彰显了刘勰的文章整体观:可以分而析之,但一定要有整体之把握,文章的各个不同侧面的分析是纳入“文章之体”来统一考虑的。纲目中呈现的文之整体观是一方面,而更为值得重视并挖掘的是创作论内容剖析中时时处处的整体观念(这将在下文详细探讨)。总之,创作论自始至终体现出对写作文本的一种整体视角,这种“文之整体感”伴随着生成过程中的层级转化,又是对自身多层次结构的综合把握,尤其值得今日之写作教学加以借鉴。
综上,《文心雕龙》之“文体”理论是需要综合全书加以审视的,并不仅仅局限于“论文叙笔”,刘勰对文体的高度重视几乎体现于所有章节,而尤其值得我们加以挖掘借鉴的是其贯穿于创作活动始终的文之整体观。
二、反思:文体感培养的具体思路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文心雕龙》以贯穿全书的文之整体观念彰显其对文体的高度重视,并集中体现于创作论诸篇。如果说“论文叙笔” 侧重各种既成文类的条分缕析,是静态之“文体”,那么“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则是写作过程中对文体的具体把握,体现出一种动态的“文体感”。实际上这种动态的文体感,左右着写作的全过程,在写作实施中通过不断对文本加以矫正,从而实现文体的由隐及显的转化生成,并最终体现为对自身多层结构内涵的整体之把握。
文体感,亦有人提出又称文体意识,就是写作或阅读过程中“对各种各样的文章体裁的认定和辨析”。[6]本文认同具有多重结构内涵的整体之“文体”概念,因而,文体感并不仅仅针对文章体裁;而“文体感”或与“文体意识”近似,但相较来说,“感”字强调主观之综合感觉,更为感性直观,似更符合“文体”之模糊多义与整体形相性。
至于文体感在写作中的作用发挥,“认定与辨析”诚然是一方面,但过程中还应有更为细腻的把握。姚爱斌先生曾对文体之生成有一段详细论述:
在文体创作过程中,创作者一般先有一个关于所有文章的整体观念,尽管很多作者未必在每次写作时都能清楚地自觉到这一点,但这是文章写作的一个基本前提,不能想象一个毫无文章观念的人能够进行文章写作;然后是确定选择何种文类文体,在这一环节中,作者需要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关于已选文类文体的整体观念,包括适合这种文类文体的题材内容和语言形式等;最后才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文章整体的完成。当作者完成这一创作过程后,基本文体和文类文体便自然融人了现实存在的直观的文章整体之中,实现了体与用的合一;也即是说,基本文体层面的文章整体存在、文类文体层面的文章整体存在和具体层面的文章整体存在,在现实中是完全统一的。[2]
文体之生成经历了这样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由潜在到现实的过程,文体之层级转化一目了然。但在实际创作中,层级之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如普适意义的文章观念常与文类文体之规范合二为一共同制约着文体之走向,具体文体的创造又常常回环往复于其他层级,这一生成过程会通于写作者的文体感把握。依托于写作实践,本部分试结合《文心雕龙》相关篇目从以下四个方面具体审视写作过程中的文体感:
(一)《宗经》:“论文叙笔”与文体之规范归属感
前文说过,《宗经》是枢纽论的核心,亦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指导思想,而“宗经”主要就是宗经之体。篇中说:“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可见刘勰正是要在建言修辞的意义上宗经,并视其为“性灵熔匠,文章奥府”,“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这里的“经”具体指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五经,《文心雕龙》认为其文章典范意义可以烛照写作之多个方面,并综合体现为对经典之体的内外多层次的模范与把握,即所谓“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另外,篇中还说到“圣文殊致,表里异体”,五经实际上代表了五种不同的文章大类,并将“论文叙笔”的多种文类做了比附五经的归纳①前已详引,归纳之合理或牵强不在本文论述范围,暂不议。。可见,“论文叙笔”部分正是在“宗经”统摄下对各个文类的进一步铺展,从“经”到各类“文、笔”,体现了文类体系的不同层次。《宗经》篇又指出,圣文异体亦是相通的,它们共同作为文之最高典范,具备普适意义的文之特性:“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六义,正是刘勰认为的普适意义的文体之规范标准:情深、风清、事信、义贞、体约、文丽。从这里亦可再一次验证《文心雕龙》中文体涵义的多层次性。
以今日之眼光来看,“经”自然不必再做拘泥之理解,而可以视为某种标准与规范的代称。前文说普适意义的文章观念常与文类文体之规范合二为一,共同制约着文体之走向,这正体现于《宗经》及“论文叙笔”的论述中。五经既有文之普适意义,又是某一角度归并的文体大类之典范,“论文叙笔”的论述亦溯源于五经,规范标准的树立总是包含着对殊致异体的辨析,普适意义的文体总要依托于某种文类之体。而规范标准又是体现在具体文体中的,“宗经”和在其统摄下进一步铺展的“论文叙笔”,都是依托于“经”或“文、笔”这些具体之文。我们将这种依托于具体文体而显现的对普适文体、文类文体规范的认识与把握称之为文体之规范归属感,这正是文体感的初步体现。
文体之规范归属感是基于大量阅读而逐步形成的一种文体感知能力,并在自身之写作实践中得到强化,绝非外在的文体知识灌输所能达到。近年来学生论文写作中常出现的散文化倾向、缺少思辨的抒情式语言即是缺乏文体之规范归属感的典型体现,论文写作知识可以轻易获得,但日常阅读与写作训练的缺乏无疑难以形成准确的论文文体感知能力,也就无法有效驾驭论文写作的各个方面以达到最终成文的整体统一。因而,文体教学应注意依托文本,引导学生多读多练,在读文时具备“体”之眼光,对这一具体之文有文类体系上的判断和比对文体规范的思考。前文提出可以基本文体(文体大类,非姚文所指之普适文体)中的典型代表为切入点,以点带面。实践证明这一思路是切实可行的。从各类精选文本的阅读中,能更鲜明地感受“殊致异体”,从而对文之规范归属有较好把握。这里还要注意不是单纯的体裁层面,应是建立在对“文体”概念理解之上的多层次把握。如果说文体之规范归属感可以在阅读中有意培养,在写作过程中则体现为一种潜在力量而左右着写作行为。执之有度,可以较好地调整写作走向从而形成最终之成功文本;执之无度,过或不及,则导致两极:因循套路或文体涣散。这将在下文有所述及。
(二)《体性》与文体之选择
文体之规范归属感其实已隐含一种选择性判断,一种确定大方向的文体定位,但着眼在规范归属,结合《文心雕龙》之《体性》篇,我们对写作中的文体选择当有更清晰认识。写作中需要有一个文体定位以确定写作的方向,这个方向会潜在规范着写作行为。实践中有指定文体写作和自选文体写作之别,而即便是指定文体写作,基于文类体系的多层次性,亦包含写作者个人的逐步细化选择。而且“文体”是有自身多重结构内涵的概念,这种选择性亦体现在体裁而外多个层面的考虑。写作行为在文体定位之上,不断加以调整细化落实,从而实现具体文体的生成,在这转化过程中,不能忽视个人对文体的个性化选择。
《体性》篇中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本着“因内而符外”的观点,其认为文章写作“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并归纳出八种文章之体和不同作家的个性文体表现,具体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从用词看主要就是风格层面的归纳,但结合下文之详细论述则不难看出,每一体亦包含文辞、体制等多个层面之特性,因而,所谓的八体,即是从风格角度归纳的蕴含多重结构内涵的文体之大类。刘勰认为“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八体”之典范或可学而得,最终之文体创造取决于个体之情性。所谓“表里必符”。《定势》篇中说的“因情立体”正可以做本篇之恰切注脚:纷繁之文章样态与作者之主观情性关系密切,下笔为文无不是个人情性之体现,具体文体的创造是顺应情性的选择。
写作中个人情性的确影响着作者对文体的选择,朱自清先生当年就曾慨叹:“写小说真不容易。我一辈子都写不成小说,不知道从哪里下笔。铺展不开,也组织不起来。不只长篇,连短篇也是。”[7]虽是自谦,亦可见情性之取向,散文诗歌在先生那里则更为得心应手。人之情性有别,对不同文体的驾驭亦各有短长,因情立体,选择更为契合己之情性的文体发挥所长才是明智之举。今日之写作考试中经常面临的“文体不限”、“文体自定”等题目要求,无疑也是考查作者的文体选择能力,当然作为应试,还需考虑材料储备、驾驭难度、时间等其他因素而不单纯出于情性之考虑。但作为日常之写作实践,情性无疑是影响文体选择的重要因素,这种选择也不只在体裁意义上,亦体现于语言、风格等其他层面。
反观当今,学生在无文体限制的日常写作中,往往总是选择写自己喜欢或自认为较擅长的文体,即主要就是出于一种情性考虑,但应引起重视的现象是:对“不擅长文体”尚缺乏足够的认识与写作尝试却一味排斥;对“擅长文体”却在不断的自我重复中面目雷同难有超越,这便将“因情立体”片面化了,是一种盲目任情的表现。《体性》篇对这一问题有较为辩证的态度,虽标举性情,但非常重视学之功,即后天的习染,尤其是初学为文,认为“才由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因而提出“童子雕琢,必先雅制”的主张,并进而提出“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的具体训练方法。
因情立体是有前提的,应对各类文体之规范有较深入了解并通过反复的摸索实践去揣摩碰撞后才会有清晰之把握。“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正是较好的训练途径,要从不断的摹、练中慢慢确定自己的方向,而不是盲目任情。
(三)《定势》、《通变》与文体之定与变
文体实施过程中的个性选择同时引出文体之定与变的问题,文体的细化落实,不是对外在某种固定程式的照搬,而是一种动态的随机把握。这在《定势》、《通变》两篇中有详细论述。
《定势》篇中提出的“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篇中说“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势者,乘利而为制也。”详析字义,“体”侧重静态之文体呈现,而“势”侧重动态之行文趋势,二者是紧密关联的,“势”的把握体现了文体生成过程中定与变的辩证统一。
《定势》篇中归纳了四种“即体成势”的表现:“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从整体文意上看,亦大致呼应了《体性》中提出的“八体”,从中可见“体”之与“势”的紧密关联和制约作用,体现出势之“定”的一面。一旦选择某种文体,必然在各个层面制约着文之走向,写作者应因应其自然之势成文,体不同则势不同。但“势”隐含着不确定性,是动态的,并非某种固化之体的再现,“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必须具备“兼解以俱通”、“随时而适用”的能力,并且在具体行文中,防止“总一之势离”,注意文之体势的统一。因而在文体的创造过程中,既有定,又有变,所谓“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篇中“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的比喻形象说明了这一变与不变的道理,行文当“随势各配”,亦应遵循体之根本属性和自身的完整统一。机械因循,必然形成套路而固步自封,失去写作的创造之义。如学生习以为常的议论文写作,越来越沦为一种程式化的教学文体,结构固化、材料罗列、论证简单,呈现为一种一厢情愿地自说自话而没有真正地“论起来”,即是忽略了对文章之势的具体分析与灵活把握。而无视规范任意行文,即所谓“随性文字”,失去了“本采为地”的文体考虑,亦多忽视自身的完整统一,则沦为“失体之文”,或曰“讹体”,亦难以达到真正的文体之创造。《定势》篇总结应“执正以驭奇”,谨慎“逐奇而失正”,一旦“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
亦可结合《通变》篇来进一步辨析。“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可以说文各有体又文无定体,这一问题应辩证对待。文章本同末异,“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这涉及从不同层级来看待文体之义,普适文章之体、文类文体是为“有常”,具体文体则为“无方”之灵活创造。但这一创造是以掌握“有常”之体为前提的,“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方可“与言通变”。《阿Q 正传》的序中,鲁迅曾对古往今来各种“传”之特点做了一个总结,虽说有些游戏调侃,但亦可见其对传统史传文学、进而章回小说的深厚功底,正是建立在对多种文章旧式的了然于心和融会贯通的基础之上,鲁迅实现了“传”这一文体的突破,开创了现代小说的新范式。
《通变》篇指出通变之数即为“参伍因革”,有继承才能有创新,盲目求新,只会成为“讹体”。因而在“规略文统,宜宏大体”的基础上,写作者乃“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从而造就“颖脱之文”。这正体现了写作过程中文体之规范归属感与个人之情性选择的综合作用。
(四)《附会》与文体之整体自圆
具体文体是在对普适文体、文类文体融会贯通基础上的生成创造,其本身自成一体而完整统一。无论哪个层级,都蕴含着刘勰一以贯之的文之整体观,而集中体现于显性的具体文体创造中。通过上述对《文心雕龙》内容的分析我们看到,创作论自始至终体现出对写作文本的一种整体视角,这种“文之整体感”伴随着生成过程中的层级转化,又是对自身多层次结构的综合把握。前文亦已指出,创作论行文纲目的“总—分—总”的视角特点,正彰显了刘勰的文章整体观;而《附会》篇置于创作论之最后,笔者以为在强调具体文体之整体把握方面不无用意。
《附会》篇的内容,有人认为是就附辞会义角度谈命意谋篇的,有人认为是讲文章结构的,有人认为亦包括文章之修改。总之,本篇之文章整体视角显而易见,又置于整个创作论之最后,其彰显的文体论意义不容忽视,写作过程中文体层级的转化、文体感的作用发挥最终落实到具体文体的整体自圆。
何为附会?篇中说“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体现出明确的文之整体观。“附辞会义,务总纲领”,本篇着意强调“体统”之大视角而反对有句无篇。而附会之术又需“表里一体”,这与刘勰的多层次文体观紧密相联。篇中提出“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情志、事义、辞采、宫商正是由内而外多层次的文体之把握。“附会”体现出纵、横多向度的文之整体观。变文之术无方,文体之实施创造,应具备超越各种规范之上的独立把握能力,有效调动多种创作手段,使文章首尾各部、各个层面协调统一以达到自身的整体自圆。篇中说驭文之法“齐其步骤,总辔而已”正是此义,而如果“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
体之为义,最根本即其整体性。落实到具体文体的创造,在基于文体之规范归属、文体之个性选择的定与变的交错之上,文体感集中体现为对其自身纵横各向协调统一的判断把握。无体不成文,超越范式之后的整体自圆是文体创造之最终把关,倘若没有这种整体自圆的判断把握能力,则必定“统绪失宗”,写作中忽此忽彼,情志、事义、辞采、宫商不能相互协调,文章亦涣散零落,写成所谓“四不像文体”,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
有文就有体,文体之于写作意义重大。现今文体意识的淡薄已成为普遍现象,知识灌输型的文体教学方式亦应摒弃,培养写作过程中的“文体感”是提升学生文体把握能力的有效方法。而禀文之整体观,依托大量的阅读与写作实践,久之必形成强烈的“文体感”(包括规范归属感、文体选择、定与变、整体自圆等多个方面),文体知识也才会真正地内化为自己的能力。这,是《文心雕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1] 杨东林.开放的文体观——刘勰文体观念探微 [J].文史哲,2008 ,(4).
[2] 姚爱斌.论徐复观《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的学理缺失 [J].文化与诗学,2008,(2).
[3] 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 [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 赵红梅.论《文心雕龙》与高校基础写作课程的内容体系 [A].文心雕龙研究 (第十辑) [C].北京: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5] 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6] 李秋萍.不能忽视文体意识的培养 [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4).
[7] 陈孝全.朱自清传 [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