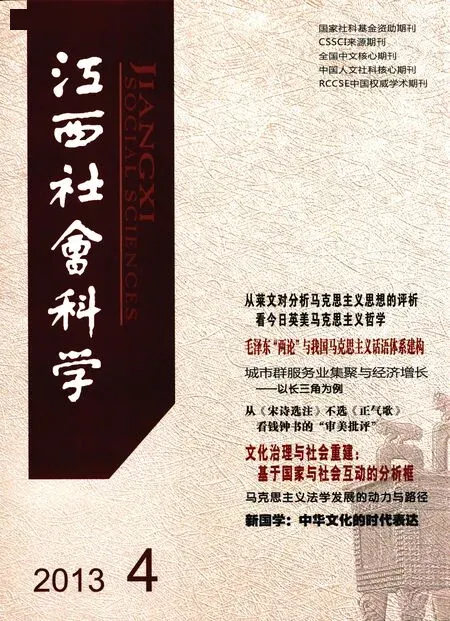现代政治应该如何对待宗教——以《利维坦》的分析为例
■李育书
在目前的政治哲学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把霍布斯视为近代政治哲学的开端,他们认为霍布斯最早提出以社会契约模式来设计现代政治,为现代政治哲学奠定了基础。但是,持此观点的很多研究者对霍布斯的研究多是以《利维坦》前两卷尤其是第二卷为基础,忽视了霍布斯政治学说中对政治与宗教关系的处理。然而,霍布斯的政治学说要与基督教背景联系在一起讨论才更有说服力,而且,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更是霍布斯政治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因此,本文以《利维坦》中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为分析视角,探讨霍布斯对政教关系的处理,借此了解现代政治对宗教的重构,并进一步认识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等原则的由来与限度。
一、政治学说讨论宗教问题的原因
正如很多研究者业已发现的,“霍布斯在他所有的政治著作与一系列其他著作中都讨论了宗教问题”[1](P117)。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霍布斯为什么会在几乎所有著作中都要讨论宗教问题,他本人在《利维坦》中给出了回答。霍布斯在《利维坦》第三卷卷首指出:“直到目前为止,我仅是根据经验证明为正确的、或在语辞用法上公认为正确的自然原理引伸出了主权权利和臣民的义务。”[2](P290)但我们不能仅根据人类社会的一般原理来讨论国家学说,还需要讨论具有宗教信仰的教徒如何组成基督教国家,因为“这个自然人不仅仅是孤单而非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某种实在的宗教的信徒”[3](P215)。在霍布斯生活的年代,主权者和臣民都是基督徒,“一个世俗国家、相同的基督徒的一个教会,其实是两个名称下的同一样东西”[4](P214),这种普遍的原理如何在基督教国家走向现实,“从基督政治学原理(即《圣经》)中究竟能推论出一些什么结论来证明世俗主权者的权力和他臣民的义务”[2](P488),是霍布斯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结合宗教来讨论政治才能更加切中当时欧洲社会的具体状况。长期以来,特别是在近代主权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政权和教权的关系非常复杂、甚至是长期敌对的,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因此,霍布斯要真正为现代国家建立根基,就必须论证清楚政权和教权的区别,处理好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因此,仅仅讨论一般政治原理是不完整的,《利维坦》前半部分讨论的正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它必须以在宗教背景之下对政治的讨论作为补充。
二、政治与宗教关系的处理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从自然哲学角度讨论过宗教问题,但直接讨论政治与宗教关系的篇章不多,在更多情况下他是通过政权和教权关系的梳理来论述政治与宗教的。他论述政权和教权的关系,主旨是确立政治权力对教会权力的支配地位,防止宗教干涉政治,它包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国家只能存在一个最高权力;第二,教会不享有权力;第三,最高权力是主权者的权力,教权从属于政权。
(一)只有一个最高权力
在《利维坦》的前两卷中,霍布斯讨论了国家与自然法的一般理论。在这些理论探讨中,霍布斯指出,从国家的本性与国家自身的维系来看,要让“利维坦”这个“人造的、有朽的上帝”在世间获得维系自身生存的力量,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就国家的生存与维系来看,只能存在一个主权者。在《利维坦》第二十九章“论国家致弱或解体的因素”中,霍布斯论述了国家可能的疾病,其中最主要的疾病是权力分属不同主体。“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主权者存在,而又有一个最高权力者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制定法律,另一个可以制定神律,那么同一群臣民就必然具有两个国家,这就是本身分裂的王国,无法立足。”[2](P256)“当这两种权力互相对立时,国家便只会陷入极大的内战和解体的危机之中。”[2](P256)因此,从一般政治原理来讲,要维持国家的生存就必须只有一个最高权力。
在《利维坦》的后两卷中,霍布斯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既包括圣史也包括俗史——后指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一直都只存在一个最高权力。在对圣史的考察中,霍布斯对《圣经》所记载的历史做了梳理,并把历史分为三个时代:上古时代是从亚当时期直到洪水灾难,现在的时期是耶稣降临以来的时期,将来的时期是耶稣再次降临之时。上古时期的国家由上帝直接统治,摩西等人实际上是上帝的代理。现时代只有一个最高权力,并属于世俗主权者。将来耶稣再次降临之时,天国将在地上建立,基督享有主权者所有的权力,政权教权合一于基督。而在俗史中,霍布斯认为,异邦人最早的主权者们都是在制造宗教,把服从国王纳入教义之中,教权属于政权,而在之后的俗史中,宗教事务也是属于主权者的职权。
因此,无论是从一般的政治理论来看,还是从宗教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都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霍布斯那里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也是不被允许的。
(二)教会不享有权力
在《利维坦》第二卷,霍布斯已经从世俗的角度论述了主权者的职权,在《利维坦》三、四卷,霍布斯进一步消解了传统的教会权力。在基督教传统中,教会一般拥有开除教籍、征税、决定教义、解释《圣经》等权力,霍布斯依据圣经与早期基督教传统讨论了这些权力。他指出,在基督教传统中教会本不应该拥有这些权力,教会本是信徒聚会的地方,不产生任何权力。在《利维坦》第三卷第四十二章“论教权”中霍布斯特别说明了使徒的使命只限于传道、教导、施洗等几个方面,传道只是传递信息,施洗只是主持外在仪式,都不产生管理外在行为的权力。相反,使徒的传教活动还得在主权者的授意下进行。至于通常认为属于教会的赦免与保留的权力,因为基督的代理人无法像上帝那样知道人们的内心,从而很难决定是否赦免,因此教会不再享有该项权力。
(三)教权从属于政权
就一般的政治原理来讲,国家只能存在一个最高权力;就人类历史来讲,也只存在一个最高权力。在《利维坦》所区分的圣史三个时代中,最重要的时代无疑是现在的时代,最高权力属于世俗主权,教权从属于主权。权力的来源在于世俗理性,从理性出发才能建构政治权力,宗教不但不享有对事务的管理权力,而且要经主权者允许才可以传播教义。主权者可以审查教义,决定传播的内容、方式和人选,享有决定宗教事务的权力。霍布斯把一度出现的政权、教权分离的状态称为“黑暗王国”,他认为这种状态带来了社会动荡与人民的无所适从,因此他坚决反对政权与教权分属不同主体。在此我们可以看出,霍布斯主张以政权统摄教权,以世俗政治主导宗教,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教分离,即政治与宗教互不干涉。此前,宗教还享有很多直接的政治权力,到了霍布斯时代,教权实际上已经开始萎缩,霍布斯从这种萎缩中认清了教权,并开始进一步褫夺教会权力。
三、霍布斯处理政教关系的思路
(一)公民神学的思路
霍布斯以政权统摄教权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说,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设计?宗教学说在他的政治学说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对此,有两个可能的解释:第一,宗教具有政治属性,宗教属于政治的一部分;第二,霍布斯的政治学说本身从属于神学体系,政治是神学的一个部分。
霍布斯对宗教的政治属性的论述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宗教和政治具有同构性,都源于人们的恐惧等基本情绪;另一方面,宗教影响政治。对此,霍布斯没有过多从正面来论述宗教本身的政治特性。但是,政治是关乎权力来源、如何治理、如何避免死亡的学说,在这些学说中,宗教的作用基本都是消极的;同时宗教虽不直接等于政治,但是可以强化政治,有利于政治发挥作用。宗教的负面作用在于宗教带来了政教分离,影响了主权者的权力,造成了国家的分裂与利维坦的死亡。
对政治从属于神学而言,霍布斯的努力也常被理解为站在信仰的立场来理顺政治与宗教关系,人的政治最终只是神的政治的一个部分,政治属于神学。霍布斯也指出:“信仰和服从结合在一起是为了得救。”[4](P233)欧克肖特指出,《圣经》背景下,政治具有神学意义,“要遵守他与同伴一起达成的契约,就不仅仅是一种契约的智慧,还是一种宗教义务。”[3](P221)这可以看作是对“政治属于神学”的说明。
在此,有必要回应上文提出的问题:霍布斯的学说究竟是要解决神学问题还是要解决政治问题,它究竟是政治神学还是神学政治?笔者以为,霍布斯的学说根本上是政治学说,他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欧克肖特认为,霍布斯属于“公民神学家”,“他不是一个自然神学家,自然神学和宗教的前提是外在于他整个的哲学体系的;他是在新环境中的旧式公民神学家”[3](P238)。笔者同意这样的判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可以从霍布斯学说中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来理解。霍布斯的政治学说根本上关心的是人类政治事务,他讨论宗教问题是出于政治目的,他的政治学说中虽然讨论政治与神学的关系,但绝不是要把政治变成神学。对此,很多学者都有清楚的认识,霍布斯“关心的不是为了某些关于上帝和来世的普遍的、理性的真理而改造哪些信仰,而是排除它们干扰社会的力量”[3](P238)。“霍布斯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家和自然法学家对宗教的首要兴趣在于防止它带来反政府的言论或政治的不团结,从而影响到政权的生存。”[1](P119)霍布斯区分政权和教权的目的是把教权纳入政权之下,建立主权国家。他讨论宗教问题是为了巩固政治,“霍布斯个人对体制化的宗教的态度,各个时期都是一贯不渝的:宗教必须服务与国家”[5](P89)。
其次,可以从霍布斯的个人信仰来理解其宗教学说。目前学界对霍布斯个人是否具有基督教信仰充满争议,他的宗教信仰的最根本原则就是相信“耶稣就是基督”。这一原则在《论公民》、《利维坦》中都有表达。霍布斯之所以在讨论政治时引入宗教,是因为他需要依靠上帝来保证社会秩序,需要以宗教加强政治让政治更具有力量。对于这一过程,斯特劳斯曾做出清晰的描述:“霍布斯首先是利用《圣经》的权威,鼓吹他自己的理论,然后特别是通过诠释,撼动《圣经》的权威本身。”[5](P85)后者更为关键也更为隐蔽。
(二)政治对宗教的解构
霍布斯不但把教权纳入政权之下,还以政治的思路解构宗教,这里以他对耶稣权力的论述为例。霍布斯认为,耶稣传教也需主权者的认证,不能违反主权者;其次,在耶稣被处死这件事情上,耶稣的死也是为了成就神人之间的新约,背后是立约精神;而当基督重新降临时,上帝国虽然实现了,但基督届时将依据人法进行统治。在这里,霍布斯完全是以世俗政治的思路在解释神学,神权的行使最终要在世俗政治中找到依据,这样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以世俗政治为基础的政治哲学,而独立意义上的信仰则显得无足轻重。
霍布斯以政治解构宗教,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宗教宣传的学说对霍布斯的政治学说构成了威胁。诚如斯特劳斯所言:“宗教是霍布斯政治学真正的敌人。因为,霍布斯政治学所依据的公理是:暴死是最大的恶;而宗教则宣扬还有比暴死更大的恶,即死后地狱中的永惩;宗教以此否定了霍布斯政治学的基础。因此,只要不驳倒宗教的说教,霍布斯的政治学就会受到质疑。霍布斯的政治学依赖于宗教批判。”[6](P85-86)霍布斯对神学的解构依赖于基督教的古典传统以及对圣经的重新解读。“在霍布斯时代很久以前,将宗教从世俗生活中割断的做法就已经被废弃了,这种做法只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做法。”[3](P236)霍布斯重拾这个传统。与此同时,“《圣经》是他推论出他所在社会的宗教信仰的权威来源”[3](P236)。然而,霍布斯有选择地引用《圣经》中对他的学说有利的章节,正如他自己声明的:“在引证《圣经》的时候,我尽量避免了含糊或解释有争议的经文;而只引证了意义最明白易懂、同时又跟全部《圣经》的一贯精神与见地相符合的经文。”[2](P488)因此,霍布斯表面上是按照圣经来解释并维护宗教,实际上是在依照政治目的来裁剪《圣经》、掏空宗教的基础以及教会权力的一切合法性说明,他是以《圣经》反教会,手法与稍早的宗教改革者们如出一辙,但结论更具破坏力。
(三)在信仰问题上的进退失据
为了解决政治问题,政治必须不受神学干涉;同时,一般宗教活动具有政治内涵,因此要纳入政治治下。这是霍布斯的本意,但是,关于如何看待信仰本身的意义,霍布斯的态度并不清晰,这一暧昧的态度也使霍布斯在对宗教的认识问题上有两方面失误。
一方面,他没看到宗教本身的独立意义和信仰本身的价值未能明言。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霍布斯出于怀疑主义立场,拒斥启示神学与自然神学,他甚至“通过对《圣经》权威的历史批判与哲学批判,暗中削弱这个信仰的根基”[5](P91-92)。另一方面,他虽然指出宗教具有政治功能,但他只是消极防范宗教干扰政治,未能果断地把宗教信仰纳入政治治下,来建立公民信仰,他的这个犹疑带来了很多风险。
四、对霍布斯思路的评价
(一)霍布斯对信仰自由的犹疑
霍布斯否定教权,把教权纳入了政权的统治之下,为现代国家真正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奠定了他在整个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信仰,霍布斯却有所犹疑。一方面,霍布斯认为信仰不单是个人的事,只要与利维坦的生存相关,它就是公共事务,应该由主权者来决定。“世俗权威尽管不能规定他的臣民的信仰,但他有权审查和支配他的臣民 (特别是那些对许多听众或观众说话的人)所有表达出来的、关系到对团体和平的推进或破坏的意见或学说。”[3](P211)另一方面,霍布斯认为,对于个人的信仰似乎也不便干涉。“敬拜也有公众的和私人的两种。前者是国家作为一个人而进行的敬拜,后者则是个人所表示的敬拜。前者对整个国家说来是自由的,但对每一个人说来则不如此。后者在私自举行时是自由的,大众之前举行则绝不可能没有一些限制。”[2](P282)
信仰自由和主权者权力之间最极端的冲突是殉教问题,对此霍布斯最后做出了妥协。他一方面坚称信仰只能由主权者提供,臣民只有服从义务;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主权者颁布的命令与臣民的信仰发生冲突该怎么办。霍布斯的解答是这样的:首先,臣民可以在内心坚持自己信仰,只要不表达出来;其次,内在信仰实在不被许可的话,可以选择殉教。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霍布斯对臣民内在信仰的妥协,从这个妥协扩张开来,那就是内在的信仰不属于主权者过问的范围,只要这个信仰不和公共政策发生冲突,也没有公开表达出来。这一犹疑最终带来了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但是思想自由就如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无法再合上,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
(二)思想自由之殇
霍布斯的犹疑,为近代政治哲学中个人信仰与思想自由预留了缺口。这一缺口后来被自由主义进一步发展,自由主义主张宗教信仰与思想自由属于内在范畴,政权不得干涉,这一原则也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而按照卡尔·斯密特的分析,这个缺口对于维系利维坦的生命来说是致命性的,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会打着思想自由的幌子从事危害利维坦的活动,而政权对此无能为力,最终会带来利维坦的死亡。
与霍布斯同时代的犹太学者斯宾诺莎接过了霍布斯信仰自由的话题,他在论述信仰的限度时角度与霍布斯类似。一方面,斯宾诺莎承认“执掌统治权的人什么事情都有权过问,所有之权都有赖于他们的命令。我说这话的时候,我不只是指世俗之权,也是指宗教之权而言……宗教之获得法律的力量完全是由元首的命令而来的。上帝借现世的统治者以临民”[7](P258-259)。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斯宾诺莎沿着霍布斯的逻辑来论证思想自由。他认为应该把思想区分为两个层面:主权者无法管的与主权者不应该管的。在没法管的层面,“强制言论一致是不可能的”[7](P275),“人的心不可能由别一个人处置安排的”[7](P270)。在不应该管的层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力,而且应该保有自己的思想;思想自由为科学艺术研究所必需,它的流弊可以由当局管理所遏制;危险性意见不是因为意见本身,而是因为其涉及行动;如果管得一致,“其结果必然是,人们每天这样想,而那样说,败坏了信义(信义是政治的主要依靠)”[7](P275)。
在这里,斯宾诺莎已经突破了霍布斯的犹疑,清晰表达出在很多情况下思想应享有不受干涉之自由,洛克则进一步把思想自由确立为唯一原则,“必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8](P5),主张信仰属于内在自由,政治属于外在事务,信仰自由不受政治干涉,这一思路最终发展成为自由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成了现代社会的一条基本原则。霍布斯那里,只是留下了宗教自由,留下这一空白的原因尚在于信仰问题难以干涉,主权者无法得知臣民的内心。通过斯宾诺莎、洛克等人的发展,宗教自由扩展到了政治思想自由领域,并借助制度来保障信仰、思想、出版等自由权利,这一变化虽是后来才出现的,但根源在霍布斯那里。政治与宗教信仰得到了明确的区分,政治开始成为一个独立范畴,并一度成为支配宗教的范畴。
信仰问题本非霍布斯关注的重点,他关心的是如何维系利维坦的生命。要维护利维坦的生命,就必须让主权者享有一切权力;同时,要限制教会对信仰的过问,说明信仰本身是独立的,教会无法过问。在这个说明过程中,霍布斯采用了宗教改革以来的基本立场,认为信仰是内在的,“因信才可称义”。这一过程不得不为主权者留下了限制,表现在认为主权者应该允许内在信仰。这一个缺口被后来的学者们加以阐释和扩大,这也是霍布斯的利维坦本身无法完成的缺口。如果没有这个缺口,就无法摆脱教会对政治事务的干涉;但如果允许这个缺口,的确可能带来利维坦的死亡,但对于霍布斯来讲,他也许并未清楚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的后果。
(三)利维坦的危境
在希腊神话中,卡德摩斯(Cadmus)用他的宝剑在东方杀死了一条毒龙,在雅典娜的劝谕下,他在杀死毒龙的地方埋下了毒龙的牙齿,毒龙的牙齿很快生根发芽,长出了一队武士,幸运的是这队武士最后帮助卡德摩斯建立了忒拜城。在《利维坦》中,霍布斯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霍布斯以理性驱除宗教,为政治争取了独立的空间与支配的地位,但在他杀死毒龙的地方,毒龙的牙齿却生根发芽了。只是利维坦未必有卡德摩斯那般幸运,这些武士可以成为城邦的护卫者,也可以从内部杀死利维坦。不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用施密特的话来说就是,利维坦已经被阉割了,它没有任何力量来对付思想自由,那支曾经用来杀死毒龙的宝剑现在已经掌握在由毒龙牙齿长出的武士手中,利维坦只能听任这批武士摆布了。
政治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必然要留下自己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思想自由。在《利维坦》中,政治对于神学的优先地位与宗教信仰自由使用的是同一种逻辑,这种逻辑思路更为清晰的表达就是洛克的内在信仰与外在信仰,霍布斯认为宗教只关心信仰,因此无权干涉政治,政治取得独立地位乃至对于宗教的支配地位,它的依据在于宗教是内在信仰,不产生干预外在政治的权力。而这一逻辑被沿用之后,带来的后果就是,思想是内在自由,只要不影响政治秩序,就必须予以尊重,政治权力没有理由可以干涉思想自由。因此,诚如施密特所指出的,当政治止步于思想自由的门槛之际,正是利维坦失去力量之时,政治从宗教处取得权力的那把宝剑其实正是对思想的解释权。由于政治不得插足思想,政治也就失去了自己曾经的宝剑而任人宰割,思想自由随时可能侵犯城邦的安全,也可以捍卫城邦的安全。政权只能听任自由的思想来摆布它的命运,这也是它在终结宗教对政治的干涉之后不可避免的宿命。
[1]Perez Zagorin,Hobbes and the Law of N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2](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英)迈克尔·欧克肖特.利维坦导读[A].渠敬东,译.现代政治与自然[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英)托马斯·霍布斯.论公民[M].应星,冯克利,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5](美)列奥·斯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M].申彤,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6](美)列奥·斯特劳斯.霍布斯的宗教批判——论理解启蒙[M].杨丽,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7](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M].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英)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M].吴云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