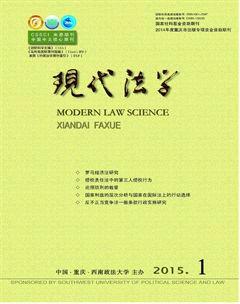对奥斯丁法律概念的再认识
周祖成++张印
摘要:奥斯丁用“主权者的命令”来解释法律,在学界引发很多争论和误解。其实,这只是一种认识方法,以证成法律的存在方式与作用,并不排斥法律与其他社会要素的联系。事实上,奥斯丁为解决法律与一般功利之间的张力,阐释了主权者与臣民之间的制衡关系,为主权者设定了必要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法律概念的社会张力。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梅因和哈特对法律的思考有了进一步的延伸与拓展。所以,在谈到奥斯丁的法律概念时,不能只强调其作为主权者命令的一面,还要看到其为化解法律概念的内在张力而为法律概念所开放的空间。片面强调法律中的单一要素,就会使法律与社会脱节,对法律的这种僵化解释将成为社会实践的阻碍。
关键词:奥斯丁;主权者;法律概念;张力;开放性
中图分类号:DF0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5.01.17
在什么是法律的问题上,奥斯丁提出了一个经典命题:“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在这一概念中,主权者成为解释法律的最核心的要素。用主权者来解释法律,肯定有其合理性及其现实的社会需要,但也会使法律产生与社会的张力,甚至被误认为法律就是主权者的意志与利益。奥斯丁在用主权者来解释法律时,已经认识到了这样的可能性,基于法律与社会的关联对主权者设定了必要的限制,这也是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在奥斯丁的法律概念中,主权者固然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我们不能局限于此,还应该看到其基于法律与社会的关联为法律概念所开放的空间,梅因和哈特对法律的解释实际就是在这一空间下的延伸,是对其法律概念产生的张力的进一步化解。
一、奥斯丁为何强调法律概念中的主权者因素奥斯丁选择“主权者的命令”来阐释法律,他的意图是否仅在于界定法律的概念、划定法理学的范围呢?为何他要以“主权者”作为理论建构的工具呢?这种路径有何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方法背后有何深意?
(一)主权的至高性及其服从基础上的统治秩序
奥斯丁用主权来解释法律,与主权在政治社会的至高性及其臣民对主权者的服从并以此而形成统治秩序有关。“主权”概念暗含着“独立政治社会”,一个独立的政治社会意味着存在一个主权者。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主权者处于政治优势地位,而臣民则处于隶属状态。主权者的统治需要隶属者的服从,这种服从以制裁为后盾,主权者具有施加这种痛苦的力量和目的。在奥斯丁的理论中,法律是主权者实施政治目标的工具。“义务”和“命令”(法律)具有紧密的联系,一旦主权者将其命令公布,那么,一个与此相关的义务便被设定。主权者以其强制力作为后盾,威慑臣民,使得臣民不得不履行其法律义务。
臣民对主权者的服从,首先是自愿服从,强制仅仅是次要的选择。如果将奥斯丁的服从观念理解为纯粹的威胁,这必定是对他的极大误解。臣民对政府的服从,往往基于他们对政府存在的便利性之认同。在全民教育普及的情况下,民众必然更为理性和独立,能够正确理解和判断各种偏见、恐惧以及盲目,最终对主权者的服从也将更为理性。
主权者与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没有关系,其权威源自一种事实——习惯性服从。所谓的习惯性服从,臣民有能力进行利益衡量,对服从主权者可获得的利益与抵抗主权者所获得的利益进行权衡,最终选择服从。一般而言,服从一个主权者比无政府状态更符合功利原则。良好政府的标准便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标准本身对政府提出了要求和约束。显然,奥斯丁为臣民抵抗政府留下了理论可能性。
现代法学周祖成,张印:对奥斯丁法律概念的再认识主权权力是一个最高权力,它可以随时废除任何现存法律。因此,如果主权者受到法律限制则是不真实的。因为主权者享有任意立法的权力,这样一种优势权力可以随时废除约束自己的法律。因此,奥斯丁说,“然而,在法律上,只要自己愿意,它就可以任意地或没有规律地运用自己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实现自己的目的。”[1]依此原理,主权者不会承担任何法律义务。相应地,主权者对于自己的臣民,也不享有法律权利,因为一项法律权利是以一部客观存在的法律作为基础的。
在此,奥斯丁赋予主权者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其根本目的在于宣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而非其不受约束的属性。正如梅因所言,奥斯丁的“主权”概念也许无法与所有的历史特例相吻合,但是他的方法仍然是科学的。在概念的抽象过程中,奥斯丁剔除了诸多不重要的细节。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主权”概念是一种先验的存在。不受法律限制的属性仅仅是主权的部分属性,奥斯丁并没有否认主权的其他属性 [2] 。
一个独立的政治社会中,主权者的存在,暗含着臣民对主权者的习惯性服从,标志着一种秩序的存在。有了秩序之后,生命和财产才得以保全。因此,奥斯丁将“主权者”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进行探讨,也许出于他对秩序的渴求。主权者拥有最高的权力,其他权力都是源自于此。因此,一个权力的金字塔便已形成,其中主权者处于塔顶位置。
在独立的政治社会中,能够保证一个统一的权力体系,权力关系自主权者向下辐射。一旦权力有了共同的出处,权力之间的冲突便能和平解决。因此,主权者作为最高权威,保证了一个统治秩序基本结构。假如不存在唯一的最高权威,一旦权力出现冲突,最终可能导致内战和无政府状态。这种结局是奥斯丁最不能忍受的。因此,主权者的意义,首先在于维持一种秩序。在独立的政治社会里,如果权力之间出现冲突,诉诸共同的上级权威,便能在不动摇秩序的前提下获得解决。在奥斯丁这里,主权者不仅是立法者,也是裁判者。
(二)主权者需要依托法律作为统治工具
依照科特威尔对奥斯丁的理解,要想理解法律,必需理解主权者,也就是理解统治。因此,奥斯丁的主权观念与一种统治方式密切相关。主权者的命令得不到服从的话,一个法律制度的作用便无法发挥出来,也就不存在法律。奥斯丁将立法置于研究的中心,政府是法律的根源。他想要用一种权力的结构来展示法律与统治的关系,这与现代社会的统治模式互相一致[3] 。endprint
在奥斯丁看来,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主权者又是社会的最高权力。由此可以推断,法律必定具有权力属性,需要依托主权者的权力,法律运行的背后必定是权力的运行,法律也才能发挥作用。法律和主权者使得独立的政治社会得以存在,它们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达成社会控制。一般公众对法律的服从,证明了主权者的存在,在实际上是对主权者的服从。法律本身和主权者密不可分,“法律”概念中包含着“主权者”的概念和权力的因素。
在整个权力阶梯中,主权者的权力是不能继续向上追溯的。主权者政府的建立是否合法,是一个与逻辑无关的问题,主权者先于法律,因此,主权者是否合法与法律本身没有关联。如果主权者可以受到法律限制,那么必定存在这种限制的来源,也就是法律,但是在一个独立的政治社会里,除了主权者自己为其臣民制定的法律之外,不存在另外一种法律。退一步讲,假如存在另外的法律,必定存在着颁布该法律的政治优势者(不同于主权者),自然地,便存在诸多的凌驾于真正的主权者之上的“主权者”,这些虚假的“主权者”则会共同统治一个政治社会,这样一种混乱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法律的权力属性使得一种统治秩序成为可能。在一个独立的政治社会里,法律是政治优势者对政治劣势者发布的命令。如果隶属者违背了这种命令,主权者便有权对违反者施加痛苦。假如法律已被违背,而痛苦却未加诸于违反者,那么,这部法律的有效性便值得怀疑,同时,处于优势地位者便没有被真正服从,当然主权者的这种统治可能不再存续。就此而言,主权者需要通过法律的服从建构统治秩序。在法律形式上,只要是主权者发布,就具备成为法律的条件,但并不影响法律还具有其他意义上的特征。
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只需要寻找它的权力根源即可识别,主权者便是法律是否存在的根据。一部法律是否符合道德感觉或者上帝法,都不会影响它的效力。假如因此而认为一部“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那么,主权者可能不再被习惯性地服从,进而,一个由法律构建起来的统治秩序必将失去,与统治秩序相伴随的安全和平可能不复存在。
(三)主权者与现实关怀
奥斯丁强调法律中的主权者因素,也是基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是一种基于当时社会诉求与需要的法律解释路径。对法律概念的解释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关,是一定现实关怀的产物。
十八世纪末,主权问题对英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加拿大、北美、西印度的地方当局与英国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确实属于当务之急。因此,面对不列颠与殖民地的这种关系,展开所谓“主权者”的讨论便顺理成章。在不列颠和美洲殖民地进行对抗之时,英国国民的偏见加上政府的失策,导致了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宣告成立。该事件的影响远超其直接结果,不列颠面临着半个世界的挑战。而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政治家,大多抱有一种意图,即英帝国应当紧密联合成为联邦。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对英国社会造成巨大震荡。雅各宾专权使得英国国内对于一切贫民的集会抱有恐惧。法国革命中激进主义的爆发以及托马斯·潘恩《人权论》的发表,一部分人深受鼓舞,另一些人则抱有恐惧。1792年之后,法国向欧洲开战,革命转向恐怖,英国国民对国内改革派充满敌意。改革者与镇压改革者形成剑拔弩张水火不容之势。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同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贫富差距悬殊加剧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仇视。经济的动荡使得大批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向工业城市集聚,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境遇,只好对政治活动倾注大量精力。物价上涨,使得反《谷物法》运动得以展开。其中,雇主和工人联合起来反抗地主阶层。穷苦阶级尝试通过政治活动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托利党政府则采取高压手段。暴动者和印刷品制造者被课以重罪。社会底层民众的待遇并未得到提高,而政府对他们的抗争则采取压制态度。皮特时期的《禁止结社法》便是明证。1819年,曼彻斯特发生“彼特庐”大屠杀,掀起了一波惶恐骚乱,死伤颇多,英国的秩序大有崩溃的危险。
恢复秩序结束乱象,需要废除高压政策及不公平的法律,因此,新的立法成为必要。一个强有力的主权者,通过适当的立法可能终结乱局,这种立法必须考虑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当时的英国,通过法律实现政治、经济目的已是常态。
当时,社会改革的呼声极大,小规模的暴力冲突时时都有升级的危险。在不列颠人民的民族性中,在他们睿智的思想家的头脑中,内战则是万万不能被允许的。因此,法律成为了社会变革的工具和标志,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围绕《改革法案》(1832年)的斗争,大有激化之势,一旦《改革法案》不通过,激愤的民众可能采取过激行为,国家的和平之局可能被打破,要想短期内恢复良好秩序将成困难。最终,《改革法》的通过确保了不列颠的和平与秩序,民众的成分得以注入英国。在此,主权者的立法行为确保了英国的统一[4] 。其后,一系列的统一立法巩固了政治斗争的结果,同时,社会的管理也趋于体系化。这表明,法律只有与主权者结合,才能产生相应的社会功效。
当时英国法律制度面临严重的问题,促使作为法学家的奥斯丁进行理论探讨,为法律体系的改革寻找出路。18世纪末至19世纪,英国普通法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普通法调整范围窄,程序复杂,很多社会关系都没法调整。衡平法由于其原则的确定僵硬繁琐,使得权利很难得到救济。另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使得人民的权利可能受到威胁。司法机构职能重叠冲突,管辖权限不清。对于相同的案件,普通法和衡平法往往得出截然相反的判决。司法程序复杂冗繁,诉讼成本极高。司法效率低下,冤假错案多发。一个案件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最终结果,这与工业社会格格不入。英国当时缺乏职业警察,大部分城市都由底层民众负责保安事务,治安混乱,人民缺乏安全感。当时的英国选择严刑峻法以防止犯罪,并迫切需要改革法律程序、制度和机构。
18世纪末,英国法学家开始从大陆法系中寻找资源,以实现普通法的体系化和科学化。奥斯丁研究罗马法的意图则在于为英国法找到一些通用的概念、原则和体系,这也是法律科学化的一个过程。普通法和衡平法体系各自的弊端层出不穷,彼此之间冲突不断。当时的英国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完成普通法与衡平法之间的融合。在这种背景下,奥斯丁认为通过主权者的立法便能实现如上目的。而在当时,多数人的统治成为了思想家们的目标,议会改革是政治领域的核心话题,这在法律领域表现为,议会立法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普通法与衡平法的不足[5] 。endprint
(四)小结
奥斯丁借用“主权者的命令”来阐释法律,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法律运行背后的权力因素,恰好是奥斯丁对政治过程的准确体认,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法律的运行也就是权力的流动。主权者意味着一种统治权力体系,这种权力结构便是统治秩序的基础。所有的权力具有一个共同的终极根源,便能和平地解决权力(权利)冲突。最终,一个独立的政治社会凭借臣民对主权者的服从建立并维持下去。
在英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奥斯丁对主权者“情有独钟”也显得顺理成章。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当时政治家极为关注的问题,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对英国社会产生巨大震荡。因此,思想家探讨和交流什么是主权,以及主权的范围有多大,显得理所当然。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使得海峡对岸的英国战栗不已。工业革命的副作用也已发作,贫富分化严重,阶级对抗激烈,社会暴动时常发生。眼看一个表面统一的社会秩序就要崩溃,在这种背景之下,奥斯丁对秩序的渴望便寄托在一个强有力的主权者身上,制定符合全体民众利益的法律可能结束乱局。英国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冲突,使得英国法律科学化的任务亟为迫切。要想走出此困境,科学的立法也许是一把钥匙。主权者通过立法的方式居中裁判,解决普通法与衡平法之间的冲突。因此,奥斯丁将立法(而非法官造法)置于讨论的中心。
如上可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奥斯丁极为强调法律的权力因素。一旦社会面临失序的危险时,秩序的价值应当得到优先关注。奥斯丁描述和构建的是一个法制国家的意象,在其中,法律得到臣民的遵守,而被臣民所遵守的法律符合功利原则。法律成为了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工具,臣民的服从义务被强调。该谋划为法治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倘若完成对一切权力的法律规训(包括主权者),一个法治国家便已初步建立。
二、奥斯丁法律概念的方法论意义及其社会空间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强调了秩序和权力对社会的重要性,准确把握了法律运行的规律。但是,其中“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和“主权者不受法律限制”的观点很容易被误解。法律作为规范体系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需要在社会中运行,也必然存在社会性因素的制约,这使作为主权者命令的法律与社会之间产生一定的张力,对这种张力的化解,实际上为法律概念的解释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主权者命令说”的方法论意义
在奥斯丁的理论体系中,法律与“主权者”这一概念之间存在着依附关系。“主权”概念定义了“法律”的概念,进一步,法律规定了“义务”、“权利”以及“惩罚”等概念。因此,“主权”是奥斯丁理论链条的起点[2]。
在奥斯丁这里,既然主权是法律存在的根基,那么,与主权没有必然联系的东西便不是法律。如此推论下去,那些不属于法律这一概念的东西应该全部从“法律”上剥离。当然,自然法、道德、习俗以及数学和物理定律这一类的东西不能被称为法律。能够以“主权者的命令”为名进行统治的,也只有法律。当然了,奥斯丁并不否认:在现实社会中,道德、风俗、习惯和身份对个人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个人确实生活在一个不只包含法律的复杂社会中。他只是认为,法理学的恰当对象是一个独立政治社会中的主权者为其臣民制定的实在法,其他的现象则应当交由其他科学分支去研究和探索。
奥斯丁准确把握了现代社会的统治模式,权力通过法律的实施而运作。现代社会极其复杂,需要有一种富有抽象属性的工具进行统治。主权者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抽象和化约出共通的东西,进行立法,便能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奥斯丁从政治现实中抽象出了“主权者”、“命令”等概念,同时为这些概念开拓了一个自治的领域—法理学。该领域以研究“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为己任,法理学的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法律是什么”的问题,法律的资格根源于一个独立政治社会中的主权者。只要一部法律是主权者制定通过的,这部法律便是有效的,它便是法理学分析研究的对象,这种分析并不需要以伦理科学为基础。在此处,相较于哈特,密尔对奥斯丁的理解更为准确。他认为奥斯丁使用的方法是化约和抽象,共通的东西构成了他的法理学[6] 。
因此,奥斯丁用“主权者的命令”来界定法律,并不是为法律划定一个封闭的空间。事实上,“主权者的命令”只是法律的一般属性,或许是最重要的属性,但绝不是法律的全部属性[7]。以奥斯丁当时的眼光看来,法律的共通属性便是权力属性。出于理论和现实的需要,其他的一些属性已被剔除掉,他只是强调了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这种属性而已。实际上,奥斯丁也认识到他的法律概念可能引起的误解,对主权者与臣民及法律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一方面化解了其法律概念的内在张力,另一方面也为法律概念扩展了新的空间。
(二)主权者与臣民之间的平衡性制衡关系
主权者的命令与一位暴徒的命令是不同的。臣民对主权者的服从建立在一般功利的基础之上,奥斯丁所理解的统治具有一种交换的意蕴。主权者为人民提供一般功利的满足,臣民向主权者奉献出忠诚。独立政治社会中秩序并不仅仅是主权者对民众的压制和威胁,更是理性臣民对主权者的道德认可。
奥斯丁将主权者建基于一种社会事实——臣民的习惯性服从——之上。臣民意识到服从一位良好主权者的利益远大于抵抗的利益,便实际地服从。这种逻辑将主权者和臣民置于一种互相合作的动态关系之中,主权者实质上受到了舆论的广泛限制。臣民和主权者之间的关系是流动的,服从涉及臣民对统治权威的道德认知[8]。主权者虽然不受法律限制,实际上会受到社会舆论的约束,主权者与臣民之间会形成一种相互制衡关系。社会必须形成一种平衡性制衡关系,否则,社会关系就会破裂,实质上这也是对法律的要求和规制。法律作为主权者的命令,仍然有着内在的制约机制。
在一个理性社会里,如果主权者的立法违背了功利原则,那么,全体民众的一般幸福可能无法实现。理性的民众必将起来抵制这些有害的法律,一个主权政府有可能会被民众所推翻。因此,主权者虽然不受法律的限制,但是,主权者个人或群体仍然不能恣意而为。一个政治社会里,优势者和劣势者不会保持不变,主权者和臣民的力量关系并非固定不变。民众完全有可能推翻主权者,这对主权者是一种威胁和约束。endprint
(三)法律并非主权者的恣意
在奥斯丁的理论中,主权者不受法律限制,那么,主权者是否可以恣意发布命令呢?当然不是。原因在于,主权者受到各种因素的约束,进而,主权者不可能毫无顾忌地发布命令,最终,法律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结果显而易见,法律除了体现主权者的意志之外,还具有其他的含义。法律除了具有权力属性之外,还具有其他属性。
主权者受到上帝法的限制,那么,法律也受到上帝法的检视。上帝法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上帝的明示命令,另一部分则是默示命令,该默示命令则只能通过一般功利来理解的。其他法都要由上帝法来衡量和评价。因此,法律应当与上帝法及一般功利相一致,主权者的命令也非完全不受限制。在奥斯丁的思想中,上帝法是对实在法律的终极衡量标准。因此,“法律或者道德在伦理上的善取决于其遵守神法的程度。”[9]
正如前文所谈到的,主权者不受法律限制是其主要属性,但是奥斯丁并没有否认主权者还具有其他属性。奥斯丁不会犯常识性错误,他不会允许主权政府的权力沦为恣意的工具。因此,有必要为主权者设定其他类型的限制,社会道德、民众舆论也是立法者需要考虑的东西。“毕竟,一个政府只能因为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而受到限制,不去剥夺其留给或授予臣民的政治自由。而且它只能受到上帝法的约束,从而,不为臣民设定一般功利所谴责的义务,这里的上帝法,当然是人们通过功利原则来理解的。”[1]320
奥斯丁对无政府状态抱有很深的恐惧,如果一部法律是违背一般功利的,那么,民众应当通过理性的抵制促进该法律的修改或废除。因为法律不符合一定的标准(上帝法或社会舆论)而否认其作为法律的资格,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可能会导致现存统治秩序的崩溃。
主权者往往积极倾听某些人的舆论和利益要求,他需要尊重作为实在道德的国际法之约束,同时也要尊重臣民的舆论和感觉。立法者需要考虑社会既存的习惯,在不明白习惯据以存在的缘由,或者明知习惯具有有益效果时,制定法律横加禁止便是不明智。当社会舆论、道德感觉和宗教情感已经压制了习惯的生存空间时,主权者可能不需要另立法律。如果习惯与社会舆论等保持一致时,法律的禁令可能激起社会普遍的恐惧和仇恨。
对于一个行为,法律、道德和宗教往往抱有相同的态度。但是,不可否认,一些行为应当由法律来调整,而另一些行为则应当交由道德进行控制。法律的范围并非无限,而其功能也非无限。因此,伦理科学对于法律应当调整哪些行为提供指导。
在奥斯丁的功利主义思想中,他对个人自决原则深信不疑。个人是其利益的最佳裁判者,对于如何行为能够促进自己的利益,并不需要主权者为此发布命令。具体的善和一般的善一样重要,如果损害了具体的善,那么,一般的善也会被牺牲。因为一般的善是具体的善的总和。个体只需追求切身利益,在此过程中,一般的善也得到实现。“在这里,一般而言,每个单独个人是其自己利益的最佳裁判者。而且,对何为最大快乐,以及何为最大痛苦等等问题,每个单独个人,也是最佳以及最为适当的裁判者。”[1]139
在奥斯丁的思想中,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依附共生关系。主权者掌握了政治权力,通过法律的运行,对臣民的行为进行惩罚和奖赏。同时,主权者掌握了知识力量,通过社会教育,对臣民的愿望和知识给予指导和控制。但是,统治者无法完成所有任务,应当为个人留有足够的自主空间。理性的个人能够最好地判断自己的利益,同时,个人利益在其实现的过程中能够与社会利益达到自动和谐。在奥斯丁的功利主义思想中,这两种思想力量的冲突极为明显,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这种理论任务被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继承,并得到严肃对待和尝试性解决 [10] 。
在奥斯丁看来,法律要想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民众的素质和修养则是一个必备条件。臣民可能会支持一个暴虐的主权者,也可能会痛恨一个勤勉的主权者。因此,开明的人民必定强于法律的权柄。社会上流行的那些无知的偏见以及邪恶的动机,迫切需要“公众教育”的补救[6]92。民众便能理解自己处境的真正原因,从而发现一些方法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同时获得一定的闲暇,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最终摆脱任意的统治[1]93。科学知识的普遍传播最终可以使得民众摆脱对权威的盲目尊崇,具有理性的思考能力,为生活找到确定的指导。虽然精确的科学知识掌握在那些专门研究者的手中,在权威的指导之下,民众必然获得理性思考的能力。因此之故,奥斯丁始终殷切希望全民教育的普及。
(四)小结
奥斯丁提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但是,法律与主权者的意志之间却不能划上等号。在奥斯丁的体系中,“主权者”首先是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概念,“主权者”充分阐释了法律运作背后的权力因素。对于法律而言,主权者(或权力)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却非全部因素。
由于主权者受到诸多的约束,可知,法律也会受到诸多的限制。奥斯丁为主权者设置的约束,同样适用于法律。法律需要经过上帝法和功利原则的检验,民众的道德舆论也会对法律的制定提供意见。主权者的意志代表了法律中的权力因素,而制约主权者意志的成分则代表了法律中的其他因素。奥斯丁的论说强调了法律与主权者意志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并没有否认法律具有其他的属性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法律可以从主权者的角度进行解释,当然也可以从与其他要素的关联上进行解释,法律的社会性决定了法律概念的开放性,如何选择则取决于现实的需要。
法律的作用和功能是有限的,应当将不属于法律调整对象的事项交由习惯、道德和宗教来调整。对于立法而言,主权者并不需要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应当为民众的自由行动保留足够空间。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民众的开明,民众的素质和修养制约法律的作用。
三、梅因和哈特对奥斯丁法律概念的延伸与拓展奥斯丁为法律概念打开的空间在梅因和哈特的理论中得到充分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解释是对奥斯丁法律概念的延伸与拓展。
(一)梅因的拼图:法律的历史属性endprint
在许多方面,梅因和奥斯丁的观点是相似的。他们二人都研究罗马法,从中寻找理论资源。梅因也极为重视法律概念的准确含义,探究概念内涵的历史演变。梅因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他从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中寻找和归纳法律的一般规律。对于奥斯丁的研究方法以及思想观点,梅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梅因认为奥斯丁准确体认了现代国家的法律运作过程,其中权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2]192。现代国家幅员辽阔,具有颇多的复杂性,要想进行良好的统治,必需借助最为有效的工具——法律。为了实现权力的高效运转,具有抽象性的法律往往会忽略掉一些琐碎细节。现代社会中,主权者是远离臣民的,真正进行日常管理的是法律以及经过授权的公务人员。
梅因以印度的旁遮普为例对奥斯丁的主权概念提出了质疑,他将帝国划分为两类:立法性的帝国与征税性的帝国。根据历史事实,旁遮普属于后者。虽然绝对统治者极为专制残暴,而且以武力维持其征税行动。但是他们并不立法,也没有立法意图,而且很少干涉臣民的民事生活。进行日常管理和宗教指引的往往是无法溯源的古代习惯法,虽然“主权者”的临时命令会打断这些习惯,但是,这只是特例。旁遮普的习惯获得服从,并非武力威胁的缘故,而是因为其依赖民风、习俗、迷信以及某种说不清楚的本能。
在梅因看来,奥斯丁的目光被罗马法所吸引,具有某种必然性。罗马帝国是立法性帝国的典范及源头,罗马注重立法,而立法恰恰是消解地方习惯的有力工具。与习惯的运行不同,立法活动无法关注所有的特殊情形,为了使得法律切实可行,就需要剔除习惯法所依赖的迷信民风等,实现法律的普遍性和公平性,同时得到严格执行。奥斯丁想要维护法律的统一、逻辑一贯与概念清晰,这种意图与罗马法的风格一拍即合[2]191。
因此,梅因对奥斯丁的法律及主权者观念提出了客观的评论,该评论恰当地弥补了法律命令说的漏洞。他认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是主权者的命令,有些法律则远离了主权者的命令,这些法律与社会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以及地方权威密切相关。事实上,主权者日益活跃的立法活动则直接或间接地挤压了这些习惯和传统的生存空间,同时,法律与越来越多的强制联系在一起。梅因赞同法律的具有权力因素,提出了法律的历史因素,为理解法律提供一种历史分析的视角。
(二)哈特的拼图:法律的规则属性
哈特从细节上对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取得了一定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哈特认为“主权者命令说”无法解释法律的持续性,同时,不受法律限制的主权者(或立法者)并不是法律体系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奥斯丁用主权者来识别法律,而哈特则用承认规则来识别。
哈特举了一个“雷克斯”的例子来反驳奥斯丁,他认为,第一任主权者将权力交付给第二任主权者的过程中,继任者具有发布命令、进行立法的权利,但他获得该权利并非因为臣民对他的习惯性服从,而是基于法律的持续性,权利来源于授权规则。服从习惯不同于规则,习惯并不必然带来权利。其实,臣民接受的是授予新任主权者权利的规则而已。法律作为一个规则体系,具有持续性,并不因为主权者个体的消失而失效。第一任主权者制定的法律本身具有效力,并非像奥斯丁所说的那样——新任主权者默认其效力[11] 。
当然,哈特的“雷克斯”例子也有漏洞:首先,在雷克斯例子中,第一任主权者与第二任主权者之间的权力交接以和平方式进行,两任主权者的法律之间确实存在持续性。但是,对于第二任主权者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取得统治权的情形而言,法律规则的持续性就无法提供解释。其次,第一任主权者肉体的去世并非主权者的消失。因此,臣民对主权者的习惯性服从并没有变化,变化的仅仅是具体承担统治功能的人而已。
其实,可以如此理解:在第一任主权者的世界里,主权权威的存在本身是一种事实,并不讨论其产生是否符合理性、是否正当,主权者的意志足以自行。奥斯丁关注的是第一任主权者的统治。而在第二任主权者的世界里,主权权威已然树立,主权权力的运行和实现更为迫切。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的构成性要素,本身的运作比主权者的立法更为重要。哈特关注的是第二任主权者的统治。
在奥斯丁看来,主权者除了受到上帝法的约束之外,还受到社会道德的限制,既存的宪法是一种社会道德,主权政府“违宪”其实是违背了某种社会道德。哈特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限制最高立法权力的宪法并不只是一种法院所关注的道德。对最高立法权威进行法律限制,并不影响法律体系的独立性,更不会使得一个主权者服从于另一个“主权者”。宪法性限制可以被理解为立法应该遵循的条件,违背这些条件的立法将是无效的。这些限制附加给立法权威的并非“义务”,而是“无能力”[11]63。
奥斯丁和哈特都意图解决如下问题:法律是什么?奥斯丁将法律视为一种人为的创设物,被用来贯彻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是一种主权者的统治工具。在哈特这里,他认为法律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而非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本身就是一种统治形式,一切人(包括主权者)都要服从法律的治理。只有成为一个社会秩序的积极参加者,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律[3]99。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在这个意象上,哈特和奥斯丁的立场是相同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奥斯丁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贯彻法律,在他的构想中,需要一个高于法律的权威,才能实现有序的统治,这与当时的法典化运动密切相关。而在哈特这里,他以一种内在于统治秩序的观点来思考,秩序和权威已然建立,法律作为一种型构社会秩序的存在物,其发挥作用并不必然与主权者直接相关。其实,哈特更为关注法律的规则属性和社会自治特征,而奥斯丁更为关注权力运作而已。
(三)小结
奥斯丁的主权和法律观念经受了不同评论者的批判,特别是梅因和哈特,他们二者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是,这些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奥斯丁的理论体系。客观而言,梅因和哈特的思想完美地弥补了奥斯丁思想的漏洞,为后来的评论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在承认法律的权力属性的前提下,梅因关注到了法律的历史属性,而哈特则更为关注法律的规则属性。梅因将法律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研究,社会的风俗、习惯、甚至迷信等因素得到了重视。法学研究的目光被拓展了,经由立法产生的法律和习惯法都是法律的表现形式。而在哈特这里,法律本身是一种社会构成因素,每个人都难免要与法律打交道,法律与民众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压制关系,更是一种积极接受与参加的互动关系。endprint
当然,法律仍然具有一些梅因和哈特没有涉及到的属性。在此意义上,法律具有开放性。强调法律的权力属性无可厚非,但是,法律的属性并不限于主权者的命令这一种。哈特的观点给人们提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单纯强调民众对法律的服从已属逆历史潮流而动。奥斯丁完成了法制基本框架的建构,在此基础上,哈特的法治理想才得以实现。
结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秩序面临奔溃的边缘,使得奥斯丁格外重视法律的权力因素(主权者)。同时,为了完成英国法律科学化的历史任务,他意图采用主权者的立法来完成英国法律体系的改革。
主权者象征着一个层级性权力体系的存在,该体系保证了一个基本的统治秩序。奥斯丁从主权者的视角来阐释法律,也就是用一种权力运作关系来界定法律。显然,他对现代社会的法律运行有深刻的体认,看到了诸多法律现象背后的“真相”。奥斯丁采用抽象和化约的方法,识别出了隐藏在所有法律现象身后共通的东西:权力。
虽然,主权者的暴力和强制是所有法律现象中蕴含的普遍因素,这种认知侧重于政治社会的权力属性,但是法律的其他属性并没有被奥斯丁所否认。法律虽然以惩罚制裁作为后盾,但是纯粹的武力并不足以维持统治,主权者对民众的“教示”显得尤为重要。法律的作用不仅在于约束和惩罚,更在于指导和帮助。
在奥斯丁的法理学体系中,主权者的意志与一般功利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张力,这为以后的评论者留下了发挥的空间。在承认法律具有权力属性的前提下,梅因关注了法律的历史属性,哈特关注了法律的规则属性。
法律并未被某个思想家局限于某个单一的方面,相反,法律具有开放性。针对不同的社会问题,需要强调不同的因素。法律需要随着的社会变化而变化,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秩序是社会运转的基础,当社会面临失序危机时,强调法律的权力属性具有现实意义。当一个统一的法制体系得以建立之后,单纯强调民众对法律的服从便丧失了法律的进步意义,而民众对法治秩序的主动参与则更具积极意义。同时,现代社会极具复杂性,抽象的立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习惯法、法官造法能够充分弥补制定法的僵化和漏洞。作为一种学理解释与认知方法,法律概念可能偏重于某一方面,以证成法律的存在与特征,但在实际社会运行中,必须根据社会需要来认识法律与不同社会要素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事实上,许多理论家就是根据法律与不同社会要素的关系来认知法律,强调法律中的特定要素,但并不否定法律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使法律概念呈现开放性特征。片面强调法律中的某一种要素,使法律只与某一要素相联系和等同,可能会使法律与社会偏离,甚至成为法律与社会发展的障碍。法律概念的开放性可以消解特定法律概念可能产生的社会张力,通过多维认知为法律与社会的契合开辟道路。ML
参考文献:
[1] 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M].刘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41.
[2] 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M].冯克利,吴其亮,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77.
[3] Roger Cotterrell. The Politics of Jurispruden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Legal Philosophy[M]. London: Butterworths, 1989:50.
[4] 屈勒味林.英国史[M].钱端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714.
[5] 程汉大.英国法制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1:384.
[6] J. M. Robson.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Vol.XXI[M]. Routledge & Kegan Paul: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170.
[7] W. L. Morrison. John Austin[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86.
[8] Oren Ben-Dor. Constitutional Limits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Critical Study of Benthams Constitutionalism[M]. Oxford-Portland Oregon: Hart Publishing, 2000: 40.
[9] Wilfrid E. Rumble. Doing Austin Justice: The Reception of John Austins Philosophy of Law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M].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66.
[10] 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M].李桂林,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57.
[11] 哈特.法律的概念[M].许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