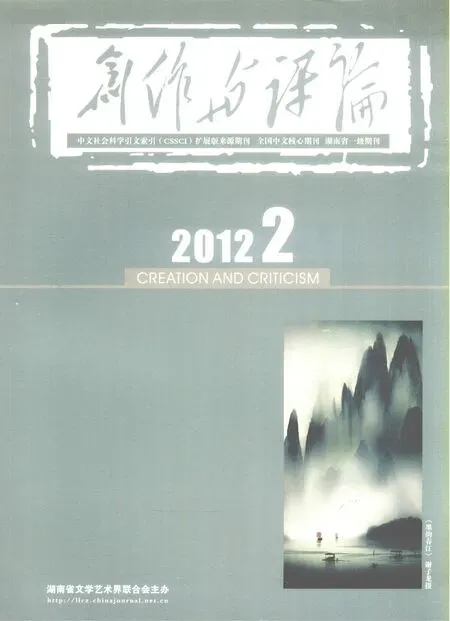无根者的孤独与言说*——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文学言语学解读
■ 李清霞
有人说《一句顶一万句》讲述的是“贱民”的生存经验,认为“贱民”“是指那些不安分于土地上进行传统耕种的以小手艺为业的三教九流的农民。”①文本中,杨百顺先后做过的事由有卖豆腐、杀猪、染布、破竹子、挑水、种菜、卖馒头等,其他事由包括赶车、贩牛、剃头、打铁、卖盐、卖葱、做首饰等等,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称他们为小工商业者。中国文学中,工商业者是被忽略的群体,他们很少以正面形象出现,《水浒》、《金瓶梅》中就是这样,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连妓女都瞧不起卖油郎。《阿Q正传》是最早为这群人立传的,鲁迅说阿Q身份“卑贱”,以往立传的种类、通例皆不可用,只好取了小说家的“闲话休题言归正传”套话中的“正传”,且所用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即白话文,用白话文写作是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标志。新时期,冯骥才、邓友梅、陆文夫、林斤澜等作家的市井小说开始关注这一人群的现实生存现状,这些作品关注市民阶层的现实生存状况和各地的风俗民情,对这群人精神世界的开掘还不够充分。刘震云从自己的创作经历出发,深切地体悟到言说不被人理解、甚至误解的痛楚,从《一腔废话》、《手机》等作品开始,将叙事的笔触指向说话本身,即探寻言语的形而上意义,他说:“我不认为我这些父老乡亲,仅仅因为卖豆腐、剃头、杀猪、贩驴、喊丧、染布和开饭铺,就没有高级的精神活动。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活动特别‘低等’,他们的精神活动就越是活跃和剧烈,也更加高级。”②作者试图用“引车卖浆者流”的话讲述了这群无根者几千年来的孤独、寻觅与痛苦。
一、言语,引车卖浆者流的存在方式与意义
语言是人的本质属性,它不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和手段,而且包含着丰富的“人性”内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言语学首先分析了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系统的、静态的,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不能独自创造或改变语言,它凭借社会成员间的契约而存在。而“人类的言语活动贯穿在人类生存的各个层面,从生物性层面,到社会性层面,到精神性层面。”③杜夫海纳认为,艺术是言语,不是语言。原始时代,人类言语活动的心理内涵与人类实际的言语表现之间,可能出现过最初的、“低层次”的统一,随着人类文明理性和语言学的发展,语言与心灵之间产生了裂隙,人们开始在语言与心灵的断层间痛苦地游移、盘桓,用刘震云的话说就是“原来世上的事情都绕”,人们说话时总是“绕着说”,而不直接说。杨百顺想跟老裴学剃头,老裴却介绍他去老曾那里学杀猪,后来老曾告诉他患难之交只能做朋友,不能做师徒,老裴不收他做徒弟不是怕老婆,而是因为两人有患难之交。
从文学言语学来看,《一句顶一万句》不是现实主义或新写实的,而是超现实主义的,作者试图使用“裸体语言”来讲述,裸体语言指能再现“心灵中感应到的气氛”、捕捉到“潜意识里的喧嚣与骚动”的语言,能表现人的“纯粹的精神的无意识活动”的语言。言语是人的潜意识未加雕饰的表达,人常说酒后吐真言就是这样的意思,牛爱国喝醉了酒,对冯文修说要杀小蒋的儿子,要杀庞丽娜,冯文修将这话传了出去,全县城的人都知道牛爱国要杀人。这时牛爱国拿起刀想杀的人竟是冯文修,我们发现“话走了几道形,牛爱国没有杀人,但比杀了人心还毒。”④他被迫离开了沁源县。朋友掰了,知心话就成了“刀子”,“反过头扎向自己”。话比人心毒。文本中,老裴、杨百顺都在心里杀过人,在杀人的路上,老裴碰到了杨百顺,杨百顺碰到了来喜,于是悟到“世上的事情,原来件件藏着委屈。”从而打消了杀人的念头。他人(如杨百顺和来喜)的苦难间接拯救了那两个人的命。牛爱国确实在心里杀过人,在言语上也杀过人,却没有行动,在法律上这也是无法界定的,但言语一旦说出就成了事实,传播开来就更可怕,牛爱国觉得自己似乎真的杀了人。
作者试图通过言语让读者进入人物的深层意识中,从人物的内心或潜意识层面来讲述故事,找朋友、找话实际上是人物借助他者来确认自己身份,进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用世俗的故事讲述人的形而上的价值追求。老詹的故事从表层看是信仰坚守与迷失的故事,根上是中西方对信仰的不同阐释,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是“到哪儿去”,中国人无法理解天主教的原罪意识,中国人是道德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崇信的是“士为知己者死”。上帝是普度众生的,知己是针对个体的,渴望回报的。找朋友本质上是找自己,通过朋友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老曾说他“跟主没有一袋烟的交情”,大家隔着行,所以“跟木匠的儿子(耶稣)说不着”。在《白鹿原》中,祠堂和乡约是人与世界的中介,个体通过家族与社会和他人交流,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个体通过言语与社会和他人交流,“说得着”大约就是人与人交流完美的境界,即诗的境界。
言语成为引车卖浆者流的存在方式,根源就在于孤独,这种孤独感源自于他们的“无根”感。在农耕社会,土地、故乡、祖先、姓氏就是人的根。延津是刘震云生活和文学中的故乡,位于河南省东北部,晋冀鲁豫交界处,是客观实在,这也是文本被划入乡土叙事的重要原因。延津对曹青娥来说只是一个镜像——一个模糊的影像,是故乡、家园和童年的象征,并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延津在刘震云笔下经历了一个意象化的过程,在《手机》中,延津是严守一的心灵故乡和精神家园,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延津和吴摩西(象征着改心的根和灵魂归宿)在老曹老婆和改心的吵声中具象化为“改心的伤疤和短处。”所以改心说她其实“挺恨延津的。”改心这种复杂的情感体验类似于《围城》中方鸿渐对婚姻的感悟。延津在杨百顺、曹青娥、牛爱国三代人的言说中最终完成了意义体系的建构。
在文本中,延津是出走与回归的原点,有具体的街道、人事,是实体;又是杨百顺、曹青娥、牛爱国等走不出的心结或“心狱”,“延津”与钱钟书笔下的“围城”一样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意象或文化寓言,就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镇,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一样,是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蕴藉的审美意象。读者和评论者之所以纠结于“故乡”和“乡土”叙事,是因为刘震云之前的“故乡”系列小说都是以“延津”为原型展开叙事的,“延津”在刘震云的反复“言说”中早已虚化,升华为一个象征、一种意象,片面地以昆德拉关于小说“连续性”的理论解读《一句顶一万句》,恰好陷入了刘震云的“叙事圈套”。刘震云在文本中制造了一系列的叙事圈套,最具有迷惑性的一是“延津”,二是文本的标题“一句顶一万句”。从文革走来的中国人对“一句顶一万句”实在是太熟悉了,这是林彪的名言,是一段历史的记忆。那顶一万句的话,引来不少读者和论者的探究,杨百顺为了找话走出延津,牛爱国为了找话“回到”延津。是老高当初说给吴香香那句,或者是曹青娥临死前没说出的那句,或者是罗长礼(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要罗安国捎给养女巧玲那句,亦或是章楚红约牛爱国私奔时说“到时跟你说”的那句,还是罗安国的遗孀何玉芬跟牛爱国说的“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还是牛爱国顿悟后要去寻找章楚红要跟她说的那句话?在文本中寻找这句话的吴摩西、牛爱国和读者一样陷入了作者的叙事圈套,找话成为主体寻找自我的方式,成为主体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主体得到朋友的认可,就意味着得到了社会和历史的认可。老詹坚信主是万能的,杨百顺、牛爱国坚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话,这种念想成为个体生存和民族繁衍生息的强大动力和支撑。那“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成为人的“故乡”或精神家园。
二、从阿Q到牛爱国,言语构建起来的悲剧人生
阿Q对土地和姓氏都有一种天然的迷恋,他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土地最终、最直接的联系就是土谷祠,土谷祠寄托了他对土地的依恋。杨百顺们与阿Q们的区别是,他们根本没有土地,他们是手艺人,祖祖辈辈都是,他们不是不愿意种地,而是“从根上”说起就无地可种。对吴摩西来说,种菜和剃头、杀猪、劈竹子、蒸馒头一样都是事由,是谋生的手段。
阿Q的人生和悲剧是言语构建起来的,姓赵是他自己说的,没有族谱为证;“革命啦”、“造反了”也是他自己说的,谁也没看见;在城里见了世面、做了贼还是他自己说的;他的精神胜利法也是通过言语来表现的。祖先的历史是阿Q言说的历史,在《白鹿原》中白鹿两家的祖先供奉在祠堂里,阿Q的祖先挂在嘴上,他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儿子打老子”等。通过阿Q对自己的言说,他的身份也随之改变,由阿Q到老Q、Q哥,其身份与社会地位也随着称呼的改变而改变,他用“言语”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历史,阿Q就是自己的“上帝”,老詹说信了主,人就知道“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前两样,阿Q都是自己说的,“到哪儿去”却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他的悲剧命运最终是由他人的言语建构完成的,阿Q当然不是革命党,阿Q也没有造反,但他是被作为革命党枪毙的。阿Q的言语与未庄人和作者的言语共同完成了“阿Q正传”。
杨百顺之成为“喊丧”的罗长礼、老鲁在脑子里“走戏”、杨百利的“喷空”等与阿Q的白日梦具有同质性,阿Q骂人一般也只在肚子里骂,他的革命也是在土谷祠里做的白日梦。姓氏是一个人身份确定的根本要素,阿Q想姓赵,赵老太爷不许他姓赵,杨百顺则发现姓什么远没有生存本身重要,他由杨百顺成为杨摩西、吴摩西,最后为了自己心中最后的那点念想将自己命名为罗长礼;巧玲被拐卖成为改心,改心出嫁成为曹青娥,曹青娥的一生都在寻觅,找跟自己说得着的人,先是吴摩西,再是老曹、侯宝山,后来跟老曹说不着了,跟吵了一辈子的娘说得着,跟牛爱国说得着,跟百慧说得着,但牛爱国从不与娘说心里话。曹青娥像猴子一样丢了吴摩西,丢了侯宝山,却始终没能找到自己;牛爱国找话给庞丽娜说,她觉得恶心,给她洗衣服、擦皮鞋、做鱼吃,“没了自己”,却没能换到“回心转意”,庞丽娜说:“本来就没有心和意,哪儿来的回和转?”这句话说到了两人关系的实质,即“根”。
很多论者解读文本时,总是走不出男性中心的观念,忽略或有意悬置女性的孤独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和精神追求,《一句顶一万句》看似以男性为中心展开叙述,其实“根”却在女人身上,作者反复引用的一句话就是“这件事从根上就错了”,文本从根上就是女人的事,杨百顺的漂泊从根上说不是他的自主选择,源头在于吴香香的精神诉求——要一个说得着的男人,“娶”吴摩西之前,吴香香就与银匠老高“说得着”,为了方便两人“偷情”,吴香香鼓励姜虎去山西贩葱,才有了姜虎的暴死和吴摩西的出现,还是为了方便两人“偷情”,吴香香鼓励吴摩西去山西贩葱。因假找吴香香丢了巧玲彻底改变了吴摩西和巧玲的命运,吴摩西成为罗长礼,罗长礼的孙子罗安国回延津找巧玲,却没有回杨家庄(时空上杨百顺的根),因为罗长礼没有“话”带给杨家庄的人,在杨百顺那里,生命的根具象化为一句话,一个说得着的人,而不是宗族或种姓,这是对中国传统宗法制的颠覆,而杨百顺、曹青娥、牛爱国所代表的是一个社会阶层,是一群人,这群人独特的精神存在预示着中国宗法制度“从根上起”就不是“铁板一块”,杨百顺、曹青娥的后代牛爱国的身份却又相对确定,牛家的历史是绵长而清晰的。牛爱国的出走与漂泊从根上说是因为庞丽娜的背叛,庞丽娜跟牛爱国说不着,却跟小蒋和姐夫说得着,牛爱国找庞丽娜是“假找”,找话(朋友)却是“真找”,牛爱国找到了说得着的章楚红,最终却闪了她,牛爱国不离婚是因为他离不起,他有牵绊——母亲曹青娥和女儿百慧,三代人构成了牛家的历史,血缘和精神需求(话)相互制衡,于是,人在痛苦中总是有希望。文本绕了一圈又绕回了原点——女人,基督教中,亚当就是受了夏娃的诱惑偷食禁果的,女人是人类历史、灾难和痛苦的根,于是,杨百顺和牛爱国的孤独和痛苦就具有了普适性,不再是个体的命运,而具有了群体性和人类性。
杨百顺的命运因言语而改变,向往“喊丧”而不愿卖豆腐,与巧玲说得着而重新回到吴香香家,临终还惦记带话给巧玲,他一生的漂泊就是为寻找说得着的巧玲。牛爱国与庞丽娜说不着,就四处寻找说得着的朋友,后来找到了说得着的章楚红,却因亲情的羁绊闪了她,从而陷入更深的孤独,并最终在痛苦中顿悟开始新的寻找。
三、言语观照下的性道德
文本的外在结构是吴摩西和牛爱国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俩寻找跟人私奔的老婆,内在结构是找朋友或找话,深层结构是找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探寻人与人之间理想的关系模式或交往伦理。刘震云在性泛滥的时代,关怀着人肉体之外的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他敏锐地意识到两性之间的和谐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的、心灵上的和谐与满足,用文本中的话说就是“说得着”,做爱是两性交融的重要方式,但说话同样重要,吴香香、庞丽娜、章楚红三对做爱之后几乎都说相同的话——“咱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在作者看来,说话才是两性交往中最重要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作者没有试图去解决偷情的问题,也没有丝毫的企图给他们道德的评判,他只是把人的内心世界和深层意识剖开,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种“不介入”有明显的新写实小说的痕迹。读完《一句顶一万句》,我们对性问题的解决越发迷茫、混沌了,对吴香香、庞丽娜、章楚红等,我们很难做出道德的评判,反倒被她们的真诚、执着、无畏所感动。通篇作者没有用爱情这个词,在性吸引、性和谐之外,他们还彼此说得着,这种状态或“行状”是否爱情?这难道不是完美的两性关系模式吗?但问题在于他们总是在不合适的时间相遇,与现行社会规范与伦理相悖。于是,他们出走、寻觅,永无止境,所以,他们寻找的与其说是话,不如说是一种新的、更加合乎人性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模式,或者说一种社会形态,徐志摩曾说他的人生理想是能与一个身心俱美的女子自由结合,他处的时代显然无法实现,牛爱国的时代也没能实现。于是,人类陷入了“寻找”(找人和找话)的宿命和轮回。人,永远都在找的路上,所以人是永恒孤独的存在。杨百顺与牛爱国超越血缘的存在,使孤独不再仅属于一个家族,如《百年孤独》和《白鹿原》那样,而成为整个民族或人类的本质和宿命。
吴摩西假找跟自己有夫妻关系的吴香香,却真找养女巧玲,曹青娥最惦记的爹是跟自己说得着的吴摩西,很少想起亲娘吴香香,牛爱国到延津找姜家是为了找吴摩西,找话,而不是为母亲曹青娥寻根问祖,在吴摩西、巧玲和牛爱国的潜意识里,血缘远没有话重要。这种寻找模式表现了作者内心的孤独,及其对人际关系的迷茫、困惑与探索。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关系”。言语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生命个体真实的生理、意识和情感活动,它具有真实的物质或精神对象,拥有或强或弱的动机或动力,追求或隐或显的价值和目的,它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找话不仅是人的生理需要,而且是人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吴香香、庞丽娜、章楚红们在与情人完事后都“说话”,说话是他们心灵和感情交流的方式,在说的过程中,他们实现了自我价值的确认,超越了两性间纯粹的肉体需要,与《废都》中的“两性相悦”及《红高粱》中的原始激情相比,这种两性关系模式更高级、更合理、更人性化,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感。在探寻人类自我救赎途径的道路上,刘震云的探索是积极而有效的,我们期待他走得更远。
注 释
①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干叙事新面向》,《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②刘震云、孙聿为:《与记者的对话》,《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9年第3期。
③鲁枢元:《言语活动的空间——兼谈修辞学与人类生态观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④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回延津记》,《人民文学》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