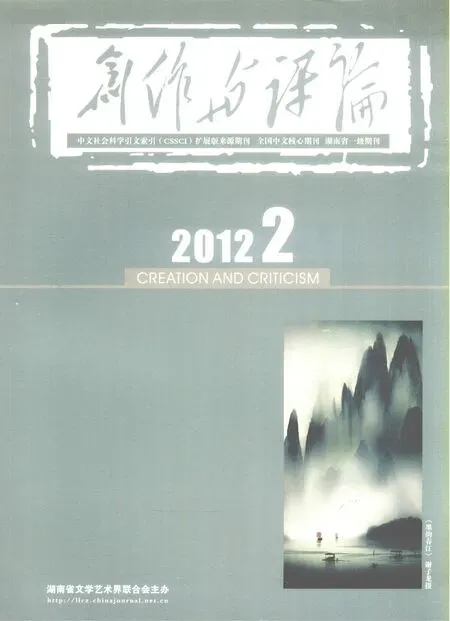一生的河流
■ 黎梦龙
大河向北
我一生未离开过河流,但我从不关注河流的方向。
从西洞庭到东洞庭,这条百里大河纵贯我的故乡。
儿时,我到码头边乘船,先要有小木船递送,穿过洪水泱泱的杨树防浪林,才能登上喘着粗气的慢班船。顺流而下,我不知道它的流向,也不知道它的远方还有多远。
它叫赤磊河,在我成长的版图上,一路向北。
多少次漫步河堤,望河中终年不停的各种船舶,大大咧咧来往,望两岸长堤上的行人、堤坡上的牛羊,都如同老树干上的嫩芽。
因为亲近,我觉得它窄了、细了、静了,甚至于躺在河坡的草地上,感觉大河如同身体中的一脉血管。
人到中年,大河忽地又从我心中复苏:半生的坎坷,无非大河清浪之几行!
在这个壮丽的黄昏,河的上方金鳞闪闪,河堤下是辽阔的平原和村庄。我默立于河岸的水泥码头上,风从河那边吹过来,有点青草、炊烟、米饭的香味。我知道河那边还是平原和村庄。
如果波浪只是河流的心情,不需要倾听,止住一念就能感受河流的深广——在古老的洞庭大水系,哪怕是一截哑河,都是水的精灵,向北,然后改道归于东海!
仅仅是一河之隔,有多少东西从不过河!
这时,我仿佛听到了儿时宏阔的涛声——大河依然向北,我的逝水,在河上方!
资江口
江水千里迢迢,穿过湘西南莽莽大山,穿过湘中漠漠平原丘陵,一路赶到洞庭湖边。
一闻到湖的呼吸,江水就静了,一层层清波列队走进湖口。
迎接她们的是滩头茂密的青草,以及几株残留的杨树桩。
那个老渔夫也走了,摇走一叶窄窄的乌篷船,拖走一挂黑黑的旧网,就像扯去了江口的一块补丁。
远远的江堤上,青青草丛间,矗着一块石碑,石碑中央刻着几个猩红的字:资江口。
这是在提醒不相信的人:看啊,这静的水、深的草、堤脚凌乱的麻石,就是资江口!
一只白鹭从浮云与苇荡之间穿飞过来,谁说她不像一万年前的那一只?
她不一定落在资江口,但一定是来看望资江水!
运河长满水草
那个年代,挖一条运河,只需要一句口号。也许是一万个农民的汗水太咸,运河多年不怎么长水草。
河水清亮活泼,运粮的木船在纤谣的牵引下沉稳前行,浣衣姑娘的长辫柳条一样探入水中,牧鸭人的竹竿,指挥一个大合唱团……
三十年水路,四十年陆路。
当水井和车轮催生新的乡村时代,故乡的运河什么时候成了一条青青的草河:各种水草从两岸拥挤过来,长长的河道只露出零星的水面。
当河水不再需要走出故乡,水草们像当年开挖运河,齐唱一个“绿”字,浩浩荡荡将运河改版!
运河两岸是树林,是人家,是菜地。清晨,河边轻雾缭绕,我看到一个老者在提水浇地。他弯下腰去,草把他淹没;他直起身来,草把他托起。就像河水,涨退之间,都把水草暖在心口。
岸边还有不少坟地,亡者们年青时一定参加过开挖运河,现在他们都匿藏在草中,像水草一样与运河亲切交谈。
在洞庭水乡,所有水一样的光阴,可以行船,可以长草,都一样恬淡、素净!
午后的羊群
午后,河滩边的小树林里,一群羊在默默吃草。
夏草高出羊的头,小树高出草的头,风高出小树的头,蓝天高出风的头。
所以,羊的幸福还未一层层剥开。
然而,认真吃草的羊群已经完成了对幸福的咀嚼。它们偶尔抬起头,将嘴角的草香撒进小小的一阵风……
宁静的午后,一只羊忍不住咩了一声,只是清亮的一声,就像给时光拉了一下刹闸——那流动的阳光、暖风、草叶都停下来,欢喜谛听。
那样的快乐准是在心中停不住了,像不远处河叉内的红莲,在碧叶间轻轻一闪,就把浅水中的心事透露。
这时候,我们去亲近一群羊,心里不要有金属,手里也不要有花朵,否则,在一只被羊群惊起的蝴蝶看来,都是可笑的!
就变成一朵白云吧,站在羊群的上方,让羊群悲悯我们:喔!还有兄弟,尚在天空寻找青草!
一只白鹭飞起
一只白鹭飞起。
一大片阳光乱了,一大片湖风亮了,一大片水波重新起步。
一只白鹭或许太孤独,它带着原始的光明,在同一片水域飞起、落下,仿佛是一朵忧郁的浪花,让天空和湖水都心痛。
一只白鹭展开双翅,就像光焰忘情地一闪!
我们倾听湖面千年潋滟的行吟,那天的蓝、云的白、水的碧、草的青……是一只白鹭豁亮的音符!
一只白鹭飞起。
空间,好像被撕开了什么。
白鹭想打开一扇门,张开翅膀以后,它发现根本没有门。
它撕开的是胸膛、是天空、是湖水、是草滩,是亘古流动的恩泽。
一只白鹭仍将飞起。
冷冷的月、暖暖的星、失眠的风,梦中的水花,擦亮第一缕晨光,好像是白鹭温柔的翅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