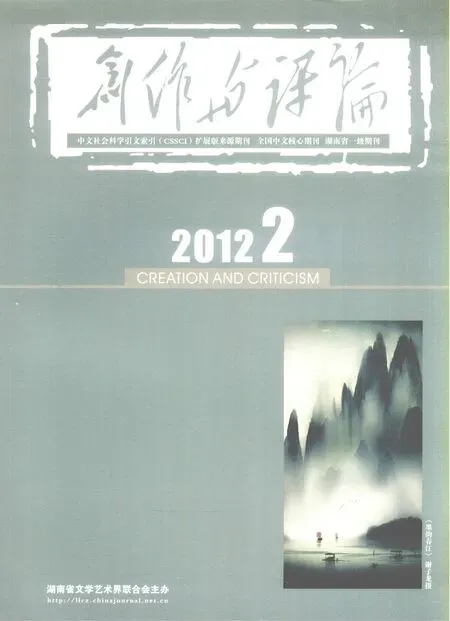煞 气(短篇小说)
■ 小牛
满成是小鬼里的头。所以他敢吓唬大人,下次到你家来!
大人就怕了,脸上发白。
也有恼的,追着要揍他,骂,你个屁眼嘴!满成跑得狗一样快,一个劲叫,就到你家来就到你家来!大人再追不得,瞪着眼喘气,越追越会“到你家来”。
到谁家来都不是好事。脸上涂着锅灰,头上戴个马粪纸做的尖尖角,衣服反穿,举一柄竹片削成的剑,率一帮小鬼吆喝喧天冲进你家,你家就一定是进了邪气,有野鬼藏着了。
当然,真是进了邪气的人家,又巴望他去。床上有病人哼哼,栏里的猪发瘟,要不就是丢了钱财,损了地里收成,总而言之家里倒了运,就都希望他把藏在家里的野鬼捉了去,让邪气消散,运气转过来。
这种时候满成最神气,冲到人家门口,高举竹剑大喝,野鬼野鬼快出来,阎王要你下火海!然后朝身后的喽罗们一挥剑,搜!喽罗们便噢噢叫着冲进屋去,用手里的竹刀木枪在门上壁上拍得噼噼啪啪响。其实也不用搜,那野鬼早在茅房边立着。当然是稻草扎的,套上破衣烂衫,用一根棍子插在地上。待小鬼们装模作样在院里屋里四处搜一通之后,满成才直奔茅房,嗨一声将野鬼捉住,高高举起。小鬼们立即跑过来,拥着他乱喊,欢呼胜利。
这家人高兴了,拎过篮子来,将枣啦桃啦花生啦炒米糕啦,一个劲往小鬼们的衣兜里装。满成衣兜里装得最多。
满成自然很喜欢捉野鬼的了,但这种机会并不常常有,要等村里请了戏班子,而村里只在过年的时候、割了禾的时候,或者有钱人家办红白喜事的时候,才把戏班子请了来。那戏班子无论演一天两天三天,也无论演《铡美案》、《苏三起解》,还是《白蛇传》、《七仙姑下凡》,总要在头天演一出打叉戏,戏名叫《刘氏四娘》。刘氏四娘究竟是个什么人,满成弄不清楚。反正是个男人扮的假女人,好像是阎王身边逃出来的冤魂。冤魂肚子饿了,在路上偷人家的鸡煮了吃,鸡骨头乱扔,叫追她的巡夜大鬼嗅着了气味。这巡夜大鬼很厉害,说,鸡骨头香一定把野鬼全逗出来了。于是喝一声,小鬼们,快快搜捕野鬼!早在台后等不及的小鬼们噢一声冲上台来,围在大鬼身边,大鬼背上插几柄叉,手里还握一柄。他将手里的叉在头上舞一圈,站个金鸡独立,右手高举叉,左手伸两个指头指着台下,拖着腔调,速去也!小鬼头满成就一声得令!率众小鬼跳下台去。
捉野鬼有一衣兜的吃食,又能台上台下的威风,自然很带劲。那演技也不费劲。除了满成一声得令,要按戏班子叮嘱喊出戏腔来,其余小鬼们就由着性子乱喝乱吆了。
因此盼着捉野鬼的就不只满成一个,所有的男孩都在盼了。
其实胆大的女孩也盼。但满成不收女孩,说女孩跑不快,力气小,还说女孩爱笑,把野鬼笑跑了,因此连女孩追了屁股后头看热闹他也不准。
只有一个女孩例外。花子。
花子比满成小一岁半,刚满九岁。花子不爱嘻嘻嘻地乱笑,实在要笑了,就抿紧嘴,将一双乌亮的眼睛飞快眨个不停。就连满成搔她胳肢窝搔得她浑身乱颤,她也是抿紧嘴将一双乌亮亮的眼睛飞快眨个不停,顶多鼻子里头哼哼哼的。满成就佩服她得很。满成要被谁搔胳肢窝了,一定在地上滚个昏天黑地。
当然满成让花子跟在屁股后头捉野鬼,也不仅因为这一点点佩服,实在是玩得太好了。已经记不得几岁起开始玩一块的,反正是有满成的地方就有花子,有花子的地方就有满成。
而且满成认了花子的爹做干爹。
于是每一次捉野鬼,都有花子跟在满成屁股后头跑,跑得脑后那根小辫一跳一跳,却总不叫不笑。只有满成捉住野鬼了,小鬼们都胜利地嚷一通,她才拍着手跟着嚷。等到人家来往衣兜里塞吃食,又赶快抿住嘴,手按住衣兜,一个劲摇头不要,那是奖赏小鬼的,她不是小鬼,不好意思。
满成就在这时候大叫,她不要,装我兜里来!人家就真的把花子那一份也装进满成衣兜里去,还逗一句,把你堂客的一块兜了呵。
满成不在乎。堂客就堂客。反正在坡上也常常玩拜堂的。
每次捉了野鬼,找空地烧了后,就要去坡上玩了。
不去坡上玩不行。那打叉戏接下来的场面小孩子看不得,凶险得很。刘氏四娘被巡夜大鬼追着,无路可逃,先是往台左的木柱上一扑,再往台右的木柱上一扑。巡夜大鬼一见刘氏四娘扑上木柱,扬手将一柄叉掷去,嘭地一声贴着刘氏四娘的脸叉在木柱上。那叉是雪亮亮的三齿钢叉,连柄二尺半长,真家伙哩,所以叉一飞出台下就惊呼连片,这惊呀连坡上也听得到。
花子一听这惊呼就要打哆嗦,她不明白,小孩子看不得的凶险戏,为什么大人还要吓得叫喊连天地看?
满成也不明白。要看就不要吓得叫,吓得叫就不要看。他想,他要是去看就不会吓得叫。
因此他很想去看,但大人们太可恼,戏围子门口把守着,那戏围子其实并不牢实,是戏班子带来的白家织布围幛,一个大人高,虽然用木桩子绷紧了,贴地钻进去不费劲的。只是从没哪个孩子敢钻。钻进去就会臭揍一顿。
为了不臭揍一顿就只好在坡上玩。何况还有一衣兜里的吃食。
大家就把兜里的吃食都掏出来,比谁的多。当然都不敢跟满成比。满成一脸的得意,把吃食分出一半来给花子。花子这下就好意思了,全装进兜里,零零碎碎地吃。
也常常把吃食都堆拢来,不准随便动。那是玩接堂客的时候,等接回堂客,新郎新娘拜了堂,大家上席了,才能吃。
接堂客是最有味的。新郎新娘照例归满成和花子,四个轿夫手搭手做一顶轿子,让新娘坐上去。吹鼓手们走在前面,嘴巴顶了唢呐锣鼓,一路悠悠摇摇热热闹闹。新郎“屋门口”则候了一群放鞭炮的。轿子一到,噼哩啪啦拼着嘴巴响。新郎就赶紧跑到轿子边,撩开帘子请新娘下轿。新娘这时候要羞羞答答,最好还在轿子上忸忸怩怩一阵。轿夫的手腕酸了,还得忍着。村里接亲他们都见了,新娘子是该在轿子里磨蹭一阵的。
但有时花子也磨蹭太久了,指着满成的脸说,哪有新郎一脸锅灰的!又不是做了爹,让别人往你脸上打喜。
吹鼓手们也起哄,是的是的,丑八怪,不嫁他。
满成只好撩起衣襟使劲擦,还沾着口水擦。
那锅灰擦不彻底,花子就继续赖在轿上。
轿夫们苦了,嚷起来,行咧行咧,戏台上包公也是黑脸咧。
满成神气了,嫁个包公还不肯?不下轿不要你了!
花子撅撅嘴巴,只好下轿来。将手绢当红绸带,让满成牵着一步一步进“屋”去。贺喜的客人就陆陆续续地来,都是刚才抬轿子吹唢呐敲锣打鼓放鞭炮的。这时候全换了神态,捋胡须的端水烟壶的弯着腿的弓着背的,把村里大人们摹得俨像。
然后就拜堂,就上席,大吃大喝,笑笑闹闹。
花子说,不让我们看打叉戏更好,这坡上几多快活。
孩子们就附和,就是,就是,还吓死人哩。
满成扬起眉头,说,吓死人?我爹还看见叉死人哩!一叉叉到脖子上。用手做成叉往脖子上一叉。
所有的孩子都将脖子一缩,眼睛瞪得老大。
满成仍然伸着脖子,很神气。
叉死人是真的。不过在很多年前了,也不在这个村子里。那时候满成的爹刚长成小伙子。刚长成小伙子尤其爱看打叉戏。就赶到七里外的地方去看,就赶上叉死人的场面了。那刘氏四娘刚扑上柱子,锣鼓响起一串急点:扑噜……擦!—道白光闪过去,那叉中目标的声音就有点不对,闷闷的。刘氏四娘死死抱着柱子,身子扭动起来。台下这时候本是要放鞭炮的,香火都举起了。细细一看,不得了,刘氏四娘脖子上涌出一股股殷红的血来,还有痰水泡沫。那叉将刘氏四娘的脖子钉在了柱子上哩。
满成爹尽管已经长成小伙子,回来后还是吃不下饭。就绘声绘色地给别人讲,讲得所有的人都瞪大眼睛嘴里啧啧啧啧,除了恐惧还有遗憾,自己没看到那场面。
那场面是不能经常看到的,戏班子不会把自己的命不当命。打叉的大鬼、刘氏四娘、打鼓师傅三个人,都晓得要严丝合缝地配合。满成爹看到的那场面,据说是打鼓师傅因为上茅房踩了一脚屎在懊恼,鼓点乱了一下。
后来是再没听说有叉死人的场面了。当然残了耳朵伤了脸颊甚至脖子上断了一根筋的事,常常还有。即使没有,当那雪亮亮的叉照人狠狠飞去也够吓人的。所以台下的右边角落里仍然摆着棺材。
这是演打叉戏的规矩,从来没变过的。棺材由点戏的东道家置备。台上死了人,棺材便是死者的厚殓。台上没死人,这棺材就由戏班子退给东道家,东道家按棺材价付给戏班子酬金。
虽然没看到吓人的把戏,满成和所有的小鬼都看到了台下右边角落里那口黑漆漆的棺材。棺材头上淋着鸡公血,卧在地上阴森森的,逼得人透不过气,台上台下窜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不敢往棺材上溜。
不过,棺材被村里大人们抬回来的时候,满成和所有扮小鬼的孩子又全都是兴奋的,晓得戏班子要来了,又要捉野鬼了。
然而好久都没有兴奋了,民国三十七年的漫长夏天是这样平静,平静得没有一点请戏班子的理由。孩子们都有点乏味了。于是在坡上玩也有点乏味。花子说,老坐轿老坐轿,不想坐了。
满成搔搔光溜溜的头,说,那就骑马好不?
轿夫们赞同,骑马骑马,新娘子也该骑马的!
花子扭扭身子,也不想当新娘子了。
满成说,那就当堂客吧,堂客骑马回娘家。
花子仍然扭身子,也不想当堂客。
满成不停地搔着光头,那你当个什么嘛?
花子眨巴眨巴眼,突然说,当刘氏四娘。刘氏四娘骑马跑,巡夜大鬼就追不上了。
孩子们一片赞同,来了兴致。
满成就作马。弓着背,双手在腰后十指交叉做成“蹬子”,让花子屈腿伏在背上,双膝压在“蹬子”上,然后伸着脖子昂起脑壳,“咴咴咴咴”,一声长嘶,跑起来。
花子兴奋得很,左手抓牢满成左肩,右手在满成右肩拍着,唱,马儿马儿快快跑,巡夜大鬼追不到!
满成就更加“咴咴咴咴”嘶叫得有劲。
孩子们一片哄叫,快跑呀,快跑呀,巡夜大鬼追来啦!
有谁捡一根长长的细树枝掷过来,叫,飞你一叉!
树枝从花子身旁飞过去,把花子吓慌了,身子一晃,花子就摔在了地上。
满成赶紧去扶。花子咧开了嘴巴,左臂动弹不得,大声叫痛。
孩子们都围上来,吓懵了。
这祸闯得大,花子左臂脱了臼。
满成被爹爹结结实实揍一顿,第二天又跟着爹去花子家赔礼。
满成爹捉了一只大母鸡,提了一块肉。让满成挽一篮鸡蛋。
花子爹举起铜水烟壶,这是做什么?孩子嘛,孩子嘛!东西还是收下了,连连摇头。
花子躺在堂屋里的竹凉板上,左臂被杉树皮裹着。痛是不痛了,乌亮亮的眼睛瞅着满成飞快地眨个不停,嘴紧紧抿着。满成也低着头,偷偷向她笑。
满成爹就照满成头上拍一掌,崽子,还笑!不给干爹赔个罪!
花子爹伸出一只手,在满成光溜溜脑壳上摸着,孩子嘛,孩子嘛。又抓起桌上的炒米糕给满成吃。
满成接了,却不敢吃。
花子躺在竹凉板上说,吃呀吃呀,孩子嘛,孩子嘛。
大人们都笑起来,接着,大人就谈大人的事了。
满成低头吃炒米糕,偷偷朝花子扮鬼脸。他不愿听大人的事。只知道说的是今年地里旺,该谢天老爷。
但马上支起耳朵了。大人在说,村里所有佃户和田主都凑份了,开镰前请戏班子来演一天戏,谢天老爷。
满成爹问,还点《刘氏四娘》么?
花子爹端着铜水烟壶,一边咕噜咕噜地吸烟,一边点点头,当然哪。
满成朝花子眨眨眼。
花子也朝满成眨眨眼。
戏班子来了。
孩子们兴奋得很。马粪纸做的尖尖角,竹刀木枪,都备好了。
好些人家也忙着扎野鬼。都因为家里有不顺畅的事。
就有一个个大人对满成说,先上我家去啊,我给你好多吃的。
满成都应下来,扬着脸,先去谁家,谁家的运就转得快些哩。
满成特意新做了一柄长长的竹剑。还从河里捡块卵石将剑打磨得光光的,差不多跟真的一样。
但事情出了点变故。
戏班子的本家(即头儿)跟满成的爹说,打叉戏怕是演不成了,扮大鬼的花脸发了病,手老打颤。
满成的爹急了。那如何好?他搓着手。想看的就是这一出哪!
本家说,所以我也想硬撑着演,就怕出岔子啊,拿命耍哩。
满成的爹不吭声了。他脑子里泛上那个冒着鲜血和痰水泡沫的脖子。
我得跟庚二爷去说说,是庚二爷让我去请你们的。满成的爹说。他急急找到花子的爹。
花子的爹端着铜水烟壶,咕噜咕噜一气,才说,请大家来议议吧。
村里参加主事的人就都来了,聚在花子家里,水烟壶、长烟锅、短烟锅……花子家堂屋里烟雾腾腾。
满成就蹲在堂屋门外山壁下,花子紧挨他,弯腰站着。她左臂上还裹着杉树皮,用一块长汗巾吊在脖子上。两个人偷偷听大人们议,眼睛瞪得老大。
大人们七嘴八舌,都主张打叉戏要演。
满成的爹却还在犹豫,说怕出岔子,他是亲眼见到岔死人的。于是他把叉死人的情形又绘声绘色说了一遍,说得堂屋里全是啧啧声。
满成也听得头皮发麻。他扭头看花子,花子已经紧紧闭上了眼。他皱了眉,有点讨厌爹。
花子的爹说话了,还是演吧。他说得很慢,还伴着咕噜咕噜声音。棺材头上多淋点鸡公血压煞,杀两只鸡公啰。
大家都赞成。
满成眼里又亮了,他又轻轻捅了捅花子,花子也睁开了眼,朝他扬起眉。
演打叉戏了。
满成握着长长的新剑,浑身劲鼓鼓的。
戏台上早已等满了大人,挤挤涌涌。
巡夜大鬼朝满成发令,速去也!满成一声得令,率众喽罗哇哇叫着跳下了戏台。
满成!满成!挤挤涌涌的大人们一片声叫,急切得很。都是家里扎了野鬼的。
满成没长耳朵。他从人群里挤出来,飞快跑了。小鬼们哇哇吼着紧紧追随着他。
一直跑到花子家。
花子早候在门口。左臂仍然吊在胸前,满成刚站定,她跑过来,嘴巴凑在满成耳朵边,我照你说的,让娘扎了个好大的野鬼咧。
满成急不可耐。捉了野鬼,花子手臂就好得快了。他高举长剑吆喝一通,待喽罗们刚涌进屋,他就挥着长剑冲进去了。
果然好大一个野鬼呆在茅房边,比满成还高出一头。
满成将剑别在裤腰带上,双手抓牢野鬼脚下的棍子,嗨一声拔出地来,将野鬼高高举起。
众小鬼涌过来了,挥着竹刀木枪欢呼。花子也跑来了,挥着右臂跟着欢呼。
花子娘赶紧提来一个篮子,将喷香的炒米糕往小鬼们衣兜里装。
自然还是满成兜里装得多。花子却觉得不够多,用右手又抓了几块塞进他兜里。
满成威风凛凛喝一声,将野鬼推下火海!扛着野鬼率喽罗们奔出门去。
花子追到门口,眼巴巴望着他们。她手臂没好妥。爹不准她出去玩的。
烧过野鬼了,满成领着喽罗们又去坡上玩。花子不在,当然不能接堂客了。满成就有点兴致不高,盯着坡下远远的戏围子出神。
那戏围子里人满满的,坡上能看到一片黑黑的脑壳,戏台上的戏却看不到,戏台背向着坡上。
日头快落山了,阳光有点发红。那绷成围幛的白家织布也跟着发红。
有惊呼声从戏围子里响起,在发红的阳光里抖抖颤颤地飘到坡上来。
喽罗们嚷嚷着,又吓得叫了!又吓得叫了!
满成在肚里说,吓得叫就不要看,要看就不要吓得叫。又在肚里说,我要去看就不会吓得叫。
于是就真的想去看,越想越坐不住。终于,他跳起来,扔了长剑,飞快向坡下跑去,把喽罗们的惊愕全抛在坡上。
满城一口气跑到戏台上右边的围子下。戏台下的右边摆着棺材。钻过围子躲在棺材后头,兴许大人不会发现呢。
台上锣鼓正响得激烈,戏围子里一片惊呼接着一片惊呼。满成心咚咚跳起来。他想,我要告诉花子,我看了打叉戏了,一声都没叫咧。
他就趴在地上,掀开围子钻了进去。
棺材正好挡住他。满成高兴了,爬到棺材边,双手支起脑壳望着台上。
刘氏四娘正呼地一声朝台右的木柱扑过来。那样子就像朝满成扑过来。满成一个激灵,绷紧了头皮,又瞪着眼珠一动不动。
巡夜大鬼举起了叉。
满成的心呼地蹿到喉咙边。仍然瞪着眼珠一动不动。
扑噜……擦!锣鼓点子急得很。
一道白光。
满成打个哆嗦,紧紧闭上了眼。
只听得一声惨叫。
满场哗乱。
满成怎么也没想到,那叉叉着他爹了。
正是爹弓着腰向棺材跑过来的时候,——他是不是发现满成了?那雪亮的叉嗖地叉进他后颈窝里。
谁也弄不清楚,那叉怎么偏过木柱,飞向台下了呢?扮巡夜大鬼的戏子说,举叉的时候心里突然一阵慌,手颤得厉害,想着要出事,要收手也收不住了。
村里找戏班子论理。本家说,早说过演不得,你们偏要演呀,而且,人要跑到棺材那里去做什么呢,棺材煞气好重!
理没论上,不过,戏班子没要那棺材的酬金了,棺材就给了满成的爹。
出殡的时候,戏班子也吹吹打打地送。满成的娘由几个女人架着,哭得昏天黑地。
满成没哭。他披麻戴孝,手拄哭丧棒。一双眼呆呆地睁着,脑子里空洞洞的。花子爹在一旁陪着他,手里端着铜水烟壶,却一口没抽。
又过年了。村里的又要请戏班子了。
满成的娘对满成说,我家也扎个野鬼吧。她嗓子还哑着。自从为满成的爹哭哑了嗓子,就一直哑着了。
满成咬咬嘴,大声说,扎个野鬼!扎个野鬼!
满成就和娘一块扎。扎了个老大的,比花子家的野鬼还高半个头。套上满成爹一件旧衣衫,脸是满成用一张草纸画的,三只眼,长獠牙,很凶气。
只等着小鬼来捉了。
演戏那天好大的雪。整个天空麻麻点点。却没有一丝风,因此并不觉得太冷。何况有戏看就更不冷了。大人们大都披着蓑衣顶着斗笠去看戏,有钱人家便撑一把油纸伞。实在有耐不住冷的老人,就抱—个装了火红柴炭的烘笼。气氛是热闹得很了。
满成倚着门框,望着门外的雪,等着从那雪地里冲出一支队伍来。
今天谁当小鬼头呢?娘能不能把他们最先喊到自己家来呢?满成想。
又点点头。肯定会的。于是又扭头看桌上的篮子,那是娘炒的一篮花生。
远远的锣鼓传过来,热热烈烈,震得满天雪花乱颤。
满成脸上渐渐地有了迷茫。怎么有这么久的锣鼓?早该冲出来捉野鬼了啊。
一个人影出现了,在纷乱的雪花里慢慢走来。
那是娘。满成一眼认出。
娘缓缓走近了,一脚一脚十分吃力。
满成垂下了脑壳。
娘连头上身上的雪花抖也不抖就走进屋,坐在凳上,一声不吭。
满成问,娘,不肯先来我家了?
娘叹一口气,嗓子哽咽了,没有小鬼,一个也没有。
满成怔住了,大睁着眼。
家里都不准自己的孩子当小鬼了。说是,小鬼当多了沾上煞气,娘沉沉地勾着头。
满成张大了嘴。一会儿,也勾下了头。
好一阵,娘慢慢起身,走到满成身边,拉着满成的头,说,我们自己去把野鬼拆了吧。
满成点点头。跟着娘往屋后走。
门外突然响起个声音,野鬼野鬼快出来,阎王要你下火海!喉咙是使劲鼓着的,却藏不住嫩声嫩气。
满成转身奔到门口。
门外站着个小鬼头,戴一张马粪纸做的尖尖角,脸上用锅灰和米花红水画得乌七八糟;穿的是一件老长的青布衫,罩住膝盖,滑稽得很。
满成一眼认出,是花子。
花子气势壮壮,用竹剑向身后空空的雪地一挥,喝令,搜!然后一头冲进来,穿过堂屋,直奔茅房。
满成赶紧也跟着跑去。
花子跑到野鬼身边,将剑往地上一插,双手抓住野鬼脚下的竹棍,却拨不出来。她朝满成喊,快帮帮呀!
满成跑上去,抓住竹棍,嗨地一声,野鬼拔出来了。
噢!花子欢呼胜利,又接过野鬼摇摇晃晃举起头。
满成娘赶紧往花子衣兜里装花生。一把一把使劲装。
够了,够了!花子叫起来。然后又鼓起喉咙喝一声,将野鬼推下火海!扛着野鬼冲出了门。那样子全是学了满成的。
满成追着跑出去。追上花子,问,你怎么来了昵?
花子眨眨眼,说,我偷偷跑出来的。我爹不准我出门,说捉野鬼会沾煞气。还说,你当小鬼头沾了好重的煞气,你爹就是你害死的。花子停一停,声音低下去,我也有点怕,当这一回,就不当了。
满成久久瞪着眼,呆呆立着。突然,他脚一顿,抢过花子肩上的野鬼,扛着就跑。
花子叫起来,哎哎,你不能的!不能的!
满成发狂地跑,雪地里留一线歪歪扭扭的脚印。
他一口气跑到坡上,跑到爹的坟前。
爹的坟也全被雪盖住了,像个老大的雪馒头,在漫天大雪里默默耸着。
满成将野鬼摔到坟头上,掏出衣袋里的火镰子和纸引子,一边狠狠砸火,一边哭喊,爹,爹,我害死你了,我害死你了!
花子气咻咻赶来,掏出衣袋里一盒洋火要划,说,满成哥……你别烧……我是小鬼头呢……
满成重重甩开花子的手,不要你烧!不要你烧!你不是小鬼头!
花子裂裂嘴,眼里也漫上泪了。十分委屈。
满成仍然放声地哭,爹,爹,我再当一回小鬼头,给你烧野鬼了……
野鬼烧起来了,将满成一脸泪水映得红红的。
野鬼烧完了,满成也止了哭。他站起来,怔怔地望着坡下远远的戏围子。
热热烈烈的锣鼓声飘过来,夹着一阵一阵的惊呼。
花子挨着满成,怯怯地轻声叫,满成哥。
满成没应,眼珠子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