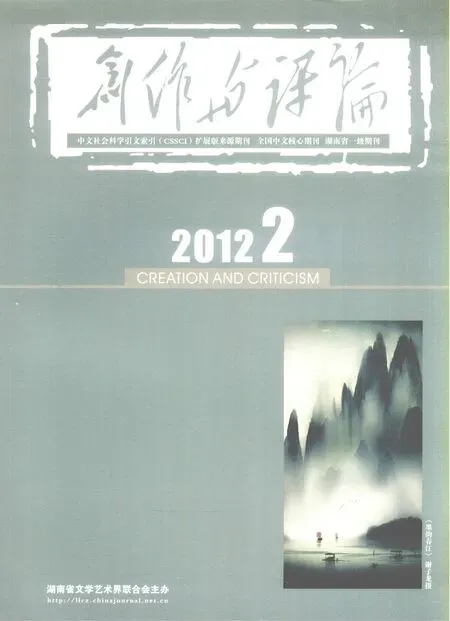从“奇观”到“日常”*——毕飞宇《推拿》底层叙事的意义
■ 明飞龙
问世于2008年并于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推拿》延续了毕飞宇一贯的写作风格,它以细腻绵密的细节描写、内敛饱满的叙事语调、灵动曼妙的艺术手法,在展现身处社会底层的盲人推拿师的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彰显出一种丰沛沉郁的审美内涵。而就其底层叙事来说,它有别于当下流行的那些以“苦难”为关键词的的底层叙事,它为底层文学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立场,对底层文学的发展来说,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
对“底层”的书写是文学史中常见的主题,因为文学离不开对苦难的关注。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底层写作思潮的兴起,那种“对一切有关底层平民生活模态的叙述”的“底层叙事”显得异常活跃,一大批表现底层民众生活和命运的作品呈现于文坛。这些作品有的是呈现底层人物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深陷苦难的生存状态,作者对生活矛盾不回避、不粉饰、不遮盖,把惨烈残酷乃至血腥的生存场景赤裸裸地揭示出来,比如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孙惠芬的《民工》、陈应松的《马嘶鸣血案》等。有的逼直地展现社会的不公及社会制度的不健全对底层人物带来的严重伤害,揭示出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大多是社会现实所致,比如曹征路的《那儿》、《豆选事件》、胡学文的《行走在路上的鱼》等。有的深入解剖人性的黑暗,呈现人性的劣根性对底层人物带来的灾难,呼唤一种健全人性的回归,比如刘庆邦的《神木》、《卧底》、《穿堂风》等。这些作品基本上是紧紧贴近时代的脉搏,把当下阶层化日益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严重不公等社会现实揭示出来,充满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对底层群体苦难生存状况的积极表达,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
但是,这些作品在充分展现底层人物生存困境的同时,在叙事艺术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有的论者指出:“底层文学书写出现了内容上的奇观化、主题上的欲望化、情节设置上的偶遇化模式。内容的奇观化主要体现为对猎奇感的追求,这一方面表现为对底层生活的陌生化领域和独特生活经验的挖掘,如荒山野岭、矿山矿难、民工生涯、风月生涯、国企破产、逼良为娼等边缘场所边缘人生成为通行的表现场域;另一方面则是在这些场域中发生事情的夸张化,具体表现为对苦难的猎奇和夸张转化为残酷与悲惨的比赛。”①这在底层文学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比如在《马嘶鸣血案》中,九财叔和“我”仅仅因为二十块钱的缘故而连杀七人,最后九财叔连“我”也不放过,而其中九财叔打架,被电枪击中,连杀七人的场景,被作者叙述得鲜血淋漓,惊心动魄,弥漫着血腥的暴力。比如在《奔跑的火光》中,农村妇女英芝忍辱负重,为的是过上幸福的生活,但生活的美梦却一次次被撕成碎片。丈夫毒打她、虐待她,婆婆轻贱她、刁难她,英芝不得不一次次逃避,一次次抗争,但都是枉然,最后在走投无路之际烧死丈夫,也毁掉了自己。这些过程也被作者展现得异常惨烈。比如在《家园何处》中,那位农村女孩在包工头的引诱下失身,继而又被包工头转给别人玩弄,久而久之,那女孩也就习惯了卖身生涯,对自己的堕落没有一点抗争的迹象。在底层文学中,类似的作品很多,它们缺乏坚实的叙事逻辑,不顾人物的内在挣扎与精神变迁,缺乏一种对底层现实困境的真切反映,沉浸于对人物性格的极端化描写,把残酷、苦难与堕落推向极致,给读者展现一种“奇观”,而不太体验底层人物的日常生活常态,“写‘男底层’便是杀人放火、暴力仇富,写‘女底层’便是卖身求荣、任人耍弄,不仅人物命运模式化,故事情节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一律大悲大苦,凄迷绝望,鲜有十分丰饶的精神质感。”②这是因为对底层人物那种极端化与绝对化的“奇观”式的生存状态的表现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它蕴含着先在的道德判断,作者不太需要进行深入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挖掘。而日常生活的呈现需要作者的想象力与理解力,需要对生活的肌理及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有扎实的推进,对人物内在精神需求进行精细摹写与展示,把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揭示出来,让生活自身呈现人物的命运,而不能仅凭故事的精巧与奇诡来推动小说的演进。正如有的论者指出:“在当前关于底层生活的小说中,大多作家关注的是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却鲜有见人对底层人的心灵世界进行深入挖掘与呈现。而关注人的心灵,正是作家独擅胜场、应该大显身手的地方,在这方面,我们的一些作家做得还很不够,他们仍只限于粗线条地勾勒,或者写作‘问题小说’,还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底层人的内心。”③在“苦难”成为底层叙事关键词的底层文学中,以日常生活为核心的底层叙事就有了别样的意义。毕飞宇的《推拿》呈现了这种意义。
二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给《推拿》的颁奖词中有“在日常人伦的基本状态中呈现人心风俗的经络”这样一句话,可以说很好地概括了小说的艺术特征之一,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讲述故事,在日常生活中呈现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境界。而对日常生活的描摹与展现,即在于对世态人情的深入洞察。毕飞宇曾说:“对小说而言,世态人情是极为重要的,即使它不是最重要的,起码也是最基础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是小说的底子……我觉得世态人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拐杖。这根拐杖未必是铝合金的、未必是什么高科技产品,它就是一根树枝。有时候,就是这个不起眼的树枝,决定了我们的行走……任何时候,小说只要离开了世态人情,必死无疑。”④缘于此,毕飞宇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同情眼光来打量那生活在现实边缘的底层人群——盲人推拿师,把重点放在“日常生活”而不是“底层苦难”上,家庭、股票、房子、恋爱、结婚、以及“沙宗琪推拿中心”里纠结缠绕的世态人情。通过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敏感、细腻、繁复而又独特的内心感受的叙述,让读者看到他们正常的人生,体会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助与无奈、痛苦与悲伤,同时也感受到他们的梦想与尊严、甜美与幸福,以及他们在黑暗世界中相濡以沫的情怀。毕飞宇呈现出了那个底层人群世界鲜为人知的曲折、隐秘与幽微,同时,我们还可以体会到作者那种最大程度地贴近盲人内心世界,尽力在黑暗世界中提炼光芒的努力。由此,尽管《推拿》给我们呈现一个陌生的世界,但我们不会对此产生一种“奇观”感,而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自然流露。
《推拿》没有底层叙事中那种常见的奇异跌宕的情节与强烈尖锐的矛盾冲突,作者对笔下的人物不是“哀其不幸”也不是“怒其不争”,只是以一种平和的理解与宽容,在缓慢的叙事节奏中把他们呈现在读者面前。毕飞宇采用一种屏风式的结构,让王大夫、沙复明、小马、都红、小孔、金嫣、徐泰来等一个个出场,在一个个人物的出场中,一幅“盲人推拿师群像图”也就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在展开过程中,毕飞宇又设置多种关系把相关人物勾连起来,最后在尾声中又把全部人物汇集在一起而收束全篇,小说结束了,“盲人推拿师群像图”也在我们脑海中清晰地立了起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活的形象,他们的形象都是在内在的生活逻辑中推演出来的,而不是象征符号的概括,更不是“奇观”的展示。我们可以看到主要人物王大夫是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对“家”充满着复杂的情绪,亲密又疏离,他在“对不起”父母的心态中长大,而作为补偿的弟弟,王大夫虽也嫉妒他,但却很快转化为对他的溺爱。弟弟结婚时不希望他回去参加婚礼,怕影响形象,他赌气汇款两万元,并决定与弟弟断绝关系。然当他带着女友回家后,便立即原谅了他。后来不成气的弟弟又欠下赌债,王大夫本想不管,但他最后还是决定替弟弟还债,并独自面对债主的威逼。但最后带钱回家看到弟弟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及债主那种冷静的逼压,他用菜刀自残以表达自己的愤怒以及心酸、痛苦与挣扎。此时,王大夫那种有情有义、宽容、血性、担当又不失匪气的形象便浮雕般地凸现出来。这种凸显没有发生在极端的环境中,也没什么你死我活的冲突,一切都在繁杂的日常中展开,弥漫着日常气息。金嫣在偶然间听到泰来的故事便千里追寻心中的爱情,而她来到泰来身边后表达爱情的方式也是日常的。她很希望泰来能亲口对她说“我爱你”,但在得知泰来的自卑后,还是她说出了“我爱你”。都红的自尊与独立,小马的纯粹与痴迷,张一光的荒唐,沙复明的执着,张宗琪的自闭,小孔的泼辣,季婷婷的宽慰,等等。他们那鲜活而独特的形象毫无例外都是在日常的疼痛与欢欣中站立在读者眼前。当我们读完小说后,脑海里异常清晰的是他们那种“人”的形象,而不是“盲人”形象。把这个处于现实生活边缘的底层人群作为“人”来写,而不是作为“盲人”来写,让他们在正常人的日常生活中演绎自己的平凡人生,而不是在他者的眼光中呈现黑暗世界的另类“奇观”,这是《推拿》中不动声色却奠定大局的基调。
日常生活的描写关键在于细节的刻画。从《哺乳期的女人》到《平原》,我们可以看到毕飞宇是一位在细节刻画中长袖善舞的作家。但《推拿》对他来说仍是一种挑战,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一个盲人的世界,从盲人感受世界及表达对世界的认识来看,对一个正常人的表达来说是一种局限,这种局限对呈现细腻绵密、且与叙事对象的内心世界相契合的细节来说,无疑是一种障碍,然也正是这种障碍考验着作家的艺术功力及其作品所能抵达的境界。毕飞宇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这种障碍,他那种在细节处见功力的手段在《推拿》中展现得异常精彩和结实。其中,心理描写最为精妙,他施展开对人物心理的大力“推拿”,把握住人物心理经络中最敏感的部位,推、拿、提、捏、搓、揉,乃至不惜撕裂,把盲人沉默的内心展现得纤毫毕现,把那黑暗的世界呈现得格外丰饶。
其最精彩之处是小马在孤独中冥想:“小马整天抱着这台老式的时钟,分分秒秒都和它为伍。他把时钟抱在怀里,和咔嚓玩起来。咔嚓去了,咔嚓又来了。可是,不管是去了还是来了,不管咔嚓是多么的纷繁,复杂,它显示出了它的节奏,这才是最紧要的。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它不快,不慢。它是固定的,等距的,恒久的,耐心的,永无止境的。”“小马就此懂得了时间的含义,要想和时间在一起,你必须放弃你的身体。放弃他人,也放弃自己。这一点只有盲人才能做到。健全的人其实都受控于他们的眼睛,他们永远也做不到与时间如影随形。与时间在一起,与咔嚓在一起,这就是小马的沉默。”小马在孤独中寻到了一种理解时间、理解世界的方式,他对时间的感知已经比健全人更加深刻。时间,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而对少年小马来说,他的日常生活就是理解时间与世界的关系,他在这种对“咔嚓”声的想象与感知中,枯燥与沉寂变成了一种辽阔与博大,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也是一个超越的世界。其他的细节描写也同样精彩,比如王大夫回家替弟弟还赌债时,看到弟弟也在家等他,“王大夫的血当即就热了起来,有了沸腾和不可遏制的迹象”。拿起菜刀,在“规矩”的逼债面前,在自己身上划了两刀,毕飞宇连用四十个短促的、连续的、斩钉截铁的,犹如进入无物之阵的“王大夫说”来呈现王大夫那血性的形象。再比如,小说中描写王大夫和小孔抽空“相好”后穿衣服的细节,如果盲人不是按通常的习惯和次序按部就班地放衣服,他们的生活次序就会变乱。这看似可有可无的一笔,却有力表现了盲人爱的艰难,日常生活的艰难。这些细节描写显示了作家对盲人日常生活精细入微的洞察力与想象力。
在众多的底层文学叙事中,鲜有《推拿》这样的作品在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中花费这么多笔墨,因为琐碎繁杂的日常比那戏剧化的场面和极端化的想象更难把握。这来自于作家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毕飞宇笔下的日常生活,是有温度、有气息、有血有肉的,有光泽度、有尊严感的。“毕飞宇在《推拿》中写出了盲人对温暖对尊严尤其是对尊严的强烈渴求,这集中体现在都红身上。当她的大拇指受伤后,认为自己再也不能做推拿了,她不顾别人的好心劝告及老板沙复明爱情的挽留:“不能欠别人的。谁的都不能欠。再好的兄弟姐妹都不能欠。欠下了就必须还。如果不能还,那就更不能欠。欠了总是要报答的。都红不想报答。都红对报答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她只希望赤条条的,来了,走了。”尊严书写,是理解《推拿》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毕飞宇在《推拿》中竭力表达的一个主题:“我一直渴望自己能够写出一些宏大的东西,这宏大不是时间上的跨度,也不是空间上的辽阔,甚至不是复杂而又错综的人际。这宏大仅仅是一个人内心的一个秘密,一个人精神上的一个要求,比方说,自尊,比方说,尊严。”⑤这种对尊严的理解,是毕飞宇建立在对世间生命理解的基础之上:身处社会底层的盲人也是人,也需要正常人的尊严,他们不是我们窥视、同情、怜悯的对象,他们是我们理解、尊重的对象。看待他们应该是如小说结尾所说的那种“最普通的、最常见的、最日常的那种目光”。正是用这种目光看待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盲人,毕飞宇在小说中有的是体贴和理解,同时,也没有拔高他们,更没有为他们唱励志的赞美诗。因为他对他们有着清醒的认识,能认识到作为盲人的局限。这是一种诚实而严肃的写作态度,这种态度是对对象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这种态度能使作品与底层文学中那些“传奇故事”区别开来。
毫无疑问,盲人是这个时代最底层的底层,在那些热闹的媒体中,我们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即使偶尔看见,也大多是可怜与苦难的符号。他们是我们社会的盲区,基本上消失于我们的世界之中。然而,在《推拿》中,我们不会感受到那种苦难的场景,不会以为他们是在底层苦苦挣扎的人群。这同样是因为作者的写作态度。毕飞宇在《推拿》中远离了自上而下的同情和高高在上的悲悯,他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正常人的世俗世界与平凡人生,他用其敏捷的心智和平等的眼光,给我们描绘了黑暗世界的光亮和日常生活的尊严。而这种写作态度,这种观察世界的眼光则能够为那些以农民工、下岗工人、失学少年、拾荒者、发廊女或其他类型的残疾人等同样身处社会边缘的底层人群为叙事对象的底层叙事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范式,这个范式的核心就是从“奇观”回到“日常”,给叙事对象以平等、理解和尊严。我们不否认同情和怜悯,但要警惕那种把同情和怜悯当成施舍的心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作家的创作。这是底层文学创作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不断推延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说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有“知识分子立场叙事”“阶级立场叙事”“民间立场叙事”三种叙事向度,那么《推拿》为我们提供了第四种叙事向度,那就是“人性立场叙事”。毕飞宇在《推拿》序言中说:“我们就这样处在飞奔的路上,带着我们的表情。我一点也不担心风驰电掣,——再快的速度也不能把我们的表情扔出窗外,因为表情在我们的脸上。它从容,镇定,最终会回溯到我的心灵。”可以把毕飞宇所说的“表情”理解为平等和尊严,这也就是“人性立场叙事”的关键词。尽管《推拿》在艺术上还不是很完美,小说书写的盲人感知到底还是大多可以推断出来的常人常情,还是缺乏那种特殊经验所具备的穿透力,有轻微的矫情与隔膜之感,但这不是毕飞宇才华的限制,而是每一个正常人自身的限制。但毕飞宇毕竟用他的睿智和技艺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丰饶的黑暗世界,在平淡中可见动人,在世俗中显现温文尔雅,避免了把这个底层人群写得扁平化,而是写出了这个底层群体生活内部的各种真相,及他们的生存意志和精神禀赋,激活了他们内心深处尊严意识的同时,让他们在精神上获得了某种完整。同时,作者还摆脱了那种底层文学中常见的过度冷漠甚至尖刻的叙事,字里行间散发出人性的温暖。而关于“平等”“尊严”则不仅仅是一个写作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我们国家身处底层的人民有数以亿计。因此,《推拿》对正在进行的底层叙事来说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注 释
①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②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③李云雷:《2007:底层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1期。
④毕飞宇:《文学的拐杖》,《雨花》2007年第 11期。
⑤毕飞宇:《〈推拿〉的一点题外话》,《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