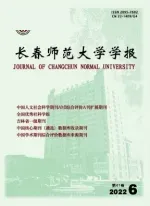《女勇士》:多重叙事的“变奏”
汤文益
(池州学院中文系,安徽池州 247000)
《女勇士》:多重叙事的“变奏”
汤文益
(池州学院中文系,安徽池州 247000)
汤亭亭《女勇士》协调运用了教材叙写、故事重构、“鬼”叙事、“偶像”叙事、隐藏的叙事者与不可靠的叙事者等多个主题、手法,实质是多重叙事的“变奏”。
重构;“鬼”叙事;“偶像”叙事;叙事者
《女勇士》(1976)是汤亭亭的处女作和成名作,被视作美国亚裔文学进入主流文学的标志[1]。汤亭亭最初把它定位为小说,题为“金山故事”,但编辑以考虑读者和评论家的反应为由,将其作为“非虚构类作品”推向市场[2]。作为糅杂了多种文化元素的文本,《女勇士》协调运用了多个主题手法,实质是多重叙事的“变奏”。
一、施教者的教材叙写与受教者的故事重构
“妈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叙事者。在讲故事之前,她明确要求女儿不能把她说的话告诉任何人[3]。这样的开篇是对读者好奇心的一种迎合,同时也加深了叙事的在场感。在故事里,小女孩得知自己有个自杀身亡的“姑姑”,以及“姑姑”那个尘封多年的秘密。作为叙事者的“妈妈”之所以要将这个秘密告诉女儿,不是为了怀旧,甚至也不带有任何同情,而是要为女儿提供一个“反面教材”,借此教育孩子遵守礼仪和规矩,避免重蹈覆辙,让她和家族丢脸[3]。
在施教者精心营构的“反面教材”中,年轻的姑姑刚刚婚嫁,就被迫离开丈夫,后来却怀上别人的孩子,从此被贴上“不贞”的标签。分娩时,不堪忍受村民百般羞辱的姑姑抱着刚生下的孩子投井自杀了。在完成这一“教材叙写”后,施教者还郑重其事地交代,千万不要让父亲知道,因为,他始终否认有姑姑这么个人。事隔多年,伦理的魔咒犹在。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孩重新审视母亲这个“特别交代”时,忿忿之意油然而生。
施教者的反面教材还有很多。而受教者,也就是女主人公,似乎看穿了这一切。她为姑姑的悲剧增添了很多浪漫或粗野的元素,彻底重构了“姑姑的故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悲剧女子孤独、寒冷、震颤而又绝望的夜晚。受教者还嘲弄了“重男轻女”的传统,一针见血地指出,姑姑刚出世的孩子也许是个女孩,“要是男孩,还会有几分宽恕的希望。”[3]
施教者的教材叙写与受教者的故事重构这一对应模式还体现在两代人的“鬼”叙事中。第三章“乡村医生”首先由母亲(而非第一章中的“妈妈”) 讲述在老家求学、行医和驱鬼的经历。女主人公则偶尔打断讲述并提些问题,希望能还原母亲当年的故事。她隐约捕捉到一些微妙的情感并进行重构,试图在母亲粗线条的框架上补足温度和血肉,以此弥补现实生活的缺憾。也即,将从前母亲认真刻苦又无忧无虑的状态与当下“我”的尴尬境遇对应起来,构建成长,表达诉求。基于此,故事有意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不时穿插现实世界中母亲和“我”的声音。声音的凸显模式把施教者从幕后推向台前,使她与受众的联系更为密切,从而实现逼真、客观的叙事效果。声音愈加凸出,形象便愈加生动。
通过“鬼”叙事,我们得知学生时代的母亲就试图通过否定鬼、讲述鬼、闯鬼屋的自我表现方式,把自己跟其他女同学区别开来。其中,梦魇片段、“与鬼对话”、“招魂”、“灭鬼”等情节的描述非常细致。来美国后,母亲的“鬼”叙事仍然没有中断,那些故事纷繁驳杂、煞有介事,使受教者的童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鬼”。但在“我”的思维体系中,所有感到陌生的和难以理解的东西都可以算作“鬼”。显然,受教者所面对的是身份寻求和角色定位的难题。如何破解难题,就成了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个难题得到破解,已在受教者头生白发之后。那时,“我”已不愿意再与“鬼”纠缠,即不再参与“鬼”叙事,而是认定自己就是美国人;母亲也已是白发苍苍,但还是觉得美国是个“真可怕”的“鬼国家”,甚至认为自己不该来,但是“也不想回去了”[3]。
二、童真时代的“偶像”叙事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不仅仅是我们联系这个世界的手段,更是我们个体生命的本体存在。生命在语言中找到家园,以及存在的理由。我们鲜明地感受到语言本体的存在。“白虎山学道”为我们引出了一个杂糅多个英雄形象,尤其是女性英雄形象的角色:巾帼英雄与女剑客花木兰。通过极富个性的语言策略和实践,作品建构了一个鲜活的生命本体,构筑了一道独特的语言景观。
叙事者首先让女主人公和她所构想的花木兰形象纠缠在一起,通过身份重叠、角色代入等手法,模糊二者界限,使之亦幻亦真,既追求现实的骨感,又获得了超现实的质地。
引子部分讲述了一个女孩(女儿)在白鹤的教导下创立新武学的离奇故事,故事来源仍然是“妈妈”,因此,女主人公在睡梦中常把“妈妈”的声音和女英雄的声音混为一体。“妈妈”给她定位的角色是长大后的“妻子和佣人”,而她则憧憬着能成为女中豪杰。
7岁的主人公跟随飞鸟进入群山,闯进了一个明媚世界。这个世界生活着一个老汉和一个老太太。当他们问她有没有吃饭时,出于礼貌,她采取了“中国式”的回答,说吃过了。她的实际想法并非如此,所以“很恼火中国人撒那么多谎”[3]。作为叙事者的女主人公经常打断正常的叙述,加入一些极具个性色彩的口语。有论者认为,汤亭亭受中国口头文学的影响,有意采用口头叙事的一些惯用手段,“有效地吸引了读者的参与”[4]。
大量东方文化元素经过筛选和改写后,变成一个中西混杂的新故事。如,在“我”饥饿的时候,居然有只兔子主动舍弃生命,投入火中,变成美餐。作者有意穿插西方小说情节、中国神话传说和佛教故事。子虚乌有的东西在她的笔下诗意充盈且饱含感情。如对水葫芦这一奇妙道具的描写。在小小的水葫芦里,可以发现人生万象、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当她得知父亲被征做兵丁时,赶紧下山替他出征,并且骁勇善战,带领追随者建功立业。但是回到家乡后,却又做起了公婆面前乖巧的小媳妇。主人公相信这一定会得到村人的世代传颂。
幻想故事戛然而止。一旦回到现实,“生活真令人失望”[3]。因为周围都是“宁养呆鹅不养女仔”、“女儿都是赔钱货”的可恶论调,尽管她很努力、很小心地活着,换来的却是不公的待遇。现在她所剩下的,就只能是幻想。叙事者对经典人物花木兰的改写,寄寓了这个正在成长的小女孩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施展才能时的偶像之梦。她要成为“这样”的女勇士,而这个花木兰仅仅属于她。这是典型的童真时代的“偶像”叙事。
三、隐藏的叙事者与不可靠的叙事者
“西宫门外”较为特殊,作者用第三人称视角讲述月兰姨妈来美国寻找丈夫的故事。这是《女勇士》唯一采用全知视角的章节。尽管叙事者隐身文本之后,但文本极力凸显的另一个女性形象,即母亲勇兰,并没有从文本隐退,而是继续主导故事,与月兰姨妈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女主人公“我”并不在场,读者仍然能够感觉到“我”的存在。这是“不在场的在场”作为一种策略参与叙事。
故事从母亲为已有30年没有见面的妹妹接机开始。68岁的母亲还沉浸在过去的思维定势里,总有些奇怪的想法和行为,把很多年轻的女子误认为是月兰。但是她所见到的却是一个很老很瘦的女人。两人的手同时伸了出来似乎想摸对方的脸,又同时缩了回去抚摸自己的脸,并感叹对方成了老太太了。母亲勇兰的回话却是:“你是真的老了。我却不然,我老了,却和你不同。”[3]
这里,我们很难发现有所谓的“后现代”手法。即使是反讽手法,也不能视为“后现代”所专有。有论文称,后现代主义作家“一反以往传统的编年史式和直截了当的讲故事的方式,有意识迷惑读者。它的叙事风格令人望而却步。”[5]显然,“后现代”的界定和阐释不适用于《女勇士》。这也是汤亭亭不满于评论界对其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标题为“西宫门外”,“西宫”即是勇兰为月兰谋划的新角色。她首先讲了一个“东宫和西宫”的故事,将月兰定位为善良正义的“东宫”,而把妹夫那个西方妻子比作玩弄权术的“西宫”。她试图以此为蓝本,营构正当的“夺权”路线:月兰做大太太,那位美国妻子成为奴婢。勇兰的叙述越严整,故事的悲凉意味就越明显。她幻想用古中国的方式来解决现代美国的问题,幻想纤弱的妹妹变得和她一样坚强。然而月兰并没有按照姐姐的谋划成功“夺权”,最终悲剧性地死在疯人院。我们隐约感觉到故事的讽喻意味。勇兰越积极、越自信,读者就越感觉到悲哀。这是一场“笑中有泪”的人生悲喜剧。
最后一章“羌笛野曲”,女主人公“我”重新现身,不再以隐藏的叙事者身份出现。“西宫门外”给人以客观真实的感觉,但在“羌笛野曲”里,这种感觉被叙事者有意颠覆。从而,之前对各类故事的再现或重构,其权威性也受到了挑战。叙事的不确定性,造成读者多种阐释的可能。这种可能,正是作者有意造成的。“羌笛野曲”开篇即以“弟弟”之口说他开车送妈妈和二姨到洛杉矶,去看另有妻子的姨夫[3]。随即又说:“事实上,弟弟并未对我说起去洛杉矶的事;我的一个妹妹转述了他说的话。”[3]
叙事者明确表示,自己就是那不可靠的叙事者。读者若想从文本中获得真实的东西,那就错了。在叙事者看来,任何围绕叙事者或作者文化身份、女性角色的解读,都是不可靠的。
“割舌头”叙事,也是“不可靠”的表现。母亲割掉“我”连接舌头的筋。正在我们惊诧之际,突然戏谑性地笔锋一转:“我记不得她干过此事,只记得她这样对我讲过。”[3]随后种种关于“割舌头”的叙事,如:“我”让其他孩子张开嘴,与自己的舌头进行比较;“我”有时为母亲割舌头的举动感到自豪,有时又觉得恐惧;等等。母亲说“割舌头”是为了说外国话,但在“我”看来,这种举动影响了说话能力,尤其是在该说英语时,几乎难以张口。自卑困扰了“我”(还有妹妹)很长时间。那在图画作业上一律涂上的黑颜色,就是困境的证明。这里,我们确实感觉到女主人公在边缘地带无所依凭的现实处境。因为是华人,多数女孩都选择了沉默,这一集体“失声”现象显示少数族裔在美国的边缘地位。这也难怪作品难以逃脱族裔文学先入为主式的解读。大多数人都认为女主人公最初几年的沉默主要是因为文化的隔阂,而非从个体心理层面寻找原因。文本有意表现孩子们在美国学校和华人学校的反差。我们猛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笼罩着她们。这个身影属于母亲勇兰。她还活在“蟾蜍吞月”的阴影里,并且言之凿凿;当送药的伙计误送一盒药片后,母亲认为这是“诅咒”而怒发冲冠。在“我”看来,母亲有些自以为是,会做出一些惊天动地又令人难堪的事来。母亲固执得让人有些同情,但她并未感觉到痛苦。真正痛苦的是她的孩子们。孩子们既不能正常融入美国社会,又无法完全理解母亲。
“失声”的不止是“我”,有个女孩更厉害。“我”恨她中国布娃娃的发式,恨她在音乐课上发出的呼哧呼哧的声音。“我”后来抓住了一个机会,带有拯救的意味迫使她说话——汤亭亭不惜笔墨,刻意渲染同样“失声”的“我”是如何煞费苦心地逼迫他人说话。令人沮丧的是,所有方式都于事无补。徒劳无功的女主人公随后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既无痛楚,也无症状,整整卧床一年半。这一年半却成了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原因是可以不见任何人,万事皆无。毋宁说这是种心理疾病。唐人街以及华人的一切,尤其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疯女巫婆、将女孩子视作蛆虫的老头、智力迟钝的男孩、各种“鬼”——始终困扰着女主人公。终有一天,主人公彻底爆发,打破了沉默,向母亲一口气“嚷出”积压于心的愤懑。这可以视为华人女性“发声”的一种诉求和实现。
结尾部分,女主人公想起了蔡琰的歌声,这歌声,外婆和母亲在从前看戏时听到过。蔡琰作为一位著名的女性历史人物,在我们看来,也是一个“女勇士”。在汤亭亭的笔下,已为外族生养两个孩子的蔡琰,高亢而清脆地歌唱“中国和在中国的亲人”,伤感而又怨愤。多年后,蔡琰被赎回,一同赎回的还有她的思乡之歌。以蔡琰的故事压轴,可能表示女主人公已经在蔡琰的故事中找到了想要的答案,正试图认同自己的双重身份。
四、结语
《女勇士》中,母女二人声音经常并置,互相冲突。女儿总是在不断评价、挑战和修正母亲的故事,不惜破坏故事的整体性和权威性,甚至打破读者的传统期待,使叙事总是处在不确定的语境之中。或者,作者正是要通过对传统叙事的反叛,为我们呈现一个复杂多义的成长故事。也许,这才真正契合“成长”二字的要义,因为,成长本身就是复杂多义的,成长的真谛就在这复杂多义之中。
[1][美]屈夫.《女勇士》译序[M]∥汤亭亭.女勇士.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7.
[2]林涧,戴从容.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及归类[J]复旦学报,2003(5).
[3]汤亭亭.女勇士[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1,3,14,98,17,41,105-106,146,147,147.
[4]黄芙蓉.论汤亭亭文本的口承叙事特征[J].当代外国文学,2006(3).
[5]徐颖果.后现代美国小说叙事特点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2005(2).
I712
A
1008-178X(2012)11-0103-03
2012-07-26
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2SQRW189)。
汤文益(1981-),男,安徽桐城人,池州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