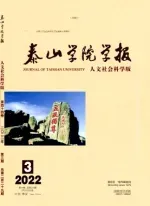华侨大学境外生语言现象例析
胡萍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华侨大学的境外生,基本上来自东南亚和港澳台,他们生活在“汉字文化圈”,自然母语[1]往往是汉语方言,其实就是“域外方言”[2]。来华侨大学之前,境外生们无一例外地都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学过一段时间汉语,有的则还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等机构补习或强化过汉语;他们平时会话基本上是使用双语甚至多语,而且时刻在“切换”。在与境外生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时时发现一道道异域风情。本文就结合我留意、捕捉到的几个书面语特例,谈谈自己对华文教育及母语安全的点滴看法。除非特别说明,下文例子均取自华侨大学商学院2007级作业。
一、上课的地点:教堂/课室?
“教堂”,指的是“基督教徒”举行宗教仪式的会堂,我想,无论我们是否信仰基督教,这个常识我们还是有的。可是,在境外生笔下,“教堂”可以指上课的地方:
(1)班长说,我们不要在教堂办,为了让同学们更加放松,就办在我们宿舍附近的一个地方。
([缅甸]林青青《记住一辈子》)
不仅如此。“教室”在境外生的语言里还有另外的叫法:
(2)课室是跟星期一一样的吗?
(香港 林煌杰短信)
(3)第二件事发生在十月中旬……下课我忘记拿走我的钱包,到我发现、回课室找时,已经不见了……在之后几天,我的心情很低落,整天都在责怪自己……
(澳门 陈卓江《印象最深刻的两件事》)
学校里进行教学的房间,英文单词classroom,汉语对应的是“教室”——强调老师的主导作用;如果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又有“课堂”一词对应classroom——课堂是学生学习的场所。用生造词“课室”(课堂+教室)来对应classroom,似乎是原汁原味的“直译”。但这种不走样的“直译”却折射出港澳地区有些学校的华文教育亟待加强。香港和澳门都已经回归祖国多年,港澳学生也都是接受了华文预科教育才来华侨大学读本科的,而今他们连平时上课的地点“教室”一词居然都没有掌握——不会使用就是没有掌握的最好说明。
香港曾长期是英国殖民地,世界各大宗教在香港几乎都有人信奉。在这样一个宗教氛围里,“教堂”所指不会有误解。香港的人口绝大多数为原籍广东、主要说粤语的华人,但英语很流行——香港人似乎普遍有英文名,社会普遍以进英文学校或去英语国家学习为荣。虽然回归带来了变迁——近年普通话也流行,一般机关和机构也鼓励应用,但目前香港的法定语文(不称作“官方语言”)是中文和英文,政府的语文政策则是“两文三语”,即书面上使用中文白话文和英文、口语上使用广州话(俗称“广东话”或“粤语”)、普通话和英语。香港华裔人口中主要使用广州话,而非华裔人口则多以英语作交际语——普通话明显被边缘化,地位挺可怜,这是口语方面。书面语方面呢,长期使用正体字版的教材,且教室里进行的课堂教学并不能保证用普通话授课。众所周知,口语对书面语的负面影响时刻存在。即使凤凰卫视的招牌主持人的播音中还带有“港腔”呢。人都是生活在具体的家庭里的,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受社会评价体系影响很大。在一个耳旁充满了、萦绕着广东话的环境了生活十多年,社会期望是“英文OK就OK”,现在到祖国大陆的大学来求学深造了,香港来的大学生居然不知道“教室”就是classroom,这就一点不奇怪了。澳门的历史与香港不一样,但道理相同。
缅甸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缅甸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是著名的“佛教之国”、“佛塔之国”,佛教传入缅甸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80%以上缅甸人信奉佛教;缅甸更是一个农业国——森林覆盖达50%,超过六成劳动人口从事农业。它也有过一段殖民时期(1885年-1948年),但63年的殖民统治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简直就是“沧海一粟”,其影响微乎其微,更何况遍地存在的佛教寺庙毕竟是和基督教的教堂不一样的,大学生缅甸人照样不知“教堂”所指,竟然用“教堂”(教室+课堂)来“对译”classroom!——缅甸的华文教育比较落后由此可见。
仿照学界对“假借”和“通假”的分析,港澳学生的“课室”可谓“本无其词”的假借,而缅甸学生的“教堂”则俨然是“本有其词”的通假,二者都是对现代汉语、对普通话陌生乃至隔膜的表现,不知然否?
二、关于吃饭问题
学生的天职是学习,学习固然是第一位的,但“民以食为天”,“吃”,摄取食物是生命存在的前提,所以下文接着说吃饭及其场所。
华侨大学一年一度的“饮食文化节”总是如期而至,热热闹闹、红红火火,让人不由得想家——思念千里之外的亲人也想念家乡小吃,而在异地他乡品味家乡菜肴似可一解乡愁。不信你看:
(4)因为我们都是澳门和香港的,所以我们就去了一间广东的菜馆,食一些比较有亲切感的菜。
(澳门 林霭玲《不一样的地点,但一样的情》)
(5)至于在小食方面,香港的街边小食也满有名气,如鱼蛋、蛋挞及酒楼的一盅两件,如果想一次过尝尽各式各样的小食,只要到旺角便可一尝(偿)所愿。
(香港 江铭专《香港》)
例5是用正体字蝇头小楷写的,作者是数学学院来自香港的江铭专。内容朴实又亲切,书写既工整又美观,印象深刻的还有“小食”一词。“小吃”在《汉语大词典》中有三个义项:①正式饭菜以外的熟食,多指下酒菜。明清文学作品中常见。②今多指点心铺出售的熟食或饭馆中的经济膳食。③西餐中的冷盘。普通话中不见“小食”——它是个不折不扣的“生造词”。要弄明白例4、例5二例为何用“食”不用“吃”,须对表示“吃东西”这一行为的动词溯源一番。
现代汉语中“吃”排在4000个常用词的第77位[3],是一个频率非常高的语词,而先秦两汉一般用“食”表示“吃东西”这一行为。“吃”本是为“口吃”义而造的一个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为“言蹇难也”。“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属皆从口。”他在“口”部分析了“文一百八十,重二十一”,有“吃”无“喫”,“喫”到北宋徐铉《说文新附》才有收录:“喫,食也。从口,契声。”东汉之前一直用“食”不用“喫”,甚至“喫”产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食”仍比“喫”的使用频率高。“食”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中一直是“吃”语义场中的主导词位。[4]
“喫”字字形早在《庄子·天地》中就有所见:“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喫诟”是人名,不是单用的动词。这是先秦典籍中所见最早也是惟一的“喫”字字形。[5]一般认为表“进食”义的“喫”始用于魏晋南北朝,所举最早用例见于《世说新语·任诞》:“(罗)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其实“喫”在东汉、三国时期的汉译佛经中就已出现,如“喫酒嗜美”(《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喫食其半”(《奈女祇域因缘经》)。[6]梁朝顾野王《玉篇·口部》收录了该字:“喫,啖也。”“喫”作为动词明确地表示“吃”义一般出现在较口语化的场合,使用还很不广泛,唐代逐渐增多,但与“食”相比,仍处于弱势。“喫”作为口语词,多见于唐代以后的语体作品。在唐初白话诗中,“喫”已开始比“食”使用频率高了。
唐五代佛经里,表示“吃”的概念基本上用“喫”而很少用“食”了,五代以后,二者的使用频率差距更加悬殊,这说明,至迟在晚唐五代,“喫”在口语中已代替了“食”的动词义,“吃”语义场基本上完成了“食”和“喫”的义位更替。但是,在唐代,“食”与“喫”有很大的文白差别:除沿袭古代用语外,“食”主要用于诗词等避俗求雅的文学语体,而“喫”则活跃于口语中。比如,在唐诗中,即使是善用口语词入诗的杜诗中,“食:喫”是50:7。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11:“孙季昭云:杜子美善以方言俗语点化入诗句中。”主张作诗不尚雕华的宋代福建人黄彻著《巩溪诗话》品评诸家之诗,极推崇杜甫,发现杜甫作诗善用俗字,“数物以‘个’,谓‘食’为‘喫’,甚近鄙俗,独杜屡用。”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喫”在唐代是一个文人避用的俗字。
“从外部接受食物”的“吃”在唐宋资料中皆作“喫”,《广韵》“喫”(苦擊切,溪母锡韵-k)“吃”(居乞切,溪母迄韵-t)韵尾不相同,到了元明之际“喫”“吃”二字韵尾变得一致起来,所以“喫”“吃”二字通用、混用,并渐以笔画简单的“吃”字取代“喫”。江蓝生(1989)认为,在唐五代“喫”就已开始虚化为“受,挨”,最迟不晚于北宋,在含有白话成分的资料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表示被动的关系词——“吃”。[7]这反过来又说明:在唐代,“喫”就已经在口语中取代了“食”在语义场中的主导地位。宋代以后,“喫”(吃)有了迅速发展,并且很快战胜了“食”,直至现代汉语中取而代之。解海江、李如龙(2004)认为“喫”的出现及“喫”取代“食”在语义场中的主导地位是中古汉语的表现;语言随移民一起南迁,远江的客、闽方言区的人们从中原南迁的时代应该处在“食”在“吃”语义场中占主导地位时期,因为地理阻隔而受官话方言的影响较小,所以保留了“食”在“吃”语义场的主导地位。[8]港澳等粤方言区就更加“远江”了,上文例4的“食”与例5的“小食”似乎在告诉我们:粤方言区的人们南迁的时代也处在“食”在“吃”语义场中占主导地位时期,同样因地理阻隔而受官话方言的影响较小,所以保留了“食”在“吃”语义场的主导地位。[8]
无论哪个占主导地位,“食”与“吃”在使用上分工互补,表示的都是“把食物放入嘴中经咀嚼咽下”这个动作。现代汉语中一般说“吃饭”,“饭”是对象宾语,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境外生文中“饭”的用法似乎在提醒我们什么:
(6)在我的家乡是有很多的美食,很多菜、苹果,最特别是葱木瓜、烤鸡和糯米。(我没有饭这些东西三个月了,好饿!)
([老挝]维拉碧《我的家乡》)
该老挝学生的作文字字句句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虽然会写的汉字实在有限(许多字写成错别字,还有许多字空着、在上面用拼音标注),但热爱祖国、想念家乡的浓烈情感还是完完全全地表达出来了。“好饿”,可能真正想表达的是“好馋”的意思。
是人都得吃饭。大家熟悉的“饭”在现代汉语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名词,读fàn,最常用的两个义项是:①煮熟的谷类食品,南方多指大米干饭,北方则多指面条等面食。②指每天定时吃的食物,如早/中/晚饭。但古文中的“饭”却除了名词用法外还常常用为动词。黄斌(2005)发现《论语》和《墨子》中“饭”全部用作动词,在稍后的《庄子》《韩非子》中,“饭”字有了名词用法。《说文解字·食部》:“食,亼米也。”“饭,食也。”段玉裁注:“亼,集也,集众米而成食也,引申之,人用供口腹亦谓之食,此其相生之名义。下文云‘饭,食也’,此‘食’字引申之义也。人食之曰饭,因之所食曰饭,犹之亼米曰食,因之用供口腹曰食也。……食者,自物言之;饭者,自人言。”“云‘食’也者,谓食之也,此‘饭’之本义也,引申之,所食为饭。”到了《玉篇》时代,为本义(动词)和引申义(名词)赋予不同的读音以示区别:“饭,扶晚切,餐饭也;又符万切,食也。”结合文献中的实际用法和工具书中的概括,可以发现“饭”本是动词,并且特指人们在正式的用餐中吃东西。在中国早期农业社会中,人们“定时的、正式的用餐时所吃的食物”主要是煮熟的谷物类的粮食,所以“饭”字用作名词主要指“煮熟的谷物类的粮食”。这也就成为现代汉语“饭”的词义来源。[9]古文中“饭”为动词(读fǎn):①吃饭。如《论语·乡党》:“君祭,先饭。”②泛指吃。③给饭吃,使吃饭。如《史记·淮阴侯列传》:“有一母见信饥,饭信。”④指使吃。⑤指饭含。古丧礼,以玉、珠、米、贝等物纳于死者之口。[10]——其中②是①“吃饭”本义的引申,③④则是古汉语中的使动用法,而⑤“饭含”的做法在现在中国某些实行土葬的农村还有所保留——人活得要有尊严,同样做鬼也要有尊严啊,倘若死了也要做个“饱鬼”,这样到阴间去报到时不至于被说成是“饿死鬼投胎”。
老挝学生在我校境外生中语文水平普遍偏低,因此,维拉碧同学文中的“饭”意味深长。境外生用文言词的原因多种,最主要的应该是,一方面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深远,至今许多日常习俗还有深深的中国痕迹,表现得甚至比中国本土还“中国”;另一方面又因为近现代的殖民统治而对现代汉语了解不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华文教育的教材,内容可能偏文言文,尤其是先秦文学作品比例较大,《论语》、《史记》等典籍中的名篇常常被引进课本。当然,“源头作品”确实应该多读,但因为平时听说的环境并不是汉语、普通话语境,所以,一旦下笔行文,措辞往往给人文乎文乎又怪怪的感觉。该境外生似乎仍旧生活在古代。那么境内生呢?
(7)虎毒不吃儿(食子)果然有理。
(广东 布信森《我看<射雕>》)
该例句出自广东籍学生布信森之文,“虎毒不吃儿”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宋·释普济《五灯会元·杭州龙华寺灵照真觉禅师》:“山僧失口曰:‘恶习虎不食子。’”这可能是“虎毒不食子”的最早出处,至今已有千年之久,早就家喻户晓。大家知道,成语指长期习用、结构定型、意义完整的固定词组,一般不可随意改动,可是该生就这么更换其中的字眼。这种改动成语字眼的现象其实也是对汉语隔膜的表现。
粤语被认为是国内的强势方言,但近年很多方言城市都出现普通话小区,然后是出现普通话城市,现在广西粤语已经被边缘化,广东粤语城市也在不断萎缩,因此时有“方言保护”的呼声。由于邻近广东的港澳普遍说粤语,改革开放初期乃至今日,为了方便港澳同胞、华人华侨,国家对粤语的使用政策一直比较宽松,广东珠三角地区粤语使用者没有明显减少,改革开放的需要使得粤语继续顽强生存。来自广东的“布信森同学们”耳边充斥着再熟悉不过的母语——广东话,动笔行文时毫不犹豫地写下口语味浓浓的“虎毒不吃儿”,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三、点滴思考
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150多年,澳门也于1999年回归祖国,虽然统一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但“国语”在台湾的普及率远高于普通话在中国大陆的普及率,而且国语取代台语、客家话、原住民语言的趋势很难停止,愈来愈多家庭和城市转变成“国语之家”、“国语城市”。曾不知个中道理,后阅鲁国尧《台湾光复后的国语推行运动和<国音标准汇编>》[11]得知:宝岛台湾被日治50年后于1945年10月25日回归中国,但光复时的台湾,语言使用情况十分混乱。“日据”期间的“皇民化”政策带来“皇民化”运动,在全岛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即推广日语运动以贯彻语言同化政策。“强迫台湾同胞学日语日文,用高压手段来推行文化侵略”,“所有学校都用日语教学”,“又规定报刊书籍全用日文,大小机关全用日语”,“用尽方法来消灭我国的语言与文化”。台湾光复时,“台湾同胞三十岁以下的人,不但不会说国语,不会认汉字,甚至讲台湾话(闽南话、客家话),也没有说日本话那么的方便”。“受日本人五十年的文化压制,年轻一辈的只知有日语、日文,而不知有祖国语文”,当时台湾省的情况是,“自政府机关、学校,以至一般社会,还多是用日本话”,“在城市里交谈的语言多是日本话”,“通信也用日文”。殖民当局别有用心地实行同化政策,一方面强迫所有台湾学生学习日语,同时极力向民众灌输忠于日本天皇的思想,以期消磨他们的反抗意志。以魏建功先生为首的一群语言学家临“难”受命,1946年4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领导推行国语的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民到于今受其赐”。这样一次主动推行通语且有深远影响的语言运动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魏先生等参与编订的《国音标准汇编》作为地方政府的法令公布,鲁先生誉之为“是中国语言学史的珍贵文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推广汉语通语运动的最重要的‘物质遗产’”。我们往往“港澳台”并提,而其实港澳在汉语普通话的普及和推广上需要向台湾多多取经才是。此外,方言有其存在的价值,也必定会继续被使用,我们不用担心,引起我思考并警觉的是来自方言区的大学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漠视与隔阂。
王宁先生《论母语与母语安全》[1]一文提出:“当今社会,母语问题的意义已远不能局限在语言学习的领域里,它已经与民族平等、民族独立问题联系在一起,母语的概念应进一步明确区分为自然母语和社会母语两个不同的层次。”“社会母语的安全涉及它的地位是否得到保障,它的语音、词汇、句法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大量不规范现象。”“中国的母语安全意识淡薄,已到了必须重视的地步。”目睹境外生文中的不规范语言现象,我深深感到:华文教育任重而道远。希望王宁先生的呼吁得到更多的响应。
[1]王宁.论母语与母语安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2]鲁国尧.“方言”和《方言》[A].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3]陶红印.从“吃”看动词论元结构的动态特征[J].语言研究,2000,(3).
[4]解海江,张志毅.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兼论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论的转折[J].古汉语研究,1993,(4).
[5]王青,薛遴.论“吃”对“食”的历时替换[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6]香川孝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汉译考对译者及时代考证[J].佛教文化,1990,(2).
[7]江蓝生.被动关系词“吃”的来源初探[J].中国语文,1989,(5).
[8]解海江,李如龙.汉语义位“吃”普方古比较研究[J].语言科学,2004,(5).
[9]黄斌.“饭”字词义及其演变考[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10]汉语大词典编篡处.汉语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11]鲁国尧.台湾光复后的国语推行运动和《国音标准汇编》[J].语文研究,2004,(4).
——一项基于《匆匆》五译本语料库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