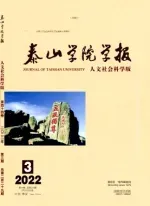泰山石敢当起源研究
崔广庆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南开 300071)
“石敢当”是中国历史上较为流行的灵石崇拜习俗,其文字记载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由于史游的《急就章》把当时流行的“石头镇宅”功能总结成“石敢当”一语,更因为《急就章》的广泛传播客观上推广了这一总结,使得在石碑上书写“石敢当”成为其后颇为流行的习俗。同时泰山在古人心目中具有镇鬼、升仙等等一些列神圣的功能,使得“石敢当”这种镇宅、厌禳的习俗有着与泰山结合的可能。自元代以降,泰山在官方的地位不断下降,泰山不再是帝王们的专属品,尤其是洪武三年的诏书,使得“泰山”二字的使用进入寻常百姓家,“石敢当”与“泰山”开始结合,在明代中晚期开始出现“泰山石敢当”这种新的镇宅方式,进入清朝之后,这一方式逐步定型完善。傅斯年图书馆的金元石刻“泰山石敢当”有着与历史事实诸多矛盾之处,其应是翻刻品而不能佐证“泰山石敢当”出现在金元时期,这是与历史发展相悖的,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一、“石敢当”溯源
“石敢当”信仰的载体是“石”,这是基于中国古代浓厚的灵石崇拜文化渊源。因为中国自古就有着丰富的灵石崇拜信仰故事,如早期的“女娲炼石补天”(《列子》、《淮南子》)、“燧人氏钻燧取火”(《庄子》)、“大禹生于石纽”(《帝王世纪》)、“启生于石”(《淮南子》),以及祭祀高禖石等等活动。正如刘锡成先生所言,“石敢当”是先民灵石崇拜的遗俗[1],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灵石崇拜又向后来的“镇宅”功能演化。
在清人倪璠《庾子山集注》里面注解庾信《小园赋》之“镇宅神以埋石,厌山精而照镜”引用西汉刘安《淮南毕万术》“曰埋石四隅家无鬼”;他如庾信同时代的《荆楚岁时记》亦言,“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为镇宅”,都讲到用石头镇宅的习俗。此外,在敦煌文献中记载的唐开元年间的民俗,更是详细地说明了镇宅石的用法和功能,高国藩在其《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中作了详细的介绍:
伯三五九四《用石镇宅法》:“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利。”“人家居宅已来,数亡遗失钱不聚,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辰地大吉。”
伯四五二二背面《宅经》中介绍的“占宅法第十”之镇宅法,实际上仍是石头镇宅的衍化形态。此卷叙述镇宅法,是用各种石头粉末配成一个镇宅药方,再加上念咒语等来“镇宅”。镇宅药方的原料都是石头(矿物质)有雄黄、朱沙、石膏等等,并用“石函”盛之,置中庭[2](P501-502)。
此外还有宅舍遇街巷之镇宅法和迁官的方法,其根据不同情况而“埋石”地下等等[2](P502)。
最早关于“石敢当”的文字记载出现在西汉史游的《急就章》里面,该书所成年代与《淮南毕万术》是同一时代,其中有这样一段:“朱交便,孔何伤,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3](P20-24)颜师古注解“石敢当”为:卫有石碏、石买、石恶,郑有石癸、石楚、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亦以命族。敢当,言所当无敌也[3](P22-23)。根据文意“石”和朱、孔、师、所、龙一样都是姓氏,颜师古的注释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把“敢当”解释为所当无敌犹有商榷余地。因为按照句式可知首字是姓后两字是姓的解说,如师猛虎,一方面是说师姓,同时也暗含像猛虎一样;故而石敢当,一方面也当是指石姓,同时也有可能含有石头敢当之意。由于《急就章》是启蒙读物,它里面的故事肯定是通俗易懂的,故而“石敢当”能够“敢当”什么,也应该如同“朱交便”亦即当时朱家善交的故事广为人知一样。考虑到上古灵石崇拜的遗俗以及汉代流行的“埋石四隅家无鬼”的信仰,这种“敢当”很可能是一种镇宅式的“敢当”。
现存最早的“石敢当”实物是在福建省福州市郊高湖乡江边村发现的一块宋碑,其上横书“石敢当”三字,其下文为:“奉佛弟子林进晖,时维绍兴载,命工砌路一条,求自考妣生(升)天界。”[4]古代最早记载的实物“石敢当”碑刻可以追溯到唐代,据宋人李俊甫《莆阳比事》卷9、王象之《舆地碑记目》等书记载,在庆历四年莆田宰张纬重修县中堂发现用墨书写的石碑上面有:“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昌。唐大历五年四月十日县令郑押字。”等字样。另据《通俗编》卷24引宋代施青臣之《继古丛编》载录吴地的石敢当之用:“吴民庐舍,遇街衢直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这种“镇鬼”、“厌殃”、“当冲”的信仰和现在的泰山石敢当信仰已经基本一致。
综上所诉,“石敢当”是上古灵石崇拜的产物,在灵石崇拜的信仰下,石头的“镇宅”功能被着重发挥。其后史游作《急就章》根据当时的风俗把石头镇宅敢于抵冲的功能简化成“石敢当”这一短语。由于《急就章》是一种启蒙通俗读物,其被社会广为接受,“石敢当”一语也广为流传。至迟在唐宋时期古人就已经把“石敢当”三字书写在石头上来驱邪、抵冲、镇鬼,这和现今“泰山石敢当”的功能已无区别,惟一的差别就是“泰山”二字的未曾使用。
二、“石敢当”与“泰山”的结合
(一)金元时期出现“泰山石敢当”碑刻辨析
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17言: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这种厌禳功能信仰和唐宋时期的“石敢当”功能是无区别的,考虑到陶宗仪的生活时代已经是元代末期,虽然“石敢当”在当时已经颇为流行用来厌攘灾异,但是尚未与“泰山”二字结合形成“泰山石敢当”。
叶涛先生认为金元时期已经出现“石敢当”与“泰山”的结合,其根据是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宋金时期的碑刻[5](P9):
碑文上面出现“泰山石敢当”五字,并有“大金”、“皇统六年”字样,故叶涛先生判定其为金代遗物,并判定在这一时期或更早已经出现“泰山石敢当”[5](P9)。
但是笔者细审这些拓片发现诸多问题:首先是大金皇统六年是金熙宗年号,时间为公元1146年。而蒙古出现文字是1204年成吉思汗征讨乃蛮之时,乃蛮掌印官人被俘,成吉思汗命令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命令他教授太子、诸王畏兀字以书写蒙古语,形成早期的畏兀儿蒙古文,时间要比石刻晚近半个世纪!此外,八思巴创造的蒙古文字是在忽必烈时期,更是晚于石刻近百年。如上,既然是金代皇统年间的石碑,为何会有尚未发明的蒙古文字?再者,“泰山石敢当”五字与蒙古文字重叠,设想如果这一组字是同时刻上去的,刻者一定会避开重叠部分,不会刻重而影响到其他字迹的显示。第三,根据“金如意院尼道一首座幢记”拓片,可推测这很可能是刻画佛像佛经用的,因为只有佛像佛经才使用“幢”。如上所述,这种石碑存在着被“翻刻”的可能性很大,其实石碑被翻刻的事情很多,有的经常引起人们的误会,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有很多的:
在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4、叶昌炽《语石·妄人题字一则》卷9中都有这样的事情:
《佛顶陀罗尼经》,唐永淳二年波利自五台回印度,获是经。复回长安,天子大喜,令日照三藏法师同宾寺典客杜行凯译。后译本留禁中,梵本仍交波利。再延汉僧顺贞再译,是此经。至唐高宗时,始流入中国。唐前之幢,大半佛像,罕见刻经。此经盛行,佛幢林立。明清又多刻七佛名,幢遂日见消灭矣。北地之幢,改刻“泰山石敢当”五字,止残一面;南方之幢,改刻七佛名,则止剩一面矣。
(《云自在龛随笔》)
新出隋《苏孝慈志》,一达官跋其上,恶札也,黄子寿师在关中磨而去之,今尚有斧凿痕。碑估以此定拓本之先后。魏《高植墓志》左空处,后人题“龙飞凤舞”四字。南山一唐幢,为明人李得渊题字其上,极鄙拙。又见一《金刚经幢》经文之末镌一“阳”字,又一殘幢有“泰山石敢当”五字,此皆所谓“燬瓦画墁”也。(《语石》)
这两条笔记的故事很相似,都是说一些佛幢佛经被改刻成“泰山石敢当”,并且这种现象往往误导后人认为其时代久远。此外傅斯年纪念馆里面的石刻“泰山石敢当”字体明显和后来的明清石刻通行的正楷字体相符合,故而笔者推断这块石碑被翻刻的可能性很大,“泰山石敢当”的出现不能藉此判定为金元时期。
(二)古代泰山地位的变迁
其实“石敢当”与“泰山”结合的原因,应该在“泰山”二字上寻找原委。
据《尚书·禹贡》记载泰山的特产有“岱畎丝、枲、铅、松、怪石”,关于其中的“怪石”,蒋铁生先生认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供人欣赏的美石,而应该理解成为有‘灵气’的泰山石。这既是上古时期泰山崇拜的证明,也是上古灵石崇拜的遗俗”[6]。如《山海经·东山经》也写到:“泰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可见早在先秦时期泰山就以其所产山石而闻名。
此外,泰山还被称为“五岳独尊”,因是群岳之长,故而又有“岱宗”的称号。唐徐坚《初学记》卷5“泰山条”引《三经通义》云:“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报功告成,必于岱宗也。东方,万物始交代之处,宗长也。言为群岳之长。”作为群岳之长,泰山是最大的名山。凡名山必有山神,而山神则有献宝驱邪之功能。如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7引《地镜》云:
入名山,必先斋戒五十日。牵白犬、抱白鸡,以盐一升。山神大喜,芝草、异药、宝玉为出。未到山百步,呼曰:林林央央!此山之名,知之却百邪。
泰山也素有“鬼府”之称谓,自古就有驱邪招魂、知人生命的能力。汉代以来就有把泰山作为“治鬼之山”的观念,如《博物志》卷1引《孝经援神契》曰:“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地之孙也。主招魂,东方万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长短。”再如《贞松堂集古遗文》卷15记载的墓券之刘伯平镇墓券上写有“生属长安,死属大(泰)山;死生异处,不得相防(妨)”之语,另一块残券也有“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太山”之语。
由于泰山自古就享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故而在《管子》、《史记》等书中都提到远古时期的七十二位帝王封禅泰山。此后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宋真宗等帝王也都亲临泰山封禅,尤其是唐宋时期帝王们还为泰山加了很多封号。在这种形势下泰山属于官方占有,尤其是封禅那种既神圣又神秘的举措更是使得普通老百姓对泰山敬畏三分,这一方面提高了泰山的威望但同时由于泰山基本属于帝王们的所有,客观上也剥夺了普通民众对“泰山”二字的使用,所以一直到元代,石碑上屡屡出现“石敢当”三字而未出现“泰山石敢当”五字,其中之一就是老百姓随便使用“泰山”是一种“犯讳”,犹如穿黄色的衣服和随意刻画龙凤一样是一种大不敬。
但是自从元代开始泰山在官方的地位持续下降,元代统一全国不及百年,其各种礼仪制定都很仓促,例如郊祭大典一直到文宗才确定。这样一方面是政府对各种祭祀大典的制定缓慢或不够重视,一方面又基于民族文化的不同,泰山开始在官方的祭祀典礼中走下坡路。而这种传统为明清所承袭,并且不断深化、定型:
诏书条画内一款: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在祀典者,所在官司岁时致祭,钦此。(《元典章·礼部·祭载祀典神祗》)
其天子亲遣使致祭者三:曰社稷、曰先农、曰宣圣。而岳镇海渎使者奉玺书即其处行事,称代祀。(《元史·祭祀志》)
(洪武)三年诏定岳镇海渎神号,略曰:为治之道,必本于礼。岳镇海渎之封,起自唐宋。夫灵英之气萃而为神,必受命于上帝,岂国家封号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今依古定制,并去前代所加名号。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神,北岳恒山之神。(《明史·礼志》)
顺治初,定岳、镇、海、渎既配飨方泽,复建地祗坛,位天坛西,兼祀天下名山、大川。三年,定北镇、北海合遣一人,东岳、东镇、东海一人,西岳、西镇、江渎一人,中岳、淮渎、济渎一人,北岳、中镇、西海、河渎一人,南镇、南海一人,南岳专遣一人,将行,先遣官致斋一日,二跪六拜,行三献礼。(《清史稿·礼志》)
尤其是明清以来泰山不再添加封号,皇帝也不再举行封禅大典,泰山神不享受皇帝亲祭,而只享受“代祭”,不再是帝王们的“专属品”。这样泰山在官方祭祀系统中的地位不断降低,而民间的习俗信仰就可以大胆使用“泰山”来崇拜。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东岳大帝信仰的普及、泰山老奶奶信仰的普及和泰山香社的活跃[6]。泰山的信仰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利用泰山来驱除邪患的方式当然也会流行,而历史上早就流行的“石敢当”这种灵石崇拜方式,怎么能舍得“泰山”这个既没有官方限制而又颇有灵验和神圣的名字?所以明清时代的“石敢当”逐步变成“泰山石敢当”,而流风于大江南北,神州内外!
(三)“石敢当”与“泰山”结合
综上所述,在明代之前“石敢当”和“泰山”结合的几率是很小的,我们发现的唐宋碑刻、以及宋元时期的笔记都证明了这种推测。
在元代泰山的地位虽然开始下降,但是把泰山完全从帝王独占的大权“解放”出来的是明朝洪武时期的诏书。然而习俗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然民间使用泰山不再属于“犯讳”,但是由于长期的历史意识积累,普通百姓一时也不会大张旗鼓地使用“泰山”二字,故而明代早期的一些笔记文集里面仍然是“石敢当”而并非“泰山石敢当”:
如万历年间陈师之《禅寄笔谈》卷6言:“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万历野获编》卷121里面也提到过“石敢当御史”,洪武年间居顶之《续传灯录》卷36也提到过“十字街头石敢当”,石敢当在十字街头其厌禳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几位明代早期人物均未提到“泰山”二字。
“泰山石敢当”的出现据现有文字资料是在明中后期开始,明杨慎之《升菴集》卷44《钟馗即终葵条》言:
石敢当本《急就章》中虚拟人名,本无其人也。俗立石于门,书“泰山石敢当”,文人亦作《石敢当传》,皆虚辞戏说也。昧者相传久之,便谓真有其人矣。呜呼,不观《考工记》不知锺馗之讹;不观《急就章》不知石敢当之诞。
此外如雍正时期的《四川通志》卷38言:
龚懋熙,江津人,生而颖异,能识“泰山石敢当”五字,七岁能文。崇祯巳卯,举于乡,时年十八,旋登进士,任太常博士。
龚懋熙是崇祯时期人物,杨慎是正德、嘉靖时期人物,后者生活时代比前者早百年,可知在明朝中后期“泰山石敢当”即已颇为流行,其出现应当更早。尤其是《升菴集》里面出现“泰山石敢当”,而稍后的《万历野获编》却仍然使用“石敢当”,这正好反映出这一时期“石敢当”新旧两种方式的并存。
逮及清代,泰山石敢当五字的形式基本定型,如清初王士祯之《古夫于亭杂录》卷5:
齐鲁之俗多于邨落巷口立石刻“太山石敢当”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北人谓医士为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案:“石敢当”三字出《急就篇》,师古注但云所当无敌。石贤士祠本汝南田间一石人,有妪遗饵一片于其下,民遂讹言能治病,是两事而讹为一也。“太山”二字义亦难解,或以劭为太山太守而转讹耳。
其后的李斗之《扬州画舫录》卷9、王端履之《重论文斋笔录》卷8等等众多的文人笔记都是记载“泰山石敢当”而非“石敢当”。
可以推测,“石敢当”与“泰山”的结合是在明代中晚期,逮及明代末年“泰山石敢当”已经较为流行,自清以后“泰山石敢当”逐步定型。
三、结论
“泰山石敢当”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下的产物,它既承袭远古时期的灵石崇拜以及灵石镇宅功能的习俗,同时也由于《急就章》对灵石镇宅功能总结——“石敢当”的推广,使得这种镇宅方式广为接受。同时,由于泰山在元明时期官方祭祀系统中的地位降低,泰山被剥夺了帝王独占的“神圣外衣”,而使得“泰山”的信仰和使用进入寻常百姓家。在这一时期,由于泰山的镇鬼、升仙等等功能和流传已久的“石敢当”信仰习俗相通,在明朝中晚期“石敢当”与泰山逐步结合,而发展到现如今家喻户晓的“泰山石敢当”。同时,傅斯年图书馆里面的金元“泰山石敢当”拓片石刻很有可能是翻刻,不能藉此来判定“泰山石敢当”产生的时代在金元时期。
[1]刘锡成.石敢当——灵石崇拜的遗俗[J].东岳论丛,1993,(4).
[2]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3]管振邦,宙浩.颜注急就篇译释[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李绪民.“泰山石敢当——山石信仰”刍议[J].黑龙江史志,2010,(22).
[5]叶涛.泰山石敢当[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6]蒋铁生.泰山石敢当习俗的流变及时代意蕴[J].泰山学院学报,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