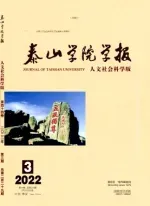“有毒话语”——文学警示录
方丽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47)
生态批评家和文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科技发展有可能给自然和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在英美文学界,从19世纪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1818)到21世纪初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与“秧鸡”》(2003),许许多多的作家创作了大量预测和想象未来生态灾难和人类毁灭的作品,这类作品我们也常常把他们称为“生态预警作品”或生态灾难(ecocatastrope)作品。这些作品将文学文本与人们的生存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他们不仅传达和构建了一种生态美学和价值观,同时也担负起了树立读者环保意识的使命。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其生态批评专著《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它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2001)中对生态预警作品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是生态批评在这一领域的新的尝试。本文将重点评析布伊尔这一领域所进行的开创性工作,以期对中国生态批评有所启迪。
一、“有毒话语”扫描
在布伊尔看来,有关环境污染的话题即“有毒话语”(toxic discourse)是文学的警示录,它表达了人们对环境恶化的焦虑。布伊尔认为,文学警示录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20世纪末以来,环境危机对人类的威胁越来越大,“有毒话语”也因此成为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1]。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污染开始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许多著名的环境公害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对有毒或中毒的关心可以追溯到古代,但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极大地得到了强化和广泛的关注。在美国,最大规模的有关环境污染事件应该说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拉夫运河事件”。
拉夫运河(Love Canal)是一个世纪前为修建水电站挖成的一条运河,20世纪40年代就已干涸而被废弃不用了。1942年,美国一家电化学公司购买了这条大约1000米长的废弃运河,当作垃圾仓库来倾倒工业废弃物。这家电化学公司在11年的时间里,向河道内倾倒的各种废弃物达800万吨,倾倒的致癌废弃物达4.3万吨。1953年,这条已被各种有毒废弃物填满的运河被公司填埋覆盖好后转赠给了当地的教育机构。此后,纽约市政府在这片土地上陆续开发了房地产,盖起了大量的住宅和一所学校。
厄运从此降临在居住在这些建筑于昔日运河之上的建筑物中的人们身上。从1977年开始,这里的居民不断发生各种怪病,孕妇流产,儿童夭折,婴儿畸形,癫痫、直肠出血等病症也频频发生。1987年,这里的地面开始渗出一种黑色液体,引起了人们的恐慌。经有关部门检验,这种黑色污液中含有氯仿(CHCl3)、三氯酚(C6H3Cl3O)、二溴甲烷(CH2Br2)等多种有毒物质,对人体健康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这件事激起了当地居民的愤慨,并且引发了美国从地方到全国的数千团体的抗议运动。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宣布封闭当地住宅,关闭学校,并将居民撤离。事出之后,当地居民纷纷起诉,但因当时尚无相应的法律规定,该公司又在多年前就已将运河转让,诉讼失败。直到20世纪80年代,环境对策补偿责任法在美国议院通过后,这一事件才被盖棺定论,以前的电化学公司和纽约政府被认定为加害方,共赔偿受害居民经济损失和健康损失费达30亿美元。
布伊尔指出,“拉夫运河事件”使得美国公众对污染的关心程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随后美国的反环境污染可以说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有关环境污染的话语也不断出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可以算作是生态正义行动与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结合的时期。[1]
布伊尔认为,有关污染的话题总是不那么好听、顺耳,“但那些不断出现的令人不安的污染事件总是会为这类话题补充新鲜的素材,激发它的动力”。谈论“有毒话语”必然会涉及环境公正的话题,谈到“穷人的环境保护主义”,这也许会加剧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尽管如此,“有毒话语”仍然是我们共同关心的主题。[1]
文学批评家菲利普·费希尔(Philip Fisher)认为,恐惧可能是“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将相互依存割断”。但是却能产生“一个更广泛的相互依存……那就是共同的恐惧”[2]。19世纪末的塞勒斯·爱迪生(Cyrus Edson)也有相似的观点:“疾病用一个不能打破的链条把人类都捆绑在一起;”“富人和穷人通过传染病这个链条被捆在一起。”[3]这些观点与洛夫乔伊的“生命链”、布鲁克纳的“生命之网”、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拉夫洛克的“盖亚假说”如出一辙。他们都认同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把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编织在一起的存在之网,我们只能与整个存在之网患难与共。
在21世纪之交,在布伊尔看来,“如果有可能出现有关环境的全球性话语的话,‘有毒话语’必定会成为这个话语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
二、“有毒话语”解剖
在美国,“有毒话语”始于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1962)。卡逊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生态文学作家,是生态文学史上里程碑一般的人物。
《寂静的春天》是她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寂静的春天》以大量的事实和科学依据揭示了滥用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人类健康的损害,激烈抨击了这种依靠科学技术来征服统治自然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寂静的春天》于1962年一面世立刻引起了全国性轰动和全民性大讨论。一方面是化工公司、食品公司、农业部、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等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与这些利益集团有利害关系的媒体和科研机构的强烈抗议和恶毒攻击,另一方面则是绝大多数科学家、广大民众、多数传媒的大力支持和热烈赞扬。
争论和冲突愈演愈烈,各种政治力量也参与进来,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立专门小组进行调查,国会举行听证会。这样一场上至总统下至百姓的大讨论,使得生态观念和环境意识深入人心,并对政府决策、国会立法和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股热潮很快又跨过大洋,在欧洲及世界其它地方迅速蔓延。两年间就有数十种语言的《寂静的春天》译本在世界各地热销、流传。继之而起的是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环境政策和修正发展战略,各类环保组织、生态学研究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卡逊,这个弱小的女人,在美国和整个世界掀起了一股永不消退的环境意识浪潮。她改变了历史,创造了奇迹。
布伊尔以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开始,对“有毒话语”进行了解剖。布伊尔总结了“有毒话语”的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对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时所产生的恐惧”[1]。卡逊“明天的寓言”向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美国中部一个曾经美丽如画,生气勃勃的小城镇突然莫明其妙地变成了一个怪病流行、生命凋零、死气沉沉的地方,纵然是到了春天,那里也没有声息,只有一片奇怪的寂静笼罩着田野、树林和沼泽地——那是一个被生命抛弃了的地方。在被唤醒的感知中,我们第一感觉就是恐惧。
“明天的寓言”正在变成今天的现实。继卡逊之后,20世纪70年代的“拉夫运河事件”,是后卡逊时代第一个被广泛曝光的污染事件,与此同时,也引发了类似事件的曝光。
利奥·马科斯(Leo Marx)在《花园里的机器》(1964)一书中指出,美国传统的主导思想是将美国看作一个大花园,这缓解了对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焦虑。美国的国家政策中就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幻想,认为自然之美是永不枯竭的。马科斯把这种主导思想称作是“天真的田园诗”(simple pastoral)。梭罗和梅尔维尔等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对这样的观念提出了批评,他们看出了技术的推崇者和田园风景特征的美国文化之间内在的矛盾,马科斯把那些觉醒的知识分子的观点称为“复杂的田园诗”(complex pastoral)。[4]
布伊尔认为,卡逊和后卡逊时代的知识分子受到马科斯的影响,他们想复苏伊甸园这一古老的神话。因此“有毒话语”的现代重述就是从“天真的田园诗”到“复杂的田园诗”的觉醒。这是“有毒话语”的第二个特征。[1]
从田园的幻觉中觉醒,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总体世界的景象:有毒的物体四处渗透,无处不在,我们没有避难所。在《寂静的春天》里,卡逊沉重地说到:“在世界历史上,我们每一个人第一次受制于有毒的化学物质,直到死亡。”毒物四处蔓延,田园梦想破灭。毒物话语也蔓延到大众文化,生态灾难小说在美国也出现了。菲利普·狄克(Philip Dick)的《机器人梦见电动羊吗?》,约翰·布鲁纳(John Brunner)的《绵羊仰望》,斯格特·桑德(Scott Sander)的《玻璃容器》等生态灾难小说大量涌现,这些生态小说表现了冷战时代对核武器的恐惧。
但是,布伊尔认为,在冷战或核时代,有关环境污染的持续性和复杂性等问题还没有理论能够从文化或文学上加以解释,这一时期有关全球“有毒话语”的理论还不具有这样的阐释能力。
布伊尔提到了美国第一位黑人市长理查德·哈切(Richard Hatcher)。哈切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公正意识,他成功地将城市黑人、居住在郊区的中产阶级以及白人蓝领阶层联合起来,共同促进环境的健康。布伊尔认为,哈切成功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将环境改革和社会公正联系起来,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企业和集团的贪婪。这就是‘有毒话语’的第三个要素:道德激情”[1]。
“有毒话语”并没有像其它话题——化学的、医药的、社会的、法律的一样受到同样的关注,在布伊尔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与实用性有关。有毒话语并不像社会、法律等话题那么实际,实用性决定公共讨论的话题。第二,环境问题通常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环境保护运动也是一种潜在的作用。在文学和修辞的研究中,研究环境问题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生态批评运动。尽管最近一些文学和文化研究著作将环境问题置于中心位置,但自然还是作为一种附带的现象来表现,如将自然作为地缘政治、资本主义、技术等的产物。[1]
三、毒性、风险和文学的想象
“有毒话语”呼吁对自然环境的想象应该将社会建构主义与环境修复观点融合起来,反对生态批评主张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模式,因此“有毒话语”认为整体主义是空想的。当然,“有毒话语”也承认,带有感情色彩和负有激情的呼吁对人类和地球的健康也有益处。“有毒话语”主张去除空想、浪漫,将“自然”作为一个实际的、可操作的范畴。
布伊尔发现,自然已失去在文化上的重要性。事实上,作为避难所的自然已不复存在,自然和人类应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这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置身于其中的自然不应该受到损害,当然这个自然是“第二自然”的结果或“现代的自然”。从另一方面来看,“自然的”作品和“环境的”作品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之间的区分变得更有弹性,因为“有毒话语”打破了这种区分。人们可以认为赖特(Richard Wright)和狄更斯这样的作家具有地方的“生态”意识,他们的这种生态意识和居住在乡村的同行左拉、哈代同样敏锐。
布伊尔以当代作家特里·威廉(Terry T.William)的《心灵的慰藉》(1991)为例,为我们展示“有毒话语”已经跨越了自然和人类的界限。布伊尔指出:“《心灵的慰藉》是有关环境污染带来的焦虑和恐惧的自然写作。在这个作品中,我们通常所界定的那些文类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1]威廉描述的两条主线:一条是荒野,一条是家族的疾病。这两条主线时而相交、时而分开,交织纠葛在一起。《心灵的慰藉》没有将大城市和边远地区分开,强调了大城市和边远地区的重叠,这不仅避免了传统自然文学的局限,而且还对传统的自然文学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认为城市和乡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依赖的。事实上,在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瓦尔登湖》中,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开始和结尾都坦白地承认作家是“文明生活的旅居者”。布伊尔认为,“恰恰就是从那种混杂的视角开始了《瓦尔登湖》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向”[1]。
在布伊尔看来,证据是“有毒话语”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尽管文本的主题就是对被污染的环境或因人受到环境的污染而产生的焦虑,但是通常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焦虑的来源,因此“‘有毒话语’只能是一种断言的或暗示的语篇”。它不能称作是科学的或法律上的证据,这使环境的受害人成为某种自我界定的受害者,在不能决定毒性的证据和对毒性的恐惧中挣扎。[1]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在知识层面的不确定就是某种确定”[1]。“有毒话语”是一种想象的行为,可以将对毒物的焦虑作为一种心理上的现实隐藏起来。既然没有能力了解,因此而欣然接受这一现实。由此,布伊尔指出,“有毒话语”只停留在对问题的批判层面,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方法,从而使“有毒话语”有可能变成自身的避难所。因此,“‘有毒话语’有可能被压制、不能实现、或与其它话语交织而偏离主题”[1]。这种表现就是布伊尔所说的“环境无意识”的负面呈现。
布伊尔以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长篇小说《白噪音》(1985)为例来说明“有毒话语”的特性。《白噪音》发表于1985年,获得了1986年美国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它生动地叙述和描写了一次毒气泄漏事件所导致的可怕灾难。主人公格兰德尼是一位大学教授,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任教。他结婚数次,现在与4个孩子一起生活,现任妻子芭比特在一所成人教育中心任业余教师。一场突如其来的毒气泄露事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小说的整个叙述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共分3部分40章:第一部分“电波与辐射”,描写了格兰德尼一家的日常活动。第二部分“空载毒物事件”,作者采用“生态灾难小说”的体裁模式,描写了发生在格兰德尼所在小镇上一起有毒化工废料泄露事件。一辆火车出轨,装载着剧毒化学物质被撞破,三万五千加仑的毒气泄漏,黑色的浓雾直冲天空,在空中随风飘移。当地的居民被迫疏散迁移。格兰德尼驱车带领一家人逃难,途中下车加油,被迫在毒雾中暴露了两分半钟,从此惶惶不可终日,煎熬于死亡的恐惧之中。第三部分是“达乐风波”,“达乐”是一种药品的名称,该部分叙述了毒气泄露之后教授家庭生活的变化以及最后导致的暴力悲剧。
《洛杉矶时报》曾评论该书说:“德里罗通过温情、机智和强有力的讽刺勾勒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这种不安我们正日益有所感觉。”[5]许多学者从后现代视角解读这部小说,认为它突出了美国后现代背景下人们的精神危机。小说将这次毒性事件作为背景,是后现代社会非真实感的隐喻,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苏珊·桑德格(Susan Sontag)对隐喻的说法就提出了质疑。桑德格认为将痛苦转换成隐喻是值得考究的:我的隐喻被忽略了、变得不真实了,因为这是其他人的痛苦[6]。
布伊尔对桑德格的评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布伊尔认为,在《白噪音》中,“事件”一直都用引号,主人公格兰德尼应对突发毒气泄漏事件的不得力,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联系。困惑地撤离、软弱无力、厌倦、对事件感到不真实,这些反应是大多数描写这类灾难的小说通常表现出来的特征。这些反应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事件”给人们带来的一系列难以应对的问题。并且,我们还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边,因此“有毒话语”在此常常被解读为某种“妄想狂”,是“一套陈词滥调”。[1]
布伊尔还认为,将毒气泄漏事件隐喻化并没有削弱事件本身的后果,而是一种表现技巧。一旦将“事件”隐喻化,毒气泄漏事件就不可能被完全地忽视,至少是一种(文学)记载的“事件”。“我们有足够地理由相信即使是‘死’喻(dead metaphors)也能够塑造或强化文化的价值”[1]。
布伊尔还从“环境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明隐喻的价值。毒气泄漏事件的隐喻化使“环境无意识”的某些部分浮出水面,得到显现。与将其压制、埋藏在意识的深处相比,隐喻化的表现方式也许使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一“事件”。[1]
布伊尔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污染的话题才开始浮出水面,对于普通的美国人说,他们才真正将其作为一个现实来看待。像拉夫运河事件的出现也没有多久的历史。在这之前,美国中产阶级还沉醉在生活的稳定和舒适的环境中,出现在报章杂志上有关污染的事件与他们的生活似乎总是有距离的。因此,隐喻可以作为一种策略,一种具有教育意义和富有启发性的间接的手段。
“有毒话语”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孤独的逃避者或消费者。我们是一个没有选择而只有与其他人合作的集体。不管你喜不喜欢,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相互依赖的。布伊尔总结道:
虽然毒性可以为社会、甚至地球提供一个文化的命题,但只有想象的行为——无论想象激发起的是有关再循环的,还是有关社会相互关系的——才会增强人们消灭它的希望。[1]
布伊尔对“有毒话语”的研究反映出美国生态批评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即从关注自然转向关注现实环境危机,从自然写作研究转向对“有毒话语”的研究,这反映了美国生态批评两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对于这一生态批评的新的领域,布伊尔对“有毒话语”的把握是比较全面的,对“有毒话语”解剖也抓住了一些标志性现象,力求发掘深层的规律,对于生态批评在“有毒话语”这一新的领域的尝试起到了提示、倡导和促进的作用。
在我国,“生态警示作品”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出现。徐刚的《伐木者,醒来!》(1988)是开山之作,《伐木者,醒来!》对中国环境发出的棒喝之声以及所起的警醒作用,可与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媲美。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涌现了大批的优秀的作品,郭耕、莽萍、苇岸、张炜、周晓枫等作家都写出了非常优秀的生态灾难作品。然而,与这些作品大量涌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态批评对这一领域却鲜有涉及,我国生态批评学者对这类作品的关注还不够,这是令人遗憾的,布伊尔对于“有毒话语”的研究对我们不无借鉴和启迪。
[1]Lawrence Buell,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Culture,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and Beyond,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Philip Fisher,"The Aesthetics of Fear",Raritan,18(Summer 1998).
[3]Cyrus Edson,"The Microbe as a Social Leveller",North American View,161(October 1895).
[4]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5]李淑言.《白噪音》中的生态意识[J].外国文学,1996,(6).
[6]Susan Sontag,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New York:Doubleday,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