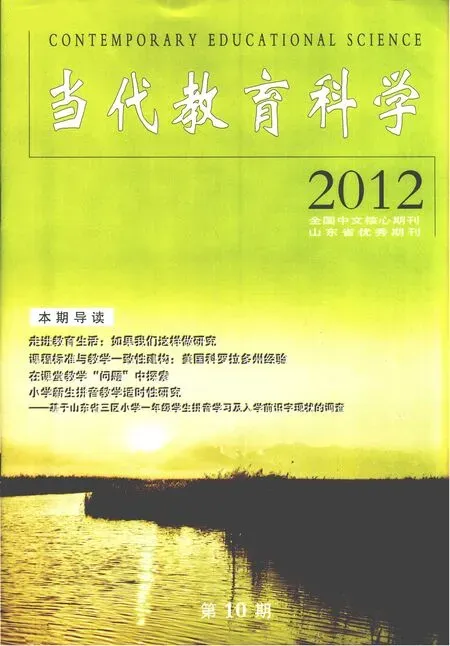教育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化:从主义取向到精神取向
● 杨建朝
教育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化:从主义取向到精神取向
● 杨建朝
教育研究需要科学化,但应该否弃单一的科学主义的研究取向,其尽管一定程度促进了教育学的科学化、有不可替代的合理性,但由于缺乏对教育本真的深刻认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需要进行多种研究思维的深度整合以形成有丰富意蕴的科学精神取向。即在对教育的本真有了充分而理性的认识后,一切以人之整体生命自由全面发展为思考和开展教育研究的立场和出发点,努力建构美好教育生态的一种取向,从而促进当代中国教育研究的和谐开展。
教育研究;科学主义;科学精神;思维取向
面对教育研究存在的方法混乱、无序、解释力差,研究成果差强人意、只能自娱自乐等现状,教育学科学化是教育学人的内心期盼,许多学者从不同立场对其作了深入探讨,例如扈中平的《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科学人文主义的方法论》、项贤明的《教育学的学科反思与重建》、冉亚辉的《哲学化、科学化与经验:教育学的多元范式发展》、马凤岐的《教育实践的特性与教育学的科学化》等对教育研究需要怎样的科学化以及如何科学化展开分析,这些讨论林林总总、意见不一并不乏争议,本文从教育研究思维取向的角度提出,教育研究需要的科学化应该从秉承自然科学范式的科学主义的研究取向转换到以成“人”为本的科学精神的研究取向。
一、科学主义式的教育研究思维取向的现实表征
科学主义(scientism)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众所周知,牛顿之前的自然科学是包含在哲学范围内的,其研究也主要不是依赖实验、实证、归纳、量化。17世纪随着文艺复兴的广泛深入,人从对上帝的崇拜和依附中解放出来,开始探索人本身、人面对的大自然和社会,整个学问领域开始形成一种要求研究者采纳的特定的要求和规范,这被库恩称作范式,新的范式随着自然科学的逐步成功并占据主流地位,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熟知的科学主义,它以自然科学技术为价值标榜,确信依靠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规范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要求研究的普适、可重复、探索本质、揭示规律等、只要是科学的研究都必须按照这种固定的思维进行开展,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虚妄的。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缺乏边界意识,把这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简单地推论到哲学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领域中。其始作俑者是德国社会学家孔德,其坚持实证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科学一样是有本质有规律的,社会本身是个巨大的有机体,其规律是自然规律、生物进化规律的延续,遵循严格的因果律,应该采用观察、实验、比较、量化、归纳等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社会研究。其后的社会学家密尔、斯宾塞、涂尔干、马克思韦伯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科学主义,并将其应用到当时已经开展的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由于受这种科学主义的深刻影响,感叹自然科学在探究自然规律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和在部分社会科学领域应用的成功以及对传统的思辨与抽象式的教育研究不满,20世纪以来,许多教育研究者都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标准,追求所谓普遍、客观的教育规律,采用实验、测量等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从而导致了一种科学主义式的研究思维取向,这种科学主义“是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应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主张……相信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有效地用来追求知识的信念。”[1]它以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为榜样,以精确、定量、客观为目标,而不顾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不加任何限定和区别地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全盘引入教育研究,孜孜以求教育学的科学化。试图破解对教育学作为一个科学的诘难,赫尔巴特作为把教育学科学化的鼻祖有目共睹,德国以梅伊曼、拉伊为首的实验教育学派更是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此后反复要求教育学少一些理论思辨,多一些实证和量化的呼声越来越强,总的来说,这都是科学主义的情结在作祟。这种科学主义式的研究思维在教育研究中具体表现为:
第一,坚持追求外显化、可表征的教育本质和规律,要求教育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可移植性,排斥特殊性、偶然性等。这样的取向本身并非没有合理性,但也因为对教育的认识理解偏误而存在明显的水土不服,例如,如果把教育分成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并且分别研究其规律;在教学活动中,把整体的知识分隔成一个个条块并总结出各种“小规律”等,则往往得出正确的废话,或好听无法用的矫揉造作之物,这是因为这样的研究忽略了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建构性和不可拆分性。
第二,存在把教育物化的现象,忘记了人之生命的复杂、独特,把学生当成可以由规律支配的机器。“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教育对象视作物,就满足了科学以物为对象(即使对人进行研究也是对人的物质自然方面进行研究)和可以以理想化的方法加以处理的要求。”[2]这样,学生就可以以工业化生产的模式进行大批量生产,无须考虑其个性、复杂性。把他们当成统一的原材料,从而在教育的大工厂里面制成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另外,科学主义的研究思维取向主要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推崇教育实验等,认为只有通过实证性的研究才能使教育学走上科学化的道路。最后,坚持科学主义研究思维的学者大多坚持价值中立说,认为教育规律研究的结果对任何学者都是普适的,不存在所谓地域和时代的差别,否则研究就因为不可套用和移植而认为无甚“价值”。
科学主义式的研究思维之所以可以在教育研究中形成风气,主要在于教育现象确实具有某些客观性、确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自然科学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巨大的优越性,可以满足人们对规律的追求,正确指导教育实践,提升教育学的科学化水平,另外也在于这样的研究思维确实也对教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和教育经济学等学科的建立及其重大功用。在这种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到了20世纪中后期,可以认定以科学为核心追求的实证主义的教育研究大获全胜。”[3]“尽管实证主义在20世纪中叶以后遭遇了猛烈的批判,如存在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都欲彻底摧毁实证主义,但实证主义思维方式至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教育学领域。”[4]
从客观角度分析,教育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必然有许多与自然科学研究相通的地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许多研究方法。而且,应该说方法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可以互相借鉴,不可能存在完全只对某种学科适用的方法。总的来看,教育研究在这种追求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中,确实获得了巨大发展,促进了许多教育问题的解决和教育理论的建构。因而当前以教育学是关涉意义、价值、精神等的人文学科为理由而全盘否定科学主义的思维取向在笔者看来是矫枉过正。
但是,这种过度追求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取向,在实践中确实会产生一些偏差,“这种科学主义的研究思维使教育研究在目的上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规范去追求教育内部的必然因果关系、追求客观性、确定性,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对自然科学的方法的崇拜和迷信,由此产生了科学教育学这种客观的追求。”[5]这种模式的广泛应用,理所当然在现实中就有许多的表征:“重微观轻宏观,重应用轻积累,重技术轻原理,重定量轻定性,重现实轻历史,重事实轻价值。”[6]而恰恰正是这样的科学主义式的教育研究思维取向在我们的教育研究领域非常普遍,影响深远。它“造成教育教化功能的削弱和人文内涵的流失,从而影响教育宗旨和教育功能的全面实现。”[7]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开始认真反思科学主义取向的教育研究思维的弊端,在对教育的本真有了明确认识后尝试做出改变。
二、科学主义式的教育研究思维取向的局限
这里的问题关键是,教育研究因为其研究问题的特殊性而不可能摆脱研究者的哲学观、人性观、价值观的影响而保持完全的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对自然科学而言,因为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是外在于人的,研究者的价值中立比较容易做到,实验实证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一旦涉及到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这种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因而体现了科学主义思维取向的局限。这些局限具体表现在:
首先,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而不是人类自身的问题,人类自身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包括教育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完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自然科学成就的滥用,已经引起了许多失误,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例如人类集体智慧的成果——核武器的发明对人类安全产生的威胁、医学上抗生素的滥用造成病毒的变异加速等。在教育领域,由于这种唯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取向的深刻影响,要求教育教学的完全客观化、精细化,指望教师在掌握了所谓教育规律后能够实现教学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但这个愿望离实现还有很大距离,反而容易出现学生厌学、逃离学校、高分低能等现象。
其次,自然科学在研究时要求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要求保持价值无涉,完全客观地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说明并建构普遍适用的自然规律,这在教育中显然难以获得广泛应用,因为“没有一个纯粹的抽象世界,所谓的抽象的客观世界,只能是人类智力活动参与后的一种建设性结果。”[8]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社会中的个人,有主观能动性,都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动态地发生着各种变化,每次教育教学活动都因为各种原因有着明显特性,是教师和学生对现有知识主动进行智力活动的结果。因此,需要思考教育活动有没有普遍适用、价值无涉的规律,即使有,这种规律应该以什么方式表征,如何与教育的特性相吻合。
最后,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过度追求客观标准规律的结果,使得我们对教育中的知识进行过度拆分、细化,存在把整体的知识“剁”成一个个知识碎块,然后一点点地喂给学生的现象。例如,把所谓认字、组词、造句的规律都以一个个清晰的条文呈现给学生,把五位数比四位数大都形成条文化的规律等,认为只有这样,学生才可能学到人类的科学文化知识,从而忽视了学生学习的整体性、感悟性。
面对科学主义思维在教育研究中的过度膨胀,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质疑,甚至要求坚决抵制教育研究的科学主义取向。这在笔者看来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错不在科学主义,错在秉承这种主义的人试图要求“一统天下”,批判并吞没其他也具有合理性的研究取向。它们是对其他学科理论做简单移植和附会的依附式的教育研究思维取向、对领导人的言论和教育政策求解合理性的指令式、政策化的研究思维取向、把教育当作个人诗意浪漫气质任情发挥的人文主义式的研究思维取向、一切为了更多名利地位打拼的功利至上式的研究思维取向、否定一切即有成果、把什么都作为尚未完成的激进建构主义式的研究思维取向、把马克思、毛泽东等权威人物的思想言论作为万古不变的圣经的教条主义式的研究思维取向、非此即彼、你错我对的二元对立思维取向及其他难以明确归纳带有混合性质的研究思维取向等。它们本身都各具合理性、在教育研究中这些思维取向都有一定程度或隐或现的表现,但由于常常缺乏深刻的视域融合和深度整合,更因为研究者本人往往缺乏“我的研究取向有偏颇、尚不完善”的自知之明,导致不同研究思维取向常常生发出不必要的纠葛,甚至互相嘲讽、谩骂、讨伐。对于教育研究来说,尽管科学主义的研究思维取向有其不可替代性,但过犹不及,越界到其他领域就会出现不应有的偏差,人文思辨式及其它的教育研究思维现在还很普遍,并具有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功用和价值,但也不能被尊奉为唯一具有正当性合法性。
三、教育研究科学精神取向的意蕴
面对以科学主义思维为代表的当前各种思维取向在教育研究领域中的种种滥觞,我们需要对引导教育研究的思维取向进行深度整合,即抛弃科学主义,倡导科学精神,这就需要给出本文界定的科学精神取向的意蕴。首先,科学精神内涵是什么呢?一般认为,它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追求事物的本然,即求真,“真”主要体现为人类面对客观世界时如何正确把握其中的本然,从而不被无知带来的盲目性奴役。科学作为一种精神张扬的是由科学中提炼、升华出来的科学理性成份,对此笔者已经在《教育研究与科学精神》[9]的论文中有所阐述。这里所谓教育研究科学化的科学精神取向,是指在对教育的本真有了充分而理性的认识后,一切以人之整体生命发展为思考和探索教育问题的立场和出发点,以复杂性思维、生成性思维等为手段,以研究取向的多元化为旨归,努力建构美好教育生态、促进教育成“人”的一种取向。
这里关于人的认识就是关键,但显然这不是一个容易解答的问题,人既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又自主构建了独特的人文世界;人是动物性的存在,却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类本性;任何人都有关于“人”的知识,但人是多元复杂的存在,蕴含着难以完全解释清楚的可能性,“任何个人,即使是最闭锁在他的最平庸的生活中的,在他本身也构成一个宇宙。他在他身上蕴含着他的内在的多重性。”[10]因而,既然研究都是人做出的,任何一种研究都与人的某个方面有关,而任何一种研究由于人的复杂性而只能是“片面”的但又内含真理性。正如人人皆知的盲人摸象故事,其实每个研究者又何尝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出发而得出了关于“人”的片面真理。正是基于此,教育研究的科学精神取向并非要排斥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而是承认其正当性,但又指出其僭越后带来的科学化危机,认为即可以在教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领域采用实证研究范式,但关于教育的价值、意义、目的等领域中则必须清楚科学主义范式的局限,而改用人文学科的探究范式,舍弃事实真理而采用价值真理。其实这就是要求吸收现有各种研究思维取向的合理性,又能够辨证地指出其不足之处,防止“怎么都行”的不顾研究责任的放任的取向,在此基础上对它们进行合理的转换和整合,从而促进人的整体生命自由和谐发展,使人科学地同时又诗意地栖居在美好的教育世界中,促成和谐美好教育生态的建构。
所谓教育生态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一种学生发展的条件系统或环境系统”[11]。建构美好教育生态、促进教育成“人”的内在逻辑需要从两方面探悉。首先,从教育的内部角度讲,所有教育研究活动的目的,都是建构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或提升现有的教育实践水平,都是为了使师生从盲目任性、随心所欲中解脱出来,在教育使人成为自由、完整的“人”的道路上迈进,过上美好和谐的教育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由于即遵循了教育的特殊“规律”,又张扬了师生理性的自由意志,所以学生想学乐学,教师善教乐教,教和学都获得了完美的交融、成为一个整体中不可分隔的部分。这样,对教师和学生来说,由于把握了教育的本真精神,教育的生活就会成为完整生活历程中愉悦的构成部分,也即获得了美好的教育生态。
其次,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看,在美好的教育生态中,教育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关系因为研究的深入也获得了完美的结合,教育与社会不再对立,教育作为一个耗散结构,不断从社会中获得各种信息和资源,完善并壮大自身,同时它又为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由此实现和谐共生、相得益彰的局面。(当然,这样的理想跟现实对照还有相当的距离,社会不正当干预教育的发展,教育培养的人只满足于机械适应社会需求,而无益于社会革新的现象都存在。)在教育的内部与外部都处于这种完美生态的时候,在应然意义上的憧憬和实然意义上的问题之间寻找到联结的途径后,笔者认为梦寐以求的教育成“人”真谛就有可能得以实现。
但是,我们描绘的这副美好画卷并非容易实现,甚至可能永远是可望不可即的水中月、镜中花。但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却可以步步接近,那么实现理想的路径何在呢?这就需要不断对教育的本真进行探究,以提高对教育的认识水平和层次,整合业已存在的多元化教育研究思维取向,不断向着建构美好教育生态的理想而努力。
明了这种科学精神取向的意蕴后,我们还需要思考,理想总是从现实起步的,建立在空中的理想最终都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科学精神取向的实现也要从当前现实起步,需要摆脱互相对立和排斥的偏颇做法、一切以是否有益于美好教育生态的建构为标准,以是否能促进学生整体生命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成“人”为准绳。
[1]冯契.哲学大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1506.
[2][8]郭思乐.经典科学对教育的影响及其与教育生命机制的冲突[J].教育研究.2003,(2).
[3]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92.
[4l郝德永.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332.
[5]郭元祥.关于教育学研究的科学性的若干问题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1).
[6]张斌贤.试析当前教育研究中的“唯科学主义”[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1).
[7]杨东平、周谷平.我国当代教育中的科学主义取向[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7,(1).
[9]杨建朝.科学精神与教育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
[10](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3.
[11]郭思乐.素质教育的生命发展意义[J].教育研究.2002,(3).
杨建朝/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09级博士生,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
(责任编辑:曾庆伟)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